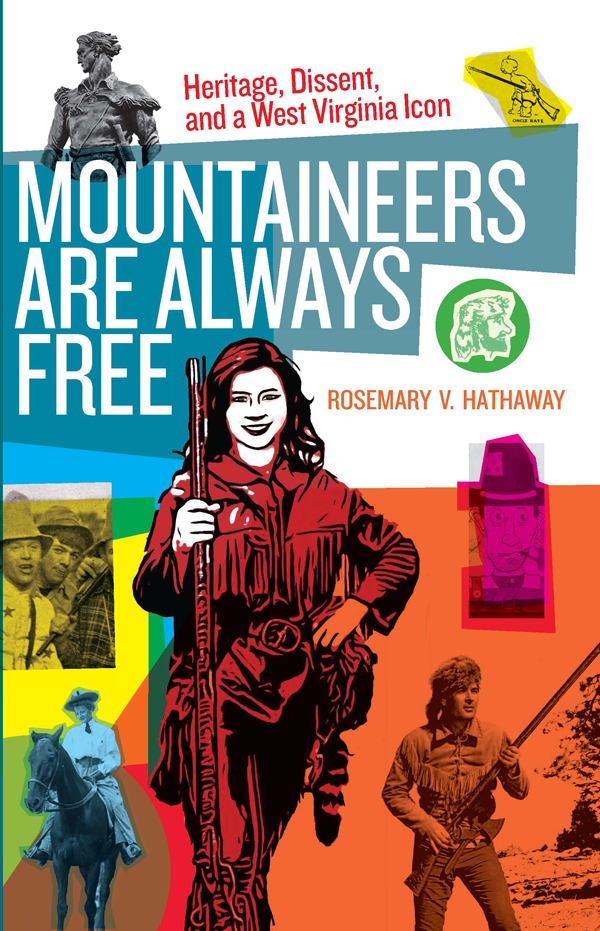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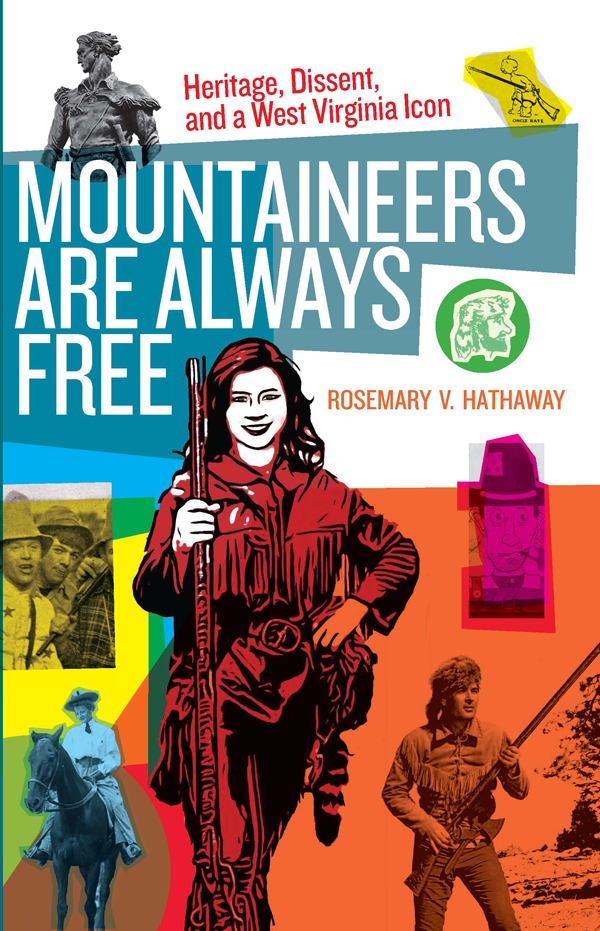
传统、异议与西弗吉尼亚的象征

罗斯玛丽·V·哈撒韦

西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摩根敦
版权所有 © 2020 西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保留所有权利
第一版于2020年由西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印刷
ISBN
精装 978-1-949199-30-7
平装 978-1-949199-31-4
电子书 978-1-949199-32-1
国会图书馆出版物编目数据
名称:哈撒韦,罗斯玛丽·V.,作者。 | 西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题名:山地人永远自由:传统、异议与西弗吉尼亚的象征 / 罗斯玛丽·V·哈撒韦。
其他题名:传统、异议与西弗吉尼亚的象征
说明:第一版。 | 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 | 包含参考书目和索引。
标识符:LCCN 2019044561 | ISBN 9781949199307(精装)| ISBN 9781949199314(平装)| ISBN 9781949199321(电子书)
主题:LCSH:西弗吉尼亚大学——历史。 | 学校吉祥物。 | 西弗吉尼亚——历史——20世纪。 |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
分类:LCC GV958.W4 H37 2020 | DDC 796.332/630975452—dc23
LC记录可查阅:https://lccn.loc.gov/2019044561
图书和封面设计:Than Saffel / WVU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山地人们,
大卫·巴尔·哈撒韦和乔伊斯·图斯曼·哈撒韦。
这本书既属于你们,也属于我。
[致谢]
[引言]
[1. 山地人的起源]
[2. 从软呢帽到浣熊皮帽:乡巴佬山地人对抗拓荒者]
[3. 步枪与胡须:1960年代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
[4. 监管学生群体:“山中女神”与(性感的)持枪女孩]
[5. 包容、排斥与21世纪的山地人]
[注释]
[参考书目]
[插图来源]
[索引]
这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许多人的合作。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David和Joyce (Toothman) Hathaway,他们都是自豪的西弗吉尼亚州本地人。他们对这个州和家族故事的热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在我最疯狂的梦想中,我从未想过那些故事会成为我自己人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非常感激它们确实成为了。很少有学者能如此完美地将个人生活和职业兴趣结合在一起。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献给他们。我只希望他们还在,能看到这个项目的完成。
我还要感谢Trinity Hall的前住户们,感谢他们讲述关于摩根敦和大学生活的故事;真的,这些我在整个童年时期听到的故事,塑造了我对西弗吉尼亚大学(WVU)的所有认知,也是2007年把我带到这里教书的部分原因。
当我开始思考如何把最初为《西弗吉尼亚历史》撰写的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的项目时,我意识到要真正理解山地人(Mountaineer),我需要和最了解成为山地人意味着什么的人交谈:那些担任过WVU官方山地人的男女。与他们联系离不开我称之为”山地人管家”的超级女性Sonja Wilson的慷慨帮助,她在2019年3月退休前担任山地人顾问和山地人周的组织者多年(即使在退休后,她仍继续她的顾问工作)。Sonja帮助我联系到前山地人们,并随时解答我(众多的)问题。谢谢你,Sonja。
我采访的所有前山地人的慷慨大度让我感动和谦卑。他们愿意与我交谈,并且带着热情、幽默和坦诚这样做。他们的热情推动了我的进展,并教会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山地人需要什么:无限的精力、同情心、对界限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这个州坚定不移的热爱。非常感谢Dave Ellis、Lou Garvin、Doug Townshend、Bob Lowe、Ken Fonville、Mark Boggs、Matt Zervos、Natalie Tennant、Brady Campbell、Michael Squires、Rebecca Durst和Brock Burwell。我希望将来能采访所有仍健在的前山地人,并将这些采访存档在WVU图书馆的西弗吉尼亚和地区历史中心,供未来的研究者使用。
还有许多其他人在这一路上帮助了我:非常感谢WVU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Ronald Lewis,他引导我找到西弗吉尼亚和地区历史中心的正确材料。说到西弗吉尼亚和地区历史中心,我深深感激那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总是让我感到受欢迎,定期向我提供新的信息,并通过他们对档案研究的热爱,帮助我完善了自己的研究。WVU历史系的Ken Fones-Wolf在让这个项目聚焦并启动方面非常重要,他邀请我向《西弗吉尼亚历史》提交一篇基于我初步研究的文章。当我(经常)发现自己在历史的水域中力不从心时,他总是准备好提供很好的建议。Kelly Diamond帮助我整理了参考书目的所有来源,再次证明了图书馆员确实是信息超级英雄。我还要感谢西弗吉尼亚人文委员会,它以多种方式支持了这个项目:首先通过夏季奖学金帮助我开始实地调查工作,然后通过其小型讲座系列让我有机会从观众那里获得反馈。
我还要感谢Randy McNutt,《辛辛那提的King唱片公司》和《辛辛那提之声》(均由Arcadia Publishing出版)的作者,他提供了第2章中出现的King唱片公司广告,还要感谢Affrilachian诗人和活动家Crystal Good以及查尔斯顿Grace Bible Church的Matthew Watts牧师,他们提供了第5章中出现的《黑色三角》壁画图像。与Watts牧师的对话提醒我,关于WVU非裔美国学生的历史,特别是1960年代的历史,还有更多内容值得书写。多亏了他,我想我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下一个项目。
我要感谢在西弗吉尼亚州和地区历史中心进行档案研究时遇到的几位人士。首先是Scott L. Bills,他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专业学生和学生活动家,后来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德克萨斯州斯蒂芬·F·奥斯汀州立大学的摄政历史学教授。他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的著作《肯特州立/五四事件:十年回响》在出版二十多年后,仍然是关于那个可怕日子的最佳历史著作之一。我对Bills保存了他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期间的每一张传单、小册子和通信的先见之明感到惊讶,但我非常感激他这样做。当我发现他的收藏品时,我希望能和他交谈——但遗憾的是,我得知他在2001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这真是一个打击。尽管如此,他作为学生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第3章的支柱。
我也感谢Patrick Ward Gainer,西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传奇的民俗学家,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他在该大学(以及格伦维尔州立学院)教了数十年的数千名学生。他为我们后来的西弗吉尼亚大学民俗学家留下了很大的鞋子要填。在西弗吉尼亚州和地区历史中心研究他的文件时,我发现了一份几乎完整的手稿,标题为”山地人”(见第2章),这是Gainer或他的一个学生在1970年代初写的。该手稿的序言清楚地表明,作者正在做我四十年后着手做的同样工作:试图梳理出山地人(hillbilly)和拓荒者(frontiersman)交织在一起的形象。显然,这对西弗吉尼亚大学民俗学家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我希望我对我尊敬的前辈做了公正的评价。
我的许多当代民俗学同事在这个项目的每个阶段都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和支持。当这一切看起来微不足道和晦涩难懂时,他们对我所做工作的坚定信念让我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刻。Sheila Bock Alarid、Emily Hilliard、Debra Lattanzi Shutika和Martha Sims:你们是我的民间英雄,你们的指纹遍布这个文本。
最后,感谢Tom Bredehoft,他让写书看起来很容易。感谢你对我写书能力的坚定信心。
我开始这本书关于西弗吉尼亚山地人(Mountaineer)时,我承认我是一个俄亥俄人(Buckeye)。我不仅在俄亥俄州出生和长大,而且我也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友。但作为父母都毕业于西弗吉尼亚大学并在西弗吉尼亚州长大的女儿——我的父亲David Barr Hathaway在格兰茨维尔(卡尔霍恩县),我的母亲Joyce Toothman Hathaway在雅典(默瑟县)——我对山地人也不陌生,无论是作为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吉祥物,还是更广泛地作为西弗吉尼亚人的绰号。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长大时,我的父母听到民间谚语说,西弗吉尼亚州的三个R是”阅读、写作和33号公路”(在其他地方被确定为23号公路,或”通往哥伦布的道路”,如果那是离开该州更近的路径)。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是1950年代离开该州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西弗吉尼亚人外迁的一部分。但像许多西弗吉尼亚侨民一样,我的父母从未失去对家乡的热爱,并自豪地展示他们的山地人身份:特别是我的父亲,在主要节日,包括6月20日西弗吉尼亚日,在美国和俄亥俄州国旗旁边悬挂西弗吉尼亚州旗,深感颠覆性的乐趣。相信我,在哥伦布郊区,西弗吉尼亚州旗引起了一些好奇的目光和问题,这让我父亲很高兴。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他们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不是在摩根敦出生的——于2007年被西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聘用,并从我当时的科罗拉多州家搬回到一组更温和、更绿色的山脉时。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我的家人经常回到格兰茨维尔和雅典探亲,但我们从未访问过摩根敦。然而,在我住在这里的最初几个月,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不断遇到通过家庭故事熟悉的地方:Spruce街和Willey街拐角处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所在地是我父亲的寄宿房屋三一堂(Trinity Hall)的前址;Stansbury Hall,当时英语系所在的地方,是以前的体育馆,他在那里看到Hot Rod Hundley用他的篮球技巧让观众惊叹。Woman’s Hall,我母亲在两人结婚前住的地方,俯瞰着校园,我父亲传给我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物品:他从Woman’s Hall门厅”解放”的电话,那是在一次约会前妈妈让他在那里等得太久时。每天在我步行去校园的路上,我都会踩到或跨过大都会剧院前Don Knotts的星星。Knotts在我父亲的同一时期是学生,有时在我父亲在城里与舞蹈乐队表演时担任中场休息表演。这很不可思议,就像回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我被困扰着,以所有最好的方式。
当我在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VU)任教时,我开始理解并对山地人(Mountaineer)的重要意义感到好奇。我以为我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经历中了解大学吉祥物;作为一名研究生助教,我甚至教过一个担任布鲁图斯七叶树(Brutus Buckeye)吉祥物的学生。但这些都没有让我做好准备去理解西弗吉尼亚人与山地人之间联系的深度和复杂性。在第一学期期间,我清楚地认识到,山地人远不止是一个吉祥物:西弗吉尼亚人对山地人的认同,远远超出了体育迷的范畴。事实上,正如我采访过的多位曾担任WVU山地人的人所强调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认为山地人是一个吉祥物:吉祥物只是穿着服装、戴着卡通化超大泡沫头套的匿名人士。他们告诉我,山地人是整个州的象征和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用提示就提出了这一区别,并且以极大的自豪感谈论他们作为代表的服务。
当然,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运动队并不是唯一自称为山地人的大学体育项目:这个绰号也被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伯里亚学院(肯塔基州)、圣玛丽山大学(马里兰州)、施赖纳大学(德克萨斯州)、西科罗拉多大学、东俄勒冈大学、东俄克拉荷马州立学院和南佛蒙特学院的运动员、学生和校友所共享。在所有这些队伍中,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吉祥物约瑟夫(Yosef),在象征意义上最接近WVU的山地人。根据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网站的介绍,“‘Yosef’在山区方言中是’yourself’(你自己)的意思,其理念是如果你是阿巴拉契亚的校友、粉丝或朋友,心中充满黑色和金色,那么你就是Yosef。” WVU山地人和Yosef的历史非常相似:Yosef诞生于1940年代后期,被构思为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1948年年鉴中的一个乡巴佬(hillbilly)漫画形象。接下来的一年,即1949年,约翰·盖弗里奇(John Geffrich),“一位48岁的二战老兵”,成为非官方的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山地人吉祥物。与当时的WVU山地人一样,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山地人被”男本科生描绘成一个蓄胡子的男人,穿着工装裤,叼着烟斗,戴着草帽”,并携带一支火枪。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这种描绘与当时WVU山地人的图像非常相似,反映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精致的阿巴拉契亚身份认同感。
但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山地人和WVU山地人在1980年代分道扬镳,当时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通过卡通式的头部和身体使Yosef的外观现代化”。WVU保持了由一名可识别的学生扮演山地人的传统,这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或缺乏决定)。由真人担任山地人是一个实体提醒,表明这个形象象征着西弗吉尼亚人在历史上和现在的独立性和个性。然而,在1980年代后期,WVU发现这一传统也存在问题,当时娜塔莉·坦南特(Natalie Tennant)竞争并被任命为第一位担任山地人的女性。第四章表明,虽然WVU山地人可能代表着自由,但一些学生和粉丝认为只有男性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角色。事实上,正是对丽贝卡·德斯特(Rebecca Durst)在2009年被选为第二位女性山地人的类似抵制,成为点燃这个图书项目的火花。当一些学生——包括大量女学生——抱怨女性不能成为山地人时,我开始看到山地人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它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保持持续的平衡。
因此,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本书是对成为山地人意味着什么的迷恋的结果,这是自2007年我来到摩根敦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发现的是,尽管山地人的形象随时间而变化,但关于山地人代表谁和代表什么的观念,自从这个术语在19世纪初首次作为弗吉尼亚西部居民的同义词出现以来,一直非常一致和持久。山地人是一系列无形价值观和理想的镜子:它代表对自己历史和传统的自豪。它体现了州座右铭Montani semper liberi(山地人永远自由)中反映的叛逆、独立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既是贫穷”白人垃圾”乡巴佬刻板印象的化身,也是对这种刻板印象的解药。它一直是一个避雷针,吸引和吸收关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更广泛文化关切。它一直是学生释放压抑的工具,也是大学行政部门用来约束学生不当行为的工具。个人使用山地人形象来展现他们认为作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州公民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居民意味着什么。这些展现方式差异巨大,有时甚至直接相互冲突,并且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然而,尽管具有灵活性,山地人身份仍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使其能够在两百多年来继续反映西弗吉尼亚人身份的关键部分。山地人身份中有什么独特且长久吸引人的特质?
为了理解当今的Mountaineer(山地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形象的来源。正如第1章中将详细讨论的那样,Mountaineer源于两个由来已久的美国标志性形象:hillbilly(乡巴佬)和frontiersman(拓荒者)。这两个形象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远早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建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早于美国的建立。我认为,分别发展的拓荒者和乡巴佬的人设在Mountaineer这个形象中融合了。虽然这两个形象有一些共同特质——强烈的独立性、直言不讳——但它们在很多重要方面也有所不同。拓荒者代表着荒野中的天生绅士,虽然不通世故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仍然聪明、善于表达且坦率。拓荒者所见即所得;他是典型的朴实无华之人,带有大量的粗犷个人主义和勇气。另一方面,乡巴佬则是一个几乎未开化的惹事者,先行动后思考。他的乐趣来自肉体:狂欢作乐、饮酒、斗殴。即使他意识到现状的存在,乡巴佬也不理解为什么这很重要,甚至可能主动违抗它。然而,他敏锐地意识到,外人常常将他视为傻瓜,事实上他有时会故意扮演傻瓜,以欺骗外人并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似乎不可能共存于Mountaineer这个单一形象中,但它们确实做到了。通过结合看似对立的拓荒者和乡巴佬形象,Mountaineer成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单独的乡巴佬或拓荒者的标志性形象:他成为了一个trickster(骗子/诡计者)。Lewis Hyde将trickster定义为”边界跨越者”,存在于”对与错、神圣与世俗、洁净与肮脏、男性与女性、年轻与年老、生与死”之间的边界。3 Trickster在无视传统的意义上是无道德的:他随心所欲地做事和说话,如果需要欺骗和诡计来实现目标,他会毫不羞愧地进行欺骗和诡计。正是这种无耻的特质使trickster如此吸引人;但正如Hyde(和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trickster不是反社会者或混乱的代理人。相反,通过其”与其他力量、人民、制度和传统的关系”,trickster的功能是”揭示和破坏文化所基于的那些东西”。4 简而言之,每个文化群体都需要一个trickster形象来守卫群体价值观的边界,既监督又挑战群体行为的界限。
Trickster形象几乎存在于每种文化中,5 关于他们的故事是几乎每个文化群体叙事民间传说的一部分:熟悉的例子有Brer Rabbit(兔子大哥)、Coyote(郊狼)、Anansi(蜘蛛)以及——在阿巴拉契亚传统中——Jack故事中的Jack。在这些故事中,trickster通过欺骗、聪明才智和机智胜过他人——尤其是那些试图伤害他们的人。我们将看到Mountaineer在19世纪关于荒野居民智胜花花公子的故事中如何扮演同样的角色。但trickster也可以是文化英雄,一个体现特定群体理想的形象——当然Mountaineer就是一位文化英雄。Mountaineer代表了西弗吉尼亚神话的核心:他是最早冒险进入该地区并定居的先驱;他是有原则的(尽管贫穷)公民,其对奴隶制的抵抗导致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建立;他是坚忍、自给自足且天生好客的绅士,按照自己的标准评判人和事,并据此行事,即使他的行为不合常规。在所有这些品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Mountaineer的美德如何跨越文明与秩序之间的边界:他不怕离开文明,直面自然世界的模糊性和危险,他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即使这意味着拒绝现状。Mountaineer值得称赞的品质——独立性和坦率——与他潜在的破坏性品质——愿意拒绝和抵抗社会规范——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
一个既是文化英雄又是trickster的单一形象的想法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且矛盾的组合。事实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就这种由单一角色同时体现两种角色的倾向进行了长期辩论,而人们原本期望这些角色由故事中独立且对立的角色来承担。6 Trickster通常是一个喜剧形象,如傻瓜或小丑,而文化英雄则更多是悲剧形象。然而,正如人类学家Franz Boas所指出的,存在”一种普遍倾向,即将最恶劣的粗俗滑稽或道德失范归于理想的文化英雄”。7 Mountaineer的情况正是如此:根据不同的语境,他既可以是坚定的拓荒者,也可以是粗俗的乡巴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角色都内置于WVU Mountaineer的职责中,要求他或她既要成为大学举止良好、善于表达的公关代表,又要成为有效的煽动者,能够通过比赛日的滑稽表演激发球迷的热情。
民俗学家芭芭拉·巴布科克-亚伯拉罕斯通过回顾捣蛋鬼(trickster)“体现了我们存在的基本矛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自由与约束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将文化英雄和捣蛋鬼结合在一个形象中的问题。8 海德也观察到,捣蛋鬼生活在文明的、被认可的行为与不当行为之间的边界上,有时通过参与测试边界限度的活动来模糊、挑战和移动这个边界。捣蛋鬼的测试功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仅因为这是捣蛋鬼的本性:这种边界测试对于那些其惯例受到捣蛋鬼挑战的群体和机构本身也至关重要。这些群体和机构明白”它们的活力取决于这些边界被定期打破”。9 捣蛋鬼的挑战使群体或机构那些未明说的、看不见的价值观变得可见。这种可见性反过来让群体或机构有机会重新审视其核心价值观,并在必要时重申和修改这些价值观。就像肌肉的小撕裂和损伤能让它变得更强壮一样,捣蛋鬼对群体价值观的挑战也能让这些价值观得到转化和加强。
文化群体和机构需要偶尔打破其边界,这对理解山地人(Mountaineer)的角色,特别是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角色至关重要。如上所述,西弗吉尼亚大学官方山地人已经体现了矛盾的双重角色:既是机构的正直代表,又是学生、球迷和校友的煽动性啦啦队长。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身份和功能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扮演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个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将这个边界推进多远,才会打破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西弗吉尼亚大学经常受到测试的边界正是巴布科克-亚伯拉罕斯所阐述的边界:那些位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自由与约束之间”的边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山地人通过其双重根源诚实地获得了这些矛盾:一方面是早期的擅占者(squatter)和乡巴佬(hillbilly)形象,另一方面是森林居民(backwoodsman)和边疆人(frontiersman)形象。虽然乡巴佬和边疆人都是自由的象征,但乡巴佬代表的是一种比边疆人更具破坏性、更不受约束的自由。正如巴布科克-亚伯拉罕斯和海德所暗示的,山地人的这些乡巴佬和边疆人特征并不会相互抵消;相反,它们相互补充。它们赋予山地人比单独任何一个形象都更广泛的特征,也为个人表演山地人身份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根据不同的情境,认同自己是山地人的人可以选择强化或推动两者之间的边界:在与州外人士讨论西弗吉尼亚时,他们可能会展现身份中边疆人的一面,强调西弗吉尼亚人的勇气、坚韧和谦逊。然而,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橄榄球队大胜(或大败)之后,他们可能会喝醉并点燃一张沙发。无论大学是否喜欢,这两种行为都与山地人身份的双重性质相一致。
在本文中,当我使用术语”表演”(performance)时,我不仅指西弗吉尼亚大学官方山地人吉祥物的正式表演,还指认同自己是山地人的人所从事的非正式表演,比如上述的两种表演:与外人的严肃对话和焚烧沙发。山地人如何理解成为山地人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向自己和外人展示这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如何表演山地人身份?这种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简而言之,这就是本书的工作。
让我在研究中着迷的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山地人光谱的边疆人和乡巴佬两端之间,出现了一种规律的、几乎可以预测的摆动。在山地人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首先,作为弗吉尼亚西部人民的总称,然后作为西弗吉尼亚新州公民的名称,再然后作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球迷和校友的特定术语——边疆人和乡巴佬一直和平共处。但很有规律地,这两种身份会在上述文化边界上发生冲突。具体来说,西弗吉尼亚大学在不同时期曾试图扼杀那个推动边界的捣蛋鬼——乡巴佬——并提升更受约束和文明的边疆人。
[第一章] 探讨了山地人的根源,回顾了从殖民时期到二十世纪初的早期形象。要真正理解关于山地人身份的争论——特别是野性未驯的野人一面与坚毅的拓荒者一面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理解这一身份的两个方面的根源有多么久远:它们不仅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英格兰本身。随着美国向西扩张,擅自占地者(squatter)和边远地区居民(backwoodsman)的形象进入了美国大众的想象,并成为强大的政治工具,既可以被用来造福也可以被用来损害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们。南北战争之后,解放、重建以及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乡村白人在不同时期被外来者视为蔑视、施舍和浪漫种族主义的对象。
第二章 探讨了二十世纪初山地人的概念如何受到流行文化中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影响,到1930和1940年代,这一形象在电影、音乐、漫画和其他媒体中无处不在。乡巴佬恰好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决定将山地人作为其官方吉祥物的时刻流行起来,永久地将这两个形象联系在一起,尽管后来大学管理者试图切断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将通过对二战后立即就读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男性的研究和实地调查来追溯,那是一个大学学生群体急剧增长的时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文化多样性上都有所增长,来自族裔和工人阶级背景的退伍军人依靠《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成为第一代大学生。这也是山地人作为乡巴佬形象的描绘达到顶峰的时代,山地人日(后来的山地人周)在这个时期诞生,同样在1950年代,乡巴佬形象被大学管理层正式禁止。
第三章 聚焦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的山地人,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对西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影响与对其他地方和大学校园的影响一样深刻。然而,这也是林登·约翰逊宣布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的十年,该运动重点关注阿巴拉契亚地区,而其理由往往是延续了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人们如何看待阿巴拉契亚的浪漫与厌恶的老套组合。在一个年轻人被征召为国家扛枪参加不得人心的战争、国内学生反抗制度权威的时代,山地人再次成为探讨反叛、异议、爱国主义和阿巴拉契亚身份等观念的焦点。
在第四章中,我转向仅有的两位曾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女性——娜塔莉·坦南特(Natalie Tennant)和丽贝卡·德斯特(Rebecca Durst)的经历。尽管两人担任山地人的时间相隔近二十年,但两位女性在担任山地人期间都面临着激烈的批评和性别歧视。前几章关注的是山地人身份如何始终与种族和社会阶层观念相联系,而第四章则探讨坦南特和德斯特如何揭示了山地人与男性气质之间的联系。
最后一章着眼于围绕山地人身份的最新争议,延续丽贝卡·德斯特作为第二位女性山地人所引发的争议。从MTV短命的系列节目《Buckwild》到J·D·万斯(J. D. Vance)出人意料的畅销书《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再到2018年西弗吉尼亚教师罢工,阿巴拉契亚文化近年来一直处于全国聚光灯下。而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本身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大学”Go First”宣传活动的推出,这似乎旨在将山地人价值观与特定的山地人形象分离。然而,关于成为山地人意味着什么的冲突仍在持续,学生们继续拥抱山地人的野性一面,而管理者则继续压制它。在这个术语首次用于描述西弗吉尼亚西部居民两百多年后,是什么让山地人保持如此相关和充满争议?而且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特别是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校园里——山地人的未来是什么?
并非所有读者都会同意我在接下来章节中关注的山地人身份的各个方面,我怀疑有些人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记录每一位担任过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人的服务的书。那当然是一本值得撰写的书。然而,这本书是广义上山地人形象的文化史,而不仅仅是官方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形象及其历史是相关的:官方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当然是基于这样一个更广泛的理念,即山地人代表所有西弗吉尼亚人,代表他们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但山地人的这两个化身并不总是完美契合。事实上,本书经常聚焦于这样的时刻:大学关于山地人应该是谁以及应该是什么的官方理念与关于山地人身份的更广泛理念发生冲突。
毕竟,Mountaineer(山地人)这个词汇在大学采用它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因此它的历史比WVU Mountaineer(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历史更为悠久、更加复杂、涵盖范围也更广。(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可能使用WVU Mountaineer这个术语来特指大学的吉祥物,而使用Mountaineer来指代更宏大、更古老的山地人概念。)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认为,大学在塑造和定义Mountaineer这一概念时行使了过多的控制权:毕竟,这个名字属于所有西弗吉尼亚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与大学有关联的人。当WVU在二十世纪初采用这个绰号时,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同意接受Mountaineer在流传了一百多年后所携带的历史包袱。从某些方面来说,WVU Mountaineer的历史记录了大学逐渐意识到其吉祥物选择是多么复杂和有争议,更不用说它持续试图规范和控制Mountaineer这一概念的努力。
作为一名民俗学者,我对关于Mountaineer的传统民间观念与大学”官方”观念之间的互动十分着迷。剧透警告:在这类较量中,民间版本几乎总是获胜。我确实是以民俗学者而非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处理这个项目的。因此,虽然我希望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并尽可能提供深入详细的文化背景,但最终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故事:那些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在WVU经历的学生和校友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帮助我理解的更宏大的叙事。
我之前在民俗学田野调查方面的经验可能为我从事口述历史和档案研究工作做好了准备,但它并没有让我为史学编纂的挑战(和深切的乐趣)做好准备。即便只是浅尝辄止,我也对历史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敬意。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总有另一个档案来源需要查阅,总有另一本书需要阅读。为此,我非常感谢那些历史学家,他们的工作帮助我将研究置于西弗吉尼亚和阿巴拉契亚历史的更大背景中:约翰·亚历山大·威廉姆斯的《西弗吉尼亚:一部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事实和细节,我特别感激威廉姆斯坚持积极抵制讲述该州历史的常规方式。除了个人访谈和档案研究之外,许多书籍对于帮助塑造我对这个项目的思考特别有用。南希·艾森伯格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白人垃圾:美国阶级的四百年未述历史》和史蒂文·斯托尔的《Ramp Hollow:阿巴拉契亚的苦难》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理解Mountaineer身份如何被更宏大、更古老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塑造方面。安东尼·哈金斯的《Hillbilly:一部文化史》——一项既宏大又极其精确的关于hillbilly(乡巴佬)在流行文化中的化身和意义的研究——帮助我构建了与Mountaineer密切相关的hillbilly(乡巴佬)图像的悠久历史。这些只是支撑我工作的部分长篇资料来源,我特别提到它们是为了那些有兴趣更深入详细地探索西弗吉尼亚和阿巴拉契亚更广泛历史的读者。
作为大学体育吉祥物,Mountaineer是为数不多由单一、可识别的个人扮演的吉祥物之一。大多数吉祥物都是我所说的”泡沫头”类型;扮演吉祥物的个人身份被超大的服装所掩盖,尤其是那些超越基本面具的精心设计的头饰。这些典型的吉祥物服装夸大了吉祥物的尺寸,使原本就不像人的形象因其巨大的身体比例而显得更不像人。但吉祥物的个性也以其他方式被掩盖。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有幸采访了木偶大师和木偶制作者英格丽德·克雷波,她为华盛顿国民队总统吉祥物以及许多其他大学和职业运动队设计并制作了吉祥物服装。正是克雷波告诉我关于”吉祥物守则”的事,这是体育吉祥物之间的一套非正式规则,用于创造和保护吉祥物的魔法般的异质性。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占据吉祥物服装的表演者的身份必须保密。团队很少透露占据吉祥物服装的人(或多人)的姓名。守则的另一部分是,如果吉祥物确实由多人扮演,即使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场所,两个人也不能同时扮演吉祥物。然而,最关键的是,吉祥物不允许说话。他们学会通过手势和动作与粉丝交流,但他们不能说话。
显然,WVU山地人打破了所有常规的吉祥物规则:在任何时候只有一位WVU山地人(以及一位候补);这个人的身份不仅为人所知,而且对于他们的选拔和服务都至关重要;并且这个吉祥物绝对会说话。事实上,多年来,WVU山地人的职责已经变得更多地(即使不是主要地)是作为大学的公关发言人,而不仅仅是在体育赛事上欢呼。早期的山地人只需要出现在体育赛事上欢呼,而近年来的山地人平均每年要参加250次非体育相关的公开露面活动,包括参加校友活动和筹款活动、在学校发表演讲以及探访医院里的儿童。当我向克雷波解释这一切时,她也认为不会把WVU山地人称为吉祥物——这也是许多前任山地人已经告诉过我的。克雷波只是帮助我理解了原因。所以,套用电影《伴我同行》的话,如果不是吉祥物,那么山地人到底是什么?
虽然山地人的面容是可见的,但他或她确实会穿一套服装——尽管至少有一位前任山地人说他不认为这是服装,因为那会让人联想到伪装、表演和虚假的概念。因此,在本书中,我将把WVU山地人的典型装束称为山地人的”配套装备”,借用英国俚语中kit的含义,即”用于特定目的或活动的一套物品,如工具或衣物”。值得注意的是,kit也被南北战争重演者用来描述他们的服装和配饰——这是一个特别贴切的联系,考虑到西弗吉尼亚州诞生于南北战争。Kit这个词也承认了山地人不只是穿上鹿皮衣就出门。浣熊皮帽、鹿皮鞋(moccasins)、火枪以及所有的配件也是必要的装备部分。可以说,近年来,胡须也成为了非正式装备的一部分。胡须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争议: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两位担任山地人的女性都因为没有或无法留胡须而遭受了无休止的批评和嘲笑(事实上,许多人引用这一点作为不应允许女性担任山地人的主要理由)。由于这些事件,大学一直强调胡须不是山地人装备的必需部分(尽管WVU的一个网页确实说”男性山地人通常在任期内蓄须”)。然而,在官方吉祥物存在的前三十年里,很少有山地人留胡须;直到男性面部毛发变得更被广泛接受后,胡须才成为WVU山地人习惯装备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山地人的装备与西弗吉尼亚州牧师兼作家约瑟夫·多德里奇描述的服装非常相似,他笔下的边疆猎人穿着”狩猎衫、弹药袋,右侧挂着火药角,双脚和双腿当然穿着绑腿和鹿皮鞋”。这段描述虽然写于1823年,但却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今天WVU山地人的整体外观。几位前任山地人告诉我,穿上这套装备是一种转变性的体验:它将他们从个人转变为山地人的象征。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如上所述,WVU山地人与其他吉祥物的区别在于,穿着装备的人是一个可识别的个体。然而,他们也不是个体:在穿上装备时,他们超越了个人身份,承担了一种集体身份,这种身份不仅将他们与以前的WVU山地人联系在一起,还与州历史以及一整套无形的价值观和信念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悖论:WVU山地人怎么能既是一个可识别的个体,又是州身份的象征性体现?然而,仔细看来,根本没有悖论:鉴于山地人身份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拥有一个既是独特个体又通过这种个人主义本身成为关于自主和自由的更大理想的化身的吉祥物,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并非一直都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扮演WVU山地人。事实上,指定官方山地人似乎是对20世纪30年代之前许多大学男生在体育赛事上非正式扮演山地人这一现象的回应,他们穿着”工装裤、法兰绒衬衫、浣熊皮帽、羊皮或熊皮背心”并携带步枪出现在比赛中。那套装束——带有工装裤和法兰绒衬衫——显然更能让人联想到乡下人(hillbilly)形象,而不是边疆人(frontiersman)。
即使在1937年大学正式选定单一山地人之后,仍有其他男性继续在比赛和其他场合扮演山地人,根据个人所拥有的装备,穿着从乡巴佬到拓荒者风格范围内的各种服装。拓荒者或乡巴佬的造型都很容易复制,在山地人存在的早期年代,当时还没有授权的标志性装备可用,学生们穿上自己对山地人服装的理解是一种展示他们粉丝身份的方式。我认为许多在吉祥物存在早期扮演山地人的学生这样做,是因为它为他们创造了与几位前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向我描述的相同的转变感:穿上这套服装将他们与更深层、更集体的身份感联系起来,这种身份不仅包括同学和粉丝,还包括所有过去和现在的西弗吉尼亚人。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种非凡的魔力,也是一直吸引和打动我的山地人形象的一部分。
MONTANI SEMPER LIBERI: 山地人永远自由。西弗吉尼亚州的座右铭巧妙地概括了山地人身份核心的反精英、反建制态度。150多年后,这句始于该州宣布脱离弗吉尼亚独立的短语,继续反映出当代居民仍然认同的反传统精神;肯定没有多少其他州的座右铭能与居民的当代身份保持如此相关。在2016年6月的一份通讯中,参议员乔·曼钦巧妙地概括了这个理念,他写道”西弗吉尼亚人总是抛弃现状,为正确的事情而战”。
山地人身份早在该州成立之前就已存在。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弗吉尼亚西部的居民就认为自己在文化和经济上与东部同胞不同。大多数山区居民是独立的、地理上分散的小农场主,他们并不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而该州东部则由富有的蓄奴地主主导。当弗吉尼亚州在1776年起草宪法时,它仅授予”拥有至少25英亩改良土地或50英亩未改良土地的白人男性”投票权。这一要求明显偏向该州已经开垦的东部地区的居民。西弗吉尼亚人还因弗吉尼亚州”无论人口多少,每个县只有两名代表”的法律而被剥夺了选举权。西部居民对这些限制感到愤怒,1803年,来自西弗吉尼亚哈里森县的州代表约翰·G·杰克逊给《里士满审查报》写了一封信,谴责这些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署名为”一个山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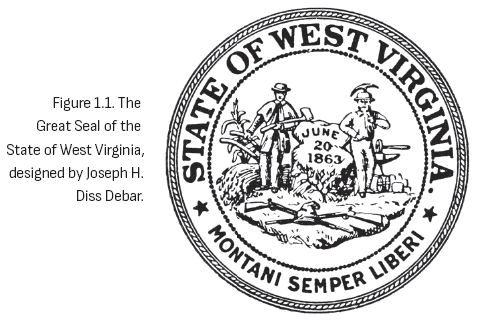
西弗吉尼亚历史学家约翰·亚历山大·威廉姆斯淡化了这种弗吉尼亚东西部分裂,他认为”到1861年西弗吉尼亚是一个与东弗吉尼亚如此根本不同以至于州的分裂不可避免”的信念更像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西弗吉尼亚传统”而非历史事实。他说,这种分裂既非不可避免也非独特:
弗吉尼亚的冲突并不比东西田纳西州或伊利诺伊州北部和南部或北加州和南加州之间的冲突更严重。弗吉尼亚与这些州的区别在于,南北战争在该州划了一条军事分界线。这条线保持相对稳定超过两年,将该州最不满的地区——西北角——与老自治领的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州可能会分裂,但它只发生在弗吉尼亚,也只有弗吉尼亚分裂了。
可以肯定的是,“穿过该州的线”不是按照文化界线选择的,而是出于交通、基础设施和军事战略的目的。然而,威廉姆斯关于这条线”隔离了该州最不满的地区”的随意评论掩盖了一个关键的文化信息。“该州最不满的地区”表明,事实上在弗吉尼亚西部存在广泛的情感和意见共识,这与其东部人口的情绪明显不同。当然,西弗吉尼亚有许多人不想脱离弗吉尼亚,并在战争中支持南方联盟事业。在《西弗吉尼亚:一部历史》中,威廉姆斯竭力暗示,在发展其州地位意识时,西弗吉尼亚在文化和政治上看起来像弗吉尼亚并渴望成为弗吉尼亚,而不是相反。
虽然威廉姆斯正确地引导我们远离传统、回归历史事实,但传统、神话和传说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强大力量,这也是本章将要探讨的重要内容。民俗学家有时会互换使用”地方传说”和”地方历史”这两个术语,以展示社区历史(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如何聚焦于极少数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象征着社区的过去,也代表着其当下的特征。这些故事通常有事实依据,但随着时间推移,叙事的某些方面会被强调、夸大甚至修饰,故事逐渐变得不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更多关于讲述者希望听众理解的更深层意义。这些故事几乎总是更多地反映当代人对其过去的期望,而非过去本身。这些叙事中强调的价值观通常是社区希望重新获得和强化的,而非那些被视为不再相关的价值观。
很少有历史神话和传说能像山地人(Mountaineer)那样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自1803年首次在印刷品中出现,作为弗吉尼亚西部居民的同义词以来,山地人的概念一直是西弗吉尼亚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唤起了反叛、独立和异议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的表现形式随时间而变化。
山地人是两个不同但密不可分的形象的独特混合体:边疆人或称为丛林人(backwoodsman)——在其早期化身中的称呼——以及乡巴佬(hillbilly)或称为擅占者(squatter)的形象。在19世纪,这两个形象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尤其是在弗吉尼亚西部,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在一起,那里的居民甚至在西弗吉尼亚成为一个州之前就自称为山地人。本章将探讨这些形象如何融合,并考察上述所有术语如何成为19世纪美国种族和阶级的标记。山地人总是自由的,而且——随着这个术语和身份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也总是被假定为白人,并且几乎总是贫穷的。事实上,在内战期间,尤其是战后,山地人这个术语获得了额外的含义层次,它被用来区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与”白色垃圾”(white trash),后者是指那些被认为已被奴隶制经济不可挽回地腐蚀的南方白人。
山地人形象起源于殖民时期美国的乡村土包子形象,而这一形象本身基于英国戏剧中约克郡人”霍奇”(Hodge)这一固定角色。最早的美国例子可以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威廉·伯德关于1728年考察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争议边界的记述中找到,他描述了懒惰的男人”躺着打鼾……点燃烟斗……虚度光阴”,而他们的女人则承担所有工作——这一形象在大约两百年后由比利·德贝克在连环漫画角色斯纳菲·史密斯(Snuffy Smith)中具体化了。伯德将该地区描绘为新世界的”懒人国”(Lubberland),这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虚构领域,在那里”懒惰具有传染性”,甚至连狗都懒得在叫唤时把头靠在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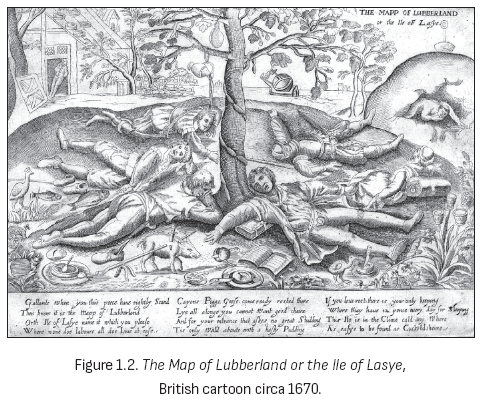
伯德笔下的新世界”懒汉”后来演变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擅占者”(squatters)和”穷白人”(crackers),然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变成了”白色垃圾”和”乡巴佬”(hillbillies)。山地人的根源可以在所有这些形象中找到,但山地人的家族谱系在丛林人和边疆人形象中有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分支。理解这两个山地人身份来源之间复杂而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理解西弗吉尼亚州,特别是西弗吉尼亚大学如何以及为何采用山地人作为其称号,以及为什么山地人形象多年来一直受到争议和管制至关重要。正如引言中所述,山地人既是恶作剧者(trickster)又是文化英雄,虽然这两个角色在大多数时候协同作用,但偶尔也会相互冲突。
18世纪和19世纪初美国边疆的西进扩张意味着,伯德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边界”发现”的乡巴佬(lubbers)领地很快就延伸到了该地区之外。最终,它扩展到包括从西弗吉尼亚州到阿肯色州之间的所有山区,包括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尽管南希·艾森伯格追溯这个偏远地区的人物”北至缅因州,南至佛罗里达州,横跨西北和东南领地。“[9] 在这个时代,山地人身份的两个分支才刚刚开始作为独立身份出现;像cracker和squatter(擅自占地者)这样的贬义词与backwoodsman(偏远地区居民)这个词或多或少可以互换使用,尽管作家们显然试图在贫穷的农村白人之间建立某种社会区分或等级制度。Squatter和cracker是专门用来指那些占据他们没有所有权土地的定居者的术语,这些土地通常他们不耕种或务农,而是用于木材、狩猎和捕鱼。[10] 擅自占地者基本上是流动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不是占据和定居在某块特定的土地上。
但此时另一个美国人物形象开始出现:高尚的偏远地区居民或边疆人,以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皮袜子故事集》中的纳蒂·邦波为代表。尽管偏远地区居民也是流动的猎人和探险家,但他的常识、机智和慷慨使他有别于普通的擅自占地者。偏远地区居民具有”平民魅力:虽然衣着和举止粗俗破旧,但革命后的偏远地区居民有时被描述为热情好客和慷慨大方,会邀请疲惫的旅行者进入他简陋的小屋。“[11]
然而,偏远地区居民并非普遍被这样看待:正如艾森伯格所描述的,“美国荒野的’亚当’有着分裂的人格:他一半是热情的乡下人,一半是携带匕首的强盗。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作为偏远地区居民,他是一个朴实的哲学家,一个独立的精神,一个强大而勇敢的人,不追求名利。但翻过来看,他就变成了白人野蛮人,一个无情的斗殴者和挖眼者。”[12] 偏远地区居民与”野蛮人”之间这种暗示的联系是山地人身份拼图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正如第二章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穿着鹿皮和鹿皮靴(moccasins)并非巧合。尽管其他因素似乎影响了大学推广那个版本山地人的决定,但山地人服装的某些方面将他与美洲原住民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是对这些文化不准确且高度浪漫化的想法。凭借他的鹿皮靴和衣服,山地人将自己与阿巴拉契亚的白人和原住民历史联系起来,暗示偏远地区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对土地——它能提供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尊重它——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实践这些价值观的共同技能。
当然,这并不反映该地区的实际历史,这主要涉及白人定居者夺取原住民土地,并驱逐——通常是暴力驱逐——在这些土地上生活或狩猎了数千年的群体。许多偏远地区居民,如西蒙·肯顿,特别因为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凶猛猎手而出名。但是,就像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一样,一旦原住民消失了,高尚化和浪漫化他们就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必要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山地人的服装是对该州原住民过去的某种致敬。
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讽刺。早期观察者经常将偏远地区居民和擅自占地者置于社会等级中美洲原住民之下,认为”至少美洲印第安人属于森林。“[13] 后来,在19世纪中叶,南方实业家威廉·格雷格会把他们提升一个等级,指出贫穷的农村白人生活”在一个仅比森林印第安人先进一步的状态。“[14] 基于种族将人按社会等级排序的做法在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而且不限于美洲原住民;更常见的是,贫穷的农村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包括被奴役的和自由的)进行比较,我们稍后会看到。然而,虽然白人身份过去和现在经常通过与种族和文化他者的对比来衡量,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白人身份都可以融入一定程度的”印第安性”。声称某种程度的美洲原住民身份不会削弱一个人对白人身份的主张,反而可以通过赋予其历史根基和真实性的光泽来增强它。见证一些白人家庭声称其家谱中有切罗基公主的长期存在,这是一种错误但顽固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15] 只要美洲印第安人被保持在过去,他们(想象中的)遗产就可以自豪地展示。
但在共和国早期,正是通过与擅自占地者或贫苦白人进行对比,富裕的白人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1817年,托马斯·杰斐逊的孙女科妮莉亚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姐妹,描述了她和祖父对杰斐逊位于弗吉尼亚州天然桥的地产进行访问的经历。在那里,科妮莉亚与一家擅自占地者面对面相遇,她将他们描述为”住在山脊之外的半开化种族”。孩子们几乎没穿衣服,一个男人赤裸上身,她注意到他们所有人加起来只有”两三双鞋”。她对他们粗俗的言语感到震惊,更让她震惊的是这家人似乎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毫无羞耻感。考虑到她感受到的恐惧,科妮莉亚能够向姐妹写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情是令人惊讶的,但她确实写了。她唯一遗漏的部分是,“半开化”的家庭可能对她同样感到困惑。
在科妮莉亚·杰斐逊的观察中,我们看到了至今仍存在的典型hillbilly(乡巴佬)刻板印象的痕迹:不合身的衣服、光脚、奇特的方言,以及对社会习俗的无知。但科妮莉亚并没有创造这些特征;事实上,她对贫穷边疆白人的描述很可能来自她之前多次遇到的既有观念。伊森伯格简洁地总结了这些观念:“擅自占地者在美国的普遍存在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比喻。他们开始与五个特征联系在一起:(1)简陋的住所;(2)夸张的词汇;(3)对文明和城里人的不信任;(4)对自由的本能热爱(即:放荡);(5)退化的繁殖模式。然而,即使具有这些不吸引人的特征,擅自占地者也获得了一些有利的品质:质朴的backwoodsman(森林居民)欢迎陌生人进入他的小屋,离谱的讲故事者整夜娱乐他们。”
在这个列表中,我们看到了从擅自占地者被重新称为white trash(白人垃圾)和hillbillies(乡巴佬)所持续存在的刻板印象的全部范围。这些刻板印象包括肮脏的家园、近亲繁殖、对外来者的敌意以及对恶习的放纵,以及更积极的特质,如好客和热爱讲故事。
虽然这种特征组合可能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它是十九世纪早期美国日益增长的文化比喻的核心:没有受过教育、不世故的乡下人,但仍然有头脑和力量来巧妙地对付试图利用他的更”有教养”的人。塞西尔·埃比很好地总结了这个形象:“那个持久而无处不在的美国英雄,一个由简单的心和常识大致相等部分构成的强健天真的生物,在正常情况下温顺谦虚,但拥有智胜或推翻侵犯其文化领地的自作聪明者的力量。”在当代,我们将其识别为乡下人对抗城市骗子的比喻,它继续成为笑话、电视节目、电影和其他娱乐的主要内容。
这个主题在十九世纪美国写作中如此普遍,以至于它的类型有时被统称为”擅自占地者对抗花花公子”,而包含这个主题的故事可以合理地称为民间故事类型。马克·吐温的第一个发表的故事《吓唬擅自占地者的花花公子》(1852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其中,花花公子从蒸汽船上下来,看到岸边一个乡下的backwoodsman(森林居民),决定抓住机会给船上的单身女士留下深刻印象。“女士们,如果你们想好好笑一场,请走到护栏外,”他喊道,宣布他”打算吓唬站在岸边的那位先生昏过去”。他走近backwoodsman(森林居民)并大喊:“终于找到你了,是吧?你就是我找了三个星期的那个人!做你的祷告吧!……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谷仓门,我会亲自钻钥匙孔!”backwoodsman(森林居民)什么也没说,而是用一记重拳将花花公子打入密西西比河。当花花公子浮出水面时,擅自占地者喊道:“我说,你啊,下次你来钻钥匙孔时,别忘了你的老熟人!”擅自占地者先出拳,最后笑到最后。
大多数花花公子/擅自占地者的故事都以这种拳头和妙语的组合结束,但实际上可以在西弗吉尼亚州自己的约瑟夫·多德里奇的作品中找到这个故事更复杂和相关的版本,他是一位在刘易斯堡和克拉克斯堡周围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牧师、作家和历史学家(多德里奇县以他的名字命名)。1823年,在吐温的故事发表近三十年前,多德里奇写了一部短剧,题为《森林居民与花花公子的对话》。多德里奇设定场景如下:“幕布升起,呈现穿着hunting shirt(狩猎衫)的森林居民,一个shotpouch(猎枪袋),他的powderhorn(火药角)在右侧,脚和腿当然穿着leggins(绑腿)和mockasons(鹿皮鞋)。一个时髦的小花花公子穿着他那个阶层的服装走近他。然后对话开始。”花花公子以早期民族志学者的方式,向森林居民询问关于他生活方式的各种问题。正如早期民族志学者经常做的那样,花花公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为了确认他已经相信自己知道的关于边疆生活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学习任何新东西。森林居民忍耐了他一会儿,但随后花花公子走得太远了:
我从你所说的一切中察觉到,伐木者先生,你一定曾经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你的国家是一片荒野;你的住所是简陋的棚屋或小木屋;你的家具是葫芦;你的婚礼是喧闹和淫秽的场景:没有礼拜场所;没有学校、法院,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民政;与印第安人持续交战。没有舒适;身体没有优雅,心灵没有改善的手段——天哪!这是怎样的人类社会状况!这个国家是鞑靼还是西伯利亚?当然,先生,你们必定不过是一群半野蛮人!
伐木者做了他自然倾向于做的事,那就是一拳打在花花公子的脸上。他对”野蛮人”这个标签的回应是称呼花花公子为,嗯,花花公子,大声质问为什么”我要忍受这样一个矫揉造作、瘦弱、拘谨的小东西,称呼我和这个国家的其他第一批定居者为简单的野蛮人?“与吐温的故事不同,多德里奇的故事并非以笑话结尾,而是以说教收场,伐木者在一拳之后紧接着给出了一堂关于边疆生活和边疆人真实本质的课程:
伐木者是一种古怪的家伙……如果他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有朴素的良知。如果他的衣着不华丽,他的内在品质是好的,他的心是健全的。如果他不富有也不伟大,他知道他是他国家的父亲……你们这些小花花公子和其他大人物可以自由地享受我们艰辛的果实;你们可以在我们挨饿的地方享宴;在我们战斗的地方欢闹;但你们所有人都要冒险,别给伐木者任何你们的废话。
为了增加喜剧效果——并突出花花公子生活的轻浮——伐木者不得不帮助花花公子重新站起来听这堂课,因为花花公子紧身的束腰让他无法自己站起来。
关于多德里奇的剧作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它与十九世纪早期浪漫民族主义更大力量的联系。在欧洲,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可能如何改变传统文化的担忧促使格林兄弟收集德国童话,华兹华斯为英国的采水蛭者写诗。浪漫民族主义在新成立的美国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问题是,谁构成了美国的农民阶级?谁是那些在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并代表国家身份灵魂的朴素民众?最接近的类比是伐木者,尽管(正如多德里奇的剧作所暗示的)他只在边疆待了五十年。尽管如此,多德里奇笔下的花花公子以欧洲上层学者接近他们研究对象时那种奇特的崇敬和势利的混合态度来接近伐木者。不同之处在于,多德里奇笔下的伐木者拒绝——相当有力地拒绝——被贬低到过去和野蛮状态。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惊人的现代故事,因为伐木者非常清楚花花公子是如何试图代表他的,并让他知道他活得好好的,而且比花花公子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伐木者反击刻板印象的双管齐下的方法:先用武力,然后用理性。多德里奇笔下的伐木者在立即的暴力反应之后,紧接着进行了一场理性的说教,既向花花公子解释了伐木者的真实本质,又表明伐木者是一个更真实、更勤劳的公民,他未被认可的辛劳让”小花花公子们”过上了轻松的生活。这是对占地者/花花公子故事的一种非常不同的诠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主题在当代西弗吉尼亚仍然引起共鸣。在多德里奇的《伐木者》中,我们看到了最终成为山地人的形象的出现:他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穿着实用的衣服,有一颗健全的心,而且——最明显的是——对那些把自己置于他之上的人有些怨恨。后一种品质——面对精英主义的防御性自豪——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品质,一直延续至今。例如,我们在关于”煤炭战争”的言论中看到了它,其支持者很快提醒今天的”小花花公子们”和”大人物们”,“煤炭让美国的灯保持明亮”。埃比将多德里奇后来的书《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的定居和印第安战争笔记》(1824年)的”情绪”描述为”怀旧和防御性的”,这些特质在许多方面成为了整个山地人身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多德里奇对边疆怀旧的描述出现得多么早,因为今天我们想象十九世纪早期正是边疆生活的顶峰。我们做出这种联想是有特定原因的,这将在关于安德鲁·杰克逊和戴维·克罗克特的部分中讨论。但多德里奇的剧作揭示了到1820年代,已经有一种感觉认为”真正的”边疆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伐木者与花花公子的对话》中,两个角色都谈论边疆,仿佛它已经不复存在,仿佛伐木者已经是一个时代错误:
花花公子。早上好,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经常听说和读到关于伐木者的事情:从你的衣着推测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想和你谈谈关于这个国家的第一次定居以及你们与印第安人的战争。
伐木者。非常乐意。
丹[迪]。我毫不怀疑你关于往昔时光的故事既有趣又引人入胜,当然值得铭记。
后[山人]。说实话,我不能说它们有多好。我没什么学问,也从来不擅长讲故事;不过,我会像我常在西自由城法院看到的那样对待你,我会回答你向我提出的问题。
丹[迪]。你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后[山人]。1773年,邓莫尔战争前的那个夏天,我父亲翻过大山,在这一带定居下来。那时我还是个壮实的小伙子,大概十岁或十二岁。
丹[迪]。你最初记忆中这个地方的外部景象是什么样的?
后[山人]。嗯,先生,这地方的外部景象就是到处都是荒野森林,满是鹿、熊、火鸡和响尾蛇——到了夏天,野草长得那么高,你都能追踪到一个人骑马疾驰的痕迹。
丹[迪]。我想,先生,那时你们几乎没有文明生活的舒适条件吧。
后[山人]。是的,我们确实不怎么讲究,但我们够文明;因为那场让我们的睡帽每天都处于危险之中的战争,使我们彼此非常友爱;那时一个人抵得上现在二十个人的价值。
到了1823年,多德里奇笔下的后山人已经感到美好的旧时光已经过去,后代人已经失去了边疆美德。在剧本的序言中,多德里奇将这部作品定位为历史而非喜剧或虚构,坚称”它所描述的社会状态正是所提及时期确实存在的。甚至’后山人’所陈述的事实也是历史性的。它的语言正是我们最初定居者日常使用的语言。”
那么在建国不到五十年的1823年,失去了什么呢?多德里奇将后山人重塑为”国父”给了我们一个重要提示。M. J. 希尔认为”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边疆英雄需求很大”,解释说”西部代表着对旧世界的拒绝。西部似乎是美国独有的。渴望建立一个非欧洲身份的许多美国人开始将西部特征视为美国或民族特征。”
这种建立独特美国身份的焦虑不仅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和文学性的:希尔指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在这一时期在美国很受欢迎,将它们与前述的《皮袜子故事集》相提并论;司各特和库珀的作品都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浪漫主义美德。著名民俗学家本杰明·博特金在其1944年经典著作《美国民俗宝库》的开篇讨论了他所称的”不可抑制的后山人”这一形象的核心地位,指出”后山人是我们第一批高大的人,他们的话语是豪言壮语,他们的事迹是传奇故事。““浪漫小说充分渲染了他们凶猛、狂野的独立性,”博特金写道,并补充了现在熟悉的对比,即这位早期美国民间英雄还拥有一种”’粗犷钻石’般的骑士精神”和”步枪技巧”。值得注意的是,博特金将后山人形象的全盛时期精确定在与多德里奇剧本相同的时期:大约在1815年至1822年之间,当时喜剧演员诺亚·拉德洛首次表演了他的歌曲《肯塔基猎人》,这”标志着后山人从历史进入传说”,因为美国边疆进一步向西推进。
很容易看出后山人如何演变成山地人,因为后山人具有特定的价值观和理念组合:他是一个与社会表象——管理花花公子的规则——分离的人,这使他比城市居民更文明、更诚实、当然更有男子气概,可能也更深刻地”美国化”。多德里奇的剧本还向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初生活在边疆的人们对外界看法的深刻意识。就像虚构的后山人一样,边疆人渴望挑战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也急于证明他们和生活在更稳定、人口更多地区的人一样文明。这种对自己传统的自豪和对外界看法的焦虑的强大组合至今仍然存在于西弗吉尼亚州,那里的新闻报道和其他广泛传播的关于该州的表述要么因延续刻板印象而受到审查和谴责,要么因让西弗吉尼亚州看起来文明和进步而受到赞扬。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张力往往直接通过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表现出来。
多德里奇的戏剧仅在科妮莉亚·杰斐逊向她姐姐写信描述在弗吉尼亚自然桥遇到”半文明种族”六年后出版。这两份文件如此接近的时间表明,擅自占地者(squatter)和边疆居民(backwoodsman)已经是确立的类型,并且关于如何定义这些类型以及谁有权定义它们的激烈辩论正在酝酿。在多德里奇戏剧出版后的十年里,这种冲突将在全国舞台上通过两位田纳西人上演,他们对边疆居民身份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特定品牌的边疆资本谋取政治利益:大卫·克罗克特和安德鲁·杰克逊。
擅自占地者/花花公子故事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广泛流行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到那时,隔离更多是边疆神话的一部分,而非边疆现实:多德里奇认为真正的边疆时代到1820年代已经结束的感觉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证实——到1800年,美国人口中有整整20%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边疆地带。投机者和其他外来者此时已经是边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的人们对这些地方及其居民充满好奇。虽然擅自占地者/花花公子故事为外来观众提供了娱乐,但对于生活在边疆的人们来说,这类故事提供了一种对独立和身份的叙事重塑。埃比这样解释这类故事在边疆人群中的流行:“面对社会变革阴影的延长和地方自治的削弱,边远地区的观众似乎发现那些聚焦于痛打花花公子的短剧和故事难以抗拒。这是他们对蜂拥而至的繁荣时期投机者、费城律师和来自哈德逊河以东的洋基化访客的替代性复仇。”声称擅自占地者或边疆居民的标签是一种获得对它控制的方式,将其变成荣誉徽章——或至少变成抵御外部力量的盾牌。但与所有这类语言角力一样,即使在”内部人士”——那些自称为擅自占地者或边疆居民的人——之间,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和含义,或如何最好地部署和表演这些身份,也没有达成一致。
安德鲁·杰克逊和大卫·克罗克特向公众展示的边疆居民形象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争议。两人都来自田纳西州,尽管他们各自的出生地在他们出生时仍属于北卡罗来纳州西部。两人都在1820年代崛起为政治和文化名人,尽管许多人忘记了除了如电视主题曲所说的”荒野边疆之王”,克罗克特还是”民兵侦察员和中尉、治安法官、镇委员、州众议员,最后是美国国会议员”,于1827年首次当选。
在两人中,杰克逊更符合当时对穷白人(cracker)或擅自占地者的刻板印象。正如艾森伯格委婉地说的,杰克逊”并非因政治家素质而受钦佩”,而是因为他的”粗糙边缘、土地饥渴以及与田纳西荒野的紧密认同”。1824年、1828年和183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努力推销杰克逊”野性”本质的积极方面,同时淡化他传记中暴力和放荡的部分——他在1806年的决斗中射杀律师查尔斯·迪金森;他与雷切尔·多纳尔森·罗巴兹(他最终会娶的女人)有通奸关系;以及1818年,在他担任陆军将军期间,他领导了对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西班牙防御工事的未经授权的军事入侵。这些只是他众多著名事迹中的几个。对老山胡桃(Old Hickory)的支持者来说,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的独立性和行动意愿而非过度思考;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证明了他不适合做政治家。
然而,正如博特金指出的,这正是边疆居民作为典型美国民间英雄出现的时刻——那么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在国家首都代表成长中的共和国呢?杰克逊首次(不成功的)总统竞选发生在1824年,就在多德里奇出版《边疆居民与花花公子的对话》一年之后,也是多德里奇出版其《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西部定居与印第安战争笔记》的同一年。美国公众对边疆故事似乎有永不满足的胃口,无论是事实还是虚构。希尔将当时公众对边疆的迷恋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曾经被保守派视为野蛮温床的西部,现在几乎被所有东部人接受了。可以说,像克罗克特这样西部英雄的温和(即使粗野)形象帮助消除了保守派的恐惧;可以说,西部被其神话驯服了。”1820年代的阅读受众和选民显然对边疆居民形象着迷,即使他们仍不确定他是像多德里奇所暗示的”我们国家的父亲”还是一个野蛮人。杰克逊和克罗克特提供了两个版本供公众消费和评判。
杰克逊的做法是接纳,甚至直接利用人们对边疆人的印象——粗鲁、好斗、行动派,他推崇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以此对比早期共和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做事谨慎的柔弱绅士政治家们。暗示这些花花公子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应对美国边疆的严酷现实。讽刺的是,杰克逊——因制定《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强制东南部原住民群体迁移而闻名——常常被批评者比作野蛮暴力的印第安人。亨利·克莱在1825年将杰克逊描述为”军事酋长”,杰克逊自己也承认”有人费尽心思把我塑造成性情野蛮的人;总是一手拿着剥头皮刀,一手拿着战斧。“35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边疆人身份与美洲印第安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在杰克逊的案例中,这种联系源于人们对印第安人作为暴力、可怕的野蛮人的印象;其他联系则更多涉及对印第安人懒惰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助长了关于擅占者(squatters)和穷白人(crackers)的观念。
大卫·克罗克特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形象。克罗克特最初是杰克逊的盟友,后来因反对杰克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而著名地与其决裂。当克罗克特被施压要求服从党的路线并停止批评杰克逊时,他声称自己”不会在脖子上戴项圈,上面写着’我的狗’,项圈上刻着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36 这样做,克罗克特体现了边疆樵夫(backwoodsman)那种自由思考的反抗精神,但方式不像杰克逊那样咄咄逼人。然而,杰克逊的支持者们回应时给克罗克特贴上了擅占者的刻板标签,称他”令人不快且没有受过教育。“37
事实上,克罗克特反对杰克逊《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更多是因为该法案对边疆擅占者的潜在影响,而非对印第安人的影响。在印第安人被强制迁移中,克罗克特看到了一个类比——以及一个法律先例——可能导致白人擅占者被驱逐出他们已开垦的土地。克罗克特自己曾是擅占者,深知擅占者权利的不稳定性,他政治生涯的核心议题就是保护擅占者免受投机者不择手段的土地掠夺计划的侵害,他支持一项”允许联邦政府直接向擅占者出售土地”的法案。38
为了避免把克罗克特描绘得过于正面,我们应该记住克罗克特和杰克逊都是奴隶主,克罗克特臭名昭著地吹嘘自己能”像狐狸一样跑,像鳗鱼一样游,像印第安人一样吼叫,把黑鬼整个吞下去。“39 最终,正是这种粗俗、离奇的吹嘘和克罗克特那传奇般的人格魅力确立了他的遗产,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就是如此——1835年开始出版未经授权的《戴维·克罗克特年鉴》系列。对于一个生命相对短暂(他在阿拉莫50岁时去世)、政治生涯更短的人来说,克罗克特充分利用了他成名的几年时间,如此成功地扮演了边疆樵夫的角色,以至于他的名字现在几乎成了这个词的代名词。希尔认为”克罗克特是首批至少在某些时候以名人身份谋生的美国人之一。作为农民和政治家,他的记录参差不齐,但作为名人,他取得了巨大成功。“40 克罗克特非常精心地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图1.3]),深刻理解他的政治经纪人和听众欣赏什么、想从他那里听到什么;克罗克特”利用了美国公众对白手起家者的喜爱”,甚至指示他的书籍出版商保留拼写错误和糟糕的语法,“因为我没有文学野心。”41 这种未受教育、爱吹嘘的乡巴佬形象是精心打造的。
克罗克特表演的自觉性意义深远,既说明了他所处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预示了后面章节将讨论的山地人(Mountaineer)身份表演方式。克罗克特如此精湛地演绎了边疆人的角色,以至于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电影和电视节目仍继续将他塑造为典型的边疆人。而且,正如下一章将讨论的,克罗克特的名声——以及他与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吉祥物的联系——在1950年代的沃尔特·迪士尼电视剧中得到了更新和巩固。杰克逊同样是边疆樵夫身份的完美表演者;在许多方面,他更加成功,因为他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两人在塑造人们对山区人形象的普遍观念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表演的不同之处同样重要:杰克逊认识到被视为未开化和暴力所固有的威慑力量,而克罗克特则转向光谱的另一端,体现了无畏、冒险但本质上侠义的自然人。同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山地人起源的这两个根源至今仍在其身份中发挥作用。
到杰克逊时代末期,定居者(squatter)的形象已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固定角色;在1840年总统竞选期间,“定居者演变成了民主传说中通俗的普通人。两党现在都拥护他……[用]木屋的描绘、流行的绰号、饮用烈性苹果酒和浣熊皮帽来展现。”[42] 总统候选人丹尼尔·韦伯斯特”哀叹自己没有出生在木屋里,但通过他的哥哥姐姐们曾出生在木屋这一事实来声称间接的美德。“[43] 定居者/边疆人(backwoodsman)远非局外人,现在成了美国普通人的代表——至少是生活在美国东部权力中心之外的贫穷、无地的普通人。多德里奇在1821年暗示的内容——边疆人是”他国家的父亲”——现在已成为更广泛的信念。

然而,尽管杰克逊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政客利用他们的艰苦出身谋取政治利益,但他们的政策却积极地驱逐和使生活在边疆的定居者陷入贫困,这些定居者——正如史蒂文·斯托尔在《荒凉之谷》(Ramp Hollow)中所说——“在与印第安人相同的假设下,如果不是相同的策略下,失去了他们的土地。”[44] 仅仅占据一块土地不再构成对它的所有权。在杰克逊时代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土地是由不在地主(absentee landlords)大片持有的商品,而在这些土地上狩猎和耕作的定居者是篡夺者,他们缺乏对货币经济的参与使他们成为懒惰的经济负担,是需要被安排从事”真正”工作的浪费的劳动力。因此,就在定居者成功地部分按照自己的条件定义自己身份的时刻,针对同一阶层人群的另一个术语出现了:穷白垃圾(poor white trash),这绝非巧合。
随着国家为内战做准备,诸如cracker和squatter之类的术语让位于一个更新、更阴险且更持久的标签来称呼生活在边缘的穷白人:白垃圾(white trash),这个术语”早在1821年就出现在印刷品中[并]在1850年代获得了广泛的流行。“[45] 尽管我们现在倾向于将这个术语几乎专门与南方联系起来,但当它首次出现时,它是一个可以应用于任何生活在边疆的穷白人的术语。甚至亚伯拉罕·林肯也未能幸免于这一标签;1862年联邦将军大卫·亨特将林肯描述为出生于”一个蓄奴州[肯塔基州]的穷白人。“[46]
然而,正如詹姆斯·C·克洛特所指出的,“山区社会在历史上一直与南方’穷白人’的社会分离,塑造舆论的人很快就抓住了这种差异。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因为山区居民(Mountaineers)被认为是值得提升的独立民族。”[47] 因此,当squatters和crackers演变为white trash和后来的hillbillies时,边疆人(backwoodsman)正在转变为高贵的开拓者(frontiersman),在那位著名的南方邦联将军石墙杰克逊身上得到了体现。杰克逊当然是西弗吉尼亚州最杰出的本地之子之一,1824年出生于当时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但虽然西弗吉尼亚可能声称拥有杰克逊,杰克逊却不认同西弗吉尼亚。他坚决反对分裂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并认同自己是弗吉尼亚人直到去世。[48] 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
大多数传记作者……通过试图将石墙杰克逊塑造成某种”典型山区居民”的模式来回避[杰克逊认同自己为弗吉尼亚人的]问题,创造出一个人物,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自觉选择和行为,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生物,在其性格中代表了塑造他的社会的显著特征,从而可以与西弗吉尼亚联系起来,即使不是在他的行为上。因此,弗兰克·范迪弗在《伟大的石墙》(Mighty Stonewall)中将杰克逊描述为”一个山地人[具有]来自弗吉尼亚偏远西部地区的边疆人的坦率诚实、坚定和自力更生。“[49]
这种将石墙杰克逊奉为典型山区居民的呼吁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正是西弗吉尼亚脱离弗吉尼亚留在联邦以及肯塔基州拒绝加入邦联,导致北方人赞扬”忠诚的山区居民。“[50] 杰克逊尽管是邦联忠诚者,但仍设法保持了他的山区居民身份;他的政治立场显然被范迪弗归于他的”坦率诚实、坚定和自力更生”所掩盖。正是这种坚忍不拔和不屈意志的感觉,石墙杰克逊与当代山区居民共享:他是一个有荣誉的人,而不是一个几乎未开化的傻瓜或”小丑”,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克罗克特的描述。[51]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喧闹叛逆和勇敢坦率的两极化品质塑造了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区居民的形象,它们至今仍在相互争夺优先地位。
Mountaineer 这一形象中粗野、叛逆的版本可以追溯到擅自占地者(squatter)这一人物形象,以及其后续化身白人垃圾(white trash),随后演变为山地人(hillbilly)形象,这将在本章末尾和下一章中讨论。white trash 和 hillbilly 这两个术语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们与种族和白人身份特定且不断演变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前者明确,后者隐含——这种联系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如上所述,擅自占地者(squatters)、穷白人(crackers)和边疆居民(backwoodsman)常常因其与美洲原住民”野蛮人”的相似性而被定义。随着真正的原住民被强制驱逐出边疆地区,这种联系不再具有先前的相关性或刺痛感。
在缺乏明确的他者来衡量贫困边疆居民的种族身份的情况下,种族差异的概念直接被嵌入对贫困白人的称谓中。他们不是”白人”,而是”白人垃圾(white trash)“:在种族上与更城市化和文雅的白人分离。那个时代的描述指向北方白人希望与这个”穷白人种族(Cracker race)“保持距离的愿望,正如一篇报纸文章所说,同时也将”白人垃圾”置于白人和伪白人的等级制度中,以防止这些人获得提升。1866年,一位波士顿新闻记者声称,南方贫困白人生活在”如此肮脏的贫困、如此污秽的无知、如此愚蠢的低能”中,以至于”时间和努力将使黑人达到智慧的成年状态……我几乎怀疑是否有可能将这些’白人垃圾’提升到体面的地位。“一位纽约炮兵军官威廉·惠勒(William Wheeler)表达了他的怀疑,认为他在战后在阿拉巴马州遇到的白人难民是否真的是”高加索人”,怀疑他们是否与”我们自己的血肉”相同。其他观察者稍微更有同情心,但同样种族主义;联邦牧师哈洛克·阿姆斯特朗(Hallock Armstrong)表达了他的希望,“战争将敲掉数百万贫困白人的枷锁,他们的奴役实际上比非洲人更糟糕。”然而,无论观察者持何种观点,被贴上白人垃圾标签的人只是名义上的白人。

这个时代的美国文学也记录了跨阿巴拉契亚地区贫困人口对白人身份的脆弱主张。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白人垃圾”角色是乔治·华盛顿·哈里斯笔下的萨特·洛文古德(Sut Lovingood),他有着美国小说中第一个贫困的阿巴拉契亚白人角色这一可疑荣誉(图1.4)。萨特是一个粗俗、种族主义和恶毒的恶作剧者,他为后来Mountaineer形象的化身奠定了基础,他乐于愚弄权威人物,但由于自己的轻信,他往往最终成为这些把戏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为Mountaineer这一看似矛盾的交织概念奠定了基础,即拥有敏锐的天生智慧与无穷的天真相结合。一个类似的形象出现在阿肯色旅行者(Arkansas traveler)身上,这是19世纪中后期的民俗和流行文化现象,其中外来者——旅行者——被看似愚蠢的本地人所欺骗。这个主题也许在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其中公爵,一个经验丰富的骗子,在他为《皇家无稽之谈》做的广告中添加了一行字,写着”女士和儿童不得入内”,并高兴地预测”如果这行字不能吸引他们,我就不了解阿肯色了!“当然,本地人识破真相并在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中带着六十四只死猫出现这一事实,呼应了傻瓜只能被愚弄这么久的平行主题。事实上,吐温小说中对阿肯色的描述指向了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地区的混淆——安东尼·哈金斯(Anthony Harkins)在其文化史《山地人》中更全面地描述了这一点——这种混淆将持续到20世纪,最显著的是在艾尔·卡普(Al Capp)的连环漫画《小艾布纳》中,其狗斑镇(Dogpatch)社区最初位于肯塔基州,但后来转移到欧扎克地区。
吐温的小说还指向了19世纪末Mountaineer身份的另一个新兴方面,即位于阿肯色州的竞争对手谢泼德森(Sheperdson)和格兰杰福德(Grangerford)家族之间的世仇情节。正如哈金斯所指出的,“从1870年代到下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地区和全国性报纸报道了数十起以家族为导向的冲突,仅1874年至1893年间就有四十一起”,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特菲尔德家族(Hatfields)和麦科伊家族(McCoys)之间的冲突。历史学家现在将暴力归因于一系列战后社会和经济困境,并认为这是许多人维护地方自治的唯一手段。然而,当时,这种暴力被建构为来自”野蛮的苏格兰高地祖先”的人们不可避免的反应。事实上,虽然这些冲突最初被标记为仇杀(vendettas),但术语逐渐转变为将它们标记为氏族之间的世仇(feuds),从而强调了对暴力的所谓苏格兰解释。这种苏格兰血统与世仇之间的谬误联系一直持续到今天,最显著的是在J.D.万斯(J. D. Vance)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中,他反复将自己家族的暴力与他们的苏格兰-爱尔兰血统联系起来。
也许在某人首次积极扮演乡巴佬的例子中,“魔鬼”安斯·哈特菲尔德显然摆好姿势,拿着他的步枪——单独地或与他家族的其他成员一起,同样持枪——为插图和照片摆拍(图1.5)。但安斯·哈特菲尔德的表演非常有意识地就是:一场表演。他是一位精明的、多元化经营的商人和耐心的遗产继承人,他”对自己的产权有足够的信心,愿意等待诉讼结果”,他”活到了舒适的晚年,靠煤炭租赁的收入生活”,他的后代”在世仇年代之后的工业时代倾向于从事白领工作”。哈特菲尔德的侄子亨利·D·哈特菲尔德在路易斯维尔上了医学院,回到明戈县行医,并在1912年成为西弗吉尼亚州州长,也是第一位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州而非老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哈特菲尔德-麦考伊世仇更多地关乎政治和经济,而非任何天生的苏格兰人喜欢争吵和结仇的倾向;1880年代和1890年代其他报道的世仇也是如此,当时”一些山民拿下他们的步枪,向出现在山区的新一代测量员的路径上空开枪示警”——这些枪声可以预见地”经常被大都市报纸报道为世仇的新反响”。

所有这些都表明,外界公众对白人垃圾擅占者故事的兴趣在19世纪末期依然强烈,报纸也愿意迎合。但这些故事的一些主角也是如此,比如安斯·哈特菲尔德本人,他愿意让人们拍摄他拿着步枪的照片。正如安德鲁·杰克逊和戴维·克罗克特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的那样,从外界人士的刻板印象中榨取资本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西弗吉尼亚人(在许多方面现在仍然是)“当时对这种宣传感到不满”,但也”将世仇永久性地纳入了他们的民间传说”。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世仇”帮助使南方高地人成为美国流行文化中的一个固定形象,强化了坚毅的山民这一如画般的形象,但也帮助创造了乡巴佬的负面刻板印象,他穿着那个时期的服装——软呢帽和牛仔裤,留着大胡子,拿着步枪,提着威士忌壶,其举止被哈特菲尔德编年史的一位作者……巧妙地描述为清醒时迟钝,醉酒时危险”。威廉姆斯的描述完美地总结了山民新兴身份的两个极端;虽然他一方面是坚毅的或”清醒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危险的乡巴佬。正如前一个时代努力区分高贵的边疆居民和堕落的擅占者一样,这个新兴形象也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
这个形象会在19世纪末出现,恰恰在”山民的生活方式开始消失”的时刻,这似乎是讽刺的。但当然,这一点也不讽刺:这两种动态密不可分。正如美洲原住民直到被强制从土地上驱逐后才在美国东部白人文化中成为浪漫形象一样,山民也只有在他成为濒危物种后才能成为浪漫形象。将世仇家族描绘为”野蛮的山民”——正如《美国世仇:野蛮故事》(1889年)的作者T.C.克劳福德所做的那样——既满足了外界人士对这些美国他者的好奇心,同时也让外界人士能够置身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描绘让外界人士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开发感到完全心安理得,因为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认知: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外部慈善家和实业家才能拯救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和人民。在这个时代,伊丽莎白·卡特说,“呈现山民无助且没有工业用途就注定失败的叙事比比皆是。煤炭大亨将他们的产业归功于为一个未开化的地方带来秩序和和谐。”
当然,正如我们在多德里奇的戏剧中看到的那样,边疆及其精神已经丧失的感觉在1820年代就已经存在。但在19世纪末,西弗吉尼亚人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和法律变化,这些变化规范或移除了传统的靠土地为生的方式:森林”以野味肉类、野韭(野生韭菜)、黄樟、浆果、坚果……以及可以换取现金或更常见地用于以物易物的皮毛和草药,特别是人参的形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收成”,由于木材工业的大规模砍伐,该州在1870年存在的一千万英亩原始森林到1920年完全消失了。为遏制猎物和鱼类种群的枯竭而设计的捕鱼和狩猎法规进一步限制了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些19世纪末的激进变化标志着边疆居民故事弧的终点。在许多方面,西弗吉尼亚人比其他地方在这个故事中维持的时间更长,但正如哈特菲尔德家族自己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山民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采用新的方式。”
那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只能用怀旧来填补。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边疆地带在西弗吉尼亚的内陆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到1900年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灭绝之路。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们对其某些习惯和风俗产生了强烈的怀旧之情,但无论新的工业边疆多么令人不快,都无法回到过去的方式。”71 在这里,时机至关重要:对边疆地带的怀旧情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顶峰,此时西弗吉尼亚大学正在发展壮大,并开始在其他拥有知名绰号的赠地大学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比如印第安纳大学的Hoosiers或俄亥俄州立大学的Buckeyes。Mountaineers(山地人)这个词不仅符合采用州居民绰号作为大学吉祥物的传统,还为大学提供了一个容器,可以将对该州消失的历史和遗产的所有怀旧之情倾注其中。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将Mountaineer——无论好坏——与争吵不休、互相仇杀的非法占地者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形象很快就被重新命名为”hillbilly”(乡巴佬)。
就在西弗吉尼亚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将边疆开拓者变成时代落伍者的同时,美国其他地区也正在经历另一种转变,移民涌入城市和工业中心,对白人身份的界限提出了新的挑战。爱尔兰人以及东欧和南欧移民的到来造成了一个种族困境:这些人是白人吗?还是他们本质上属于不同的种族?虽然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来说可能显得荒谬,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关于种族的”科学”理论出现,并最终让位于伪科学的优生学,这些都是严肃甚至科学的关切。这种新伪科学的支持者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即源自英国血统的人,位于种族等级制度的顶端,这可以通过颅骨测量和其他”科学”手段来”证明”。这些关切直接影响了阿巴拉契亚身份的发展。正如艾伦·巴托所写: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被编纂成法典。约翰·菲斯克、阿尔伯特·B·哈特、亨利·卡伯特·洛奇和纳撒尼尔·沙勒等人系统化了种族分类的思想,并发展了其社会学含义……在他们的概念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高等的种族……提出科学种族主义思想的同一圈子的成员积极参与了阿巴拉契亚的定义……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山地人民所带来的困境之一,就是要根据他们(可能)值得称道的祖先血统来解释他们的退化状况。72
简而言之,对”真正”美国血统被稀释的焦虑使这些理论家中的一些人直接走向了阿巴拉契亚。突然之间,该地区以前被称为”白人垃圾”的乡村居民被提升到了种族优越的地位。他们不仅是完全的白人,他们被认为的地理隔离确保了他们比国家其他地区的人保持着更纯粹、更”真实”的白人身份。
至关重要的是,这也是Mountaineer(山地人)一词专门附加到阿巴拉契亚人身上的时期。在这种术语转变及其与白人身份的隐含联系方面,也许没有比伯里亚学院院长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和作家小约翰·福克斯这两个人更负责的了。这两人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与他们的校友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是同时代人,后者都是关于”科学种族主义”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家。73 弗罗斯特和福克斯在推广阿巴拉契亚的地理隔离使其人民在种族上保持”纯粹”(尽管落后)的神话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福克斯关于无知但高贵的阿巴拉契亚人的浪漫化小说将他们描绘成在毁灭与文明的边界上摇摇欲坠。他们只需要被外部力量救赎,之后他们反过来可以通过与自然和自由的强健联系来救赎和振兴整个白人美国。74 虽然福克斯本人住在肯塔基州,但他与东部精英保持着密切联系。福克斯和罗斯福是特别的朋友,斯托尔声称福克斯”塑造了他们对一个好斗且难以捉摸的白人山地人的概念”,并”向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和乔治·卢克斯、作家欧文·威斯特和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以及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包括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和威廉·迪恩·豪威尔斯)解读阿巴拉契亚”。75 简而言之,福克斯对山地文化的虚构描绘几乎渗透到19世纪末美国艺术创作的每一种模式中。
然而,更具影响力的是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他从1892年到1920年担任肯塔基州伯里亚学院的院长。在他任职期间,弗罗斯特本质上”发明了阿巴拉契亚作为一个被命名的社会实体”76,并创造了一套关于阿巴拉契亚的修辞话语,这套话语至今仍在被引用,尽管其中多有谬误。弗罗斯特也与哈佛的种族理论家们有联系,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在努力将”山地白人”确立为一个与”白人垃圾”截然不同的种族群体:“我们听说’山地白人’(他们鄙视这个称呼,就像我们会鄙视’北方白人’这个词一样)被描述为文盲、私酿酒者、杀人犯,但直到现在,山地人在我们的想法中仍然几乎无法与’贫穷白人垃圾’区分开来。”77 弗罗斯特认为,山地人——不同于”贫穷白人垃圾”——没有”因与奴隶劳工的实际竞争而堕落”;相反,因为山地白人”与奴隶制接触很少,[他们]保留了那种在土地所有者中普遍存在的独立精神。“78
弗罗斯特根据一个群体与奴隶制的历史关联(或缺乏关联)来塑造白人身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同寻常的是,弗罗斯特作为伯里亚学院院长的职位迫使他做出直接反映这一信念的政策决定。伯里亚学院是肯塔基州唯一的跨种族学院,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所之一。该学院由废奴主义者于1850年代创建,言行一致:在其运营的第一个十年中,60%的学生是非裔美国人,学院规章没有将种族分开,允许混合住宿和跨种族约会。79 学校的董事会包括非裔美国成员,直到1914年。不用说,这些政策在当时的任何背景下都是非常进步的,更不用说是在前蓄奴州肯塔基州了。
在他担任院长的早期大部分时间里,弗罗斯特支持学校最初的融合理念。当他在1892年接任时,弗罗斯特有雄心勃勃的计划来增加招生人数和扩大学院的捐赠基金。他做到了,到1920年卸任时,“将伯里亚的资产和捐赠价值从20万美元提高到1200万美元”。80 然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重大牺牲:他不得不放弃学院的跨种族使命。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判决使种族隔离合法化并开启了吉姆·克劳法时代后,伯里亚的政策受到外部力量更严格的审查。弗罗斯特面临两难困境:他对”山地白人”的定义根植于这样一个观念,即因为肯塔基州的山区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奴隶经济之外,山地白人摆脱了奴隶制的污点,因此是与拥有奴隶的白人不同的”品种”。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之后的政治格局转变,使得弗罗斯特很难既声称山地白人是”例外的”,又支持学院的跨种族政策。
在《黑人南方与白人阿巴拉契亚》一文中,詹姆斯·C·克洛特展示了19世纪末山地人和非裔美国人被描述得多么相似。根据当时主导新兴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的”文化进化”观念,山地白人和非裔美国人都被视为野蛮或原始文化的当代”遗存”。换句话说,他们是白人精英认为自己早已进化超越的文明发展较低阶段的活生生例子。这使得山地白人和非裔美国人在学术上很有趣,但在政治上却是个问题。克洛特认为,随着重建时期的失败以及大量新移民对更大范围内白人身份观念构成额外威胁,进步人士和慈善家故意转移了对非裔美国人关切的关注,转而专注于帮助他们身边贫穷的白人他者。正是这个事件的熔炉诞生了关于阿巴拉契亚的两个最普遍的神话:它的孤立使其成为18世纪美国的活化石,以及它的孤立使其成为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缩影,该地区的语言和民俗习惯就是证据。
这两种对阿巴拉契亚落后状态的解释都使其”野蛮”的人民成为更容易接受的资源和改革努力的受益者。这些人只是需要被带入现代性;他们不是顽固或具有威胁性的新来者(移民),也不是拒绝消失的丑陋复杂历史的代表(非裔美国人)。克洛特写道:“随着大量东欧移民在美国定居,害怕这种涌入的老牌美国人将阿巴拉契亚地区视为避难所和希望之地。”81 阿巴拉契亚人不仅主要是英国血统的后裔,而且他们是新教徒,不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移民是天主教徒。而且”阿巴拉契亚白人美国人的状况和需求在一个对黑人进步感到失望的适当时机被呈现给全国。以前专门用于黑人的努力现在可以部分转向山地白人。“82
这就是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所抓住的慈善思潮转变。因此,弗罗斯特对阿巴拉契亚文化的浪漫化渲染以及他为援助贝雷亚学院的山区白人学生而募款,可能更多是出于机会主义而非真正的关心。他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扬的关于山区人民和山区文化的神话,还是这些只是为了给贝雷亚学院带来资源的宣传话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弗罗斯特为当时一些最受欢迎的杂志撰写关于阿巴拉契亚文化的文章,包括《女士家庭伴侣》和《大西洋月刊》。弗罗斯特的事业获得了他的哈佛校友、未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1899年,时任普林斯顿教授的威尔逊告诉”纽约观众,贝雷亚学院将向阿巴拉契亚人民传授’自我控制’。”
在许多方面,弗罗斯特似乎完全认同”阿巴拉契亚人即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先驱”的理论,这在他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我们在南部山区的当代祖先》中得到了证明,该文章发表在1899年3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在文中,弗罗斯特对阿巴拉契亚人民及其生活进行了深度浪漫化和刻板化的描绘。他写道,前往肯塔基东部是”一段比从美国到欧洲更长的旅程;因为一天的行程就能把我们带到十八世纪。“到达那里后,旅行者会看到”美国历史上如此突出的先驱生活的当代延续”,这也是古老英格兰的当代延续:“伴随着这些撒克逊技艺(纺纱、织布等),我们会发现撒克逊语言惊人的延续。山区粗俗的方言与其说是退化,不如说是延续……许多乔叟时代的词汇已被上流社会抛弃,却在这些偏远地区流传下来。”显然,二十世纪之交的肯塔基东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主题公园。
在《当代祖先》一文中,弗罗斯特还回应了外界人士对该地区”世仇新闻”可能产生的焦虑:“家族情感的另一面是血仇,它至今仍完全存在……作为一种制度,它深深植根于旧世界传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人民尚未理解生命神圣这一显然现代的观念。山区凶杀案不是为了抢劫。它们几乎都是以荷马式酋长的精神实施的,动机是某种’荣誉问题’。”这里的措辞很值得注意;在短短几句话中,弗罗斯特成功地将阿巴拉契亚人与旧世界、古典希腊和苏格兰氏族联系起来。这是文化合法化的三重奏。
但弗罗斯特在这篇文章中的真正目的是间接地将阿巴拉契亚人与”穷白垃圾”和非裔美国人进行对比,他指出山区白人与这两个群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历史中没有奴隶制的污点。更直接地,他通过将前者塑造为美国建国理想的活生生体现,将山区白人与新移民进行对比,声称”由于阿巴拉契亚美国没有接受外国移民,它现在包含的革命’儿子’和’女儿’的比例比我国任何其他地区都要高。“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说法并不新鲜:约瑟夫·多德里奇在大约七十五年前就将边疆人描述为”他的国家之父”。最终,弗罗斯特对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所有方面都是错误的:肯塔基是一个蓄奴州,欧洲移民几十年来一直在阿巴拉契亚的木材、煤炭和其他行业工作。
弗罗斯特在文章结尾呼吁那些愿意拯救这些”可悲地落后”的人行动起来,说”没有比这更明确地呼吁智慧的、爱国的援助介入了。“弗罗斯特暗示,支持这项事业不仅有益于阿巴拉契亚人,也有益于整个南方,因为”一旦开化,这些高地种群可能会加强整个南部各州。“换句话说,受过教育的山区白人可能会抵消种族危机。弗罗斯特的呼吁还援引了日益增长的优生学伪科学,他声称”当更优雅的圈子中美国家庭不再多产时,山区美国人仍在养育大量健壮的孩子,其数量足以让族长们满意。这样一个人口的潜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弗罗斯特在这里有点含蓄,让读者自己推断这样的繁育计划如何有价值,但其含义是,培养更多这些”当代祖先”并将他们培养成”聪明而不世故”的人,可能会抵消欧洲移民带来的文化和宗教威胁。
在贝里亚学院,这种对帮助山区白人的关注意味着弗罗斯特必须刻意拆除该学院长期以来的种族平等历史。首先,他”推翻了批准种族间约会的决议。他还阻止种族之间的社交接触。为了寻求与该州整体黑白人口比例相近的有限黑人入学率,他成功了,因为到1903年,961名学生中只有157名是黑人。正如弗罗斯特后来所说,‘我们坦率地转移了重点,更多地吸引山民。’“后来,肯塔基州立法机关于19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肯塔基州公立学校进行跨种族教育。尽管弗罗斯特竭力反对该法案,认为贝里亚的模式可以进一步缩减规模以减少激进程度,但最终他承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是’目前肯塔基州最好的安排’。““隔离但平等”的神话赢得了胜利。贝里亚学院直到1950年才再次招收黑人学生。
然而,阿巴拉契亚身份的种族化仍在继续。事实上,到1914年,“山区白人”这个标签被认为过于冗余,以至于该地区的长老会传教士塞缪尔·威尔逊建议改用”山民”一词,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山区黑人、棕色人种或黄种人。”同样,这是一个明显不真实的陈述,但它强调了二十世纪初创造一种融合的白人意识作为共享的、规范的和无争议的愿望。随着种族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成为一个日益有争议的公共问题,阿巴拉契亚人为发展统一和团结的白人意识定义提供了两个相互依存的好处:一方面,阿巴拉契亚人作为其他被长期稀释的英国过去的孤立遗存的神话支持了种族纯洁性的幻想;另一方面,将阿巴拉契亚人建构为白人他者继续加强了他们与更富有的北方白人之间的阶级障碍。
这种对白人他者的拥抱导致了对该地区产生持久影响的干预和思想。当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在北方城市忙于为新移民建立定居点时,其他人则离开种族日益多样化的城市地区前往阿巴拉契亚,建立类似的机构来帮助一个现在被视为”美国最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群,正如人类学家艾伦·丘吉尔·森普尔在1901年《地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森普尔的说法与1900年《纽约日报》上首次出现”hill billie”一词的印刷品相吻合。在那里,hillbilly(乡巴佬)被描述为”阿拉巴马州山区的一个自由不羁的白人公民,他住在山里,没有什么财产可言,随意穿着,随心所欲地说话,有威士忌就喝,心血来潮就开枪。“有趣的是,《纽约日报》的文章特别将hillbilly描述为白人,因为——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词已经成为白人的同义词,就像”山民”已经取代了据称冗余的”山区白人”一词一样。
hillbilly时代已经开始,它引发了一股热潮,将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达到顶峰,但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术语——“山民”和”hillbilly”——在二十世纪初获得了文化影响力,恰好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采用山民作为昵称的时候。而当大学在1930年代末决定选择一个官方的山民吉祥物时,hillbilly热潮正如火如荼。因此,要理解山民新兴意义的全部范围——以及理解围绕山民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他(偶尔是她)应该如何行为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hillbilly现象。因为无论好坏,大学吉祥物的基础都是按照流行文化偶像hillbilly的形象创建的,同时也是与之对立的。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民吉祥物诞生的通常年份是1934年,当时Mountain Honorary——一个1904年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成立的服务组织——选出了该大学的第一位官方山民劳森·希尔。1937年,Mountain组织制定了年度选拔程序(当前程序的基础),导致博伊德”瘦子”阿诺德当选,他从1937年到1939年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民三年。(唯一一位担任山民三年的人是洛克·威尔逊,他从1991年到1993年任职。)然而,希尔(图2.1)和阿诺德(图2.2)远非第一批打扮成山民的人;这一传统在Mountain介入规范选拔程序之前已经存在多年。在1934年之前,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个人就穿着法兰绒衬衫、工装裤和毛皮背心打扮成山民。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Mountaineer(山地人)这个标签在1863年建州和1867年大学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里,就已经被用来称呼弗吉尼亚州西部——后来的西弗吉尼亚州——的居民。然而,这个绰号直到1915年才正式与西弗吉尼亚大学挂钩。4 最早的西弗吉尼亚足球队于1891年由学生梅尔维尔·戴维森·波斯特和比利·迈耶组建,早期的球队被称为Snakers(蛇队)。5 然而,一旦被采用,Mountaineer这个绰号立即受到了球迷的欢迎。1933年西弗吉尼亚大学与西弗吉尼亚卫斯理大学足球比赛的纪念册包含了以下欢呼词,该纪念册将其追溯到1915年:
这是西弗吉尼亚,这是西弗吉尼亚
每个山地人的骄傲。
来吧,老校友们,加入我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我们为西弗吉尼亚欢呼。
该纪念册还包括一个标注为1923年的欢呼词,归功于弗雷德·施罗德,这很可能是无处不在的”Let’s Go, Mountaineers”(加油,山地人)欢呼的起源:
西弗吉尼亚——山地人,
西弗吉尼亚——山地人,
西弗吉尼亚——山地人,
加油——加油!
加油!!!6
施罗德的欢呼词被命名为”Split Yell”(分裂呐喊)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这个欢呼词与今天的”Let’s Go, Mountaineers”欢呼遵循着相同的一呼一应结构。
西弗吉尼亚大学在1915年采用Mountaineers这个绰号很可能不是巧合,考虑到——如第1章所述——大约在这个时候,术语Mountaineer被建议作为阿巴拉契亚地区居民的更好称谓,以替代之前常用的术语mountain whites(山地白人)。7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是外界对阿巴拉契亚产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部分原因是公众对1880年代媒体津津乐道报道的世仇(feuds)持续着迷,部分原因是新兴的神话认为,山地白人是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或十八世纪美国,取决于你的偏好)的活生生的化身。尽管伊丽莎白神话主要是从阿巴拉契亚内部产生的,但它也是为外人精心编织的叙事。

山地白人,或山地人,被呈现为一个独特且更真实的美国人类别。他们被认为是全国最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并且——正如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艾伦·森普尔和其他人当时所暗示的那样——与”白人垃圾”(white trash)形成鲜明对比。阿巴拉契亚的捍卫者,如贝里亚学院的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通过宣扬山地白人来自纯正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未受奴隶制腐蚀(而南方”白人垃圾”已被腐蚀)的福音来增加学校的捐赠基金。这是种族分类先前轨迹的一次不寻常转向:此前,当该地区仍是边疆时,山地人的白人身份是与美洲原住民相对照来衡量的,在南北战争之前和之后尤其是与非裔美国人相对照。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山地白人既与被认为因与奴隶制捆绑而被毁掉的”白人垃圾”形成对比,也与从东欧和南欧进入该国并挑战种族分类的新移民潮形成对比。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白人身份被视为一种权利而被囤积起来,如果扩展给新来者就会被削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且重要的转变。白人阿巴拉契亚人曾经是东部精英用来增强其种族优越感的标尺——回想1817年科妮莉亚·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天然桥遇到”半文明”的原始乡巴佬时的反应。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观点发生了翻转:白人阿巴拉契亚人,或山地人,被认为是白人种族中”最纯正”的,移民他者被用来与他们进行衡量。在那个时代的种族氛围中——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影响——阿巴拉契亚山区”未受污染”、与世隔绝的人们成为了最白的白人,他们的血统没有被(按照那个逻辑)其他种族或族裔群体的血液所玷污。到1915年,山地人已经成为所有真正美国特质的浪漫化身,使其成为大学特别吸引人的绰号。但在采用Mountaineers这个名字时,西弗吉尼亚大学无意中采用了一个其身份将永远与二十世纪初关于种族和白人本质的关切紧密相连的吉祥物。
对阿巴拉契亚人民”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坚持与该地区此时日益增长的族裔多样性现实背道而驰。鲁迪·艾布拉姆森和罗伯塔·坎贝尔解释说,“即使在作家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塑造神话般的盎格鲁-撒克逊阿巴拉契亚时,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其他族裔工人在煤田劳动力中占到了40%之多,更不用说他们在新兴工业革命的城市商店和工厂中的存在。”8 许多非裔美国人也在这些行业工作。因此,关于山地白人”纯正性”的叙事是一个虚构,但却是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等筹款人和优生学家可以利用的虚构。
然而,二十世纪初关于种族和族群的观念并不是影响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形成的唯一因素。阶级意识和作为弱势群体的感觉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回想一下多德里奇1823年《乡巴佬与花花公子的对话》中的乡下人(Backwoodsman)。在击倒那个胆敢称他为”野蛮人”的自以为是的花花公子(Dandy)后,乡下人教训他,告诉他如果没有乡下人的劳动,花花公子和他那些”上流人士”朋友将一无所有:他们”可以自由享受我们辛劳的果实;可以在我们挨饿的地方饱餐;可以在我们战斗的地方欢庆;但你们所有人都要冒险,别对乡下人说废话。“这个《对话》很容易改编成一个世纪后西弗吉尼亚的工作环境:只需将乡下人变成煤矿工、伐木工或钢铁工人,他们被富有的外来工业家侮辱和利用,这些工业家自以为知道什么对他们无知的员工最好。乡下人通过言语和武力展示了他对权力失衡的清醒认识,并展示了他对外来者精英主义的抵抗。二十世纪初西弗吉尼亚的劳工组织者采取了类似的抵抗态度。难怪西弗吉尼亚成为劳工运动的有力熔炉。西弗吉尼亚人在山地人(Mountaineer)这个形象中已经拥有了一个代表草根诚信和固执的有力象征。我认为,正是这种防御性的自豪感是山地人身份的核心,也是山地人与早期的擅自占地者和后来的山地乡巴佬(hillbilly)的区别所在。
随着木材、天然气和煤炭工业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占据了西弗吉尼亚就业部门越来越大的部分,西弗吉尼亚人看到这些行业的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外州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不是工人。这一时期该州劳工激进主义的高涨证明了人们对这些状况日益增长的不满。但外来者坚持用”山地乡巴佬”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抵抗。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前面提到的哈特菲尔德-麦考伊世仇,历史学家约翰·亚历山大·威廉姆斯认为,这场世仇更可能根植于经济冲突,而不是归因于涉及的苏格兰-爱尔兰家族天生喜欢斗殴的特性。威廉姆斯说,“世仇在西弗吉尼亚这一地区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折点爆发并非巧合”,并指出这场特定的世仇”恰好在山地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消失的历史时刻,戏剧化地展现了西弗吉尼亚偏远地区的传统生活。”
因此,我们开始看到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初自称为山地人就不足为奇了;到那时,前面提到的经济变化已经发生。山地人再次成为一个怀旧的形象,回顾一个更简单、更浪漫的时代——当然,多德里奇的乡下人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就像多德里奇的乡下人一样,新兴的山地人也有一些东西要证明:他不是那个容易被精英外来者——无论是花花公子还是富有的工业家——吓倒的愚蠢乡巴佬。山地人生来就有自我意识,了解外来者如何看待他,并且肩负着反驳这些刻板印象的责任。
然而,这种强烈证明别人错误的欲望的另一面,是同样强烈地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在创造这些刻板印象的精英世界中发挥作用的能力。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也诞生于这种融入、被视为”正常”的焦虑。正如威廉姆斯所说,“大多数西弗吉尼亚人——特别是代表他们集体行动的领导者——都试图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他们在每个时代都试图找到绕过、跨越、穿过或突破大山造成的经济繁荣障碍的方法。”在这种背景下,将西弗吉尼亚大学的运动员——以及延伸到学生和校友——描述为山地人是具有策略性和颠覆性的。第一批山地人只能声称拥有源于经验的天生智慧,而现在这种智慧可以通过正规大学教育来培养和磨练。现在成为山地人意味着一个人受过教育,而不是没有受过教育。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山地人可以与任何州受过大学教育的公民平起平坐。
这种被视为主流一部分的焦虑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和其他章节中看到的:在山地人历史的特定时刻,关于山地人在外来者眼中的形象、它代表西弗吉尼亚大学和西弗吉尼亚人的意义的焦虑,爆发成关于山地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为的全面战斗。这种焦虑特别集中在该州的旗舰大学是合理的,它象征着该州与边界外更大文化的联系和渠道,代表着该州在提供教育和经验以准备其公民进入那个更大的、有人可能会说更精英的领域方面的(实际)投资。
但当然,正如西弗吉尼亚大学在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采用了山地人这个绰号一样,另一个描述阿巴拉契亚人的术语也在涌现——这个术语将在大众文化中获得更广泛的流传,并产生更持久的影响:乡巴佬。正如第1章中提到的,hill billie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900年的《纽约日报》上。在那里,乡巴佬被描述为”阿拉巴马州山区自由自在的白人公民,他住在山里,没什么财产可言,穿着随意,说话随心所欲,有威士忌就喝,想开枪就开枪。“12 有趣的是,《纽约日报》的文章特别将乡巴佬描述为白人,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术语成为了白人的同义词,正如山地人取代了据称多余的术语山区白人。
这个术语迅速流行起来。帕特里克·盖纳指出,“八年后,即1908年10月27日,德克萨斯大学英语讲师小莱昂尼达斯·沃伦·佩恩博士完成了他的第一份方言和口语表达列表,其中包括’hillbilly’。”13 到1934年,这个术语已经被广泛认可,被收录进《韦氏新国际词典》。在1900年到1934年之间,推动这个术语流行的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乡村音乐的爆炸式增长。当乡村音乐首次被录制然后广播时,这种新声音还没有统一的标签,hillbilly这个术语填补了这一空白。不过,与山地人这个术语一样,hillbilly这个术语虽然表面上去种族化了,但本质上仍是种族性的。这个术语吸引唱片公司,因为它将其所描述的音乐与白人爵士乐和古典音乐区分开来,也与当时另一个主要的小众音乐类型区分开来,后者被称为种族音乐(或使用辛辛那提国王唱片公司广告中的术语,深褐色唱片;[图2.3])。hillbilly这个术语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艺术家的种族,而无需明确的标签;它也承认白人音乐家可能有多种音乐流派,同时将黑人音乐仅仅基于种族限制在单一类别中。但是,在将乡巴佬音乐和种族音乐对立起来的同时,制作人或许无意中也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正如安东尼·哈金斯所说,“尽管’hillbilly’作为一种音乐流派和表演者的标签,明确表示’白人’,但它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混合文化和种族类别,既不同于又类似于非裔美国人和其他非白人形象。”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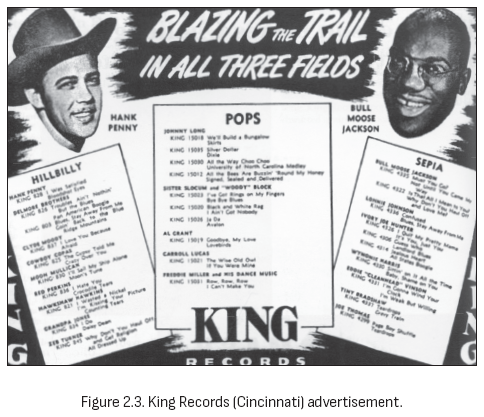
当西弗吉尼亚大学在1915年采用山地人这个绰号时,它是在依附于这个形象家族谱系中高贵的一面,那一支源自荒野居民(backwoodsman)和拓荒者(frontiersman)——被吹捧为真正的白人和美国人的那一支。hillbilly这个术语在这种对山区人民极度浪漫化的观点之后出现,这可能不是巧合。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它可以被视为贬义的(当局外人使用时)或赋权的(当内部人声称时)。无论如何,乡巴佬的形象似乎部分是为了戳破关于山区白人纯洁性的过度夸大的观念而出现的。哈金斯关于乡巴佬形象代表”一个奇怪的混合文化和种族类别”的观察进一步表明,乡巴佬的出现是为了挑战关于该地区种族纯洁性的虚假主张。因此,正如西弗吉尼亚大学自我认同为山地人一样,乡巴佬——一个更新、更广泛吸引人的山区人民漫画形象——也在获得动力。而且乡巴佬不仅仅吸引局外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也被它吸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大学将努力把山地人的形象拉回到拓荒者/荒野居民的谱系一端。
很难夸大二十世纪初”hillbilly”(乡巴佬)这一形象的巨大流行度和持久力。在对hillbilly形象的全面研究中,Harkins将1920年代和1930年代描述为hillbilly图标的全盛时期,他指出”到1930年代中期,这个词已经无处不在。“[15] 它的影响力超越了乡村音乐,延伸到电影,尤其是连环漫画:1934年见证了Al Capp的连环漫画《Li’l Abner》、Paul Webb的《Mountain Boys》(《Esquire》杂志的固定栏目)以及Snuffy Smith角色在Billy DeBeck长期连载的连环漫画《Barney Google》中的首次登场。[16] 虽然我们可能对《Li’l Abner》和《Snuffy Smith》最为熟悉,但Webb的《Mountain Boys》在当时似乎更具影响力。这部漫画描绘了三个可互换的兄弟Luke、Willy和Jake,巩固了hillbilly懒惰、暴力酗酒者的刻板印象,并将他们与月光酒罐、玉米芯烟斗和猎枪紧密联系在一起([图2.4])。这部连环漫画在《Esquire》杂志连载至1948年,1938年《Mountain Boys》在电影《Kentucky Moonshine》中被永久记录([图2.5])。[17] 正如Harkins所指出的,”这部电影几乎获得普遍好评,揭示了到1938年hillbilly形象已经变得多么不具争议性”:虽然《制作守则》明确将黑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和墨西哥人角色列为电影中可能存在问题的角色,但《Kentucky Moonshine》在获批时没有对其山区人物形象提出任何异议。[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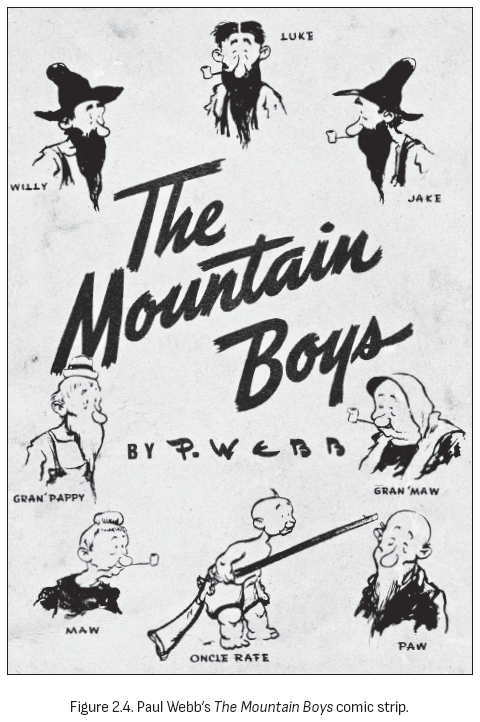

同年1938年,西弗吉尼亚州第二任桂冠诗人Roy Lee Harmon出版了一本名为《Hillbilly Ballads》的诗集,收录了他为Beckley《Post-Herald》同名专栏撰写和发表的诗歌,他同时也是该报的体育编辑。在书的前言中,Harmon解释了他这样命名这本书的原因:
“在许多场合,我看到西弗吉尼亚人仅仅听到’Hillbilly’这个词就感到冒犯。
坦率地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
对我来说,这个词没有任何污名。
相反,我将它作为荣誉徽章佩戴。
毕竟,什么是Hillbilly?
他是在我们心爱的群山中出生和成长的人,在那里上帝将自然之美倾洒成辉煌的堆积。那里有无法用简单数字计算的自然财富,在曾经是荒野的地方,坚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了一个现代而重要的联邦。“[19]
Harmon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正如我们从William Goodell Frost等人早期对阿巴拉契亚的描述中所知,是白人的代名词。到1930年代末,“hillbilly”这个词在经济上颇具价值,Harmon在1945年接受《National Hillbilly News》采访时讨论了这一激励因素。在采访中,Harmon
“讲述了一个晚上,大约在1938年左右……他试图在收音机上调到一个好节目。但他从收音机扬声器里听到的都是他所谓的’悲伤哭泣的民谣’。据说他厌恶地踢了收音机一脚,说他可以在一小时内写出四首这样的’感伤曲调’。他妻子建议也许他可以用这种方式赚点钱。然后他开始打赌说他必须在15分钟内写出一首感伤曲调。在灵感闪现中,他写了《Deep in the Hills》。他在钢琴上弹奏了它,但似乎忘记了它。多年后他在书桌里找到了手稿,把它给了在芝加哥WLS电台《National Barn Dance》节目中演出的Judy和Julia Jones。他又忘记了它,直到她们告诉他芝加哥的一位出版商喜欢它并想出版它。”[20]
虽然我们可能会想象当时只有阿巴拉契亚地区以外的人有兴趣利用hillbilly形象赚钱,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尽管Harmon似乎没有从他的任何hillbilly作品或感伤曲调中获得多少利润。
Harmon对hillbilly形象污名的不关心,大概是因为到1930年代末,hillbilly已经是一个可识别的喜剧类型,大多数消费者理解它是一长串”智慧傻瓜”的最新化身。《Li’l Abner》中的Dogpatch, USA足够通用,可以在不同时期被认为是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乔治亚州或阿拉巴马州[21],这表明没有一个州声称拥有hillbilly这个称号,或感到被它独特地压迫。事实上,正如Harmon的前言所暗示的,到1930年代末,这是一个可以作为荣誉徽章佩戴的标签。hillbilly这个形象,就像一个世纪前的backwoodsman(边疆居民)一样,已经演变成民间英雄和骗子形象。hillbilly的巨大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扮演傻瓜从而智胜”上层人士”的能力,即使他的胜利有时可能是无意的。
hillbilly热潮是二十世纪初大众媒体在美国传播的一部分,当时美国人开始通过广播、唱片和电影拥有集体流行文化。随着这些媒体将hillbilly介绍给阿巴拉契亚地区以外的人们,它们也将hillbilly介绍给了他自己: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就像十九世纪初关于backwoodsmen的故事在东部流行时一样。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到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阿巴拉契亚人要么接受这个标签并自豪地佩戴它,要么强烈反对它。
反对hillbilly形象的斗争已经开始。到1945年,即使是Grand Ole Opry的George Hay——在1920年代曾将自己的广播节目描述为”hill billy effort”——也宣称:“我们从不使用[hillbilly]这个词,因为它是带着嘲笑意味创造出来的……而且,根本没有这种人。”[22] Hay可能对这个词在他首次使用后的二十年间的演变方式感到不满,但到他在1945年发表这一声明时,hillbilly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流行文化形象,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WVU学生积极接受了这一形象。但Hay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阻止hillbilly发展的人: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也在紧追其后。
Mountaineer的frontiersman和hillbilly版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30年代升级,这十年是WVU决定选择官方Mountaineer吉祥物的时期。尽管早在1927年Clay Crouse自愿担任这一角色时,就有许多学生非正式地打扮成Mountaineer参加体育赛事,但第一位由Mountain Honorary选出的官方Mountaineer是1934年的Lawson Hill。[23]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也是漫画人物Li’l Abner、Mountain Boys和Snuffy Smith首次亮相的同一年。改编自漫画Mountain Boys的电影Kentucky Moonshine将在1938年上映,也就是Mountain正式确定Mountaineer选拔流程的一年后。大学决定在流行文化hillbilly处于巅峰的同一个十年正式确定Mountaineer的选拔流程、职责和外观,这不可能是巧合。WVU体育网站指出,“1930年代末Mountain会议的记录表明,一位捐赠者向荣誉组织捐赠了几张鹿皮,要求为Mountaineer制作鹿皮服装。在此之前,Mountaineer穿着工装裤、法兰绒衬衫、浣熊皮帽、羊皮或熊皮背心,并携带一支步枪。”[24] 工装裤和法兰绒衬衫明显代表hillbilly;而鹿皮则代表backwoodsman/frontiersman。
Mountaineer装备的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到1934年,当大学正式采用Mountaineer作为吉祥物时,不难理解为什么学校——以及整个西弗吉尼亚人——可能更喜欢backwoodsman的形象而非hillbilly。该州的经济遭受了大萧条的严重打击;在一些县,失业率超过80%。[25] Mountaineer在大萧条期间对西弗吉尼亚人承担了更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一形象让人回想起居民别无选择只能自给自足、节俭和坚定的时代。Mountaineer在很多方面是西弗吉尼亚人的榜样,他们试图在艰难的经济时期生存下来,同时保持自主和尊严。
这场将西弗吉尼亚人与他们的边疆根源联系起来并将他们与hillbilly形象分离的斗争,正在由政府正式发起;战场便是联邦作家计划(FWP)的西弗吉尼亚分支。联邦作家计划是工程进度管理局的一部分,旨在雇用失业作家研究和撰写美国指南系列丛书,被描述为”一种公共Baedeker指南,它将向好奇的旅行者指出每个州和县真正有旅行价值的地点。“[26] FWP各州和市政分支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出版各州及其主要城市的指南——这些出版物将列出游客的驾车路线和目的地,同时也作为所描述地点和人民的便携式历史。这些指南试图捕捉美国各地无形的文化遗产,并在强调工业和进步的同时,对过去和当地传统保持敬意。
《美国指南》融合怀旧与进步的特点在西弗吉尼亚州尤其难以实现,主要是由于时任州长霍默·“洛基”·霍尔特近乎偏执的担忧。他对《西弗吉尼亚指南》的顾虑使其直到1941年他任期结束后才得以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霍尔特整个州长任期的议程都围绕着文化表述问题展开。他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成立了州宣传委员会,“一个负责反驳负面宣传并推广州正面形象的机构。”27 八十年前的西弗吉尼亚州比现在更为乡村化,但尽管如此,大部分人口都能轻松接触到广播、报纸和电影。鉴于乡村音乐、连环画和电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迅速兴起,山区人民突然能看到外人眼中的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外人希望看到的他们。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州身份认知。
霍尔特对西弗吉尼亚形象的焦虑集中体现在州指南上。霍尔特对其内容拥有绝对否决权。他主要关注的是指南对该州劳工历史的叙述;霍尔特希望从稿件中删除整篇关于西弗吉尼亚劳工的文章,认为这是激进的宣传。28 霍尔特还反对指南对西弗吉尼亚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想删除一张农业安全管理局拍摄的煤矿工人使用锡制洗衣盆的照片,因为这暗示西弗吉尼亚人没有室内管道。他想删除一张儿童坐敞篷卡车上学的照片,因为这暗示西弗吉尼亚的孩子”像赶往市场的牲畜一样被赶去上学”。他希望删除所有关于咀嚼烟草的内容。他反对一篇描述传统草药疗法的民俗文章,因为这带有迷信色彩,他也不喜欢那个老笑话——农民用霰弹枪将玉米粒射进山坡来种玉米。29 综合来看,这些例子清楚表明霍尔特非常在意这类内容会如何强化外人对西弗吉尼亚人作为乡巴佬的刻板印象。他还反对指南中更进步或更具批判性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反驳西弗吉尼亚是全白人州观念的照片和描述。霍尔特要求删除关于墨西哥和意大利移民对该州劳动力贡献的细节、关于”黑人歌手拿着班卓琴和吉他在查尔斯顿街头用约德尔唱法演唱山地民谣”的内容,以及关于”查尔斯顿的黑人公民受到政党说客诱骗”的叙述。30 这些内容显然妨碍了霍尔特明确表述的西弗吉尼亚作为”一个为其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感到自豪的州”的观念。31
因此,霍尔特公开决心维护山地人与白人身份之间的联系:他使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这一措辞明确呼应了世纪之交的观念,即阿巴拉契亚人是更”正宗”、更少”污染”的白种人,而不是南方的”白人垃圾”。然而,到霍尔特在20世纪30年代末做出这一声明时,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纯正性”的主张已经过时且备受争议。正如安妮·阿姆斯特朗在1935年题为《南方山地人》的文章中所写:
关于南方山地人,人们说了很多、写了很多荒谬的东西,田纳西河谷项目将影响他们中许多人的命运,因而使人们再次关注他们。关于这些原始民族,似乎一方面没有什么太过浪漫,另一方面没有什么太过怪诞而不可信。他们被称为”南方山区人民”、“我们的南方高地人”——这些名称对山地人自己来说同样陌生;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为我们的”当代祖先”,并与其他落后的美国人一起被更轻浮的评论家称为”乡巴佬”。但无论用什么名称,他们仍然是一个显然引起无穷好奇的民族,似乎任何人即使只是最随意的接触后,都可以冒险做出解释。来访的诗人和小说家编写关于他们的故事,让他们说出一种显示作者自己创造力的行话,但这会让任何真正的山地人像听到印地语一样深感困惑。32
仅在这几句话中,阿姆斯特朗就巧妙地戳穿了几乎所有关于阿巴拉契亚人的刻板印象,并有效描述了外人对该地区及其人民仍然存在的”无穷好奇”。
霍尔特在”阿巴拉契亚人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话题上来得太晚了。但他可能有进一步的动机这样标记他们。在她文章的其他部分,阿姆斯特朗展示了这些关于该地区人民种族纯正性的主张如何被用来剥削他们的劳动。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神话本质上是由外人制造以惠及外人的公关手段:
最能说明误读这些人的例子,是北方实业家在南方商会的帮助下,近年来试图将山地居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进行剥削的著名行动。他们四处宣扬,在南部山区的高速公路沿线的广告牌上大肆宣传,这里终于有了百分之百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赖的忠诚、感恩、顺从的工人。33
Armstrong的话表明,Holt可能是出于经济而非情感原因坚持西弗吉尼亚人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向外人宣扬这个神话对他来说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样可以吸引工业和就业机会进入该州。Holt将州指南——一份明确旨在向外人介绍西弗吉尼亚并鼓励旅游和商业投资的出版物——视为向读者重复这一神话的理想工具。Armstrong的文章表明,到1930年代,阿巴拉契亚人在种族上与”穷白垃圾”截然不同且在种族上优越的伪科学观念已被认清其本质:一派胡言。在她的文章中,Armstrong还巧妙地驳斥了外人对阿巴拉契亚方言的描述,并将阿巴拉契亚人民和土地遭受的任何退化归咎于外部剥削。这并不是说Armstrong所说的都正确;在文章后面,她又重复了关于私酿酒和乱伦的阿巴拉契亚刻板印象,并在描述山地居民为”一个强壮、骨架粗大、桀骜不驯的种族,对他们来说,为某事或根本不为什么而战,构成了生命的呼吸,是尘世欢乐的精髓”时显得过于浪漫。34
然而,Armstrong文章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她将山地居民的身份描述为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既迎合又偏转外人的刻板印象:
南部山地居民,虽然不识字、“落后”,但并不容易解读。他不会向雇他在山路上当向导、向他购买野生浆果、自制炉边扫帚、钩针地毯甚至私酿酒的避暑别墅住客展露自己;更不会向在山区酒店与他偶遇的博学而文雅的客人展露自己;也不会立即向提议以他为稳定而廉价基础进行建设的实业家展露自己;甚至对为他尽心尽力工作的山区安置工作者也不会完全展露自己。就像黑人一样,他们经过几代人的适应以达到保护目的,在与白人的关系中成为了出色的演员,山地居民——尽管他的行为源于不同的根源——以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狡猾方式掩饰自己。35
这让人想起非裔美国民俗学家和小说家Zora Neale Hurston对黑人人类学研究对象如何应对白人人类学家的精彩描述:
黑人提供的是羽毛床式的抵抗,也就是说,我们让探针进入,但它永远不会出来。它被大量的笑声和玩笑闷住了。我们策略背后的理论是:“白人总是试图探究别人的事。好吧,我会在我思想的门外放些东西给他玩弄和摆弄。他可以读懂我写的字,但他肯定读不懂我的心思。我会把这个玩具放在他手里,他会抓住它然后走开。”然后我会说我要说的话,唱我要唱的歌。36
用外人或北方人替换”白人”,Hurston的引述同样可以描述阿巴拉契亚人为保护自己免受那些试图剥削或嘲笑他们的人而采取的掩饰行为。非裔美国人和山地居民面对外人时的狡猾提醒我们,成为一个骗术师(trickster)不仅仅是当小丑:它更多的是关于生存和抵抗。
Armstrong的描述在多个层面上都很重要。首先,尽管她回到了用其他种族群体——这里是非裔美国人——来衡量白人特质的旧模式,但她这样做的方式完全不同。她将”黑人”的身份表演与山地居民的身份表演进行比较,目的不是像历史上那样建立种族等级制度,而是将两个群体联系起来。她建立的联系是文化上的而非生物学上的,她描述的共同行为是保护性的: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黑人”和山地居民都戴上面具来保护自己免受外人伤害,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有理由怀疑外人意图伤害他们。面具允许Hurston所描述的那种”羽毛床”式互动:它给外人一种有所收获的感觉,而实际上只是触及了表面。骗术师偏转了对其社区的潜在威胁,而外人则带着自以为理解了他者的想法离开。
阿姆斯特朗对山地人”面具”的描述尤其重要,因为在她的文章发表的同一时期——1930年代中期——西弗吉尼亚大学选择山地人作为其官方吉祥物,并决定扮演这一角色的人不戴面具。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为数不多的大学体育吉祥物之一,他是一个可识别的个体,而不是穿着服装的匿名人物。然而,在山地人形象中仍然存在着面具化的元素。尽管我采访过的前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经常告诉我,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吉祥物,也不认为鹿皮服装是一种装束,但他们常常描述穿上鹿皮服装是一种变革性的体验,这种体验将他们从日常身份中提升出来,进入一个更宏大、更超然的身份。尽管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因其没有真正的面具而显得特殊,但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在穿上装备并转变为山地人的神话形象时,仍然戴上了象征性的面具。
阿姆斯特朗对山地人如何”以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狡猾方式”表演他们身份的描述,也可以用来描述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期间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非正式地演绎山地人身份的方式。尽管大学在1934年正式认可了山地人吉祥物,并在1937年规范了山地人的传统服装,但这仅仅发生在学生们已经自己扮演这一角色多年之后。重要的是要记住,官方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是从学生们非正式、自发的表演中产生的,这些学生在大学正式任命之前就主动扮演山地人角色多年。而且学生们在选拔程序正式化之后仍然继续扮演山地人。这种演绎包含了恶作剧者的所有元素:通过装扮成山地人,学生们可以沉迷于原本会受到谴责的行为。他们可以携带枪支和私酿酒壶(moonshine jug),大喊大叫,侮辱对方球队,而这一切都是以支持自己社区的名义。在许多方面,这与当前球迷和学生在比赛日采用的行为放纵许可相同。那么,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大学决定指定一位官方山地人之后,学生们从扮演山地人中得到了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对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表演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30年代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巨大流行,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提供了一个榜样和目标,当他们在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文化舞台上思考作为山地人的意义时。哈金斯指出,乡巴佬形象”在193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乘着…对普通民众的美化和对地区生活与文化的迷恋”的浪潮,这使得联邦作家计划(FWP)的指南得以普及。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们免费收到了韦伯的《山里的孩子们》漫画平装本,而壶乐队(jug bands)是军队中流行的娱乐形式。当退伍军人回到校园时,他们沉浸在乡巴佬的流行文化图像中,并且刚从海外的经历中回来,这使他们能够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文化遗产,战后时期正是重塑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成熟时机。与此同时,《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使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与”白人身份”的传统关联变得复杂,因为它允许来自代表性不足的族裔群体和工人阶级家庭的男性首次上大学。这些变化为山地人形象表面之下潜藏的阶级意识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挑战了山地人必然是(借用霍尔特州长的话)“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假设。
西弗吉尼亚大学成立时,只招收白人男性。第一批女性于1889年入学,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于1891年毕业。非裔美国人直到193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后才被录取,该裁决要求大学录取非裔美国学生参加”在非裔美国人州立院校中不提供的任何研究生课程”。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唯一的非裔美国人是研究生;非裔美国人直到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裁决后才能作为本科生入学。
因此,战后的西弗吉尼亚大学仍然以白人为主,尽管白人的定义正在迅速扩大,包括移民和族裔群体的成员,这些人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都不会被归入这一类别——意大利裔和东欧裔人。战后的西弗吉尼亚大学比战前和战时要大得多。1946年秋季,当《军人权利法案》生效时,“入学人数飙升至创纪录的6,010人”,而新生班级中60%是退伍军人。到1948年秋季,入学人数已达到八千名学生。为了满足住房和教室空间的巨大需求,“课程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以及周六进行…学生们涌入公寓和宿舍楼、政府剩余的营房和拖车以及摩根敦家庭的住宅;五名退伍军人与欧文·斯图尔特校长的家人一起住在校长住宅的二楼”。
在1946年秋季入学WVU的六千名学生中,有我的父亲David Barr Hathaway,他是Calhoun County本地人,最近刚从军队退役,曾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步兵部队服役。和其他退伍军人一样,他四处寻找住处,最终通过朋友介绍住进了Trinity Hall,这是一座由圣公会教堂拥有和管理的寄宿房屋,“专供贫困的圣公会男性居住”。我父亲既不贫困也不是圣公会教徒,住在这栋三层楼房里的大多数人也都不是。事实上,Trinity Hall已被定为危房并计划拆除,但为了解决住房短缺问题被允许暂时继续开放。我父亲在那里住了四年,直到这栋建筑最终在1950年左右被拆除。从他在Trinity Hall房间里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图2.6),他认为自己是个hillbilly,并为此”该死地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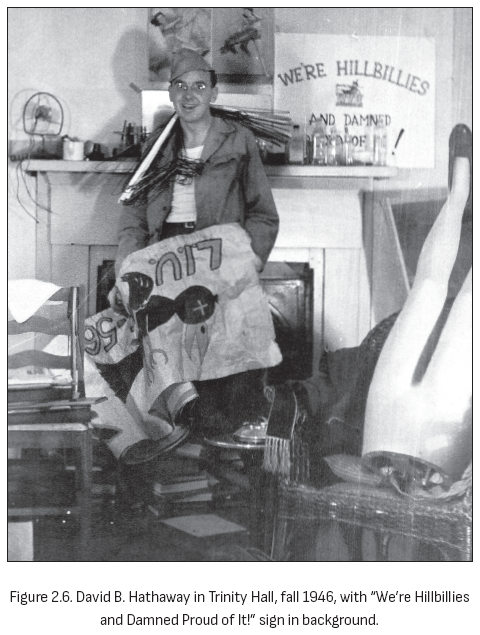
如前所述,hillbilly这个词既普遍又有争议。和其他文化标签一样,一些被贴上hillbilly标签的群体成员拒绝接受它,而另一些人则在文化再挪用的行动中拥抱它。在1949年《Rayburn’s Ozark Guide》的一篇文章中,作家Elsie Upton这样解释这个过程:
如果我伸出手与你相见并说”我是个hillbilly”,我就把睦邻政策带到了你的门前。我传递的是友善,这种友善体现了多年来与那些寻求帮助同胞的人们的接触。我带来的是勇气,这种勇气由那些克服障碍、战胜贫困的先辈们所培养。我带来的是正直,这种正直源于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我碰巧听到有人贬低性地使用这个词,“hillbilly”这个崇高的称号就不复存在了,而且由于我自己作为hillbilly和那个粗俗肮脏、无知贫困的hillbilly之间没有区别,我敢说——
一个人自称hillbilly是完全可以的、光明正大的,但普通人喜欢自己来做这个声明——因为这样做就额外赋予了尊重之光。
Upton的描述准确概括了被文化局外人称为hillbilly和自称hillbilly之间的情感和修辞差异。她也简洁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对局外人来说,hillbilly是肮脏的、贫穷的、无知的;对局内人来说,他是友善的、勇敢的、高尚的。
然而,Upton没有指出的是,hillbilly标签允许这两种版本共存于同一个形象中。当然,我父亲声称自己是hillbilly并为此”该死地自豪”,与其说是因为做个好邻居,不如说更多地与粗俗和”自由”有关(尽管Upton将hillbilly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联系起来值得称赞)。更具体地说,我父亲对hillbilly身份的认同是他拒绝并宣布独立于主导校园社交生活的传统希腊文化的方式。这是所有住在Trinity Hall的人共同的情感,他们以自己是GDI(goddamned independents,该死的独立人士)而非兄弟会成员为荣。事实上,住在Trinity Hall的许多人当时不会被任何兄弟会接纳,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来自意大利、亚美尼亚、波兰和其他族裔社区,是在西弗吉尼亚煤矿、钢铁厂和玻璃厂工作的移民的儿子。这些移民群体中的许多人当时仍然只是勉强被视为白人,而Morgantown本身就为其庞大的工人阶级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设有隔离街区。许多Trinity Hall的住户也是来自Wheeling等工业城市或贫困农村县的第一代大学生。大多数人是二战退伍军人,决心充分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提供的机会。由于其构成特点,战后时期的Trinity Hall成为研究这一时期Mountaineer概念转变的有用案例。
Trinity Hall 绝对不是兄弟会,但它确实将自己定位为校园社区中的官方宿舍。事实上,1948 年《Monticola》年鉴中对该宿舍的描述(图 2.7)展示了 Trinity Hall 如何有意识地在校园社区中定位自己,并与兄弟会形成对比。年鉴 Trinity Hall 页面上的文字指出,“Trinity 是校园中最杰出的宿舍之一”,并且”它已连续数年在学业成绩排名中位居第一”。45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宿舍居民的描述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使 Trinity Hall 成为”校园中更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46 Trinity Hall 清楚地意识到,其自身的种族和阶级多样性使其作为校外住宿空间显得不同寻常且与众不同。尽管如此,它仍积极参与希腊社区和更大的大学社区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竞争。因此,虽然居民可能希望将自己与兄弟会的阶级精英主义区分开来,但他们也想积极地与希腊社区竞争,既包括正式方式,如返校节装饰和其他比赛,也包括非正式方式。因为虽然 Trinity Hall 吹嘘自己拥有校园内所有住宿宿舍中最高的平均 GPA,但它也为自己类似《动物屋》的氛围感到自豪。这是一座满是恶作剧者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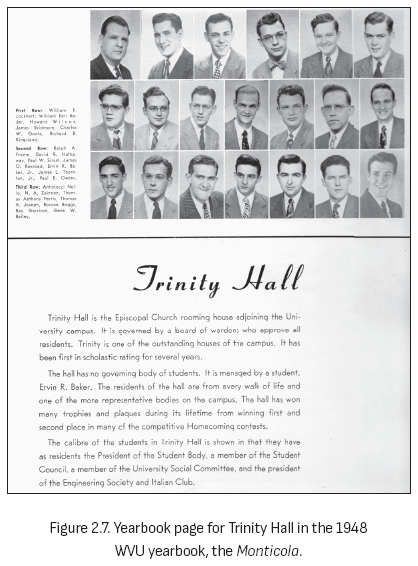
2007 年对前居民进行的访谈始于讨论宿舍中经常供应的”激情潘趣酒”的配方(“把你手头的任何酒瓶都扔进去,包括标签”)。一位前居民在 2007 年重聚前收到的一封信讲述了一个关于宿舍外观不佳的故事:显然,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一位准居民)来到 Trinity Hall 查看,看看这里是否可以作为儿子在 WVU 上学期间的住处。仅仅几分钟后,他们就下楼了,父亲被听到说:“你不会住在这个脏兮兮的宿舍里!见鬼,我宁愿为你建一座兄弟会会所,也不让你再踏进这里!”47 Trinity Hall 居民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看似矛盾的既聪明又叛逆,而且往往体现在同一个行为中。他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尽情狂欢,但仍然”在学业成绩排名中位居第一”,正如他们年鉴页面上所记载的那样。
1946 年的新生班级与以前的班级截然不同,不仅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如此,在整个美国也是如此。大多数入学的男性是返校退伍军人,年龄比普通大学新生大,并且拥有丰富得多的世界经验。我父亲经常讲述大学对录取这么多退伍军人的焦虑,管理人员担心战争会使学生更具攻击性并容易诉诸暴力。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只是渴望回归正常生活。唯一关于退伍军人殴打其他学生的故事与退役军人用暴力抵制强迫他们戴之前强制性的新生小圆帽有关。
1947 年的《Monticola》在多个层面反映了学生群体的这一里程碑式变化。开篇页面设定了主题,用军队风格的字体拼出信息”欢迎回来……回到学校……回到工作……回到娱乐……最重要的是……回到西弗吉尼亚大学”:这是一条旨在将退伍军人融入国内和校园生活的信息(图 2.8)。48 1947 年年鉴在其他方面也值得注意。由于战争期间纸张短缺,年鉴自 1943 年以来就没有出版过,似乎只是在 1946-47 学年期间,由于 Weirton Steel 的慷慨赞助才在经济上成为可能,该公司补贴了其制作并在多个页面上展示自己,包括一个全彩页面(图 2.9)。49 整个出版物中男子气概的叙述力量强大:从战争中归来的男人、工业实力以及大学橄榄球的恢复(在战争期间也曾暂停)。

1947年和1948年年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两本年鉴的图形都突出展示了一个乡巴佬风格的山地人(Mountaineer)形象。这些图像不是那种超男性化的拓荒者,而是典型的衣着寒酸、扛着步枪、豪饮私酿酒的乡下人刻板形象([图2.10])。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允许这些图像出现在官方出版物中,这意味着对这一形象的默许认可,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绝不会发生。尽管在这些年鉴出版时,身穿鹿皮装的官方山地人吉祥物已经存在了十年,但众多不一致的乡巴佬山地人形象表明,官方形象尚未完全成形。官方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可能看起来像拓荒者,但非官方的乡巴佬山地人在战后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远比前者更受欢迎。校园幽默杂志《私酿酒》(Moonshine)——无论是其标题还是其艺术作品——都表明,乡巴佬形象实际上比拓荒者形象更受青睐,至少在其幽默和娱乐潜力方面是如此([图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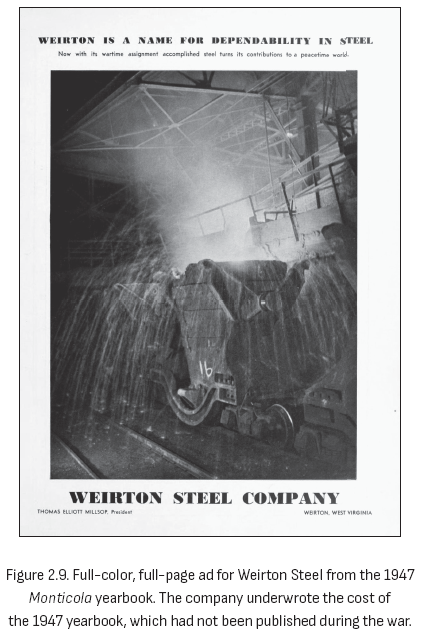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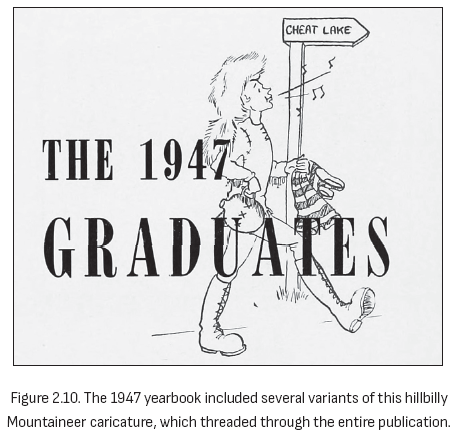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个山地人形象并非西弗吉尼亚大学所独有。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乡巴佬式吉祥物约瑟夫(Yosef)几乎在同一时间诞生,并通过类似的过程形成。约瑟夫最初是为1942年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年鉴《杜鹃花》(The Rhododendron)设计的一个形象,但真正流行起来是在1946-49年的战后年代,当时
约瑟夫在学生报纸《阿巴拉契亚人》(The Appalachian)担任客座社论作者。他使用山区方言写作,喜欢拼错单词。
1947年1月,Yoseff去掉了第二个”f”,变成了Yosef。1947年11月22日,大学举办了约瑟夫先生和夫人比赛。获得这些头衔所需的技能包括呼唤猪和鸡。
1948年3月12日《阿巴拉契亚人》版面上的一张照片首次提到约瑟夫作为山地人队吉祥物。这张照片称他为永久的大一新生。
1949年,48岁的二战老兵约翰·盖夫里奇(John Geffrich)成为最早的约瑟夫吉祥物之一。盖夫里奇帮助建立了男性本科生扮演留胡子、穿工装裤、叼烟斗、戴草帽男子的传统。
显然,阿巴拉契亚州立山地人队和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队一样,在二战后的几年里都乐于玩味典型的乡巴佬形象。然而,与约瑟夫不同的是,到1940年代末,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已经身穿鹿皮装十年了。当时涌入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退伍军人渴望扮演山地人,但他们选择了更像约瑟夫的乡巴佬版本,穿着工装裤、法兰绒衬衫和软帽。这种装扮与更广泛的流行文化中的乡巴佬形象密切相关,这一形象不仅在那个时代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中复制,也以其他形式出现。1946年秋和1947年秋返校周末的花车和兄弟会房屋装饰都以乡巴佬山地人为特色。但不仅仅是希腊会员在竞相展示他们能设计出最巧妙的乡巴佬身份展示。三一堂(Trinity Hall)的独立学生决心与更有特权的同学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以赢得最佳返校装饰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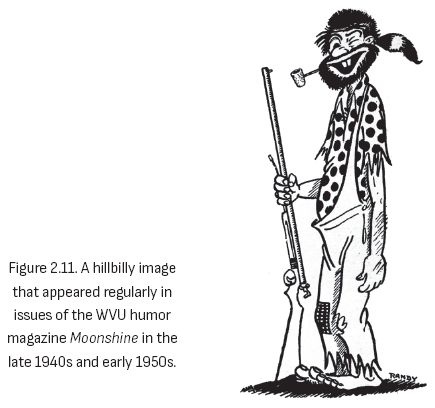
他们成功了:三一堂凭借1947年返校装饰获得了第二名,他们在房屋外部安装了一个巨大的山地人脸,能说话、抽烟斗,还能间歇性地吐烟草([图2.12])。由于三一堂的许多住户都是工程专业学生,或者在战争期间有机械方面的技术经验,这让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精心设计的装置,他们在一套规格说明中详细规划了所需材料以及山地人脸的建造和操作步骤。
六十年后,三一堂的前住户们仍然为这一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在2007年的同学聚会上,他们中的一群人讲述了这个获奖展示是如何诞生的幕后故事。
大卫·哈撒韦(DH):汉克·辛谢尔伍德(Hank Hinshelwood)……他去了查尔斯顿,把这一切都画了出来。他和鲍勃·里格斯(Bob Riggs)。他们……他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在前廊上方有一张山地人的图片,叼着一个正在冒烟的玉米芯烟斗,还有我们录制并通过扩音器播放的对话,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清清嗓子,然后吐。我们有一个人坐在楼上大厅里,浑身被水淋湿,用一根绳子绑在那里一个弹簧式水龙头上,你知道,当他听到”吐”的时候,他就会拉下把手,向前院吐出一大股水。
但我们需要一个大框架……来建造、支撑那个山地人。我们决定让它每个方向大约20英尺。你看过那些照片了。而Tom Ferris……[对Tom说]现在Tom你纠正我,如果我说错了——
Tom Ferris (TF): 矿务局提供的管子。
[笑声]
DH: Tom,Tom Ferris在Field House那边的美国矿务局工作。他说,“嗯,我们院子里堆了很多管子……一英寸半的管子,我们可以把它弄到那里。”……Tom说,他认识那里的看门人,而且……在换班之前,Tom说他总是洗澡。所以,他在11点过后在淋浴间里待大约十分钟,于是我们弄到了Jim Thoms的车,他有一辆大型敞篷轿车,我们把车开到Beechurst Avenue,老Field House旁边,停在矿务局前面。
然后Tom下车……车主……他真的很担心。我想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盗窃![笑声]
DH: Tom上去把那扇大门推开,你知道,走进去按下那个大开关,打开了所有的泛光灯!
[笑声]
DH: [笑]嗯,车主开始发动引擎,他现在就要离开了。Ferris说,“不,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在黑暗中到处移动会可疑!你知道,警察路过看到我们打开了所有泛光灯,搬运管子,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很明显,为这些来路可疑的装饰赢得奖项,对战后Trinity Hall的居民来说是纯粹胜利的时刻,证明他们不仅能与希腊兄弟会竞争,而且能用他们的智慧和机械技能击败他们。在很多方面,通过建造这个典型的山地人形象,Trinity Hall的男生们成为了山地人,既完全融入了大学社区,也展现了山地人的价值观——独立、机敏和生存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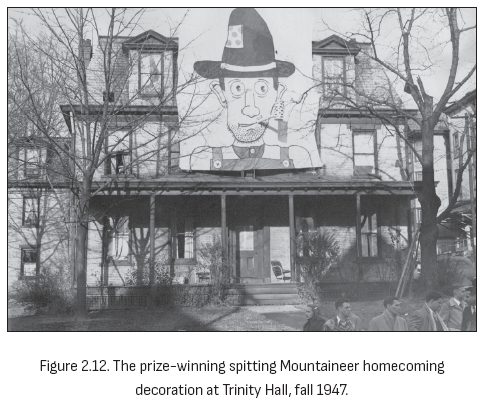
他们试图在1948年返校节重复这一壮举,当时他们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机械山地人,模拟砍掉一只斗鸡的头,因为返校比赛是对阵南卡罗来纳大学([图2.13])。在这些人物后面,他们在床单上画了一幅乡村场景的壁画,覆盖了整个前廊,前台阶上方画了一个户外厕所;要进入Trinity Hall,你必须穿过厕所进入。
在2007年的重聚会上,他们回忆起完成这项工程所需的工程技巧:
David Hathaway (DH): 我记得……驱动整个装置的引擎是220伏的。Trinity Hall里没有这个电压,而且……他们拿着大鳄鱼夹进到地下室,把它接到城市电表那一侧的线路上——
Howard Atkinson (HA): 他们免费得到了220伏电压!不用花钱——
DH: 不用花钱,就能运行那个。
HA: 那东西一直运转。我们前几天还在说,如果你记得的话,有人被指定一直守卫着。日夜守着那个东西,因为有很多人……嫉妒那个东西,或者就是足够顽皮想要破坏它——
Nello Antonucci: 是兄弟会——他们总是赢得奖项。
DH: 是的,没错。而我们,我们在赢得……奖项的那一年打破了局面。
我们再次看到,Trinity Hall的男生们通过与兄弟会对立(并积极竞争)来定义自己,并凭借他们的天生智慧和规避法律的意愿将自己定位为优越者。这样,他们的故事与欺骗者故事的悠久传统相吻合,特别是那些关于乡下人战胜试图贬低他们的人的流行故事。就像Doddridge笔下的拓荒者一样,Trinity Hall的居民给兄弟会的花花公子们狠狠地一拳,并用这一拳提醒他们,他们不仅理解而且怨恨,并会积极抵制基于社会阶层的贬低。只是这一次,这出戏剧在校园里上演——而且更有意识地定义了成为山地人的意义。

然而,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Trinity Hall的男士们致力于为自己定义山地人形象。战后年代见证了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非常积极和充满活力的努力,他们玩弄山地人的形象——尽管(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大学在十年前就已经将这一形象正式化和界定化。1947年返校节后,一群学生决定下一个比赛日将成为山地人日。1948年《Monticola》年鉴中的一张照片清楚地显示了Webb的《Mountain Boys》连环画的影响(图2.14);这些男士特意打扮成那个非常具体的乡巴佬形象,下方”Mountain Boys”的标题更强化了这一点。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张照片是刻板和贬低的,但事实上,通过装扮成Mountain Boys,这些男士展示了他们的文化素养。《Esquire》杂志当时将自己定位为相对高雅的男性刊物(尽管其穿着暴露的女性照片可能会让人对这种评价产生怀疑),只有那些熟悉该杂志常规栏目(包括Webb的《Mountain Boys》连环画)的人才能理解这身打扮的笑点。这些男士远非简单地接受和反映更广泛的乡巴佬文化观念,他们实际上在积极地抗争:他们的服装展示了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使他们能够对《Mountain Boys》身份提出比普通《Esquire》读者更有效的主张。
在1947年第一个山地人日,男学生被鼓励打扮成乡巴佬以激发学生对球队的支持(当然,女性仍然被要求穿裙子、丝袜和高跟鞋)。显然,这项活动相当成功,Mountain Boys携带的大多数酒壶不仅装满了真酒,而且在比赛期间和之后都被喝光了,因为一种无序的精神席卷了校园。在某些方面,管理层对返校退伍军人缺乏控制的最大担忧在第一个山地人日得到了证实。我父亲喜欢讲述他的一位教授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当时我参加了由James Paul Brawner教授的美国文学课……他是英语系主任……在山地人日之后的星期一,他明显不安地来到班上。他就”文明的薄弱外表”向我们讲了大约十五分钟。他觉得他在星期六观察到的情况可能会使大学生活倒退几十年……不用说,这次活动对学生群体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事实上,山地人日在1947年之后的每年秋季都成为一项非官方的、由学生组织的活动,并最终被大学接管,重生为现在所庆祝的山地人周。根据西弗吉尼亚大学对该活动的官方历史,山地人日”是在1947年构思的,作为一项激发更多学校精神的活动。最初的周末从西弗吉尼亚大学对肯塔基大学橄榄球比赛前一晚在旧运动场举行的集会开始。比赛后,举行了一场要求穿山地人服装的舞会,并为最能代表真正山地人的服装颁发奖项。“显然,官方历史已经净化了对第一个山地人日的描述。正如我父亲对这一描述冷静地评论:”关于这一周的在线历史非常有趣,但遗漏了最初庆祝活动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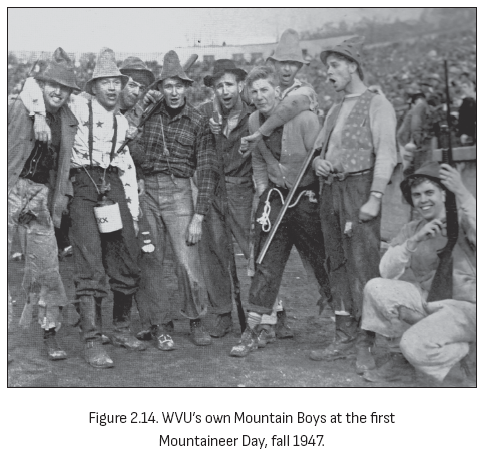
“最初的庆祝活动”具有Mikhail Bakhtin狂欢理论的所有元素——一个人们可以暂时参与颠覆性甚至怪诞行为的空间。在狂欢氛围中,通常的社会规则不仅被抛弃,有时甚至被颠倒:每个人都被要求参与通常被禁止的行为。第一个山地人日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它具有更容易识别的狂欢形式的所有元素,比如新奥尔良狂欢节:夸张的服装、酗酒和整体的不良行为。正如我父亲的邮件所暗示的,管理层随后进行镇压的事实是该活动成功的最明显标志。如果Brawner博士读过Bakhtin的作品,他至少会在理论上理解,通过暂时抛弃社会规范,狂欢化起到强化这些相同社会规范的作用。一旦无序之日结束,参与者预计将再次循规蹈矩,就像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狂欢节后进行圣灰星期三和大斋期的庄严仪式一样。
尽管—或者很可能正是因为—校方对第一届山地人日的谴责,它成为了一年一度的传统。1949年,一位摩根敦的记者声称”不完全满意大学生们在将山地人描绘为’穷苦白人垃圾’时所展现的原创性和足智多谋,这些人显然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拿着目录册去户外厕所上。“显然这位作者没有理解学生们在表演山地人身份时所进行的深层演绎。1951年6月版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公报》将山地人周末(现在已经延长到不止一天)描述为”学生们为自我娱乐而留出的”庆祝活动。公报中的照片和说明都表明,四年后,这一传统已经稳定下来并发生了转变。山地人周末成为了一项既定活动,但文字表明大学仍希望与之保持距离:这是一项学生自发的、为”自我娱乐”设计的活动,这一描述反映了校方对其作为一种不成熟、放纵活动的厌恶。七十多年后,大学仍然延续这一传统,这一事实表明校方最终认识到,在庆祝”山地人”身份的活动中存在某些潜在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希望由自己来定义这一身份,并确保它尽可能与乡巴佬形象脱钩。
第一届山地人日的年鉴照片显示了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的这种转变(图2.15)。虽然照片中仍有一些穿着《山地男孩》风格服装的男子,但我们也看到了更具拓荒者特征的人物,身着鹿皮衣、头戴浣熊皮帽。重新想象和扮演山地人似乎成为战后学生,特别是退伍军人重新融入大学生活和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这似乎特别适用于三一堂的一些居民,他们以前因为种族和阶级背景而被排除在山地人身份之外。将山地人描绘为一个讽刺形象、一种夸张,为其他人扮演这一角色打开了空间;而将其描绘为肌肉发达的拓荒者则不然。在许多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继续潜藏在关于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应该是谁、应该是什么,以及他或她在代表该州时应尽什么职责的辩论之下。有些人认为山地人代表了自由思考、打破常规的乡巴佬—一个从与压迫他的权威对话甚至破坏权威中获得极大乐趣的个体。另一方面是那些将山地人视为天生温文尔雅的荒野居民的人,认为他凭借源于艰苦经历的常识和智慧,成为领导者和粗犷同胞的榜样。

如果这场辩论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应该的:二十世纪中叶乡巴佬与拓荒者山地人之间的斗争在许多方面呼应了十九世纪初占地者/荒野居民的辩论。我们又回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和戴维·克罗克特,乡巴佬处于杰克逊那一端,拓荒者处于戴维·克罗克特那一端。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推进,这两个人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乡巴佬版本被消除了,拓荒者山地人成为官方认可的、有人可能会说是被驯化的版本。这一转变呼应了乔治·海伊在20世纪40年代拒绝使用”乡巴佬”一词来描述大奥普里剧院,以及霍尔特州长希望微观管理西弗吉尼亚州的形象以远离乡巴佬刻板印象的愿望。但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导致了乡巴佬山地人的消亡:华特·迪士尼工作室,其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戴维·克罗克特,印第安战士》提供了一个标志性的流行文化版本的强悍拓荒者,令人无法抗拒(图2.16)。正如艾伦·巴拉所写:
直到迪士尼工作室的《戴维·克罗克特,印第安战士》于1954年末在ABC播出(该电视台与迪士尼共同制作了这些剧集),戴维·克罗克特才被人们遗忘,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但这位老猎熊人转国会议员再转民间哲学家已经陷入了某种低谷期。在迪士尼之前,他曾是大约二十多部故事片的主题,但其中大部分是在无声电影时代拍摄的。最接近近期主要电影的是1950年乔治·蒙哥马利主演的《戴维·克罗克特,印第安侦察兵》。
在他1954年的著作《被遗忘的拓荒者:戴维·克罗克特的一生》中,马里昂·迈克尔·纳尔通过对克罗克特拓荒时代逝去所代表的纯真丧失的哀叹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几乎是在回应纳尔一般,迪士尼的前三集,以1955年初的”戴维·克罗克特在阿拉莫”结束,不仅使克罗克特重焕活力,而且将他变成了电视史上第一个主要的商品化狂潮。
迪士尼的克罗克特故事作为其每周《迪士尼乐园》选集节目的一部分播出,开启了玛格丽特·J·金所说的”克罗克特热潮”。60 这档电视节目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其主题曲——由比尔·海耶斯录制的《戴维·克罗克特之歌》——在公告牌排行榜上停留了二十周,其中五周位居全国第一。61 正如肖恩·格里芬指出的,“众多其他艺术家(包括田纳西·厄尼·福特、埃迪·阿诺德、伯尔·艾夫斯、米奇·米勒,甚至是好老费斯·帕克本人[在迪士尼剧集中扮演戴维·克罗克特的演员])都录制了自己的版本……在六个月内,所有版本的唱片总销量接近700万张专辑。”62
尽管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所戴的浣熊皮帽在1937年就成为吉祥物官方服装的一部分,但它的重要性是通过”克罗克特热潮”得以巩固的。尽管许多当代记载和历史表明,实际上克罗克特很可能从未戴过浣熊皮帽。在《迪士尼乐园》播出克罗克特剧集后的几个月里,仿制浣熊皮帽的销量激增。63 在迪士尼的呈现中同样突出的还有鹿皮衣、软皮鞋和步枪,这些至今仍是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标准装备。
众多学者推测,为什么克罗克特在历史的这一节点成为典型的边疆人,取代了此前更知名、更受推崇的丹尼尔·布恩。64 金认为”迪士尼的克罗克特,这个有尊严的普通人——和蔼可亲、睦邻友好、关心公民事务、积极向上,简而言之,以他人为导向——使他成为1950年代最合适的理想人物,“65 而艾伦·纳德尔推测”像他主要观众的父母一样,[克罗克特]是一名退伍军人(印第安战争),像他们的总统一样,他进入了政治生涯。“纳德尔进一步指出,迪士尼对克罗克特在阿拉莫之死的呈现”以冷战战士的形象塑造了克罗克特的记忆,因’自由’事业而被吸引到异国土地上。“66
在他1940年关于克罗克特持久传奇的开创性文章《六个戴维·克罗克特》中,沃尔特·布莱尔描述了克罗克特人格的六个不同变体,这些变体在克罗克特生前和死后被普及并用于政治利益,其中大多数与”第一个克罗克特”,即克罗克特本人几乎没有相似之处。67 布莱尔描述了后来克罗克特化身所附加的特质:他是一个乡下人,虽然书本知识不多,但常识丰富;一个”不仅愚蠢和滑稽,而且恶毒”的乡野之人;一个坚定独立的”土布先知”;一个”本能地逃离文明的无远见的孩子”;以及”初期的穷白人……内含衰败因素。“68 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戴维·克罗克特既为乡巴佬山地人提供了模板,又以高贵边疆人的形式为他提供了完美的解药。
因此,乡巴佬版本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在克罗克特热潮后几年就走向终结,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乡巴佬山地人最终在1957年5月中旬被正式”取缔”,当时学生会主席罗杰·汤普金斯写信给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欧文·斯图尔特,宣布学生政府执行委员会通过以下决议。汤普金斯在这里对理想山地人的描述显然来自迪士尼的戴维·克罗克特:
鉴于执行委员会认为山地人的真正精神体现在浣熊皮帽和鹿皮制服上,并且鉴于我们认为对山地人精神和传统的自豪感和尊重确实有明确的需要,我们特此决议,所有涉及或暗示将山地人解读为”乡巴佬”的标志、符号和形象的销售,即带酒壶、毡帽、赤脚和破烂衣服的形象,应立即停止,因为这些使用会引发对我们山地人精神和传统的不良和贬低的含义。69
斯图尔特热情地表示同意,在回复汤普金斯的信中说:“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可取的一步。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寻求所有学生组织的支持,以实现这项决议的精神。”70 他立即写信给校园中心(山地人会堂)的鲍里斯·贝尔普利蒂和校园书店的露丝·罗宾逊,请求他们合作”结束将山地人表现为’乡巴佬’的做法。“71 斯图尔特进一步要求立即停止”销售将山地人解读为’乡巴佬’的商品”,72 这引发了罗宾逊相当不满的回复,她指出虽然她会遵守,“我检查了我们的滑稽山地人印刷商品库存,发现我们的损失超过300美元。”73 显然,乡巴佬山地人的消亡既有商业影响,也有文化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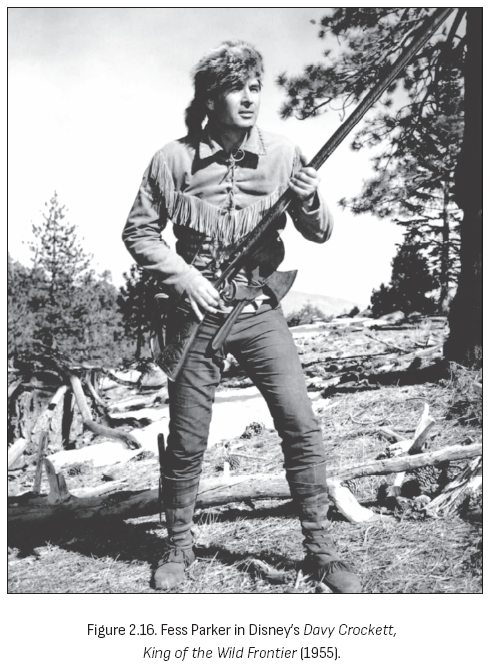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们和Stewart实际上只是用另一个大众媒体塑造的阿巴拉契亚身份形象替换了原有的形象:Paul Webb的《山地男孩》中的滑稽乡巴佬(hillbilly)版本被迪士尼的Davy Crockett所取代。而边疆人(frontiersman)山地人的定义更加狭隘,相比乡巴佬山地人留下的游戏和颠覆空间要小得多。然而,乡巴佬和边疆人确实共享独立和反叛的特质。正如Griffin所指出的,迪士尼版本的Crockett并不是第一个被描绘成永远孩子气、容易感到无聊的冒险家的版本;相反,这种将Crockett描绘为”自由漫游、热爱玩乐的暴发户的形象可以追溯到更早于这些电视剧集的时期”,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Crockett滑稽年鉴。这些年鉴将Crockett描绘成一个”自主的、自由漫游的青少年”,他是”放荡的、边缘的、野性的”。因此,用边疆人替代乡巴佬,赋予了边疆人山地人以体面,同时仍然允许偶尔的野性行为自由。但是用Davy Crockett边疆人替代乡巴佬延续了山地人必须是白人的观念。也许并非巧合的是,1954-55年的Crockett热潮恰好在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裁决后几个月爆发。Crockett热潮可能部分是由于白人身份不再等同于美国身份的焦虑所推动,使白人观众能够重新连接一个据称不受种族紧张局势困扰的边疆过去,并重新确立美国历史的白人至上主义版本。
到1950年代末,这种对消失中和已消失的边疆过去的怀旧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可以追溯到Doddridge的《荒野居民与花花公子的对话》,经过杰克逊时代,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阿巴拉契亚的倡导者恳求外来者在山区白人文化被现代性不可逆转地玷污之前保护和保存它。随着1950年代过渡到动荡的1960年代,这种怀旧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也更加复杂。随着美国卷入越南冲突,以及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一个手持步枪的年轻人的形象从怀旧转变为令人不安地唤起当下。这个武装的山地人是爱国者,为他的国家而战吗?还是一个愤怒而危险的年轻人?山地人身份的双重根源将在这个时代发生冲突——无论是比喻上还是实际上。
1960年代的WVU山地人
大学的举措在1950年代末将Davy Crockett式的WVU山地人神圣化是完全成功的:六十多年后,山地人的外观或装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乡巴佬版本——至少在外观方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他的影响以无拘无束、离谱行为的形式挥之不去,这将在第5章中讨论。
在许多方面,山地人外观和装备的这种转变体现在Thomas Haines在1960年代末创作的艺术作品中,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一位发育障碍青年,是该市信仰工作坊(Faith Workshop)的客户。Haines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自学成才艺术家,1967年,信仰工作坊与Kanawha县智力迟缓儿童协会(现为三河区Arc)合作出版了一本Haines作品的小册子,书名不幸地定为《男童Tom眼中的西弗吉尼亚》。该书似乎是作为筹款活动而创作的。该书的序言指出,Haines对”为西弗吉尼亚插图一本关于’他们骄傲的州’的书的兴趣促成了这部经典作品。工作人员……欣赏他的作品并希望展示它。”
Haines的插图比我可能做的更简洁清晰地总结了山地人形象的乡巴佬版本和边疆人版本之间的区别。根据Haines的说法,“乡巴佬(Hillbillys)留胡子并射击枪支”(图3.1)。西弗吉尼亚边疆人也携带步枪,但这个形象穿着鹿皮衣并戴着浣熊皮帽,据推测是刮过胡子的(图3.2)。案件结束。
Haines 1967年的插图捕捉了WVU山地人在1960年代整个十年间所呈现的一系列形象变化,这十年见证了山地人的步枪被拿走,但也在其结束时迎来了第一批留胡子的山地人之一。虽然WVU山地人形象的这些方面在这个时代继续保持流动性,但其他方面在校园内委托和竖立山地人雕像的努力中变得固定下来,这完全是字面意义上的固定。这项工作于1950年正式开始,但征集设计和筹款活动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持续进行,最终在1971年10月在Mountainlair前揭幕了标志性雕像(图3.3)。
这一过程漫长而充满争议,正如学生事务助理副校长戈登·索恩(Gordon Thorn)在其著作《山地人雕像》(The Mountaineer Statue)中所述。索恩是推动雕像项目实现的最重要力量,他指出到1950年代后期,该项目陷入了关于雕塑设计和位置的争论中,但有一点”达成共识的是斯图尔特校长提出的想法,即雕像应该帮助消除西弗吉尼亚州的’乡巴佬’形象。“不仅山地人(Mountaineer)乡巴佬形象已从校园书店的库存中清除,现在还将竖立一座拓荒者山地人雕像,以确保乡巴佬形象被彻底驱逐。
雕像的建造过程贯穿整个1960年代,这是一个巨大变革的十年,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西弗吉尼亚大学都是如此。虽然在1950年代竖立一座持步枪的年轻人雕像似乎没有争议,但到1971年雕像实际揭幕时,一个持步枪的年轻人形象已经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联想,因为越南冲突在1960年代不断升级,强制征兵制度及其抵抗运动也重新启动。从该过程的最早阶段来看,设计方案似乎就包括了步枪。唐纳德·德卢(Donald DeLue)是最终被选中的雕塑家,他创作了这座标志性雕像,他将模型中的山地人描述为一个”坚韧粗犷的类型”,他”坚守自己性格中坚韧诚实的美德”——这些美德包括”想象力、勇气、正直和信念。“到1960年代,德卢列举的这些形容词呼应了150年来对边远地区居民、拓荒者和山地人的历史描述,从约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开始,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的克罗克特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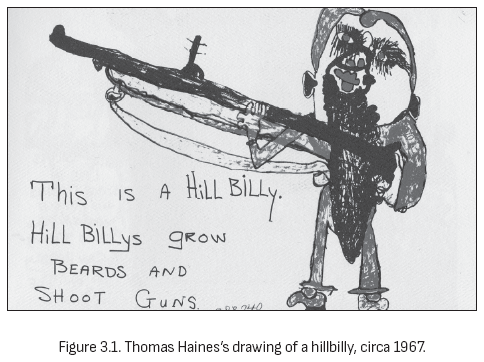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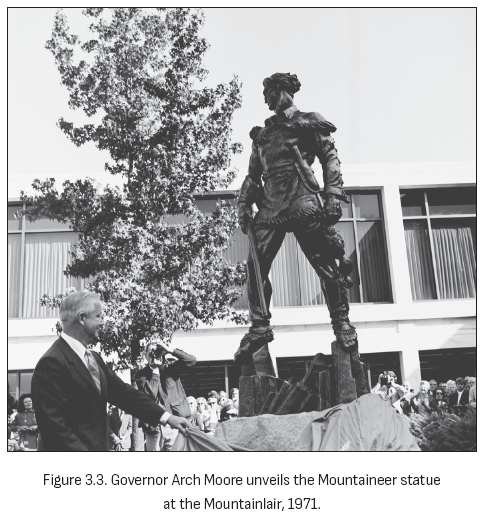
索恩关于雕像历史的著作描述了1960年代期间阻碍雕像进展的诸多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最终雕像的放置位置以及完成工作所需的资金。然而,尽管确保雕像设计和创作的努力是在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迅速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从1962年的9000名驻军增加到1969年的50万,征兵范围也在扩大,让越来越年轻的人手中握上了真正的步枪——包括许多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年轻人——但对于步枪的存在似乎根本没有任何争议。可能是我的郊区成长经历让我觉得奇怪,在那个年轻人拿着枪每天在越南死去、政治暗杀震撼全国、许多美国人突然对自己叛逆的孩子感到恐惧的十年里,竟然没有人质疑描绘一个持枪年轻人的智慧。
步枪被纳入而从未受到质疑这一事实表明,这个形象更多是该州失落和令人惋惜的过去的象征,而不是对更加混乱的现在的反映。可以肯定的是,雕塑家德卢希望山地人雕像通过提醒观众祖先的拓荒精神来激励他们努力提升自己。雕塑家指出,山地人”站在巅峰之上,俯瞰整个世界”,他希望雕像能提醒观众这个崇高形象的美德,即前面提到的”想象力、勇气和正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卢将这些美德与当下的混乱对立起来,他写道:“这些是我们希望在当今这个时代唤起人们记忆的美德,在这个时代,许多人在低谷中挣扎。”德卢在1967年12月写给山地荣誉组织(Mountain Honorary)的信中表达了这些观点,在这一年里,美国许多城市的贫民区发生了起义,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越战抗议活动,旧金山的爱之夏吸引了嬉皮士们响应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号召”打开思想,融入时代,退出主流”。这些近期事件无疑代表了德卢所看到的”许多人正在挣扎”的”低谷”。
德卢的话不仅为山地人雕像蒙上了怀旧色彩,也带有反动色彩:这个类似戴维·克罗克特的山地人唤起了德卢列举的美德,但也清楚地表明山地人有一把步枪,而且他不怕使用它。我并不是说德卢或大学管理层有意将山地人雕像塑造成一个威胁性的形象。但推进德卢设计方案的决定似乎确实受到了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即年轻人需要一个可见的提醒,提醒他们”真正的”山地人美德,以及”更好的”时代,那时世界(据称)更加简单。
然而,到1971年山地人雕像揭幕时,西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大学已经深受越南冲突的影响。事实上,这十年的第一位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1960年的山地人威廉·麦克弗森——毕业后参军,并于1965年12月在越南阵亡(图3.4)。麦克弗森的堂兄罗伯特·R·理查兹回忆他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他似乎没有任何顾虑;事实上,他能惹的麻烦越多,他就越高兴……比尔是一个外向且富有创造力的人,甚至认为规则只是为了创造例外的机会”——这是麦克弗森之前和之后许多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哲学。理查兹在一篇在线纪念文章中写道,麦克弗森的淘气性格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当得知他毕业后通过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获得了军衔并打算把军队作为职业时,真是令人惊讶!像比尔这样富有创造力、外向、打破规则的人进入军队?!这似乎是一场灾难的配方。”但事实上,正如理查兹后来从一位认识麦克弗森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教授那里了解到的,“比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外向的领导者。”到这个时候,麦克弗森既能成为恶作剧者又能成为坚定领导者的能力应该不会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山地人这个形象经常体现这些看似矛盾的品质。
这十年的第一位山地人成为那个年代最具决定性和分裂性冲突的受害者,这当然是悲剧性的。但遗憾的是,考虑到西弗吉尼亚年轻人在整个战争中遭受的巨大生命损失,这也并不特别令人惊讶。西弗吉尼亚州在越南冲突期间的人均死亡率是所有州中最高的:1,182名西弗吉尼亚本地人丧生,人均死亡率为每万名居民8.41人,而其他州的全国平均水平为每万名居民5.89人。这场冲突影响了每个人。也许正因为如此,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的反战情绪在这十年后期之前一直很低沉,直到越南和国内发生的事件,如美莱大屠杀的揭露和肯特州立大学的国民警卫队枪击事件,使得即使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质疑美国的介入是否值得造成如此多的死亡和动荡。当山地人雕像于1971年竖立起来时,一个拿着步枪的年轻人的形象唤起了士兵和反战抗议者的双重意象。这个整洁的拓荒者是爱国者还是反叛者?山地人的根源使他被以两种方式看待。

1960年代对西弗吉尼亚人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历史意义:阿巴拉契亚地区再次被渴望帮助(和剥削)该地区穷人的外来者”发现”。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选举期间大力争取西弗吉尼亚州和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选民;记者查尔斯·库拉尔特在1965年通过他的”阿巴拉契亚的圣诞节”电视特别节目揭露了农村穷人的困境;林登·约翰逊的反贫困战争通过一个名为”美国志愿服务”(VISTA)的国家服务项目,将许多年轻志愿者带到该地区以对抗贫困。
这些干预措施都不是特别新的。在许多方面,这些努力反映了1930年代的努力:库拉尔特对贫困的电视报道类似于大萧条时期农业安全管理局项目的阿巴拉契亚贫困照片,而VISTA志愿者则与二十世纪初外来者在阿巴拉契亚定居学校所做的传教工作相似。但正如广播、电影和连环画在一代人之前向阿巴拉契亚人展示了外来者对他们的看法一样,在1960年代,阿巴拉契亚人能够通过电视见证这些外来者的看法,无论是通过库拉尔特这样的纪录片,还是通过非常受欢迎的情景喜剧,这些喜剧刻画了刻板的乡村土包子,如《贝弗利山人》、《安迪·格里菲斯秀》、《衬裙交界处》和《绿色英亩》。乡巴佬(hillbilly)再次无处不在,成为一个被嘲笑或怜悯的形象,具体取决于语境。
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计划特意将阿巴拉契亚地区纳入其中,以向批评者保证这项努力不仅仅关注城市(即非裔美国人)贫困问题。约翰逊知道,为了实现他在民权方面的更大目标,他需要表明联邦政府既关注并积极帮助农村白人,也关注城市黑人。这项努力的成果之一是1965年成立了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ARC),进而创建了阿巴拉契亚这个可识别且统一的地区(至少在联邦层面如此)。在许多方面,阿巴拉契亚在ARC定义它之前并不存在,该地区的边界至今仍在变化。确定哪些州以及这些州中的哪些县属于ARC对阿巴拉契亚的定义,不仅仅基于地理位置,还基于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这种关注带来的积极成果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阿巴拉契亚研究,它汇集了来自众多学科(历史、文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教育等)的学者,所有人都对解决该地区的特殊关切和需求感兴趣。经过两个世纪主要由外部人定义之后,阿巴拉契亚人终于有了一个回应刻板印象和构建自己关于阿巴拉契亚身份认同观念的论坛。
虽然1960年代被永久铭记为”性、毒品和摇滚乐”的十年,但在阿巴拉契亚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情景略有不同。这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及其政治没有成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当我开始研究这一时期的《山地人》杂志时,有人告诉我西弗吉尼亚并未深受1960年代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人呼应了Mary Beth Bingman的观点,她在写到1970年代的反露天采矿运动时指出,“我们在1972年所拥有的模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国际革命斗争——在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上都不适合阿巴拉契亚的背景。”
所有这些都被夸大了。这十年中第一位山地人William McPherson在越南阵亡这一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确实深受战争影响。毫无疑问,许多在1960年代就读该大学的年轻男子去那里正是为了利用大学生延期征兵的优势。许多其他年轻的西弗吉尼亚男子无疑是自愿入伍的,因为军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摆脱贫困的现成途径之一。如果你上不起大学,军队是一个可靠的高中后选择,而且许多西弗吉尼亚人将服兵役视为家族传统。如果你能负担得起大学,那么你就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正如在1960年代末就读于马歇尔大学的朝鲜战争老兵Bob Cassell所说,那时西弗吉尼亚的大学生们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你去上学,保持清白,接受教育,比你的父母做得更好。”相信大学是自由和公开辩论的重要场所是一种奢侈,这种观念”侵扰了当时学生所理解的教育。”
因此,越南战争时期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是复杂的。但校园里确实存在反战活动,并在1970年4月底和5月初美国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后在摩根敦达到顶峰。该大学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民主社会学生会(SDS)分部,其成员——虽然人数从来不多,影响力也肯定从来不大——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校园内的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组织起来并为他们的权利进行游说,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更广泛的民权和妇女运动。
如果说1940年代和1950年代见证了山地人身份从暴发户乡巴佬到粗犷开拓者的转变,那么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则见证了山地人身份的又一次转变。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固有的叛逆和反权威性质使他成为1960年代学生活动家的理想榜样。当然,留着胡子赤着脚的山地人版本很容易被重新想象成一个嬉皮士。就在大学镇压了乡巴佬山地人并用高贵的开拓者取而代之仅仅几年后,它就以抗议者和嬉皮士的形式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捣乱学生。
在整个美国,1960年代的社会动荡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经历。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如同其他地方,学生们挑战了长期确立的传统,即大学在与学生的关系中充当”代替父母”的角色——字面意思就是代替父母。学生山地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总是自由的:大学以”代替父母”的名义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西弗吉尼亚大学新兴的SDS分会发出的一张巧妙地以”爹政部门”为标题的传单直接挑战了”代替父母”制度:
你来到大学时以为自己将成为学生和学者成人社区的一部分……我们将就大学的运作方式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些答案是否接近你对大学应有样子的设想。
为什么大学采用了代替父母(in loco parentis)的政策?这是大学与学生之间的正确关系吗?责任是如何获得的?是通过被控制?还是通过控制自己的生活?18
传单接着质疑了大学一些具体的代替父母政策:禁止学生在宿舍和校外住房中拜访异性学生;要求女学生在宿舍居住的时间比男学生更长;尽管80%的学生在公投中投票支持,但不在Mountainlair供应啤酒。
虽然这些例子可能暗示学生只是在寻求饮酒和性行为的许可,但传单也提出了关于学生会的目的和效力以及消费者问题的重要观点——“为什么州立大学书店对学生用品的收费比其他商店更高?”传单最后将所有这些问题置于更大的权力和民主背景下,不仅是在校园内,而是在整个美国:
有一群学生关注这些问题,并有兴趣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大学,在那里学术和个人自由不会受到行政官僚机构的威胁。学生通过在大学中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参与大学治理,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分会。我们有兴趣在大学社区和当代美国社会中带来改变,以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和福祉。19
也许在越南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传单中关于校园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的问题:“为什么ROTC要设在校园?军事训练与追求知识和智慧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在教导无条件的服从而不是公开质疑、自由探究吗?”20
正是这类问题使全国各地校园的SDS分会被列入FBI的监视名单。Scott Bills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期间是一名学生活动家([图3.5]),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并将他收集的反战和其他抗议材料捐赠给了西弗吉尼亚和地区历史收藏馆。收藏中包括FBI关于Bills参与西弗吉尼亚大学SDS分会以及他随后在校园成立的山地人自由党(Mountaineer Freedom Party)的报告。Bills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了这些记录,尽管FBI似乎最终认定他没有构成危险,但他被监视的事实表明联邦政府对学生活动家的潜在威胁有多么重视。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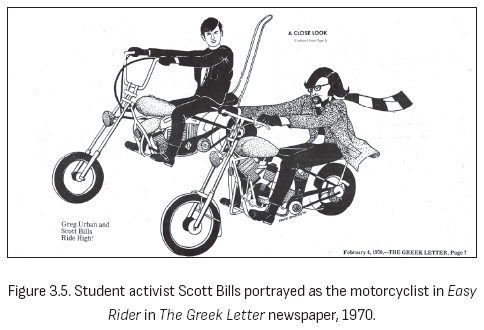
SDS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地方也很活跃:马歇尔大学学生活动家Al Miller于1965年宣布他打算建立马歇尔SDS分会,但该组织直到1968年秋天才正式成立,当时它寻求成为官方认可的校园组织。保守派学生和社区成员都反对这一努力,但马歇尔大学的新任校长Roland Nelson——虽然个人并不支持SDS——认为没有办法在不侵犯该组织言论自由权的情况下否认其合法性。当地的反共人士在当地媒体上大量表达对”校园红色危机”的担忧,以”号召他们的支持者警惕”马歇尔大学的”颠覆性暗流”。他们的努力似乎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导致一些之前不关心的学生支持SDS,给大学行政部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1969年3月,Nelson批准了该组织的请求,他说他”基于大学是知识和探究的场所这一基本原则行事,在这里对立的观点可以公开呈现和研究。“马歇尔大学的辩论引起了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Robert Byrd的关注,他在《亨廷顿广告报》上撰文表达了对该组织的反对。Byrd声称SDS有”摧毁整个美国教育体系的蓝图。“Byrd写道,他担心SDS在成功渗透到不仅是大学校园,还有高中之后,会”利用[学校]作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革命化美国社会的手段。“22
远非革命化任何东西,西弗吉尼亚大学的SDS分会从未获得多少动力。事实上,到1969年春马歇尔SDS获得官方认可时,西弗吉尼亚大学苦苦挣扎的分会已经解散了。在他关于越南战争时期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激进主义和异议的详细历史中,Jeffrey Drobney指出”根据FBI记录,[西弗吉尼亚大学SDS分会]活跃成员不超过10到15人,并在1968年后停止运作。“23 在1969年10月1日《摩根敦邮报》的一篇文章中,Bills说”SDS因’陈词滥调’和糟糕形象而失败。“24
在SDS分会解散后,Bills和其他活动人士采取了”全球思考,本地行动”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名为”山地人自由党”的学生政府党派和活动组织。该组织的材料展示了它如何延续了西弗吉尼亚大学SDS分会的许多基本目标——一份题为”加入MFP”的小册子指出”代替父母(in loco parentis)的理念已经过时”,并呼吁承认”所有学生、教职员工的完整宪法权利”。25 这份小册子涉及了许多SDS”爹政”(Dadministration)传单中提出的相同本地关切,特别是关于书店价格和学生更有意义地参与大学治理的问题。然而,“加入MFP”小册子表达的关切比”爹政”传单更为广泛,包括”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支持葡萄抵制运动的纠察线”,以及”参与1970年4月22日的环境教学活动”——第一个地球日。MFP还对本地关切做出了重大承诺,不仅在校园内,而且在整个西弗吉尼亚州;小册子提到该组织参与寻求”充分的黑肺病立法”,以及在”1969年12月为联合矿工工会选举提供投票监督员”。26
然而,这些本地关切超越了政治层面。“加入MFP”小册子的整整一版专门呼吁西弗吉尼亚大学扩大其阿巴拉契亚中心,并创建阿巴拉契亚研究系([图3.6])。虽然这些要求框定在该组织关于民主的总体修辞中,论证这些努力将有助于”解决该地区殖民经济带来的问题”,但在这一具体主张之前的内容更多地关乎社区、文化自豪感和反叛态度:
曾几何时,被称为阿巴拉契亚的土地上居住着一群坚韧的人民,他们有着社区精神。当邻居建造新谷仓时,远近的人们都会前来帮忙。社区方块舞(square dances)、拼布蜜蜂会(quilting bees)和教堂社交活动提供了娱乐。山间回荡着小提琴和班卓琴(banjo)的声音。
那种自豪的文化如今所剩无几。同化政策和被压迫人民的破碎态度几乎消灭了过去的阿巴拉契亚。27
这无疑是对阿巴拉契亚的夸张和浪漫化的看法,而且在历史上这一时刻之前和之后都存在:对”自豪的文化”变成”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悲痛,让我们直接回到Doddridge的《丛林人》(Backwoodsman)以及他对那些”自由享受我们艰辛成果”并”盛宴,而我们却要挨饿”的花花公子(Dandies)和”大人物”的抨击。28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小册子对重振山地人身份的呼吁,从字面上讲,是与当时学生活动人士更大、更为人熟知的目标——结束越南战争——并列放置的。此外,“保护我们的阿巴拉契亚文化”的呼吁在小册子中获得的篇幅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单一主题。配合文字的插图包括州箴言Montani semper liberi!(山地人永远自由!感叹号为原文),以及班卓琴、小木屋、矿工镐和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式山地人侧影的图画。
山地人自由党这个名字本身大概就是为了将学生自由与州箴言及其”山地人永远自由”的主张联系起来。从视觉和修辞上看,小册子暗示眼前的学生关切和全国性关切与地区关切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植根于地区关切,而文字进一步表明,重新找回阿巴拉契亚祖先坚韧不拔的社区精神,是成为各类当代议题积极活动人士的第一步。
Bills本人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海报明确唤起了”高贵的拓荒者转变为政治家”的比喻:标语声称他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出生在木屋中”([图3.7])。在只有历史学家才有的先见之明中,Bills还想到要抢救并最终归档一个被破坏的竞选标语([图3.8])。这一版,他描述为”带有涂鸦的海报,来自Woodburn Hall(我想是)“,包括破坏者添加的短语没有父亲(without a father),因此更新后的标语变成了”Scott没有父亲出生在木屋中”。我喜欢想象Bills看到了这一添加的幽默之处,它如何将他原始海报上高贵的拓荒者变成了一个出身可疑的堕落山地人(hillbilly)。29
山地人自由党(Mountaineer Freedom Party),无论是在名称还是议程上,都明确致力于重新诠释山地人身份中那种不安分的、占地者/乡巴佬的特质。尽管其招募材料中使用了拓荒者山地人的形象,MFP 清楚地将山地人精神与行动主义和异议联系起来,复兴了 WVU 山地人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武装的先驱者/爱国者,而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反叛者。尽管山地人雕像和 MFP 都使用拓荒者形象来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山地人,但两者背后的意识形态却截然不同。正如 DeLue 的话所暗示的,这座雕像旨在遏制反叛,提醒观众回忆更高尚的拓荒时代,我们应该努力重拾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而 MFP 的山地人同样与过去的价值观相连,但这些是政治参与和反抗的价值观。同样是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的形象,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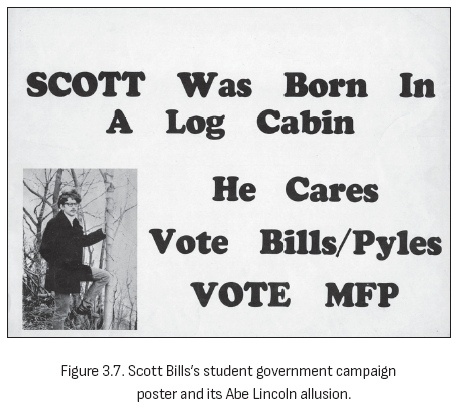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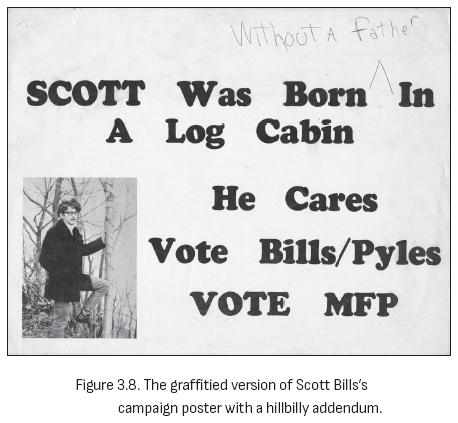
这确实是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在校园内关于 WVU 山地人身份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下一节将通过两位在此期间担任 WVU 山地人的人的经历来探讨这些关于山地人的竞争性观念,他们是 Doug Townshend(1969-70)和 Robert Lowe(1970-71)。
1970 年 4 月下旬,包括 WVU 在内的全美各地大学校园都开始升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以及其他传统的自由主义堡垒多年来一直是反战和其他学生抗议的场所,但随着越南战争的拖延以及政客们对反战运动和年轻人越来越充耳不闻(这正是尼克松总统著名地称学生活动家为”流浪汉”的时刻),全国更多校园都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1970 年 4 月初,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回答关于本州校园抗议者的问题时说:“如果需要流血冲突,那就让它结束吧。”1970 年 4 月 30 日,当尼克松下令美军入侵柬埔寨时,紧张局势升级,而他此前曾声称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在柬埔寨入侵前的几周,尼克松曾提议从该地区逐步撤军,显然是为了兑现结束战争的竞选承诺。
柬埔寨入侵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立即走上街头抗议,即使是在以前平静的院校也是如此。学生与校园警察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冲突很常见,广泛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驱散抗议人群的战术。在俄亥俄州,学生抗议在哥伦布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更北边的另一所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尤为激烈。1970 年 5 月 2 日,俄亥俄州州长 James Rhodes 谈到肯特州立大学的抗议者时说:“他们比褐衫队(brown shirts)、共产主义分子、夜行骑士(night riders)和治安团(vigilantes)更糟糕。他们是我们在美国收容的最坏的人。我认为我们面对的是美国历史上集结起来的最强大、训练最有素、最具战斗力的革命团体……我们要根除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只治疗症状。”说到做到,两天后,Rhodes 命令俄亥俄国民警卫队(Ohio National Guard)进入肯特州立大学校园,他们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和旁观者开火,造成 4 人死亡,9 人受伤。
肯特州立事件后,各地校园都爆发了抗议,包括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许多学校:除了 WVU 的抗议活动外,学生们还在莱克星顿的肯塔基大学示威,那里的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Air Force ROTC)大楼被烧毁;在雅典的俄亥俄大学,两枚燃烧弹被投向校园内的 ROTC 办公室;在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据报道超过 75% 的学生在罢课;以及整个地区的许多其他校园,包括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堡的麦迪逊学院、匹兹堡的卡洛大学、查塔姆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俄亥俄州的玛丽埃塔学院,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戴维森学院、利文斯顿学院和格林斯伯勒学院。那些可能感觉自己与亚洲的战争相隔绝的学生,再也无法忽视国内的战争。在几周内,全国超过两百所校园关闭,学生们在春季学期结束前被送回家。WVU 的学年日程比许多其他学校提前几周,因此肯特州立枪击事件发生的那一周——事件发生在周一——也是 WVU 的期末考试周,这意味着学生们即将完成学期。正是这一点,而非学生的冷漠,使得 WVU 对肯特州立枪击事件的反应相对温和。尽管如此,还是有反应的。
然而,在我对WVU这些事件进行任何正式研究之前,我从2015年采访的两位那个时代的前山地人吉祥物那里听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第一人称叙述。第一个叙述来自Doug Townshend,他从1969年春季学期到1970年春季学期担任WVU山地人(图3.9)。当我第一次听到Townshend的故事时,我并不知道他描述的事件是对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的具体回应;我更笼统地问他,在他担任山地人期间WVU校园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是美国各地校园动荡不安的时期。Townshend回答说:
“当时,我们有所谓的’嬉皮士’……然后……自由运动,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我记得我们发生了骚乱——摩根敦的学生骚乱,州警察行进到……是在Oglebay Circle那里吗?在Mountainlair前面?他们穿着全套防暴装备。而且,我——我们在那里观看,再说一次,我——在我所处的位置(作为官方山地人)是不参与任何事情的。我只是有兴趣观察。而且那是——他们在互相扔水球。我的意思是,基本上就是兄弟会对抗……‘嬉皮士’。”
Townshend在这个故事后补充说”他们担心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最初,Townshend的叙述证实了我对WVU的怀疑:它在越南战争时期并不是学生激进主义的温床,而是一个春季水球大战在转述中被夸大成全面”学生骚乱”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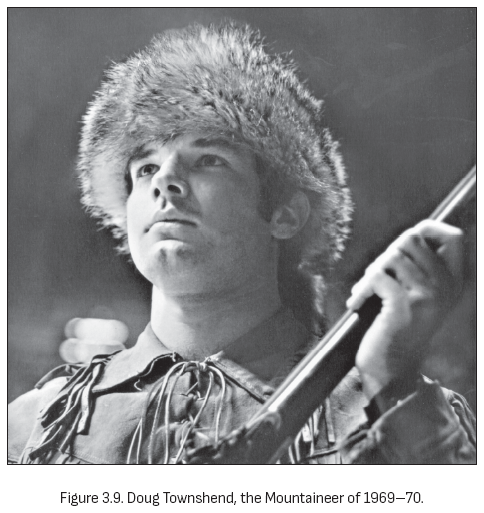
几周后,我采访了Bob Lowe,他是Townshend之后的山地人,在1970-71学年任职(图3.10)。1970年5月,Lowe正在WVU完成他的大三学年,他是校篮球队队员,并且最近被选为下一年的山地人。在我们讨论了一段时间他的经历后,我问Lowe关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校园的氛围。值得注意的是,Lowe的女儿在采访时在场。她几个月前刚从大学毕业,在他开始讲述以下故事之前,Lowe看着她,非常认真地问:“记得这个故事吗?”——这表明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经常讲述且重要的叙事:
“那是在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之后……有一群学生占领了Grumbein’s Island三天,要求当时的大学校长James Harlow……代表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憎恶……肯特州立大学的无谓杀戮……我们的教练告诉我们,任何参与反战抗议的人都会被取消奖学金,会被踢出篮球队,(但)我还是去了那里,因为我真的坚信(反战运动)。但在第三天早上(抗议期间),你听到扩音器说,’你们需要立即离开这个区域。我们将要使用催泪瓦斯。’你抬头看——从一条路下来的是穿着防暴装备的西弗吉尼亚州警察。从图书馆和法学院原址那边过来的是城市警察,从旧山地人球场过来的是国民警卫队,他们都穿着防暴装备。然后催泪瓦斯罐飞了进来,我立刻就跑了。”
显然,这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虽然Townshend承认州警察驱散了抗议,但他没有提到他们投掷了催泪瓦斯。实际上,他的言辞和语气都表明,他觉得州警察对他所描述的水球大战反应过度了。
在我与Lowe的谈话后期,在我关掉录音机之后(当然!),他在他对示威的叙述中补充了另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学生中心台阶上的反示威者向反战示威者扔了装满氨水的水球。突然间,使Townshend的故事看起来如此有趣的主题变成了一个更加险恶的主题;水球不再是玩具,而是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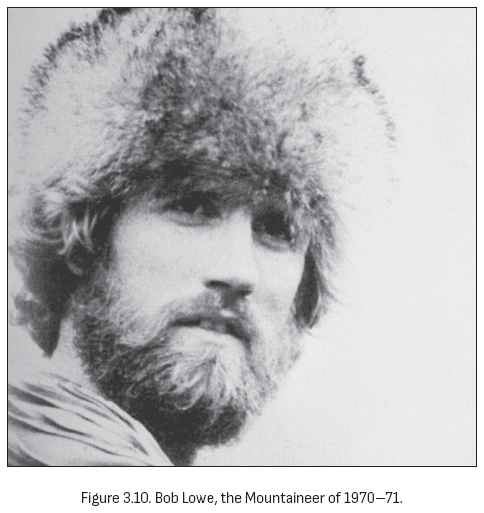
在听完Lowe的故事后,我意识到需要进行一些档案研究,以查明1970年5月在WVU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发现摩根敦确实发生了重大示威活动,既有校园内的,也有在县法院的。来自该大学历史照片档案的照片以及摩根敦报纸和《Daily Athenaeum》的文章都证实,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被召来驱散抗议者,并向示威者投掷了催泪瓦斯罐(图3.11和3.12)。WVU英语系讲师Lynne D. Boomer在给摩根敦《Dominion News》的一封信中证实了Lowe关于充满氨水气球的描述。在描述Mountainlair台阶上反抗议者的行为时,Boomer写道,该团体”向抗议战争的学生投掷鸡蛋和石头。虽然我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激动,但我很难理解那种精心策划、将气球装满氨水投向和平抗议者的心态。“35 Boomer还指出,一些反抗议者喊道:”我们应该把这些嬉皮士都枪毙了。“36
Townshend和Lowe故事之间的差异当然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记忆的变化莫测、每个人目睹的多日抗议的哪些部分,以及两人政治倾向的差异。但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叙述这些故事的方式的差异:Townshend轻松随意地讲述他的经历,我们在几个地方一起笑了,主要是对州警察对大学生释放紧张情绪的学期末水球大战反应过度的想法。Lowe的叙述是严肃的,因为他女儿在场而更加郑重:这不是一次随意的回忆之旅——这是个人和国家历史的重要片段。他在讲述后说,几周后他在巴尔的摩参加了Neil Young的音乐会,Young首次演奏了”Four Dead in Ohio”,这强化了那种严肃的基调。Lowe还描述了1969年12月1日臭名昭著的征兵抽签前一晚他与父亲的电话交谈:他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一位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现役军官——问Lowe如果抽到低征兵号码他打算怎么办。Lowe说他告诉父亲不确定,而他父亲只是回答:“如果你需要搭车去加拿大,告诉我。”37
在完成额外研究后,我对两人进行了跟进,给他们发送了描述事件的报纸文章和Boomer的信件副本。Lowe确认所有这些都与他的记忆相符。Townshend说他”只记得那不过是一场口角和扔了些水球。“38 此时,历史学家可能会质疑哪个人的描述更真实或准确。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也许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民俗学家,我知道现实和讲故事都比简单的真相概念复杂得多。每个人对原始事件的感知都深受其自身经历和信念以及每个人实际在场的时间和地点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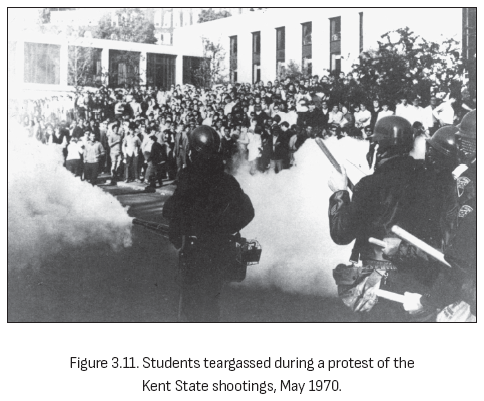
毕竟,示威持续了三天,冲突不断升级,直到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用催泪瓦斯清理了该地区。很可能在早期示威不那么激烈、更具游戏性,后来才变得难看。当然,时间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对事件的叙述:Townshend和Lowe在事件发生后立即描述他们的经历的方式可能与45年后向我讲述的方式非常不同;后见之明和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肯定会塑造他们的记忆。Lowe之前曾向女儿讲述过这个故事,以及他用当时其他事件来构建这个故事的方式——他父亲提出帮助他去加拿大和Neil Young演奏”Four Dead in Ohio”——表明对Lowe来说,这个故事是关于历史的:他自己的个人历史以及国家历史。对Townshend来说,这个故事是关于失控的大学恶作剧。尽管它们如此不同,但两个版本都是绝对真实的,当时在场的一千多人未被收集的描述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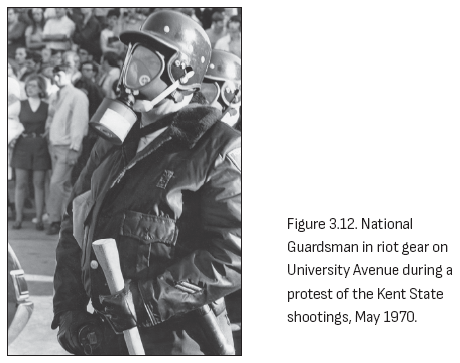
Townshend和Lowe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们突显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深刻分裂,以及个人的政治观点如何塑造和影响对事件的认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不要假设每个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上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反战运动。虽然这是关于那个时代学生的持久刻板印象,但它只是一个刻板印象。那时和现在一样,校园里充满了持有各种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个体。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WVU山地人(Mountaineer),另一个将在第二年成为WVU山地人——都是WVU校园活动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见证者。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在越南战争辩论中立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都能在1970年这个动荡的年份担任该大学的官方代表。Townshend和Lowe连续担任WVU山地人一职,突显了这一时期山地人身份的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任职期间的照片中,Townshend是干净剃须的,而Lowe留着胡子。事实上,Lowe告诉我,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留胡子,但作为校队运动员,他被禁止这样做。成为山地人的好处之一是他有了一个留胡子的官方理由。正如他在采访中告诉我的,“篮球教练不允许你留面部毛发或长发,所以在我大四最后一场比赛,我带着三天的胡茬出现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他补充说,从那时起他只刮过一次胡子,当他刮胡子时,他的”女儿们看着[他]说,‘不,爸爸,把胡子留回来。’“参加采访的Lowe的女儿Bethany补充说,”我们都认不出他了。”
在美国历史的这个时期,面部毛发的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他的优秀著作《胡须与男人:面部毛发的启示性历史》(Of Beards and Men: The Revealing History of Facial Hair)中,Christopher Oldstone-Moore解释说,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干净剃须的面孔一直是顺从的标志,这使得”现状批评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选择面部毛发作为抗议的标志。“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留长发或胡子是一种政治声明。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胡须主要由”学者、神职人员、艺术家、流浪汉、音乐家和拓荒者”留着,正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社会版编辑Eleanor Page在1958年一篇题为《胡须能增添男子气概吗?》(“Does a Beard Add to Manly Charm?”)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但当Page的文章在1950年代末出现时,这群留胡子的社会边缘人”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当然,到1960年代末,面部毛发几乎成为证明年轻人对反战事业承诺的必需品。正如传奇反战活动家Jerry Rubin所说,”反叛从你的脸开始……我们的头发是我们的纠察标志和燃烧瓶。我们的头发伤害/冒犯[建制派]比我们说或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严重。“1968年的一期《新闻周刊》(Newsweek)宣称,”今天,头发力量仅次于黑人力量,是美国生活的第二大推动力。”
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面部毛发是主流男性时尚的一部分,甚至是潮人和职业运动员的时髦造型,可能很难理解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留胡子有多么激进——以及胡子既传达又招致了多少危险。旅行作家Richard Atcheson很好地捕捉到了留胡子的风险,他写道:“我曾经在赞比西河上没有桨;我曾在大堡礁上空一架失灵的直升机中飞行;我曾被提华纳眯眯眼的皮条客威胁……但我在远方从未像1970年夏天在自己的国家旅行时那样害怕,当时我留着长发和胡子。”在1970年夏天,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之后,每个留着长发和胡子的年轻人突然都成为对现状的潜在威胁。Bob Lowe在那个夏天决定留胡子确实很冒险,即使他确实有完美的借口这样做。
Eleanor Page在她的《芝加哥论坛报》文章中列出的留胡子者名单包括一些熟悉的名字,包括最后一项:拓荒者(frontiersmen)。在留胡子者名单中包含这个形象似乎很奇怪,因为最知名的拓荒者——迪士尼的Davy Crockett,由Fess Parker扮演——是干净剃须的。即使拓荒者通常被想象成留胡子的,正如Page的文章所暗示的,考虑到胡子在1960年代越来越多地与激进政治联系在一起,电视制作人当然不想把他们描绘成留胡子的。流行文化中的拓荒者需要是干净剃须的,这样观众才会把他视为现状的捍卫者,而不是反对者。可以推测,DeLue的山地人雕像反映了这个经过美化的、无胡子版本的拓荒者,这一形象由这两个电视系列剧推广。到DeLue在1967年提交设计时,给山地人雕像加上胡子会传达一种政治信息,没有大学会同意为此付费并展示。
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胡须日益流行,最终导致社会对男性面部毛发的接受度大幅提高,这无疑标志着WVU山地人形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面部毛发不再被污名化,甚至成为时尚,担任WVU山地人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将胡须作为装备的一部分。看看1970年代之前山地人的照片,很少有人留胡须;1970年之后,绝大多数男性山地人都蓄须。45 这一转变清楚地反映了面部毛发如何随着其与左翼政治观点或不良仪容联系的减弱而变得更加主流。但是,关于WVU山地人应该留胡须的期望也会在日后导致问题,当纳塔莉·坦南特(Natalie Tennant)成为第一位担任山地人的女性时,这将在下一章讨论。正如取缔乡巴佬山地人以确立边疆人山地人形象对大学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一样,山地人应该蓄须的非官方期望也是如此。
但回到1969-70年未蓄须的WVU山地人道格·汤森德(Doug Townshend),以及1970-71年蓄须的WVU山地人鲍勃·洛(Bob Lowe):一个剃得干干净净的山地人仅仅一年后就被一个蓄须者接替,这似乎标志着这一文化转变的开始,也提醒我们,尽管大学对山地人形象进行管理,但当时仍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WVU山地人理念。剃须干净的山地人代表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版本——粗犷的、全美式的边疆人,随时准备为他的土地而战。另一方面,蓄须的山地人代表叛逆版本——永远自由的人,敢于直言并挑战权威——当胡须是他反权威观点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时,他就会留胡须。这些也是当时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对立形象:一个人的忠诚是通过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意愿来衡量,还是通过对建国所依据的言论自由和异议原则的承诺来衡量?这场辩论以实体方式体现在汤森德的剃须山地人和洛的蓄须山地人之间的转变中。
在WVU抗议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的示威不仅对汤森德和洛来说是一段重要记忆;它也标志着WVU学生/行政关系和学生行动主义的转折点。1970年6月,包括斯科特·比尔斯(Scott Bills)在内的六名学生被要求参加纪律听证会,理由是涉嫌在5月示威期间破坏伍德伯恩大厅(Woodburn Hall)。所谓的”摩根敦六人组”被指控”拆毁两块公告板……损坏公告板和墙壁,以及打破窗户和破坏某些教学材料”,造成约五百美元的损失。46 这封信声称,有一个由三十五名学生组成的更大团体进入了伍德伯恩大厅,当其他人被确认后,他们也将被带到纪律委员会面前。然而,这从未发生,事实上,大学似乎针对这六名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是知名的学生活动家。如果大学认为在夏季举行这次听证会可以保持低调并清除煽动者,那他们就错了:六名被告中有四人聘请了律师赫伯·罗杰斯(Herb Rogers),罗杰斯又咨询了芝加哥七人案(Chicago Seven)的辩护律师威廉·昆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昆斯特勒同意作为罗杰斯的共同律师出席纪律听证会。一篇《每日雅典娜神殿报》(Daily Athenaeum)的文章称,罗杰斯和昆斯特勒正在”起草一份联邦诉讼以驳回纪律程序”,理由是大学没有正式的学生规章制度,尽管州法律要求大学通过州董事会备案此类规则。47
听证会最初定于6月24日举行,后来推迟到8月19日,然后无限期推迟;最终,听证会从未举行,大学似乎决定让这一事件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过去。48 这可能是因为行政部门的回应非但没有平息校园骚乱,反而激发了学生行动,即使在夏季学期这个淡季也是如此。斯科特·比尔斯的收藏包括三张传单,上面列出了学生可以致电参与”这个校园和这个国家的政治议题……在它变成摩根敦14,000人而不是摩根敦六人之前”的电话号码。49 这些传单于1970年夏天在校园分发,包含比那些敦促学生更加积极的传单更为激进的言辞。一张传单在其呼吁中直接援引了对肯特州立大学的记忆:“记住肯特州立大学,记住现在保护摩根敦六人组,实际上你是在保护自己免受未来的镇压!”50
6月24日,原定举行听证会的那天,学生们改为组织了一场支持摩根敦六人的集会,并更广泛地呼吁学生团结。大约175人聚集在伍德伯恩圈,讨论摩根敦六人案。“就叫它伍德伯恩斯托克音乐节吧,”人群中一名学生调侃道。演讲者包括威廉·海蒙德,一位哲学教授,他在参加五月示威活动并”和示威者一起留在街头,因为(他)觉得他们的抱怨是正当的”之后失去了哲学系主任的职位。与五月的示威活动一样——实际上,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样——伍德伯恩斯托克音乐节的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参加理由:一些人是来了解更多关于摩根敦六人案的信息,一些人是来”听音乐”,还有一个人利用这个场合敦促其他人”倾听基督在他们心门上的敲门声”。受访的参与者对大学的纪律处分也有不同的反应。一个人说大学对学生造成的(所谓的)损害追究责任是正确的,而另一个人问:“受审的只是他们,还是我们所有人?”另一名学生——不愧是”公共关系专业大四学生”——称赞这次活动”在两个极化群体,嬉皮士(freaks)和传统派(straights)之间开启了有意义的交流”。
伍德伯恩斯托克音乐节只是五月示威活动后整个夏天学生行动的一个事件。《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的文章和斯科特·比尔斯收藏中的文件描述了1970年夏天在山地要塞(Mountainlair)新生迎新会期间发生的额外行动。7月下旬,校园内发生了几起炸弹威胁,两次针对山地要塞,一次针对塔楼宿舍综合楼。这些威胁与在这两个地点进行的新生迎新会同时发生,似乎是专门打电话来破坏迎新活动的。在这三次情况下,要塞和塔楼综合楼都被疏散了。然而,在这些虚假警报之后,尽管没有收到进一步的威胁,大学管理人员继续清理要塞内的学生。《每日雅典娜神殿报》报道,7月22日星期三下午3点,对讲机广播告诉学生”出于安全原因”离开要塞;然而,“新生迎新会参与者被允许留在大楼内”。拒绝离开的学生被拍照,并被要求向要塞员工提供他们的姓名和学号,其中一人因”猥亵手势指控”被逮捕。当大楼重新开放时,任何想进入的人都必须出示教职员工卡或学生费用收据卡,证明他们是在校学生。这些监控手段让一些学生感到不安,所以他们传阅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山地要塞主任埃德温·雷诺兹辞职,因为”他公然无视学生权利和需求”。
比尔斯收藏中的文件延续了这个故事。一本题为”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日出:属于人民,来自人民”的多页小册子以”伍德斯托克民族”的新闻稿开头,解释说”随附的小册子是在注册期间分发给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的20,000份副本之一”。“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日出”巧妙地让读者了解了自春季学期结束以来充满事件的几个月,并为秋季学期的激进主义奠定了基础,称”关于今年秋天校园会发生什么,有很多不同的传言。这份出版物应该澄清所有疑虑。“小册子随后列出了其内容:
• 对围绕摩根敦六人案的问题的解释。
• 专门欢迎/告知新生的信件。
• 关于要塞解放的免费回顾表。
• 包含各种内容的文化表:城里的新商店、成立的新团体、信息来源等。
• 对新的强制性学生行为准则的批评。
• 北本德声明的文本!
• 以及最后的”武装号召”,建议将挫折感和激进主义转化为有效政治武器的可能方法!
小册子包括一页传单,“在山地要塞的迎新仪式期间分发给入学新生”,将迎新会描述为”灌输仪式”,旨在”将你编程成他们想要你成为的被动型学生”,并鼓励学生”参与进来”,“努力将这所大学改变成一个可行的社区,在那里思想的自由交流是现实而不是口号”。它建议新生参与”音乐会、集会、示威、友爱聚会(love-ins)、同居(live-ins)和敏感性小组”,所有这些都是”相互交流我们思想的合法而美好的方式”。
显然,正是这份传单的散发导致校方疏散了Mountainlair并将其关闭,在迎新期间仅对新生开放;隔离新生防止了年长的学生煽动者与他们交流。正如”Sunrise”小册子接下来所解释的,“在这些仪式期间,有人打了炸弹威胁电话”,导致了疏散,“’Lair的管理者立即武断地认定散发传单的团体应对此事负责”。管理者搜查了疏散的建筑,然后在”为期两周的项目中,每次新生集会之前”将迎新团体带回来。63 根据”Sunrise”的说法,7月22日的事件发生在几次例行的下午驱逐之后,当时”150-200名学生在小吃部竖起了一个标语,’见鬼去吧;我们不走!’并冷静地告知校方他们不会离开”。一位Mountainlair官员告诉他们,疏散是”消防队长下令的”,而”消防队长后来否认了这一说法”。第二天,学生们焚烧了这位Mountainlair官员的人像。作为回应,这个人像的真人原型出现了,浇灭了火焰,并向抗议者挑衅要打一架。64 在小册子对1970年夏天Mountainlair事件的描述中,无论是学生还是管理者,都没有人显得体面。显然,校方希望在大多数学生离校的夏季校园能够平静下来的愿望并未实现。而学生们似乎有效地利用了不那么拥挤的夏季日程来组织起来,并计划和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示威活动。这个”炸弹”原来是象征性的,而校方似乎认定唯一能够化解它的方法就是审查它。但这样做,他们只是火上浇油。
然而,大学和州政府正在努力采取其他策略来缓解1970年夏天的紧张局势。例如,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41个州一起引入了旨在防止校园抗议并明确抗议者惩罚措施的立法。在西弗吉尼亚州,这采取了对1849年《骚乱法》(Riot Act)修正案的形式,这部法律在西弗吉尼亚州还是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时就开始生效了。简而言之,该修正案规定”任何拒绝被法律授权官员征召为临时警员的人……将被视为骚乱者”。换句话说,任何拒绝协助执法的人都将违反《骚乱法》,并面临监禁和罚款。该修正案还宣布,射杀骚乱者的执法官员将”被视为无罪”,警察有”在追捕骚乱者时无需搜查令即可进入私人住宅的权利”。该立法还规定,破坏建筑物可处以一到十年的监禁。65 其他州通过的立法甚至更明确地限制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在加利福尼亚州,学生如果”因参与校园骚乱而被定罪”,可能会失去州财政资助,而在俄亥俄州,参与校园骚乱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立即被大学开除。66
西弗吉尼亚大学也加强了自己的规则。如前所述,校方无法让针对Morgantown六人组(Morgantown Six)的指控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它没有正式的学生行为准则存档,尽管法律要求大学必须有一个。《每日雅典娜神庙报》(Daily Athenaeum)的文章表明,大学在制定学生行为准则方面已经拖延了近两年,67 但不出所料,在1970年夏天,完成并批准一个准则跃居校方优先事项清单的首位。正如一份日期为1970年8月9日、题为《北本德声明》(North Bend Statement)的传单所表明的,州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在5月示威活动之后的几个月里迅速制定并正式确立了学生行为准则。从一开始,学生参与制定准则的程度就很有限,68 但《北本德声明》表明学生被明确排除在最终确定准则的过程之外:“董事会……一直拒绝向公众开放他们的会议。现在,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他们傲慢地颁布了一项行为准则,而没有咨询任何学生,因为他们’不选择咨询任何人’”。69 《北本德声明》最后将董事会的决定比作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tt case),并以宣言结束:“西弗吉尼亚州的学生不会袖手旁观,任由他们的权利被践踏。镇压越严厉,反抗就越激烈”。70 正如校方希望在安静的夏季学期处理Morgantown六人组案件能够阻止进一步的学生抗议一样,大学急于在夏季且在没有学生参与的情况下制定正式的学生行为准则。这一努力不仅未能平息学生的异议,反而激化了矛盾。
与此同时,摩根敦的一些市民也在表达他们自己对五月抗议活动和校园政治气候的担忧。在整个1970年夏天,一个自称”关心的公民委员会”的团体传播了一份所谓的《向西弗吉尼亚董事会请愿罢免激进教师活动分子》,声明签署者”对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日益增长的反美激进主义感到震惊和担忧”,并要求将任何”在1970年5月5日至7日在摩根敦通过示威协助、教唆和鼓励此类活动”的教师”立即从…职位上开除”。71 根据摩根敦《自治领新闻报》的一篇文章,该组织是为了回应该报6月21日由弗兰克·布卡(摩根敦六人之一丹尼尔·布卡的父亲)发表的一篇文章而成立的。72 在他的文章中,老布卡声称”他的儿子丹尼尔…已经变成了一个’寄生虫’、一个’激进分子’和一个’叛徒’,这主要是因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哲学教师的影响”。73 该公民团体成员之一C. E.梅森杰解释说,该组织要求罢免激进教师而不是激进学生,因为”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正处于容易受影响的年龄”。74 然而,丹尼尔·布卡这个”激进的叛徒寄生虫”本人驳斥了这种说法,说:“我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今天许多教师正在被孩子们影响”,并补充说,“实际上我在西弗吉尼亚大学从未有过一位我认为是自由派的老师…这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激进教师活动分子’”。75 布卡进一步暗示这是一场与更大问题无关的家庭冲突,说他父亲的指控”歪曲了当前的真正问题。他认为的我的’堕落’是我的政治理想。这是问题的事,而不是个人恩怨;这才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76 布卡家族的争执可能公开上演,但它确实反映了让许多保守派父母与他们反战子女对立的代际鸿沟。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从”代替父母”原则的更大转变。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家长和管理层对学生异议的反应再次显示,大学很难定义和限制在越南战争时期学生山地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管理层在五月示威后对学生的镇压与詹姆斯·布劳纳教授对1947年首次山地人日庆祝活动的回应相呼应:玩得开心和发泄一些情绪是可以的,但必须保持”文明的薄薄表层”,如果它被侵蚀了,那么成年人就会介入并结束这种玩闹。当然,首次山地人日的参与者纯粹是为了好玩,即使他们的大部分快乐来自于违反正常界限。正如汤森和洛的叙述所说明的,五月示威的参与者有复杂且有时相互矛盾的参与理由。一些人在那里表达真正的政治关切;一些人在那里嘲笑那些似乎把自己看得太严肃的人;一些人在那里希望挑起肢体冲突;无疑,还有许多其他人只是在那里观看这场景,以便他们可以说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越南战争时期的学生抗议和骚乱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严肃动机和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结果的节日活动。虽然一些活动可能看起来像玩耍,但它们通常服务于更大、更具变革性的目的,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轻松和不集中。这种动态的一个近期例证可以在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典礼后的华盛顿妇女游行中看到:许多参与者戴着”pussy hats”(看起来非常像中世纪的傻瓜帽),举着玩笑标语,并高呼有趣的口号。这场活动的嬉戏性本身就突出了它的严肃目的。扮演傻瓜来表达观点是山地人身份的核心:大卫·克罗克特、安德鲁·杰克逊以及多德里奇和吐温笔下的荒野居民都知道如何敷衍他们的观众,让观众相信他们正在目睹一个无知者的丑态,结果却被这个傻瓜愚弄了,因为观众发现他们才是被欺骗和教训的人。
这正是当管理层拒绝回应学生抗议者的关切时发生的事情:管理层试图驱逐摩根敦六人并关闭未来抗议活动的做法适得其反。就像多德里奇和吐温叙述中的花花公子一样,学生们通过聘请威廉·昆斯特勒来辩护他们的案件,对管理层造成了严重打击。在那个夏天,学生们继续以严肃和滑稽的方式进行反击,并主张他们的智慧和独立性,通过充满笑话和尖刻机智的书面材料,倡导成为制定学生行为准则的充分参与者。虽然那些向Mountainlair打炸弹威胁电话的学生无疑享受了他们制造的混乱,但其他人认识到他们最终的成功取决于更理性的行动——但无论如何,这些行动提醒管理层他们不是傻瓜,将他们当作傻瓜对待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当山地人雕像在1971年10月的山地人周末期间揭幕时,距离1970年5月的动荡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越南冲突仍在拖延。这座梦想已久的青铜拓荒者雕像矗立在Mountainlair前,对于70年代初的学生来说,可能看起来像是50年代的倒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座光滑面容的山地人雕像成为大学官方象征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山地人吉祥物和许多男学生更可能是留着胡子的。乡巴佬山地人可能已经让位于拓荒者山地人,但担任官方山地人角色的人看起来越来越像几年前许多保守学生、管理者和家长所担心的嬉皮士。
尽管这只是巧合,但就在新雕像手持步枪的同时,官方山地人却被解除了武装。关于60年代末山地人故事中未被讲述的部分,与Doug Townshend作为山地人的任期为何是18个月而不是整整一年(或两年)有关。1968年秋天,时任山地人Gil Reel在对阵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比赛中遭遇了一次不幸的事故:在检查步枪是否上膛时,步枪意外走火,Reel”失去了他的右手食指”,并”被救护车送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住了几天。“Reel告诉《Daily Athenaeum》记者,他讨厌住院——”反正我是个户外活动爱好者”——并且担心回到课堂,因为他知道自己”写字会有些困难。“但接下来的周末是WVU的返校日,而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候补山地人。因此Mountain匆忙寻找临时替代者,选中了大三学生Steven Hite担任这个职位。
Hite在前一年春天曾申请过山地人职位,但Reel被选中了。不过Hite一定给面试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在Reel出事后,他说:
我接到一个电话……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说,“下周你要当山地人了。”我说,“真的吗?”他们说,“是的。Gil Reel受伤了。”我说,“哦,”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他们说,“我们会把制服送过去——你住哪儿?”这是我记得的情况。我站在客厅里,不管是谁来到门口,直接把它(制服)扔了进来,就落在地板上。没有任何指示。
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需要替补的原因,Hite被允许在比赛中开火,尽管他以前从未开过火枪。“我一定得到了一些指导……(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装填火枪,”他说。不过他确实知道不要把手指放在枪口上方,并记得他”确实向……另一个吉祥物……远距离开了枪。”
当然,正如Hite所指出的,那是返校比赛,“我想他们心里想着其他事情。”Hite只在返校日和1968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中担任山地人。到Doug Townshend在1969年冬天接任山地人职位时,大学显然已有时间思考Reel的事故,并决定解除山地人的武装。Hite认为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开火的山地人,直到1980年搬到Milan Puskar体育场。因此,Townshend和接下来十年的未来山地人被允许携带步枪但不能开火。感到需要有某种噪音制造器,Townshend借了一位教授的猎犬——它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响亮嚎叫——并把它带到比赛中。如今,山地人和候补山地人都必须在春季橄榄球比赛前通过西弗吉尼亚猎人安全课程。因此,对于山地人来说,动荡的60年代以一声枪响和猎犬的呜咽结束。
在肯特州立大学示威一年半后,山地人雕像竖立起来,雕塑家DeLue希望它能提醒学生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当许多人在山谷中挣扎时,我们希望回忆起的美德。“但虽然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其他文化转变可能改变了山地人的外表,但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山地人的角色将继续由白人男学生担任近二十年。与此同时,WVU篮球比赛在1973-74赛季期间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鹿皮宝贝(Buckskin Babes)“,即”四位可爱的女大学生……自然地穿着鹿皮装扮,展现山地人形象。“正如《Dominion Post》文章宣布的”西弗吉尼亚大学篮球项目最新和最具吸引力的补充”所解释的,“这套两件套服装包括热裤和吊带上衣。”这或多或少就是”鹿皮比基尼”,后来两位女性山地人Natalie Tennant和Rebecca Durst都因此受到嘲讽。随着这两位女性的选拔,山地人形象的性别性质将变得非常清晰。
“登山女郎(MOUNTAIN DEARS)”与(性感的)持枪女孩
如果说有一位女性山地人的标志性人物,那就是”疯狂”安妮·贝利。她是一位英国移民,18世纪末生活在弗吉尼亚边境地区。1774年,她的丈夫在普莱森特角战役中阵亡后,她发誓要为丈夫报仇,自学射击步枪并成为一名侦察兵。直到1795年格林维尔条约结束边境战争之前,她一直在弗吉尼亚西部的边境堡垒之间传递信息。此后,她在该地区运送邮件和驱赶牲畜。西弗吉尼亚诗人路易丝·麦克尼尔的《疯狂安妮·贝利之歌》(1939)描述她穿着”一件粗布衬衫/和用红鹿皮做成的马裤/而不是亚麻短裙”,还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浣熊尾帽”。为了完善这幅画面,麦克尼尔笔下的安妮还携带着一支步枪和”一壶朗姆酒”。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在莱拉·杰西·弗雷泽这个人物身上有自己的女性先驱(图4.1)。弗雷泽是最早进入西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女性之一,1898年骑马来到摩根敦,“穿着……‘分体裙’,‘男式’骑马,携带’一对左轮手枪’”。弗雷泽是英国人,后来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女性联盟主席,这是该校第一个女学生组织。1899年毕业后,她与丈夫詹姆斯·弗雷泽在摩根敦从事律师工作。聪明、独立,对争议和枪支都感到自在的莱拉·杰西·弗雷泽为后来的女性山地人树立了很高的标杆。然而,将近一个世纪后才有女性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官方山地人。
尽管弗雷泽戏剧性地到达校园,但西弗吉尼亚大学最初招收女性的过程,就像后来招收非裔美国学生一样,是悄然发生的,并且是对外部情况的回应:1889年4月23日,摩根敦女子神学院被大火烧毁。针对这一事件,大学董事会在6月投票决定,从秋季学期开始向所有院系招收女性。在1889-90学年,10名女性入学,其中包括第一位获得西弗吉尼亚大学学位的女性哈丽特·莱昂,她于1891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自1883年以来,女性就非正式地参加课程,俄亥俄县参议员内森·B·斯科特在1885年夏天成功通过了允许女性正式进入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立法,但众议院搁置了类似法案,因为女性免除军事训练与所有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都必须在学员团(Cadet Corps)服役三年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
即使在1889年悄然招收女性之后,州立法机构仍然对让大学完全男女同校的想法犹豫不决,一位立法者争辩说,如果没有女性专用宿舍(以及对女学生的严格监督),大学不会吸引”你想看到的那类年轻女孩……而只会吸引那些父母不太关心监督她们的女孩”。尽管有这样的担忧,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女学生人数继续增长,当大学在1897年正式允许女性进入除军事系以外的所有院系时,有112名女性,这个数字在1899-1900学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40人。大学的法学院也在这个时候向女性开放招生,并于1895年培养出第一位女律师艾格尼丝·J·莫里森,比弗雷泽戏剧性地骑马进入摩根敦早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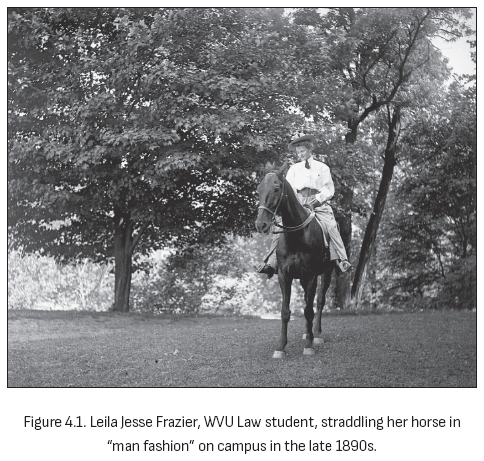
关于山地人的传统观念和形象一直将这个人物塑造为男性,山地人最受推崇的许多特征也经常与美国男子气概相关联:特立独行的精神、对权威的抵抗,以及为自己的荣誉而战的能力和意愿。这些山地人与男子气概之间的联系因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边疆山地人被确立为大学官方认可的形象而得到加强。然而,在努力摒弃乡巴佬山地人并用类似戴维·克罗克特的山地人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大学无意中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授权的边疆人山地人毫无疑问是男性,这一现实随着山地人雕像的建立而变得具体,其形象随后成为大学的授权标志。边疆人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可能将这个人物从乡巴佬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它也会被证明在其自身方面是受限的和有局限性的。
1990年春天,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娜塔莉·坦南特决定,既然她没有当选姐妹会主席,就去竞选山地人的职位。她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山地人雕像的驱动。在被选中后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她说自己曾担任北马里昂高中的吉祥物超级狗,但当她作为新生来到西弗吉尼亚大学时,“不确定女性能否被选中(成为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吉祥物)。我见过的大多数山地人都有胡子。”然后”她注意到学生会前的山地人雕像没有胡子”,于是”决定去尝试。“当然,雕像是男性形象这一事实反过来被坦南特的反对者用作反对她当选的理由,一名恶作剧者甚至在山地人雕像上放了一个胸罩——目的是抗议还是支持尚不清楚。2009年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丽贝卡·德斯特成为第二位担任山地人的女性,反对者再次引用雕像作为女性不能成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证据。与之前的坦南特一样,德斯特指出”山地人没有胡子——甚至雕像都没有。”
坦南特和德斯特时期标志着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两位女性的候选资格挑战了长期以来只有男性才能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假设。在某些方面,让女性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使这个形象向学生在二战后时期所喜爱的那种有趣的重新诠释敞开了大门。坦南特和德斯特揭示了大学在1950年代末将山地人形象制度化为戴维·克罗克特/丹尼尔·布恩形象的局限性。仅凭她们的性别,坦南特和德斯特就重新挖掘了这个形象的游戏性和转变潜力。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们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僵化的传统观念宣称女性不可能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但这两位非常坚强的女性激发了内心的安妮·贝利和莱拉·杰西·弗雷泽精神,来应对她们在任职期间所遭受的骚扰。
当娜塔莉·坦南特(图4.2)在1990年初申请成为山地人吉祥物时,她告诉学生报纸:“当人们第一次听说女性山地人时,他们会想’哦,不’。但我申请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展示我的热情。”她的室友芮妮·齐米安斯基告诉学生报纸,坦南特”不是为了成为第一位女性吉祥物而这样做的。“无论意图如何,障碍永远无法被悄无声息地打破,也不会没有反对。坦南特不仅是她申请那一年进入决赛的第一位女性,而且她和另一位女学生是有史以来第一批申请成为山地人的女性。尽管这个职位向全体学生开放,但据当时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岳荣誉会主席玛丽莲·麦克卢尔说,1990年”是有女性申请的第一年”,该组织当时负责选拔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现在由一个委员会选拔山地人)。事实上,山岳荣誉会本身在那时只接纳女性大约八年:该荣誉会在1982年之前完全是男性组织,最初否决了吸纳女性的动议,只有在大学撤销了对该组织的赞助后才同意接纳她们。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选拔过程非常严格。申请者必须提交书面申请,包括几篇论文,并接受荣誉会成员的面试。然后,决赛选手参加”助威比拼”,传统上在本赛季最后一场主场篮球赛举行。决赛选手穿着山地人服装出现,带领观众欢呼。山地人选拔委员会成员观察哪位候选人最有热情,最成功地让观众兴奋起来。
“兴奋起来”当然可以用来描述一些球迷对坦南特在助威比拼中出场的反应。学生报纸报道说,一些球迷对她发出嘘声,而坦南特本人报告说,她听到的评论从”回厨房去生孩子”到质问她的胡子在哪里。“我不希望他们喊’回厨房去’,”坦南特后来说,“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性别问题,而我从来不希望它变成这样。”《每日雅典娜神殿报》体育记者柯克·布里奇斯雪上加霜地指责受害者,说坦南特”激励观众喊出像’回厨房去’这样的话,她让人们如此激动,以至于那些人觉得有必要侮辱她。“然而,据学生凯莉·韦伯斯特说,这些”大批起哄者事先就组织好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把(坦南特)轰下场。”
布里奇斯继续推测,坦南特的竞争对手道格·麦克朗是逆向歧视的受害者,并不祥地问道:“如果明年有女性参加选拔但失败了会怎样?荣誉称号可能会被说成是基于女性性别的歧视。”19 显然,与其冒着被指控歧视女性的风险,或者——更糟糕的是——对男性实施逆向歧视,不如干脆不让女性参与竞争。
随着1990年春季学期的推进,《雅典娜日报》的社论版定期刊登反对坦南特当选的信件:有些公然带有性别歧视,认为女性根本不应该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大使,而另一些则试图通过传统修辞或批评选拔程序本身来掩饰他们的观点,通常会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并非质疑坦南特本人,而是质疑Mountain的选择方法。
一位西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写了一封逻辑混乱的信,认为坦南特应该让位,以免给已经饱受诟病的西弗吉尼亚州带来更多负面报道:
新奇再次凌驾于理性之上。她(坦南特)赢了,而大学将会输。她的任期只有一年。但对于相关人员,从校友和学生到全国各地的潜在学生,以及大学本身,负面影响将伴随他们的余生……
关于性别的笑话,比如提到”女山地人”,已经传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像许多忠实的大学支持者一样,我的室友卡尔·福克勒和我已经听够了对我们州,更具体地说是对我们学校的廉价攻击。在过去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准备好了,愿意也能够捍卫所有相关人员。然而,在新山地人形象大使这件事上,我发现自己既没有准备好也不愿意,更不用说能够抵挡这种怪异的猛烈攻击……
娜塔莉·坦南特,你的雄心、专注和贯彻始终值得钦佩。然而,我真诚地认为你选错了展示这些才能的舞台。你所代表的这所学校通过分别称呼其运动员为”山地人”和”女子山地人”来区分他们。也许仅凭这一点就表明,一位女士不应该成为”那个”山地人。20
这位作者德里克·福利是1988届新闻学毕业生,他在这里暗示,他一直遭受的乡巴佬笑话只会因为选择一位女性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大使而加剧;他认为终结先前毫无疑问的、基于性别的特权会让西弗吉尼亚显得更加落后,而非更加进步。
“传统”论点出现在体育作家柯克·布里奇斯的社论中,他要求读者”想象一下下个赛季的橄榄球比赛。一位女性山地人在台阶上跑上跑下,开枪,与尼塔尼雄狮和美洲豹大闹一番。不!“21 土木工程研究生马克·兰伯特在四月给编辑的一封信中也诉诸传统感,他问道:”让传统主导使山地人形象大使是男性有什么错?一所伟大的大学如果没有伟大的传统算什么?……我们应该停止喊’去你的,匹兹堡’吗,因为它包含粗俗用语?……伟大的传统不会轻易消失,但大学最优秀的传统之一现在永远消失了。“22
1990年春季学期所有反对坦南特当选的《雅典娜日报》信件似乎都是由男性撰写的(根据名字判断),而只有一位男性写信支持坦南特。所有其他春季学期的支持信件都来自拥有女性名字的作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反转了反对者引用的论点。主修生物学的大二学生莫妮卡·高迪奥直接回应了兰伯特关于传统的担忧,她写道:“回答马克·兰伯特的问题……让传统主导使山地人形象大使是男性有什么错?这是错的,因为这是一种性别歧视和大男子主义的态度。这是错的,因为它说女性不能成为’山地人’。”23 许多支持坦南特的信件颠倒了传统修辞,转而采用我称之为乡巴佬羞辱的方式,暗示那些反对坦南特的人正在强化关于西弗吉尼亚作为一个偏狭之地的刻板印象。高迪奥说”那些一直在抱怨娜塔莉·坦南特的人只是在证明他们确实是西弗吉尼亚的乡巴佬,“24 而杰恩·阿姆斯特朗写道”外人给西弗吉尼亚及其人民贴上落后的标签。我们一直谴责这些观点是不公正的,但现在我必须怀疑了。我们学生群体中一些人最近的行为实际上在助长这种刻板印象。“25 啦啦队选拔赛后《雅典娜日报》的一篇社论呼应了这些观点,指出那些对坦南特的表现报以嘘声的球迷提供了”第一手证据,说明为什么西弗吉尼亚人饱受无知名声的困扰。“26 当坦南特在秋季学期开始正式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形象大使时,更多男性开始表示支持,同样经常通过乡巴佬羞辱的修辞。例如,1984届校友蒂姆·威尔逊敦促粗鲁的球迷”成熟起来”,因为”这正是我们西弗吉尼亚人几十年来一直努力摆脱的那种落后、社会贫乏的形象。“27
山地乡巴佬羞辱被山地乡巴佬自豪的表达所抵消,有时在同一专栏或信件中,作家们试图主张女性在该州历史中的存在和重要性。在谴责西弗吉尼亚人”无知声誉”的同一篇社论中,作者指出”从所有这些来看,人们会认为数百年前行走在西弗吉尼亚山丘上的山地男人一定是无性繁殖的。“28 在同一期的另一篇社论中,Daily Athenaeum 城市编辑Dawn Miller引用了萨卡加维亚和南部联盟间谍(马丁斯堡本地人)Belle Boyd作为坚强拓荒女性的例子,然后她继续描述自己的母亲如何在家里的公鸡开始攻击新孵化的小鸡时拿起步枪对付它。29 Mountain的指导老师Gordon Thorn说:”我确信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拓荒精神来度过那些日子。“30
针对1990年秋季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Frank Betz引用了Elizabeth Zane的例子,这位拓荒女性在1782年9月从惠灵的亨利堡溜出,成功从堡外60码处的小屋中取回火药([图4.3])。Betz认为Zane在这场独立战争最后一战中的行动应该被认为结束了战争,并问道:“难道Elizabeth Zane白白服役了吗?所有拓荒记忆都要留给Daniel Boone们和Davy Crockett们吗?向山地人吉祥物Natalie Tennant、Elizabeth Zane的记忆以及拓荒女性们致敬……醒醒吧,上西弗吉尼亚历史101课。”31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将女性重新写入mountaineer一词的历史意义中,但将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具体化为专属男性标志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春季。有人发起请愿要求赶走Tennant,并出现了印有”我们不要母鹿山地人(Mountaindear),还给我们山地人(Mountaineer)“的保险杠贴纸和徽章。32 Tennant觉得”Mountaindear”的口号很有趣,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
我看到了一个[“Mountaindear”]保险杠贴纸,还看到了一个徽章。我有……一个保险杠贴纸。我在姐妹会会所……我把它留在咖啡桌上然后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它不见了。我认为[我的姐妹会姐妹们]拿走了它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看到。但我真的很想要它!然后,那年秋天[1990年],有一位女士……特别不喜欢我,而且……我特意每场比赛都经过她那一排去见她。有一场比赛她给我看了一个徽章,上面写着”我们不要母鹿山地人,还给我们山地人。“我想,”哦,这挺酷的!“她说[Tennant伸出手模仿那位女士递出徽章的样子],”给,你想要吗?“我说,”是的,是的,我想要。“她说,”不。你不能拥有它。“[Tennant收回手表示那位女士如何抢走徽章。]如果我不想要它,她会给我的,但因为我想要它,她就不给我了。所以我想把它作为纪念品。”我们不要母鹿山地人。“……我觉得那真的很聪明!就像,”天啊,有人花钱花时间来反对我——这真的很棒。“33
Tennant的幽默感是她作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取得成功的基础,甚至在她正式担任这一角色之前就是如此。关于啦啦队比拼,她说:
我一走出去就听到嘘声。他们在嘘,他们在嘘,而且……他们在喊”回厨房去”,“回厨房去生孩子。”所以,你知道,我以前在高中当过吉祥物。我是超级狗(Superdog)。但我被有趣的毛皮覆盖着。我知道如何用手势和类似的方式对人们做出反应。嗯,我在这里不能用手势,但我记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做饭!”[用可爱的、讽刺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有点开玩笑,因为你……必须用幽默来化解事情,而且……这就是我。34
那种用幽默化解事情的能力将对Tennant很有帮助,因为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不得不反复运用它。
Tennant在1990年夏天悄悄开始了她的正式职责,并且能够在没有公开批评的情况下这样做,因为学生报纸的任何夏季版本中都没有出现任何文章或致编辑的信件。但一旦秋季学期开始,争议再次爆发。在本赛季第一场足球比赛之前,Daily Athenaeum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向学生重新介绍Tennant。在文章中,Tennant描述了她如何赢得了一位不情愿的年长校友的认可,这位校友是她在夏天遇到的,他最终”说他是她最大的粉丝,并补充说,‘如果我年轻一点,我会娶你。’“35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报道了Tennant迷住另一位同样顽固的反对者的类似事例:
去年夏天,参加在煤矿区布恩县举行的烤猪聚会时,[Tennant]被告知要避开一位70岁的居民,人称”老巴斯特(Ol’ Buster)“。相反,她径直向他走去,伸出手说,”我听说你是我最大的粉丝。”
“见鬼我才是!”巴斯特哼了一声,拒绝握手。
但Tennant坚持不懈。她有她的步枪;巴斯特也带着前膛枪(muzzle-loader)。因火药而结缘,他们俩去了一片废弃的田地射击。“巴斯特”——Mosie Atkins——被她征服了。今天他对她假小子般的坚韧给予了最高评价。“见鬼,她比该死的男孩还厉害!”他钦佩地说。36
这些故事的流行在几个层面上都很有趣。首先,它们将对Tennant当选的性别歧视抵制重新定位到年长的农村男性身上,而实际上最直言不讳的公开反对者是该大学的男性本科生、研究生或应届毕业生。其次,它们展示了媒体如何将女性WVU山地人塑造得更容易被接受:她既迷人又有吸引力,足以赢得最不可能的追求者的求婚,而她射击的能力只是”假小子般的坚韧”,并非威胁。《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另一则轶事描述了一个”金发小男孩”在足球场跑向Tennant,递给她25美分,并说:“给我打电话。”所以,女性山地人吸引儿童和老年人,但不吸引她的男性同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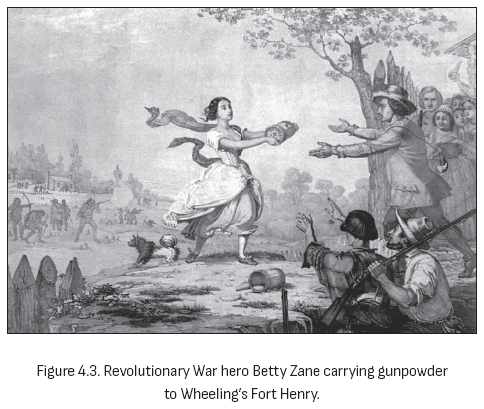
媒体和粉丝让Tennant的服务更容易被接受的最普遍方式之一,是将这位女性山地人塑造成符合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冲动的一个特别奇怪的表现出现在Charleston的James A. Swart写给《Daily Athenaeum》的一封信中,他建议:“既然Natalie Tennant让自己和1990年山地人粉丝及校友感到尴尬,让我们一起理性思考。大学应该有一位登山先生和登山女士。为了避免婚姻的感觉,他们将是兄妹。”37 Swart的信可能是半开玩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坚持认为虽然在选择男性和女性山地人时都应该考虑性别,但需要排除两者之间任何性行为的暗示。如果Swart不是写信反对Tennant,人们可以想象他的信可能会继续开一个关于乡巴佬和乱伦的低俗笑话。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对西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人的刻板描绘方面特别有趣:Tennant和老Buster克服了他们的分歧,发现他们本质上都是喜欢开枪和吃烤猪的乡巴佬。诸如布恩县的主要工业是煤矿开采这样的细节也提醒读者,这次相遇发生在某种现代版的Dogpatch,美国,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嘲笑这些角色落后、性别歧视的滑稽行为。全国媒体将西弗吉尼亚人描绘成与全国其他地方可悲地脱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并且在21世纪继续成为标准套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
然而,尽管《华尔街日报》可能沉迷于刻板印象,但它对粉丝向Tennant大喊”回厨房去”和”山地人不能有经前综合症”并向她投掷杯子和冰块的描述是完全准确的。38 《Daily Athenaeum》称赞Tennant忍受这种待遇的能力,称”她在忽视来自学生区的嘘声和嘲笑方面做得很好,同时拒绝向那些粗俗地嘲笑她并向她投掷杯子的心胸狭窄的学生低头。“39 9月前几周的许多读者来信表明,这种行为在赛季首场比赛之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多数写信人呼吁他们的同学停止这种行为,尽管一位Tennant的批评者认为她因表现不佳而应该被嘘,同时承认也许”学生和粉丝(主要是学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抑制嘘声。“4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封信出现在《Daily Athenaeum》上的那天,正是9月26日,也就是《华尔街日报》文章发表的那一天。它的发表引发了一连串的信件和社论,谴责那些反对Tennant的人的行为,不仅因为他们的性别歧视,还因为他们强化了关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刻板印象。《华尔街日报》文章发表两天后,《Daily Athenaeum》刊登了一篇社论,开头写道:“当来自全国其他州的人们错误地将西弗吉尼亚州刻板化为一个充满文盲、赤脚乡巴佬的州时,这是一回事;但当真正的州居民——其中一些是大学学生——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如此偏见和无知,以至于他们帮助强化了关于我们州的那些普遍态度时,这是另一回事。”41
读者来信反映了同样的担忧。1989年WVU毕业生John Morgan写道:“搞什么?作为一名忠诚的校友,我一直在忍受,而且最常与一系列负面的西弗吉尼亚刻板印象作斗争,我只能说:……嗯。天哪……现在是1990年了——即使在西弗吉尼亚州也是。女孩可以成为她们想成为的任何人,你知道其余的。这真的很尴尬。”42 校友Glenn H. Gould III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说”自1974年12月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以来,克服通常针对西弗吉尼亚州及其居民的耻辱和偏见一直是一项持续的努力,“并以讽刺的评论结束了他的信:”邀请西弗吉尼亚州加入20世纪将是多余的,因为这个邀请已经由比我准备得更好的人多次发出了。“43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引来了几封来自州外、与西弗吉尼亚州或该大学没有任何关联的人士写给《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编辑的信件。但有趣的是,这些信件只关注球迷行为中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提及这种行为如何证实了他们对西弗吉尼亚的看法。盐湖城的海蒂·齐默曼指出,《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夸耀山地人代表着’该州粗犷边疆历史的象征’“,她反驳说”即使在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时代,女性所受到的尊重也比她们从这些1990年代的某些男性那里得到的要多。“44 芝加哥居民丹·麦卡洛说,对坦南特的骚扰”是对贵校光荣传统的侮辱”,并呼吁学生和球迷”为坦南特的当选鼓掌,将其视为女性的突破,而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加以嘲笑。“45 麦卡洛接着指出,如果他的母校圣母大学的小妖精(leprechaun)吉祥物”由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或其他非传统学生来扮演,我会欢迎这种进步性,并赞扬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为学校的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撇开圣母大学自身与其战斗爱尔兰人小妖精吉祥物的斗争不谈,这封信对传统的进步定义很有意思,强调传统需要灵活并反映当代风俗,而不是静态和僵化的。
然而,回到《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编辑的焦点完全放在了对乡巴佬(hillbilly)的羞辱上。专栏作家凯文·西拉德和吉姆·麦肯齐在《华尔街日报》文章发表后的一周内都发表了专栏文章作为回应。西拉德写道:“我们就在那里,西弗吉尼亚和这所大学,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想,‘太好了,我们成了全国的笑柄。’”46 几天后,专栏作家吉姆·麦肯齐批评”那些心胸狭隘、不支持本校吉祥物、拒绝接受变革的人”,暗示他们是”我国其他人认为西弗吉尼亚人’落后’的原因。“ 麦肯齐继续强调他认为自豪的西弗吉尼亚人应该更关心的其他近期事件:”在过去两年内,近20名公职人员被起诉和/或正在联邦监狱服刑……除了州政治的腐败,西弗吉尼亚在几乎所有50个州的统计研究中都排名最低或接近最低,包括经济增长、教育和教师工资。“麦肯齐认为,坦南特远非”损害”大学和州的形象,而是”帮助为一个背负太多不实刻板印象的州投下积极的光芒。“47
尽管受到全国关注,对坦南特的批评在秋季学期持续不断。几周后,她在返校节游行中行进时显然受到了嘲弄和骚扰,48 一位校友专门写信抱怨她在感恩节对阵南卡罗来纳斗鸡队的橄榄球比赛中”反复将橡胶鸡扔到草坪上”。49 那些没有专门写信抱怨坦南特的人继续抱怨山地人的选拔过程。同一期描述坦南特在返校节游行中遭遇的《每日雅典娜神殿报》还刊登了一封编辑来信,再次声称道格·麦克朗是逆向歧视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编辑在信后附加了一条说明,称”山地荣誉协会(Mountain Honorary)成员……上学期表示道格·麦克朗违反了吉祥物选拔比赛的规则。“50 随后的一封信建议”应该废除山地荣誉协会选择山地人的现行传统”,让”学生和球迷来决定。“51 有趣的是,那些认为当一名女性被任命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时伟大传统已经终结的人,却愿意废除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其他长期传统。
因此,当1月份《每日雅典娜神殿报》上出现关于申请1991-92学年该职位的公告时, 显著地包含了关于评判和选拔过程的详细信息,这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在广告中,山地荣誉协会主席蒂姆·贝利强调,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在非大学活动中代表大学的时间比在大学活动中的时间多”,而且欢呼比赛(cheer-off)只是选拔吉祥物的一个标准:“我认为去年存在一个误解,认为两位候选人在欢呼比赛中处于同等地位。我们希望今年每个人都明白这是累积性的。”52 几天后,《每日雅典娜神殿报》前执行编辑苏珊·C·马龙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表达她”希望女性不会因此气馁而不去参加山地人的试镜。此外,我很乐意看到少数族裔或少数民族(无论性别)作为山地人代表大学。“53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止了关于Mountaineer身份的另一个学期的辩论。在整个春季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Daily Athenaeum》的文章和社论都被战争报道和相关辩论所主导。到2月下旬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战争结束时,新的吉祥物——二年级法学院学生Rock Wilson——已被选为新的Mountaineer。Tennant没有再次申请这个职位(尽管她可以),Mountain报道称那年根本没有女性申请,他们总共只收到了15份申请,比前一年的20份有所下降。54 也许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疲惫,《Daily Athenaeum》将其对选拔过程的报道降到了最低:体育版关于加油赛举行的篮球赛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及加油赛,实际上还指出这场比赛的上座率是整个赛季最低的。55 缺乏上座率似乎有点令人惊讶,考虑到一些学生对前一年加油赛上感觉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感到愤怒,尽管这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在1991年甚至懒得出现的原因。或者也许他们已经收到了Mountain的 信息,即加油赛并不是比赛中的决定性因素。
在Wilson被选中后,《Daily Athenaeum》的社论版面上既没有出现对新Mountaineer的赞扬,也没有批评。唯一对这一变化的认可出现在2月19日短命的学生绘制连环漫画《I Don’t Get It》中。单幅图像显示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穿着童子军制服,做着童子军敬礼,配文是”Natalie Tennant小时候”。2月22日一封致编辑的信批评了漫画作者Jim Dierwechter,说”Natalie今年已经经历了够多的,不需要在她准备结束Mountaineer任期时再把整个情况翻出来。“56 写信人Louis D. Schwartz补充说”重新揭开这个过度宣传的伤疤是不公正的”,并总结说”不明白的”是Dierwechter。值得注意的是,《I Don’t Get It》在2月22日后不再出现在《Daily Athenaeum》上。这是否是由于Tennant漫画或其他因素导致的,在报纸的后续期数中从未得到解释。
在春季学期晚些时候,几个人写信感谢Tennant作为WVU Mountaineer的服务,并赞扬她对争议的处理。在一次采访中,新的WVU Mountaineer Rock Wilson称Tennant面临的审查是”不公平的”,并说”没有其他人能如此出色地承受住压力。“57 Wilson说在年度Gold-Blue春季赛期间,许多球迷大声为他欢呼,一些人对Tennant”发表粗鲁评论”,或者只是说”他们很高兴有个男人回来了”。“这是一种获得良好反应的糟糕方式,”他承认。58
持枪的女孩(以及其他武器)
在我对Tennant和Durst的采访中,两人都没有提到因作为女性携带步枪而受到任何具体抨击——这相当令人惊讶,考虑到 一些球迷对让女性承担WVU Mountaineer工作的所有其他部分感到焦虑。人们会想象那些人会特别担心那个女人挥舞着一支真枪的想法。也许有一些关于枪的闲话,但Tennant和Durst都不介意,因为两人都对操作步枪感到自在。两位女性都在农村地区长大,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接触过枪支,尽管Tennant在成为Mountaineer之前没有开过步枪,但当她被选中时,她向她的兄弟们寻求训练。59 Durst”在一个狩猎家庭长大”,小时候曾与父亲一起打猎;即使现在,她说,她和父亲”会出去纯粹为了好玩而射击枪械”。60 重要的是,两位女性都将她们对步枪的熟悉与更广泛的Mountaineer身份意识联系起来,Tennant说”这真的就是农场生活”,Durst说”在树林里,学习大自然,能够在野外照顾自己……这也让你感到真正被赋权,也让你感觉像一个真正的西弗吉尼亚人。“61
像大多数前WVU Mountaineers一样,Tennant和Durst都有自己使用火枪的小插曲(和不当行为)。Tennant回忆起在她担任Mountaineer期间赛季第一场足球赛后的那晚去参加派对:
第一场比赛后……我去了一个朋友家,我还穿着Mountaineer服装,因为他们离体育场很近,我走到了他们家。他们说,“开枪吧,Natalie。开枪!”我还穿着Mountaineer服装,所以我开了枪。他们说,“好!好!好!”那是星期六。
周一,我接到一个电话,赫尔曼·摩西(Herman Moses)[学生事务主任]坐在这里,还有戈登·索恩(Gordon Thorn)[山地人顾问],他们说:“第一场比赛进行得怎么样?”……你知道,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女山地人。他们说:“我们收到报告说你在市政地产上开枪了。你在比赛后开枪了吗?”我就像[用一种沮丧、羞愧的声音]“是的,我开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知道,“嗯,你朋友的一个邻居报了警。”所以,我说:“好吧。”他们说:“别再那样做了。”我没有再那样做。我想他们很惊讶……我就直接说”是的,我开枪了。“你不能说不!所以那是唯一的处分——如果你想称之为处分的话——我,我受到的。因为我在市政地产内开枪了。
同样,德斯特回忆说
在匹兹堡比赛之后……贾勒特·布朗(Jarrett Brown)是四分卫,我们刚刚打破了对匹兹堡的两年连败。所以JB走过来找我,我们在唱”乡村路”,他说:“我能拿着步枪吗?”除了山地人之外,没有人应该拿着步枪。但我让他拿着……那一次。那真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大家都在场上,他拿着它,而且……我也为他装填了子弹,他开枪了,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酷的时刻……我后来请求原谅,就像布雷迪(Brady)[坎贝尔]说的那样。而且……我仍然是山地人!他们没有把我踢出去!
对步枪的熟练掌握无疑为以下论点提供了大量弹药:边疆女性和边疆男性一样坚韧和有能力,这个论点被用来为选择坦南特和德斯特担任山地人辩护。如果伊丽莎白·赞恩(Elizabeth Zane)可以在被围困的堡垒中跑出去取火药,那么女性当然可以在足球比赛中发射火枪。
但是,对武器的熟练掌握——如果你原谅这个双关语的话——对女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操作步枪让坦南特和德斯特都占了上风,并获得了一些必要的街头信誉,因为她们担任了山地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对武器的熟练掌握可能会给女性打上不自然或不够女性化的烙印。娜塔莉·坦南特在任期初期经历的一个事件说明了这一点。经过一个夏天的紧张准备成为山地人,包括在体育场的台阶上来回奔跑,坦南特告诉那些询问的人,她”精神上准备好了,[而且]我可以在身体上准备好’……用枪,以及一切。“然而,她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是对即将到来的骚扰的清醒体验,也提醒人们,女孩拿枪的想法仍然对一些球迷构成威胁:
你参加的第一个活动之一是为新生举办的野餐。他们在塔楼举办。我记得开车过去……然后停在塔楼前面,走过那里,心想,你知道,“一切都平息了,不会有太多麻烦。这些是……年轻的新生,他们甚至不知道去年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在上高中。”然后……[我]下车,走过去,穿着服装,带着枪,心想,“这将是小菜一碟。没有人会说什么。”然后我听到有人从窗户喊道:“女同性恋!”我当时想,“来了。”
坦南特没有收到更多这类评论有些令人惊讶。也许她赢得孩子和老年男性的能力使她看起来符合性别规范——或者也许她和《每日雅典娜神殿报》(Daily Athenaeum)选择不关注对她服务的恐同反应。
重要的是要结合1990年代初对赋权女性的更大反应来考虑对坦南特的反应,这表明对坦南特的反应不是一个乡巴佬问题,而是更大的全国性趋势的本地化版本。1990年代对强大女性以及最终对持有武器的女性的焦虑增加。1991年10月,著名律师和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站出来指控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希尔声称,当她在1980年代为托马斯在美国教育部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时,托马斯对她发表了性挑逗的言论。希尔的证词持续了三天,结果成为令人惊讶的电视热门节目:美国人被在政府权力最高层上演的他说/她说的辩论所吸引。尽管托马斯的提名最终得到确认,但这一事件揭露了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普遍性,也帮助许多人注意到美国参议院是多么白人和男性化。也许不足为奇的是,1992年,创纪录数量的女性竞选公职并获胜,在参议院获得了四个席位,在美国众议院获得了二十四个席位。当然,坦南特本人最终会继续从事公职,从2009年到2017年担任西弗吉尼亚州州务卿。事实上,她认为自己作为山地人的经历为她竞选公职的艰苦工作做好了准备:“我记得……在2003年,当我开始为2004年竞选时——人们会说’她够坚强吗?她对政治够坚强吗?‘’哦,是的——我搞定了。我搞定了。’”
关于Tennant担任WVU山地人的愤怒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关于性别和权力的更大焦虑,这些焦虑即将爆发。尽管Anita Hill/Clarence Thomas争议在Tennant担任山地人之后一年才爆发,但一些球迷对她”篡夺”他们认为是男性特权的愤怒,反映了其他人对Hill从”无名之辈”冒出来威胁Thomas赢得最高法院提名机会的愤怒。在Hill/Thomas案件中,观众被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女性几乎能够破坏一个有权势男性的职业生涯这一景象所吸引,公众对Hill的挑战反应深深分裂。虽然许多人支持她,但其他人诋毁和质疑她。当然,这些正是在Tennant被选为山地人之后几个月内上演的同样动态,最明显的是在早期阶段,当时一些学生认为Tennant”抢走”了她的男性对手Doug McClung应得的胜利。
1990年代初期的其他事件也反映了这种对强势女性日益增加的焦虑。1992年Bill Clinton当选总统时,人们对他的妻子Hillary Rodham Clinton感到焦虑,她本身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律师,以及她可能在丈夫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在他就职后,Hillary Clinton在医疗保健辩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恐惧升级了。但Hillary和其他强势女性的潜在威胁在1993年和1994年达到顶峰,当时两个更具轰动性和色情性的强势女性危险的例子曝光了。1993年Lorena Bobbitt因切断丈夫的阴茎(在他多次强奸她之后)而受审,1994年初,冠军花样滑冰运动员Tonya Harding被发现策划了对竞争对手滑冰运动员Nancy Kerrigan的攻击,试图让Kerrigan无法参加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和1994年奥运会。突然间,强势、愤怒或有野心的女性似乎不仅构成社会威胁,而且也构成身体威胁。正如当时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美国最危险的女人是谁?Tonya Rodham Bobbitt。”
这些笑话表明1990年代初期对女性在公共生活中角色变化的焦虑程度。在这种更广泛的背景下,对Tennant被选为山地人的长期而激烈的反对似乎更符合当时的时代——这不是一个落后州的问题,而是一个落后国家的问题。人们不禁想知道,如果在Lorena Bobbitt和Tonya Harding事件之后立即选择一名女性担任WVU山地人,反应会是什么;毫无疑问,担忧还会包括给女性武器的危险。然而,对持有装填步枪的女性的焦虑仍然可见:抗议Tennant的标语上写着”没有山地人应该有经前综合症”,这具体体现了对给”荷尔蒙”女性装填武器的这种担忧。
鉴于这些更大的文化事件,对Tennant的爆炸性反应实际上是1990年代初期性别政治转变的一个缩影。Tennant以幽默和毅力应对了这场冲击,似乎为未来的女性山地人铺平了更平坦的道路。但在接下来的十八年里,不会再有另一位女性被选为WVU山地人。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Tennant担任WVU山地人近二十年后,对第二位被选中的女性的反应会大不相同。然而,当Rebecca Durst在2009年春天被选为WVU山地人时,她面临着同样的批评。唯一重大的变化与批评表达的地点和方式有关:在Tennant的时代,争议在《Daily Athenaeum》的社论版面展开,而在Durst的时代,它在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展开。对Durst的敌意持续时间不长,也不那么恶毒,但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一些观众认识到他们负面反应的性别歧视;相反,我认为这是由于在这些年里出现的另一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具体来说,这是一种允许女性拥有权力,但仅通过物化她们的身体:“性感”是有力量的,因此,Durst的许多批评者能够通过将她定位为”性感女孩山地人”来克服对她的反对。
像Tennant一样,当宣布选择Durst时,她遭到了嘘声,并被问到她的胡子在哪里。在宣布之后,学生们没有在学生报纸的社论版面,而是在Facebook上表达他们对这一选择的不满或支持。Facebook群组——如”WVU学生反对没有胡子的山地人”、“如果Rebecca Durst能长出并保持浓密的胡子,我会完全支持她”,以及更直白的”去你的Rebecca Durst”——纷纷出现,支持者的群组也出现了,如”我完全支持Rebecca Durst成为新山地人”和”只要那支火枪能开火,并且经常开火”(指的是山地人在每次WVU得分后开火的传统)。其中最大的两个,“WVU学生反对没有胡子的山地人”和”我完全支持Rebecca Durst成为新山地人”,到2009年春季学期结束时,每个都有1,700到1,800名成员。
反对达斯特当选的论调或多或少遵循了十九年前反对坦南特当选时的相同修辞模式——反对者声称”其他学校会因为我们有一个女孩吉祥物而取笑我们”,正如学生托德·古塔所说的那样。70 每日雅典娜神殿报专栏作家布兰南·拉霍达驳斥了”那些荒谬的、头脑简单的、愚蠢的论点……说她不是男性,(大概)不能留胡子,而且每次足球队得分时她都很难做传统的俯卧撑”,以及”稍好一点的’传统’论点”——这种论点基于大学官方标志是一个男性山地人的事实,坚持认为山地人必须是男性。71
然而,拉霍达也是达斯特的批评者。虽然他暗示自己对达斯特当选的反对意见会更复杂,但他的社论还是回到了坦南特时代的另一个逻辑谬误:认为选拔过程存在缺陷的论点。拉霍达写道,“许多人对在欢呼赛中与现任山地人迈克尔·斯奎尔斯竞争的三名候选人的热情水平不太满意”,重现了十九年前对坦南特欢呼赛表现的类似批评。和以前一样,“程序有缺陷”的论点被表述为一种性别中立的批评。像许多坦南特的批评者一样,拉霍达暗示他对达斯特当选的不满与达斯特是女性这一事实无关,而是与山地人委员会未能将欢呼赛中的观众反应作为选择下一任山地人的主要标准有关:“选拔赛 本应是选拔过程的主要部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个论点都不是真正性别中立的证据在于拉霍达专栏的结尾,他推测:
从外部看来,委员会选择达斯特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完全是为了修复大学糟糕的形象——过去一年中包括学术丑闻以及前教练提出的种族歧视指控。
为一个男性主导的角色选择女性,尽管只是作为大学吉祥物,似乎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尝试,试图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原本传统的性质添加”进步”色彩。
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对……达斯特的资格的侮辱。72
拉霍达方便地省略了一个细节:在欢呼赛中竞争的四名决赛选手中有两名是女性:除了达斯特,大三学生丽贝卡·芬克也进入了最后一轮。73所以新山地人是女性的概率是50/50。如果选择的是芬克而不是达斯特,拉霍达会说芬克的资格受到了侮辱吗?如果另一位男性决赛选手、大四学生布洛克·伯韦尔被选中(事实上他在2010年和2011年确实被选中了),拉霍达会因为伯韦尔缺乏热情而抱怨这个选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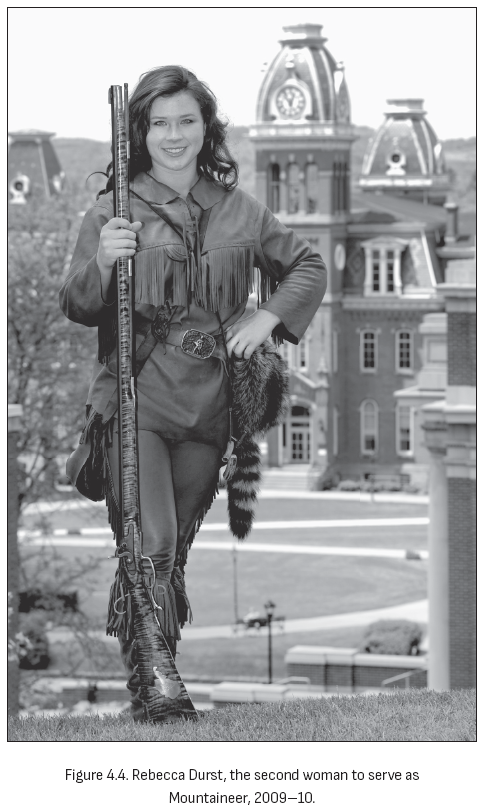
在坦南特和达斯特任职之间的二十年里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变: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的作者以及他们在文章中引用的许多学生(无论男女)都非常小心地与公开的性别歧视保持距离,就像拉霍达将基于性别的歧视标记为”荒谬的、头脑简单的、愚蠢的”一样。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声明,性别偏见仍然是他们观点的根源。当拉霍达将达斯特的胜利描述为”耻辱”和”侮辱”,由大学设计以显得”进步”时,他暗示达斯特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她只是大学公关机器的天真工具。此外,他暗示择优录取的理想因她的当选而受到玷污,这也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本质上,拉霍达的论点与一些人对娜塔莉·坦南特当选提出的反向歧视论点相同,但在2009年,它被表述为对女性去赋权的关切而软化了。
对达斯特当选的反对引发了另一轮乡巴佬羞辱,尽管这种羞辱的表达不如坦南特任命争议期间那么公开。每日雅典娜神殿报关于达斯特当选的社论更多地关注山地人的自豪感,并呼吁学生和球迷”认识到吉祥物代表什么。它是我们的战斗精神、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品格。我们愿意超越性别,这只会继续加强我们的品格。“74这里传达的信息与其说是”如果你不支持她,你会让我们难堪”,不如说是”通过支持她——或者至少不侮辱她——你才是真正的山地人。“甚至2009年4月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也用山地人团结的语言包装了乡巴佬羞辱:
那些批评丽贝卡·达斯特的人……应该意识到他们造成的伤害,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我们的大学。
作为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我们都清楚我们大学以及西弗吉尼亚州面临的负面刻板印象。
请认识到,基于性别批评我们大学的吉祥物只会延续这些误解,并将西弗吉尼亚大学描绘成一个不支持文化多样性和性别平等的机构……
通过嘲笑和批评丽贝卡·达斯特,我们证实了他们的论点,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甚至比我们的对手所能造成的更大。75
这些信件的作者在结尾处将”真正的山地人”描述为”体现了努力工作、镇定自若、包容和荣誉等价值观的人”。76
1990年和2009年人们对西弗吉尼亚大学选出女性山地人的反应之间另一个显著差异与受访学生和写信人的性别有关。正如我们所见,1990年对Tennant当选的反对意见完全来自男性,而绝大多数支持她当选的信件都来自女性作者。上述支持Durst的信件很好地说明了从1990年到2009年的转变:在签署该信的五个人中,只有两个人有明显的女性名字。然而,2009年公开反对女性吉祥物的女性明显增多。在助威比赛后,学生Dianne Cerulli对女性获胜的可能性表达了犹豫,她说”因为我们在西弗吉尼亚,没有人会尊重女性山地人”。77 Cerulli的担忧似乎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乡巴佬羞辱:既然你知道这个州落后的人口会不尊重她,为什么还要选择女性山地人?最好在性别歧视有机会抬头之前就向它低头。其他女学生对Durst无法蓄胡须表示担忧。在2009-10赛季首场足球比赛后发表在《Daily Athenaeum》上的一篇文章中,大一新生Kelsey Jagger说她”起初因为她的性别而犹豫是否支持Durst担任这个职位”,但在第一场比赛中”对她的表现印象深刻”,“尽管有些人对她没有胡须这一事实有点反感”。78
在一次采访中,Durst承认来自其他女学生的反对很普遍,她说”我感觉到并经历到的最不接受我的群体实际上是大学适龄女性,我觉得这非常有趣”。79 Durst推测这可能反映了女学生自己对打破性别障碍的焦虑,以及因此而遭到反对的可能性。她说,“许多女性可能没有尝试担任山地人的倾向,因为她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她们能够完成或达到大学标准的角色”。80 以她典型的积极风格,Durst通过将她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服务作为证据来转移她从其他女性那里收到的批评,证明女性”真的可以做任何事情,不应该因为另一个女性做了不同的事情而对她生气”。此外,她指出,“现在我看到很多在我担任山地人时还在上小学的年轻女孩,她们会说,‘我记得你当山地人的时候!那太酷了!我现在也想做那个。’” Durst还表示希望不会再过二十年才有第三位女性被选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81
尽管对Durst当选存在重大阻力,但反对声音的平息速度远快于1990年Tennant被选为第一位女性山地人时的情况。然而,Durst担任山地人的那一年并非没有自己的挑战。她是否有体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问题继续成为一些学生和球迷的担忧,尽管程度不及Tennant任职期间那么严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理和山地人的身体在这次争议中没有发挥作用。像Tennant一样,Durst遭受了性别歧视的嘲讽,像Tennant一样,她学会了”半信半疑地带着一点幽默感”来对待。她解释说:
每个人总是说,“她会穿鹿皮比基尼吗?”“她会戴假胡子吗?”“她应该待在厨房里做饭,或者光着脚怀孕。”我只是觉得很多这些评论真的很有趣。在我与山地人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之前,他们指导我应该如何与公众互动,我实际上在一些留言板和论坛上做了一些回应。球迷们也对此感到很开心,他们意识到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应并为此生气。我只会对此一笑置之,告诉你事实是怎样的。82
然而,正如关于”鹿皮比基尼”的问题所暗示的,在Durst任职期间,对女性山地人的反应带上了更明显的性意味。在许多方面,2009年女性山地人的身体甚至比Tennant当选争议期间更容易受到批评和评论。其中一些关注集中在Durst体能上履行山地人职责的能力上。反Durst Facebook群组的成员Brian Combs在春季黄金-蓝色对抗赛上观看她的表现后,显然改变了对Durst是否适合这份工作的看法:“她做了俯卧撑和所有动作,我印象深刻”。83
但对Durst身体的其他形式的关注则更具性别色彩。在2009年12月一篇关于Durst典型比赛日的文章中,记者Samantha Cossick这样描述Durst从法学院台阶进入体育场的情景:
当[Durst]试图走下台阶时,人们排队与她打招呼并拍照,导致交通堵塞,其中一些人不如其他人那么清醒,但所有人都要求她的关注。“和醉酒的人打交道一定是个噩梦”,人群中的一个男人说。
Durst 已经习惯了人们对她大喊大叫和抓她的关注,并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见到人们。
“我会去找任何想抓住我或想要合影的人,”Durst 说。
这种对球迷”抓人”行为的描述,以及 Durst 明显的听之任之态度,让人感到不安。虽然对 Natalie Tennant 与持怀疑态度的男性球迷互动的报道往往暗示她能够用”女性魅力”(和她的火枪)赢得他们,但对她性可获得性的暗示还算温和。我们只听到幽默、安全的互动,比如年迈的 Ol’ Buster 向她求婚,以及那个给她一个25美分硬币并让她打电话给他的孩子。Rebecca Durst 似乎经历了更具侵略性的球迷示好;Daily Athenaeum 报道球迷们说”至少她们现在有个性感女孩了”,并告诉 Durst”给我你的号码”或”我会在 Facebook 上找到你”。Durst 自己说”今晚,一些球迷对我大喊’脱掉它’,指的是鹿皮衣服”,但她将此归因于球迷”只是融入比赛”。看来一些球迷对拥有女性吉祥物的反对被将 Mountaineer 性化的潜力所抵消。
Durst 将这种关注更多归因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而非她的性别:
那时 Twitter 和社交媒体开始变得流行……我想建立一个 Mountaineer Twitter 账号,但 Mountaineer 顾问委员会还不太放心。但现在 Mountaineer 确实有了 Twitter 账号,能够以这种方式与球迷互动,我认为这真的很棒。而且,你知道,人们现在都喜欢自拍,所以他们……试图抓住 Mountaineer 并做更多这样的事情……我会拍很多照片,然后我觉得我不得不拒绝很多照片,因为,你知道,你只能站在那里拍照这么长时间,这会消耗其他人群应该从吉祥物那里获得的能量。
毫无疑问,在自拍时代,观众对 Mountaineer 的期望发生了巨大变化,Mountaineers 花在与球迷合影上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然而,球迷抓着 Durst 并要求她”脱掉它”的画面仍然是令人不安的证据,证明对一些人来说,证明选择女性 Mountaineer 合理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她的身体物化和商品化。因为她”性感”,所以她能不能留胡子就无关紧要了。虽然男性 Mountaineers 也因为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而面临批评(胡子不够浓密或不符合球迷对男性 Mountaineer 身材的想法),但这种身材羞辱与要求女性 Mountaineer 穿比基尼鹿皮装或脱掉衣服之间有很大区别。然而,骚扰既不令人受宠若惊也不赋权:它是权力的宣示,提醒人们女性的身体总是受制于男性凝视及其评判。
在 Durst 担任第二位女性 Mountaineer 之后的几年里,许多女性申请了这个职位,其中两位担任过候补 Mountaineer:2013-14年的 Daryn Vucelik 和2016-17年的 Savannah Lusk。Durst 的当选引发的争议以及这些争议被对她身体的关注所掩盖的方式,清楚地表明 Mountaineer 的身体具象化已经成为问题。正如许多美国人在 Anita Hill 听证会后第一次突然看到美国参议院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一样,Durst 争议似乎让大学意识到,通过使用 Mountaineer 雕像作为官方标志,它默认推广了 WVU Mountaineer 作为白人和男性的特定和静态形象。
因此,在 Durst 任职后的几年里,大学开始重新定义其与 Mountaineer 图标的关系,聘请公关公司分析和改造大学品牌,似乎并非巧合。结果是2015年推出的”Let’s Go”品牌,其关键变化是将 Mountaineer 标志的使用限制在体育运动领域。Mountaineer 的形象不再是大学学术品牌的一部分。相反,营销机构相当巧妙地通过一项新活动重新包装了 Mountaineer,该活动借鉴了与 Mountaineer 相关的价值观和品质,正如下一章所讨论的。这种品牌重塑将 Mountaineer 身份从特定的身体化身转向更抽象的一系列特征。
这种从雕像中描绘的 WVU Mountaineer(以及基于雕像的标志)的官方转变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策略,因为它设法在抽象意义上保留了 Mountaineer 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从等式中消除了有问题的物理身体。然而,这是否会导致下一位女性 Mountaineer 面临更少的反对还有待观察。
民俗学家们总是在寻找群体叙事中的模式,当我采访前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时,有一个特定的叙事反复出现在他们描述穿鹿皮装时光的过程中: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他们违反官方规定的事情,比如允许其他人开枪或穿着制服出现在派对上,然后用”事后请求原谅总比事前请求许可要好”来为自己辩护。我对这句话如此频繁地自发出现感到震惊,直到我意识到这是山地人的完美座右铭:按照自己的冲动行事,做你需要做的事,不用担心规则或社会期望。如果你走得太远,以后可以忏悔。
这种山地人先行动后请求原谅的观念现在已经是一个熟悉的主题。然而,近年来它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因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围绕山地人身份和”山地人先行”的理念推出了新的品牌宣传活动,同时乡巴佬(hillbilly)这个形象也重新出现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文化和整个美国文化中。在2010年代,hillbilly这个词重新出现,通过MTV的Buckwild等电视节目和J.D.万斯的畅销书Hillbilly Elegy,它既代表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也是一张政治牌。与此同时,西弗吉尼亚大学在这十年中花费了大量精力与乡巴佬联想作斗争,这些联想伴随着该大学被指定为全国顶级派对学校之一以及校园内几起广为人知的学生骚乱。仍然普遍存在的是西弗吉尼亚人与从这些陈旧刻板印象中获益的外来者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随着Mountaineer这个词进入第三个世纪,关于成为山地人意味着什么的斗争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关于山地人的旧刻板印象难以消除。2012年,有线电视网MTV推出了一部以西弗吉尼亚为背景的新真人秀节目,名为Buckwild(图5.1)。该系列节目展示了爱玩的年轻乡巴佬(我的用词,不是MTV的)做21世纪乡巴佬做的事,至少根据MTV的说法:开四轮车在泥地里玩和过度饮酒。甚至在节目播出之前就引起了争议,促使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向MTV高管发送了一封先发制人的信,要求取消该节目,并谴责他们诋毁西弗吉尼亚人民:“这个节目迎合了关于西弗吉尼亚人民的丑陋、不准确的刻板印象……让我告诉你:人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付出了一切。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来生产能源,这些能源用于生产钢铁,建造我们的工厂和城市……我们州的骄傲退伍军人流的血比大多数其他州都多,做出了更多的牺牲来保持美国的自由。”曼钦的信通过用另一套现在熟悉的刻板印象来反驳Buckwild的负面乡巴佬刻板印象:颂扬该州谦逊、朴实的劳动人民美德的浪漫版本。这是一个感人的致敬,但不用说,MTV高管并没有被感动而取消节目或用矿工和退伍军人重新选角。
Buckwild在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以南的西森维尔拍摄,尽管该节目让西森维尔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乡村化。MTV希望Buckwild能成功取代其最近结束的Jersey Shore系列;像Jersey Shore一样,Buckwild聚焦于一群20多岁朋友的疯狂滑稽行为。MTV的赌博成功了:据该网络称,该节目每集吸引了约300万观众,并且”在MTV 12至34岁目标年龄人群中,是相应晚间收视率最高的原创有线电视节目。“它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唤起了从萨特·洛文古德时代以来一直被持续挖掘的同一个乡巴佬形象:生活在主流文化边缘、喜欢休闲、几乎未开化的白人叛逆者。
该节目在其明星之一沙恩·甘迪意外死亡后于2013年4月被取消。另外两名演员曾有法律麻烦,包括一名囤积羟考酮和海洛因意图出售的演员。尽管甘迪的死亡既悲惨又不合时宜,但节目的停播对查尔斯顿市长丹尼·琼斯来说是个好消息,他说他”为节目被取消感到宽慰和高兴,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如此。这个节目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夸大了关于我们的每一个负面刻板印象。“甘迪去世后,亨廷顿市长史蒂夫·威廉姆斯透露Buckwild第二季的部分内容原本会在他的城市拍摄,他对这个决定感到矛盾:”查尔斯顿被描绘得非常积极,可爱而充满活力。当(演员们)去摩根敦(在一集中)时,它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描绘。我们期待亨廷顿以有利的方式出现,同时担心未经编排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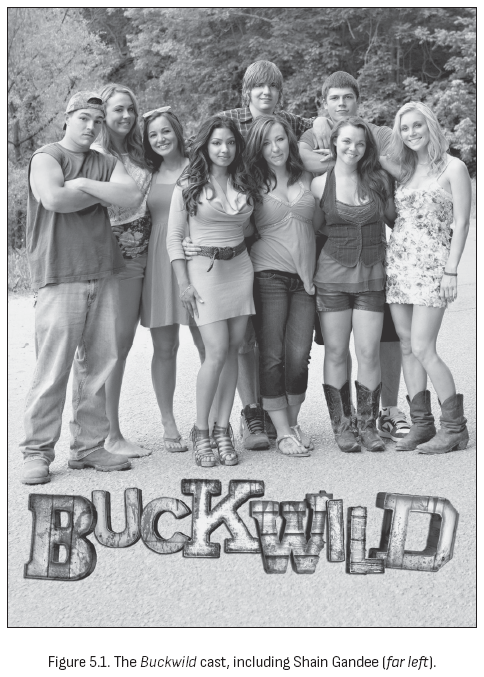
一些亨廷顿居民不太愿意看到这些好处:Elsa Littlepage 谴责这档节目的刻板印象,说”西弗吉尼亚人不是乡巴佬。许多人住在城市里。他们不会在泥地里开全地形车,也不会表现得不文明……为什么他们不去阿肯色州、田纳西州或密西西比州呢?“——显然,那些都是不太”文明”的地方,“真正的”hillbilly(乡巴佬)住在那里。7 与此同时,亨廷顿电影、戏剧和广播办公室主任 Joe Murphy 呼应了早期几代人对外来者剥削的不满,声称:“当电影’carpetbaggers(投机商人)’正在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利用美国人对阿巴拉契亚男女的迷恋,我们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对电影友好的城市,同时成为我们城市人民和形象的好管家。”8
尽管 Buckwild 争议随着 Gandee 的死亡和电视网取消该节目而突然结束,但围绕其对西弗吉尼亚人代表性的激烈争论表明,内部人士对外部人士如何看待山地人的焦虑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存在。Manchin 和 Littlepage 的评论避免专门使用 hillbilly 这个词,但这显然是两人都担心 Buckwild 会重新唤起的形象。Murphy 关于 carpetbaggers 的评论唤起了一段悠久而传奇的历史,即在重建时期及之后,狡猾的外来者进入阿巴拉契亚欺骗当地人——这些故事在当时就让人回想起更古老的关于拓荒者和花花公子的故事。
Buckwild 争议也预示着公众对阿巴拉契亚重新产生兴趣。在 2016 年总统大选及其后续期间,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抓住阿巴拉契亚作为”被遗忘的美国”的完美缩影,正是这个美国崛起并推动唐纳德·特朗普获胜。在选举前夕,以及选举后令人困惑的日子、周和月里,媒体争相寻找特朗普受欢迎的解释,将阿巴拉契亚视为记者想要与特朗普的”人民”交流的某种圣地。 一个世纪前,William Goodell Frost 宣称阿巴拉契亚”比我国任何其他地区都拥有更大比例的革命’儿子’和’女儿’“,两个世纪前,Joseph Doddridge 将拓荒者描述为”他的国家之父”,阿巴拉契亚再次成为美国主义的晴雨表。花花公子们——沿海”精英”——被拓荒者象征性地击倒了,媒体蜂拥而至,想要了解这个奇特的物种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虽然一些记者以开放的心态接近该地区及其居民,但其他人则带着 hillbilly 刻板印象而来,这些刻板印象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并深刻地塑造了他们讲述的故事。9 正如 Frost 和其他”阿巴拉契亚例外论”倡导者为了获得北方富有捐赠者的支持而方便地忽视了该地区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一样,二十一世纪的记者也忽视了当代阿巴拉契亚的种族、民族、经济和政治多样性。选举后出现的故事暗示所有西弗吉尼亚人都是现任或前任煤矿工人,而且大多数人要么是未受教育、不健康的 hillbilly,要么是坚定、长期受苦、朴实的拓荒者。很少有报道试图提供该州及其人民的另一种观点。
J. D. Vance 的《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乡巴佬的挽歌:一个家庭和危机中的文化回忆录)》同时流行也无济于事。Vance 的书于 2016 年 6 月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 2016 年 8 月和 2017 年 1 月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许多评论家将其吹捧为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中心地带受欢迎的原因。事实上,2016 年 7 月下旬《美国保守派》对 Vance 的一次采访吸引了大量流量,以至于该出版物的网站短暂崩溃。10 采访者 Rod Dreher 以一则轶事开始采访:“一位几年前搬到西弗吉尼亚州的朋友告诉我,她从未见过那里常见的贫困和绝望。她说你可以 开车穿过该州最贫穷的地区,只能看到特朗普的标志。阅读《Hillbilly Elegy》告诉我为什么。”11 Dreher 不在乎 Vance 与西弗吉尼亚州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显然,Vance 童年时期与肯塔基州东部的家人一起访问的经历,就授予了他所有的”hillbilly cred(乡巴佬资格)“,正如他自己的表亲所描述的那样,他需要为西弗吉尼亚人和所有阿巴拉契亚人发言。12
Vance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长大,但他的回忆录强调了家族在肯塔基州东部的起源——这是他在标题和全文中所声称的hillbilly身份的根源。然而,Vance对hillbilly一词的定义是模糊和多变的。奇怪的是,鉴于Vance是一名律师,他从未完整或准确地解释他所说的hillbilly是什么意思。文本早期部分将hillbilly身份与阿巴拉契亚地区以及二十世纪中期许多阿巴拉契亚人迁移到的北方城市重新定居社区联系起来。不幸的是,Vance对hillbillies的描述重复了所有常见的刻板印象;他说”当时(也许现在也是)的Hillbilly文化将强烈的荣誉感、对家庭的忠诚和奇怪的性别歧视混合成了一种有时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他进一步吹嘘自己是”hillbilly皇室成员”的亲属,因为他父亲这边的一位祖先嫁入了Hatfield家族,并补充说他母亲的祖先”有着几乎与Papaw一样辉煌的世仇历史。“Vance笔下的hillbillies是暴力的,他为自己继承了”阿巴拉契亚荣誉准则”而自豪,这迫使他与任何侮辱他家人的人打架。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中,Vance的祖父母在药店店员让年轻的Vance离开后破坏了商品,Vance以可疑的道德结论结束了这一事件:“这就是苏格兰-爱尔兰裔阿巴拉契亚人在有人欺负你的孩子时会做的事。”他的祖母在很多方面成为了这本书的女主角,她经常威胁要射杀入侵者,并曾经放火烧她的丈夫。忠于刻板印象,Vance强调了他的hillbillies的苏格兰-爱尔兰背景,将他们的种族与暴力本性联系起来。
Vance关于hillbillies是谁的概念是一团糟,是基于地区、阶级和种族的陈词滥调的大杂烩。最令人不安的是Vance坚持认为hillbilly身份是遗传的——贫困不仅仅是文化上传播的,而是生物学上的。尽管他将hillbilly身份与苏格兰-爱尔兰人的联系到书的结尾时逐渐减少,但Vance仍然以他的担忧作为结论,即他永远无法摆脱他的hillbilly命运:“冲突和家庭破裂似乎是我不可能逃脱的命运。在我最糟糕的时刻,我说服自己没有出路,无论我如何与旧恶魔斗争,它们就像我的蓝眼睛和棕色头发一样是一种遗传。”他甚至暗示摆脱这种命运的唯一方法是使基因库多样化,指出”我家族中每一个建立成功家庭的人——Wee姑妈、Lindsay、我的表妹Gail——都嫁给了我们这个小文化圈外的人。“hillbilly近亲繁殖的刻板印象和优生学的遗产在Vance书的结论中响亮地回响。
我当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Vance书中优生学令人不安的回声的批评者;Elizabeth Catte在《你对阿巴拉契亚的误解》中详细分析了这些,John Thomason在《新探究》杂志上题为”Hillbilly人种学”的文章中也是如此。两位作者都认为这些回声对Vance来说远非无意,Catte指出了Charles Murray在2016年10月对Vance的采访。Murray是1994年有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的合著者,该书使用伪科学声称非裔美国人在基因上倾向于智商较低。Murray最近的书《分崩离析:1960-2010年美国白人状况》是Vance在《乡巴佬的挽歌》中引用的少数来源之一。在他们的采访中,Murray和Vance讨论了白人工人阶级,“在笑声和玩笑中,两人讨论了他们’相当纯净的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同时深入探讨了’hillbilly文化’究竟是什么。”虽然Vance通过声称《乡巴佬的挽歌》不是一本学术书籍来为自己开脱,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的少数来源是Murray和”Razib Khan的,后者是《纽约时报》在《Gawker》揭露他’与种族主义、极右翼在线出版物的历史’后取消了其常规科学撰稿人身份的作家。“Thomason说,虽然”Vance对阿巴拉契亚文化的看法感觉更像是机会主义而不是真诚的白人民族主义……但这种机会主义使得这本书的种族决定论更加阴险:它使那些通常会对明确的白人民族主义保持警惕的受众更容易接受。”
事实上,《乡巴佬的挽歌》不仅对那些在阿巴拉契亚地区以外寻求关于我们地区”特殊人群”简单答案的人来说是可接受的,它也赢得了该地区内部许多人的青睐。一些读过这本书的WVU教职员工告诉我,他们认为它”解释了我们学生的很多问题”,应该成为必读书目。这些人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会声称既了解又批判种族和族裔刻板印象。对我来说,这是对Vance这本书最令人不安的反应:不知何故,他对hillbilly文化的”洞察”可以解释阿巴拉契亚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对于WVU的教职员工来说——学生行为。
《乡下人的悲歌》被许多人视为阿巴拉契亚文化的民族志记录,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感到不安,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万斯的观点。万斯的书重新强化了外界的看法,即阿巴拉契亚是一个奇怪而落后的地方,到处都是无知、无助的人——因为他们似乎拒绝了进步——反过来也可以被进步所抛弃。万斯为自己与”乡巴佬贵族”的血缘关系感到自豪,并对他那位说话强硬、持枪的祖母充满浪漫情怀;他赞赏他所谓的”阿巴拉契亚正义”,同时也描述了他意识到”不是每一次感觉到的轻视——来自路过的驾车者或批评我的狗的邻居——都值得引发血仇”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认同将乡巴佬视为叛逆的苏格兰-爱尔兰暴发户,因荣誉而必须保护家人的浪漫观点,同时又谴责乡巴佬文化的功能失调。简而言之,他的书重复了数百年来关于乡巴佬、边远地区居民、占地者、白人垃圾和山地人的老生常谈。
2018年春天,西弗吉尼亚州的公立学校教师创造了这个故事的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多年来对低工资、摇摇欲坠的医疗保险计划以及对资历威胁的沮丧,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为期九天的罢工。西弗吉尼亚州全部五十五个县的教师和学校服务人员都参与其中,产生了#55United和#55strong的话题标签。但罢工期间的一个事件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激励教师。在2018年2月26日惠灵市的市政厅会议上,观众席上的一位教师打断了州长吉姆·贾斯蒂斯,促使他告诉她,他也可以成为”镇上的红脖子”,这一回应引起了观众的嘘声。许多教师想知道州长是否意识到”红脖子”(redneck)一词在西弗吉尼亚州劳工史上的历史意义:这个词源于1920年代的矿工战争,当时罢工的煤矿工人在脖子上系红色头巾来识别自己。作为回应,纠察线上和州议会大厦里的教师开始佩戴红色头巾,既是回击州长,也是将他们的运动与该州劳工运动的更大历史联系起来。
教师们也在回击J.D.万斯和那些将乡巴佬描绘成懒惰、不关心他人、因此不值得尊重的州外人士。罢工的教师们,就像多德里奇笔下的边远地区居民一样,终于受够了州议会大厦里那些”花花公子”的故意误解和侮辱,他们进行了反击。与此同时,他们展现了山地人传统的好客和关怀,确保那些没有学校早餐和午餐就会挨饿的学生得到食物。无论人们对罢工持何种看法,在2016年总统大选及其给阿巴拉契亚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关注之后,看到西弗吉尼亚州在国内和国际新闻中的报道方式打破了最近大量新闻报道核心的刻板印象,并让山地人的声音为自己发声,令人耳目一新。
到2016年大选时,西弗吉尼亚大学已经尝试了几年来塑造山地人身份的另一种愿景,这一努力在大选后加快了几个档次。
2015年2月,该大学启动了一项新的公共关系和品牌推广活动,其标志性口号是”山地人先行”(Mountaineers Go First)。在向大学社区宣布新活动的信中,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戈登·吉敦促人们”花时间思考成为山地人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项新活动的启动似乎部分是为了对抗西弗吉尼亚大学作为派对学校日益增长的声誉:2007年,西弗吉尼亚大学登上了《普林斯顿评论》的派对学校榜首,2013年又登上了《花花公子》杂志的榜首。在这两次榜首之间和之后不久的时期,西弗吉尼亚大学目睹了几次骚乱,考验了校方和执法部门对学生传统的容忍度。这些骚乱的情况差异很大。第一次值得注意的事件发生在2011年5月2日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后,当时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庆祝。这次庆祝活动发生在春季学期的期末考试周,学生们需要释放一些压力,活动升级到包括22起故意纵火事件。2012年3月,圣帕特里克节的庆祝活动失控,部分原因是YouTube频道”I’m Schmacked”在校园拍摄活动。该频道关于莫根敦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活动的视频的受欢迎程度无疑是《花花公子》在第二年将西弗吉尼亚大学列为最佳派对学校的一个因素。但真正考验大学容忍度的两次事件是2012年10月在足球赛中战胜德克萨斯大学后以及2014年10月战胜贝勒大学后发生的骚乱。
我使用”骚乱”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事件时有些犹豫,因为这是一个带有负担的词。2017年夏天标志着底特律和纽瓦克等城市发生城市起义的五十周年。虽然这两个事件当时都被标记为骚乱,但五十年后,“骚乱”这个词已经背负了如此沉重的种族主义包袱,以至于人们使用其他标签来描述底特律和纽瓦克发生的事情:它们是起义、反抗、示威,或者仅仅是动乱。自1967年以来,“骚乱”这个词本身已经带上了种族色彩,主要与有色人种联系在一起;称某事为骚乱是一种妖魔化参与者并贬低他们合法诉求的方式。例如,2014年8月,年轻的非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被一名白人警察致命枪击后,那里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黑人社区走上街头抗议警察暴行。当其中一些事件变得暴力时(通常是由于警察的挑衅),它们被标记为骚乱,从而使其目的失去了合法性。
但”骚乱”这个词有第二层含义,表示一种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暴民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人们以在正常情况下永远不会采取的方式行事。骚乱涉及有意识地违反公认的行为规范,要么是为了特定目的,要么是为了违反这些规范的宣泄。在某些方面,骚乱可以是一种节日活动:参与者进入一个临界空间,在那里正常的社会规则被暂停,违反这些规则不仅是预期的,而且是令人愉快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骚乱”一词,我用来描述2012年和2014年两场重大足球胜利后在摩根敦发生的各种事件。
显然,那些在2012年和2014年赛后庆祝活动导致肆意破坏财产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表达政治观点或表达某种不满而参与这项活动。这些事件与1970年5月WVU发生的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后的抗议活动相去甚远,那是另一次穿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向学生发射催泪瓦斯的时刻。相反,2012年和2014年的事件是第二种意义上的骚乱:学生们创造了一个自我认可的、临时的无规则区域,在那里允许醉酒、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当警察通过向参与者发射催泪瓦斯来应对2014年事件时,这是两个按照截然不同规则行事的群体发生冲突的实例。
2014年WVU足球队战胜贝勒后发生的骚乱特别具有破坏性,造成约四万五千美元的损失,大学严厉打击,开除了三名学生,并要求校园文化改变。在贝勒骚乱后的一份措辞强烈且冗长的声明中,吉校长谴责了”少数学生将注意力从球队的成就转移到不可原谅和无法无天的行为上”的行为,并发誓”对这种犯罪和无序行为零容忍”。最值得注意的是,吉宣称”这不是山地人的行为方式”。
或者是吗?在一篇关于2014年骚乱的报纸文章中,摩根敦消防局长马克·卡拉瓦索斯评论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事件一直是大学文化的一部分,并指出消防部门的记录记录了1919年WVU足球队战胜普林斯顿后的一次骚乱。在那次事件中,学生们显然烧毁了大学天文台。可以肯定的是,恶作剧和其他各种喧闹的、临界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大学文化的一部分。三一堂(Trinity Hall)男生们喜欢的恶作剧是他们展示自己是大学文化主人的方式,尽管其他人可能认为他们——作为退伍军人和第一代大学生——是那种文化的局外人。他们精心设计的恶作剧肯定比同一时代对内衣突袭的狂热要聪明得多——内衣突袭是指成群的男学生突袭女生宿舍房间偷她们的内衣——WVU学生热切地参与了这种恶作剧。关于1952年一次特别大规模的内衣突袭,WVU副校长查尔斯·内夫写道:“这一事件以娱乐精神进行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它既缺乏想象力又愚蠢至极的事实”。在我们当代看来,内衣突袭可能显得古雅无害,尽管明显带有性别歧视。即便如此,我们可能希望学生们能够回到那个传统,而不是放火。但在许多方面,内衣突袭和沙发火灾是同一轨迹的一部分,这两种行为都可以被合理化为大学生普遍的粗暴、无法无天的行为,特别是乡巴佬山地人的行为。
作为一名民俗学者,我对2014年10月骚乱后爆发的关于传统的争论很感兴趣。当时我正在教授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民俗与文化课程,当我与学生讨论这些事件时,他们对于这类活动是否属于传统,以及将某事标记为传统是否能为在其他情境下被视为暴力或犯罪行为的事情开脱,意见分歧很大。回想一下,西弗吉尼亚大学2014年的骚乱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事件之后不久,当时人们正在抗议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枪杀迈克尔·布朗的事件。学生们对被警察催泪弹袭击感到愤怒,觉得自己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坦率地说,考虑到弗格森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爆发的类似抗议活动的背景,我对这种感受没有多少同情。但更大的问题——骚乱是否是或应该被视为西弗吉尼亚大学文化的传统组成部分——是一个更引人深思且模糊的关切。
在2007年至2014年间,这种传统文化中特别受到审视的一个方面是烧沙发。不知何故,学生们确信这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特有的传统,尽管其他大学也发生过许多烧沙发事件。事实上,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在2002年就禁止了门廊上摆放软垫家具,原因是科罗拉多大学学生烧沙发的事件太多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博尔德市法令的文章说,该法令是针对1996年至2002年间一百多起烧沙发事件而出台的,并且该市的新规定”效仿了其他大学城的法律,包括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伊利诺伊州诺默尔和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烧沙发可能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了一个更广泛的大学传统,但它肯定从来都不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独有的传统。
尽管如此,烧沙发是西弗吉尼亚大学核心传统的信念已被广泛接受甚至拥护。在2011年5月1日学生们烧沙发”庆祝”奥萨马·本·拉登之死后,大学和摩根敦市开始打击故意纵火行为。这种打击反过来激发了学生们的反抗,他们创建了一个名为”西弗吉尼亚大学烧沙发——通过将其变成大学活动来拯救传统”的Facebook群组,其论点正是如此:大学应该让烧沙发”正式化”并监督这一活动。2011年11月发表在《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的一篇社论支持这一想法,认为官方认可的焚烧活动”将展现定义阿巴拉契亚的叛逆的montani semper liberi(山地人永远自由)精神,但采用更现代和注重安全的框架。“它还将有助于消除这一传统的乡巴佬(hillbilly)含义,通过”将我们大学的一个污点转变为一个独特的特征,可以安全地融入我们校园文化的结构中。”
不仅学生将烧沙发视为传统;社区企业当然也通过制作庆祝这一传统的商品来支持这一观念。有几年,摩根敦Suncrest Towne Centre的Kroger面包店在橄榄球赛季制作和销售”烧沙发蛋糕”。这些糕点被制作和装饰成看起来像沙发的样子,还配有蜡烛,这样你就可以点燃你自己的含糖”沙发”,然后把它吃掉。(这些蛋糕只在2009-10年左右供应了几年,@westva75最近的一条推文说”#kroger不肯卖给我们烧沙发蛋糕[因为]它’助长不良行为’。“)镇上商店里出售的T恤衫反复引用这一做法,比如一件上面写着”伟大在此学成,沙发在此燃烧”,另一个更近期的例子声称”周六是用来烧沙发的”(图5.2)。
2012年德克萨斯橄榄球赛获胜后,《每日雅典娜神殿报》的一篇文章问道:“烧沙发的做法真的是一种传统吗?”文章引用摩根敦消防队长肯·坦南特的话说,沙发火灾”几乎就像民间传说……人们从他们的父母在这里时或从其他兄弟会成员那里听到故事。“坦南特引用统计数据表明,这一”传统”的起源相当晚近:“1997年之前,每年街头火灾从未超过20起。1997年有120起。自1997年以来的年平均数是113起,在2003年达到峰值255起。”在现场对警察和消防员进行骚乱和报复是”传统”中更为近期的部分;正如坦南特所说,“如果你在庆祝胜利,这怎么会演变成捡起石头扔向消防员或警察?我无法理解这种联系。”
然而,对于一些学生来说,甚至骚乱和向警察投掷物品都已成为深深”传统”且珍视的大学经历。在《每日雅典娜报》2015年毕业特刊的一篇文章中,毕业生们怀念地回忆起2012年圣帕特里克节的事件——一位学生将其描述为”镇上发生过的最美好的日子之一”,《每日雅典娜报》的作者泰勒·乔宾也呼应这一观点,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棒的(圣帕特里克节)“。另一位学生对德克萨斯橄榄球赛后2012年骚乱的描述表明,警方的反应——”用催泪瓦斯覆盖整条街”——导致了该赛季橄榄球队的衰落:“果然,在那之后我们连输了五场比赛。”显然,执法部门的反应不仅过度,而且直接导致了橄榄球队的低迷。《每日雅典娜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无论好坏,山地人全力以赴”——道出了当代山地人身份观念的一切:真正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全情投入,不计后果。45
很难反驳这种对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意义的诠释。在某些方面,学生骚乱和焚烧沙发正是我们对乡巴佬山地人所期待的那种反建制行为:这与1947年第一个山地人日那场失控的激励活动或动员大会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哪一种行为更不犯法:在骚乱中破坏私有财产,还是像三一堂的男生们那样为了制作返校节装饰而从美国矿业局偷取管道,盗窃政府财产?在许多方面,校方对2014年10月骚乱的回应与1947年第一个山地人日之后的回应并无太大差别:詹姆斯·布劳纳所说的”文明的薄薄外衣”再次被侵蚀,学生们越过了无害娱乐与不文明行为之间的界限。
这一界限在2019年初再次受到考验。一月底的最后几天,美国东海岸经历了极地漩涡——一股北极寒流给摩根敦带来了零度以下的气温,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从1月30日周三中午到2月1日周五关闭了三天。虽然最初两天寒冷但阳光明媚,周五气温略有回升并降下了约六英寸的雪。在室内被困了几天后,学生们享受着真正的雪天。在云杉街的顶部——校园上方一条陡峭的山路,那里坐落着许多兄弟会会所——数百名学生开始滑雪橇、玩滑雪板和饮酒。下午时分,一辆市政扫雪车来清理街道;学生们强烈反对,堵住了道路,冲突升级到一些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头和酒瓶的程度。警方则试图用声波爆破、胡椒弹和烟雾弹驱散聚集人群。果然,到当晚当地新闻播出时,西弗吉尼亚大学再次因学生”骚乱”成为焦点。然而,《每日雅典娜报》将关于此事的报道标题定为”云杉街之战”。46 骚乱的乡巴佬山地人与备受困扰的边疆山地人之间的冲突再次点燃。就像之前的”骚乱”之后一样,大学再次呼吁学生以”代表我们山地人价值观”的方式行事。47 但如何定义这些山地人价值观取决于你问谁来描述它们。

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在2019年,就像1947年第一个山地人日一样——这些价值观包括喧闹的行为和醉酒。在这方面,西弗吉尼亚大学并非独一无二:自大学建立以来,喝醉和闹事几乎一直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被正式宣布为顶级派对学校的地位是一个新现象;《普林斯顿评论》和《花花公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进行此类排名。48 西弗吉尼亚大学出现在这些榜单的榜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压力,要保持在榜单顶部——一旦山地人在派对学校排名中”领先”,他们难道没有义务维持这一地位吗?这样的排名实际上可能鼓励一些学生升级派对行为,以被认为更加失控和更加激烈。在2014年10月贝勒骚乱之后,西弗吉尼亚大学犯罪学家、《派对学校:犯罪、校园与社区》一书的作者凯伦·韦斯指出,美国各地的大学都在经历更具破坏性的行为,而从事此类行为的少数学生”认为这有利于学校……他们对学校有一种扭曲的认同感,好像他们的派对行为实际上对学校有好处。“49”全力以赴”的山地人才是真正的山地人;其他人都在山地人身份认同上失败了。
在贝勒暴动之后,Gee校长似乎暗示,正是这种错误的对等观念——认为作为山地人意味着”全力以赴”而不顾后果——需要被挑战,这反映在他坚称这”不是山地人的行为方式”。Go First品牌宣传活动在2014年贝勒胜利暴动之前就已经在筹备中,恰好与校方改变校园文化的承诺相吻合,同时也敦促学生以更学术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全力以赴”和”勇往直前”。
2012年、2014年和2019年的暴动重新点燃了狂野疯狂的乡巴佬山地人与高尚的拓荒者山地人之间的旧有冲突。虽然一些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因派对过度而成为焦点时乐在其中,但其他人则呼应校方的请求,拥抱更高尚的山地人价值观。2014年事件发生后,学生Deonna Gandy和Chris Hickey立即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使用#RespectfulMountaineer标签,以表明他们版本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不是那种失控的、破坏性的乡巴佬。50 2014年的暴动也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外来者被标记为问题根源的”不文明”粗人。在2014年暴动后的首次学生会(SGA)会议上,学生会主席Chris Nyden将暴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州外学生,他说:“我们需要停止招收那些因派对原因而非学术原因选择就读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这将要求大学提高州外学生的录取标准,但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能为了更高的入学率而牺牲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诚信。”51 Nyden的声明并非仅仅基于传闻,而是反映了事件的真实情况:摩根敦警方报告称”周六晚上暴动期间逮捕的九人中有六人是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八人来自州外”;被捕的一名拥有西弗吉尼亚永久地址的人并非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52 2019年”雪暴”之后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真正的肇事者据称是州外学生——事实上,根据《Dominion Post》的报道,2019年事件后面临指控的11名学生中有9名来自州外,而两名被指控的西弗吉尼亚居民中的一名,如同2014年事件一样,并非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53
总体上将暴动归咎于州外学生和外来者,标志着山地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有趣的新版本:在这里,醉酒、无法无天的乡巴佬不是西弗吉尼亚人,而是外来者。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转变,但与西弗吉尼亚大学州内学生和州外学生的传统观念保持一致,每个群体大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54 在州内,西弗吉尼亚大学通常受到高度尊重(也许马歇尔大学的球迷除外)。对许多本地西弗吉尼亚人来说,就读西弗吉尼亚大学是教育成就的巅峰。从刻板印象来看,州外学生,尤其是来自东海岸的学生,被怀疑选择西弗吉尼亚大学要么是因为其派对声誉(正如Nyden的评论所暗示的),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成绩或考试分数进入自己州的大学。55 这种信念在Nyden的评论中得到呼应,将乡巴佬行为归咎于外来者,暗示关于西弗吉尼亚的刻板印象可能给这些学生行为不端的许可,因为他们想象这是文化中被接受和传统的一部分。(当然,J.D. Vance对乡巴佬文化的描述似乎支持了这一点。)#RespectfulMountaineer标签颠覆了这一观念:真正的山地人不会这样行事。Nyden的评论和这个标签将山地人身份认同中经典的内部人/外部人结构颠倒过来。其逻辑是,如果外来者不认同关于西弗吉尼亚人的错误刻板印象,外来者就不会觉得可以自由地来这里这样行事。
尽管#RespectfulMountaineer标签是由学生发起的,但大学很快接纳了它,并开始以更官方的方式推广它。然而,这个标签只是2014年10月暴动后重塑山地人形象的更广泛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大学在1950年代有意识地重塑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形象,取缔乡巴佬并将拓荒者制度化一样,它在暴动后介入并实施了另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造,即山地人勇往直前(Mountaineers Go First)宣传活动,该活动在几个月后启动。值得注意的是,Go First宣传活动中的山地人与之前的化身是不同的生物。
Go First运动保留了山地人(Mountaineer)固有的品质——开拓精神、韧性、慷慨和无畏——同时将这些品质与任何特定类型的身体分离。换句话说,该运动将山地人特征扩展到整个学生群体,而不仅仅是白人男性。该运动利用了边疆人山地人的神话,同时抹去了边疆上的”男人”。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是将山地人身份中叛逆的方面重新包装成更积极和富有成效的品质。大学广泛的品牌中心网站明确定义(并限制)这些品质为六种性格特征:开拓性、热情、创新、不懈、脚踏实地和关怀,并指出这些特征”驱动着我们整个品牌的声音和形象。“描述品牌身份的页面说”它是一个标志,是质量的印章,是所有山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团结的骄傲象征。“最重要的是,品牌中心鼓励在其对山地人身份的描写中保持一致性。
但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山地人行为或身份只有一部分与Go First运动试图捕捉的崇高开拓精神有关。另一部分则与山地人家族树的另一边——叛逆的非法占地者/乡巴佬(hillbilly)——结盟。我们反复看到,尽管大学过去和现在都在努力控制这个形象的不受控制和不可控制的方面,但你不能只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当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介入正式化WVU山地人的选拔和管理时,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那时起,行政部门和学生群体就山地人的形象和身份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Go First运动可能有权正式定义WVU山地人是谁、是什么,但它无法压制大学社区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形象的冲动,实际上也无法压制这种权利。

这个由大学LGBTQ+中心相关学生制作的未经授权、非官方徽章是对这种现在已经熟悉的冲动的一个可爱例证,徽章上写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queer),我们是[山地人]“(图5.3)。如上所述,山地人标志的使用在Go First品牌下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但LGBTQ+学生对该形象的挪用完全符合重新诠释和扩展山地人身份的悠久传统,使其适合那些被认为在其参数之外的人。徽章对山地人形象的玩味方式与Trinity Hall那群来自移民社区的第一代大学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玩味山地人形象的方式相似——而且目的相似:为自己主张山地人身份。将山地人标志与ACT UP口号”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习惯吧”的修订版配对,徽章同时将山地人的身份扩展到包括LGBTQ+群体,并将山地人描绘为酷儿。
徽章再次提醒我们,非正式的、学生驱动的WVU山地人形象与大学关于该形象的官方想法可以和平共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其他时刻,对WVU山地人的这两种愿景之间的脱节已经扩大,造成了冲突,最终以大学重申其对山地人形象的权威而告终,就像Stewart校长在20世纪50年代驱逐乡巴佬山地人时那样。Gee校长和现任政府似乎决心驱逐乡巴佬山地人的当代化身,即暴乱者。这些努力是否会成功在于理解边疆人山地人和乡巴佬山地人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表达。Mountaineers Go First品牌的语言可能鼓励学生克服障碍,但正如Gee关于贝勒暴乱的声明所暗示的,还有其他学生不被允许跨越的界限。不过,作为山地人,尝试是他们的天性。
重要的是,Go First山地人植根于语言,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形象或人物。它是一种修辞建构和抽象理念,而不是一个人。Go First运动进一步将WVU山地人的特征与山地人本身的漫画分离,逐步淘汰了一个基于Mountainlair雕像的山地人形象的标志性标志。最终,山地人标志只被允许由大学体育部门使用。因此,Go First品牌巧妙地将山地人价值观与任何特定的物理身体分离。在该运动的初始阶段,运动材料中出现的人物仅以剪影形式出现,从背后拍摄,或由代表性物品描绘,如山地人的鹿皮软鞋(moccasins)。由于山地人不与任何种族或性别相关联,其含义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山地人,这一目标在品牌中心网站上明确说明。
鉴于该大学通过招募和录取更多有色人种学生和更多国际学生来实现多样化的努力,这种试图将山地人身份与物理身体分离的尝试——特别是与一直被构建为白人和男性的身体分离——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Mountaineer”一词开始被用作弗吉尼亚西部居民的同义词那一刻起,它就一直是白人和男性气质的标记,甚至被明确用作特定白人阶层的描述词,正如上世纪之交阿巴拉契亚倡导者如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William Goodell Frost)所使用的那样。因此,通过悄悄淘汰山地人标志并引入基于概念的Go First山地人身份理念,该大学巧妙地向任何种族、性别或国籍的人开放了这一身份。
西弗吉尼亚大学并不是唯一试图重新定义和重塑其昵称的高等教育机构。2018年4月,怀俄明大学推出了自己的新营销活动,其核心口号是”世界需要更多牛仔”,牛仔代表怀俄明州旗舰大学的学生、运动员和校友。反对声音迅速而至,教职员工反对这种”非常1950年代”的”认为’boy’(男孩)以某种方式包括’girl’(女孩)“的方式,校园里的美洲原住民指出”牛仔和原住民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积极的。“该大学的传播总监反驳说,这些冲突正是”为什么这个活动有效的原因——’牛仔’一词与吸引注意力的形象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在一个宣传视频中得到了强调,视频展示了从事各种活动的多元化学生,包括在实验室工作和学习,还有一张传单”将伽利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马丁·路德·金等历史人物认定为牛仔。“然而,正如一位批评者指出的,”如果你必须……展示一个关于你口号的视频,并对你的口号进行一页纸的解释,那你的口号就很糟糕。“61
怀俄明大学似乎正试图以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方式使其昵称和品牌现代化:通过重新想象成为牛仔的意义,就像西弗吉尼亚大学的Go First活动重新想象成为山地人的意义一样。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品牌重塑没有遇到怀俄明大学那样的抵制,这一事实凸显了山地人身份令人惊讶的流动性。尽管担任官方吉祥物的两位女性都被告知女性不能成为山地人,但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排除她们的内容,不像”cowboy”(牛仔)具有性别特定性。在许多方面,西弗吉尼亚大学营销活动的成功取决于那一点点回旋余地。
然而,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民间对大学自上而下管理这一长期文化象征的回应是复杂的。山地人真的能只存在于文字和理念中吗?大学能否成功地将山地人作为概念的柏拉图式理想与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这个实体人物分离开来?学生和校友能否对谁能担任这一职位持足够开放的态度,以允许那些看起来不像山地人的人成为山地人?或者另一位女性或有色人种是否仍会在其形象真实性上受到质疑?
似乎连大学本身也在努力将其高度概念化的理念与实体身体分离。尽管品牌重塑活动试图将山地人身份与种族和民族观念分离,但Mountainlair正面的一个巨大标志显示,这种山地人身份的新配置仍然存在本质主义元素:它的部分内容是”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我们决心成为先行者。这在我们的血液里。这在我们的汗水里。这是我们的天性”([图5.4])。特别是考虑到近年来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而且在本地的重新出现,一些学生对声称成为山地人”在我们的血液里”表示不安。这种语言似乎与上世纪之交关于种族等级制度和优生学的观念过于接近,令人不适。

在首先努力将山地人身份与人类身体分离之后,该活动最近一直在有意识地努力将山地人身份附加到意想不到的身体上。例如,2017年6月的校友杂志专题介绍了国际学生和入籍美国公民的学生。文章开头指出
我们未来的校友来自107个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儿童时期移民到美国。另一些是移民的子女。还有一些人刚刚抵达美国上大学。
当前新生班级是西弗吉尼亚大学历史上最多元化的……但真正的多样性无法用统计数据准确表达。我们的学生生活在故事中,比如:在家说乌尔都语。每年访问哥斯达黎加。祖母从印度移民。
在这里,我们与您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用他们的共同点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他们是山地人。6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颠覆了Go First运动第一波的动态;与其将山地人身份从特定的山地人身体中分离,文章刻意将山地人身份与这些特定的、非传统的”身体”联系起来。每个学生都被拍照(包括一名戴着头巾的女性;[图5.5])并附有个人简介,描述学生的背景,最后以山地人一词结尾。
校友杂志的文章似乎是该大学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将山地人身份从专属于白人和几乎专属于男性的身体中转移出来。我们可以将这个新的迭代称为”包容性山地人”。虽然最初的Go First运动材料决心完全通过文字和理念来重构山地人身份,完全不涉及身体或外表,但这个较新的阶段将山地人身份与广泛且可能出乎意料的各种身体联系起来。这无疑是该大学努力将山地人的标签延伸到日益多元化的学生群体的一种方式。
正如校友杂志文章所指出的,摩根敦校区在2016年秋季将少数族裔新生入学率提高了27%。除了更多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外,西弗吉尼亚大学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和阿曼的学生。在2016年大选前后,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报告遭受言语骚扰或威胁。西弗吉尼亚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2016年的主席Sara Berzingi写道:
在我担任西弗吉尼亚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两届主席期间,我听说并记录了近30起言语骚扰事件,其中许多事件因学生对体制缺乏信心而未被报告。通常,学生被路人针对,这些人在实施这些不公正行为后不久就跑掉或开车离开,使受害者几乎没有实质性证据可以报告或索赔。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穆斯林学生描述了他们在校园里走动时被称为从”包头巾的”到恐怖分子以及一大堆其他粗俗咒骂的事件。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Berzingi还报告了2016-17学年期间的两起事件,当时有人在该团体的祷告垫上小便。2017年初发布的一项学生氛围调查报告称,“近29%的受访者认为对穆斯林存在’不友好’氛围,27%对变性学生,19%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24%对女权主义者。30%的受访者报告他们经历过言语仇恨或偏见驱动的攻击。”针对氛围调查,该大学重申其保护边缘化学生的承诺,校长Gordon Gee表示:“包容和尊重是支撑我们所有西弗吉尼亚大学人员的核心价值观。”显然,Go First运动的预期包容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在边缘化个体在校园中如何被对待以及他们是否被视为”真正的”山地人方面创造真正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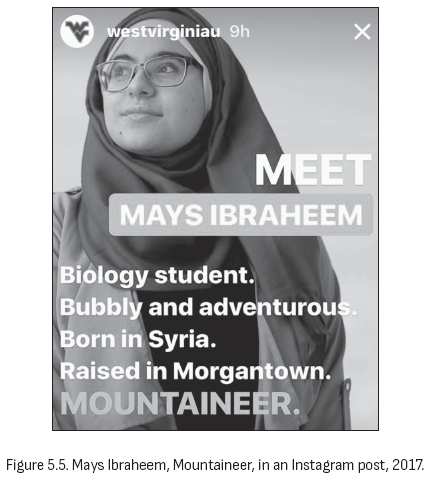
该大学并非独自努力扩大关于谁有资格称自己为山地人以及什么算作西弗吉尼亚和阿巴拉契亚文化的流行观念。民俗学家Emily Hilliard一直在为西弗吉尼亚人文委员会记录全州的民间传统和文化贡献,特别努力记录代表性不足群体和新移民的传统。Queer Appalachia是一个总部位于西弗吉尼亚州默瑟县的艺术和文化集体,最初是一个Instagram账户,此后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交媒体影响者和资助组织,出版Electric Dirt,这是一本为阿巴拉契亚和南方任何性别不符合常规的人提供多层次支持的期刊。在已故Anthony Bourdain的Parts Unknown西弗吉尼亚集中亮相的厨师Michael Costello致力于尊重传统的阿巴拉契亚农业方法和饮食方式,并推广本地食材运动和可持续性。这些和其他努力反击了西弗吉尼亚是一个文化和种族同质化地方的观念,并赋予边缘化人群将山地人或阿巴拉契亚人的绰号作为众多身份之一来声称的能力。
当我在2019年春季学期准备本书最终手稿时,发生了几起事件,促使我重新思考山地人:更多的证据,仿佛我需要它似的,表明这个强有力的形象继续成为机构和州身份的重要且适应性强的象征。一个是之前讨论过的雪天骚乱;另一个是西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推进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允许个人在校园内携带隐蔽枪支,包括在教室内:众议院2519号法案,即所谓的校园自卫法案。
类似的立法在前几年也曾被提出,但这些法案都在进入全体投票之前迅速而悄然地夭折了。然而,2019年的法案似乎即将通过,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管理层——特别是该校战略倡议副校长罗布·阿尔索普——开始在校园内组织一系列对话,为教职员工和学生准备迎接该法案的通过和实施,阿尔索普暗示该法案很可能会通过。管理层表示,虽然前两年他们一直在反对该法案,但今年他们协商了一系列豁免条款,允许在教室和宿舍公共区域携带枪支,但不包括大学的日托中心、校园警察总部、教师办公室或”容纳超过1000名观众的场馆或竞技场”——也就是橄榄球场或篮球比赛场馆。
随着这些校园对话的持续进行,社区成员——学生、教职员工——对管理层看似听天由命的做法越来越困惑。为什么他们没有更加坚决地反对它?为什么没有让最直接受该法案影响的群体代表更早参与讨论?为什么大学没有动员更广泛的社区力量来反对它,而是扮演起代理家长的角色,做出许多社区成员并不认同的决定?
随着该法案在立法机构中的推进,管理层与教职员工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著加剧。一群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职员工于2月21日举行了罢课,并开始共同反对该法案,前往查尔斯顿与立法者讨论该法案在校园安全方面的短视做法;与西弗吉尼亚大学和全州其他公立学院和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和管理人员协调反对行动;并要求教职员工,包括健康科学中心的人员,准备专家证词提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火枪——该形象标志性装备之一——突然具有了新的意义。大学网站上关于HB 2519的”常见问题”页面包含了一份目前允许在校园携带枪支的人员名单。该名单的开头如人们所料,列出了执法人员、军事人员和惩教部门雇员,但以一个令人惊讶的个人结尾: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起初,山地人出现在名单上似乎有些荒谬;山地人携带武器的理由显然与执法人员截然不同。而且所涉及的枪支——一支前装火枪——与该法案提议允许在校园携带的手枪完全属于不同类别——更不用说隐蔽携带火枪会很困难。然而,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出现在名单上这一事实提醒人们,山地人是一个多么非典型的吉祥物。这个人物不仅是一个可识别的个人,而非泡沫面具下的匿名学生,而且他或她目前也是唯一被授权在校园携带枪支的学生。校园携枪法案本来会允许所有学生像山地人一样携带枪支。
对于立法机构和整个州的许多人来说,这一提议的变化完全没有讽刺意味;相反,允许所有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携带武器是践行座右铭”Montani semper liberi”(山地人永远自由)的一种方式:山地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携带枪支,特别是因为西弗吉尼亚州是一个无需许可携枪的州。在一系列校园对话中,大学管理层似乎暗示能够争取到任何豁免条款都算幸运,因为这些豁免被支持该法案的人——特别是西弗吉尼亚公民防卫联盟(WVCDL)——视为侵犯了这种自由。
但对于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将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持有武器的权利扩展到所有山地人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是一个悲剧性的标志,表明过度关注山地人装备中的一件物品——步枪——将其作为该形象自由的最重要象征,削弱了山地人自由精神中更重要但不那么显眼的方面。正如Go First运动一直试图强调的那样,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的自由从未明确或直接地与他携带火枪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我们可能会记得,那位拓荒者用拳头而非枪支制服了那个令人讨厌的纨绔子弟。而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实际上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禁止携带步枪。暗示步枪是山地人自由的最重要象征,掩盖了赋予该形象力量的更重要但更抽象的品质,包括山地人敢于反抗权威和对陌生人表示热情好客的意愿。
最后一个品质似乎在当今被低估了,尽管许多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体育迷以礼貌和热情地接待前来摩根敦观赛的对手球队球迷而自豪。好客,即使自己几乎没什么可分享的,也是边疆拓荒者山地人身份的重要方面。大学最近试图践行山地人身份这一部分的一种方式是,将”山地人”这个标签延伸到那些通常被排除在这一身份之外的学生,就像上面提到的Go First活动中的例子一样。鉴于这些努力使山地人身份更具包容性,当国际学生、有色人种学生、LGBTQ+学生和穆斯林学生表达他们担心该法案会让他们在校园里感到不那么安全时,听到校园里的对话令人痛心。正如Sara Berzingi所描述的那样,穆斯林学生遭受的骚扰,在一个允许隐蔽携枪的校园里变得更加可怕。一些山地人与携枪相关联的自由威胁着其他山地人,这些山地人的身份更新、更不稳固。虽然Go First活动努力将边缘化学生纳入山地人身份的范围,但大学对校园携枪的明显妥协向许多同样的学生传达了一个信息:他们的大学将他们排除在保护之外。
在校园携枪对话会上以及在其他更非正式的场合,我听女学生、有色人种学生、LGBTQ+学生、国际学生和其他人讲述,知道其他学生可能携带枪支,他们会在校园里感到不那么安全。我听他们讲述在校园和教室里被骚扰的故事,我听到了他们的恐惧,担心这些言语攻击可能会变成致命的。然后我听到代表Brandon Steele说他”不在乎我们的学校是否会失去国际学生”,69几天后,我对一个极端主义团体在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日在州议会公开展示的反穆斯林宣传感到震惊。70
在我的青年文学课上,我正在教一本关于一个跨性别青少年的小说,她担心自己无法在高中生存下来,更不用说上大学了,而代表Eric Porterfield在一次采访中开玩笑地暗示,如果他的孩子向他出柜,他会淹死他们。71几天后,我在众议院的旁听席上,当时该机构投票决定不从委员会中释放一项法案,该法案本可以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添加到该州的《人权法》中。回到校园,在体育馆这个无枪区,Brooke Ashby,2019-20年度山地人职位的唯一女性决赛选手,输给了一位留胡子的男性。两天后,众议院议员们——特别是Brandon Steele——声称校园携枪本质上是一项旨在帮助女性的法案:通过携带枪支,女大学生在校园里会更安全。即使Steele和其他州议员强烈反对让年轻女性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进入校园,允许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携带枪支的唯一学生仍然是一名白人男性,就像大学在六十六次选择官方山地人中的六十四次一样。72女大学生集体携枪保护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安心,但一个女性和/或有色人种拿着山地人的步枪并获得山地人称号的想法仍然存在争议。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山地人的火枪既是一种时代错误——对边疆拓荒者那个浪漫化时代的回溯——又是自由与枪支之间感知联系的有力象征。火枪和座右铭Montani semper liberi(山地人永远自由)都被用于校园携枪争议双方的论据中。西弗吉尼亚公民防御联盟的标志突出地展示了这一座右铭,下方是猎枪和军用突击步枪的重叠图像。Taylor Giles,一名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和西弗吉尼亚大学NRA校园协调员,在支持校园携枪的《Daily Athenaeum》专栏文章结尾写道:“我们自己的吉祥物都携带枪支。为什么要剥夺其他所有人的这项权利?”73应该注意的是,每一位新选出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只有在春季的传递步枪仪式后才成为正式吉祥物。这一传统似乎表明,火枪实际上是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装备中最关键的部分。
然而,校园持枪的反对者用同样的论据反对该法案,他们说他们希望在校园里持枪的唯一学生是官方的Mountaineer——或者是WVU学生Ginny Thrasher,她是校队步枪队成员,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项目中赢得金牌。74 Monongalia县代表Danielle Walker是校园持枪的反对者,她在引用州座右铭时指出:“Mountaineers是自由的,但你应该有自由在校园里行走,而不必担心不知道走在你旁边的人拿着什么。”75 毫不奇怪,Montani semper liberi和Mountaineer的形象贯穿于校园持枪辩论的整个过程,因为这个问题涉及Mountaineer身份的许多有形和无形方面。WVU Mountaineer的步枪与学生携带枪支之间的具体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关于Mountaineer价值观的抽象理念也是如此,包括自由、异议和对抗感知到的威胁。
对于参与校园持枪辩论双方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来说,正是那些无形的特征以一种新的方式产生了共鸣,激发了对Mountaineer形象更强烈的认同感,特别是对Mountaineer对待权威的直率和反叛态度的认同。尽管多年来一直在推广Mountaineers Go First的理念,并不断提醒人们Mountaineers是那些敢于发声、采取行动和走自己道路的个体,但大学管理层似乎对反对HB 2519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强烈反应感到惊讶。一位反对HB 2519的教职员工告诉我,她在反对该法案的过程中,从未如此自豪地感到自己是一个Mountaineer。对一些人来说,曾经看似空洞的公关术语突然变得鲜活起来,Mountaineer从一个单一维度的吉祥物转变为如何生活的蓝图。简而言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Mountaineers。就像战后Trinity Hall的男子们为自己和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夺取Mountaineers称号一样,校园持枪辩论为一些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了一种更加扎实和真实的感受,让他们明白成为Mountaineer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结束是合理的,这是本书长长的类似时刻列表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即关于WVU Mountaineer的概念受到了民间、草根关于Mountaineer身份概念的挑战,而这些概念是由大学官方定义和管理的。Mountaineer这个词诞生于两百多年前,当时John G. Jackson在给Richmond Examiner编辑的信中署名为”A Mountaineer”,谴责西弗吉尼亚居民缺乏立法代表权。那时和现在一样,声称Mountaineer称号宣告了一个人不愿被沉默或边缘化,决心独立行动,以及愿意与立法机构作斗争,无论是在Richmond还是Charleston。
鉴于这些近期事件,Mountaineer的未来会是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形象将如何被构建和体现?2019年立法会议的激烈争论表明,西弗吉尼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固守己见、继续推广代表浪漫化、安全和过时的Mountaineer版本,与拥抱独立思考、抵抗压迫和欢迎陌生人的Mountaineer版本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朝哪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指标肯定是WVU Mountaineer的实际体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位担任Mountaineer的女性因为不符合一些学生和粉丝对Mountaineer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期望而面临强烈反对。
其他大学也面临过类似的挑战,例如上文讨论的怀俄明大学关于其牛仔吉祥物的争议,以及圣母大学,其小矮妖吉祥物是少数几个身份不被泡沫头遮挡的大学吉祥物之一。一方面,西弗吉尼亚大学可以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它在圣母大学选择第一位担任小矮妖的女性之前很久就选择了两位女性Mountaineers。这刚刚发生在2019年4月,当时圣母大学选择Lynnette Wukie作为其第一位女性小矮妖吉祥物。然而,圣母大学在吉祥物的种族多样性方面远远领先。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Wukie是圣母大学的第二位非裔美国人小矮妖,继第一位Michael Brown之后,他在1999-2000年任职。76由于圣母大学在一年内选择三名学生担任小矮妖,它还宣布2019-20年被选中担任该角色的其他人之一Samuel Jackson将成为该大学第三位担任小矮妖的非裔美国学生。来自爱尔兰的国际学生Conal Fagan也曾担任过这一角色。77
有色人种从未担任过山地人(Mountaineer)。国际学生也从未担任过山地人。大学将山地人身份与特定体型分离的努力,是否会让非白人或国际学生更容易或更少争议地担任山地人?正如Tennant和Durst的经历所示,无论是谁打破这些障碍,都需要有坚韧的意志。有趣的是,当有色人种或国际学生成为山地人时,那些用来反对或支持两位女性山地人任职的修辞策略是否会被重新使用。Go First运动有效性的真正考验将是当第一位有色人种山地人被选中时。那时我们才能相信,选拔真正基于该个人的山地人品格,而不是基于他或她与某个不存在的身体理想的相似度。查尔斯顿HOPE社区发展公司的儿童已经在他们与艺术家Calvin Jones和Crystal Good共同创作的壁画中想象了这一点,壁画描绘了一位非裔美国山地人站在西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后面(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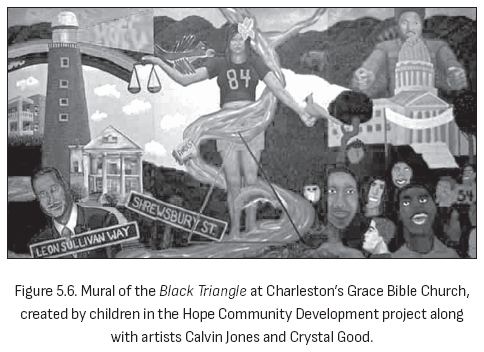
我希望我能说我相信Go First运动具有这种革命性潜力。但关于山地人是谁、代表什么的非正式、草根观念,在该州和该大学的历史比大学官方自上而下的山地人版本更悠久、更深厚。而且,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当任何传统的民间版本与官方版本发生冲突时,民间版本几乎总是获胜。这并不是说民间版本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和适应新环境。事实上,山地人漫长历史中最令我惊讶的是,“山地人”这个术语被证明是多么灵活。从最初作为描述弗吉尼亚西部居民的狭义术语,山地人身份已经发展到涵盖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没有失去其核心特征:山地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自由思考(即使有时叛逆)、慷慨(即使有时怨恨)、勤劳和坚定的个体。如此特定的一组特质在该术语首次使用两百多年后仍然与山地人相关联,并且仍然具有相关性和吸引力,这简直令人惊讶。
引言
“Yosef,”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Athletics, May 30, 2017, https://appstatesports.com/news/2017/5/30/athletics-yosef.aspx.
“Yosef.”
Hyde, Trickster, 7.
Hyde, Trickster, 13, 9.
参见Paul Radin开创性著作The Trickster的序言。
关于这场辩论的良好总结,见Babcock-Abrahams, “A Tolerated Margin of Mess,” 161–64.
Babcock-Abrahams, “Tolerated Margin,” 162.
Babcock-Abrahams, “Tolerated Margin,” 161.
Hyde, Trickster, 13.
Ingrid Crepeau,作者采访,2015年8月8日。
Cambridge Academic Content Dictionary, s.v. “kit,” 访问于2019年4月16日,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kit.
“Mountaineer Masco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访问于2019年4月16日, https://birthday.wvu.edu/traditions/mountaineer-mascot.
Doddridge, Dialogue, 43.
Doddridge, Dialogue, 43.
第一章
“Senator Manchin’s Newsletter: A West Virginia Day Message,” 作者收到的电子邮件,2017年6月20日。
“West Virginia Statehood,” West Virginia Department of Arts, Culture and History, 访问于2017年7月11日, http://www.wvculture.org/history/archives/statehoo.html.
“West Virginia Statehood.”
“West Virginia Statehood.”
Williams, West Virginia, 36.
Harkins, Hillbilly, 14.
Harkins, Hillbilly, 14.
Isenberg, White Trash, 53.
Isenberg, White Trash, 115.
Isenberg, White Trash, 107–8.
Isenberg, White Trash, 106.
Isenberg, White Trash, 106–7.
Isenberg, White Trash, 114.
Isenberg, White Trash, 149.
“Why Do So Many Americans Think They Have Cherokee Blood?” Slate, October 1, 2015,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history/2015/10/cherokee_blood_why_do_so_many_americans_believe_they_have_cherokee_ancestry.html.
Isenberg, White Trash, 114–15.
Isenberg, White Trash, 112.
Eby, “Dandy versus Squatter,” 33–34.
Twain, “The Dandy Frightening the Squatter,” 6.
Doddridge, Dialogue, 43.
Doddridge, Dialogue, 49.
Doddridge, Dialogue, 49.
Doddridge, Dialogue, 46.
Eby, “Dandy versus Squatter,” 36.
Doddridge, Dialogue, 43–44.
Doddridge, Dialogue, 41–42.
Heale, “Role of the Frontier,” 409, 411.
Heale, “Role of the Frontier,” 407.
Botkin, A 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 3.
Isenberg, White Trash, 105.
Eby, “Dandy versus Squatter,” 34.
Isenberg, White Trash, 116.
Isenberg, White Trash, 113.
Heale, “Role of the Frontier,” 423.
Isenberg, White Trash, 124.
Isenberg, White Trash, 119.
Isenberg, White Trash, 119.
Isenberg, White Trash, 117.
Isenberg, White Trash, 117.
Heale, “Role of the Frontier,” 406.
Heale, “Role of the Frontier,” 415, 417.
Isenberg, White Trash, 129.
Heale, “Role of the Frontier,” 423.
Stoll, Ramp Hollow, 28.
Isenberg, White Trash, 135.
Isenberg, White Trash, 167.
Klotter, “Black South,” 837.
Williams, West Virginia, 38.
Williams, West Virginia, 38.
Stoll, Ramp Hollow, 15.
Isenberg, White Trash, 118.
Harkins, Hillbilly, 15.
Isenberg, White Trash, 172.
Harkins, Hillbilly, 19.
Harkins, Hillbilly, 26–27.
Twain, Huckleberry Finn, 195.
Harkins, Hillbilly, 127.
Harkins, Hillbilly, 35–36.
Harkins, Hillbilly, 35–36.
Harkins, Hillbilly, 37–38.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8, 126.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27, 129.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8.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0–101.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1.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1.
Catte, What You Are Getting Wrong, 43.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3, 115.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4.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5.
Williams, West Virginia, 106.
Batteau,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59–60.
Batteau,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61; Stoll, Ramp Hollow, 205.
Batteau,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63. 关于福克斯的小说和故事对阿巴拉契亚认知的巨大影响还有更多要说。参见Batteau在Invention of Appalachia第64–74页对福克斯小说主题的深入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以及Stoll在Ramp Hollow第202–7页对福克斯作品在世纪之交阿巴拉契亚工业和环境变化背景下的有趣分析。
Stoll, Ramp Hollow, 205.
Batteau,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74.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1.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6.
Klotter, “Black South,” 844.
Klotter, “Black South,” 844.
Klotter, “Black South,” 840.
Klotter, “Black South,” 842.
Klotter, “Black South,” 845.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1.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2, 313.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6.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3.
Frost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经常歪曲事实。在”Southern Mountaineer”中,他声称在内战期间,“整个山区都忠于”联邦(304页)。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但考虑到Frost的目标是促使北方慈善家慷慨捐赠给Berea,这是一个好故事。忠诚的山地居民远比他们支持南部联盟的贫穷白人更值得援助。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9(强调为后加)。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8.
Frost, “Contemporary Ancestors,” 319.
Klotter, “Black South,” 846.
Klotter, “Black South,” 847.
Harkins, Hillbilly, 44.
Harkins, Hillbilly, 49.
“WVU’s Mountain Honorary to Celebrate Centennial,” WVU Today Archive,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April 15, 2004, http://wvutoday-archive.wvu.edu/n/2004/04/15/3998.html.
Clay Crouse在1927年担任第一位非官方的Mountaineer,但Hill是第一位正式选出的WVU Mountaineer。参见”History of the Mountaineer,”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updated January 29, 2019, https://mountaineer.wvu.edu/history.
3. Sonja Wilson,西弗吉尼亚大学员工,与作者的讨论,2014年6月27日;“150 Years of Mountaineers Going First,” Daily Athenaeum,2016年2月6日;“Mountaineer Mascot,” 西弗吉尼亚大学,访问于2019年4月16日,https://birthday.wvu.edu/traditions/mountaineer-mascot。
4. Doherty 和 Summers,West Virginia University,104。
5. Doherty 和 Summers,West Virginia University,57。
6. Bobcats versus Mountaineers,纪念节目单,1933年11月18日,14。
7. Harkins,Hillbilly,49。
8. Abramson 和 Campbell,“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239。
9. Doddridge,Dialogue,46。
10. Williams,West Virginia,97,101。
11. Williams,West Virginia,199–200。
12. Harkins,Hillbilly,49。
13. Gainer,“Hillbilly”。
14. Harkins,Hillbilly,76。
15. Harkins,Hillbilly,86。
16. Harkins,Hillbilly,103。
17. Harkins,Hillbilly,155。
18. Harkins,Hillbilly,154–55。
19. Harmon,Hillbilly Ballads,无页码。
20. “Roy Lee Harmon,” Hillbilly Music,访问于2019年4月16日,http://www.hillbilly-music.com/artists/story/index.php?id=16352。
21. Li’l Abner,维基百科,编辑于2019年3月29日,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27l_Abner#Setting_and_fictitious_locales。
22. Harkins,Hillbilly,84–85。
23. “Mountaineer Mascot,” 西弗吉尼亚大学,访问于2019年4月16日,https://birthday.wvu.edu/traditions/mountaineer-mascot。
24. “The Mountaineer,” WVUSports,访问于2019年4月16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4025837/www.wvusports.com/page.cfm?section=9614。
25. Jerry Bruce Thomas,“The Great Depression,” 西弗吉尼亚百科全书,修订于2012年8月9日,https://www.wvencyclopedia.org/articles/2155。
26. Mangione,The Dream and the Deal,45–46。
27. Thomas,“Nearly Perfect State,” 105。
28. Thomas,“Nearly Perfect State,” 100。
29. Thomas,“Nearly Perfect State,” 99。
30. Thomas,“Perfect State,” 102。
31. Thomas,“Perfect State,” 99。
32. Armstrong,“Southern Mountaineers,” 539。
33. Armstrong,“Southern Mountaineers,” 540。
34. Armstrong,“Southern Mountaineers,” 540。
35. Armstrong,“Southern Mountaineers,” 541。
36. Hurston,Mules and Men,2–3。
37. Harkins,Hillbilly,141。
38. Harkins,Hillbilly,136。
39. Howe,“History of WVU,” 西弗吉尼亚大学,访问于2018年7月27日,http://www.as.wvu.edu/cwc/WVU-history-bhowe.html。
40. Howe,“History of WVU”。
41. Doherty 和 Summers,West Virginia University,193。
42. “Timeline,” 12。
43. Howe,“History of WVU”。
44. Upton,“Hillbilly,” 23。
45. WVU Monticola,1948,97。
46. WVU Monticola,1948,97。
47. Shirley Doubleday Baker,致Trinity Hall同学会小组的信,通过Tom Ferris转交,2007年4月17日。
48. WVU Monticola,1947,1和14–20。1947年年鉴显然也用来纪念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学生。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Irvin Stewart在致一位阵亡军人父母的信中写道:“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是退伍军人,将他们的年鉴献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捐躯的本校学生和校友。他们寄给您一本[1947年年鉴],因为您的儿子是受此纪念的人之一。” Irvin Stewart致Urbanoff夫妇,1948年1月16日,Stewart Display,通信,A&M 690,331号箱。
49. WVU Monticola,1947,12–13,272–73。
50. “Yosef”。
51. Nello Anotonucci,William Howard Atkinson,Daniel J. Dowling,Tom Ferris,David B. Hathaway,Don Kersey和George Lewis与作者的讨论,2007年4月20日。
52. Anotonucci等人与作者的讨论。
53. WVU Monticola,1948,8。
54. David B. Hathaway,致作者的电子邮件,2007年10月29日。“文明的薄薄外衣”(thin veneer of civilization)这个短语并非Brawner创造。Google Ngram显示它自1870年代以来就在使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出现在阿巴拉契亚作家John Fox Jr.的小说The Kentuckians中,当角色Reynolds告诉一位记者”在山区生活一年之前,人们不知道文明是多么薄薄的一层外衣”(引自Stoll的Ramp Hollow,205页)。虽然我确信Brawner并非引用Fox的话,但有趣的是,Brawner和Fox都将”hillbilly行为”解释为这层外衣剥蚀的结果。
55. “Mountaineer Week,” 西弗吉尼亚大学,最后更新于2019年4月10日,https://mountaineerweek.wvu.edu/about。
56. 参见Bakhtin的Rabelais and His World了解更多Bakhtin关于狂欢化(carnivalesque)的理论。
57. Doherty 和 Summers,West Virginia University,189。
58.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Bulletin,36。
59. Barra, “Davy Crockett Returns (on DVD),” 31.
60. King, “The Recycled Hero,” 138.
61. Griffin, “Kings of the Wild Backyard,” 102.
62. Griffin, “Kings of the Wild Backyard,” 102.
63. Griffin, “Kings of the Wild Backyard,” 112–13.
64. 迪士尼《Davy Crockett》的主演Fess Parker后来在NBC电视台1964年至1970年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中扮演了Daniel Boone。这种跨界演出凸显了Crockett和Boone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融合成为单一民间英雄形象的方式。
65. King, “Recycled Hero,” 151.
66. Nadel, “Johnny Yuma Was a Rebel,” 57.
67. Blair, “Six Davy Crocketts,” 449.
68. Blair, “Six Davy Crocketts,” 455–59.
69. Roger Tompkins致Irvin Stewart,1957年5月15日。Stewart Display, Correspondence, A&M 690, box 331, WVRHC.
70. Irvin Stewart致Roger Tompkins,1957年5月22日。Stewart Display, Correspondence, A&M 690, box 331, WVRHC.
71. Irvin Stewart致Boris Belpuliti,1957年5月22日。Stewart Display, Correspondence.
72. Irvin Stewart致Ruth Robinson,1957年5月22日。Stewart Display, Correspondence.
73. Ruth Robinson致Irvin Stewart,1957年5月28日。Stewart Display, Correspondence.
74. Griffin, “Kings of the Wild Backyard,” 110.
75. Smith-Rosenberg, “Davy Crockett as Trickster,” 93–95.
76. 2012年底,YouTube上出现了一段标题为”WVU山地人用火枪射杀熊”的视频。视频中,2012-14届山地人Jonathan Kimble在WVU战歌的伴奏下,用他的官方山地人步枪射杀了一只幼熊。尽管该视频很快被删除,Kimble随后也进行了道歉,但这仍然为Davy Crockett与山地人的联系增添了持续的共鸣,因为Crockett传说的很大一部分就与他”三岁时射杀了一只熊”有关,正如电视主题曲所唱的那样。
77. Nadel在他的文章中讨论了Brown案件与Crockett热潮之间可能的联系。参见上文[注66]。
1. “州官员向费耶特协会发表讲话”,《贝克利(西弗吉尼亚州)先驱邮报》,1967年7月11日,第6版。
2. Haines, West Virginia.
3. Thorn and Rubin, Mountaineer Statue, 7.
4. Thorn and Rubin, Mountaineer Statue, 9.
5. Thorn and Rubin, Mountaineer Statue, 11, 15.
6. Thorn and Rubin, Mountaineer Statue, 13–25.
7. “越南战争”,History.com,2019年2月22日更新,http://www.history.com/topics/vietnam-war/vietnam-war-history。
8. Thorn and Rubin, Mountaineer Statue, 15.
9. “William Richar [原文如此] McPherson”,Wall of Faces,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2019年6月20日访问,https://www.vvmf.org/Wall-of-Faces/37237/WILLIAM-R-MCPHERSON/。
10. “William Richar [原文如此] McPherson”,Wall of Faces.
11. Jeffrey M. Leatherwood,“越南战争”,《西弗吉尼亚百科全书》,2010年11月5日修订,https://www.wvencyclopedia.org/articles/869;Dennis Imbrogno,“从西弗吉尼亚人的视角看越南”,《查尔斯顿公报邮报》,2017年9月14日,https://www.wvgazettemail.com/_arts__entertainment/vietnam-seen-through-west-virginians-eyes/article_8fdc333c-78e1-5e19-a74f-83d177e9a8d5.html。
12. 关于这项工作的精彩论述,参见Whisnant,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
13. Catte, What You Are Getting Wrong, 82.
14. Webb-Sunderhaus and Donehower编,Rereading Appalachia, 4.
15. Bingman, “Stopping the Bulldozers,” 29.
16. Hennen,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130–31.
17. SDS成员Scott Bills获得的FBI报告,Bills文件,A&M 2828,WVRHC。
18. “Dadministration”,WVU SDS分会传单,WVU学生反战运动文件,A&M 2506,WVRHC。
19. “Dadministration”,传单,WVRHC。
20. “Dadministration”,传单,WVRHC。
21. Bills文件,A&M 2828,WVRHC。
22. Hennen,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140.
23. Drobney, “A Generation in Revolt,” 107. 关于WVU和更广泛的摩根敦社区协同反战活动的更多信息,参见Sutton的优秀文章”Have You Bought Enough Vietnam?”
24. “这里确实有’激进分子’,但不太可能发生对抗”,《摩根敦邮报》,1969年10月1日,1B,8B。
25. “加入MFP”,宣传册,WVU学生反战运动文件,A&M 2506,WVRHC。
26. “加入MFP”,宣传册,WVRHC。
27. “加入MFP”,宣传册,WVRHC。
28. Doddridge, Dialogue, 50.
29. Scott Bills MFP竞选海报,Bills文件,A&M 2828,WVRHC。
30. “里根获加州州长提名”,History.com,2019年3月1日更新,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reagan-nominated-for-governor-of-california。
31. “人物简介:James A. Rhodes”,History Commons,2019年4月19日访问,http://www.historycommons.org/entity.jsp?entity=james_a__rhodes_1。
32. “May 1970 Student Antiwar Strikes,” Mapping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访问于2019年6月20日, http://depts.washington.edu/moves/antiwar_may1970.shtml.
33. Doug Townshend与作者的讨论,2015年7月1日。
34. Robert Lowe与作者的讨论,2015年8月7日。
35. Lynne D. Boomer, “‘We’ve Got to Go beyond Surface’ of Frustrations,” 致编辑的信,Morgantown Dominion News,1970年5月9日,6A版。
36. Boomer, “Go beyond Surface,” 6A版。
37. Lowe,讨论。
38. Doug Townshend,给作者的语音留言,2016年6月7日。
39. Lowe,讨论。
40. Oldstone-Moore, Of Beards and Men,“ 235页。
41. Oldstone-Moore, Of Beards and Men, 239页。
42. Oldstone-Moore, Of Beards and Men, 243页。
43. Oldstone-Moore, Of Beards and Men, 242页。
44. Oldstone-Moore, Of Beards and Men, 244页。
45. “Mountaineer Photo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更新于2017年2月3日,https://birthday.wvu.edu/traditions/mountaineer-mascot/list-of-mountaineers/mountaineer-photos.
46. “Accused Win Continuance,” Daily Athenaeum,1970年6月25日,1版。
47. “Accused Win Continuance,” 1版。
48. “Morgantown Six Petition; No University Reply Yet,” Daily Athenaeum,1970年7月2日,1A版。
49. “Solidarity,” 传单1,日期不详,Bills文件,A&M 2828,WVRHC。
50. “Information,” 传单,日期不详,Bills文件,A&M 2828,WVRHC。
51. “Solidarity,” 传单2,日期不详,Bills文件,A&M 2828,WVRHC。
52. “Rappers Reap Harvest of Reaction,” Daily Athenaeum,1970年6月25日,无页码。
53. “Haymond Plans No Appeal on His Demotion,” Daily Athenaeum,1970年6月25日,1A版。
54. “Rappers Reap Harvest,” 无页码。
55. “Three Bomb Threats Slow Lair, Towers Activities,” Daily Athenaeum,1970年7月23日,1版。
56. “‘Security Measures’ Close ’Lair; Students Angered by Mass Eviction,” Daily Athenaeum,1970年7月23日,1版。
57. “‘Security Measures’ Close ’Lair,” 1版。
58. “‘Security Measures’ Close ’Lair,” 1版。
59. “Sunrise at WVU: To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小册子,Bills文件,A&M 2828,WVRHC。
60. “Sunrise at WVU,” 小册子,Bills文件。
61. “Brothers—Sisters!” 传单,Scott Bills文件,A&M 2828,WVRHC。
62. “Brothers—Sisters!,” 传单,Bills文件。
63. “Sunrise at WVU,” 小册子,Bills文件。
64. “Sunrise at WVU,” 小册子,Bills文件。
65. “State Joins Move to Curb Campus Disorders,” Daily Athenaeum,1970年7月23日,8版。
66. “State Joins Move,” 8版。
67. “Students Attack Code,” Daily Athenaeum,1968年9月19日,1版。
68. “Students attack code,” 1版。
69. “North Bend Statement,” Bills文件,A&M 2828,WVRHC。
70. “North Bend Statement,” Bills文件。
71. “Citizens Circulate Petition to Fight WVU ’Radicalism,” Daily Athenaeum,1970年7月9日,1版。
72. “VFW Leader, Citizens Hit at Radicalism,” Morgantown Dominion News,1970年6月24日。
73. “VFW Leader.”
74. “VFW Leader.”
75. “VFW Leader.”
76. “VFW Leader.”
77. “Hite Selected Sub Mountie for Tomorrow,” Daily Athenaeum,1968年11月1日,1版。
78. Steven Hite与作者的讨论,2018年7月18日。
79. Hite,讨论。
80. Hite,讨论。
81. Townshend,讨论;Lou Garvin与作者的讨论,2015年8月2日。
82. Townshend,讨论;Garvin,讨论。
83.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untaineer Mascot Application 2018–19,”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访问于2018年8月1日,https://students.wvu.edu/files/d/6c6bc93d-acc4-488d-a934-af384b0f9bc6/mountianeer-mascot-application-18-19.pdf.
84. “‘Buckskin Babes’ New Coliseum Attraction,” Dominion Post(晚报版),1973年12月3日,2B版。
1. Christine M. Kreiser, “Mad Anne Bailey,” West Virginia Encyclopedia,修订于2012年9月25日,https://www.wvencyclopedia.org/articles/327.
2. McNeill, Gauley Mountain, 15页。
3. Lofstead, “Trailblazers at the College of Law,” 18页。
4. Doherty and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43–44页。
5. Doherty and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36页。
6. Doherty and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45页。
7. Doherty and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64页。
8. “New Look for W. Virginia Mascot,” USA Today,1990年3月26日,2C版。
9. “Eye Openers,” St. Louis Post Dispatch,1990年8月31日,2D版。
10. Rebecca Durst与作者的讨论,2015年7月7日。
11. “Female Mascot Applicant Just Enthusiastic,” Daily Athenaeum,1990年2月27日,3版。
12. “First Woman Performs as Mountaineer Mascot,” Daily Athenaeum,1990年2月28日。
13. “首位竞选山地人吉祥物的女性,” Daily Athenaeum, 1990年2月23日, 1, 12.
14. “首位竞选山地人吉祥物的女性.”
15. “首位竞选山地人吉祥物的女性.”
16. “Tennant成为大学首位女性吉祥物,” Daily Athenaeum, 1990年3月2日, 1.
17. Kirk Bridges, “最好的男性本应获胜,” 社论, Daily Athenaeum, 1990年3月21日, 4.
18. 致编辑的信, Daily Athenaeum, 1990年4月16日, 4.
19. Bridges, “最好的男性本应获胜.”
20. 致编辑的信, Daily Athenaeum, 1990年4月4日, 4.
21. Bridges, “最好的男性本应获胜.”
22. 致编辑的信, Daily Athenaeum, 1990年4月10日, 4.
23. 致编辑的信, Daily Athenaeum, 1990年4月18日, 4.
24. 致编辑的信, Daily Athenaeum, 1990年4月18日, 4.
25. 致编辑的信, Daily Athenaeum, 1990年4月23日, 4.
26. “可悲:球迷行为令人震惊,” Daily Athenaeum, 1990年3月1日, 4.
27. “大学男生应该成熟点,把敌意留给对手,” Daily Athenaeum, 1990年9月7日, 4.
28. “可悲:球迷行为令人震惊,” 4.
29. “女性能否激励观众?” Daily Athenaeum, 1990年3月1日, 4.
30. “女性吉祥物申请者只是充满热情,” Daily Athenaeum, 1990年2月27日, 3.
31. 致编辑的信, Wall Street Journal, 1990年11月1日, A23.
32. “令人大开眼界,” St. Louis Post Dispatch, 1990年8月31日, 2D.
33. Natalie Tennant与作者的访谈, 2014年7月7日.
34. Tennant, 访谈.
35. “山地人吉祥物准备迎接工作挑战,” Daily Athenaeum, 1990年8月30日.
36. “在西弗吉尼亚,吉祥物的性别不是小事,” Wall Street Journal (东部版), 1990年9月26日, A1.
37. “大学应该有男女山地人吉祥物,” Daily Athenaeum, 1990年9月14日, 4.
38. Tennant并非这些”杯子战”的唯一目标,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学生区似乎很普遍,因为许多Daily Athenaeum的文章和社论都讨论过此事.
39. “Tennant:以优雅方式完成工作,” Daily Athenaeum, 1990年9月4日, 4.
40. “Tennant被嘘是因为她没有提升士气,” Daily Athenaeum, 1990年9月26日, 4.
41. “吉祥物:性别歧视态度让州和大学难堪,” Daily Athenaeum, 1990年9月28日, 4.
42. “谢谢你们这些笨蛋,让我们州难堪,”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4日, 4.
43. “吉祥物争议让大学难堪,”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4日, 4.
44. “大学成了刻板印象混蛋的避风港,”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3日, 4.
45. “吉祥物争议,” Daily Athenaeum, 4.
46. “如今,笑话在我们身上,”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3日, 4.
47. “真正的山地人品格:骚扰Natalie Tennant的人根本没有这种品格,”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8日, 5.
48. “Natalie Tennant不应在游行中遭受虐待,”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16日, 4.
49. “山地人在赛季收官战中毫无精神,”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2月6日.
50. “吉祥物争议是有偏见的选拔过程造成的,”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16日, 4.
51. “大学吉祥物需要新的选拔流程,” Daily Athenaeum, 1990年10月17日, 4.
52. “新山地人吉祥物面试即将开始,” Daily Athenaeum, 1991年1月24日, 3.
53. “女性和少数族裔应尝试成为下一任吉祥物,” Daily Athenaeum, 1991年1月30日, 4.
54. “四位候选人竞争吉祥物,” Daily Athenaeum, 1991年2月18日, 2.
55. “山地人队大胜公羊队,94-61,” Daily Athenaeum, 1991年2月15日.
56. “Tennant漫画纯属无谓的胡闹,” Daily Athenaeum, 1991年2月26日, 4.
57. “新山地人认为Tennant遭遇不公平对待,” Daily Athenaeum, 1991年4月29日.
58. “Tennant遭遇不公平对待,” Daily Athenaeum, 1.
59. Tennant, 访谈.
60. Durst, 访谈.
61. Tennant, 访谈; Durst, 访谈.
62. Tennant, 访谈.
63. Durst, 访谈.
64. Tennant, 访谈.
65. “女性之年,1992,” 美国众议院, 访问时间2019年4月19日, https://history.house.gov/Exhibitions-and-Publications/WIC/Historical-Essays/Assembling-Amplifying-Ascending/Women-Decade/; Alix Strauss, “自1992年’女性之年’以来的关键时刻,” New York Times, 2017年4月2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4/02/us/02timeline-listy.html.
66. Tennant, 访谈.
67. 关于这些笑话的普遍性、多样性和重要性的精彩讨论,请参见Pershing, “His Wife Seized His Prize and Cut It to Size,” 1-35.
68. “委员会选出大学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山地人”,Daily Athenaeum,2009年3月9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committee-selects-second-female-mountaineer-in-university-history/article_36ed52a5-bf07-5a56-b23e-8d7e8a9614d4.html。
69. “无胡须的故事”,Daily Athenaeum,2009年4月21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the-tale-of-no-beard/article_5fc6442c-bcbe-5ec1-9ffe-005384f37c4b.html。
70. “无胡须的故事”,Daily Athenaeum。
71. “新山地人吉祥物的选拔引发质疑”,Daily Athenaeum,2013年8月8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selection-of-new-mountaineer-mascot-raises-eyebrows/article_de3ef4a4-0676-5376-b5f6-47fd6369245e.html。
72. “吉祥物引发质疑”,Daily Athenaeum。
73. “吉祥物决赛选手将于今晚进行欢呼对决”,Daily Athenaeum,2009年3月4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mascot-finalists-to-compete-in-cheer-off-tonight/article_d7d1f970-152b-5940-ab4b-f1fb3fe7b7de.html。
74. “拥抱我们的新山地人吉祥物”,Daily Athenaeum,2009年3月9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embrace-our-new-mountaineer-mascot/article_cd4b8c3e-3b98-5f0f-8390-8c6b77ad256e.html。
75. Will Turner、Jason Zucarri、Whitney Rae Peters、Cassie Werner、Jason Parsons 和 Tommy Napier,致编辑的信,Daily Athenaeum,2009年4月23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letters-to-the-editor/article_8984bdf7-9c79-5b25-a7b4-8584e0e41d61.html。
76. Turner等人,致编辑的信。
77. “鹿皮装、步枪和欢呼——天啊”,Daily Athenaeum,2009年3月5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buckskins-and-rifles-and-cheers—oh-my/article_6c84cc9e-0dbd-5ead-a5ad-ccadd1849460.html。
78. “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评价Rebecca Durst的表现”,Daily Athenaeum,2009年9月8日,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wvu-students-weigh-in-on-rebecca-durst-s-performance/article_fdcb49e1-b672-5688-adb5-98bc276855f6.html。
79. Durst,讨论。
80. Durst,讨论。
81. Durst,讨论。
82. Durst,讨论。
83. “无胡须的故事”,Daily Athenaeum。
84. “在橄榄球比赛日,吉祥物的生活从不无聊”,Daily Athenaeum,2009年12月1日,https://www.thedaonline.com/on-football-gamedays-the-life-of-a-mascot-is-never/article_7965522f-2d77-5f6c-9bba-d094111ddc48.html。
85. “吉祥物的生活从不无聊”,Daily Athenaeum。
86. Durst,讨论。
1. Ed O’Keefe,“Joe Manchin反对MTV的’Buckwild’真人秀节目”,Washington Post,2012年12月7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2chambers/wp/2012/12/07/joe-manchin-objects-to-mtvs-buckwild-reality-show/?utm_term=.762095046c4。
2. Philiana Ng,“MTV续订’Buckwild’”,Hollywood Reporter,访问于2017年8月1日,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live-feed/mtv-renews-buckwild-418757。
3. Krishnadev Calamur,“MTV在明星去世后取消’Buckwild’”,美国国家公共电台,2013年4月10日,http://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3/04/10/176851845/mtv-cancels-buckwild-after-star-s-death。
4. Hollie McKay,“MTV是否应该在明星Shain Gandee去世后取消’Buckwild’?”,福克斯新闻,http://www.foxnews.com/entertainment/2013/04/02/should-mtv-cancel-buckwild-following-star-shain-gandees-death.html。
5. Tony Rutherford,“Buckwild演员们本应在第二季期间在亨廷顿欢呼”,HuntingtonNews.net,访问于2013年7月31日,http://www.huntingtonnews.net/68125。
6. Rutherford,“Buckwild演员们”。
7. Rutherford,“Buckwild演员们”。
8. Rutherford,“Buckwild演员们”。
9. Elizabeth Catte将此类故事定性为属于”特朗普乡村类型”,并指出它们”巩固了’极端美国’的叙事,可以根据个人目的进行谴责或救赎”(What You Are Getting Wrong,35页)。
10. Rod Dreher,“J. D. Vance关于贫困的坦率言论”,American Conservative,2016年7月25日,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dreher/jd-vance-straight-talk-about-poverty/。
11. Rod Dreher,“特朗普:贫穷白人的护民官”,American Conservative,2016年7月22日,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dreher/trump-us-politics-poor-whites/。
12. StefanieRose Miles,“作家J. D. Vance确实有乡巴佬资历——不管你喜不喜欢”,Lexington Herald Leader,2016年9月9日,https://www.kentucky.com/opinion/op-ed/article100925787.html。
13. Vance,Hillbilly Elegy,41页。
14. Vance,Hillbilly Elegy,24页。
15. Vance,Hillbilly Elegy,126页。
16. Vance,Hillbilly Elegy,40页。
17. Vance,Hillbilly Elegy,43页。
18. Vance,Hillbilly Elegy,230页。
19. Vance,Hillbilly Elegy,230页。
20. Vance,Hillbilly Elegy,8页。
21. Catte,What You Are Getting Wrong,89–90页。
22. John Thomason, “Hillbilly Ethnography,” New Inquiry, November 29, 2016, https://thenewinquiry.com/hillbilly-ethnography/.
23. Thomason, “Hillbilly Ethnography.”
24. Thomason, “Hillbilly Ethnography.”
25. “W. Va. Governor Talks Work Stoppage in Wheeling Town Hall,” WTRF.com, February 26, 2018, https://www.wtrf.com/news/education/w-va-governor-talks-work-stoppage-in-wheeling-town-hall/992616486.
26. “Sharing Our Story: Mountaineers Go Firs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February 2, 2015, https://presidentgee.wvu.edu/messages/mountaineers-go-first.
27. Vicki Smith, “W.Va. University Tops Party School Lis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1, 20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8/20/AR2007082001242_pf.html.
28. Peter Jacobs, “The Top 10 Party Schools in America According to Playboy,” Business Insider, September 26,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playboy-west-virginia-university-top-party-school-2013-9.
29. “22 fires Set Following Bin Laden’s Death in Morgantown,” Daily Athenaeum, May 2, 2011, http://www.thedaonline.com/article_72ca393e-a39b-5050-b757-e71342148fa3.html.
30. “St. Patrick’s Day Sends WVU through Culture Changes,” Daily Athenaeum, March 17, 2017, 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article_32ceb3f0-0acb-11e7-996c-2f0a9232c9dd.html.
31. “WVU, City Officials Discuss Fire Plans,” Daily Athenaeum, October 12, 2012, http://www.thedaonline.com/article_f38a74b0-79f4-5b90-903d-2bd0c38d7d7e.html.
32. “Victory Spawns Riot, Destruction,” Daily Athenaeum, October 20, 2014, 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article_63625906-5824-11e4-abd0-001a4bcf6878.html.
33. “Roughly $45k Worth of Damage from Riots,” Daily Athenaeum, October 28, 2014, 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article_f8122d32-5e5b-11e4-86b8-0017a43b2370.html.
34. Marcus Constantino, “3 WVU Students Expelled over Postgame Riots,” Charleston Gazette-Mail, October 23, 2014, http://www.wvgazettemail.com/article/20141023/DM01/141029588.
35. “President Gee to WVU Community: ‘Time to Take Our University Back,’”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October 20, 2014, http://wvutoday-archive.wvu.edu/n/2014/10/20/president-gee-to-wvu-community-time-to-take-our-university-back.html.
36. “Time to Take Our University Back.”
37. Constantino, “3 WVU Students Expelled.”
38. Doherty and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11.
39. Doherty and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11.
40. Nick Madigan, “Peace Plan in Boulder Bans Sofas on Porches,”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05/30/us/peace-plan-in-boulder-bans-sofas-on-porches.html.
41. Madigan, “Peace Plan in Boulder.”
42. Tomas Engle, “University Should Sanction Official Couch Burning Event,” Daily Athenaeum, November 16, 2011, https://www.thedaonline.com/column---university-should-sanction-official-couch burning-event/article_84bd2dca-a49e-577e-9d1f-1fe828c8db41.html.
43. Football Jesus (@westva75), “#kroger wouldn’t sell us a burning couch cake bc apparently it ‘promotes bad behavior.’ Settled for football Jesus,” Twitter, November 18, 2017, https://twitter.com/westva75/status/931931375107805184.
44. Bryan Bumgardner, “Couch Fires Really a True WVU Tradition,” Daily Athenaeum, December 5, 2012, http://www.thedaonline.com/article_5ec897ac-0002-52ca-846f-cc008f4a428b.html.
45. Taylor Jobin,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Mountaineers Go Hard,” Daily Athenaeum (graduation edition), May 2015, 20–21.
46. “The Battle of Spruce Street,” Daily Athenaeum, February 4, 2019, 1.
47. William Dean, “Police Disperse Spruce Street Block Party after Crowd Hurls Bottles,” Dominion Post, February 1, 2019, https://www.dominionpost.com/2019/02/01/spruce-street-party-turns-to-riot/.
48. Bronner, Campus Traditions, 202.
49. Mazzella,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20.
50. Evelyn Merithew, “Recuperating from News of Riot,” Daily Athenaeum, October 21, 2014, 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article_5c320dc8-58da-11e4-abe6-001a4bcf6878.html.
51. Alexis Randolph, “SGA Discusses Aquatic, Community Center, Club Hockey Team,” Daily Athenaeum, October 23, 2014, 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article_8e296544-5a7c-11e4-9582-0017a43b2370.html.
52. Constantino, “3 WVU Students Expelled.”
53. William Dean, “Eleven Facing Charges for February Snow Day Riot,” Dominion Post, March 6, 2019, https://www.dominionpost.com/2019/03/06/eleven-facing-charges-for-february-snow-day-riot/.
54. “WVU Student Population: Who Goes Here?” Collegefactual.com, accessed April 19, 2019, https://www.collegefactual.com/colleges/west-virginia-university/student-life/diversity/.
55. 我一直很惊讶的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生群体之间的冲突在课堂上并不经常爆发。当然,当外州学生吹嘘自己家乡州的某些特殊之处时,我也见过一些土生土长的西弗吉尼亚人翻白眼。但总的来说,这两个群体至少在课堂上和平共处。
56. “个性”,西弗吉尼亚大学品牌中心,访问于2019年4月21日,https://brand.wvu.edu/brand-guide/voice/personality。
57. “身份”,西弗吉尼亚大学品牌中心,访问于2019年4月21日,https://brand.wvu.edu/brand-guide/identity。
58. “纽约酷儿国度:我们的历史”,纽约酷儿国度,更新于2016年8月25日,https://queernationny.org/history。
59. 据传闻,关于大学品牌的调查显示,人们认可飞翔WV标志并觉得它很吸引人,但对于基于Lair前雕像的山地人标志持中立态度。一些受访者显然声称,山地人标志暗示只有白人男性才能成为山地人,可能会使一些学生无法认同大学的品牌。
60. “我们的受众”,西弗吉尼亚大学品牌中心,访问于2019年4月21日,https://brand.wvu.edu/brand-positioning/our-audiences。
61. Claire Hansen,“一所旗舰大学的提议口号——‘世界需要更多牛仔’——在西部引发争议”,《高等教育纪事报》,2018年7月10日,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Flagship-s-Proposed-Slogan/243883。
62. Diana Mazzella,“群山中的家”,《WVU杂志》,2017年3月29日,https://magazine.wvu.edu/stories/2017/03/29/home-among-the-hills。
63. Mazzella,“群山中的家”。
64. Sara Berzingi,“来自WVU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的一封信”,《每日雅典娜神殿报》,2016年11月3日,http://www.thedaonline.com/opinion/a-letter-from-the-wvu-muslim-student-association-president/article_b1df514a-a239-11e6-a459-0392c88a817a.html。
65. Sara Berzingi,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18年7月2日。
66. “’氛围调查’显示总体安全感,但承认存在问题”,WVU今日,西弗吉尼亚大学,2017年2月17日,https://wvutoday.wvu.edu/stories/2017/02/17/-climate-survey-shows-general-feeling-of-safety-but-acknowledges-issues。
67. “校园携枪在WVU校园可能是什么样子”,《每日雅典娜神殿报》,2019年2月17日,http://www.thedaonline.com/news/what-campus-carry-could-look-like-on-wvu-s-campus/article_f363e9ea-331a-11e9-a48a-43fffd74bd71.html。
68. 尽管大学已经撤下了关于HB 2519的原始FAQ页面,但缓存的html版本可在https://governmentrelations.wvu.edu/files/d/ce5599a3-5511-4a7a-9b2e-f1925d828198/campuscarry.pdf获取。
69. WV众议院法案2519,校园携枪,第三次宣读,YouTube,https://youtu.be/YulkQBlZ5VQ?t=7234。
70. Jake Zuckerman,“反穆斯林展示在西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引发冲突”,《查尔斯顿公报邮报》,2019年3月1日,https://www.wvgazettemail.com/news/legislative_session/anti-muslim-display-sparks-con;ict-at-wv-capitol/article_728c7654-9b4c-5b32-b45f-5b224ce866bb.html。
71. “Porterfield坚持对LGBTQ社区的声明”,WVVA.com,2019年2月10日,https://wvva.com/news/top-stories/2019/02/10/delegate-porterfield-stands-by-his-statements-regarding-the-lgbtq-community/。
72. Bill Schackner,“在WVU,‘传递步枪’为新山地人加冕,为另一位结束’最伟大的经历’”,《匹兹堡邮报》,2019年3月11日,https://www.post-gazette.com/news/education/2019/03/11/West-Virginia-University-WVU-Mountaineer-mascot-Eads-Kiess-colllege-football-higher-education/stories/201903080084。
73. Taylor Giles,“关于校园携枪的真相”,《每日雅典娜神殿报》,2019年2月24日,http://www.thedaonline.com/opinion/the-truth-about-campus-carry/article_f732ac42-38a5-11e9-9ecb-3f11d3235ef6.html。
74. “WVU历届奥运选手(按奥运会)”,WVU体育,访问于2019年4月28日,https://wvusports.com/sports/2018/1/31/all-time-wvu-olympians-by-olympiad.aspx。
75. “更新:允许在西弗吉尼亚校园隐蔽携枪的法案未通过”,WTAP.com,2019年3月5日,https://www.wtap.com/content/news/WVa-lawmakers-listen-to-comments-on-campus-carry-bill-505686431.html。
76. “Michael Brown:我作为圣母大学小矮妖的岁月”,WBUR,2015年10月17日,https://www.wbur.org/onlyagame/2015/10/17/notre-dame-leprechaun-mascot。
77. “圣母大学将迎来首位女性小矮妖吉祥物”,《国会山报》,2019年4月18日,https://thehill.com/blogs/blog-briefing-room/news/439614-university-of-notre-dame-to-have-first-female-leprechaun-mascot。
Abramson, Rudy, and Roberta M. Campbell. “种族、族裔和身份”。收录于《阿巴拉契亚百科全书》,Rudy Abramson和Jean Haskell编辑,239–45页。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2006年。
Armstrong, Anne. “南方山区居民”。《耶鲁评论》24期(1935年3月):539–43页。
Babcock-Abrahams, Barbara. “‘容忍的混乱边缘’:对骗子及其故事的重新考虑”。《民俗学研究所期刊》11卷第3期(1975年):147–86页。
Bakhtin, Mikhail.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ra, Allen. “Davy Crockett Returns (on DVD).” American Heritage 53, no. 2 (May 2002): 31.
Batteau, Allen W. The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Bills, Scott. Papers. A&M 2828. West Virginia and Regional History Center,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Libraries, Morgantown.
Bingman, Mary Beth. “Stopping the Bulldozers: What Difference Did It Make?” In 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Traditions of Resistance and Change, edited by Stephen L. Fisher, 17–3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lair, Walter. “Six Davy Crocketts.” Southwest Review 25 (1940): 443–62.
“Bobcats versus Mountaineers.” Souvenir program, November 18, 1933.
Botkin, B. A., ed. A 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 Stories, Ballads, 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44.
Bronner, Simon. Campus Traditions: Folklore from the Old-Time College to the Modern Mega-University.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2.
Catte, Elizabeth. What You Are Getting Wrong about Appalachia. Cleveland: Belt Publishing, 2018.
Doddridge, Joseph. The Dialogue of the Backwoodsman and the Dandy, in Logan: The Last Race of Shikellemus, Chief of the Cayuga Nation. A Dramatic Piece to which Is Added the Dialogue of the Backwoodsman and the Dandy, First Recited at the Buffaloe Seminary, July the 1st, 1821. Cincinnati: Robert Clarke & Co., 1868.
Doherty, William T., Jr., and Festus P. Summer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Symbol of Unity in a Sectionalized State.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Drobney, Jeffrey. “A Generation in Revolt: Student Dissent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a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West Virginia History 54 (1995): 105–22.
Eby, Cecil D. “Dandy versus Squatter: An Earlier Round.”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20, no. 1 (1987): 33–36.
Frost, William G. “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s.”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899, 311–19.
———.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 Our Kindred of the Boone and Lincoln Typ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21 (1900): 304–5.
Gainer, Patrick Ward. “Hillbilly.” Unpublished, undated manuscript. Ward Papers. A&M 3003. West Virginia and Regional History Center,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Libraries, Morgantown.
Griffin, Sean. “Kings of the Wild Backyard: Davy Crockett and Children’s Space.” In Kids’ Media Culture, edited by Marsha Kinder, 102–1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ines, Thomas. West Virginia as Seen by Man Child-Tom. Charleston, WV: Faith Workshop, n.d.
Harkins, Anthony. Hillbilly: A Cultural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c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armon, Roy Lee. Hillbilly Ballads. Beckley, WV: Beckley Newspapers Corporation, 1938.
Heale, M. J.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Jacksonian Politics: David Crockett and the Myth of the Self-Made Man.”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4, no. 4 (1973): 405–23.
Hennen, John.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arshall University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the Red Scare in Huntington, 1965–1969,” West Virginia History 52 (1993): 127–47.
Hurston, Zora Neale. Mules and Men.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935. Reprinted with a foreword by Arnold Rampersad and an afterword by Henry Louis Gates J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Hyde, Lewis. Trickster Makes This World: Mischief, Myth, and Ar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8.
Isenberg, Nancy.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2016.
King, Margaret J. “The Recycled Hero: Walt Disney’s Davy Crockett.” In Davy Crockett: The Man, the Legend, the Legacy, 1786–1986, edited by Michael A. Lofaro, 137–58.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5.
Klotter, James C. “The Black South and White Appalach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no. 4 (March 1980): 832–49.
Lofstead, Becky. “Trailblazers at the College of Law.”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Alumni Magazine 23, no. 1 (Winter 2000): 18.
Mangione, Jerre. The Dream and the Deal: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1935–1943. New York: Avon Books, 1972.
Mazzella, Diana.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WVU Magazine, Fall 2014, 20.
McNeill, Louise. “Ballad of Mad Ann Bailey.” Gauley Mounta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9.
Nadel, Alan. “‘Johnny Yuma Was a Rebel; He Roamed through the West’: Television, Race, and the Real West.” In Reality Squared: Televisual Discourse on the Real, edited by James Friedman, 50–74.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Oldstone-Moore, Christopher. Of Beards and Men: The Revealing History of Facial Hai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ershing, Linda. “‘His Wife Seized His Prize and Cut It to Size’: Folk and Popular Commentary on Lorena Bobbitt.” NWSA Journal 8, no. 3 (1996): 1–35.
Radin, Paul. The Trickster: A Study in American Indian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 1956.
Smith-Rosenberg, Carroll. “Davy Crockett as Trickster: Pornography, Liminality, and Sexuality.” In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90–108. New York: Knopf, 1985.
Stewart Display, Correspondence. West Virginia and Regional History Center,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Libraries,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Stoll, Steven. Ramp Hollow: The Ordeal of Appalachi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7.
Sutton, Nora. “‘Have You Bought Enough Vietnam?’: The Vietnam Antiwar Movement a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67–1970.” West Virginia History 13, no. 1 (Spring 2019): 27–55.
Thomas, Jerry B. “‘The Nearly Perfect State’: Governor Homer Adams Holt, the WPA Writers’ Project and the Making of West Virginia: A Guide to the Mountain State.” West Virginia History 52 (1993): 91–109.
Thorn, Gordon R., 和 Scott B. Rubin. The Mountaineer Statue.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006.
“Timeline.”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Alumni Magazine 34, no. 1 (2011): 4–18.
Twain, Mark.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Charles L. Webster and Company, 1885. Reprinted with a foreword by Victor Fischer and Lin Salam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The Dandy Frightening the Squatter.” Carpet-Bag 2, no. 5 (1852): 6.
Upton, Elsie. “Hillbilly.” Rayburn’s Ozark Guide 19 (1948): 22–23.
Vance, J. D.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6.
Webb-Sunderhaus, Sara, 和 Kim Donehower, eds. Rereading Appalachia: Literacy, Place,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Bulletin 51, nos. 12–22 (June 1951), 36.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Student Anti-War Movement papers. A&M 2506. West Virginia and Regional History Center,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Libraries,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nticola yearbook.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1947. Accessed June 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monticola1947west.
———. Monticola yearbook.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1948. Accessed June 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monticola1948west.
Whisnant, David E. 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n American Reg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Williams, John Alexander. West Virginia: A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4.
图 1.1. 西弗吉尼亚州州务卿网站。
图 1.2. 维基共享资源。
图 1.3. 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LC-DIG-pga-04179, https://www.loc.gov/item/93511184/。
图 1.4. Justin Howard,插画师。“Sut Lovingood’s Daddy-Acting Horse”,选自 George Washington Harris 的 Sut Lovingood Yarns。纽约:Dick & Fitzgerald, 1867。
图 1.5. A&M 2537, Ballard Collection,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2.1.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2.2.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2.3. 图片由 Randy McNutt 提供,King Records of Cincinnati 作者(Mount Pleasant, SC: Arcadia Publishing, 2009)。
图 2.4. Paul Webb,“The Mountain Boys”,俄亥俄州托莱多 Electric Auto-Lite Company 发行的宣传手册,无日期。此艺术作品的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目的。
图 2.5. 作者收藏。
图 2.6. 作者收藏。
图 2.7. Monticola,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1948。
图 2.8. Monticola,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1947。
图 2.9. Monticola,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1947。
图 2.10. Monticola,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1947。
图 2.11. Moonshine 3, no. 5, 1949, 1。
图 2.12. 作者收藏。
图 2.13. 作者收藏。
图 2.14. Monticola,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1948。
图 2.15.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Bulletin 51, nos. 12–22 (1951): 36。
图 2.16. 宣传照片。
图 3.1. Haines, Thomas. West Virginia as Seen by Man Child-Tom. Charleston, WV: Faith Workshop, 无日期。此艺术作品的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目的。
图 3.2. Haines, Thomas. West Virginia as Seen by Man Child-Tom. Charleston, WV: Faith Workshop, 无日期。此艺术作品的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目的。
图 3.3.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4.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5. Scott Bills 档案,A&M 2828,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6. WVU 学生反战运动档案,A&M 2506,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7. Scott Bills 档案,A&M 2828,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8. Scott Bills 档案,A&M 2828,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9. Doug Townshend 提供。
图 3.10. WVU 大学关系部摄影。
图 3.11.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3.12. Richard P. Rogers 摄影,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4.1.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4.2. 西弗吉尼亚与区域历史中心,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图 4.3. 插图选自 American Magazine 12 (1881): 605。Science History Images / Alamy Stock Photo。
图 4.4. WVU 大学关系部摄影。
图 5.1. 宣传照片。
图 5.2. 作者摄影。
图 5.3. 作者摄影。
图 5.4. 作者摄影。
图 5.5. WVU 大学关系部 Instagram 帖子;Raymond Thompson Jr. 摄影。
图 5.6. Pastor Matthew J. Watts 和艺术家们提供。
斜体页码指图片。
Abramson, Rudy, 65
非裔美国人:在贝里亚学院,[53]、[56];与贫穷/乡村白人的比较,[26]、[45]、[53]–[54]、[57]、[64];以及阿巴拉契亚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64]–[65]、[78];作为吉祥物,[225];以及向贫困宣战,[119];以及警察暴力,[199];关于其的伪科学声明,[195];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反应,[80]–[81];在西弗吉尼亚大学,[83]–[84]、[121]、[216]。另见 种族
阿拉巴马州,[24]、[45]、[74]
阿尔索普,罗布(西弗吉尼亚大学副校长),[218]–[19]
美国保守派(杂志),[193]
美国指南系列,[76]–[79]、[83]
安迪·格里菲斯秀(电视剧),[119]
盎格鲁-撒克逊,作为白人的委婉语,[22]、[51]、[55]、[58]、[64]–[65]、[73]、[78]–[79]、[83]
安东努奇,内洛,[97]
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119]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3]、[4]、[92]–[93]
阿肯色州,[24]、[45]–[46]、[74]、[192]
阿肯色旅行者,[45]
阿姆斯特朗,安妮,[78]–[82]
阿姆斯特朗,哈拉克,[45]
阿姆斯特朗,简,[161]
阿诺德,博伊德(“瘦子”),[60]、[63]
阿诺德,埃迪,[105]
阿什比,布鲁克,[222]
阿奇逊,理查德,[139]
雅典,西弗吉尼亚州,[1]–[2]
阿特金森,霍华德,[97]
大西洋月刊(杂志),[55]
巴布科克-亚伯拉罕斯,芭芭拉,[8]–[9]
山林居民(backwoodsman):安德鲁·杰克逊和大卫·克罗克特作为其代表,[35]–[39]、[40];以及阶级意识,[65]–[66];与穷白垃圾的对比,[42]、[48];以及边疆生活的衰落,[31]–[34]、[49];与美洲原住民的关系定义,[25]–[26]、[43];与花花公子的对比,[6]、[28]–[33]、[65]、[97]、[126]、[149]、[220];与当代文化中的花花公子对比,[192]–[93]、[196]–[99];早期概念,[25]–[28]、[33]–[34];其服装,[16]、[76];对山地人的影响,[22]、[24]、[34]、[103]、[106]、[149];作为高尚/榜样,[70]、[103]、[106]、[112];与山地乡巴佬(hillbillies)的相似之处,[74]
贝利,“疯狂”安妮,[153]、[157]
贝利,蒂姆,[170]
巴赫金,米哈伊尔,[101]、[234n56]
“大卫·克罗克特之歌”(歌曲),[105]
巴拉,艾伦,[104]、[105]
巴托,艾伦,[51]、[231n74]
普莱森特角战役(1774年),[153]
胡须: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与,[138]–[41]、[150];山地乡巴佬外貌与,[48]、[93]、[110]–[11]、[112];作为山地人装备的一部分,[16]、[111]、[121];以及针对女性山地人的性别歧视,[156]、[159]、[177]–[78]、[182]、[186]、[222];以及约瑟夫(吉祥物),[3]、[93]。另见 山地人装备
贝尔普利蒂,鲍里斯,[108]
贝里亚学院,[3]、[51]–[55]、[57]、[64]
贝尔津吉,萨拉,[216]、[221]
贝茨,弗兰克,[162]
贝弗利山乡巴佬(电视剧),[119]
黑三角,[226]
布莱尔,沃尔特,[106]
比尔斯,斯科特,[xi]、[122]–[24]、[127]、[128]、[141]–[44]
宾曼,玛丽·贝丝,[120]
博阿斯,弗朗茨,[7]
博比特,洛雷娜,[176]
博格斯,马克,[x]
布默,琳恩·D.,[135]–[36]
布恩,丹尼尔,[105]、[157]、[162]、[234n64]
博特金,本杰明,[33]–[34]、[36]
博尔德,科罗拉多州,[202]
布尔丹,安东尼,[218]
博伊德,贝尔,[162]
布劳纳,詹姆斯·保罗,[100]–[101]、[148]、[204]、[234n54]
布里奇斯,柯克,[159]、[161]
布朗,迈克尔(圣母大学吉祥物),[225]
布朗,迈克尔(密苏里州弗格森),[199]、[201]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美国最高法院案件),[84]、[109]
七叶树布鲁图斯(Brutus Buckeye)(俄亥俄州立大学吉祥物),[2]
布卡,丹尼尔,[147]–[48]
布卡,弗兰克,[147]–[48]
鹿皮宝贝(Buckskin Babes),[152]
鹿皮服装,[16]、[25]、[75]、[82]、[90]、[94]、[102]、[105]–[6]、[183]–[85]、[188]。另见 山地人装备
野孩子(电视剧),[11]、[189]–[92]
伯威尔,布洛克,[x]、[180]
布什,乔治·H·W(美国总统),[170]
伯德,罗伯特(美国参议员),[124]
伯德,威廉,[23]–[24]
柬埔寨,美国入侵。见 越南战争
坎贝尔,布雷迪,[x]、[173]
坎贝尔,罗伯塔,[65]
校园自卫法案(HB 2519),[218]–[19]、[224]、[245n68]
卡普,阿尔,以及小阿布纳漫画,[46]、[70]、[74]–[75]、[166]
卡拉瓦索斯,马克,[200]
卡洛大学,[130]
卡内基梅隆大学,[130]
狂欢式(carnivalesque),[101]、[234n56]
卡塞尔,鲍勃,[120]
卡特,伊丽莎白,[49]、[195]、[242n9]
塞鲁利,黛安,[182]
查尔斯顿,西弗吉尼亚州,[110]、[190]、[219]、[224]、[226]
查塔姆大学,[130]
欢呼比赛(cheer-off),[159]、[162]、[170]–[71]、[178]、[182]。另见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选拔流程
芝加哥七人组,[142]
芝加哥论坛报(报纸),[139]–[40]
美国内战,[10]、[16]、[19]、[21]、[41]、[64]、[232n88]
内战重演者,[16]
克拉克斯堡,西弗吉尼亚州,[29]、[42]
克莱,亨利(美国参议员),[37]
克林顿,希拉里·罗德姆,[176]
克林顿,威廉·“比尔”·杰斐逊(美国总统),[176]
煤炭,[47]
煤矿开采,[65]–[66]、[77]、[87]、[166]、[190]、[193]、[197];“煤炭战争”,[31]
哥伦布,俄亥俄州,[1]、[2]
库姆斯,布赖恩,[184]
关注公民委员会,[147]
南部联盟,[42]–[43]。另见 内战
浣熊皮帽,[16]–[17]、[39]、[60]、[75]、[102]、[105]–[6]、[153]。另见 山地人装备
库珀,詹姆斯·费尼莫尔,[25]、[33]
科西克,萨曼莎,[184]
科斯特洛,迈克尔,[218]
烧沙发,[9]、[198]、[201]–[4]、[205]
乡村音乐,[6]
穷白人(cracker),[24]、[26]、[36]–[37]、[41]–[43]
克劳福德,T·C.,[49]
克雷波,英格丽德,[15]
克罗克特,大卫·“戴维”(美国国会议员),[40]、[149]、[162]–[63];以及安德鲁·杰克逊,[31]、[35]–[40]、[48];“克罗克特热潮”,[105]、[106]、[108]–[9]、[11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其的描述,[43];戴维·克罗克特年鉴,[39]、[108];戴维·克罗克特电视节目,[36]、[39]、[104]–[8]、[140]、[234n64]、[235n76];对山地人的影响,[106]–[8]、[110]、[115]、[127]、[129]、[141]、[156]–[157]、[235n76]
克劳斯,克莱,[75]、[232n2]
每日雅典娜人报,[135]、[142]–[43]、[146]、[150]、[159]–[62]、[164]、[166]–[67]、[169]–[71]、[174]、[177]–[78]、[181]、[185]、[202]–[5]、[223]
dandy(花花公子):对比backwoodsman(边疆拓荒者),[6]、[28]–[32]、[34]、[35]、[192]–[93];对backwoodsman的剥削,[65]、[126];在近期事件中的相似之处,[67]、[97]、[149]、[197]、[220];不适合美国边疆,[37]
Davidson College(戴维森学院),[131]
Davis, Richard Harding(理查德·哈丁·戴维斯),[52]
Davy Crockett’s Almanack(戴维·克罗克特年鉴)。见 Crockett, David
deBeck, Billy(比利·德贝克),及 Barney Google 连环画,[23]、[70]
DeLue, Donald(唐纳德·德卢),[112]、[115]、[129]、[140]、[152]
Dierwechter, Jim(吉姆·迪尔韦克特),[171]
Disney, Walt(沃尔特·迪士尼),华特迪士尼工作室,[39]、[104]–[8]。另见 Crockett, David: Davy Crockett电视节目
Doddridge, Joseph(约瑟夫·多德里奇),[16]、[29];与backwoodsman(边疆拓荒者)角色,[37]、[41]、[56]、[97]、[112]、[126]、[149]、[193]、[197];Dialogue of the Backwoodsman and the Dandy(边疆拓荒者与花花公子的对话),[29]–[35]、[36]、[65]、[66]、[109];边疆的消失,[31]–[33]、[35]、[49];Notes on the Settlement and Indian Wars of the Western Parts of Virginia and Pennsylvania(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定居点和印第安战争笔记),[31]、[36]
Dominion News(自治领新闻),[135]、[147]
Dominion Post(自治领邮报),[152]、[207]
Douglass, Frederick(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43]
Dred Scott v. Sandford(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最高法院案件),[147]
Dreher, Rod(罗德·德雷赫),[193]–[94]
饮酒:作为Mountaineer价值观/身份的表达,[9]、[88]、[90]、[99]、[101]、[204]、[208];作为hillbilly(乡巴佬)或squatter(非法占地者)的象征,[6]、[39]、[72]、[189]。另见 party school(派对学校)
Drobney, Jeffrey(杰弗里·德罗布尼),[124]
Durst, Rebecca(丽贝卡·德斯特),[4]、[11]、[152]、[156]–[57]、[171]–[73]、[177]–[86]、[226]
Earth Day(地球日),[125]
Eastern Oklahoma State College(东俄克拉荷马州立学院),[3]
Eastern Oregon University(东俄勒冈大学),[3]
Eby, Cecil(塞西尔·伊比),[28]、[35]
Electric Dirt(电力尘土)(期刊),[218]
Ellis, Dave(戴夫·埃利斯),[x]
emancipation(解放),[10]
Esquire(君子)杂志,[70]、[72]、[99]
eugenics(优生学),[50]、[56]、[64]–[65]、[195]、[214]
Facebook,[177]、[185];Facebook群组,[177]–[78]、[184]、[202]
Fagan, Conol(科诺·法根),[225]
Fawley, Derek(德里克·福利),[160]–[61]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联邦调查局)(FBI),[120]、[122]–[24]
Federal Writers’ Project(联邦作家项目)(FWP),[76]、[83]
Ferguson, MO(密苏里州弗格森),[199]、[201]
Ferris, Tom(汤姆·费里斯),[95]
feuds(世仇),[41]、[46]–[50]、[55]–[56]、[62]、[148]、[194]、[196];Hatfield-McCoy世仇,[46]–[47]、[66]
fires(火灾),[145]、[198]、[201]、[203]。另见 couch burning(烧沙发)
Ford, Tennessee Ernie(田纳西·厄尼·福特),[105]
Fox, John, Jr.(小约翰·福克斯),[51]–[52]、[231n74]、[234n54]
fraternities(兄弟会),[86]–[88]、[94]、[96]–[97]、[131]
Frazier, Leila Jesse(莱拉·杰西·弗雷泽),[153]–[54]、[155]、[157]
Frazier, James(詹姆斯·弗雷泽),[154]
frontiersman(拓荒者),[113];胡须与,[139]–[40];特征,[5]、[25];与hillbilly Mountaineer的冲突,[10]、[70]、[75]–[76]、[90]–[92]、[103]–[4]、[141]、[206]、[207]–[8];Davy Crockett作为典型拓荒者,[39]、[106]、[108];对Mountaineer的影响,[5]–[6]、[7]、[9]–[10]、[22]、[24]、[102]–[4]、[108]、[173]、[221];拓荒者的消失,[50];Mountaineer服装与,[17]、[102]、[111]、[140];Mountaineer雕像与,[111]–[112]、[150];西弗吉尼亚人与,[193];Scott Bill竞选学生会主席与,[127]–[29];作为WVU官方认可的Mountaineer形象,[10]、[70]、[76]、[121]、[156]、[208]–[9]、[211]
Frost, William Goodell(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51]–[57]、[64]–[65]、[73]、[193]、[212]、[232n88]
Funk, Rebecca(丽贝卡·芬克),[180]
Gandee, Shain(肖恩·甘迪),[190]–[92]
Gandy, Deonna(迪昂娜·甘迪),[207]
Gainer, Patrick Ward(帕特里克·沃德·盖纳),[xi]–[xii]、[68]
Gaudio, Monica(莫妮卡·高迪奥),[161]
Gawker,[196]
Gee, E. Gordon(E·戈登·吉)(WVU校长),[198]、[200]、[206]、[211]、[216]–[17]
Geffrich, John(约翰·杰夫里奇),[3]、[93]。另见 Yosef(吉祥物)
Geographical Journal(地理学期刊),[58]
Georgia(佐治亚州),[24]、[74]
GI Bill(退伍军人权利法案),[11]、[83]–[84]、[87]
Giles, Taylor(泰勒·贾尔斯),[223]
Go First(宣传活动)。见 Mountaineers Go First
Good, Crystal(克里斯托·古德),[226]
Gould, Glenn H., III(格伦·H·古尔德三世),[167]
Grand Ole Opry(大奥普里),[75]、[104]
Grantsville, WV(西弗吉尼亚州格兰茨维尔),[1]–[2]
greek culture(希腊文化)。见 fraternities(兄弟会)、sorority(姐妹会)
Green Acres(绿色田园)(电视剧),[119]
Greensboro College(格林斯伯勒学院),[130]
Gregg, William(威廉·格雷格),[26]
Griffin, Sean(肖恩·格里芬),[105]、[108]
Grimm Brothers(格林兄弟),[30]
Gulf War(海湾战争),[170]
Gutta, Todd(托德·古塔),[178]
Haines, Thomas(托马斯·海恩斯),[110]–[13]
Harding, Tonya(托尼娅·哈丁),[176]
Harkins, Anthony(安东尼·哈金斯),[14]、[46]、[69]–[70]、[72]、[83]
Harmon, Roy Lee(罗伊·李·哈蒙),[73]–[74]
Harris, George Washington(乔治·华盛顿·哈里斯),[44]–[45]
Hatfield, Anse(“魔鬼”安斯·哈特菲尔德),[46]–[48]
Hatfield, Henry D.(亨利·D·哈特菲尔德)(WV州长),[47]
Hatfield家族,[47]、[49]、[194]
Hatfield-McCoy世仇,[46]–[47]、[66]
Hathaway, David B.(戴维·B·哈撒韦),[ix]、[1]、[84]–[85]、[94]–[95]、[97]、[100]–[101]
Hathaway, Joyce (Toothman)(乔伊斯·哈撒韦(图思曼)),[ix]、[1]
Hay, George(乔治·海),[75]、[104]
Haymond, William(威廉·海蒙德),[142]–[43]
Hays, Bill(比尔·海斯),[105]
Heale, M. J.(M·J·希尔),[33]、[37]–[39]
Hickey, Chris(克里斯·希基),[207]
Hill, Anita(安妮塔·希尔),[174]–[75]、[186]
Hill, Lawson(劳森·希尔),[60]、[61]、[75]、[232n2]
hillbilly(乡巴佬):竞选材料与,[127]–[28];特征/刻板印象,[5]–[6]、[27]、[48]、[58]、[68]、[86]、[93]、[111]、[112]、[166]、[193]、[195]–[97];与frontiersman Mountaineer的冲突,[75]、[103]–[4]、[206]–[9];David B. Hathaway(作者父亲)作为,[84]–[86];“魔鬼”安斯·哈特菲尔德与,[46];历史根源于squatters(非法占地者),[24]、[42]–[43];对WVU Mountaineer的影响,[4]、[5]–[6]、[7]、[9]–[11]、[22]、[43]、[50]、[83]、[90]–[94]、[110];对Yosef(吉祥物)的影响,[3]、[92]–[94];Mountaineer服装与,[17]、[75]–[76]、[94]、[107]、[150];hillbilly音乐,[69]、[73]–[75]、[77]–[78];西弗吉尼亚人与,[76]–[78]、[167]、[193];作为贬义词,[70]、[73]、[85]–[86];在流行文化中,[58]–[59]、[68]–[75]、[77]、[188]–[92];原始hillbillies,[64];抵抗与,[66]、[197]、[204];女性Mountaineer的选拔与,[160]、[166]–[67]、[174];hillbilly羞辱,[161]–[62]、[168]、[181]–[82];WVU学生对其的描绘,[92]、[99]、[100]、[103]、[201]–[2];白人身份与,[58]、[68]–[69];WVU对其的否认,[102]、[106]–[8]、[111]、[121]、[140]、[156]、[189]、[211]
Hillbilly: A Cultural History(乡巴佬:一部文化史)(Harkins著),[14]、[46]
Hillbilly Elegy(乡巴佬的挽歌),[12]、[46]、[189]、[193]–[97]
Hilliard, Emily(艾米莉·希利亚德),[217]
Hite, Steven(史蒂文·海特),[151]
Holt, Homer “Rocky”(霍默”洛基”·霍尔特)(WV州长),[77]–[79]、[83]、[104]
返校节(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大学庆典活动),[88], [94]–[99], [151], [169], [204]
HOPE社区发展公司,[226]
Hoosier:作为印第安纳州居民的称呼,[50];作为印第安纳大学学生的称呼,[50]
豪威尔斯,威廉·迪安,[52]
亨德利,罗德尼·克拉克(“Hot Rod”),[2]
亨特,大卫,[42]
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190]–[92]
《亨廷顿广告报》,[124]
赫斯顿,佐拉·尼尔,[80]–[81]
海德,刘易斯,[6], [8]
易卜拉欣,梅斯,[217]
移民:移民到美国,[10], [54], [56]–[58], [64], [78], [84], [87], [210];移民到阿巴拉契亚或从阿巴拉契亚移出,[50]
《印第安人迁移法案》,[38]
in loco parentis(代替父母),[121]–[22], [219]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国际学生,[216]
伊森伯格,南希,[14], [24]–[25], [27], [36]
艾夫斯,伯尔,[105]
杰克逊,安德鲁(美国总统),[31], [35]–[39], [41], [48], [104], [149]
杰克逊,约翰·G.(弗吉尼亚州众议员),[20], [224]
杰克逊,塞缪尔,[225]
杰克逊,托马斯·乔纳森(“石墙”),[42]–[43]
贾格尔,凯尔西,[182]
杰斐逊,科妮莉亚,[26], [27], [34], [64]
杰斐逊,托马斯,[26], [27]
《泽西海岸》(MTV电视剧),[190]
乔宾,泰勒,[203]
约翰逊,林登,[11], [118]–[19]
琼斯,卡尔文,[226]
琼斯,丹尼,[190]
贾斯蒂斯,詹姆斯·“吉姆”·康利二世(西弗吉尼亚州州长),[197]
肯尼迪,约翰·F.(美国总统),[118]
肯特州立大学,[130];枪击事件,[xi], [118], [120], [130]–[31], [139], [142];西弗吉尼亚大学与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相关的抗议活动,[130]–[32], [136]–[37], [141], [152], [200]。另见 Woodburnstock
肯顿,西蒙,[26]
肯塔基州,[42]–[43], [46], [52]–[53], [55]–[57], [74], [194]
《肯塔基私酿酒》(电影),[72], [75]。另见韦伯,保罗,和《山地男孩》漫画;里兹兄弟
克里根,南希,[176]
汗,拉齐布,[195]–[96]
金,玛格丽特·J.,[105]
装备。见 山地人装备
克洛特,詹姆斯·C.,[42], [53]–[54]
诺茨,唐,[2]
克罗格(超市),[202]–[3]
昆斯特勒,威廉,[142], [149]
库拉尔特,查尔斯,[118]
劳工,[65]–[66]。另见西弗吉尼亚教师罢工;关于奴隶劳动,见奴隶制
《女士家庭伴侣》,[55]
拉霍达,布兰南,[178], [180]–[81]
兰伯特,马克,[161]
西弗吉尼亚大学拉丁裔学生,[216]
利里,蒂莫西,[115]
妖精(圣母大学吉祥物),[168], [225]
西弗吉尼亚州刘易斯堡,[29]
LGBTQ+学生和身份认同,[210]–[11], [221]
《小阿布纳》。见卡普,阿尔
林肯,亚伯拉罕(美国总统),[42], [127]–[28]
利特尔佩奇,埃尔莎,[192]
利文斯顿学院,[131]
洛奇,亨利·卡博特,[15]
木屋,[39], [41], [127]–[28]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46],
洛文古德,萨特,[44], [45], [190]
洛维,罗伯特(“鲍勃”),[129], [132]–[39], [141], [148]
笨蛋(lubbers),[24], [197];笨蛋之地(Lubberland),[23]
勒德洛,诺亚,[34]
卢克,乔治,[52]
卢斯克,萨凡纳,[186]
里昂,哈丽特,[154]
麦迪逊学院,[130]
马龙,苏珊·C.,[170]
曼钦,乔(美国参议员),[19], [189], [192]
玛丽埃塔学院,[130]
马歇尔大学,[120], [123]–[24], [208]
吉祥物:定义,[14]–[15];吉祥物的性别、种族和民族多样性,[225]–[26];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不仅仅是吉祥物,[2]–[3], [15], [17], [82], [220], [224]。另见 布鲁图斯·巴基(Brutus Buckeye);妖精(圣母大学吉祥物);华盛顿国民队总统吉祥物;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约瑟夫(Yosef)(吉祥物)
麦克朗,道格,[159], [169], [175]
麦克卢尔,玛丽莲,[157]
麦卡洛,丹,[168]
麦肯齐,吉姆,[168]–[69]
麦克尼尔,路易丝,[153]
麦克弗森,威廉,[116], [117], [120]
梅森杰,C. E.,[148]
摩根敦大都会剧院,[2]
迈耶,比利,[62]
俄亥俄州米德尔敦,[194]
米兰·普斯卡体育场(西弗吉尼亚大学),[151]
米勒,阿尔,[123]
米勒,唐恩,[162]
米勒,米奇,[105]
密西西比州,[192]
鹿皮鞋(moccasins),[16], [25], [29], [105], [212]。另见山地人装备
montani semper liberi(西弗吉尼亚州州训),[4], [19]–[20], [127], [220], [222]–[23]
《蒙蒂科拉》(西弗吉尼亚大学年鉴),[87]–[92], [94], [99], [234n48]
《私酿酒》(校园幽默杂志),[91]–[92], [93]
摩尔,阿奇(西弗吉尼亚州州长),[114]
摩根,约翰,[167]
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2], [4], [84], [120], [134]–[35], [147], [153], [155], [190], [198]–[99], [207], [221]
摩根敦女子神学院,[154]
《摩根敦邮报》,[124]
摩根敦六人组,[141]–[44], [146]–[47], [149]
莫里森,艾格尼丝·J.,[155]
摩西,赫尔曼,[172]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山地男孩,[99]–[100]。另见韦伯,保罗,和《山地男孩》漫画
山地荣誉会(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团体),[60], [75], [115], [151], [157]–[60], [162], [169]–[72], [178]
山地人顾问委员会,[183], [185]
山地人日,[11], [99]–[102], [148], [204], [206]
山地人自由党(MFP),[123]–[29]
山地人率先行动(西弗吉尼亚大学宣传活动),[12], [188], [198], [206]–[11], [213]–[15], [217], [220]–[21], [224], [226]
山地人装备,[16], [17], [75]–[76], [105], [110], [140], [219]。另见胡须;鹿皮服;浣熊皮帽;鹿皮鞋;滑膛枪;步枪
山地人雕像,[111]–[12], [114]–[15], [118], [129], [140], [150], [152], [156], [187], [211], [245n59]
山地人周,[11], [101]。另见山地人日;山地人周末
山地人周末,[102]–[3], [150]
山地人之家(Mountainlair)(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108], [111], [114], [122], [131], [135], [143]–[45], [149]–[50], [211], [213]–[14]
山地白人,[52]–[58], [62]–[63], [68], [70]
圣玛丽山大学(马里兰州),[3]
墨菲,乔,[192]
默里,查尔斯,[195]
音乐。见《戴维·克罗克特之歌》;乡村音乐;乡巴佬:乡巴佬音乐;种族:“种族音乐”
滑膛枪,[3], [16], [151], [172], [178], [184], [219]–[20], [222]。另见山地人装备;步枪
纳德尔,艾伦,[105]–[6], [235n77]
《国家乡巴佬新闻》,[73]–[74]
美洲原住民,[25]–[26], [37]–[38], [43], [48], [64], [212];服饰,[25]–[26]。另见鹿皮服;鹿皮鞋
弗吉尼亚州天然桥,[27], [34], [64]
内夫,查尔斯(西弗吉尼亚大学副校长),[201]
Nelson, Roland(马歇尔大学校长),[123]–[24]
新闻周刊,[139]
纽约日报,[58],[68]
纽约时报,[193],[196],[202]
Nixon, Richard(美国总统),[129]–[30]
北本德声明,[144],[146]–[47]
北卡罗来纳州,[23]–[24],[36],[131]
Nyden, Chris,[207]–[8]
俄亥俄州,[1],[130],[146];Buckeye,作为俄亥俄州居民的称呼,[1],[50]
俄亥俄州立大学,[1],[130];Buckeye,作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的称呼,[50]。另见 Brutus Buckeye
俄亥俄大学,[130]
Oldstone-Moore, Christopher,[138],[139]
欧扎克山区(Ozarks),[46]
Page, Eleanor,[139]–[40]
内裤突袭事件(panty raids),[201]
Parker, Fess,[105],[107],[140],[234n64]
派对学校,[189],[198]–[99],[206]–[8]
Payne, Leonidas W., Jr.,[68]
裙角风云(电视剧),[119]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130]
花花公子,[198]–[99],[206]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最高法院判决),[53]
贫穷白人,[26]–[27],[41]–[43],[45],[54],[106]
贫穷白人垃圾。见 白人垃圾
Porterfield, Eric(西弗吉尼亚大学立法代表),[222]
Post, Melville Davisson,[62]
普林斯顿评论,[198],[206]
酷儿阿巴拉契亚(Queer Appalachia),[217]
种族:对山地人作为”最纯正”白人种族的挑战,[78]–[80],[83];从西弗吉尼亚州指南中抹去种族多样性,[78];山地人作为”最纯正”白人种族,[51]–[52],[57]–[58],[64]–[65],[70],[78];与外来者,[80]–[81];在流行文化中,[72],[106];与伪科学,[195]–[96];“种族音乐”,[68]–[69];与向贫困宣战,[119];通过与其他种族对比来衡量白人身份,[26],[43]–[45],[50]–[58],[64],[81];与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108]–[9],[152],[209],[211]–[216],[222],[225]–[226]。另见 非裔美国人;盎格鲁-撒克逊;山地白人;美洲原住民;贫穷白人;种族隔离;南方白人;白人垃圾
雷伯恩的欧扎克指南,[86]
Reagan, Ronald(美国总统和加州州长),[129]
重建时期,[10],[54],[192]
Reel, Gil,[150]–[51]
Remington, Frederick,[52]
Reynolds, Edwin,[144]
Rhodes, James,俄亥俄州州长,[130]
杜鹃花(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年鉴),[92]–[93]
Richards, Robert R.,[116]
里士满,弗吉尼亚州,[224]
里士满观察家报,[20],[224]
步枪,[109];边疆移民与,[34];女性山地人与,[153],[161]–[62],[164]–[65],[171]–[74],[176],[222];边疆开拓者山地人与,[111],[113],[173];乡巴佬山地人与,[46]–[48],[90],[111],[112];作为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装备的一部分,[17],[75]–[76],[105],[150]–[51],[220]–[21],[223];山地人雕像与,[111]–[12],[114]–[15],[118],[150]。另见 山地人装备;火枪
1849年骚乱法案,[146]
骚乱,[132],[146],[189],[198]–[201],[203]–[8],[211],[218]
Ritz Brothers,[71]
Robinson, Ruth,[108]
Rogers, Herb,[142]
Roosevelt, Theodore(美国总统),[51]–[52]
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116],[122],[130]。另见 西弗吉尼亚大学:学员团
Rubin, Jerry,[139]
萨卡加维亚(Sacajawea),[162]
施莱纳大学(德克萨斯州),[3]
Schroeder, Fred,[62]
Schwartz, Louis D.,[171]
Scott, Nathan B.(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154]
Scott, Sir Walter,[33]
苏格兰(或”苏格兰-爱尔兰”)传统,[46]–[47],[56],[66],[194]–[96]
Scribner, Charles,[52]
种族隔离,[53]。另见 “隔离但平等”;普莱西诉弗格森案
Semple, Ellen Churchill,[58],[64]
“隔离但平等”,[57]
性别歧视,[11],[159]–[63],[165]–[69],[171],[174]–[78],[180]–[86],[194],[201]
Silard, Kevin,[168]
西森维尔,西弗吉尼亚州,[190]
奴隶制,[7],[19],[20],[22],[26],[38],[52]–[53],[56],[64]
蛇人(Snakers),[62]
Snuffy Smith,[23],[70],[75]
社交媒体,[177],[185],[207]–[8],[217]。另见 Facebook,Twitter
女生联谊会,[156],[163]
南卡罗来纳大学,[96],[169]
南佛蒙特学院,[3]
南方白人,[22],[43],[45]
定居者(squatters),[22],[24]–[29],[31],[34]–[39],[41]–[43],[48],[66],[103],[197],[209]
Squires, Michael,[x],[178]
斯坦斯伯里厅(西弗吉尼亚大学建筑),[2]
Steele, Brandon(西弗吉尼亚州立法代表),[222]
Stewart, Irvin(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84],[106],[108],[111],[211],[234n48]
Stoll, Steven,[14],[41],[52],[231n74]
学生自治会(SGA),[207]
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120],[123]–[24];马歇尔大学分会,[123]–[24];西弗吉尼亚大学分会,[121]–[25]
Swart, James A.,[166]
教师。见 西弗吉尼亚教师罢工
催泪瓦斯,[136],[137],[200],[201],[203]
Tennant, Ken,[203]
Tennant, Natalie,[x],[4],[11],[140],[152],[156]–[78],[180]–[85],[226],[239n38]
田纳西州,[34],[36],[74],[192]
田纳西河谷项目,[78]
Thomas, Clarence,[174]–[75]
Thomason, John,[195],[196]
Thorn, Gordon,[111],[114],[162],[172]
Thrasher, Ginny,[223]
Tompkins, Roger,[106]–[8]
Townshend, Doug,[129],[131]–[32],[135]–[38],[141],[148],[150]–[52]
跨性别身份与学生,[216],[222]
格林维尔条约(1795年),[153]
骗子,[5]–[8],[24],[74],[81]–[82],[88],[97],[116]
圣三一圣公会教堂,摩根敦,西弗吉尼亚州,[2],[84]
圣三一厅(与西弗吉尼亚大学相关的宿舍楼),[84],[85],[87]–[89],[94]–[99],[102],[200],[204],[210],[224]
Trump, Donald(美国总统),[149],[192]–[94]
Twain, Mark(Samuel L. Clemens),[28]–[29],[45]–[46],[149]
Twitter,[185]
矿工联合会,[125]
肯塔基大学,[130]
圣母大学,[168],[225]。另见 小妖精(圣母大学吉祥物)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130]
怀俄明大学,[212]–[13],[225]
Upton, Elsie,[86]
今日美国,[156]
Vance, J. D.,[11]–[12],[46],[189],[193]–[97],[208]
世仇(vendetta),[46],[49]。另见 仇杀
退伍军人,[83]–[84],[89]–[90],[93]–[94],[99],[106],[120],[135],[189]–[90],[200]
越南战争,[109]、[112]、[114]–[18]、[120]、[122]、[125]–[27]、[129]、[131]–[32]、[148]、[150];反越南战争抗议,[129]、[134]–[35]、[149]、[236n23];美国入侵柬埔寨,[120]、[129]–[30]
弗吉尼亚州,[4]、[19]–[24]、[43]、[46]、[146]、[153]
VISTA(美国志愿服务组织),[118]
Vucelik, Daryn,[186]
Walker, Danielle(西弗吉尼亚州立法代表),[223]
《华尔街日报》,[162]、[164]–[68]
向贫困宣战,[11]、[118]–[19]
华盛顿国民队总统吉祥物,[15]
Webb, Paul,及《山地男孩》漫画,[70]、[71]、[72]、[75]、[83]、[99]、[102]、[108]
Webster, Carrie,[159]
Webster, Daniel(美国总统候选人),[41]
《韦氏新国际词典》,[68]
Weirton Steel,[89]、[91]
Weiss, Karen,[206]
西科罗拉多大学,[3]
西弗吉尼亚州:校园抗议活动,[146];人民身份认同,[5]、[22]、[34]、[60]、[73]、[76];足球欢呼口号,[62];建州过程,[16]、[20]–[21];州长Holt对州指南的影响,[76]–[79];《乡巴佬的挽歌》与该州,[194];劳工运动与该州,[66]、[76]、[197]–[98];失去边疆地位,[49]–[50];神话传说,[7]、[31];州徽,[20];石墙杰克逊与该州,[42]–[43];越南战争与该州,[114]–[18]
西弗吉尼亚州与地区历史中心,[123]
西弗吉尼亚州公民防卫联盟,[220]、[223]
西弗吉尼亚州日(6月20日),[1]
西弗吉尼亚州指南,[76]–[79]。另见 美国指南系列
西弗吉尼亚州众议院2519号法案校园自卫法案,[218]–[19]、[224]、[245n68]
西弗吉尼亚州人文委员会,[217]
西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154]、[218]–[219]
西弗吉尼亚州教师罢工,[12]、[197]
西弗吉尼亚大学(WVU):招收非裔美国学生,[83]–[84]、[154];招收女学生,[83]、[154]–[55];采用山地人(Mountaineer)昵称,[62]、[64]–[65]、[68]、[69]–[70];校内反战活动,[119]–[29]、[129]–[38]、[141]–[50];作者与该校的关系,[2];学员队,[154];与校园自卫法案(HB 2519),[218]–[24];否认乡巴佬山地人形象,[10]、[106]–[8]、[211];学生群体多样性,[216]–[17];教职员工对学生的看法,[196];LBGTQ+中心,[210];“加油,山地人们”(欢呼口号),[62];山地人日/周,[100]–[101];穆斯林学生协会,[216];对学生行为的反应,[5]、[9]、[198]–[202]、[204]、[206]–[7]、[208];派对学校的声誉,[198]、[206];法学院,[153]、[155];作为该州与更广泛文化联系的象征,[67];退伍军人,[89];越南战争与该校,[116]–[19]。另见 山地人先行(宣传活动);山地人雕像;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吉祥物)
《西弗吉尼亚大学公报》,[102]
西弗吉尼亚大学山地人(吉祥物):作者与该形象的关系,[1]–[3];荒野猎人(backwoodsman)与乡巴佬(hillbilly)的不同理念,[34]、[75]–[76]、[91]、[102]–[3]、[104]、[106]–[8]、[121]、[128]–[29]、[140]–[41]、[209];阶级意识与该形象,[65]–[66];融入主流的愿望,[67];职责/角色,[7]–[8];历史,[3]–[4]、[10]–[12];超越吉祥物的意义,[14]–[18]、[81]–[82];官方版本与山地人理念的区别,[12]–[13]、[91]、[211]、[222];历任山地人,[x];选拔流程,[60]、[159]、[169]–[70]、[178]–[80](见 欢呼比赛);针对女性山地人的性别歧视,[156]–[57]、[159]–[61]、[163]–[71]、[173]–[77]、[177]–[87];大学试图多元化山地人形象,[211]–[17];大学对该形象的正式指定,[10]、[58]–[59]、[60]–[62]、[75]–[76]、[209];非官方学生版本,[70]、[82]、[83]、[91]–[92]、[94]–[95]、[96]、[98]、[102]、[103]、[210]–[11];白人身份与该形象,[64]–[65]、[83]–[84]、[186]、[209]、[211]–[12]、[213]–[16]、[224]–[26]。另见 山地人装备套装;以及各位山地人的姓名
西弗吉尼亚卫斯理大学,[62]
Wheeler, William,[45]
Wheeling, WV,[87]、[162]、[165]、[197]
Whisnant, David E.,[236n12]
白人山地人。见 山地白人
白人垃圾,[4]、[22]、[24]、[27]、[41]、[43]、[45]、[48]、[51]–[52]、[56]、[64]、[78]–[79]、[102]、[197]、[232n88]
Williams, John Alexander,[14]、[20]–[21]、[42]、[48]–[49]、[66]–[67]
Williams, Steve,[190]
Wilson, Darren,[201]
Wilson, Rock,[60]、[170]–[71]
Wilson, Samuel,[57]
Wilson, Sonja,[ix]–[x]
Wilson, Tim,[162]
Wilson, Woodrow(美国总统),[55]
Wister, Owen,[52]
Woman’s Hall(西弗吉尼亚大学宿舍楼),[2]
西弗吉尼亚大学妇女联盟,[154]
Woodburn Circle(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142]
Woodburn Hall(西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建筑),[127]、[141]
Woodburnstock,[142]–[43]
Wordsworth, William,[30]
工程进展管理局(WPA),[76]
第二次世界大战,[11]、[83]–[84]、[93]
Wukie, Lynette,[225]
Yosef(吉祥物),[3]–[4]、[92]–[94]。另见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吉祥物
Young, Neil,[135]、[137]
Zane, Elizabeth(“Betty”),[162]–[63]、[165]、[173]
Zervos, Matt,[x]
Ziemianski, Renee,[157]
Zimmerman, Heidi,[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