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美国文化符号的历史



牛津 纽约
奥克兰 曼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开普敦 金奈
达累斯萨拉姆 德里 香港 伊斯坦布尔 卡拉奇 加尔各答
吉隆坡 马德里 墨尔本 墨西哥城 孟买 内罗毕
圣保罗 上海 台北 东京 多伦多
版权所有 © 2004 牛津大学出版社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纽约麦迪逊大道198号,邮编10016
牛津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注册商标
版权所有。未经牛津大学出版社事先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方式)复制、存储于检索系统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数据
哈金斯,安东尼。
乡巴佬:一个美国文化符号的历史 / 安东尼·哈金斯。
含参考文献和索引。
ISBN 0-19-514631-X
E184.M83H37 2003
975’.00943—dc21 2003041974
第三章部分内容经许可以修订形式转载自《“乡巴佬”在早期乡村音乐中的意义,1924-1945》,《阿巴拉契亚研究杂志》第2期(1996年秋季):311-22页。
第六章经许可以修订形式转载自《客厅里的乡巴佬:1952-1971年情景喜剧中的南方山地居民电视形象》,《阿巴拉契亚杂志》第29期(2001年秋季-2002年冬季):98-126页。
献给查尔斯·R·哈金斯
谨以此书纪念
在从事这个项目的多年里,我欠下了许多人情债,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专业层面,我很感激有机会在此正式致谢。本书始于一篇博士论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们。保罗·博耶既是我的导师也是朋友,对这部书稿影响深远。他不仅在我最初犹豫时鼓励我研究这个课题,而且他在写作和教学中展现的热情与学术严谨也激励我成为一名文化史学家。他许多发人深省的评论和问题、对我各章节的深入阅读,以及最重要的——他始终如一的支持和幽默感,都极大地改进了我的工作。史蒂夫·坎特罗维茨鼓励我扩展分析范围,更充分地探讨美国历史中的重大议题和矛盾,并给予我稳固的友谊。作为研讨课导师、教学指导和审稿人,吉姆·鲍曼是高效研究和教学的典范,总是督促我用具体证据支撑我的论点。
除了这些通读全稿的审稿人外,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项目早期阶段阅读并评论了部分内容。我感谢特蕾西·多伊奇、劳拉·麦克纳尼、查理·蒙哥马利和贝瑟尔·萨勒提供的有益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许多与我交流并帮助我理清思路的学者,特别是比尔·克罗农、阿奇·格林、吉姆·利里、比尔·马龙、大卫·罗迪格、安妮·米切尔·惠斯南特和大卫·惠斯南特。
这部作品能够付梓出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团队的支持和专业能力。我感谢尼科·普丰德对这个项目始终如一的支持,感谢苏珊·费伯无与伦比的编辑建议和沉稳的指导,感谢斯泰西·汉密尔顿在本书制作过程中的协助。我还要感谢原稿的外部审稿人,包括那些保持匿名的和那些公开身份的(德怀特·比林斯、埃里卡·多斯、大卫·修恩和斯科特·桑达奇),感谢他们精辟的评论和建议。我努力回应他们的关切,力求实现他们所看到的这个项目的全部潜力,这使本书变得更加出色。
我也深深感谢许多人与我分享了难以找到或未出版的资料,他们常常让我查阅自己即将出版作品的笔记。首先,我要向Jerry Williamson表达巨大的感激之情。Jerry远远超越了学术同行的普通礼节,向我开放了他收藏的大量乡巴佬相关资料,让我自由浏览他的大量档案并观看他收藏的珍稀影片。他还慷慨地分享了关于乡巴佬身份认同的宝贵见解,帮助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恩逗留期间找到住处,并在随后的岁月里持续提供宝贵的支持和见解。我非常感谢他的诸多善意和建议。我还要感谢以下提供了自己学术成果或其他研究资料的人:Terry Bailes、Tom Bené、Simon Bronner、Jim Clark、Stephen Cox、Jon Harris、Tom Inge、Angie Maxwell、Michael McKernan、John McCoy、Ronnie Pugh、David Whisnant、Adam Wilson和David Zercher。最后,我非常感谢Paul Henning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仍愿意参与一次长时间的电话采访。他在回忆参与制作《贝弗利乡巴佬》及其他节目的岁月时表现出的坦诚和感染力,使这次对话既愉快又富有信息量。
这项研究项目在获取插图和再版许可以及前往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我衷心感谢所获得的机构支持和研究资助。我真诚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提供的研究旅行和会议报告经费,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获取丰富文本的各种艺术作品。我感谢John Blazejewski出色地完成了大部分图片的拍摄工作。我还要向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众多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表达感谢。特别感谢堪萨斯大学斯宾塞艺术博物馆的Stephen Goddard;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南方民俗收藏馆的Steve Green;乡村音乐基金会前工作人员Ronnie Pugh;东田纳西州立大学阿巴拉契亚档案馆的Ned Irwin;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阿巴拉契亚收藏馆的Dean Williams;肯塔基大学阿巴拉契亚收藏馆和特藏部的Kate Black和Bill Marshall;伯里亚学院哈钦斯图书馆的Harry Rice和Gerald Roberts;阿什维尔公共图书馆的Ann Wright;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西部历史手稿收藏馆的Randy Roberts,以及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感谢在洛杉矶地区研究期间给予帮助的人: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图书馆的Ned Comstock;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玛格丽特·赫里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Kristine Kreug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艺术图书馆特藏部首席档案管理员Brigitte Kueppers,以及加州北好莱坞Eddie Brandt’s Saturday Matinee的热心店主们,感谢他们在其庞大收藏中帮助我找到许多冷门的乡巴佬电影。
朋友和家人的慷慨款待使我的旅途更加愉快且经济实惠,他们在我研究旅行期间让我借住。我真诚感谢Anne和Chris Kenyon、我的母亲Shanna MacLean、Harry和Katherine Petrequin,以及David Zercher。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Andrew Cypiot,他不仅让我在他的小公寓里住了一个多月,还为我进行了宝贵的研究工作。没有他的帮助和友谊,我无法完成加州部分的研究。
在这个项目历经多年最终完成的过程中,我一直依赖朋友和同事的指导与支持。我非常感激Susan Ballard、Steve Burg、Joe Cullon、Judy Cochran、Rob Good、Dan Graff、Charlotte Haller、Katherine Ledford、Charlie Montgomery和Linda Curchin、Paul Murphy、Doug Reichert-Powell、Sue Rosenthal、Bethel Saler、James Siekmeier、Kevin Smith、Lisa Tetrault、David Zercher,当然还有”Pawtuckaway湖帮”(Sam Broeksmit、Andrew Cypiot、Pat Connors、John Gregg、Jeff Speck、Mark Van Norman和Adam Wilson)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特别感谢Janet Davis和Jeff Osborne、Steve Hoelscher和Kristin Nilsson,以及Mark和Paula Van Ells及其孩子们的诸多善意,包括临时帮忙照看孩子、家常便饭,以及让我们相信大家都能挺过完成论文和出版第一本书这个过程的鼓励(令人欣慰的是,我们都做到了)。
我的家人是我最大的灵感来源和支持力量。我感谢母亲在我前往阿什维尔的研究之旅中以及后续交流中给予的帮助和鼓励,感谢Sean在电脑方面提供的大量建议和帮助,感谢Sue和Tom协助我获取Mountain Dew的相关资料,感谢Michael和Barbara始终如一的支持以及帮助维护我们的房屋。感谢我的姐妹Sue和Tammy多年来的爱与支持。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Charles Harkins,衷心感谢他多年来在经济上尤其是情感上的支持与鼓励,即使在他困惑于我究竟在研究什么、是否能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也从未动摇。他未能亲眼看到这些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但令我欣慰的是,他至少知道这本书终有一天会出版。我的孩子们Chloe和Owen也值得我感谢,感谢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无数次因我的写作计划而打断日常活动的情况,也感谢他们在工作压力几乎要压垮我时让我保持脚踏实地。
最后,对于Tracy,我欠她的远超我所能回报。这本书真正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她以数十种方式为本书的最终形态做出了几乎与我同等的贡献。她不仅通读了全部文稿并提出了宝贵的编辑和概念建议,还花费大量时间校对,整理了参考文献,并帮助解决了数十个电脑故障和危机。她牺牲了无数个周末和夜晚照顾孩子和家务,让我能有宝贵的写作和研究时间,她还陪我一起走访了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与乡巴佬(hillbilly)相关的地点。一路走来,她对乡巴佬的了解无疑远远超出了她曾经认为可能或想要了解的程度。但尽管承受着观看数十部乡巴佬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压力,她在智识和情感上的支持以及她的爱从未动摇。正是由于她艰苦卓绝的努力,我才终于能够完成这个项目,我怀着全部的爱将这本书献给她。
导言
种族、阶级、流行文化与”乡巴佬”
第一章
从扬基·杜德尔到”魔鬼安斯”:文学、图像与意识形态的先驱,1700-1899
第二章
“乡巴佬”的出现,1900-1920
第三章
乡村音乐与两次世界大战间美国”Ezra K. Hillbilly”的崛起
第四章
Luke、Snuffy与Abner: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乡巴佬卡通形象
第五章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好莱坞的乡巴佬形象
第六章
客厅里的乡巴佬:1952-1971年的电视呈现
尾声
从《激流四勇士》到网络空间:当代美国”乡巴佬”的持续影响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非印刷文化作品
总索引
1930年,洛杉矶的一支弦乐乐队以”比佛利乡巴佬”(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名字在该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追随者。三十二年后,这个名字将再次出现,成为一部极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标题。基本相同的野蛮山民家庭形象出现在1921年的电影《可敬的大卫》(Tol’able David)中的哈特本家族、Al Capp长期连载的漫画《小阿布纳》(Li’l Abner,始于1934年)中的斯克拉格家族,以及1972年电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中那些无名的山地强奸犯身上。在大萧条初期诞生六十八年后,那个懒惰、与世隔绝、脾气暴躁的漫画山民Snuffy Smith仍然出现在全国数百家报纸上。正如这些例子所证明的,将南方山区人民描绘成前现代的、愚昧的”乡巴佬”是美国流行图像志中最持久、最普遍的形象之一,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几乎出现在美国流行文化的每一个主要领域,从小说和杂志到电影和电视节目,再到乡村音乐和互联网。
尽管乡巴佬(hillbilly)的形象相对保持不变,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些表征的含义以及这个词本身,随着美国社会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而不断演变。从1900年到第三个千年之初,“乡巴佬”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无处不在并经久不衰,关键在于这个术语和形象含义的根本模糊性。在其众多表现形式中,“乡巴佬”被用于全国媒体的表征中,也被南方山区内外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所使用,既用来维护也用来挑战二十世纪美国生活的主导趋势——城市化、技术日益占据核心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生活程式化。这个术语和概念一直被中产阶级经济利益群体用来贬低南方白人工人阶级(无论是否来自山区),并通过反面例证来定义先进文明的好处,但它也被用来挑战人们对”现代性”和”进步”普遍不加质疑的接受和认可。媒体中的乡巴佬形象在1930年代经济和社会崩溃时期蓬勃发展,但它也在1960年代重新出现,那时人们普遍质疑”进步”的代价和”富裕社会”的社会公平性。作为一种独特定位的白人”他者”,一种既在美国”白人性”范围之内又超越其边界的建构,乡巴佬也一直处于美国种族身份和等级斗争的核心。最后,以同样对立二元的方式,南方山区民众既谴责它是一种恶毒的诽谤,又拥抱它来捍卫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庆祝自己的文化遗产。因此,尽管乡巴佬常被视为一种低俗琐碎的”大众”文化刻板印象而遭到忽视,但在国家反思时期以及整个二十世纪,它实际上一直作为一个不断协商的神话空间,现代美国人通过它试图定义自己和国家身份,并调和过去与现在。
本书考察的是”乡巴佬”(及其前身和同路人”山民”(mountaineer))这一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而非南方山区的实际居民,甚至也不是通俗文学、摄影和学术研究中对这些人据称”真实”的表征。然而,当然不可能完全分开这三个社会建构的范畴——南方山区人民、表征”真实”南方山民的努力,以及”乡巴佬”的形象——它们在整个世纪中辩证地交织在一起。随着大众媒体日益渗透美国文化,形象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被那些懒散、酗酒、放荡、赤脚、生活在文明触及不到的幸福贫困中的刻板形象所淹没,南方山区以外的许多美国人开始认为”真实的”南方山民与他们的文化形象之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区别。
为了回应这些贬义形象被广泛接受的现象,表面上同情山区人民的作家、摄影师和艺术家创造了一种独特但平行的建构:坚毅、正直、风景如画的山民。但这种建构基于同样的观念,即一个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神话般的白人群体。结果,旨在消解乡巴佬漫画形象的高贵山民形象,实际上强化了这些描绘,并延续了南方山区人民是一个在美国白人社会之中却不属于其中的独立”种族”的观念。与此同时,许多南方山区民众——常常困于地区低薪工业工作或被迫迁移到山区以外谋生——接受了坚韧纯朴的山民神话和乡巴佬标签的某些元素,以及其隐含的对中产阶级规范和礼仪的敌意,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全国对他们作为美国”他者”地位的认知。
由于乡巴佬形象/身份一直是对现代性态度争论的场所,它占据的是一个神话般的而非具体的地理位置。确实,制作者和观众都最常将这一形象与南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山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这两个地区内部和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地形、社会和文化多样性,这些形象的创造者却自由地将两个地区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幻想之地。由于乡巴佬形象的物理位置往往不清楚或未说明,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一形象并不仅限于这两个地区,这个标签在历史上被应用于从纽约州北部到华盛顿州西部的文学和文化人物。事实上,大多数文化消费者,就他们考虑这个问题的程度而言,将”乡巴佬之地”(hillbillyland)设想为充其量是上南方的一个模糊地区,更常见的是景观和经济边缘的任何地方。
比起地理位置,更能定义”乡巴佬”(hillbilly)的是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在这方面,“乡巴佬”与中上层阶级评论者(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创造的数十个类似标签并无不同,这些标签都是用来描述贫穷和工人阶级南方白人的意识形态和地理构建。这些贬义词旨在表明一种源于匮乏的饮食习惯(“吃黏土的人”、“玉米饼子”、“抓兔子的”)、表明艰苦劳动和特定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外貌和穿着(“红脖子”(redneck)、“羊毛帽”、“棉絮头”)、一种在社会经济和地理边缘如动物般的生存状态(“灌木猿”、“山脊跑者”、“荆棘跳蛙”)、无知和种族主义,以及在所有情况下的经济、遗传和文化贫困(最好的概括就是”穷白人”,或更尖锐地说,“穷白垃圾”)。许多这些贬义标签被交替使用,用来贬低工人阶级南方白人,尤其是那些迁移到南方和中西部城市中心的人。但它们也被一些人重新挪用,作为阶级和种族身份认同与自豪感的标志。“乡巴佬”、“红脖子”、“饼干佬”(cracker),甚至最近的”穷白垃圾”都被接受,用以标示一种对抗霸权中产阶级文化以及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社会群体相对地位提升的”对抗文化”。“乡巴佬”这个词和形象的幽默元素也并非独特;所有这些标签(即使是像”穷白垃圾”这样粗俗的词)在历史上都带有表面上的喜剧色彩,不仅对处于权威地位的中上层白人如此,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意图下,对工人阶级白人也是如此。
“乡巴佬”是这些农村工人阶级蔑称中存在时间最长、在流行文化中传播最广的一个。它是这些术语中唯一被用作后来称为乡村音乐的标签;唯一用来表示一种卡通和连环漫画类型的;唯一出现在电视剧标题中的(该剧也成为该媒介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节目之一);也可以说是这些术语中在电影中最普遍的。它的突出地位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它主要是一个善意幽默(虽然有些居高临下)的术语和描述。即使是”红脖子”,虽然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喜剧术语,并随着杰夫·福克斯沃西的”你可能是个红脖子……“笑话书和喜剧表演的成功而更全面地进入这一阵营,但它仍然比”乡巴佬”更大程度地带有恶性白人种族主义的含义。然而,“乡巴佬”也可以唤起堕落、暴力、兽性和肉欲,以及更积极的浪漫乡村概念、文化和民族纯洁性、拓荒者遗产、个人和社区的独立与自给自足。事实上,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乡巴佬”仍然是这些标签中语义上最具可塑性的,因此是在全国范围内和南方山区观众中引起最广泛共鸣的术语。
乡巴佬形象持续流行和无处不在,源于这一文化概念的二元性:它包含了美国过去和现在的积极和消极特征,并融合了”他者性”和自我认同。这些二元性使这些形象不仅在”主流”全国观众中获得了流行,也在南方山区社会的许多人中获得了认可,他们接受这种身份的积极特征,同时拒绝其消极方面。一方面,“乡巴佬”体现了与国家创建者和定居者相关的特征,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些特征在现代化、工业化和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中正受到威胁。这些元素包括拓荒精神;由仁慈的家长统治的强大家庭和亲属网络;清晰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自然和土地的亲近;真实性和纯洁性;粗犷的个人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普通人的”常识”,而非科学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通过其负面的反面来定义,以表明这些价值观与二十世纪美国的时代错位和不相容。拓荒精神也可能反映社会和经济的落后;强大的亲属关系可能意味着近亲繁殖、家庭暴力和血腥世仇;粗犷的个人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固执和无法适应变化的条件;与自然的亲近可能代表原始、野蛮和性放纵;而纯洁和常识实际上可能表明无知以及对不科学和危险的育儿、医疗、饮食和宗教实践的依赖。因此,“乡巴佬”服务于双重且看似矛盾的目的:允许”主流”——或通常是非农村的中产阶级白人美国观众——想象一个浪漫化的过去,同时使同一批观众能够通过讽刺前现代、未开化社会的负面方面来重新承诺现代性。
乡巴佬形象的双重性源于并与其白人种族身份密不可分。近年来许多学术研究正确地揭示了白人种族身份的复杂性,阐明了”白人性”在美国语境中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探讨了各欧洲族裔群体如何利用白人身份主张来获取社会和经济特权,并定义和剥夺非白人种族”他者”的权力。他们还强调了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文化的迷恋,以及”黑人”与”白人”种族和文化类别之间的相互关联。然而,这些作者较少关注白人身份本身的争议性。“乡巴佬”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且富有启示性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白人美国”这一宽泛类别内部的概念分歧。尽管他们贫穷、无知、原始且与世隔绝,“乡巴佬”却是”百分之百”的新教美国人,据称拥有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或至少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无数评论家对南欧和东欧移民潮深感忧虑,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这一点。因此,中产阶级白人美国人可以将这些人视为类似于美洲原住民或黑人的迷人而异域的”他者”,同时又能将他们视为自己更贫穷、更不现代的版本而产生同情。
这种”白人他者”的身份在整个二十世纪引发了宗教、社会和政治改革者的关注与兴趣。对于进步时代那些试图拯救山区居民的人来说,他们”顽固保守”的新教信仰和拓荒者祖先血统,既是解释其所谓原始性的现成理由,也是拯救一个受到非新教徒入侵威胁、同时被大规模工业化和官僚体制削弱的国家的潜在希望。同样,二十世纪中叶对南部山区人民的批评者和捍卫者,分别(有时同时)将他们视为危险的返祖文化残余,或是粗犷个人主义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守护者。不同年代的倡导者始终认为,后一种品质是治愈现代美国弊病的急需良药——无论是1920年代的从众倾向、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二战后”富裕社会”的盲目消费主义。在1960年代的反贫困战争中,贫困和受剥削的阿巴拉契亚白人形象也为推动主要惠及城市非白人群体的政府援助计划的自由派政客提供了”掩护”。
乡巴佬的白人身份虽然并非决定性因素,却是其在大众媒体中长盛不衰的关键,因为它使这一形象能够成为一个看似非政治化的场域,承载着围绕种族、阶级、性别规范和角色定义以及大众文化本质的激烈政治斗争。由于制作者可以描绘贫穷、无知和落后的形象,而不会招致民权倡导者以及黑人和少数族裔社区对偏见和种族主义的抗议,粗糙且往往负面的乡巴佬刻板印象得以延续,远比文化生产者早已摒弃的那些曾被接受但同样具有冒犯性和种族主义色彩的刻板印象存活得更久。同样,乡巴佬家庭和亲属网络的形象既可用于挑战所谓的男性养家糊口者和顺从的女性家庭主妇规范,也可通过反面例子来维护这些”传统”性别角色。对于那些将大众文化视为迎合最低共同标准、破坏”正统”艺术的腐蚀力量的批评者来说,乡巴佬是毫无价值的”媚俗”的完美象征。这些批评者在谴责乡村音乐、连环漫画、电影和电视中粗糙刻板的乡巴佬形象的同时,也斥责这些形象的消费者为无脑的乡下人,并将某些此类形象所吸引的庞大观众群体解读为大众媒体固有的低俗性和国家文化衰落的确凿证据。尽管如此,数百万观众和听众仍然接受了乡巴佬的形象和概念,因为它帮助他们在快速且往往令人迷失方向的变革时代中理解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乡巴佬模糊的象征意义使其能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引起改革者、文化创作者、传播者、批评者以及南部山区和全国大众的共鸣。
本书每一章都聚焦于”乡巴佬”在特定(通常是非印刷)媒介中的建构,涵盖不同但相互重叠的时期,展示每种文化形式——受制度约束、制作者和创作者的个人态度以及大众期望的影响——如何改变其身份和意义。通过阐明这一不断变形、历史化的”乡巴佬”的多面性和争议性,及其与大规模历史进程和事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力求忠实于社会学家理查德·戴尔对”表征复杂性”的认识——“生产和接受之间不平等但非单一的关系……以及它与所指涉和影响的现实之间紧张而未完成、永远无法完成的关系。”
第一章追溯了二十世纪之前美国山地人(hillbilly)形象的文学和视觉渊源,涵盖三个相互独立又有所重叠的传统:新英格兰的乡村土包子、南方边远地区的贫穷白人,以及阿巴拉契亚和阿肯色州的神话边疆人物。尽管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以不同方式运用神话山民的概念,但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忽视了十九世纪末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现实,而是将山地居民定义为永远困在无尽过去中的人群。第二章追踪”hillbilly”一词及其形象从1900年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演变过程,特别关注笑话书和新兴大众媒体——电影。虽然到1910年代中期,hillbilly的含义开始带有更明显的喜剧色彩,但在整个这一时期,“hillbilly”仍然是一个相对不常见且含义模糊的标签。
接下来的三章聚焦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hillbilly文化的核心时期——及其后续阶段,探讨这一形象在不同媒体中的建构。第三章考察了”hillbilly”在商业录制的乡村白人音乐中的核心作用,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音乐产业制作人和推广者的创造物,同时也是民间音乐家滑稽表演传统的延伸,“hillbilly”标签被音乐家和歌迷矛盾地接受,只要这一形象能唤起对神话山民的怀旧情感。然而到1930年代末,随着贬义hillbilly刻板印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音乐家和新兴的乡村音乐产业逐渐放弃了这一形象和标签,转而采用更加正面的牛仔身份和”乡村”标签。尽管如此,随着”hillbilly”和弦乐队音乐在大众想象中交织在一起,其含义从仅仅表示威胁和暴力,转变为主要象征低俗幽默和无忧无虑的轻松。第四章分析了1934年出现的三个卡通形象,它们在此后数十年间塑造了hillbilly的图像形象:保罗·韦伯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的《山地男孩》漫画、比利·德贝克在其《巴尼·谷歌》连环漫画中创造的”斯纳菲·史密斯”角色,以及阿尔·卡普的《小阿布纳》。这股hillbilly形象的爆发出现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不仅反映了公众对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恐惧,也反映了大众对山地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的突然迷恋,以及娱乐产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通过具象化长期发展的山民落后和社会堕落观念,同时呈现美国人民和精神持久力的更乐观愿景,这些形象映射了大萧条时期观众复杂的情感和态度。第五章聚焦于电影——二十世纪中期的主导媒体——中hillbilly的描绘,时间跨度从1920年代的无声电影到战后的《凯特尔夫妇》系列。受到其他媒体描绘的强烈影响,包括百老汇戏剧、韦伯的漫画、乡村音乐和杂耍表演者,电影对山地居民的呈现遵循了与其他媒体相同的轨迹,从几乎完全聚焦于暴力和社会威胁,转向越来越强调滑稽喜剧。随着战后繁荣时代的到来,hillbilly形象仅存活于凯特尔夫妇所体现的驯化版本中,以及电影产业的边缘地带。然而,后来的电影将表明,二十世纪早期关于山地居民是堕落野蛮人的观念,仍然潜藏在这些表面上轻松愉快的作品之下。
我最后几章考察了战后”乡巴佬”(hillbilly)形象及其用途和含义,特别关注196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几乎从公众意识中消失了近二十年的山民形象重新登上了全国舞台。第六章探讨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电视节目(特别是《真正的麦考伊一家》、《安迪·格里菲斯秀》以及大获成功的《贝弗利乡巴佬》),这些节目以乡巴佬角色和场景为特色。这些节目通常被认为是针对农村和小镇观众的粗俗娱乐,但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战后阿巴拉契亚山区居民大规模迁移到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工业城市的担忧,以及对生活在”富裕社会”中贫困孤立的白人山民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山民描绘成民间传统的多彩继承者,或是安全驯化的滑稽小丑——尽管周围充斥着贪婪,他们仍保持道德正直——这些节目帮助缓解了公众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担忧,既淡化了南部山区人民的困境,又将他们的贫困描绘成民间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尾声考察了乡巴佬概念在美国人想象中持续的重要性,从书籍和电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 1972)的巨大影响及其后续效应,到网络空间中乡巴佬形象的多样变体。到二十世纪末,这一形象昔日的显著地位无疑已经衰落,原因包括: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这一群体历来在城市公众眼中代表着威胁性和愚蠢的落后;南部山民在山区内外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宽泛定义的种族和民族刻板印象越来越不被接受。尽管如此,诸如肯塔基州派克维尔的”乡巴佬节”、自豪地称自己和音乐为”乡巴佬”的当代乡村音乐人、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漫画讽刺,以及互联网上”乡巴佬”的各种变体等多样例子都表明,这个术语和形象仍然作为社会嘲讽与地区和个人自豪感的模糊标记而产生共鸣。
最后,我以一篇后记结束,讲述将《贝弗利乡巴佬》复活为”真人秀”的非凡计划,以及南部山区内外人们对这些计划的反应。无论这个节目最终是否实现,这类节目再次证明,在”乡巴佬”一词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上一个多世纪之后,它仍然作为一个神话般的文化空间发挥作用,美国人通过它来努力定义自己和自己的传统。
二十世纪的乡巴佬形象起源于三个相关但独立的文学和插图传统,这些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对乡村土包子的描绘;对南部边远地区贫穷白人的概念;以及对南部山区居民的形象塑造。这三条最初独立的线索在十九世纪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复杂而模糊的地理、种族和文化意义的新图标。到世纪末,这一新的全国”类型”主要被定位在新命名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它结合了来自新英格兰、阿肯色州和东南部山区的文化元素,所有这些都经过东北部记者和插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先入之见的调和。这一形象的种族身份同样不稳定。它部分基于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奴隶主和非裔美国人的贬低性描绘——他们都将所谓的贫穷白人置于真正”白人”的界限之外;同时也借鉴了内战后传教士和作家的叙述,这些叙述赞美山区人民(尽管他们仍不确定该如何称呼他们)是拓荒者过去的骄傲继承者,对于保存美国文明至关重要。这些空间和种族上的不一致以及这一形象本身,源于美国整体以及南部山区特别经历的剧烈变化——一个仍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迅速转变为城市主导的工业强国。随着阿巴拉契亚被工业家和普通读者”发现”,这一形象所代表的人群的含义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略微孤立但总体上普通的农村居民,到早期时代的风景如画的幸存者,再到需要被改造或消灭的危险的私酿酒和世仇野蛮人。
二十世纪乡巴佬(hillbilly)形象最古老、流传最广的前身是乡村土包子。这是一个几乎普遍存在的文化角色,其美国版本可以追溯到新英格兰殖民的最早期,源自英国戏剧中的固定角色”霍奇”(Hodge)——一个典型的约克郡乡下人,特点是土气、精于算计,以及粗俗但机敏的应答。从这些起源中诞生了”扬基佬”(Yankee)这一类型人物,他们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各种名字出现,包括扬基·杜德尔(Yankee Doodle)、乔纳森兄弟(Brother Jonathan)、杰克·唐宁(Jack Downing)、申命记·达蒂弗尔(Deuteronomy Dutiful)、索伦·辛格尔(Solon Shingle)和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活跃于戏剧、年鉴、报纸杂志、短篇小说以及漫画和风俗画中。这些形象在1820年至1850年间最为突出,那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包括工业革命的开端、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围绕废除或扩展奴隶制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它们既反映了地区间的敌意,也反映了拥有社会和文化权力的人(尤其是纽约市的城市居民)试图通过贬低农村人和农业生活方式来巩固新社会秩序的努力——而他们中许多人不久前才刚刚离开那种生活。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对这些人物的标准刻画——瘦长的身体、不合身或过时的衣服、奇特的方言和憨傻的笑容——与后来的乡巴佬形象高度吻合。同样相似的还有这些角色刻意的模糊性:他们既是被嘲笑的对象(被欧洲人或美国城里人嘲笑),又是嘲讽那些所谓社会上层的虚伪和价值观的人。在这方面,扬基土包子总是戴着一副”愚蠢的面具”,表面上天真质朴,实则掩盖着与生俱来的精明和韧性。
虽然这个角色预示了乡巴佬的某些特征,但随着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从新英格兰向外传播,它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和金融欺诈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出人头地”的心态联系在一起,而非其最初的乡村土包子形象。它转变为乔纳森兄弟这一角色——美国的人格化象征,在山姆大叔成为国家象征之前代表着美国——开始颂扬美国普通人的力量、勇气和个人主义,因此变得过于泛化,无法作为后来乡巴佬形象的明确原型。与之更直接相关的是另外两种形象,它们与乡村扬基佬有所重叠,但在地理和社会层面上与后来的角色联系更为紧密:即”贫穷白人”(poor white)和”山民”(mountaineer)。
作家和学者后来称之为”南方贫穷白人”这一社会类别的最早描绘之一,来自威斯托弗的威廉·伯德二世(William Byrd II)关于其1728年勘测和绘制有争议的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边界线的远征记录。伯德是一位在英格兰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的弗吉尼亚精英种植园主,他的叙述充满了对该地区动植物和地理的科学讨论,以及对他和他的队伍所遇到的美洲原住民的描述。它还包括对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白人定居者详细而不讨好的描述。伯德对他在迪斯莫尔沼泽(Dismal Swamp)边境地区(靠近今天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附近)遇到的男男女女的描绘,引入了许多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定义南方农村白人的标准套路:
毫无疑问,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居民比北卡罗来纳人生活得更轻松了。它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接近于对懒人国(Lubberland)的描述……至于男人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把所有的活都推给可怜的女人。他们让妻子一大早就从床上起来,而自己却躺着打鼾,直到太阳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程,驱散了所有不健康的湿气。然后,伸懒腰打哈欠半个小时后,他们点燃烟斗,在一团烟雾的保护下,冒险走到户外;不过,如果天气稍微有点冷,他们就会哆哆嗦嗦地赶紧缩回壁炉角落……他们就这样虚度光阴,像所罗门笔下的懒汉一样。
伯德对他所遇到的边远地区人民的奇怪矛盾态度,反映了此后一直是乡巴佬形象特征的模糊性。伯德显然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感到震惊,认为他们不健康、邋遢、完全厌恶工作,但他的愤怒主要不是源于他们的贫困,而是源于他们对他自认为”自然”秩序的拒绝:努力工作和有目标的必要性、女性在经济和身体上对男性的依赖,以及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应有的区别。虽然表面上他似乎真的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恐惧,但他对长时间伸懒腰打哈欠和保护性烟雾云的描绘有一种夸张的、漫画式的特质,暗示的态度更多是讽刺性的嘲笑,而非道德谴责。因此,这里就是一个刻意滑稽的刻板印象的根源元素,后来的南方贫穷白人记录者,以及乡巴佬漫画形象,会反复利用这一元素。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是明确的虚构叙事还是表面上的非虚构叙事,北方和南方的评论家们都巩固了伯德对南方农村贫穷白人这一落后阶层的文学建构。查尔斯·伍德梅森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一位巡回圣公会传教士,他与伯德对南方农村白人懒惰的看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没有伯德那种喜剧色彩。伍德梅森在1766年的著作中谴责了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白人农民和牧民的贫困和”极度懒散”,他愤怒地写道,这些人”沉溺于他们目前低下、懒惰、邋遢、野蛮、地狱般的生活,似乎并不想改变它。“近一个世纪后,一篇关于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男女的报道说明了这种批评的持久性。1847年的文章《卡罗来纳沙丘人》将这些农村居民描述为”穿着和外表都很奇特”,总是穿着”最朴素的土布……常常不穿鞋……戴着最廉价质地的软帽……是一个像印第安人一样独特的种族。“与伯德和伍德梅森一样,作者强调”他们脑海中最主要的想法似乎是对劳动的厌恶。“与当地印第安人至少还有”个人勇气”不同,作者哀叹”沙丘人”没有个人抱负或”性格上的活力”,因此将永远被困在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中。
《卡罗来纳沙丘人》面向北方读者,旨在展示奴隶制对白人和黑人造成的灾难性社会影响,反映了这种形象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持久影响力,以及它被轻易用于新政治目的的便利性。事实上,对南方贫穷白人这一卑下阶层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时服务于奴隶制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利益。对于主张立即解放所有奴隶的废奴主义者,以及仅仅反对奴隶制向西部领土扩张的自由土地派来说,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证明了奴隶制对社会道德和人类勤劳精神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种植园主精英阶层过度的经济权力。它也隐含着警告:奴隶制向非蓄奴地区扩张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并对原本坚强的白人农民的职业道德产生削弱作用。对于奴隶主,特别是那些处于南方社会顶层的人来说,农村劳动阶层白人的懒惰为这一”特殊制度”提供了正当理由,并清楚表明需要一个由种植园主领导的经济和社会等级制度。种植园主D·R·亨德利写道,例如,“贫穷白人”是”地球上用两条腿直立行走的最懒惰的动物……表现出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生愚蠢或智力迟钝。“因此,对于废奴主义者和支持奴隶制的意识形态者来说,南方贫穷白人完全缺乏勤劳、智慧、社会礼仪和荣誉——这些是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基本要素——因此不应被信任参与政治决策。
北方和南方的中上层评论家认为这一阶层的人如此彻底堕落,以至于他们质疑其”白人”身份的主张——而这是南方劳动阶层白人对政治平等、“规范”地位以及相对于自由黑人和奴隶黑人的社会优越性的唯一诉求。与伯德和《卡罗来纳沙丘人》的作者一样,记者和游记作家反复将”贫穷白人”与其他所谓低等的有色人种进行不利比较,无论是被奴役的黑人、印第安人,还是墨西哥农民。通过各种论点,包括基因劣势、与”非白人”过度通婚,以及环境因素,如南方气候的破坏性影响、猖獗的疾病和极其不足的饮食,这些作家断言”贫穷白人”既不是真正的”白人”,也不是明确的”非白人”,而是一个独立的”‘克拉克’(Cracker)种族”,在各方面都如此堕落,以至于没有社会进步的能力。这种态度在1866年波士顿《每日广告报》的一篇文章中表现得很清楚,该文宣称这一社会阶层已经堕落到”如此肮脏的贫困、如此卑劣的无知、如此白痴般的愚蠢”的深渊,以至于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文明化。作者总结道:“时间和努力将引导黑人走向有智慧的成年,但我几乎怀疑是否有可能将这些’白色垃圾’提升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非裔美国人对劳动阶层白人的蔑视几乎与中产阶级和精英白人一样强烈。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发明了包含明确”白人”含义的贬义词,如”(贫穷)白色垃圾”和”穷巴克拉”(poor buckra)(源自西非语中”白人”一词的变体形式)。尽管奴隶与非精英南方白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许多奴隶深深怨恨贫穷白人作为监工和巡逻骑手的角色,并接受了他们主人的观点,即南方精英种植园主在社会和道德上更为优越。许多人还相信,无论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黑人,都形成了一个介于社会体系顶端的种植园主贵族和底层”贫穷白人”之间的中间社会阶层。因此,“贫穷白人”和”白色垃圾”这一社会和文化类别的建构,既允许黑人奴隶开辟出一个社会优越感的空间,也允许白人种植园主精英在一个据称民主的社会中为白人之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提供正当理由。
除了对真实乡村白人看似准确的描绘之外,第二股影响深远的关于贫困南方白人的文学流派是被后来学者统称为”西南幽默作家”的作家群体所创作的故事,这些作品将历史现实与文学虚构自由融合。他们笔下的人物无论在外貌还是行为上,都是即将出现的乡巴佬形象的重要原型。奥古斯塔斯·B·朗斯特里特1835年作品集《乔治亚风情、人物、事件等——共和国前半世纪》中的兰西·斯尼弗尔是这些文学形象中最早也最持久的一个。斯尼弗尔是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男人,他那种彻底无精打采的常态只有在观看他帮忙挑起的血腥打斗时,才会因那种替代性的刺激而被唤醒。朗斯特里特由此确立了一种文学类型:堕落的穷白人作为骗子,故意从他人的不幸中牟利。这一传统在随后几十年由众多作家延续,包括威廉·吉尔摩·西姆斯、理查德·希尔德雷斯、哈丽雅特·比彻·斯托,以及最为充分地由约翰逊·J·胡珀在其塑造的西蒙·萨格斯上尉形象中体现。萨格斯的早期插图展现了他衣衫不整、满脸胡须、长而棱角分明的鼻子和面部特征、蜡黄的表情以及宽边帽,这些都预示了后来插画家和电影制作人所使用的标准乡巴佬图像符号(图1.1)。

图1.1
乡巴佬原型一号:西蒙·萨格斯。F·H·达利绘制的卷首插图,约翰逊·J·胡珀,《西蒙·萨格斯上尉历险记——塔拉普萨志愿兵前队长》(费城:T·B·彼得森出版社,1845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惠允。
尽管这些作家对尚未诞生的乡巴佬形象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没有一位明确描写来自或生活在山区环境中的人物。唯一的例外是第一个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穷白人角色——萨特·洛文古德,由田纳西记者乔治·华盛顿·哈里斯创作,于1850年代中期发表在田纳西州的各种报纸和威廉·T·波特的全国性幽默杂志《时代精神》上。萨特不道德、种族主义、堕落、心地恶毒,却又充满活力,几乎不受任何社会礼仪和地位的约束,他积极地沉醉于自己的兽性和粗俗之中。哈里斯将他描述为”一个长相古怪、腿长身短、脑袋小、白头发、猪眼睛的滑稽天才”,他是一个大得离谱、名字荒唐的家庭的一员,家里有十六个孩子(名字诸如菲尼亚斯、佐迪亚克、简·巴纳姆·林德等),一个肮脏但多产的母亲,以及一个兽性十足的父亲霍斯。人类的赤裸(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是哈里斯几乎所有故事的核心,这些故事经常描写萨特或其他角色被剥光衣服或进行(暗示的)通奸。大多数故事还涉及萨特兴高采烈地对权威和权力人物施加的残忍恶作剧,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对黑人教众施加恶作剧。但同样经常的是,萨特成为自己贪婪或轻信的受害者,被迫”扮演傻瓜”,这是他自称”天生的该死傻瓜”所认识到的角色。他是北方先驱扬基·杜德尔和其他人物的更原始、更尖锐的对应物,他认识并接受自己愚蠢(以及所有人类的愚蠢)的能力,赋予了这个原本只是怪诞和淫秽的形象以持久的文化意义,使他成为比前面讨论的穷白人例子更为丰富的角色。
哈里斯对萨特及其家人和邻居在田纳西州东部蛙山的描绘,将朗斯特里特、胡珀等人的刻画固化为二十世纪美国乡巴佬的标准套路——懒惰、邋遢、堕落的人们忍受着痛苦但总是滑稽的贫困,体现着原始身体性和性欲的未开化状态,并拥有几乎超人的生育能力。但由于几个原因,哈里斯的作品只是乡巴佬形象的先驱,而非第一个例子。首先,哈里斯将故事中的山区背景更多地用作丰富多彩的背景,而非角色人格和更广泛文学意义的内在元素。其次,尽管哈里斯的洛文古德故事最初在报纸和杂志读者中相当受欢迎,但他激烈的政治立场(狂热的分裂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的强烈混合)、浓重的方言和扭曲的语法使用,以及他毫不掩饰的粗俗和不雅内容,与十九世纪晚期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主流”高雅传统”相冲突。马克·吐温非常欣赏哈里斯的幽默,但在他1867年对《萨特·洛文古德:一个”天生该死傻瓜”讲的故事》的评论中准确预言——这是哈里斯故事首次以书籍形式出版——“东部人会认为它粗俗,可能会将其列为禁忌。”直到1930年代的威廉·福克纳和厄斯金·考德威尔,哈里斯几乎没有文学追随者,他的作品也绝版了。尽管自1966年该书再版以来,萨特的爱好者变得更加突出,但他仍处于文化体面的边缘,批评家们仍不确定该将哈里斯和他的另一个自我置于文化光谱的何处。
19世纪50年代,平面艺术家们试图描绘萨特的作品清楚地表明,当时还不存在南方山民的标准形象,事实上,大多数城市美国人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19世纪中期杂志上的大多数插图都将萨特描绘成穿着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城市服装的形象(如燕尾服和高领衬衫),或者乡村绅士的骑装。贾斯汀·O·霍华德是一位纽约政治漫画家,受委托为1867年原版《萨特·洛文古德》绘制配图,他的作品最接近对艰苦生活的南方山民的准确描绘,也最接近20世纪标准化的乡巴佬形象。他将萨特呈现为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物,有着细长的鼻子和双手,赤着脚,穿着不合身的工装裤和一顶软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赤身裸体的父亲逃离一群愤怒的蜜蜂(图1.2)。然而,霍华德19世纪晚期的同行们并没有采用他的人物塑造方式,而是将洛文古德呈现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土包子或哈克贝利·芬的翻版。这种描绘的多样性表明,到世纪之交,一个全国公认的南方山民图像刻板印象尚未建立。

图1.2
乡巴佬原型之二:萨特·洛文古德。贾斯汀·O·霍华德插图,乔治·华盛顿·哈里斯,《萨特·洛文古德:一个”天生蠢货”讲的故事》(纽约:迪克与菲茨杰拉德出版社,1867年),第25页。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惠允。
乡巴佬形象发展的第二条主要脉络是对南方山区人(几乎全是男性)的文学描写,最初主要指南阿巴拉契亚地区,后来也包括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丘陵地带。虽然一些内战前对南方山民的描写强调他们原始的野蛮性,但内战前的作家和艺术家更多地赞扬他们的狩猎和战斗能力,颂扬他们是能够在恶劣荒野中茁壮成长的坚强边疆居民。这些对山民的描绘为正在形成的乡巴佬形象增添了两个重要的新元素:将土地和人民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建构;以及一种与生俱来的暴力观念,以枪支和步枪的无处不在为代表。
关于南方山民最早的描述之一来自1780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向弗吉尼亚人民发布的一份公告,警告他们”后水地带人”的危险——这些人从田纳西州东部行军到南卡罗来纳州边境,一周后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国王山战役中击败了他的部队。弗格森警告城市弗吉尼亚人,他们应该加入保皇党军队,“除非你们想被野蛮人的洪流吞噬……这些人以其骇人的残忍和无纪律行为,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懦弱和缺乏纪律。”弗格森相信城镇居民会被将他们西部边疆同胞描述为”野蛮人”的说法所打动,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早在18世纪晚期,南方山民就被视为”他者”的观念。
与此密切相关但更具英雄色彩的山民文化建构是被美化的丛林边疆人形象,主要基于丹尼尔·布恩和大卫·克罗克特真实或想象的事迹和个性。布恩尤其成为美国男性气概的主要象征,因为他带领定居者穿过坎伯兰峡谷进入肯塔基州,与印第安人战斗并杀死他们,驯服了蛮荒的荒野。布恩最初在约翰·菲尔森1784年广为流传的《丹尼尔·布恩上校历险记》中被永久铭记,随后被众多作家所颂扬,并成为美国荒野文学中典型英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中纳蒂·班波的主要灵感来源。通过菲尔森、库珀等人的文学再创作,布恩成为一个国家神话的化身,“使荒野对民主安全的人”,最好地象征了边疆的再生潜力。因此,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通常缺乏后来乡巴佬身份所固有的模糊性。
克罗克特是乡巴佬形象更直接的先驱。虽然像布恩一样,他代表着英勇的边疆人、印第安人战士和大型猎物猎人,但在他那个时代,他也象征着乡下人的无知和粗犷的幽默。尽管他多次当选田纳西州议会议员和美国众议院议员,但仍因其乡下出身而被更有教养的议员们嘲笑。讽刺的是,他最终的神话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辉格党的产物,该党利用克罗克特(在他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真正的”乡下人来谴责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党——杰克逊据说也是一位边疆人。真正的大卫·克罗克特在德克萨斯州保卫阿拉莫时牺牲后,神话中的”戴维”·克罗克特——一个超人边疆人和滑稽乡巴佬的混合体——继续活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克罗克特年鉴》系列中,活在詹姆斯·柯克·保尔丁的《西部雄狮》(1831年)和弗兰克·默多克与弗兰克·梅奥的《戴维·克罗克特;或者,确定你是对的,然后勇往直前》(从1872年到1896年连续演出)等戏剧中,以及20世纪众多的电影和电视改编作品中。
布恩和克罗克特的形象描绘及其文化含义,将成为新兴山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一形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乡巴佬(hillbilly)形象。后来的艺术家以及舞台和银幕服装设计师,会将鹿皮衣、毛皮帽或浣熊皮帽,以及长管步枪融入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中(图1.3)。此外,那些在荒野中开辟文明的人物形象,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延续了下来,在更为正面的山民叙述中,他们被描绘成精神饱满而高尚的人,在工业时代的边疆保留着拓荒者的技艺和生活方式。最后,布恩和克罗克特晚年都迁移到了新的西部边疆——布恩离开肯塔基州,在密苏里州中东部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而克罗克特则穿越阿肯色州大部分地区前往得克萨斯州——他们的真实人生经历象征性地将乡巴佬起源的两个不同地区(“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融合成了一个神话般的空间。

图1.3
戴维·克罗克特:最早由媒体塑造的乡巴佬形象。封面插图由不知名插画家绘制,《戴维·克罗克特年鉴》,第1卷,第3期(纳什维尔,1837年)(临摹自安布罗斯·安德鲁斯为詹姆斯·哈克特在詹姆斯·柯克·保尔丁的《西部雄狮》中饰演尼姆罗德·怀尔德法尔一角所作的肖像画)。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美国历史中心。CN 10458。
战前时期访问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游客所写的游记,是山民形象发展过程中较少神话化的来源。这些文字表明,尽管大多数城市评论者认为山区景观因其美丽和原始而令人敬畏,但他们眼中的南部高地居民虽然古朴,却与美国其他农村地区的人并无明显不同。少数面向大众读者的十九世纪中期南部山区著作,如《南方的冬天》,也描绘了类似的画面。这部虚构的游记由”波特·克雷永”(作家兼插画家大卫·亨特·斯特罗瑟的笔名)撰写,讲述了布罗德埃克乡绅一家穿越弗吉尼亚、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山区的旅程。虽然斯特罗瑟对当地人的外貌描写暗示了一种视觉刻板印象的萌芽,但与后来的叙述不同,山民并未被描绘成堕落或不道德的人。尽管描绘布罗德埃克乡绅的向导琼斯先生的插图标题为”山民”,呈现出一个略显阴险的形象,但他骑在马上、身穿厚布外套和尖头鞋的装扮,更接近美国西部山地人或欧洲流浪者的形象,而非后来那种赤脚、穿背带裤的乡巴佬形象(图1.4)。作者既没有将琼斯,也没有将任何其他当地居民描绘成懒散、贫困、酗酒、暴躁或对陌生人充满戒心的人——这些都是乡巴佬形象的标准特征——而是强调了他们的热情好客和该地区丰富的食物。布罗德埃克一家遇到的另一位山民坎·福斯特,他蓄着胡须、衣衫褴褛的形象指向了一种正在形成的刻板印象(图1.5)。然而在文字中,他并没有警惕地用步枪瞄准”入侵者”,而是欢迎访客来到他整洁美观的家中。因此,斯特罗瑟对琼斯先生和坎·福斯特的描写表明,在内战之前,南部山民的文学形象是贫穷但正直的乡村居民,而非战后文学中那些愚昧而充满敌意的男男女女。

图1.4
乡巴佬刻板印象形成之前南部山民的典型描绘。“山民”。插图和文字由大卫·亨特·斯特罗瑟创作,《南方的冬天》,《哈珀斯新月刊》第15期(1857年11月):725页。

图1.5
“坎·福斯特”:山民形象——衣衫褴褛但正直好客的主人。插图和文字由大卫·亨特·斯特罗瑟创作,《南方的冬天》,《哈珀斯新月刊》第16期(1857年12月):173页。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穿越偏远乡村之旅》出版于1860年,可能是战前时期对南部山区居民最具影响力的描绘,但书中也没有表明这些人与南方其他地区的非精英白人有明显不同。与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奥姆斯特德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谴责奴隶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即使在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山区——这些地区没有大规模种植园,奴隶主也相对较少——他也看到了这种负面影响。尽管奥姆斯特德经常将他遇到的劳动阶层山民描述为”粗俗”、“愚昧”和”肮脏”,并抱怨他们的懒惰及由此导致的贫困,但他将这些特征归因于奴隶经济,而非后来作家所认为的独特山地民族的文化和遗传特征。简而言之,即使到了内战前夕,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居民的诠释者们仍然不认为这些人构成了南方非精英白人的一个亚群体,更不用说是一个独立的”种族”,在文化上独特、在社会上与美国文明隔绝。
在同一时期,作家和社会评论家开始撰写关于阿巴拉契亚南部土地和人民的文章,与此同时,冒险家、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幽默作家也发现了另一个孕育”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主要地区: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的丘陵地带。由于人口稀少,即使在内战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对隔绝,阿肯色州迅速获得了一个名声——那里居住着生活在近乎荒野条件下的暴力原始定居者。亨利·罗·斯库尔克拉夫特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印第安文化研究者,他于1818至1819年间穿越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的山区,是最早详细报道该州情况的访客之一。斯库尔克拉夫特描述了”居民们……过着与野蛮人相似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他们对安逸的热爱和对农业劳作的蔑视……以及他们穿着兽皮的方式。“他还感叹道,每当狩猎季节来临,男人们就把家务和农活丢给女人。与威廉·伯德等人的批评如出一辙,他将边疆阿肯色人定义为不文明的民族,颠倒了”正常的”种族和性别等级秩序。
后来的访客进一步强化了阿肯色州是一片暴力原始之地的观念。英国地质学家乔治·费瑟斯通霍称该州部分地区为”罪恶与耻辱的污水坑”,而德国运动员弗雷德里克·格斯塔克则描绘了一片居住着酗酒懒惰的边疆居民的土地,这些人容易诉诸暴力,并热衷于粗犷的猎熊运动。幽默作品如查尔斯·芬顿·诺兰关于”皮特·惠特斯通上校”的专栏文章,以及托马斯·班斯·索普著名的《阿肯色大熊》,都在1840年代通过《时代精神》杂志广泛传播,巩固了该州的边疆形象。这些游记、冒险故事或夸张故事并非都以该州的山区为背景,也并非阿肯色州或旧西南部所独有。然而,它们共同为这样一种观念奠定了基础:懒惰、潜在危险且贫困的人们居住在阿肯色州乃至整个南方。
西南部流行文化与即将出现的乡巴佬形象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或许就是”阿肯色旅人”(The Arkansas Traveller)——这是一个书面故事、幽默演说、器乐和歌词歌曲以及图像形象,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持续出现。这个著名故事很可能是桑福德·福克纳上校的创作,他是阿肯色州建州初期的一位精英政治家。故事表面上幽默地讲述了一群阿肯色州政客在1840年竞选巡回期间迷失在山中,遇到一个贫穷定居者的经历——这个定居者在一间简陋的木屋前不停地用小提琴拉着同一首曲子。定居者对访客的每一个求助请求都以文字双关、否定回答和漠不关心来回应。举例如下:
旅人:“既然我这么冒昧,请问您贵姓?”
定居者:“可能是迪克,也可能是汤姆;但差得远呢。”
旅人:“先生!您能告诉我这条路通向哪里吗?”
定居者:“自从我住在这儿,它就没去过任何地方;每天早上我起来它都在那儿。”
最后,旅人(代表福克纳上校本人)通过抓起小提琴,演奏出定居者忘记的曲子结尾,达成了目的。感激的房主因终于想起了结尾旋律而欣喜若狂,邀请旅人们进屋享用食物和饮料。
“阿肯色旅人”于1847年作为乐曲出版,1862或1863年附上对话出版,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以各种形式出现。它还以图画形式呈现,最初是爱德华·沃什伯恩的一幅画作(约1855年),然后是基于该画的版画,最著名的是1870年柯里尔与艾夫斯的两幅版画。这些画作描绘了构成二十世纪乡巴佬生活方式形象的许多元素:一个衣衫褴褛、留着长胡子、戴着浣熊皮帽的男人;破旧木屋墙上挂着的兽皮;一个贫困的家庭,包括一个抽着玉米芯烟斗的女人和六个邋遢的孩子;懒洋洋躺在泥地里的狗;门楣上写着”威士忌”的招牌,其中一个字母倒置,表示边疆的无知;以及背景中隐约可见的群山(图1.6)。木屋主人行为和态度的模糊性后来也在乡巴佬形象中得到复制。起初对外人警惕且粗暴,定居者后来却表现出过度的热情好客。他被描绘成贫穷无知,但同时又在荒野中过着完全舒适的生活。同样,定居者象征着边疆的懒惰和闲散,他坐着拉小提琴,却忽视了庄稼和家务。这种懒散与旅人的目的性和紧迫感形成对比。然而,掌握主动权的是定居者,双方都心知肚明。就像后来的乡巴佬角色一样,定居者同时”装傻”并占了旅人——他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上等人”——的便宜。

图1.6
阿肯色旅人。利奥波德·格罗泽利尔根据爱德华·沃什伯恩画作制作的版画,1859年。阿肯色历史委员会。版权所有。G4543-18。
随着”阿肯色旅人”各种形式的受众从阿肯色州政治精英扩展到全州观众,再到幽默杂志和乐谱的全国读者群,这些角色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现存最早的1876年印刷版本中,开场场景介绍了”一位迷路困惑的阿肯色旅人,大约四十年前来到一个擅自占地者(Squatter)的小屋前寻找住处。“这一版本彻底改变了原有含义,1864年在纽约出版的《阿肯色旅人歌曲集》中的版本,则呈现为”一个东部人在阿肯色居民中的经历”。引言还指出,旅人与这位林中居民的相遇令他如此不安,以至于”此后再也没有勇气访问阿肯色!“与萨特·洛文古德早期的插画师一样,这位纽约艺术家完全不知道阿肯色的擅自占地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于是画了一个类似吉普赛人的形象——赤脚、穿着宽松的衣服、头上系着头巾,类似于对贫困流浪者的描绘(图1.7)。当作家H·C·默瑟在1896年描述这个故事时,其含义又发生了变化。在这个版本中,擅自占地者和旅人都被描绘成荒野的产物,一个是粗犷的拓荒者,另一个是堕落的擅自占地者,两者之间阶级对比的信息基本被消除了。由于两个人物现在都被装扮和描述为边疆人,故事暗示所有阿肯色人都属于这一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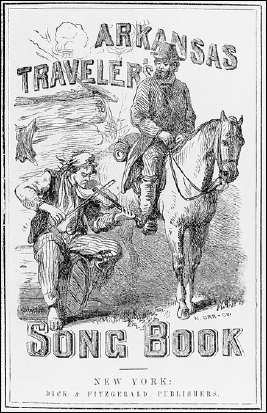
图1.7
一位纽约人将阿肯色旅人边疆人想象成欧洲吉普赛人。封面由不知名插画师绘制,《阿肯色旅人歌曲集》(纽约:迪克与菲茨杰拉德出版社,1864年)。
这首歌曲故事含义的转变揭示了一个地区刻板印象的全国化——“阿肯色”正在成为半滑稽、半野蛮的林中居民的即时可识别代名词,这一流行文化符号对美国人来说变得如同戴着全套羽毛头饰的高贵印第安酋长或懒惰的种植园奴隶一样熟悉。这个音乐故事将象征性贫穷白人的懒散和堕落叠加在早期阿肯色林中居民描述中的边疆人和猎人形象之上,反映了这两种形象的缓慢融合,乡巴佬(hillbilly)形象将在随后几十年从中浮现。
当阿肯色旅人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间逐渐成为标志性形象时,关于乡村土包子、贫穷南方白人和边疆居民的描述和形象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并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些独立的描绘不仅会在整个二十世纪以各种文化形式继续出现,而且还开始凝聚成一个与特定地理区域相关联的新的独立形象——乡巴佬-山民的二元符号。这一新创造主要是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地方色彩”写作兴起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学体裁,源于新兴的、流行的十九世纪杂志(如《利平科特》、《世纪》、《斯克里布纳》、《生活时代》,尤其是《哈珀新月刊》),这些杂志迎合了新兴扩张的城市中产阶级读者群。与十九世纪早期为专业科学界撰写游记、将其作品视为对自然、地质和气候条件客观分析的博物学家和学者不同,地方色彩作家与新杂志一样,主要将其作品定位为娱乐。这类作品以对话式的风格和语调为特征,被作者描述为”银版照片”、“速写”甚至”匆忙记录”,地方色彩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强调”国家某个鲜为人知角落的生活特色”来增加销量。
尽管地方色彩作家和作品的阵容过于多样,无法构成正式的文学”运动”,但他们共享一种关于其描写对象的异国情调和”他者性”的视角。在一个相信美国乃至更广泛的西方在智识、文化和社会上优于世界其他”种族”的时代,这些作品旨在展示的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文化等级——通过强调替代文化和社会的低劣性和异质性来颂扬现代性和”主流”进步与价值观,无论这些是异国情调、风景如画的外国地区和民族,还是美国国内在民族和地理上独特的社会,如路易斯安那的卡津人、佐治亚的黑人,或缅因海岸的新英格兰乡村居民。这些速写倾向于聚焦于内战前和前工业化的美国,既是为了浪漫化过去,也是为了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好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地方——“阿巴拉契亚”——以及一个独特的群体——阿巴拉契亚”山民”——进入了全国视野。1870年至1890年间,地方色彩作家发表了九十多篇关于该地区的游记散文和125篇短篇小说。这些作者的态度可以用最早描述该地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一片奇异的土地和一群独特的人民”。尽管威尔·华莱士·哈尼的标题颇具挑衅性,但他花在描述旅途艰辛上的篇幅远多于描写肯塔基州东南部当代居民的内容。尽管如此,他的文章引入了阿巴拉契亚”他者性”的概念,并将该地区确立为丰富的地方色彩素材来源。虽然哈尼很快就放弃了阿巴拉契亚作为文学素材,但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作家接续了他的工作,包括查尔斯·达德利·华纳、丽贝卡·哈丁·戴维斯、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和詹姆斯·莱恩·艾伦。
在阿巴拉契亚山民形象全国化方面最重要的是玛丽·诺艾尔·默弗里(笔名查尔斯·埃格伯特·克拉多克)极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开创了”南方山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尽管学者们质疑她在《在田纳西群山中》(1884年)和《大烟山的先知》(1885年)等作品中对人物刻画的准确性,但普通读者却将其视为事实。默弗里的作品巩固了早期关于田纳西州东部山区乃至整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观念——这是一片目不识丁但道德高尚、自尊自强的人们生活的土地,与现代美国完全隔绝——但她为笔下的人物注入了一种普遍的忧郁基调。她那哀婉的笔触帮助重新定义了山区,使其成为一个永远停留在过去的地区,与充满活力、快节奏的城市工业化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都相信她那些以战前时代为背景的故事记录的是山区的当代状况,这一事实恰恰说明她在确立这种关于山区及其人民的观念方面是多么成功。
尽管默弗里对山区人民和社会的描绘比许多地方色彩作家更为准确和富有同情心,但所有这些作家都重复并扩展了早期文学作品中对贫穷白人和边疆居民的描写主题。例如,詹姆斯·莱恩·艾伦评论说,虽然许多肯塔基山民过去曾离开山区前往西部追寻传说中的财富,但他们”几乎全都回来了”,无法”应对边疆生活的冲击、活力和进取精神。他们说,这里是懒人的好家园。“这些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也反映了阿巴拉契亚”他者性”和落后性的普遍观念,与奥古斯塔斯·B·朗斯特里特和乔治·华盛顿·哈里斯早期的人物描写如出一辙。哈尼声称”当地人”在人体解剖学上有”明显的特征”,所有人都表现出”骨骼的拉长、面部角度的轮廓……以及粗糙的五官”。人类学家艾伦·丘奇·森普尔受这些地方色彩作家的启发,在1901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将山民描述为”瘦削多骨的面孔、蜡黄的皮肤和暗淡的头发”,并感叹他们”几乎没有保留其’精力充沛的’祖先那种红润、健壮的外表”。
这些连载游记和短篇小说的配图与文字相呼应,反映了一种新的独立山民形象的缓慢形成。起初,这些描绘与战前的插图差别不大。例如,在丽贝卡·哈丁·戴维斯1880年虚构的弗吉尼亚西部和西弗吉尼亚山区夏日度假记述中,山地向导杰里·布朗宁是一位值得信赖、自尊自强的边疆居民的典范,他熟练地将步枪横抱在胸前,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图1.8)。然而,在艾伦1886年的故事《骑马穿越坎伯兰峡谷》中,由著名地方素描画家E·W·(爱德华·温索尔)肯布尔绘制的山民图像急剧转向乡巴佬(hillbilly)形象。肯布尔将两个山区居民描绘成衣着朴素、滑稽可笑的傻瓜,他们愚钝的面孔与对山区自然美景的生动描写形成鲜明对比(图1.9)。艾伦对这两个山民(他称之为”当地典型人物”)试图出售”一袋又小又硬的桃子”(与斯特罗瑟1857年报道的丰富食物形成鲜明对比)的详细描写,完全可以是伯德150年前描写他的”懒汉之地”居民时写下的:“瘦削、扁平、腹部凹陷而安详,温和而忧郁,他们可能就是食莲者……如果能卖掉桃子,他们会很高兴;如果卖不掉,他们也会很高兴。”我们不应过度解读单独一句话或一位喜欢将山民描绘成滑稽刻板形象的画家的插图,但无论其典型性如何,它们确实揭示了一种关于南方山区人民的新观念的出现,这种观念在随后几十年将变得越来越容易辨认。

图1.8
“杰里·布朗宁”:山民作为坚毅边疆居民的典型形象。插图作者不详,丽贝卡·哈丁·戴维斯,《山间小径》,《哈珀新月刊》第61期(1880年7月):1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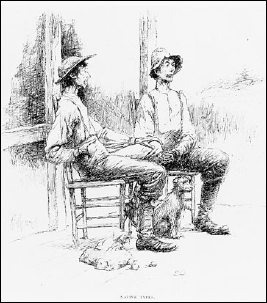
图1.9
山民被描绘成傻瓜。E. W. Kemble插图,标题为”本地类型”;James Lane Allen,“骑马穿越坎伯兰峡谷”,《哈珀新月刊》第73期(1886年6月):53页。
与男性形象类似,山区女性的形象和描绘也经历了相似但不那么显著的转变。在内战前的记述中,如《南方的冬天》,她们被描绘成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或典型的小农场主妇。但到了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地方色彩作家越来越多地将女性角色和非虚构人物塑造成几种类型之一:美丽但无知的山区少女;过度劳累、衣着粗陋、艰难照顾庞大家庭的苦命女人;或者(如Kemble所画)戴着帽子、没有牙齿的老妪,在忧郁的烟雾中抽着玉米芯烟斗度过余生(图1.10)。Charles Dudley Warner在1889年的《肯塔基评论》中概括了这种生命周期:“女孩们早早结婚,生育众多孩子,像奴隶一样劳作,在女人本应最美好的年华,她们却已凋零,牙齿脱落,变得丑陋,看起来苍老。”与男性形象相比,“山区女性”的刻板印象没有那么明显,在世纪之交的杂志插图或小说扉页中出现的频率也低得多,但她同样反映了将”贫穷白人”和边远地区拓荒者的概念融合成新的”贫穷山民”形象的趋势。

图1.10
山区女性被描绘成抽烟斗的老妪。E. W. Kemble插图,标题为”一位山民妇女”;James Lane Allen,“骑马穿越坎伯兰峡谷”,《哈珀新月刊》第73期(1886年6月):62页。
尽管地方色彩作家牢固确立了阿巴拉契亚”他者性”的”事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描绘的是一幅风景如画的景象,以及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古怪而多彩的男男女女。这个虚构的阿巴拉契亚与其说是一种担忧,不如说是一种好奇,主要用来指出先进文明的好处,并为北方城市居民提供一个神秘(但最终安全)的荒野之旅,让他们能够精神焕发地返回自己在都市社会秩序中的位置。
然而,从1880年代开始,并在1890年代迅速加速,一种截然不同的地区观念发展起来——认为南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们(最终扩展到更广泛的南部山区)不仅与文明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对文明构成威胁。将山区建构为无法无天之地、被”私酿酒”(moonshining)和”家族世仇”(feuding)这对”邪恶”双胞胎诅咒的新意识形态,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有组织的抵抗联邦消费税征收和暴力的家族间冲突确实在东南山区发展起来。这一地区的小农长期以来将部分玉米作物转化为酒精供个人消费,并与农村邻居和城镇居民交易或出售。联邦政府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曾零星尝试征收这种产品的消费税(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威士忌叛乱”是高地反对这些尝试的最著名例子),但直到内战时期,他们才开始集中努力要求所有酿酒商,无论规模多小,都必须获得许可证并缴纳税款。南部山区农民依靠出售玉米威士忌来补贴微薄收入,并将其生产视为长期享有的权利,他们深深怨恨这种他们认为是中央集权对地方事务的无端和危险干预。许多这些小型酿酒商在大众媒体中越来越多地被贴上”私酿酒贩”(moonshiners)和”走私贩”(blockaders)的标签,他们和许多顾客对执法人员经常使用的粗暴手段以及有时腐败和非法的做法怀有深深的不满。
这些紧张关系和敌意在189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经济萧条、国家化市场力量和城市化向以前纯粹的农村地区扩张,以及地方禁酒立法的蔓延,威胁到了乔治亚州东北部和该地区其他地方许多山区酿酒商的生计。结果是半正式的有组织努力兴起,通过集体暴力来维持对酒类生产的地方控制。在一个许多白人男性也感到受到黑人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社会自主权以及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工业化有薪劳动力市场威胁的地区,这种集体反抗往往与对白人至上主义和传统道德受到挑战的担忧密切相关。这些由”白帽党”(white caps)和”夜骑士”(night riders)维护经济、社会和种族现状的努力在1890年代末基本结束,因为联邦当局逮捕并瓦解了抵抗组织,现代化力量继续侵蚀农村生活。但到这时,山民作为无法无天的”私酿酒贩”永远与”税务官”(revenooers)作战的形象已经在大众想象中根深蒂固,并从那时起一直是乡巴佬(hillbilly)神话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私酒相关暴力事件引起政府和媒体广泛关注的同时,东南部高地(尤其是肯塔基州东部)的地方冲突,往往是家族之间的冲突,也登上了全国性的新闻头条。从19世纪70年代到下一个世纪的头十年,地区和全国性报纸报道了数十起家族冲突,仅1874年至1893年间就有四十一起。虽然大多数争端持续时间短暂,伤亡人数也不多,但有些冲突,如被称为”罗文县战争”的马丁-托利弗冲突,持续了三年多,造成二十人死亡。记者们最初倾向于将此类冲突视为南方现象,后来又视为肯塔基州特有的现象,认为这是持续的政治权力斗争和独特暴力历史的必然结果。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阿巴拉契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谋杀案将焦点从整个州转移到了山区。越来越多的两党报纸,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民主党的《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信使日报》和共和党的《纽约时报》,谴责山区人民是堕落的野蛮人,他们的冲突不是源于政治或经济争端,而是源于从其野蛮的苏格兰高地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甚至遗传特征。记者们在描述这些冲突时,将术语从vendetta(世仇,带有科西嘉背景)改为feud(宿怨),并将争端各方称为家族clan(氏族),强调了这种对苏格兰血统的新关注。
《信使日报》和《纽约时报》等报纸认为,山区人民威胁的不仅是肯塔基州东部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而是整个国家的。他们断言,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办法是以工业化、铁路建设以及城镇发展为形式的地区”进步”。地区新闻记者和精英们急于吸引北方资本,将他们的地区描绘成安全的投资机会,因此将任何反对工业”进步”的当地人定义为落后和异常的——换句话说,是与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以及全世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人同等的白人野蛮人。1912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篇社论,针对弗吉尼亚州山区小镇希尔斯维尔发生的致命枪战,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该报怒斥道:
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补救办法,那就是教育和消灭。对于许多人来说,后者是唯一的补救办法。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当他们蔑视文明时,就必须死亡。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北卡罗来纳的山民,就像红种印第安人和南非布尔人一样,必须学会这个教训。
这篇社论对南方山民的处方比大多数讨论都更为严厉,但它仍然代表了数百篇类似新闻报道的特点:将一个家族的行为与整个地区人口混为一谈,并将南方山民与其他处于文明边缘之外的”原始”民族相比较。
尽管这些报道坚持认为工业发展是解决山区固有暴力问题的唯一办法,但历史学家阿尔蒂娜·沃勒等人令人信服地论证,实际上,19世纪90年代的这些暴力爆发很可能是该地区内战后经济和社会转型达到高潮的结果。采掘业(如伐木、铁矿和煤矿开采)的出现,以及将这些产品运往全国市场所需的铁路线建设,土地投机的增加和外地土地所有权比例的上升,以及农业机会的减少,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主张现代化的力量与争取维护地方自治和传统农业体系的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南方山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没有理由质疑无数新闻报道的立场,即肯塔基州东部普遍存在的”无法无天”反映了南方山区人民的文化和遗传传承。因此,到世纪之交,南方山民是一个威胁美国其他地区进步的暴力野蛮人种族的观念,已经在美国人的心理中根深蒂固。
在南方山区的所有冲突中,没有哪一个比19世纪80年代的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宿怨”更能激发公众的想象力。这两个家族既不是南阿巴拉契亚地区第一起、持续时间最长或最血腥的家族冲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可疑的殊荣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无数文章和几本书,最著名的是纽约《世界报》记者T·C·克劳福德的《美国世仇:美国野蛮主义的故事》(1889年),将”魔鬼安斯”(威廉·安德森)·哈特菲尔德和”老兰内尔”(伦道夫)·麦科伊及其亲属描绘成生活在”谋杀之地”的野蛮而与世隔绝的山民,对他们来说家族忠诚高于一切,他们随时准备甚至渴望对竞争对手和执法官员使用致命暴力。实际的冲突更多地与经济纠纷和州际竞争有关,而非”暴力文化”,但大多数报道回避任何此类政治和经济分析,而是将其作为该地区所有农村人民非理性暴力和危险无知的典型例子。
这种图像学巩固了一种新的、更加堕落和暴力的山民形象,有力地强化了这一愿景。克劳福德《美国血仇》的卷首插图由《纽约世界报》的插画师绘制,将”魔鬼安斯”描绘成一个坚韧如钉、手持步枪的山地族长,留着飘逸的黑色胡须,戴着宽边帽(图1.11)。克劳福德在序言中预见到这些视觉表现在塑造标志性野蛮山民形象中的重要性,他断言这些插图”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捕捉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精神和性格”,并且”无论其他内容如何评价,仅凭这些插图就赋予了本书价值”。哈特菲尔德可能并未完全同意这种对自己的描绘,但他确实成为了媒体名人,并在世仇暴力结束很久之后积极参与摆拍照片。他反复为摄影师摆姿势,步枪总是处于待发状态(用一个图片说明的话来说就是”武装待命”),或者腰间和胸前绑着霰弹枪和步枪子弹的弹带。1897年,“魔鬼安斯”接受了一位流动摄影师的请求,与家人一起合影,枪支被显眼地展示出来(图1.12)。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照片被广泛翻印,哈特菲尔德一家作为面容阴沉的亡命之徒的形象,成为了”现代”美国人眼中所有山民的代表。哈特菲尔德甚至在后来的山民电影描绘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在1915年山民讽刺片《幼崽》于弗吉尼亚山区拍摄之前,导演莫里斯·图尔纳专程前往西弗吉尼亚州明戈县会见”魔鬼安斯”,显然是为了让他对山民角色的刻画更加真实可信。电影学者杰里·威廉姆森推测,哈特菲尔德作为山区的标志性人物在全国公众心目中如此突出,他可能是后来电影、卡通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中典型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原型。

图1.11
阴森山民形象的建构:“魔鬼安斯”哈特菲尔德。格雷夫斯先生绘制的卷首插图;T·C·克劳福德,《美国血仇:美国野蛮主义的故事》(纽约:贝德福德、克拉克公司,1889年)。

图1.12
山民作为暴力世仇者形象的固化:“魔鬼安斯”哈特菲尔德(前排左二)及其家人,1897年。摄影师不详。图片由西弗吉尼亚州档案馆提供。
野蛮山民世仇者的新概念迅速超越了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冲突的具体背景,扩展到小约翰·福克斯及众多次要作家关于阿巴拉契亚生活的虚构作品中。通过他数十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坎伯兰血仇》(1895年)、《天国来的小牧羊人》(1903年)和《孤松小径》(1907年),福克斯展现了他眼中文明社会与暴力落后的山区私酒贩子和世仇者堕落文化之间的鸿沟。这些作品中的配图强化了这种愚昧、堕落山民的概念。例如,福克斯1892年短篇小说《山中欧罗巴》的配图将女主角的父亲描绘成一个邋遢的私酒贩子,倚靠着他的枪(图1.13)。这幅画由E·W·肯布尔绘制——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是我发现的最早将后来标志性乡巴佬(hillbilly)几乎所有视觉特征汇集在一起的作品:阴沉的神情、赤脚、蓬乱的长胡须、背带裤、没有形状的超大毡帽、私酒罐或酒壶,以及长管步枪。尽管这种标志性的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直到1930年代才被普遍认知,但耸人听闻的报纸报道以及小约翰·福克斯等人小说中的文字和图像描绘,共同确立了公众对野蛮堕落山民的认知。

图1.13
标志性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出现。E·W·肯布尔绘制的插图,标题为”老爹”;小约翰·福克斯,《山中欧罗巴》,《世纪画报月刊》第42卷(1892年10月):846页。
世纪之交的作家、学者和慈善工作者对这种危险山民的新观念提出了各种回应。一些作家大多对山区及其居民并不熟悉,毫无质疑地接受了这种刻板印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乔治·文森特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滞后的边疆》(1898年)中重申了标准说法:在”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和田纳西山区的宁静角落……边疆实际上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直到今天”——这一”事实”基于他在肯塔基东部山区四天的短暂考察,以及”穆尔弗里小姐、小约翰·福克斯先生和其他作家”的”生动”故事。然而,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如此之大,以至于连文森特自己也承认”我们听过太多关于山民无知的故事,当发现他们对许多我们以为他们不会知道的事情相当熟悉时,我们多少有些失望”,并怀疑镇上人讲述的关于落后山民的故事是”玩笑”,“带有报纸杜撰的痕迹”。同样,作家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发现很难将所有山民都”无知……懒惰、邪恶、懦弱”的标准报道与他在该地区的亲身经历相调和——他只体验到”友善的对待……几乎没有道德败坏的迹象”。但最终,对这些作家以及可能大量的读者来说,白人山地野蛮人神话的意识形态力量太过强大,无法抵消他们对其真实性的怀疑。
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此轻易地接受私酒贩子-世仇者的刻板印象。弗朗西斯·林德在1896年的作品《真实的私酒贩子》中批评了小说家们急于给南部山区人民(以及南方其他地区)贴标签的做法。在从弗吉尼亚到路易斯安那寻找”地方色彩”整整五天后,他的主人公”彭克拉夫特”终于发现了他认为是”南方典型”的一家人,叙述者告诉他这可能是佐治亚山民。“山民?不是私酒贩子吗?”彭克拉夫特兴奋地问道。“当然是,”对方讽刺地回答,“所有山民都是私酒贩子。你不知道吗?”彭克拉夫特对叙述者故意的夸张浑然不觉,继续写了一个关于嗜血男女的故事,“他们对人命的尊重是负数……对他们来说所有陌生人都是’税务官’,因此可以毫无愧疚地杀掉。”林德这个警示故事的结尾是全副武装的彭克拉夫特访问田纳西东部山区,却发现他的描绘是多么不准确。“这些人贫穷、无知、淳朴、原始——你可以用这类词来形容,”彭克拉夫特忏悔道,“但他们像阿拉伯人一样好客,像他们的淳朴一样诚实,像任何地方未被污染的乡村人一样无害。”
毫不奇怪,来自山区社区的人们对堕落山民的刻板印象提出了最强烈的批评。J·T·怀尔兹牧师和J·H·波尔赫默斯牧师都曾在南部山区服务,他们愤怒地反驳了1895年《世界宣教评论》报道的一篇演讲,该演讲指责山区人民进行血腥世仇、“道德松弛”,对外部世界和基督教完全无知。怀尔兹甚至暗示山区人民利用外人对当地人无知的预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最敏锐的头脑和最机智的人……永远在愚弄陌生人,并在彼此之间评论那些从城市来的、准备相信一切所闻的无知者”。伯里亚学院学生合唱团主要由山区青年组成,他们对1896年作家小约翰·福克斯在校园演讲的反应也反映了当地人对诋毁山民形象的强烈敌意。学生们发现福克斯居高临下地朗诵关于阿巴拉契亚山区人民的读物、歌曲和故事如此令人反感,以至于他们谴责他”根本不是绅士”,并威胁要给他涂柏油粘羽毛。然而,尽管他们强烈抗议,福克斯后来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和全国巡回演讲者,并在公众想象中成为南部山区社会的权威来源。
Polhemus、Wilds和伯里亚学院的学生们都试图为山区人民的声誉辩护,将他们(在后者的情况下,也包括他们自己)呈现为与其他美国公民并无不同。但是,大量非虚构作家在十九世纪末”发现”阿巴拉契亚并着手”拯救”山民时,他们的主流回应并非否认山区文化的”他者性”,而是主张其独特性为世纪之交的美国提供了急需的积极特质。与许多进步主义改革者一样,他们谴责大规模工业化和工会化进程中美国人民所遭受的规训和官僚化,并担忧商业和政府中精英财阀势力的日益壮大威胁到美国人珍视的个人主义、自由和民主价值观。这些男男女女中的许多人还担心,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或用当时的术语称为”种族”)及其文化——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核心——将被来自东欧和南欧的非新教移民以及涌入南北城市的黑人所淹没。此外,为了对抗他们认为困扰美国中产阶级的”柔弱化”和”神经衰弱”,许多进步主义者提倡”艰苦生活”的治愈力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让城市居民重新与土地和先辈们的艰辛开拓生活建立联系。因此,对许多改革者而言,阿巴拉契亚人民代表着一个纯净而未被开发的资源,可以用来抵消这些社会弊病。正如历史学家艾伦·巴托总结的那样:“最黑暗的阿巴拉契亚被视为一个年轻人可以激发其开拓者血统的地方,一个’需要’新英格兰文明影响的地区,以及一个可以拯救美国免于最新迫在眉睫危机的人口。”
阿巴拉契亚作为民族救赎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当地人民的种族和宗教血统——简而言之,就是他们的”白人身份”。根据这一论点,南部山区的人民是殖民时代从不列颠群岛移民而来的”种族”最纯正的代表。在美国政治和知识界领袖大声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以及世界种族严格等级制度的时代,这些作者强调阿巴拉契亚人民在基因、语言、体质和文化上的”盎格鲁-撒克逊特性”并不令人惊讶。人类学家艾伦·丘吉尔·森普尔在1901年将他们描述为”全美国最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而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郊外玛丽维尔学院院长塞缪尔·威尔逊牧师则赞美他们”丰富的红色条顿和凯尔特血液的浪潮”。他们的”活力和坚韧”清楚地表明了山区人民的高生育率,他和其他人认为这可以帮助抵消中产阶级白人美国人不断下降的出生率,防止”种族自杀”。
在宣传南部山民为”百分之百美国人”的愿景时,社会”拯救者”们挑战了阿巴拉契亚人是欧洲乌合之众后裔的流行观点。这一论点最明确的例子或许是1882年一篇直白题为《贫穷白人垃圾》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记录了作者在肯塔基州东部山区的逗留,呈现了令人震惊的落后人群,“他们用木棍犁地、用棍棒打架,认为地球是平的,祖先是神……在许多情况下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而且往往只能数到十。”作者哀叹道:“这些就是’没用的’人,‘贫穷白人垃圾’。”历史学家约翰·菲斯克的《老弗吉尼亚及其邻居》(1897年)为这一理论赋予了学术权威。菲斯克断言,南部边远地区是由贫民和小罪犯定居的,他们被潮水地区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和自身堕落的遗传推到了文明的边缘,他得出结论:“毫无疑问,堕落类型的白人自由民是南方通常所说的’白人垃圾’相当一部分人的祖先。”
为了回应这些对山区人民祖先的道德和遗传批评,“高贵”山民的倡导者们努力重塑这一传统,他们认为山民之所以处于当前的未开化状态,并非因为他们是欧洲人渣的后代或天生暴力,而是因为阿巴拉契亚山脉造成的地理隔离将他们保存在了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约西亚·斯托达德·约翰斯顿在1899年最富诗意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阿巴拉契亚是”一片广阔的马尾藻海,一个被生命海洋包围的死海”,山区人民”沉浸在瑞普·凡·温克尔式的睡眠中,笼罩在忘川般的阴霾里”。约翰斯顿和这个时代无数其他人一样,强调当地人民的开拓者传统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伊丽莎白时代方言和文化,认为山区原住民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生活在过去。用伯里亚学院院长威廉·弗罗斯特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说,他们是”我们同时代的祖先”。这些作者认为,地理和时间上的隔离不仅解释了世仇和私酿酒等异常行为,而且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它保存了社会、文化和身体素质以及种族纯洁性——正是这些品质建造了他们珍视并担心正在迅速消失的美国。
山区民众自认为的捍卫者们努力否定”贫穷白人垃圾”或”卑劣白人”的标签,这也促使他们从1880年代初开始引入一个新的、理论上更为正面的称谓来指代阿巴拉契亚居民——“山地白人”。这一术语出现的时机以及山区慈善事业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恰逢全国范围内种族暴力急剧增加,而白人慈善工作者对重建时期援助非裔美国人所取得的有限进展也日益感到疲惫。“山地白人”这一阶层的建构,以及阿巴拉契亚地区定居学校和传教项目的显著增长,给了许多改革者机会,“让他们能够问心无愧地从黑人转向援助阿巴拉契亚”及其居民——与非裔美国人和南方”贫穷白人”不同,这些人具备摆脱贫困和愚昧状态的文化和种族素质。
“山地白人”所谓的种族和宗教纯洁性是此类慈善事业的主要卖点,伯里亚学院院长弗罗斯特赞扬该地区”未受奴隶制污染”,居住的不是”天主教徒、外国人或异教徒”,而是”美国人中的美国人”。然而,尽管人们努力将”山地白人”重塑为一个合法的社会和文化类别,明确区别于”贫穷白人”和”白人垃圾”,但在公众心目中,它越来越与这些被污名化的标签和文化建构画上等号。例如,在那篇激怒波尔赫默斯和怀尔兹的《世界传教评论》演讲中,S·M·戴维斯夫人认为南方不识字的白人有”三个阶层”——“‘沙洲人’(来自沿海沙洲的人)、‘穷白人’和’山地白人’,后者常被称为’苏格兰-爱尔兰异教徒’,其中四百万人生活在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弗吉尼亚、肯塔基等地。”她写道,这些人”完全不识字,他们在智力和道德上的状况难以充分描述。“即使在1901年的小册子《山地白人的分类》中,罗伯特·坎贝尔牧师也承认”这个名称或其关联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当慈善界成员开始感受到这一术语日益增长的负面含义时,他们便逐渐放弃使用它。
到1914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长老会传教士塞缪尔·威尔逊牧师拒绝使用”山地白人”,转而采用更可接受的标签”山民”(mountaineer),他强烈主张前一术语”暗示着特殊性,并由此推断出低劣性……听起来太像’贫穷白人垃圾’了,这是南方最具侮辱性的称呼。“他宣称”没有山地黑人、棕色人或黄种人”,并质疑”如果听到七叶树州的居民被称为’俄亥俄白人’会是什么感觉!“威尔逊的声明不仅忽视了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大量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以及到这个时期的南欧和东欧移民,而且还将”白人身份”定义为如此规范和核心于当代文明美国人的概念,以至于使用”白人”这个标签实际上是在否认山民的合法”白人身份”,并强调他们与其他文化边缘化群体的相似性。然而与此同时,威尔逊使用这种”种族化”语言来强调解决”白人问题”的紧迫性——“如何……将这些落后和被淹没的血亲同胞,我们自己的骨肉至亲,带入更完整地享受二十世纪文明和基督教?”他同时拒绝和使用种族化标签,完美地说明了对这些人作为”白人他者”的矛盾观念——一个既在”规范”美国社会之内又在其之外的群体。
尽管南部阿巴拉契亚人民文化建构中的根本矛盾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山地白人”这一标签在1910年代逐渐失宠,并迅速被可能更具英雄色彩和浪漫意味的术语所取代,特别是”高地人”(highlanders)和”山民”(mountaineers)。虽然”高地人”一词的苏格兰起源似乎与他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生物遗传的普遍观念相矛盾,但这对山民作为”浪漫民族”、“稳固地处于英雄往昔”的新兴形象影响甚微。最终,山区民众的捍卫者们努力否定将所有山民描绘成原始野蛮人的形象,转而推广一种正面愿景:高贵的、文化和基因”纯净”的、能够实现社会提升的人民。但他们对当前状况的文化和地理解释,而非经济和政治解释,只是翻新了关于同质化落后社会的神话观念。也许那些试图拯救山区人民的人将”山地白人”被”山民”和”高地人”取代视为一大胜利。确实,虽然”高地人”作为标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亡,但”山民”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仍是描述南部丘陵地区人民的主要术语。但就在”山民”取代”山地白人”的同时,一个新术语正在出现,它注定会被普遍认知,将南方不同地区融合为单一文化空间,并以一种报复性的方式强化”山地白人”一词中仅有暗示的负面含义。
到二十世纪初,过去两百年间乡村土包子、“穷白人”和山民形象与观念的融合,为一个新的综合文化符号——“hillbilly(乡巴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尽管十九世纪末地方色彩文学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中标志性山民的家园名义上是”阿巴拉契亚”(这个地名本身与其说是一个可明确辨识的地点,不如说是由东北部城市小说家、图书出版商、杂志编辑和作家及其中产阶级读者群新建构的文化空间),但”hillbilly”一词最早在印刷品中出现时,指的是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交界地区以及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西南丘陵地带的人们。从最初作为一个地区性标签开始,这个词汇和形象通过笑话书作者、专业语言学家、通俗作家以及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作品逐渐在全国传播开来。这个词在新世纪之初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其兴起伴随着一战前无声电影中山区私酒贩子、世仇者及其妻女形象迅速传播的同步现象,但并未立即对其产生影响。然而到了1910年代中期,随着人们对这一类型的兴趣减退,这些角色原本专指对”正统”维多利亚晚期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的暴力无法之徒的含义,开始转变为同时包含另一种形象——依然落后但如今滑稽可笑的乡野村民,他们成为现代美国人的荒唐陪衬,而这一切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外在形象。
与过去一样,这一形象最初的吸引力以及如此戏剧性转变之所以可能,在于这个词汇和形象持续的模糊性,因而具有可塑性。这些角色之所以受到二十世纪初观众的欢迎,部分原因是它们满足了观众的基本需求——用1907年《巴尔的摩太阳报》一篇关于电影吸引力的文章的话说,就是”任何能让人开怀大笑或让心跳加速、屏息凝神的东西”。但作为奇特混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美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带有刻板印象中有色人种的暴力、性和原始特征,同时占据着英雄的过去和堕落的现在,山民/乡巴佬形象既可以用来维护现代文明的优越性,又能提供令人兴奋的谋杀和混乱场景,而不会威胁到”正统”的社会和种族秩序。因此,对于许多正在努力适应快速工业增长和新技术浪潮、日益膨胀且种族和民族日趋多元化的城市、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分化和紧张关系,以及伴随新消费观念兴起而来的对”传统”社会道德和性别角色挑战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形象充当了一个出口。
对于一个几乎被普遍使用并渗透到美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词汇来说,“hillbilly”一词的词源和文化起源却异常模糊。最可信的理论是,苏格兰高地人无论是在其祖国还是在新大陆,将两个较古老的苏格兰表达”hill-folk(山民)“和”billie(伙伴或同伴的同义词)“结合在一起。虽然不清楚这种合并何时发生,但这个词很可能在十九世纪末已成为美国南方乡村方言的一部分。威廉·纳撒尼尔·哈本在其小说《阿布纳·丹尼尔》(1902年)中使用”passle o’ hill-billies(一群乡巴佬)“这一表达时没有加引号,只是顺带一提,这表明——正如民俗学家阿奇·格林所论证的——他很可能是在佐治亚州北部惠特菲尔德县长大时听到这个词的。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牧师R·S·洛文古德在1907年发表的一篇布道中将”hill billy”列入一系列必须避免使用的词汇(包括”sheeny(犹太佬)“、”dago(意大利佬)“和”nigger(黑鬼)“),因为它们”煽动种族仇恨”,这表明至少在非裔美国人中,这个词的贬义和种族含义在此时已广为人知。1900年以前”hillbilly”在方言中更明确的使用暗示了这个词的其他解释。在一张手写标注为”‘乡巴佬营地’,1899年8月”的照片中,一大群男女聚集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片林地中,“Camp Hillbilly”周围使用的引号、参与者明显的中产阶级装束——西装、高领连衣裙、草帽和女帽——以及聚会轻松的集体合影姿态表明,这里的”hillbilly”意在幽默,并指出这群中产阶级城里人在乡野度假环境中的不协调。因此,这张照片通过反衬强调了这个词的下层阶级、贫困和非城市含义。但作者也可能想表明,在城市服装之下,这些露营者与”乡巴佬”有很多共同之处。
尽管这些例子似乎表明”hillbilly”一词在南部山区甚至中西部部分地区已被普遍熟知,但1900年《纽约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却强调了这一人物形象对该地区以外美国人的新奇感和吸引力——这篇文章标志着该词首次以印刷形式出现。政治记者朱利安·霍桑强调,当他的当地”对话者”“随口提到Hill-Billies时,我不得不请他解释”,随后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八次。霍桑随后的定义完美地捕捉了这个词固有的模糊性:“Hill-Billie是阿拉巴马州一个自由不羁的白人公民,住在山里,没什么财产可言,穿着随便,说话随意,有威士忌就喝,兴之所至就开枪。”这个定义明显带有贬义,强调了其描述对象的贫困和不当社会行为,但它也暗示了更令人钦佩的特质:自由、自我认同和独立——文章聚焦于山区居民的政治重要性和自主性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乐于接受某位候选人的免费酒水和竞选贿赂,却转身投票给他的对手。
著名政治漫画家霍默·达文波特的配图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疏离感,这可能是第一幅标注为”hill-billies”的人物图像(图2.1)。这些山野村民的特征是四肢修长、胡须或八字胡杂乱、毡帽过大、穿着全长风衣,他们抬头看着铁路大亨科利斯·亨廷顿的巨大身影,眼神中带着期待却又不置可否(双手叉腰、交叉在胸前或背在身后,而非伸出),而亨廷顿正准备收买他们的选票。无论霍桑或达文波特如此突出地构建”hill-billie”的文字和视觉定义的确切意图是什么,多种可能的解读表明这个词及其形象是多么模糊,因此也具有多大的可塑性。这篇文章还表明,这个词开始被呈现给远在南部山区之外的读者和观众,这些受众对这个标签的全部含义的理解可能远不如”Hillbilly营地”的西弗吉尼亚人那么深刻。

图2.1
“阿拉巴马州一个自由不羁的白人公民”:被标注为”Hill-Billie”形象的诞生。霍默·达文波特,《科利斯叔叔与’Hill-Billies’:描绘一个好人在遥远南方的烦恼》,《纽约日报》,1900年4月23日,第2版。
这个词下一次出现在印刷品中时,其范围扩展到了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山区,这种关联强化了该词的讽刺和贬义内涵。幽默作家查尔斯·S·希布勒1902年的小册子《在阿肯色》对hillbilly进行了详尽的讨论,通过一位波士顿资本家、一位费城律师和一位堪萨斯城房地产经纪人的冒险故事展开,他们前往阿肯色州西部的沃希托山脉,希望通过低价购买土地再转卖给木材和矿业利益集团来大赚一笔。故事的大部分围绕着”阿肯色”火车缓慢这一老生常谈的主题展开,但在这里,这一形象被明确地与山区居民的思维和行动迟缓联系起来。当三人问列车员为什么火车晚点四小时才到达堪萨斯城时,他回答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伙计们,这趟车其实是昨天的车……我们有很长一段路穿过阿肯色,那儿的Hill Billies多少有点落后于时代;我们开得慢是为了给他们时间起床、处理事务。”后来在旅途中,三人在树林里迷了路,被一些”hill billies”抓住,他们怀疑这三人是税务稽查员。他们的当地向导解释了这些奇怪山民的起源和特征:
虽然尚未广为人知,但Hill Billy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Hill Billy在许多方面都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要公正地描述他需要狄更斯那样流畅的笔触……Hill Billy始终忠于其排外原则,从不到自己心爱的山区之外寻找新娘。因此,这个物种保持了纯粹和未受玷污……Hill Billy以贫穷为傲,满足于自己的环境,在与世隔绝中感到幸福。
这些关于安于贫困以及地理和社会停滞的主题,几乎在此后所有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描绘中都得到了延续。
《阿肯色往事》似乎并未广泛流传,但托马斯·杰克逊次年出版的《慢车穿越阿肯色》却截然不同。杰克逊是一位走南闯北的铁路制动员,他的书恰好赶上1904年圣路易斯路易斯安那购地百年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带来的大量火车旅客,并利用铁路关系通过车站书报亭和小贩积极推销。到1950年,这本书惊人地售出了七百万册。令人意外的是,《慢车穿越阿肯色》与阿肯色州或南方山民关系不大,主要是杂乱地复述标准笑话、双关语和黑人滑稽剧的俏皮话。然而,书名本身以及杰克逊将开篇设定在该州的做法,都强化了落后与阿肯色之间的联系。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被广泛复制的封面插图,描绘了一个高瘦、蓄须的人物,手持步枪,身边有猎犬,头戴超大帽子,坐在他那几乎未开垦的土地上的树桩上,背景是他的原木小屋。封面上提到的”南方黑人语录”和”最佳黑人滑稽剧笑话”表明,杰克逊将这个新的标志性山民形象与同样刻板的愚笨非裔美国乡下人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后者被描绘成受动物本能支配的人(图2.2)。杰克逊的作品催生了大量模仿者,包括安德鲁·盖伊·奇尔顿的《骑猪穿越阿肯色》(1908年)和乔治·比森的《我从阿肯色飘来》(1908年)。这也引发了阿肯色州内部的强烈反对,最典型的是伯尼斯·巴布科克夫人的檄文《那个诋毁阿肯色的人及其下场》(1909年)。但伤害已经造成,该州居民都是迟钝(且愚笨)乡巴佬的普遍观念一直延续到二战后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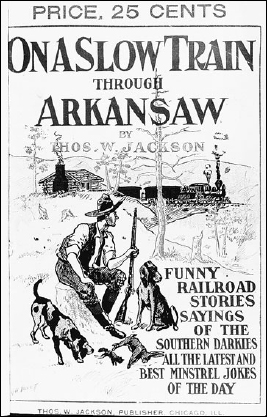
图2.2
最早大规模生产的欧扎克山区乡巴佬(hillbilly)形象。封面插图,画家不详,托马斯·杰克逊,《慢车穿越阿肯色》(芝加哥:托马斯·W·杰克逊出版社,1903年)。
在杰克逊及其前辈奠定的基础上,众多作品中,马里昂·休斯的《阿肯色三年》(1904年)对乡巴佬形象的塑造贡献最大。休斯是个多面手,曾在五个州当过农民、旅店老板和律师,1890年代末在阿肯色州的霍雷肖和哈顿峡口两个山区小镇生活了三年。他的书奇特地结合了夸张故事、民族和种族笑话,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细致评估。它还为新兴的乡巴佬形象增添了重要的视觉和文学元素,并进一步融合了山民和贫穷白人的形象建构。休斯对猪的详细讨论,包括饲养和屠宰,也加强了猪与贫穷白人之间的联系,这是乡巴佬形象的核心视觉隐喻。他对猪作为食物来源重要性的关注也强调了居民原始的生活条件,而他关于该州最初定居者的故事则暗示了与动物之间更为黑暗的关系。他将创始人描述为一个爱尔兰人和一个白人女子,他们的孩子是靠黑人奴隶和山羊的奶喂养长大的,他写道:“这就是为什么阿肯色本地人拥有许多人类或亚当后裔所不具备的特性。”休斯不仅将阿肯色人与其他人类区分开来,还暗示了种族混血和人兽交合。
休斯进一步强调他们与泥土的亲近和动物性,始终将山民与极高的生育率、早婚以及几乎完全缺乏社交礼仪联系在一起。例如,他描述一位典型的新娘回应牧师询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新郎时的情景:“她停下手中的拣羊毛活计,想了一会儿;把嘴里的鼻烟棒(snuff stick)拿出来;转过身,朝火里吐了一口烟草汁,说:‘我想是吧。’”对新娘的描写代表了乡巴佬形象中的另一个标准套路——男性化、相貌平平、粗俗、衣着寒酸的女性。休斯描述一位老妇人”袖子卷得老高,能看到她腋下的毛发。她的裙子刚到膝盖下方一点,是件宽松连衣裙……用不同牌子的面粉袋做成”,以至于她裙子前后分别印着”早起者”和”皮尔斯伯里精选”的广告。那幅粗糙的配图描绘了这位所谓典型的阿肯色妇女在洗衣服,农场动物在她脚边觅食(图2.3),加上他不断提及女性(和男性)饮酒和使用烟草(无论是抽烟、嚼烟还是用鼻烟棒),毫不掩饰地展示了他们的粗俗、肮脏和社交上的粗鄙。

图2.3
“典型的”邋遢贫穷的阿肯色妇女。马里昂·休斯,《阿肯色三年》(芝加哥:M.A.多诺休公司,1905年),第24页。
上述所有视觉套路在休斯描绘”典型阿肯色家庭”室内场景的漫画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图2.4)。画面中孩子多得过分,各种动物混杂其间,一位未老先衰的母亲,还有一个懒散的父亲在拉小提琴。配文描述了这个男人如何无视家人的需求,而他的妻子则挣扎着生火,试图温暖”赤脚、衣不蔽体、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文字围绕着农村贫困和这些人社会孤立的熟悉主题展开。然而,由于阿肯色人长期被滑稽化呈现的传统,或者因为与阿巴拉契亚地区不同,这个地区缺乏传教士和改革者持续强调当地居民”困境”的努力,这些状况在这里被呈现为只值得嘲笑讽刺,而非同情或道德愤慨。

图2.4
“典型阿肯色家庭的内部场景” 马里昂·休斯,《阿肯色三年》(芝加哥:M. A. Donohue & Company,1905年),第35页。
这种对贫困、反社会行为和原始生活方式的嘲笑,以及他与当地人和他帮助创造的乡巴佬神话之间的暧昧关系,在休斯用来结束全书的打油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住过十六个州但在我见过的所有地方没有哪里比得上住在老阿肯色
他们都穿自制的衣服男人女人都一样而脏脸的孩子们都只穿着衬衫
男人喝私酿威士忌女人嚼烟草、蘸鼻烟大姑娘们光着脚嘴唇上沾着烟草……
所有人都心胸开阔尊重道德法则这就是我喜欢住在老阿肯色的原因。
由于休斯在阿肯色农村生活了多年,加上他的工人阶级和漂泊的生活经历,他认为自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对他们粗犷的生活方式、坚韧和直率怀有一种勉强的钦佩。与此同时,他主要将他们呈现为幽默和讽刺的漫画形象,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他者性”——他们的服装、外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中产阶级城市规范的差异程度。尽管阿肯色人严厉谴责休斯的书是对他们饱受诋毁的州及其人民和性格的又一次恶意攻击(一位作家强烈驳斥他的”诽谤”,建议把休斯关进动物园,作为人与猿之间的缺失环节),《阿肯色三年》在州内外都被广泛阅读。它在强化外界对阿肯色落后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确立了乡巴佬(hillbilly)作为粗野动物性延伸的形象化意象。
在阅读休斯作品并传播和使其合法化的人中,有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阿肯色大学教授约瑟夫·W·卡尔在1904年美国方言学会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受惠于休斯的书,该文列举了阿肯色奥扎克地区特有的词汇。卡尔的词汇表包含了对”hill-billy”的首次学术引用,定义为”粗俗的乡下人,尤指来自山区的”,如引文所示:“你们这些只有一根背带的乡巴佬(hill billies),规矩点。”两年后,卡尔提供了该词的第二个定义,现在从地理和文化上区分了贫穷白人:“沼泽地人和乡巴佬(hill-billies)相处得不太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hillbilly”一词的引用被记录在密苏里州西南部、阿拉巴马州东部和佐治亚州西部,到1917年,又扩展到肯塔基州、堪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是什么导致了”hillbilly”一词在1900年后不久出现?虽然没有单一的确定答案,但可以推测,许多导致山民形象确立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后果,也催生了稍后出现的乡巴佬化身。随着阿巴拉契亚山坡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山区农场和家庭经济萎缩,成千上万原本自给自足的山民被迫成为佃农或在蓬勃发展的煤矿,尤其是棉纺厂工作,关于该地区随之而来的贫困化的报道再次将山民带入全国聚光灯下。二十世纪初,批评者抨击遍布皮德蒙特地区的新兴公司城镇和纺织厂的低工资、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尤其是普遍雇用童工的做法,有些孩子年仅九岁。作为回应,工业家们发起了一场公关运动,旨在展示山区人民落后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城镇生活的所谓优势,并将自己塑造为慈善的代理人。在玛丽·默弗里、小约翰·福克斯等人的地方色彩小说以及大量关于”世仇”的新闻报道所传播的、已经根深蒂固的绝望孤立和非理性暴力的山民形象基础上,这些纺织业的辩护者为山民概念增添了新的层面,将他们呈现为一个疾病缠身、目不识丁、营养不良、性行为放荡和堕落的群体。“山民”因此既成为工业剥削的有用陪衬,也成为不卫生和不道德的白人贫困的有力象征。尽管反童工倡导者和棉花工业辩护者在他们的著作或演讲中似乎都没有使用”hillbilly”这个词本身,但他们的辩论构成了这个词和形象出现的意识形态背景。
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也有助于解释”hillbilly”(乡巴佬)一词出现的时机。十九世纪末民主党对民粹党的动员,以及系统性种族隔离的实施,重新建立了一种带有种族色彩的阶级紧张氛围,而民粹主义者曾努力克服这种氛围。例如,1911年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詹姆斯·瓦达曼的追随者,采用了语义和时间上相近的标签”rednecks”(红脖子,首次出现在1893年的印刷品中)来称呼自己,正是为了强调他们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承诺。也许”hillbilly”一词及其相关视觉漫画形象稍晚出现,也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以及经济和社会精英们认为有必要诋毁那些可能威胁企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南方白人劳工阶层。或者,这个词在印刷品中缓慢出现,可能更多地归因于进步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对于那些渴望将科学推理应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关社会问题的自觉城市改革者来说,乡巴佬代表了他们努力根除的一切——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社会落后和野蛮性。同样,对于新来的城市居民——无论是迁移来的本土农民还是来自南欧和东欧村庄的移民——乡巴佬代表了他们试图逃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这些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单独解释”hillbilly”在二十世纪初突然出现在印刷品中的原因,但这些力量和运动共同促成了一种鼓励这种刻板印象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氛围。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hillbilly”在美国文化中的流行程度。在二十世纪初,这个词还远未普及,乡巴佬的概念虽然变得更加具体,但仍在不断变化中。即使在西南部山区,1900年前后这个词也并不常见。值得注意的是,“hillbilly”一词从未出现在休斯的书中,在《慢车穿越阿肯色》中也只被提及一次。杰出的欧扎克民俗学家万斯·兰道夫也发现,“hillbilly”在1915年之前并未被广泛使用。甚至这个词缺乏标准化的书写拼法,也反映了它仍在演变的性质。直到1930年代,“hill-billy(s)”、“hill billy(s)”和”hillbillie(s)“都出现在印刷品中,有时同一句话或段落中会出现不同版本的拼写。如果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山区居民的著作视为全国态度的代表,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更多地将山民视为潜在威胁,而非滑稽的落伍者。
这个词使用的缓慢增长以及山民形象含义的演变,可以通过相对较新的无声电影媒介得到最好的追溯。电影触及了比笑话书或地方色彩小说更大、更多样化的观众群体(到1922年每周约有4000万人),并且严重依赖于善与恶、文明与野蛮之间斗争的简单故事,电影在整个二十世纪深刻影响了乡巴佬形象的描绘和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一部电影在其标题、宣传文案或内部字幕卡中使用了这个词,那就是1915年恰如其名的《比利——山里人》。然而,尽管”hillbilly”一词在早期电影中几乎完全缺席,许多电影却以山区为背景或讲述山民的故事。杰里·威廉姆森是研究南方山区电影的主要学者,他统计了1904年至1920年间制作的400多部以山区为背景、展现山区男女”多彩”生活的电影,以及1920年至1929年间制作的另外76部此类电影。其中相当数量的电影由当时的主要电影公司制作,包括百代、爱迪生和维太格拉夫,由D·W·格里菲斯等重要导演执导,并由玛丽·璧克馥等主要电影明星主演。事实上,百代公司1904年明确以山区居民为主题制作的第一部短片《私酒贩子》(The Moonshiner)取得了巨大成功,四年后该公司仍在宣传它是最赚钱的影片——“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最受欢迎的电影”。《私酒贩子》的成功导致山民主题电影数量稳步增加,以至于电影制片厂在1914年发行了70部此类电影,平均每周超过一部新片。
这些影片在一战前都是一到两本的短片,在小型影院放映给以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为主的观众。影片以高度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和几乎不间断的动作场面为特色,包括骑马追逐、角色从悬崖坠落或跳下,以及各种形式的打斗。标准的情节涉及家族世仇、私酒贩子与税务官的对抗,以及城里人与山民之间的三角恋情,确保几乎每部影片都有一起或多起杀人事件。有些影片的死亡人数甚至更高。在《最后的族人》(1914)中,杀戮如此肆意,以至于影片结束时,曾经庞大的敌对家族只剩下两个对手站着。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实和虚构暴力的电影画面已经司空见惯,但在1929年之前发行的近500部山地电影中,暴力的数量仍然令人震惊——超过200起谋杀、500次使用枪支、斧头或徒手格斗的袭击,以及100次对女性的攻击。
这些影片惊人的暴力和动作场面几乎总是围绕着性欲和征服的故事展开。这些情节反映并经常取材于查尔斯·内维尔·巴克、默弗里和小福克斯等地方色彩小说家的故事,通常采用三角恋的形式:一个原始但迷人的山地女孩、一个来自山区社会之外与工业利益集团合作”现代化”该地区的男人(通常是山谷农民或专业人士,如税务官、工程师或测量员),以及一个同样觊觎她的潜在暴力山民。作为明确的情节剧,这些故事几乎总是以外来者击败他的山民情敌并将他的女性战利品带回城市或低地而告终,证明了现代、城市、资本主义美国相对于原始偏远社会的优越性。这些情节还强烈暗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现代男性,尽管接受了多年的正规教育并在官僚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仍然可以在边疆取得胜利。然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一旦到了城市,山地女性发现她的城市伴侣软弱、懦弱或不可信赖,并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在于她心爱的山区中的本地追求者。然而,尽管这些影片有不同的结局,其潜在主题始终如一:男性主导的正当性,强壮、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战胜软弱或自私的男人。
令人震惊的是,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女性温文尔雅和得体的观念,这些影片中的暴力不仅由山区私酒贩子和世仇者实施,还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实施。许多山民无声电影中都有女性开枪杀死男性的场景,包括执法人员和敌对家族的长辈。在一个极端案例中,格里菲斯的《山民的荣誉》(1909),一位山区母亲竟然亲手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儿子,而不愿看到他被不光彩地绞死。除了开枪和用枪指着俘虏外,这些影片中的许多女性还成功地伪装成男性参与全男性活动,如贩运私酒和伐木,或为家人被枪杀复仇。同样,一些影片描绘了”野性山地女性”,她们拒绝被社会等级顶端的人(无论是父亲、牧师、地主还是其他精英)控制。然而,女性的这种越轨行为很少被允许持续太久,山地泼辣女最终不可避免地嫁给了男主角。
显然,电影导演和制片人将这种对持枪的男性化女性和野性山地女孩的描绘,作为对跨越社会和性别界限危险的警告。当时,更加社会解放的”新女性”、女权运动者,以及越来越多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女性,正在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和男性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的结尾场景——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再次牢牢掌控一切——象征着”正当”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城市现代男性战胜落后山民的典型胜利。但正如许多观众研究所表明的,电影制作者的预期含义并不是观众获得的唯一信息。小型影院的观众可能带走了一套相反的信息:跨越性别和阶级界限与规范的刺激可能性;与拥挤和受管制的工业化美国相比,荒野生活的兴奋和魅力;以及挑战甚至击败(无论多么短暂)社会秩序和控制力量的秘密满足感。正是山民形象可能含义的这种模糊性,使这些无声电影如此受欢迎,并使山民/乡巴佬角色在整个世纪和整个文化领域中得以延续。
这些暴力和刺激性画面之所以能被接受,关键在于这些角色的独特地位——他们既处于当代白人社会的边缘,又在其范围之内,而这个白人社会似乎正面临威胁。一方面,这些电影的背景设定在遥远的南方山区(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时间上都很遥远),这缓冲了它们潜在的社会威胁。进步时代那些自封的中产阶级城市改革者们,深切担忧城市中不断膨胀的”不受欢迎的”南欧和东欧移民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和贫困问题的增加。他们对一分钱游乐厅和五分钱影院在工人阶级和移民聚居的城市社区迅速蔓延感到震惊,认为这些场所通过鼓励放松的性道德标准和肆意的暴力行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正如1910年《好管家》杂志上一篇文章所言,五分钱影院及其放映的电影是”罪犯的启蒙学校……只需五分钱就能教授淫秽、犯罪、谋杀和堕落”。为回应这些批评,电影业于1908年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全国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定,如果谋杀、枪战和露骨的性场景发生在现代城市背景中,则不可接受。但如果这些场景发生在神秘的异国他乡、半个世纪前的”狂野西部”,或者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山区这样与世隔绝的乡村地区,则较少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如果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华人和美洲原住民,甚至是新来的南欧和东欧移民实施类似的暴力行为,对种族秩序的威胁就太大了,无法通过审查。山民电影之所以能被接受,在于施暴者的种族身份;尽管他们被描绘成受动物本能支配的近乎野蛮人,但山民显然是”白人”(而且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因此,正如十九世纪晚期的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一样,当代白人以先驱祖先和有色人种的方式生活和行事,正是这一形象吸引力的核心所在。
百代公司1920年电影《禁忌山谷》的宣传文案明确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地位:“美国原始白人的最后据点;人们自己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最后边疆;这就是肯塔基山区腹地的禁忌山谷。”“原始”和”白人”这两个词的组合很有启发性,因为它指向了这些电影中山民角色的”白人他者”本质。在电影宣传文案中明确使用”白人”一词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关于这些电影的广告和评论都没有具体提及山民的种族,除非明确说明,否则默认角色是白人。然而,对他们数百年社会习俗、世代血仇和先驱生活方式的描述,都间接表明了山区居民在历史上享有的种族特权地位,因为这些描述暗示了他们的美国殖民地(因此是”白人”北欧)血统。山民角色与非白人角色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这些电影中被允许像现代白人一样行事:父亲和长辈对子女和妻子行使权威;少数黑人和印第安人角色明显处于从属地位;最重要的是,山区女性可以与外来的白人男性恋爱并结婚。
然而与此同时,山民角色的凶残、无知和原始性,与众多其他默片中对非白人角色的刻画如出一辙。种族观念和适当的种族等级制度是许多默片制片人和导演叙事和意识形态基础的核心,其中最著名的是肯塔基州人D·W·格里菲斯。格里菲斯一贯使用非裔、华裔、拉丁裔和印第安裔角色来展示所有有色人种潜在的暴力倾向、跨种族性欲望的危险,以及通过非白人服从的叙事来彰显白人的优越性;同样,他也将被编码为”非白人”的山民纳入影片,以突显”规范”白人社会的优越性。他为百欧格拉夫公司拍摄的六部明确以山区为背景的电影,全都围绕着山民角色在血仇、袭击、谋杀或参与内战中的暴力行为展开。跨文化关系以及白人男主角对非白人或山区女性的欲望是另一个显著的相似主题。虽然格里菲斯执导的电影有时会描绘山区女性与将她们带回城市或低地的非山区男性之间理论上永久的结合,但同样经常表现山区女性无法或不愿融入”白人”社会,并含蓄或明确地论证她们最好还是”和自己人在一起”。最后,格里菲斯(及其同时代人)拍摄的大量以白人男性对山区女性的性趣味为特色的电影,表明了与其他格里菲斯默片中主导的异族通婚主题同样的迷恋。
角色的服装和宣传文案中的标签也暗示了他们处于白人身份的边缘地带。大多数山区角色的外表与同时代其他电影中的”白人”角色几乎没有区别。没有人物留着过长的胡须、戴着破旧的超大帽子、穿着老奶奶式的连衣裙、光着脚,或者带有后来确立的卡通式乡巴佬的任何其他标志。相反,大多数角色穿着普通的世纪之交服装,略带乡村风格。男主角,即使是扮演私酒贩子或世仇参与者的,也常常穿着西装外套、靴子,甚至打着领带,女性角色通常穿着长款裙撑连衣裙。电影公司没有用服装来强调这些人在时间和文化上的独特性,而是在宣传文案中使用”拓荒者”、“边疆”和”封建时代”等描述词,并大量使用长管温彻斯特步枪和博伊刀(bowie knives)。
然而,邋遢、衣衫褴褛的原型乡巴佬确实开始出现在1910年代的无声电影中,通常是配角。例如,格里菲斯1911年的《税务官和他的女孩》中的男主角穿着二十世纪初的当代服装,但在与税务官枪战中出现的山民配角则被呈现为留着胡须、挥舞步枪、弯腰驼背的形象,这种姿态后来成为卡通乡巴佬的典型特征。正如文学插图中的情况一样,电影中滑稽的乡巴佬漫画形象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而是逐渐演变的,电影制作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里菲斯和其他人的山区电影主要描绘严肃致命的山区角色,成熟的喜剧乡巴佬形象直到一战结束后很久才出现。然而,正如这些配角的出现所表明的,对这一形象更幽默的解读在1910年代开始出现。早在1911年,电影公司就开始发行少量戏仿山民题材夸张剧情和表演的电影。《费迪的家族世仇》(1912)和《手提箱里的东西》(1913)等影片讲述天真的城里人或旅行者滑稽地误入家族世仇和私酒团伙的故事,这一情节在此后多年被反复使用。其他电影则是明确的滑稽模仿,角色名字荒谬可笑,如世仇家族希金斯家和贾德森家,或税务官斯尼茨,并由胖子阿巴克尔、巴斯特·基顿和哈罗德·劳埃德等无声喜剧明星主演。到这十年末,许多喜剧开始利用观众已经形成的成见(主要来自早期电影)来表现山民的落后。在《欺骗小姐》(1917)中,一位优雅的城市女性故意利用她势利家人的恐惧——担心她在肯塔基山区叔叔家的长期逗留会把她变成原始野蛮人——从访问归来时装扮成一个极其粗俗的乡巴佬。同样,《她的原始人》(1917)的幽默围绕一位女艺术家展开,她来到山区为当地人画一些”原始素描”,却画了一个大学毕业生,误以为他就是片名中的角色。
尽管数量上远远少于大量的世仇和私酒”枪战片”,这些喜剧表明,将山民及其文化视为对现代文明的真正威胁这一单一观念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行但独特的解读——将山民视为幽默的乡巴佬形象,这一观念借鉴了早期关于南方山区,特别是奥扎克地区的滑稽作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视觉符号几乎没有改变。曾经表示明显残暴的相同故事情节和形象,现在被用来暗示滑稽荒谬的角色和情境。曾经作为”白人他者”的山民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证明其男子气概并最终证明其优越性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风景背景,现在他们也在标准的”格格不入”情节中充当笨拙城市天真者的喜剧陪衬。
喜剧化描绘山区世仇者和私酒贩子的兴起,既是所有族裔和种族形象演变的自然发展,也反映了1910年代电影观众和电影产业的具体变化。在无数美国族裔和种族刻板印象中,可笑的傻瓜与嗜血的野蛮人之间的鸿沟往往能够轻易跨越,因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种族主义本质的一种更温和形式。因此,正如愚钝无忧的黑人滑稽剧角色吉姆·克劳转变为挥舞刀子的城市”黑鬼”,托马斯·纳斯特漫画中猿猴般的爱尔兰野蛮人变形为好斗但无害的小妖精,卡通化的乡巴佬也从野蛮的山区亡命徒形象中轻易浮现。转向戏仿也反映了山民情节剧中陈腐情节和刻板角色日益下降的受欢迎程度。导演莫里斯·图尔纳在1918年警告说:“如果电影要进步,我们必须把整批不可能的角色都扔下船……包括那些带着标准世仇的私酒贩子和其他所有人。”电影行业贸易期刊《电影世界》的”宣传角度”栏目建议影院经营者淡化山民电影中的世仇和私酒情节,转而强调明星和场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放映商写给《电影世界》的大量信件表明,观众现在正在拒绝标准的世仇电影。一位愤怒的伊利诺伊州放映商抱怨《肯塔基人》(派拉蒙/著名球员拉斯基公司,1921年):“我的观众说太糟糕了,所以我想他们是对的;相当多人中途离场。”认识到观众对这一题材兴趣的下降,制片厂稳步减少了每年制作的”山区电影”数量,从1914年的70部高峰降至次年的49部,到1920年仅剩18部(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持续)。
1914年后观众对山民电影兴趣的下降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电影产业转型。到1910年代末,像比沃格拉夫这样的先驱公司制作的一两卷短片正迅速被独立制片人的新型长片”电影剧”所超越,这些长片是为”高雅”电影宫殿中自认品味高雅的中产阶级客户设计的,而非老式五分钱影院的移民和工人阶级观众。这一趋势伴随着电影产业从1914年左右开始将运营中心从东海岸转移到好莱坞。随着荒野场景的拍摄地点从南方山区转移到西部牧场和加利福尼亚山麓,随着牛仔电影成为日益突出的电影类型,偷牛贼、警长及其追捕队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私酒贩子和税务稽查员。到1919年,即使是像《私酒世仇》这样有着可靠”山民”片名的电影,也会以一位名叫德克萨斯的女主角和一场骑马穿越西部草原的枪战为特色。
随着电影和美国文化从将山区人民视为纯粹危险野蛮人的观念,转向将山民同时视为威胁和落后小丑的新视角,“hillbilly”(乡巴佬)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加。1910年代中期见证了该词首次在严肃非虚构文学中的使用,是该词固化的重要分水岭。在《南方山民》(1914年)中,长老会牧师塞缪尔·泰恩代尔·威尔逊讽刺性地使用了”hill billy”一词,以反驳所有南方山民都是私酒贩子的说法。他写道:“在田纳西州立法机构中,’hill billy’立法者才是真正通过并执行禁酒法的人。”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开篇第一句就使用了这个词,但也揭示了其模糊的含义:“’The Hill Billy’或’美国山民’是对居住在南方各州山区的人们的称呼。这个名称是用作贬义词、意在赞美还是仅用于描述,我不得而知。”作者对山区人民的看法同样矛盾。一方面,他赞扬他们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纯正和普遍强烈的职业道德,承认他们山区生存的极端艰辛,以及流行刻板印象的过度之处。另一方面,他经常提到他们不健康的近亲繁殖和封闭、容易被冒犯,以及”古怪”。他总结说,为了帮助这类人,他”故意省略了许多滑稽性质的内容”。然而,这两个例子是例外而非常规。二十世纪初描述南方山区社会和文化的主要非虚构作品中,没有一部包含”hillbilly”一词,即使作为严重不准确的诽谤性称呼的例子也没有。目前仍不清楚该词在这些文本中的缺失是反映了作者认为它是不值得评论的贬义标签,还是它尚未普遍到需要被驳斥的程度。无论如何,“hillbilly”的省略再次表明,该词尚未成为它在接下来几十年中将要成为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标签。
20世纪10年代中期也标志着”hillbilly”一词首次出现在流行娱乐作品的标题中。如前所述,《比莉——山地乡巴佬》是美国参加一战前唯一一部在标题中使用”hillbilly”的电影,于1915年上映。然而,与这个词后来带有的滑稽含义不同,这里的”hillbilly”指的是一个阴郁压抑的奥扎克山区居民,他试图压制孩子们的精神,让他们与文明世界隔绝。按照常见的故事套路,这位山民的女儿被一位来访的城里人娶走,带她回家与他母亲同住,从而获得了”拯救”。尽管”hillbilly”这个新词很突出,但影片对山区人民的负面刻画以及城市外来者作为救世主的理念,与无数其他山民题材电影并无二致。同样在1915年,“hillbilly”一词首次出现在全国发行的印刷品标题中,即威廉·阿斯彭沃尔·布拉德利在《哈珀斯》杂志发表的文章《与山地乡巴佬交往》。与其滑稽的标题形成对比的是,布拉德利的文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缺乏幽默的轶事和场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而非偏离了典型的地方风情描写。布拉德利在文章正文中也没有使用”hillbilly”一词,而是依赖”拓荒者”、“山区人民”、“山民”等术语,以及明显致敬威廉·弗罗斯特用语的”当代祖先”。在这篇关于他穿越南部山区旅程的概述中,布拉德利强调了人们熟悉的主题:当地人的落后、他们像殖民地和边疆时代祖先那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他们违法犯罪和近乎随意施暴的倾向。布拉德利反复提及过去半个世纪”著名”的家族世仇,并报告说他”自己的道德敏感性”“过了一段时间就变得迟钝了”,因为他”与一位杀过人、坐过牢的福音传道者握手”,或者与”一位和蔼可亲的主人共进晚餐……据说此人至少犯下过三起谋杀案”。他报告说,这些遭遇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他的不适感很快”消退了,人们开始把任何耸人听闻的个人过去或家族血统都视为理所当然”。
在此前几十年关于该地区及其人民的众多描述中,都有这些相同的主题,但这部作品反映了山民身份认同中潜在比喻的缓慢但可辨别的转变。与早期的描述不同,布拉德利经常提到煤矿和伐木业对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入侵,煤矿城镇和铁路如何打破人民和土地的封闭性和原始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美景的破坏。最引人注目的是,布拉德利承认全国媒体扭曲了山区人民的形象,并延续了负面刻板印象。当他到达弗吉尼亚州的希尔斯维尔小镇时——三年前那里发生的法院枪击案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并促使《巴尔的摩太阳报》呼吁对当地人进行教育或消灭——布拉德利计划避免提及此事,确信当地居民不愿讨论。然而,令他惊讶的是,当地人愿意甚至渴望讨论案件的具体细节,而且小镇本身也很现代、很和平。他报告说,镇民们对”北方新闻记者为了制造现实中严重缺乏的必要地方色彩而放飞的想象”仍然感到愤慨。布拉德利因此承认了全国媒体对山区社会的故意歪曲以及该地区的工业转型,同时又延续了关于山区暴力、违法和落后的标准比喻。镇民们出人意料地愿意讨论此案,类似于哈特菲尔德家族愿意为报纸摄影师挥舞武器,这也可能揭示了他们对在全国媒体事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隐秘自豪感。尽管如此,在穿越该地区的旅途中,布拉德利只是隐约意识到当地居民如何利用山民刻板印象为自己服务,并接受了长期根深蒂固的关于与世隔绝、落后的山区人民的观点。
虽然布拉德利对”hillbilly”的使用并不表示对当地居民有新的幽默解读,但他确实以一种超越严肃人类学评论、进入滑稽领域的方式讨论了人们懒惰和无所事事的观念。例如,他描述了与一位田纳西人的相遇,此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黑眼睛从一片卷曲的黑胡子和破烂帽子下乱蓬蓬的精灵锁(elf-locks)中带着无礼和轻松的好脾气向我们笑着”,并高兴地宣布”‘你们来到了懒人之乡。’“当布拉德利第二天早上四点半醒来,发现旅馆所有客人都已起床吃过早餐时,他开始怀疑这种说法。但当他吃完早餐走出旅馆时,眼前的景象证实了他的怀疑:
……几乎整个男性人口都懒洋洋地躺在对面法院的台阶上,或坐在人行道旁的椅子上,而每道栅栏上都晃动着女性的帽子。在整个镇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似乎有什么事要做,然而每个人都在早上四点起床去做这件事。
布拉德利的文章标志着人们对山区居民认知的一个明显转折阶段,也是乡巴佬刻板印象形成的开端。他的叙述仍然依赖于早期的地方色彩报道和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强调山区生活的拓荒者和边疆特性、居民的暴力和无法无天,以及他们与现代世界的隔绝和无知。然而,他的叙述也承认了采掘业和交通网络正在改变这些人的方式,以及媒体为了强化人们对山区”他者性”的普遍成见而进行的刻意歪曲(尽管他未能认识到自己在创造这种山区神秘感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通过将滑稽的描写和轶事融入表面上写实的叙述中,布拉德利指向了一个主导性形象——将这些人描绘成邋遢、反进步的小丑——尽管”乡巴佬”(hillbilly)的这层含义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完全形成。在20世纪头二十年,“乡巴佬”一词并未被广泛使用,即使使用时,也只是作为”山民”(mountaineer)的同义词,只不过更强调这一形象的负面特征。
这个词在1910年代中期使用的最引人入胜的例子,也是最能说明”乡巴佬”一词尚未定型的例子,是1914年开始由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高中学生编写和出版的月刊文学杂志,简称《乡巴佬》(The Hillbilly)。人们可能会以为封面插图是一个戴着软帽、扛着步枪的卡通山民形象。然而,最初几年版本的扉页上却是一幅奥布里·比尔兹利风格的高度程式化的女性面容,飘逸的长发和异国情调的颈饰(图2.5)。文章和诗歌标题使用哥特式字体、纸张质量上乘,以及完全没有讨论杂志名称的含义或意义——所有这些都表明”乡巴佬”一词尚未发展出后来的刻板含义,而只是被用作一个几乎不带政治色彩的地区标识。这种不加思索地使用标题的方式产生了一些对现代读者来说似乎不协调的句子和情感,例如以下关于杂志潜在遗产的评论:“《乡巴佬》就像一个尚未成名的年轻人,他看到自己面前有一项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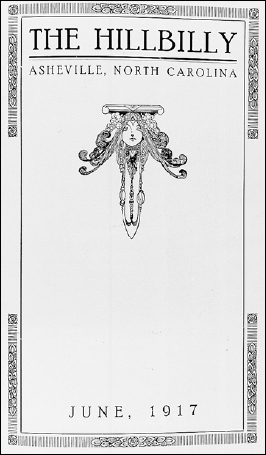
图2.5
“乡巴佬”与维多利亚晚期设计的奇异融合。《乡巴佬》(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1917年6月,第1页。图片由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帕克纪念公共图书馆北卡罗来纳收藏馆和阿什维尔高中提供。
十多年后,这份刊物才开始采用更标准化的山区意象。1927年,《乡巴佬》已从文学期刊变成更像班级年鉴,开始刊登木屋、瀑布和年轻人在山中背包旅行的地区图像。直到1933年,它才描绘了高度程式化的山区男女从事缝被子(quilting)和编篮子(basketweaving)等手工艺的形象(图2.6),直到1939年,封面才出现了经典的乡巴佬刻板形象——一个瘦长的林中人,留着过长的胡子,赤着脚,戴着软帽,扛着步枪,提着威士忌酒壶(见图4.1)。这些变化可能是新学生艺术家的作品,或是不同新闻学教师的心血来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杂志创刊之初,这个词的贬义含义与它在一份精致文学期刊中的使用之间几乎完全脱节——这份期刊是由这座蓝岭山脉脚下现代城市中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学生们创办的。

图2.6
《乡巴佬》的蜕变:20世纪30年代程式化的民俗形象。《乡巴佬》,阿什维尔高中年鉴,1933年,第95页。图片由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帕克纪念公共图书馆北卡罗来纳收藏馆和阿什维尔高中提供。
到20世纪20年代初,“乡巴佬”一词及其作为南部山区居民描述语的相关意象开始出现在各种美国文化形式中,从笑话集到电影,再到高中文学期刊。但除少数例外,它仍主要限于地区性使用。此外,它的含义仍在不断变化,不同的作家和艺术家用这个词来指代勤劳的拓荒美国人、堕落凶残的违法者、迟钝滑稽的乡下土包子,或者往往是三者的某种组合。最初,自认为是山区人民捍卫者的人,特别是南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刻意避免使用”乡巴佬”一词,认为它强化了关于无谓暴力和堕落的负面观念。相反,他们采用”高地人”(highlander)和”山民”(mountaineer)这些标签,认为这些词更能代表这些人的英雄气概和纯洁本性,以及他们高贵的殖民地传统和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近乎神话般的山民建构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强劲,并将以某种弱化的形式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文化中持续存在。
然而,随着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体继续宣传愚笨乡巴佬或野蛮世仇者的观念,加上公众越来越需要这样的角色——既能通过反面例证证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生活的好处,又能挑战它所施加的社会限制——乡巴佬形象在全国意识中缓慢但稳步地成长起来。
到20世纪20年代初,尽管杂志、小说和电影中充斥着关于”山民”和”山区白人”的评论,但公众对”hillbilly”(乡巴佬)一词及其形象的使用仍然相当罕见,其含义也仍在不断变化中。商业录制的乡村白人音乐(今天通常被称为”乡村音乐”)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将”hillbilly”一词及其形象牢牢地置于全国文化版图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乡村音乐的身份与”hillbilly”概念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商业起源到50年代成为主要文化力量期间,它几乎被普遍称为”hillbilly音乐”。除了使这个词语全国化之外,乡村音乐还用一种新的主要含义——朴实的幽默、无忧无虑的轻松和草根的真实性——取代了该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暴力和威胁的主要关联。
无论在实践中还是作为一个文化类别,“hillbilly音乐”都充满了模糊性。它被官方宣传为”白人”民间音乐,由主要来自南方农村和小镇的人们演奏和欣赏,这些人怀旧地回望更简单的农业生活,但实际上,它是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传统的融合,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和尖端技术的产物。它的社会意义也在乡村音乐”亚文化”内部——即演奏和聆听这种音乐的人——与代表外部商业利益的推广者、制作人和记者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后者中的许多人使用这个词来贬低他们认为低俗和公式化的音乐类型以及孕育它的文化。另一方面,音乐家和他们的听众持有更复杂的看法。虽然认识到这个词的贬义含义,但他们也谨慎地采用这个标签作为个人和文化自豪感的标志,反映出他们在农村过去和工业化现在之间的分裂身份认同。在大萧条时代,随着对”民间”的普遍颂扬以及关于”hillbilly热潮”席卷百老汇的新闻报道,这种立场与全国的时代精神产生了共鸣,尽管有时并不那么自在。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一个立即可辨认的贬义hillbilly刻板印象日益强大,这导致音乐家和日益利润丰厚的乡村音乐产业否定了这个标签,转而采用更具市场价值的”乡村音乐”一词及其歌唱牛仔形象。尽管如此,这个词在大众想象中与弦乐队音乐不可逆转地交织在一起,许多表演者和听众继续接受”hillbilly”标签和形象中固有的文化模糊性。
由白人表演者演奏的乡村音乐——后来几乎被普遍称为”hillbilly音乐”——其起源深植于美国的过去。这种乡村音乐常被视为几乎完全根植于盎格鲁-凯尔特音乐传统,但实际上,用著名乡村音乐历史学家比尔·马龙的话说,它是”民族、种族、宗教和商业元素的非凡融合,兼具旧世界和美国的起源”。虽然17和18世纪殖民者从不列颠群岛带来的民歌、舞曲和叙事歌谣构成了这一音乐遗产的核心,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音乐风格和乐器,以及从英国圣诗歌唱到会众音乐再到世纪之交五旬节复兴运动情感主义的宗教音乐传统,都对这一不断演变的文化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美国南部,这种丰富的文化混合深深浸染了大量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五弦班卓琴(able banjo)和吉他的引入、灵歌和福音歌唱传统,以及拉格泰姆(ragtime)、布鲁斯和爵士风格。
乡村音乐常被视为乡村淳朴和传统主义的象征,被认为是前工业时代美国的原始遗存。然而实际上,乡村音乐是”民间”与商业文化影响持续互动的产物,也是工业和技术不断向南方最偏远地区扩展的结果。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由专业的锡锅巷(Tin Pan Alley)词曲作者创作的曲调,经由巡回演出的杂耍剧团、黑人滑稽剧团或规模较小的”帐篷剧团”录制或表演,再加上马戏团、夏季文化集会(chautauquas)以及流动药品推销表演的”江湖郎中”马车所提供的娱乐节目,这一切都成为美国乡村不断演变的音乐遗产的一部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农村人口持续向小城镇和城市迁移,使成千上万的美国农村居民接触到城市文化形式和风格,并将其融入自己的音乐曲目中。工业变革对南方工人阶级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铁路的深入渗透,反映在许多乡村歌曲的标题和歌词中,包括《沃巴什炮弹列车》《等待火车》和《老97号列车失事》,以及对火车声音的音乐模仿。一战后的几首歌曲也评论了工业的影响,从汽车带来的解放潜力(《在迪克西蜜蜂线上》)到棉纺厂工作的艰辛(《织布车间蓝调》《纺纱车间蓝调》)。尽管这一多元的音乐传统在两个世纪以来在南方和美国其他农村地区发展起来,但直到十九世纪末留声机的广泛普及和唱片业的兴起,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广播的爆发式增长,它才获得全国性的知名度。到1922年底,美国有510家广播电台在播出(其中89家在南方),这十年间收音机销量急剧上升(增长近十五倍),据估计,到1929年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收音机(到1933年则达到三分之二)。这种超现代技术与所谓老式民间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摩擦,反映了这十年间围绕禁酒令、移民政策、公共道德以及地区与国家认同等问题的深刻社会冲突,这些都是美国从根植于地方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旧文化向以城市化、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为特征的新社会艰难转型的一部分。这些紧张关系正是围绕”乡巴佬音乐”(hillbilly music)在更广泛流行文化中的生产、接受和分类展开辩论的核心。
在商业”发现”南方农村民间音乐和确立”乡巴佬”(hillbilly)标签这两件事上,拉尔夫·西尔维斯特·皮尔都是核心人物。皮尔是奥凯唱片公司的星探,后来成为制作人,他被广泛认为是命名并推动”种族”唱片热潮的人——这些由黑人表演者演唱的蓝调歌曲和灵歌销量达数千张。这些唱片在二十年代低迷的唱片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加上纽约唱片公司日益意识到黑人听众的潜在规模以及能够维持”种族”音乐销量的南方黑人音乐家数量,促使皮尔于1923年在亚特兰大首次对民间音乐家进行实地录音。皮尔主要打算录制黑人音乐家,但他也录制了”小提琴手”约翰·卡森——一位著名的亚特兰大小提琴手,曾在当地广播电台WSB演出——但这只是因为他的录音日程出现了意外空档,而又找不到黑人音乐家来填补。皮尔形容卡森的歌声”糟糕透顶”,只发行了他无伴奏的小提琴曲目,放在一张没有编目、没有标签的唱片上,没有做广告,仅在亚特兰大市场销售。然而,当这张专辑出乎意料地在几个月内售罄时,他便把卡森带到纽约录音。尽管他明显厌恶他所认为的低俗音乐和音乐家(晚年被问及他录制的早期”乡巴佬”时,他回答说”我努力想忘记他们,你们却不断提起”),但他立即认识到了其商业潜力。他为奥凯唱片公司以及后来的维克多唱片公司在南方各州进行了多次实地录音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1927年在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的录音会,他在那里录制了乡村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组艺人——卡特家族和吉米·罗杰斯。两年前在纽约,他还录制了一支来自弗吉尼亚州盖拉克斯的弦乐队,他将其命名为”乡巴佬乐队”(the Hill Billies),这是第一支以此名称进行商业录音的乐队。
尽管皮尔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卡森、乡巴佬乐队及类似表演者的音乐具有市场潜力,但这种音乐对他们来说最初是如此新颖,以至于他们不确定该如何分类。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制作现在被视为”乡村音乐”的主要唱片公司(包括维克多、沃卡利恩、奥凯和哥伦比亚)都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包括”迪克西之歌”“南方老调”“老式歌唱”“熟悉的老曲调”,甚至”美洲原住民旋律”。即使到了1930年,在”乡巴佬”一词已被广播、媒体和许多表演者广泛使用之后,也只有奥凯唱片公司用这个标题来标注他们的选曲;德卡唱片和蓝鸟唱片(RCA维克多的低端子公司)——这十年间乡村音乐的主要发行商——直到1936年才采用”乡巴佬”这一标签。
无论选择何种标签,其目的都是通过将这种音乐与”种族音乐”标签下黑人表演者的作品区分开来,以彰显种族上的”白人性”。唱片公司目录以多种方式强化了音乐和表演者的白人属性,包括在分类标题中使用”迪克西”和”美洲原住民”等术语来替代”白人”,并收录明显带有种族色彩的歌曲,如《Run Nigger Run》以及传统黑人滑稽剧选段如《The Old Log Cabin in the Lane》。拉尔夫·皮尔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创造的标签具有种族化性质,后来他将Okeh唱片描述为”我发明了乡巴佬音乐和黑鬼音乐的地方”。乡村音乐作为白人音乐、几乎完全由白人表演者为白人听众演奏的普遍观念,在整个世纪中持续存在,并通过挪用黑人文化来展示白人性而得到强化。在《阿莫斯与安迪》成为美国最受欢迎节目的时代背景下,《大奥普里》乡村音乐节目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广播中经常以黑人方言喜剧表演收尾,WLS电台的《全国谷仓舞会》也在1937年播出了黑人滑稽剧主题节目。这些以及其他乡村音乐广播节目和巡回演出经常邀请涂黑脸的喜剧演员,他们的艺名包括”糖蜜与蜂蜜”、“油腻”梅德林和”慢吞吞”等,这一传统在少数情况下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初期。
然而,制作人和音乐家对这种音乐的种族建构也存在奇怪的矛盾,既否认又承认南方民间音乐的跨种族现实。正如皮尔1923年在亚特兰大的录音所证明的那样,许多实地录音都是种族融合的,黑人福音四重唱和布鲁斯歌手与白人小提琴手和弦乐乐队交流音乐理念,轮流在麦克风前表演。这种融合反映了非裔美国音乐家和音乐风格对许多早期(甚至二战后)乡村音乐家的巨大影响。戴夫·梅肯大叔、汉弗莱·贝特博士、吉米·罗杰斯和汉克·威廉姆斯只是众多从黑人音乐家那里学习歌曲和演唱风格的乡村表演者中最著名的几位。甚至包括梅肯、罗杰斯和罗伊·阿库夫在内的众多乡村音乐明星,都是从在江湖郎中表演和巡回剧团中”涂黑脸”开始其职业生涯的,这一悠久历史也反映了黑人文化对乡村表演者的巨大影响。大量早期乡村表演者通过演唱长期在黑人音乐家中流行的布鲁斯歌曲而建立声誉,这进一步反映了这种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尽管如此,这些白人艺术家认识到在音乐产业中(因此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而言)保持种族区分的重要性,艾伦兄弟1927年对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提起的25万美元诉讼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起诉的原因是唱片公司将他们录制的《查塔努加布鲁斯》作为”种族”系列发行,损害了他们的声誉。
尽管商业音乐产业和白人音乐家都试图将他们的音乐与黑人表演者的音乐明确区分开来,但由于唱片公司高管和记者将乡村音乐视为产生布鲁斯和爵士乐的同一异域南方乡村文化的奇特产物,他们经常在唱片公司出版物和新闻报道中将白人乡村音乐和音乐家与他们的黑人同行联系在一起。早期唱片目录通常将白人和黑人乡村音乐选曲分列在不同类别中,但放在相对的页面上。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蓝鸟唱片公司开始将其选曲列为”乡巴佬与种族唱片”,同时分离又统一了这些音乐形式,这一做法很快被其他几家唱片公司和音乐行业期刊采用。也许这种同步的种族融合与分离最清晰的例子,就是民间音乐学者阿奇·格林所称的乡村音乐”半官方洗礼叙事”——凯尔·克赖顿1938年的文章《那些乡巴佬身上有金子》。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关于乡巴佬音乐和音乐家的崛起,但封面页却不协调地刊登了三位黑人女布鲁斯歌手的照片,旁边是白人乡村表演者吉米·戴维斯的照片,正文反复但未明确承认地将白人和黑人表演者联系在一起,强调每一方的奇特和几乎超凡脱俗的地位。因此,尽管”乡巴佬”作为音乐流派及其表演者的标签明确表示”白人性”,但它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混合文化和种族类别,既与非裔美国人和其他非白人形象截然不同,又与之相似。
到了1920年代初,“乡巴佬”(hillbilly)一词也带上了滑稽的含义,这部分源于新兴的全国性刻板印象,但同样强烈地来自早期乡村音乐中的闹剧传统。例如,1910年代和1920年代在亚特兰大举办的佐治亚州老式小提琴手大会上表演的乐队,使用的名字包括”哞哞牛乐队”、“傻瓜交响乐团”和”舔锅底乐团”。活动由”亚历克·斯马特教授”主持,他穿着标准的杂耍剧院乡巴佬喜剧演员服装——过小的条纹裤子、高顶礼帽和燕尾服。除了确保观众能尽情跺脚欢乐之外,这些名字也是为了嘲讽亚特兰大新富阶层的”高雅艺术”做派,这些人既参加小提琴手大会,也出席歌剧节。许多参加这些比赛并后来进行商业录音的音乐家,在命名他们的表演组合时直接借鉴了这一喜剧传统,并融入了某些主题,特别是”私酿酒”(moonshining),这后来与乡巴佬形象紧密相连。吉德·坦纳和舔锅底乐队录制了名为《佐治亚的玉米酒蒸馏器》和《基卡普欢乐汁》的音乐短剧(后一个名称后来被阿尔·卡普在他的《小阿布纳》连环漫画中采用);小提琴手约翰·卡森演唱了《约翰酿好酒》,甚至给他的表演搭档女儿罗莎·李·卡森取了”月光凯特”这个艺名。
乡巴佬这个标签和身份因此很容易融入幽默和自我讽刺的歌曲、乐队名称甚至舞台人格的传统中。到1925年2月,亚特兰大的弦乐队乔治·丹尼尔的乡巴佬乐队在当地电台WSB播出节目,同年晚些时候,巡回杂耍表演”戴夫大叔和他的乡巴佬们”中的戴夫·梅肯大叔表演并录制了《乡巴佬布鲁斯》(W.C.汉迪《犹豫布鲁斯》的更新版本),开头唱道”我是个乡巴佬,住在山里”。到1920年代中期,甚至印刷媒体也开始将乡村音乐与”乡巴佬”标签联系起来。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1925年那首喧闹的诗《山地夜鹰》,副标题为”乡巴佬吉姆如何赢得小提琴大赛冠军”,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山地小提琴手如何击败卫冕冠军,并将”乡巴佬”一词与小提琴音乐联系起来(尽管他没有将音乐本身称为”乡巴佬音乐”)。贝内特很好地捕捉了小提琴手比赛的热烈气氛,但他对当时已成为标准套路的山民懒惰、贫穷和野性的乡土化暗示,也反映了一种正在固化的乡巴佬刻板印象,这种印象很快就会与音乐和音乐家联系在一起。
贝内特的诗融合了讽刺与赞美(“从没有过兄弟,也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但当我开始拉琴,你就得开始跳舞”),暗示了”乡巴佬”一词的多重可能解读,音乐家、制作人、记者和观众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为此争论不休。早期乡村表演者可能在表演中使用了丰富多彩的名字和舞台人格,但他们并不打算贬低音乐的形式或情感。小提琴比赛和早期商业音乐家的照片,即使是像约翰·卡森这样知名的喜剧艺人,都显示这些人穿着他们最好的礼拜日服装——打着领带、穿着外套和皮鞋(图3.1)。尽管他们有时会强调自己的乡村传统并热闹地表演,但这些音乐家通常追求一定程度的中产阶级舒适生活,并不认为嘲讽自己的农村和工人阶级身份有什么好处。

图3.1
商业”发现”前夕的早期弦乐队音乐家。从左到右:阿尔·霍普金斯、约翰·霍普金斯、托尼·奥尔德曼、约翰·雷克托、阿姆·斯图尔特大叔和小提琴手约翰·卡森;老式小提琴手大会,田纳西州山城,1925年。南方民俗收藏,威尔逊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P-849。
然而,早期商业表演者的制作人和评论者认为,音乐家和音乐应该有一种乡村的、甚至是土包子的外表,并据此描述和装扮表演者。因此,拉尔夫·皮尔在回忆他第一次亚特兰大录音时,将约翰·卡森描述为”一个穿着工装裤来录音的白人山民”。《亚特兰大日报》报道说,卡森来参加1914年的大会时”多次停下来观看城市的景象”,却忽略了卡森自1900年以来就住在亚特兰大边界的一个工厂城镇,而且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台表演者这一事实。报纸对卡森的描述是其对这些节日所有表演者进行”乡土化”处理的典型。一篇有代表性的报道描述参赛者”乘坐普通车厢从数百英里外赶来,光着脚,把礼拜日穿的鞋子挂在肩上”。皮尔和《亚特兰大日报》的记者可能真的相信山里人就是这个样子——或者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所论证的,他们可能觉得”这种新发现的’老式’音乐的商业吸引力在于其质朴的山地特质”。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形象和主题将继续塑造制作人、观众甚至表演者对乡村音乐和音乐家的观念,并将建立起这种音乐被贴上”乡巴佬”标签的文化背景。
“hillbilly”(乡巴佬)一词复杂而模糊的含义,以及外界对可销售的原始山区文化的认知与民间表演者自身喜剧弦乐传统的交汇,在Hill Billies乐队于Okeh唱片公司纽约录音室自发录音时的命名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尽管乐队成员都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北部和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山区长大,但他们绝非乡野村夫。Al和Joe Hopkins兄弟的父亲是前北卡罗来纳州议员,在华盛顿特区的人口普查局工作;Alonzo “Tony” Alderman的父亲是测量员、土木工程师兼治安法官。尽管如此,“hillbilly”这个词在Al Hopkins脑海中记忆犹新,因为就在他们出发去纽约之前,他父亲问道:“你们这些hillbillies(乡巴佬)觉得能在那儿干什么?”因此,当Peer问乐队领队Al Hopkins他们乐队叫什么名字时,Hopkins的回答——“我们不过是一群来自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hillbillies。随便叫什么都行”——显然带有自觉的讽刺意味。另一方面,这个词立刻吸引了Peer,他职业生涯始于堪萨斯城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据后来的记载,他”对奥扎克山区非常熟悉”,想必也了解这个词对该山区居民的贬义用法。
Tony Alderman对乐队名称的担忧进一步反映了这个词的模糊性质。他认为hillbilly是”一个会引发争斗的词”,暗示”一个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也没上过多少学的偏远山区人”。然而,乐队被老朋友、同为山区音乐家(也是商业乡村音乐先驱)的Ernest “Pop” Stoneman说服保留了这个名字,他笑着说:“你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名字了。”乐队在华盛顿特区WRC电台的首次广播中大获成功。据当时一份杂志报道,一位打电话到电台的听众将这个词视为文化真实性的标签:“你们骗不了我,”据报道他”带着明显的佐治亚口音”说道,“我知道这些小伙子来自哪里。他们肯定是Hill Billies。除非是在山里出生、在那儿长大的人,否则没人能演奏这种音乐。”尽管如此,Alderman仍然担心这个名字的选择以及它所代表的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嘲讽。他后来回忆道:“我不敢回家,因为乡下人演奏和演唱这类音乐,一看到城里人就把乐器藏起来。而现在我去了纽约,把他们的音乐录成唱片,还给它起了个难听的名字。所以我整整四年没有回家。”
Peer不仅欣然接受了”hillbilly”这个标签来命名他录制的音乐,还按照自己对这种音乐及其潜在听众的预设观念来塑造音乐家的形象。例如,Hill Billies的第一幅印刷插图是一幅钢笔素描,以Tony Alderman寄给唱片公司的一张照片为蓝本,照片中乐队成员按照他们希望展示的形象呈现——穿着西装外套、马甲和领带的体面现代音乐家,手持乐器,姿态放松但正式(图3.2)。然而,不到一年,乐队的宣传照片就变成了他们穿着工装裤、系着配套的头巾、帽子歪戴、放声高歌、置身户外而非客厅的形象(图3.3)。虽然这一形象将音乐家描绘成多彩而仍然真实的乡村音乐家,但他们1927年的短片《The Hill Billies》却不能这样说,影片中乐队”做着极其愚蠢的事情,疯狂地演奏各自的乐器”。在这里,就像他们同年的杂耍表演一样,乐队允许自己被如此刻画的方式,打破了善意颂扬传统文化与滑稽扭曲这种文化之间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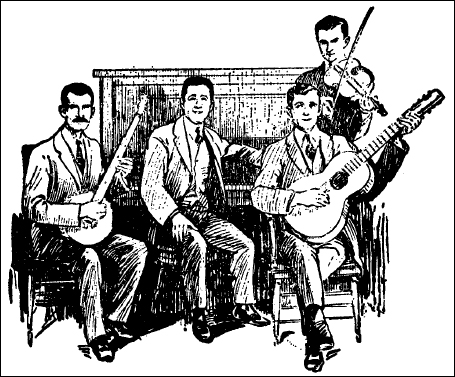
图3.2
Hill Billies乐队选择展示的自我形象……《Talking Machine World》,1925年4月15日,第50页。

图3.3
……以及Ralph Peer和Okeh唱片公司在宣传照片中呈现的形象。Al Hopkins和Hill Billies乐队,约1926年。南方民俗收藏,威尔逊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P-848。
这些早期最具影响力的两档乡村音乐广播节目——纳什维尔WSM电台播出的《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和芝加哥WLS电台历史更悠久的《全国谷仓舞会》(National Barn Dance)——同样改变了表演者的公众形象。与皮尔一样,自称”庄严老法官”的乔治·杜威·海伊在1925年至1956年间创办并主持《大奥普里》,他将音乐家的形象重塑为更具幽默乡村气息的样子。例如,他把”汉弗莱·贝特博士及其扩编管弦乐队”改名为”贝特博士的负鼠猎人”,并将其他乐队分别改名为”土包子”(the Clod Hoppers)、“果酱罐饮酒者”(the Fruit Jar Drinkers)和”沟壑跳跃者”(the Gully Jumpers)。这些音乐家最初在录音室里穿着西装打领带,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保险推销员、理发师和调度员。然而,当节目从1928年左右开始在现场观众面前播出时,表演者被要求穿上工装裤、格子衬衫,戴上草帽或压扁的毡帽等乡村服装。与”山地人乐队”(Hill Billies)一样,后来乐队的宣传照片都是在玉米地里、谷仓外或其他户外乡村场景拍摄的。与”乡巴佬”(hillbilly)这个标签一样,这种服装不仅将这些表演者漫画化,还赋予了他们独特且易于识别的商业身份,与主流流行音乐家明显区分开来。
也许最明确推广山区(而非仅仅是乡村)乡村音乐形象的人是约翰·莱尔,他是WLS《全国谷仓舞会》的核心推动力(后来还创办了《伦弗罗山谷谷仓舞会》)。后来的宣传资料称他”生来就是山里人”,但莱尔实际上来自肯塔基州的弗农山,靠近坎伯兰山脉的山麓,但该地区更接近蓝草区而非山区。他负责在上南部和《全国谷仓舞会》之间建立了一条娱乐输送渠道,鼓励源源不断的音乐家前来演出,包括霍默(“瘦子”)·米勒、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哈蒂)·泰勒、卡尔·戴维斯、莉莉·梅·莱德福德和克莱德(“红毛”)·福利。更重要的是,莱尔为他的表演者,乃至整个音乐流派,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山区形象,有时甚至是明确的”乡巴佬”形象。与海伊一样,他给个人和团体重新起了更具色彩和乡土山区气息的名字。莱尔把之前被称为”伦弗罗山谷男孩”的哈蒂·泰勒和卡尔·戴维斯改名为”坎伯兰山脊奔跑者”,并将他们与从肯塔基州和其他地方带来的其他表演者组合在一起,不准确地将所有人都描述为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他还把芝加哥夜总会的人气歌手琼·穆尼奇带到《谷仓舞会》,给她改名为琳达·帕克,“遮阳帽女孩”,让她穿着格子棉布裙和遮阳帽登台表演。
除了改名之外,莱尔还为他的表演者创造了明确的舞台和广播形象,强调他们所谓的真正山区出身。在坎伯兰山脊奔跑者的一张早期宣传照中,莱尔本人加入乐队吹奏陶罐,其他成员穿着格子衬衫、靴子和毡帽,在一座山区木屋前弹奏或拉奏乐器;而在稍晚的另一张照片中,小提琴手”瘦子”米勒赤着脚躺在乐队前面,头枕在手上。他这种日益常见的”懒惰乡巴佬”姿势旨在表现乐队的真实性,就像扬琴(dulcimer)、班卓琴(banjo)和其他各种乐器旨在展示乐队的音乐才华和民间音乐传承一样(图3.4)。莱尔为乐队撰写的广播文案也强调了他想要展现的质朴山区形象。1932年的一个典型节目用这种乡土方言介绍乐队:

赤脚的”瘦子”米勒以日益标准化的”懒惰乡巴佬”姿势躺在坎伯兰山脊奔跑者其他成员和约翰·莱尔面前,约1933年(从左至右:卡尔·戴维斯、约翰·莱尔、琳达·帕克、哈蒂·泰勒、“红毛”福利、休·克罗斯)。约翰·莱尔文献,南阿巴拉契亚档案馆,伯里亚学院,肯塔基州伯里亚,083-030。
“你们在这十五分钟里要听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是货真价实的——没有花里胡哨——就是来自肯塔基和田纳西山区的普通人,他们过着和祖辈们差不多的生活——他们知道的大多数歌曲也和祖辈们当年一边从荒野中开辟美利坚一边吹口哨唱的那些歌差不多。”
正如这些文字所表明的,Lair始终致力于将他管理的音乐家以及整个乡村音乐与一幅怀旧的美国往昔画卷联系起来,这幅画卷强调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和坚韧的拓荒者血统。对Lair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人来说,这种文化及其独立自主、重视家庭和亲族的传统价值观,似乎在南阿巴拉契亚山区得到了最完美的保存。在那里,地理和社会的隔绝使这种文化得以延续,而在其他地方,它早已被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冲刷殆尽。Lair将自己塑造成这种正在迅速消失的传统山区文化的保护者和捍卫者,他确实是一位重要的民歌和民俗收集者,在他的广播节目中收录了大量传统民谣的表演。此外,Lair本人从未公开使用过”hillbilly”(乡巴佬)一词,他谴责这是低俗商业势力强加给音乐和音乐家的标签:“广播里的乡巴佬?根本没这回事。山里人和来自丘陵地区的乡亲也许有,但没有什么乡巴佬……是Tin Pan Alley(锡盘巷,美国流行音乐产业中心)给某些类型的音乐和艺人贴上了这个名字。”他还在WLS宣传杂志《Stand By》中特意向听众保证,尽管表演者有着乡土气息的舞台形象,但他们过着真实的中产阶级生活。例如,一张小提琴手Lily May Ledford身穿便装在城市环境中的照片,其说明文字描述她”穿着鲜红色翻领毛衣配灰色花呢裙,看起来相当有大学生气质”。
尽管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Lair确实允许在构建和推广他旗下音乐家的公众形象时使用滑稽甚至带有嘲讽意味的山区形象。例如,他还让Ledford出现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9月期间在《Stand By》上刊登的Pinex止咳糖浆系列广告中,标题为”Lily May——山里姑娘”。这个粗略绘制的连环漫画的早期版本讲述了她在肯塔基山区的成长经历。Lily May、她的父母和一位拉小提琴的山民都被描绘成赤脚、穿着乡土服装的形象,说明文字则使用了老套的乡巴佬方言(图3.5)。该系列的其他广告还展示了留着超长胡须的男人,以及懒惰和对现代事物一无所知等常见的乡巴佬刻板印象。Harry Steele 1936年的文章《乡巴佬生意的内幕》提供了更清晰的证据,表明Lair与”hillbilly”这个词和形象的关联。Steele试图向显然困惑不解的芝加哥地区观众解释乡村音乐家惊人成功的原因,他透露,以”Ezra K. Hillbilly”这个角色为代表的广播和唱片乡村音乐”每年让收银机响起……高达2500万美元的进账”。随后Steele也为这一新兴的刻板印象添砖加瓦:如果把1934年所有”在广播中工作的乡巴佬……头尾相接排成一排——他们就会处于在轻松的广播收入诱惑他们离开牧场之前最习惯的姿势”。他总结道:“Ezra K.已经成为娱乐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山里那个懒散的家伙已经转变为大生意中的重要角色。”Steele用”正宗”山民John Lair的证词来支持他的说法。Lair被描述为”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据称他证实”在他的地盘上,乡巴佬就是个懒汉,只有到了吃饭时间或者去泉房取一罐新鲜玉米酒时才会从地上爬起来”。

图3.5
《National Barn Dance》明星Lily May Ledford被描绘成卡通乡巴佬形象。“Lily May,山里姑娘”,Pinex止咳糖浆广告,《Stand By》,1936年10月10日,第7页。John Lair档案,南阿巴拉契亚档案馆,Berea学院,肯塔基州Berea。
《Grand Ole Opry》的George Hay与这个词及其贬义色彩也有着类似的矛盾关系。和Lair一样,他也拒绝使用”hillbilly”这个带有贬义的标签,他在1945年写道:“我们从不使用这个词,因为它是带着嘲讽意味创造出来的。而且,根本就没有这种人……我们的组织不容忍偏见,也不允许偏见存在。”然而在同一出版物的后面,他明显缓和了批评的语气,认为这个词”是作为一个玩笑带着轻微的嘲讽意味创造出来的,我们理解这一点,但它不适合Opry”。而三年前,他曾将1925年WSM最初的乡村舞会节目描述为”我们那些小型的、非正式的乡巴佬尝试”中的第一个。他的各种回应反映出对这个词的某种矛盾心理,以及对于需要多强烈地否认这个标签的不确定性。此外,他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使用”hillbilly”,是为了将这种音乐朴实无华、真实的民间特质与紧接在乡村舞会节目之前播出的古典音乐节目形成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hillbilly”意味着对普通人——民众——文化的赞美,也呼应了Hay在每场《Grand Ole Opry》演出前对表演者的著名告诫:“好了,今晚咱们接地气点,伙计们。”
早期乡村音乐制作人和推广者,如莱尔和海伊,可能在职业生涯后期”公开”谴责了”乡巴佬”(hillbilly)这一标签——当时这个词在乡村音乐界面临越来越多的敌意——但他们在推广乡村田园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形象帮助合法化了该词的使用,以及对山区民众和乡村音乐人的幽默乡土化认知。他们可能有意识地区分”山区”和”乡巴佬”的重要差异,也区分了赞美南方民间文化的”乡巴佬”用法和贬低它的用法。但像哈里·斯蒂尔这样的作家并不做这种区分,而莱尔和海伊的做法为这种对南方山区民众和民间音乐的扭曲和恶意描绘提供了现成素材。
与莱尔和海伊一样,大多数唱片公司最初避免使用”乡巴佬”一词,而是偏好”最受欢迎的山区民谣和老歌”、“美国民间音乐”和”老式演唱与演奏”等标签。即使到了1930年代中期,乡村音乐人的音乐专辑仍继续使用类似标题,包括”家乡与山区民谣”、“乡土之歌”和”老木屋歌曲”。但尽管唱片业尽力限制该词的正式使用,讨论”乡巴佬歌曲”和”乡巴佬曲目”流行的文章在1925年秋天出现;《综艺》杂志在1926年12月刊登了关于”’乡巴佬’音乐”的头版报道;而”来自皮肯斯县的乡巴佬三人组”于1927年在WSB电台录音。到1929年,当阿尔·霍普金斯的乐队——最早以这个标签录音的组合——试图通过注册公司来保护其名称的独特性,成立”原版乡巴佬乐队”时,甚至西尔斯-罗巴克和蒙哥马利-沃德的主要邮购目录也开始使用这个词作为部分商业乡村音乐选集的标签短语。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其他唱片公司纷纷效仿:奥克在1933年,德卡和蓝鸟在1935年。
到1930年代中期,这个词已经无处不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音乐团体都自称乡巴佬。至少有十九个团体在名称中使用了某种版本的”乡巴佬”,包括好莱坞乡巴佬乐队、奥迪恩斯乡巴佬男孩(根据1935年的歌本,他们是”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宠儿”),以及”老爹”切希尔和他的乡巴佬冠军乐队。此外,许多团体采用(或至少接受)了相关的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如”山民”(mountaineers)、“乡下佬”(clod hoppers)和”山脊跑者”(ridge runners)。1930年代有数十首歌曲在标题中使用”乡巴佬”,包括”小乡巴佬心跳”、“山中有个乡巴佬天堂”和”六月的乡巴佬婚礼”。这些歌曲中有许多有意将该词与其负面含义分离,用”乡巴佬”来表明这是一首乡村歌曲而非流行音乐选曲,或唤起对南方山区的浪漫想象。
但在其他情况下,如牧场男孩乐队的”乡巴佬家庭”,这些歌曲利用了一种一眼就能认出的落后乡巴佬刻板印象:“我们是最迷糊、最疯狂的,也差不多是最懒惰的,你见过的一群乡巴佬,/我们是最粗野、最土气的,当然也不是最干净的,我们连ABC都不认识。”这首歌是那些年由专业词曲作者创作的众多所谓滑稽歌曲之一,讲述山民的奇怪习俗。有些歌曲,如”我的乡巴佬玫瑰”和”你对我来说仍是个乡巴佬”,直接利用山区刻板印象本身,通过对比山区的贫穷落后与城市的富裕精致来制造幽默,或描绘一个粗犷男性化的山区女孩形象。其他新奇歌曲如”自从尤塞尔学会约德尔调(他成了犹太山民)“和”他是个乡巴佬高乔人(带着伦巴节拍)“则自由地将乡巴佬漫画形象与其他族群的知名戏仿混合在一起。尽管”六月的乡巴佬婚礼”与后面这些新奇歌曲之间存在差异,但所有这些歌曲都反映了大萧条时期对所谓正宗美国民间文化的真正兴趣与利用山区热潮牟利欲望的融合。正如滑稽音乐四重唱胡希尔热门乐队1935年在《全国谷仓舞会》上唱的那样:“他们入侵了所有城市/用他们可爱的乡土小调/让全体居民都流下了眼泪……那些乡巴佬现在成了山区威廉姆斯了。”
“乡巴佬”一词传播最清晰的例子,或许是1930年春天”比弗利山乡巴佬”乐队的诞生。这是洛杉矶KMPC电台经理格伦·赖斯的创意,据称比弗利山乡巴佬乐队的成员来自一个真正的山民社区,是赖斯在马里布山区迷路时偶然发现的。实际上,他们是当地音乐人利奥·曼尼斯、西普里安·保莱特和汤姆·默里,被赖斯秘密招募来扮演真正的山民。赖斯精心为听众设下这个骗局:他宣布计划去山里度假,然后从广播中消失了几周,期间电台播音员不断表达对他安危的担忧,随后他带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重新出现——声称发现了”齐克·克拉多克”、“埃兹拉·朗内克”和其他同意上电台表演的”乡巴佬”。乐队成员穿着乡巴佬风格的服装,赖斯描述他们刚骑着骡子进城,乐队立即大获成功——以至于《洛杉矶观察家报》评论说,如果把洛杉矶居民分成看过和没看过乐队表演的两类人,“你会发现两边人数相当平均。如果有差别的话,看过的人可能还稍微多一点。”所有成员都采用了”乡巴佬”风格的艺名,如”齐克”、“莱姆”和”汉克”,早期的宣传照片显示他们在一棵树下摆姿势,穿着格子衬衫,戴着皱巴巴的帽子,其中一人甚至戴着假胡子。早期的报纸报道称这支乐队是”阿肯色州、欧扎克山区的小伙子”,赖斯还两次从欧扎克地区空运约德尔唱法的男孩歌手到加利福尼亚,与他们来自马里布山区的”表亲”一起表演,以此强调这种联系。
尽管大量使用了乡巴佬的术语和形象,但该乐队的音乐绝非”山地乡巴佬”乐队那种节奏明快的小提琴曲,也不是卡特家族风格的民谣,而是后来被称为牛仔音乐或西部音乐的风格。他们的典型曲目包括《当鼠尾草盛开时》、《红河谷》和《草莓骝马》。乐队的服装迅速变得越来越像牛仔风格,尽管仍保留了一些乡巴佬元素。他们不再严格穿着格子衬衫和背带裤,但也还没有完全换上皮护腿(chaps)、十加仑帽和西部衬衫(图3.6)。

图3.6
乡巴佬式宣传噱头与”歌唱牛仔”风格的融合。比弗利山乡巴佬乐队,约1934年(从左至右:汉克·斯基莱特、米兰达、埃兹拉·朗内克、格斯·麦克、埃尔顿·布里特、莱姆·贾尔斯、贾德·迪斯)。南方民俗收藏,威尔逊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P-199。
比弗利山乡巴佬乐队这个奇特案例展示了全国城市观众对乡村音乐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它发展成为一个成熟娱乐产业的过程。到1930年代中期,吉米·罗杰斯、卡特家族和吉恩·奥特里等乡村音乐表演者已经创造了百万销量的唱片,《全国谷仓舞会》和《大奥普里》节目吸引了爆满的观众,并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百万听众,好莱坞也在大量制作”歌唱牛仔”西部片。乡村音乐在这些年蓬勃发展有几个原因。在大萧条时期艰难的经济环境下,低价唱片和免费广播为城镇居民以及更偏远地区的美国人提供了廉价且易得的娱乐选择。此外,数以万计的美国农村人口迁移到中西部和西部城市,形成了一个由表演者和听众组成的不断壮大的乡村音乐”亚文化群体”。乡村歌曲中关于个人独立、浪漫风景或植根于家庭、家园和信仰等传统价值观的怀旧往昔的意象,吸引了这些背井离乡的美国人以及成千上万感到心理上无所依托的人。与当时许多呈现甜蜜爱情故事或物质富足的流行音乐不同,许多乡村歌曲直面经济和情感困境、日常挣扎甚至死亡——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议题。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星探阿瑟·萨瑟利在解释流行音乐和乡村音乐的区别时写道:“老练的城里人喜欢那些虚假的男女情歌,一切都美好得不真实,而山民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歌曲涉及孤独、苦难、死亡和谋杀。”与此同时,尽管乡村音乐歌曲常常触及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它们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逃入一个浪漫化的乡村往昔——那里的特征不是数十万美国农村人当下面临的佃农制度和歉收的现实,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农耕本身,而是”小木屋……游泳池塘……老灰骡子、浣熊猎犬”这些令人慰藉的乡村意象。因此,乡村音乐以一种流行歌曲往往无法做到的方式,与农村和工人阶级白人美国人产生了共鸣,为数百万深陷大萧条困境的听众提供了日常的精神慰藉。
然而,当时大多数外部评论者都深深扎根于一个长期贬低南方和农村工人阶级文化及其人民的社会中,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种音乐对听众的情感吸引力,并对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乡巴佬热潮”表示惊讶。有些人更多是觉得好笑而非担忧。例如,1930年代初一篇匿名报纸文章报道了”乡巴佬音乐”在纽约演出这一明显反常现象,引用了广播节目《魔毯时光》的导演沃尔特·奥基夫(后来自称”百老汇乡巴佬”)的观点:“百老汇……已经变得乡巴佬化了,自己却浑然不知。乡巴佬们曾经来自肯塔基州的松树峡和密苏里州的死人谷,但现在你在这座城市的每个热闹角落都能找到他们。”作者写道,乡巴佬音乐被接受的最终标志是鲁迪·瓦利在他的《弗莱施曼时光》节目中举办了一场谷仓舞会。尽管遭到”锡盘巷词曲作者”的反对,记者总结道,美国将会听到”祖辈们的山歌”,因为”这是乡巴佬的季节!“同样,哈里·斯蒂尔写到了来自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的”人造乡巴佬”的出现,他们的歌声”常常带有轻微的欧洲或亚洲口音”,穿着”假扮的乡巴佬服装——十加仑帽、高跟靴、灯芯绒马裤和鲜艳的法兰绒衬衫”。
然而,斯蒂尔的观察也暴露了他和许多评论者对这种音乐、表演者及其听众的潜在蔑视。这些作家将”乡巴佬”定义为”低俗”的同义词,很容易就回到了长期以来关于山民无知、贫穷和邋遢的刻板印象。这种嘲讽态度在斯蒂尔的评论中显而易见,他说与城市假冒表演者的服装相比,“私下告诉你,家乡的乡巴佬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工装裤就算幸运了。”亚瑟·史密斯是一位留声机销售员,也是1933年音乐教师杂志《练习曲》上一篇文章的作者,他将自己在音乐中发现的低俗和无脑特质与他对唱片购买和收听群体的认知联系起来。他写道,“南方卑微的本土白人”这”庞大的、无数的、沉默的群众”“生活在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地下音乐世界中”,唱的不是斯蒂芬·福斯特的正统民歌,而是关于亡命徒和监狱的歌曲。
这种居高临下态度的最佳例证是1926年12月《综艺》杂志编辑阿贝尔·格林的头版文章,这是已知印刷品中首次使用”乡巴佬音乐”一词。格林将这种音乐与他标记为”乡巴佬”的一个亚群体联系起来,并描述为:
北卡罗来纳州或田纳西州及邻近地区的山民类型的文盲白人,他们的信条和忠诚献给圣经、夏托夸集会和留声机……山民属于”贫穷白人垃圾”类别。绝大多数,可能95%,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英语……文盲和无知,智力如同低能儿。
尽管这种音乐和人民据说令人厌恶,格林和皮尔一样,认识到这一类型的潜在利润,愿意捏着鼻子一路走向银行。格林强调,对于唱片经销商来说,“乡巴佬热潮”意味着”财源滚滚”,因为”这些蠢货一次能买多达15张同一首歌的唱片”,这样他们就可以退回到他们的”山间栖息地”,“数周内不再回到最近社区中心所能提供的文明社会”。然而,格林并没有因为这种流行而重新考虑音乐的价值,他只是将高销量视为对他关于这些人和音乐都很低俗这一信念的再次确认。
另一个对商业乡村音乐持同样批评态度但原因不同的群体是自我定义的民俗学家和民间表演者。这些”乡巴佬”音乐的民间音乐批评者差异很大,从《全国谷仓舞会》明星布拉德利·金凯德——他称自己的选曲为”山地音乐”,并一贯谴责他认为的”乡巴佬歌曲”是”烂歌和监狱歌”——到约翰·雅各布·奈尔斯,一位高雅的民间音乐诠释者,他回避商业乡村音乐的所有方面,在音乐厅和学术观众面前演出。所有人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广”正宗”民间音乐并将其与商业驱动的、因此不合法的”乡巴佬”歌曲隔离开来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所有人都错误地设想了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一种原始纯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间音乐,未被市场力量玷污。讽刺的是,这些人为隔离”合法”和”非法”民间音乐的努力本身往往带有市场驱动的矛盾。例如,长期民间音乐收藏家、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山地舞蹈和民间音乐节创始人巴斯科姆·拉马尔·伦斯福德是如此的文化”纯粹主义者”,以至于他拒绝让他节日中的方块舞者穿格子衬衫和牛仔帽——但他也共同创作了经典的”乡巴佬”饮酒歌《山间露水》。好莱坞编剧转型民俗学家的琼·托马斯帮助创立了肯塔基州阿什兰的美国民歌节,她简直是在欺骗。她将东肯塔基州的半职业吟游表演者”盲人比尔”戴利重新命名为”吉尔森·塞特斯”,让他穿着土布衣服在质朴的小屋前摆姿势拍照,并将他呈现为来自偏远山区的正宗肯塔基山民。
音乐行业人士和民俗学家将”hillbilly”(乡巴佬)一词作为庸俗、平庸和粗俗商业主义的代名词,这促使一些音乐家和制作人谴责这个术语,并寻求替代的标签和形象。星探阿瑟·“阿特叔叔”·萨瑟利晚年时回忆说,早在1918年,他就对这种音乐被”粗俗地”称为”Hillbilly”感到不满。比尔和厄尔·博利克兄弟组建了蓝天男孩乐队,这是1930年代最著名的演唱组合之一,他们也对”hillbilly音乐”这个称呼感到不满,将自己的音乐称为”民歌”。词曲作家比利·希尔非常厌恶这个词,以至于在1933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以乔治·布朗的名字发表歌曲。然而,至少在整个1930年代,公开的否认声明是有限的。即使是比尔·博利克,在他职业生涯早期,也不情愿地接受了赞助商的要求,让他和乐队成员接受”疯狂蓝岭乡巴佬”这个名字(以帮助推广他们的赞助商疯狂水晶),并穿上工装裤、格子衬衫和草帽,因为这样看起来”可爱”;在大萧条的艰难岁月里,稳定薪水的保障战胜了对乐队形象的个人控制。其他人可能也不喜欢这个标签,但觉得至少暂时有义务接受它。
尽管一些学者断言”hillbilly”这个词几乎被乡村音乐的音乐家和歌迷普遍拒绝和厌恶,但大多数乡村音乐爱好者对这个词持有明显矛盾的看法,其中对它所引发的嘲讽的认识与个人和文化自豪感交织在一起。亚特兰大音乐家乔治·丹尼尔在谈到他的乐队时告诉朋友们(用词与阿尔·霍普金斯的名言非常相似):“我们只是一群乡巴佬”,并将他的音乐与他妻子古典钢琴演奏的”高雅”音乐区分开来。罗莎·李·“月光凯特”·卡森在回答侄子为什么她和父亲没有进入乡村音乐名人堂时,表达了同样的尊严与尴尬的结合:“亲爱的,我们不是乡村音乐家。我们是乡巴佬。”同样,露露·贝尔·怀斯曼(斯塔米),《全国谷仓舞会》的主要表演者,回忆说她并不介意她和同事们总是被称为乡巴佬,她说”我觉得这很有趣”,尽管她补充道”但很多演员对此感到不满”。
关于”hillbilly”一词使用最有趣的例子,也是反驳该标签只是由行业制作人和嘲讽媒体强加给不满音乐家这一论点的例子,是纽约州北部五指湖地区弦乐队的案例。这些乐队从1920年代一直演出到1950年代初,主要演奏”老式”方块舞曲和小提琴曲,如《士兵的欢乐》和《水手的号笛舞》,以及老标准曲目和黑人滑稽剧曲目,如《爱尔兰洗衣妇》和《稻草中的火鸡》。这些表演者使用诸如奥特伐木工、霍内尔斯维尔乡巴佬和伍德霍尔老式大师等多彩的名字,融入了明确的乡巴佬舞台形象,从他们的乡巴佬喜剧演员服装——滑稽的帽子、鲜艳的法兰绒衬衫和假胡子,到他们使用的道具,如干草捆、威士忌酒壶和写着”我们没疯,只是看起来像”的标语牌(图3.7)。像比佛利山庄乡巴佬乐队一样,这些音乐家甚至采用了老式的艺名,如”老爹”、“以斯拉”和”齐克”。

图3.7
霍内尔斯维尔乡巴佬乐队,1932年(从左到右:埃德温·里奥佩利、费伊·麦克切斯尼、皮特·麦迪逊、约瑟夫·索兰、阿奇·索普、莱尔·迈尔斯)。图片由西蒙·J·布朗纳提供。
与加利福尼亚的音乐家不同,纽约的弦乐队并不是被有意利用日益标准化的全国刻板印象来赚钱的广播和唱片行业制作人推动着将自己包装成乡巴佬的。当弗洛伊德·伍德霍尔在1928年组建他的乐队时,他还没有听说过阿尔·霍普金斯和乡巴佬乐队。他乐队的乡巴佬服装和形象并非基于南方乡巴佬的刻板印象,而是基于一种高度本地化的概念。正如伍德霍尔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个地区的山丘……那就是形象……这是农民的形象或乡巴佬的形象,但不是你联想到的那种与私酿酒贩子相关的乡巴佬,比如你说的田纳西之类的地方。”事实上,出现在一个乐队广告卡上的图片——一个圆胖的男人和他穿着礼服大衣、留着短方胡子的瘦高同伴——与通常对乡巴佬的概念相去甚远(图3.8)。强调乡巴佬的本地化含义,这些形象是对构成这支乐队主体的考夫家族德国血统的参考,并基于长期的杂耍艺人(卢)菲尔兹和(乔)韦伯以及他们的”荷兰式滑稽”表演——德国移民迈耶和迈克的表演,将粗犷的肢体动作与蹩脚的英语混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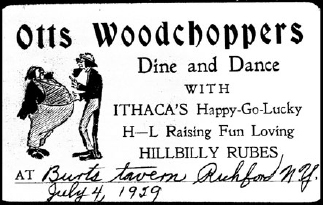
图3.8
个性化的乡巴佬:德国杂耍小丑与乡巴佬标签的融合。奥特伐木工乐队,广告卡,1929年。图片由西蒙·J·布朗纳提供。
纽约弦乐队对”乡巴佬”形象的采纳,使我们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乡巴佬”(hillbilly)概念的建构和意义有了更复杂的理解。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可能带有贬义的标签和形象会如此迅速地传播,并被各个文化层面的音乐家、推广者和听众所接受。奥特伐木工乐队和霍内尔斯维尔乡巴佬乐队的案例表明,这个术语和形象成为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过去与现在等对立概念之间的协商空间。对于许多早期乡村音乐表演者和听众来说,这个词象征着强大的乡村传统和与土地的联系、家庭和社区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将自己视为高尚的”普通人”而非城市大众或文化经济精英的一员。在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向工厂迁移、经济动荡不安、文化和技术现代化力量不可控制的世界里,这种音乐和术语吸引了许多怀念自己或家人乡村根源的美国人,尤其是当他们已经安全地远离了耕作土地的艰辛。这在纽约州中部的工厂城镇与正在工业化的南方和中西部同样适用。这并不是说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神圣或高雅,如同”母亲”或”家”那样。“乡巴佬”一词始终带有明显的幽默甚至滑稽意味,但并不必然引发嘲笑或贬低。
与此同时,这些男男女女认识到,尽管他们已经离开了农场,许多土生土长的城市美国人仍然把他们视为无知的乡下人——乡巴佬。因此,通过为自己挪用这个术语并积极参与一种保护性的自嘲——民俗学家西蒙·布朗纳称之为”可视化的方言笑话”——他们消除了这个词的部分污名,并定义了自己的身份。扮演”乡巴佬”帮助表演者和观众应对自己生活中的矛盾,同时将自己与乡村民族和文化传统分离又联系起来。这种矛盾心理在奥特伐木工乐队的广告卡片中清晰可见,卡片既宣传了他们的专业地位和音乐才华,又颂扬了他们表演的喜剧性和颠覆性。霍内尔斯维尔乡巴佬乐队在1930年代的自我描述完美地捕捉了这一点:“一支现代化的老式乐队。”
尽管有纽约州北部弦乐队的例子,到193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乡村音乐表演者和支持者都在寻求一种新形象,这种形象不带有”乡巴佬”一词和山民形象日益增加的负面含义。比佛利山庄乡巴佬乐队再次代表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即乡村音乐从乡巴佬和山地风格向牛仔和西部服饰、歌曲和形象的整体转变。将牛仔形象引入乡村音乐并非全新的发展。埃克·罗伯逊是第一位被商业录制的”老式”小提琴手,他来自西德克萨斯,在试音时穿着牛仔服装,1920年代的许多音乐家,包括卡森·J·罗宾逊、卡尔·T·斯普拉格,尤其是吉米·罗杰斯,都因演唱牛仔歌曲和穿着夸张的牛仔服装而声名鹊起。但直到1930年代,“俄克拉荷马的’歌唱牛仔’”吉恩·奥特里取得巨大成功——他从《全国谷仓舞会》节目转向好莱坞的辉煌事业——牛仔形象才真正笼罩了乡村音乐。牛仔帽和牛仔靴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乡村音乐表演者的标准装束,“红河戴夫”、“孤独牛仔”、“金色西部女孩”和无数其他艺人充斥着广播电波、唱片店和邮购目录。德克萨斯及其他地区”西部摇摆”(Western Swing)音乐的兴起——融合了布鲁斯、爵士和传统小提琴曲调——西南部作为音乐家和广播节目摇篮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德卡和奥凯等唱片公司对该地区的日益关注,都反映了音乐风格和形象从山地向西部的稳步转变。
几个相关因素导致了”乡巴佬”形象在1930年代中后期被抛弃,而牛仔形象被广泛采用:十加仑帽、皮护腿和尖头靴比传统山民服装提供了更多浪漫的可能性;弦乐队和哀婉的山地民谣风格听起来越来越老派,甚至对现代观众和表演者来说显得陌生;在大萧条时期严酷的心理和经济环境下,牛仔形象提供了(用乡村音乐历史学家比尔·马龙的话说)“一种令人安心的独立和掌控象征”,这无疑给许多与经济困难以及个人和社会信仰丧失作斗争的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在二十世纪初,神话般的山民代表着同样的个性、独立和坚韧品质。但到了1930年代中期,这些更积极的解读正被对南方山区和山民日益增长的嘲讽和负面形象所取代。全国观众经常接触到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暴力煤矿罢工的报道、社会堕落和”异常”宗教习俗(如玩蛇和说方言),以及越来越堕落的乡巴佬形象,他们再也无法维持对山区和山民的浪漫怀旧情感。关于新政援助和建设项目的新闻报道——由重新安置管理局、农业安全管理局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管理的针对南方山民的项目——也突出了该地区恶劣的生活条件,并将南方山区描绘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称的”国家头号经济问题”——十三个南方州——中一个特别萧条的地区。随着观众越来越将山区视为落后和堕落的文化场所,全国各地的乡村音乐家和听众转向了一个被大众媒体更一贯地英雄化塑造的形象。正如乡村音乐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格林简洁地观察到的,“三四十年代没有哪个年轻人想长大后成为乡巴佬,但成千上万的人想成为牛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本人也利用了这些态度,宣布《牧场是我家》是他最喜欢的歌曲。
乡巴佬和牛仔之间的文化鸿沟很容易跨越,因为乡村音乐的图像学一直占据着山区和平原之间的中间地带——这种阈限性(liminality)在1940年歌本《家乡与山地乡村民谣》封面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弧形景观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图3.9)。因此,到了1930年代中期,乡村歌手仍然唱着山中小屋的歌曲,但他们现在指的是落基山脉而不是坎伯兰山脉,《全国谷仓舞会》的肯塔基漫游者乐队变成了草原漫游者乐队,并为帕齐·蒙大拿(原名鲁比·布莱文斯,出生于阿肯色州温泉城)伴奏。1930年至1934年的《WLS家庭相册》强调了坎伯兰山脊奔跑者乐队和布拉德利·金凯德的山区出身,但到了1936年,该节目被牛仔团体的宣传照所主导,如帕齐·蒙大拿、风滚草,以及多莉和米莉——“金色西部的女孩们”。肯塔基小提琴手克利福德·格罗斯的职业生涯完美地概括了这一趋势。1931年,他搬到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组建了一支名为”肯塔基乡巴佬”的弦乐队。乐队很快解散了,但格罗斯很快获得了成功,于1933年加入了非常受欢迎的轻皮面包男孩乐队。1939年,格罗斯回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又组建了一支乐队,但意识到乡村音乐的压倒性趋势,他将新乐队命名为”克利福德·格罗斯的德克萨斯牛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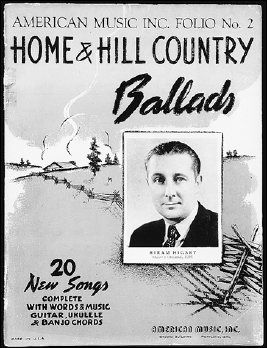
图3.9
乡村音乐的阈限景观。《家乡与山地乡村民谣》。南方民俗收藏,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威尔逊图书馆,FL-337。
尽管到1930年代末,牛仔服装、形象和主题在乡村音乐中占据主导地位,但”hillbilly(乡巴佬)“一词直到1950年代仍是该音乐类型的标准称谓,尽管这个标签从未完全令人满意。Decca唱片公司1940年的目录封面突出展示了这个词,尽管所有表演者都穿着西装打领带或戴着牛仔帽和头巾(包括Clayton McMichen,他是Skillet Lickers弦乐队的创始成员之一)(图3.10)。有影响力的乡村乐队继续在名称中使用”hillbilly”,包括Colorado Hillbillies乐队和Wilbur Lee “Pappy” O’Daniel的Hillbilly Boys乐队,后者于1935年在达拉斯成立,旨在推广O’Daniel的”Hillbilly面粉”品牌和他的政治抱负。电台赞助的期刊和乡村音乐粉丝杂志也广泛使用这个词。直到战后时期,《Hillbilly & Western Hoedown》(辛辛那提,1953-1966年)和《Hillbilly and Cowboy Hit Parade》(1957-1961年)等粉丝杂志不仅在标题中继续使用”hillbilly”,而且在整个出版物中都使用这个词(经常与”cowboy(牛仔)“、”western(西部)“、”country(乡村)“、”country and western(乡村与西部)“甚至”folk(民谣)“混用)。至少一些订阅者也继续接受这个词,用它来指代”hillbilly音乐”和作为听众的自己。正如一位读者写道:“我们非常喜欢它(《Hillbilly & Western Hoedown》),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些hillbilly都喜欢的杂志类型。”因此,正如Bill Malone回忆他在东德克萨斯州的青年时代所说,自称”hillbilly”并不是给自己贴上山民的标签,而是一种包容且积极的(尽管常常带有防御性的)表达,表明自己的音乐品味和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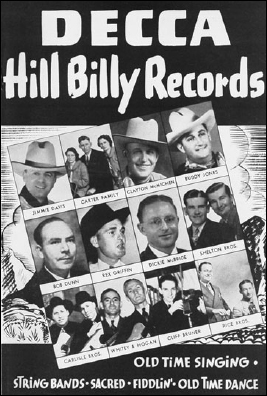
“Hillbilly”一词在乡村音乐牛仔时代的延续。Decca Hill Billy唱片目录,1940年5月2日。Peter Tamony收藏,1890-1985年,西部历史手稿收藏馆,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
自商业乡村音乐诞生以来,“hillbilly”一词在其广泛的可能解释中始终包含贬义含义。然而,在1930年代中后期之前,由于这种音乐的新颖性及其对整体大众文化相对有限的影响,加上这个词和形象很容易融入草根喜剧传统,最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标准化的hillbilly形象,这个词对许多音乐家和粉丝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推广者、音乐家和听众都努力将这个词与其负面刻板印象分离,甚至与南方山区或南方山区文化的任何联系分离。例如,“Bob Miller’s Famous Hill-Billy Heart Throbs”1934年歌曲集包括《Snow Capped Hills of Maine》《Sleepy Rio Grande》和《Harvest Time in Old New England》,但没有一首歌曲以阿巴拉契亚或欧扎克山区为主题。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些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音乐成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全国性流行文化产业,特别是在二战”突破”年代之后。寻求国防工业工作的南方移民涌入北方和西部的工业区,全国各地军事基地的军人将这种音乐介绍给成千上万的新听众,并在洛杉矶、底特律和巴尔的摩等不同城市创造了对现场表演、唱片和点唱机选曲日益增长的市场。传统的弦乐队风格和乐器编制逐渐被电吉他和鼓所取代。“hillbilly”这个词和形象明确地与一眼就能认出的卡通人物联系在一起。大众媒体继续在《Hillbilly Boom》《Hillbilly Heaven》《Whoop-and-Holler Opera》和《Thar’s Gold in Them Thar Hillbilly Tunes》等文章中贬低这种音乐及其听众,但这些主流报道现在大量借鉴了新近定型的落后山民滑稽形象。例如,在描述1920年代唱片公司代理人最初发掘本地人才的努力时,一位作者嘲讽道:“他们发现的是原生态的:赤脚的小提琴手,不识乐谱,但能唱出无尽的曲调,尤其是在玉米威士忌的帮助下。”《Hillbilly Heaven》一文的封面插图展示了数十个卡通hillbilly形象,他们提着煤油灯从山顶小屋跑出来,或者开着嘎吱作响的破旧汽车前往标有”Grand Ole Opry”的乡村谷仓。直到1950年代,一些唱片公司仍继续使用赤脚、叼着玉米芯烟斗的hillbilly形象来为他们的音乐家做广告(图3.11、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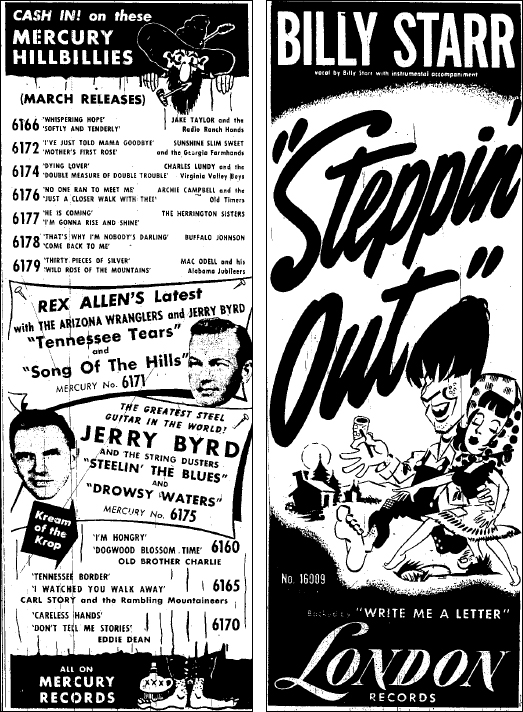
战后乡村音乐宣传中的Hillbilly图像。Mercury唱片和London唱片广告,《Billboard》,1949年3月19日,第39页;1950年6月3日,第33页。
战后年代,乡村音乐家和推广人为了将他们的音乐推向主流受众,并获得唱片和广播行业的尊重,积极努力地摒弃”hillbilly”(乡巴佬)这一标签。乡村音乐词曲作者约翰尼·邦德回忆说,他所有的音乐家同行”都认为这个词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贬低”。欧内斯特·塔布是1940年代最重要的乡村音乐表演者之一,也可能是音乐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也努力争取用其他名称取代”hillbilly”这一标签,正是因为它带有刻板印象的含义。他说服了自己的唱片公司Decca在1948年放弃这个名称,改用更易接受的”乡村与西部音乐”,并鼓励海伊法官在《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的后台和广播中停止使用这个词。正如他向海伊解释的那样:“很多人不理解hillbilly是什么意思;他们想到的是某个人……在山里,光着脚,留着长胡子,酿私酒——他们称这些人为hillbilly。看起来他们把我们的音乐当作一种低等的音乐。”《大奥普里》明星罗伊·阿库夫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告诉记者:“我们不是那么富有或聪明……但我们并不愚昧,不应该被嘲笑。”他还拒绝参演1940年的好莱坞电影《大奥普里》,除非制片厂”不加入’斯纳菲·史密斯——乡巴佬’的背景”——制片厂最终接受了这一条件。阿库夫、塔布和其他音乐家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阿特叔叔”萨瑟利的支持,他是Okeh唱片公司和后来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长期星探,发掘并录制了数十位乡村音乐表演者。萨瑟利一生都是美国农村人及其文化的捍卫者,他在晚年写道反对使用”Hill Billy”这个词,并抱怨被唱片业中指责他录制”垃圾”的人”贴上了Hill Billy萨瑟利的标签”。对萨瑟利来说,这个词直接与他对美国农民尊严的认知相冲突,也与他对农村人高度浪漫化的愿景相悖——他视他们为”乡村人民……耕耘土地的人……我们的支柱”。
来自塔布和阿库夫等表演者以及萨瑟利等制作人的压力,最终迫使唱片公司、行业和大众媒体放弃了”hillbilly”一词,转而使用更积极、更具包容性的”乡村音乐”。不过,新术语在二十多年后才被普遍采用;二战后以hillbilly为标题的歌曲,包括《乡巴佬天堂》和《乡巴佬热》都成为热门歌曲,乡村喜剧演员如霍默和杰思罗(亨利·海恩斯和肯尼斯·伯恩斯)通过使用乡巴佬服装和幽默来讽刺城市生活方式,建立了利润丰厚的职业生涯。尽管如此,到1960年代,从乡村音乐领域根除”hillbilly”一词的努力基本上成功了,只有国际hillbilly音乐歌迷俱乐部的期刊和通讯继续使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偶尔单独出现,或与摇滚乐的新音乐联系在一起,如”rockabilly”(乡村摇滚)音乐,或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早期的绰号”乡巴佬猫”。当然,普雷斯利和其他1950年代的乡村摇滚歌手,包括杰瑞·李·刘易斯和卡尔·帕金斯,与小提琴手约翰·卡森、煎锅舔手乐队和山地人乐队一样,都有着相同的南方工人阶级背景、喧闹的表演风格,以及音乐中真诚与幽默的混合。自1980年代以来,这个词卷土重来,被自称”传统”的音乐家如德怀特·约卡姆、马蒂·斯图尔特,甚至BR 5-49乐队大胆地采用,以区分他们纯正的”根源乡村”与1970年代轻松悦耳的”纳什维尔之声”或加斯·布鲁克斯和布鲁克斯与邓恩的”体育场乡村”。这个标签因此完成了一个轮回;曾经被用来贬低低俗的商业糟粕,并将其与”真正的”民间音乐区分开来,“hillbilly”现在恰恰象征着这种真实性。
在1934年11月的《时尚先生》杂志中,在展示穿着晚礼服的时髦年轻人的广告和关于纽约最新剧院演出的专栏之间,三个光着脚、衣衫不整、留着夸张胡须、戴着大帽子的男人懒洋洋地坐在一间乡村小屋的门廊上,前院杂草丛生,威士忌酒壶放在身边。“不知道妈生完孩子没有——我饿得很了,”其中一人在他们慵懒地等待消息时沉思道(图4.1)。保罗·韦伯的卡通系列就这样开始了,最终命名为《山地男孩》,每月在《时尚先生》上连载直到1940年代末,此后偶尔刊登直到1958年3月。《山地男孩》是同年首次亮相的三部以乡巴佬角色为主题的卡通/连环漫画之一。韦伯的作品、比利·德贝克对其连载漫画《巴尼·谷歌》的改编,以及阿尔·卡普新的联合发行作品《小阿布纳》,不仅是第一批主要描绘南方山区居民的连载卡通形象,也是第一批以南方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之一。这三部作品在几个月内相继问世,都是同一时期经济困境的总体情绪以及数十年来学术界和大众对农村民众——尤其是山区居民——兴趣不断扩大的产物,这种兴趣也推动了全国对”hillbilly音乐”的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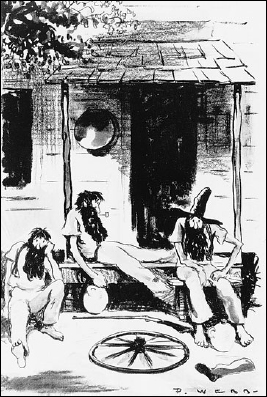
图4.1
《山里人》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知道妈生了没有——我饿得慌。”保罗·韦伯,《时尚先生》,1934年11月,第105页。本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与其他媒体对这一形象的使用一样,乡巴佬漫画和卡通反映了大萧条时期观众复杂的情感和态度。它们反映了公众对系统性经济和社会崩溃的普遍恐惧,以及每日关于南方农村困境的报道。然而,这些刻意夸张的贫困但基本满足的南方山民形象,也令人欣慰地表明农村贫困并不像新闻报道中那样凄凉。从愤世嫉俗的角度看,这些漫画和卡通提供了嘲笑他人不幸的乐趣,甚至印证了穷人因天生懒惰和无知而活该贫穷的观念。但它们有时也能反映出一种更为乐观的愿景:美国人民和美国精神在逆境中的坚韧。对某些读者而言,这些作品甚至可被视为对山民的民粹主义颂扬——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先驱的后裔,保留了殖民时代的生活技能和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乡巴佬角色拒绝以追求金钱为驱动的生活方式,珍视家庭、亲族和个人独立,或许可被视为拯救国家免受无节制工业城市化和不受监管资本主义双重威胁所需的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典范。虽然韦伯、德贝克和卡普的乡巴佬漫画和卡通在风格、内容以及艺术家对主题的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都利用了公众对山区文化以及山民在现代美国角色的多元且常常矛盾的迷恋。在此过程中,它们将图像化的乡巴佬形象符号化,从根本上塑造了此后所有对山区人民的描绘和观念。
通过他笔下三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托利弗兄弟(卢克、威利和杰克)及其家人和邻居的言行(或不作为),保罗·韦伯呈现了定义流行文化中乡巴佬形象的标准套路的无尽变体:社会隔离、身体迟钝和懒惰、粗俗的性行为、肮脏和兽性、滑稽的暴力,以及对现代性的完全无知。虽然这些都是熟悉的概念,但韦伯的描绘新颖之处在于,这些负面特质并没有被相应的神话般愿景所抵消——即将这些人视为坚韧的先驱者、骄傲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遗产的继承者。
除了已发表的作品外,保罗·韦伯生平的公开记录寥寥无几。他1902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中北部,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和欧洲接受了专业艺术训练。在为地方报纸和各种全国性杂志做了几年自由漫画家后,他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画乡巴佬,不久后又为《时尚先生》供稿,后者成为他此后二十年的主要发表平台。韦伯在开始创作《山里人》六个月后才首次踏足南方山区,也没有证据表明他阅读过当时已相当丰富的关于这一人群和地区的文献。相反,他的图像完全基于电影和期刊文学中对山民的流行观念,并经过自己的想象加工。正如他后来告诉一位记者的那样,他的作品”不是来自奥扎克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出自我自己的脑袋。”
乍看之下,这个充斥着邋遢懒汉和农村兽性的漫画系列出现在《时尚先生》这样一本刻意追求精致的出版物上似乎很奇怪。《时尚先生》本身是大萧条的产物,于1933年10月首次出版,旨在吸引其编辑阿诺德·金里奇所称的”被忽视的男性”——新兴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他们渴望获得世俗现代生活的产品和知识,但又不愿将自己主要定义为消费者(传统上被视为女性领域)。《时尚先生》巧妙地将女性杂志的形式(融合小说、插图和生活方式专题)与男性导向(在许多情况下是公然厌女的)视角相结合,将”高雅”文化与”低俗”的性驱动漫画和”海报女郎”相融合,首期销量达10万册,到1938年春季发行量已达75万册。
韦伯的漫画与杂志中的广告和高雅文化专题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大多数其他漫画截然不同——那些漫画大多描绘白人中上层城市男性与诱人年轻女性的故事。然而,它们并非看起来那么格格不入。与《Esquire》杂志中描绘城市工人阶级男女(通常被刻画为欧洲族裔或非裔美国人)的漫画类似,韦伯的作品常常呈现出过多的孩子和对现代性的普遍无知。不过,与那些身份围绕劳动和经济等级地位展开的工人阶级漫画人物不同,山地男孩的身份源于他们与真实的工作世界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完全脱节。在这方面,20世纪30至40年代《Esquire》杂志中与《山地男孩》最为相似的漫画,是那些描绘白人男性与美丽有色人种女性在南太平洋岛屿茅屋、爱斯基摩冰屋或阿拉伯后宫中的作品(图4.2)。虽然与这些强调白人男性对非西方女性的支配地位以及逃避家庭和经济责任的漫画并不完全相同,但韦伯对原始环境中乡野人物的刻画——以自然的主导地位和他们自身的本能冲动为特征——与这些描绘白人男性与诱人土著女性的漫画中的相同主题相呼应,清晰地反映出乡巴佬作为异域”他者”的比较性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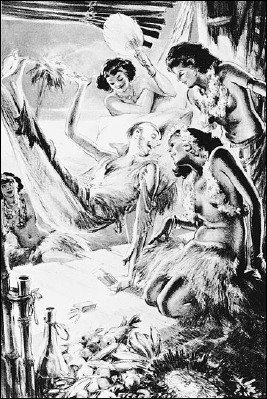
“然后我把锤子扔向了打卡钟”:《Esquire》杂志中数十幅展示白人男性逃离工作、老板和妻子、奔向原始天堂的典型漫画之一。埃弗雷特·希恩,《Esquire》,1934年8月,第80页。本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韦伯的漫画也反映了《Esquire》杂志创刊初期的主导主题——炫耀性消费、精致的性感和都市气质——恰恰因为《山地男孩》代表了《Esquire》理想的完全颠覆,存在于一个与杂志幻想世界完全隔绝的领域。文本中从未提及任何具体地点或地区,这一事实强化了这些人物生活在时空之外的神话之地的感觉。他们的隔绝如此彻底,以至于在1935年的一幅漫画中,男孩们对”胡佛不再是总统了”的”传闻”感到好奇,后来又对他们在一小片树林对面有邻居的”传说”进行猜测。这种绝对的隔绝自然导致他们对所有现代事物一无所知,从肥皂的正确使用方法(其中一个男孩说”见鬼——这味道太难吃了”)到汽车的安全驾驶(男孩们驾驶他们那辆老旧的T型车撞车是反复出现的视觉主题)。
由于与世隔绝,这些乡巴佬生活在一种动物性和肮脏的状态中。韦伯呈现了对正常社会秩序的荒诞颠覆:农场动物在小屋里吃住,而男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坐着,或者更常见的是躺在前院,手边放着威士忌酒壶。就像乔治·华盛顿·哈里斯笔下的萨特·洛文古德一样,韦伯的大多数笑话都围绕着半裸的身体和身体机能展开。数十幅漫画以老爷爷在户外厕所待太长时间为笑点,男性角色总是赤脚,经常只穿着长内衣。内衣尤其是韦伯作品中的核心符号。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它同时代表着贫穷和落后(他经常描绘穿着法兰绒连体内衣的男性和用面粉袋做内裤的女性);性化的身体(通过反复提及新生儿和过多的孩子来强化);以及不洁和永恒(因为一年一度的晾晒或更换内衣仪式是这些人物标记时间流逝的少数方式之一)(图4.3)。山民们愿意公开展示内衣也代表了他们缺乏社会礼仪和得体,这一主题在韦伯1939年的”圣诞节”作品中得到了典型体现,画面展示家中的男性(包括婴儿)透过门缝偷看”老奶奶”试穿新内裤(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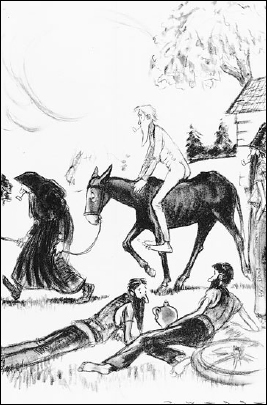
内衣的符号学:“天哪!时间过得真快——不是吗?老爷爷已经在晾他的冬季内衣了。”保罗·韦伯,《Esquire》,1936年6月,第54页。本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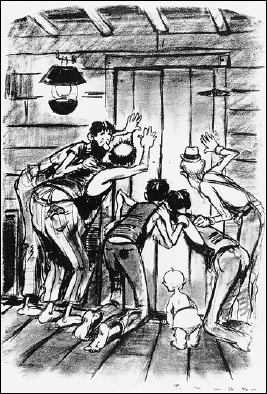
完全缺乏社会礼仪和得体:“你们该看看我们给老奶奶买的圣诞礼物——底边有蕾丝,后面有扣子。”保罗·韦伯,《Esquire》,1939年12月,第81页。本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韦伯频繁展示穿着内衣的男性形象,也凸显了他们的懒惰,与女性角色的辛苦劳作形成鲜明对比。在二战期间的一个典型例子中,一个男孩抱怨说,那些认定他们的骡子不适合服役的军队检查员,却忽视了农场上真正的劳动力:“太可惜了,他们没看到奶奶,”他对兄弟说道,而此时奶奶正费力地推着犁穿过贫瘠的田地。然而,尽管不停地劳作,韦伯笔下的乡巴佬女性却总是怀孕且多产——这些状况被单纯定义为又一项繁重的苦差事。从展示一位父亲担心他十二岁的女儿会成为老姑娘,到兄弟俩祖母所生的婴儿”拉夫叔叔”的出现,韦伯将女性以及由此延伸的男性都描绘成几乎具有超自然生育能力的人。关于父亲们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孩子、哪些是邻居的孩子的笑话比比皆是,而分娩被描绘成如此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男人们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女人中断无休止劳作的理由(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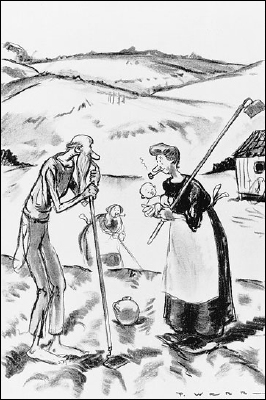
韦伯笔下的乡巴佬女性:苦役与多产的奇异结合:“哦——原来是这样——又一个小鬼!天哪——俺还以为你要出去一整天呢。”保罗·韦伯,《时尚先生》,1937年9月,第38页。此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除了通过反转手法呈现《时尚先生》早期的核心主题外,韦伯的漫画也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关于南方社会和文化的强大新神话的视觉体现。历史学家乔治·廷德尔后来将其称为”蒙昧的南方”——一个以堕落的文化、压迫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惊人的不平等以及普遍贫困为特征的社会。这一重新概念化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战前南方是由庄严种植园和文化精致构成的田园社会的观点,是关于现代美国本质的更广泛斗争的结果之一。这场斗争是美国从一个以地方化商业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向一个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特征的国家转变的一部分。“湿派”与”干派”之间的争论、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吸烟或剪短发的争论,以及关于地方和地区身份作用的争论,都是对乡村性和传统生活方式在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中应有地位的普遍质疑的一部分。
这一南方重新定义的关键人物是H·L·(亨利·路易斯)门肯,《巴尔的摩太阳报》专栏作家,以及《聪明人》和《美国信使》等有影响力杂志的编辑。在他关于南方社会和文化的众多著作中,尤其是他那篇夸张的批评文章《博扎特的撒哈拉》中,门肯哀叹内战期间战前南方贵族的消亡,以及随后由”贫穷白人垃圾”主导的社会的出现,这些人的血管里流淌着”西欧最糟糕的血液”。1925年在田纳西州代顿——坎伯兰高原丘陵地带——举行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为门肯提供了一个嘲讽南方农村人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山区居民。对门肯来说,生活在代顿周边的农村人是”来自高地山谷的目瞪口呆的灵长类动物”,他们”大汗淋漓,不受卫生习惯的约束”。
门肯关于猿猴的比喻暗示山区人民不仅不文明,而且在进化上比城市美国人更落后,这与当时关于山区落后的”科学”研究相呼应,最著名的是曼德尔·谢尔曼和托马斯·亨利的《山谷居民》(Hollow Folk)(1933年)。这是一项关于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五个社区的研究,作者们将这项工作构想为追溯”人类从原始生活方式到现代社会秩序的漫长旅程”的努力。他们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最落后的社区——科尔文山谷(Colvin Hollow),描述了一个充满动物性和肮脏的地方,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脸上”爬满苍蝇”,躺在一张”脏布床”上,“自他出生以来就没有’换过’”。尽管后来的学者对这项研究的预设和方法论提出了质疑,但这份据称科学的报告强化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山民野蛮的观念。它也与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尤其是厄斯金·考德威尔等有影响力的作家对南方贫穷白人(无论是在山区内外)的类似文学描绘相吻合。
虽然韦伯对山地乡民的不雅描绘总体上不如门肯、考德威尔和一些社会科学家那样刻薄,但在少数情况下,他也呈现出这种更阴暗、道德更堕落的山区社会形象。他1940年11月的总统选举漫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图4.6)。山民们排队在户外厕所投票这一事实本身就够贬低人的了,但画中关于”双头表亲”的妙语显然暗示了近亲繁殖(如果不是乱伦的话)。可能更具冒犯性的是韦伯少数几幅以狗脸人巴尔多叔叔为主角的漫画——据推测是人与犬类性接触的产物——他能像猎犬一样把浣熊追上树,还曾在嘉年华表演中待过。韦伯创作这些漫画的确切意图仍不清楚,但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这些画作意在表现这些角色与彻底的兽性相去无几。这种关于危险的近亲繁殖和愚蠢山民的概念在1930年代的公共话语中越来越普遍,不仅出现在《空谷之民》(Hollow Folk)中,也出现在流行的医学期刊中。例如,1936年一篇关于弗吉尼亚州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家族的文章认为,近亲繁殖和乱伦创造了一整个由智力低下的男女组成的社区。对一个住在”单间小屋”里的家庭的描述几乎与卢克和他的兄弟们完全吻合:“房间里有三个成年男孩,都是白痴,都是私生子,其中一个醉醺醺地躺在肮脏的床上。房间里没有一个正常人。”但韦伯将这样的场景描绘成荒谬可笑的喜剧,而作者杰克·曼恩则将这种情况视为需要采取激烈应对措施的社会危机。“鉴于目前医学科学在治愈这些精神疾病方面的不足,”曼恩总结道,“唯一的替代方案似乎是通过绝育来防止进一步繁殖。”

图4.6
近亲繁殖和社会退化的暗示:“莱姆·霍金斯答应带他的双头表亲一起来……那就是三张选票了。” 保罗·韦伯,《时尚先生》,1940年11月,第56页。此艺术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如果针对其他美国亚群体,即使是少数族裔和贫困群体,暗示这种兽性的漫画肯定会引起强烈抗议,但在《时尚先生》的”读者来信”栏目中没有明显的公众抗议。这种沉默可能部分表明读者不愿公开讨论像漫画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也表明许多读者——主要是自我定义为都市世界主义者的人——显然将这些图像视为夸张的,但本质上是对南方贫穷白人的真实写照。大多数人似乎认同一位男士的观点,他写信为《时尚先生》此前发表的厄斯金·考德威尔短篇小说中对南方贫穷白人的描写辩护,并得出结论说,显然没有讽刺意味:“贫穷的白人在他们所有的肮脏中似乎足够快乐,所以我们不妨让事情保持原样。”
杂志编辑通过将韦伯的漫画与杰西·斯图尔特的作品并排放置,强化了韦伯对山民的描绘是基于事实的感觉。斯图尔特是肯塔基州东部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巴拉契亚经历的重要评论者。作为《时尚先生》早期的常客,斯图尔特创作了对”永恒的肯塔基山丘”男女的深情描写,不仅强调了他们粗犷的拓荒方式和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强调了他们缺乏正规教育、暴力倾向、从私酿酒到民间偏方的独特文化习俗,以及与现代文明的隔绝。韦伯漫画与斯图尔特短篇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鼓励读者将两者都视为有些牵强,但本质上是对同一山区民众的准确描绘。
这种准可信性以及韦伯的标准描绘(除了少数显著例外)——无知且无可救药地无能但基本上温和的灵魂,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使他的作品在大萧条时期广受欢迎。尽管经历了无尽的洪水、风暴、火灾和人为灾难,卢克和他的亲属们以媒体学者杰里·威廉姆森所说的”平静的泰然自若和韧性”冷静地忍受着他们面临的所有危机(图4.7)。在这方面,当代观众可以将他们视为人类耐力的典范,以及国家也能度过当前经济和社会动荡的令人振奋的象征。

图4.7
在大萧条中,一种平静的韧性和令人振奋的耐力: “俺想俺们最好在又开始下雨之前把爹叫醒——他在那边那棵树底下。”保罗·韦伯,《时尚先生》,1938年10月,第53页。此艺术作品版权归其所有者(如适用),仅用于历史和学术说明目的。
韦伯的漫画在整个二战期间及战后时代一直广受欢迎,他还制作了一系列成功的广告商赞助日历,展示他的艺术作品。然而,到1940年代末,他的吸引力开始减弱(1948年《Esquire》内部备忘录警告说,公司能够”卖掉那年印刷的5万本日历就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他与大卫·斯马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马特的关系日益冷淡——这两位杂志的所有者兼出版商于1945年接任编辑。在与韦伯进行了长期的法律纠纷后,《Esquire》的新管理层于1948年11月得出结论:“保罗·韦伯对《Esquire》来说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他的漫画随后不久便被停刊。尽管韦伯在1950年代初开始零星地为杂志重新投稿(在大卫·斯马特去世、阿诺德·金里奇重新担任编辑之后),但到1950年代末,金里奇和他的编辑委员会认为韦伯的山地人形象已不再引起杂志目标受众——年轻男性——的共鸣,于是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漫画家和作家一起被解雇,因为杂志正准备帮助开创196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
与1934年全新创作的《山地男孩》和阿尔·卡普的《小阿布纳》不同,《斯纳菲·史密斯》是从比利·德贝克已有十五年历史且非常成功的连环漫画《巴尼·谷歌》中发展而来的。德贝克1890年出生于芝加哥,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接受专业训练,凭借巴尼·谷歌和他那匹可怜但可爱的马”火花塞”、他对奇幻对话的精湛掌握,以及他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异国冒险连续剧情而变得富有。因此,当读者在1934年6月14日的那一集中得知巴尼·谷歌被”一个名叫谷歌的山地人(hill-billy)“指定为北卡罗来纳山区一处庄园的唯一继承人时,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线将持续接下来的十年,而且巴尼最终几乎完全被更加离谱的角色斯纳菲·史密斯所取代。
这一漫画情节的变化远非仅仅是为了迎合当时对山地事物的狂热,而是揭示了德贝克对南方山区人民和文化的文学描绘的热情和持久兴趣。与韦伯和卡普不同,德贝克阅读了数十本关于山地居民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小说及非虚构书籍,他对早期南阿巴拉契亚和山民形象塑造者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他深受玛丽·默弗里和乔治·华盛顿·哈里斯作品的影响,他的《萨特·洛文古德》(Sut Lovingood)副本上有大量注释,还包括他对斯纳菲·史密斯的初步草图。他还大量借鉴了哈里斯和其他西南幽默作家使用的语言和拼写方式,像他们一样自由地将真正的地方表达与他自己发明的表达混合在一起。尽管德贝克曾穿越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山区,与当地居民交谈,但他奇幻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措辞表明,他和韦伯一样,显然主要是根据这些文学记载而非人民和实际情况本身来构建他的形象和幽默。
德贝克还依赖许多与他的文学前辈相同的比喻和主题。在山区故事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将山民描绘成贫困的(谷歌的”庄园”不过是一间破旧的棚屋,与该地区其他住所类似);无知的(谷歌对没有学校或幼儿园表示震惊);以及文化上与世隔绝的(在一幅名为”追赶历史!“的漫画中,一位担任巴尼女仆的山区妇女从未看过电影,但听说D·W·格里菲斯正计划执导新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在他最具戏剧性的画面中,他将山民呈现为一种几乎超自然的原始暴力潜在力量,从周围的树林中自发涌现(图4.8)。

图4.8
山民作为一种威胁性的、有机的自然力量。《巴尼·谷歌》,“巴尼输掉了争论!”(局部),1934年6月18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斯纳菲·史密斯,这个矮壮而暴躁的山民很快就主导了这部漫画,他体现了这些特质。他对所有现代事物一无所知,靠私酿威士忌和偷鸡偷马勉强维生,对所有来者都以他那把无处不在的松鼠步枪相威胁。他对社会礼仪和稳定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连他在胡廷霍勒(Hootin’ Holler)的山民同胞都惧怕和鄙视他——德贝克告诉读者,上次他出现时,他们给他涂了柏油粘了羽毛(图4.9)。史密斯显然是根据早期虚构和真实人物塑造的,如戴维·克罗克特、萨特·洛文古德和”魔鬼安斯”哈特菲尔德。他的妻子洛维齐警告说:“在他的酒和恶作剧之间,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给他留足空间。”在这个与世隔绝、一触即发的原始人形象之上,德贝克又加入了韦伯式的绝对懒惰愿景。斯纳菲经常被看到躺着或睡着,他的威士忌酒壶清楚地暗示着他永久的醉酒状态。和韦伯一样,德贝克的笑话经常围绕着斯纳菲一睡就是好几天展开,尽管周围不断有活动和噪音。

图4.9
Snuffy和Lowizie Smith的首次登场。《Barney Google》,“不速之客!”(局部),1934年11月19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与Webb和Capp一样,DeBeck强调了懒惰无用的乡巴佬男性与他们过度劳累、社会地位低下的妻女之间的戏剧性对比。DeBeck笔下的山区女性主要以长期受苦的Lowizie为代表,她们完全被工作所定义,将家务劳动视为人生唯一目的。因此,Lowizie醒着的每一刻都在打扫房屋、准备饭菜和照料农场。即使住在豪华酒店,她也忍不住继续做家务,无论这多么毫无意义(图4.10)。DeBeck还不断将Lowizie描绘成完全顺从丈夫的形象。尽管Snuffy对她呼来喝去、与其他女人调情、一连数月抛弃她、几乎不给她任何关爱,她仍然坚定地忠于他,甚至为他的家暴行为承担责任(图4.11)。在Snuffy二战期间服役离家数年后,她甚至催促来访的Barney Google穿上Snuffy的旧衣服,拿着棍子追着她跑,而她则高兴地喊着”是的,老爹!!……多美好的回忆啊!!!“这些形象很容易融入关于破坏性山民父权制的悠久叙事传统,这种传统通过女性的从属地位来定义该地区的落后。

图4.10
甘愿做苦工的乡巴佬女性。《Barney Google》,“Lowizie忙个不停!”1935年11月28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图4.11
Lowizie Smith作为接受女性从属地位的象征。《Barney Google》,“纯粹的真相!”1935年4月9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Snuffy Smith可能不道德、暴力、懒惰且有虐待行为,但他也代表了以Crockett和Boone为典型的神话边疆人所具有的反精英态度、粗犷独立和强健体魄。DeBeck经常将Snuffy描绘成普通人的象征,拒绝任何文化修养和品味的矫饰。在芝加哥访问时,他仅凭名字就拒绝入住”贵族酒店”。相反,他去了牲畜围场旁的廉价旅馆,但仍然指责女房东经营”贵族酒店”,因为她试图两周后换床单。显然,这些情节叠加了山民肮脏的观念,但反抗阶级矫饰的主题是明确无误的。作为边疆民主的象征和捍卫者,Snuffy拒绝向法官、军官和其他权威人物卑躬屈膝,将个人独立和文化传统置于金钱之上。他对社会规则的持续蔑视也使他成为某种性感符号,女性角色为他粗犷的个性而兴奋。“我每晚都梦见你,”漫画中一位女性崇拜者写道,“你的山野粗犷——你强势的个性——你对社会的蔑视。”简而言之,Snuffy是按照美国民间英雄的模式塑造的,这一点至少被一位当代作家Lovell Thompson清楚地理解,他在1937年称Snuffy为”一个拥有英雄全部装备的英雄”。Thompson认为,虽然对Snuffy来说,这些装备是”一顶破旧的肯塔基上校帽、一支玉米芯烟斗和一支从James Fenimore Cooper那里借来的步枪”,而不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和盾牌”,但它们的意义”在深刻性和严谨性上堪比希腊神话”。Thompson对Snuffy作为神话英雄的描述既诙谐又严肃,认识到DeBeck如何不断利用和颠覆山民神话,充分实现了高贵山民与半野蛮乡巴佬这一相互支撑的二元性中的喜剧可能性。
Snuffy作为神话边疆民间英雄化身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他毋庸置疑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或至少是北欧血统。在三位主要的乡巴佬漫画家中,DeBeck最明确地强调了他笔下人物的”白人性”,将他们与非裔美国人角色的标准刻板印象直接对比。Webb从未描绘过除乡巴佬以外的任何人,Capp几乎从未包含黑人形象,而DeBeck则延续了他长期以来的做法(与许多二十世纪初漫画家的做法相呼应),将黑人角色描绘成白人美国的仆人。作为搬运工、女仆、马夫和其他体力劳动者,这些角色充当了老练白人角色的朴实而迟钝的喜剧陪衬,在《Snuffy Smith》中,甚至是卑微山民的陪衬。虽然许多有地位和权威的角色(商人、银行家、法官、律师)通常称呼Snuffy和他的亲属为”乡巴佬”、“土包子”,甚至有一次称为”穷乡僻壤的垃圾”,但黑人角色几乎从不称呼他为”先生”或”老板”以外的任何称呼。Snuffy展现其白人身份最戏剧性的例子是他对一名黑人门卫要求他离开私人俱乐部时的暴力反应,画面既生动又怪诞(图4.12)。在这样的画格中,DeBeck通过Snuffy对非裔美国人形象的支配,明确地宣示了Snuffy的白人身份,这一特质旨在减轻其角色中的贬低方面,并强化他作为神话英雄的角色。

图4.12
斯纳菲·史密斯生动地展现他的白人身份。《巴尼·谷歌》,“卧底”(局部),1937年2月18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尽管德贝克的作品部分反映了门肯、考德威尔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韦伯笔下”愚昧南方”的形象,但它或许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更为乐观的反向视角——歌颂南方乡村居民,尤其是山区居民的独立精神和传统生活方式。这一观点得到了一群多元化观察者的支持,他们质疑日益机械化、预制化和集中化的现代美国所带来的后果。对于这些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乃至政府官员而言——他们被统称为地方主义者(Regionalists),因为他们将文化、民族和地理上独特的次区域视为美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要恢复美国最初的承诺,就必须重新发现和颂扬”民间大众”。无论是被定义为十九世纪”开拓大平原”的先驱,还是当代的美洲原住民、前奴隶或中西部农民,在地方主义者看来,“民间大众”体现了拯救国家免受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现代性腐蚀”所必需的文化价值观和简朴而诚实的生活方式。
山区居民在这场强调与土地合一、逃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束缚的文化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24年,剧作家珀西·麦凯为城市中产阶级读者撰文,阐述了他对山区社会前景的构想:
在那边的山里,有些人不住在笼子里;有一百万美国人,他们不追逐金钱,不为机器卖命,不从电影里学习礼仪,也不从美容院里获取文化。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急于去”教化”他们——把他们肮脏的木屋改造成干净的水泥笼子?还是我们应该探究一下,他们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给我们这个崭新的文明——某些我们曾经珍视但如今或许已经遗忘的东西?
山区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这一理念远远超出了地方主义运动的范畴,尤其是在本土主义复兴和移民限制的时代。山区人民被无休止地宣传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拥有”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继续过着几个世纪前祖先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整个文化光谱中被呈现为一种”原初民众”。南方山区居民频繁出现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新闻报道中,从共产主义者和当地民谣歌手如”莫莉·杰克逊阿姨”为宣传”血腥”哈兰县暴力煤矿罢工所做的努力,到关于童婚和”迷信”宗教习俗的反复报道,再到关于该地区众多新政机构活动的报道,包括重新安置管理局、农业安全管理局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这种对南方山区及其人民的迷恋延伸到美国”中产文化”的各种形式,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量关于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山区偏远地区人民的非虚构书籍、杂志文章和短篇小说,到1928年至1934年间举办的众多民间音乐节,展示据称仍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美国角落传唱的纯正伊丽莎白时代民歌和民谣。
尽管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声称呈现”真正的山区居民”,但几乎所有作品都将其描绘对象塑造成完全与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隔绝的浪漫原始人。为了更好地将其描绘对象定义为永远停留在过去的人群,他们淡化或更常见地直接忽视了该地区在种族、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以及市场力量对当代山区居民的影响。有时,这种对现实的扭曲甚至更加刻意。摄影师多丽丝·乌尔曼鼓励她的拍摄对象穿上祖母的粗毛呢(linsey-woolsey)连衣裙,周围摆放着古董纺车和织布机,然后将这些照片作为当代山区居民的真实写照进行展出。这些作品还倾向于将所有南方山区人民和地点视为可互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查尔斯·莫罗·威尔逊的《美国偏远地区》,这本书讲述的是欧扎克山区的人民,却配以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和田纳西州东部山区的照片作为插图。漫画家和电影制作人很快也接受了这种将所有南方山区融合为单一神话空间的做法。
受地方主义视野的明显影响,德贝克的艺术同样反映了对山民和山区文化的赞美与扭曲的混合。一方面,他对山区社会的描绘比同时代任何人都更加丰满和自然。与韦伯和卡普不同——他们的文本基于杂耍表演和电影中南方(而非山区)方言的标准刻板印象——德贝克在作品中使用了数十种山区表达方式,如”plime-blank”(意为”正好”)和”a lavish of”(意为”很多”)。他甚至通过在文本中加入简短的术语定义,向读者介绍不熟悉的山区表达方式(图4.13)。他并非严格追求方言使用的绝对准确性,而是自由地将自己的表达与真实的山区俗语融合在一起,创造了诸如”discombooberated”(后来演变为”discombobulated”,意为”困惑的”)、“time’s-a-wastin’”(意为”时间在流逝”)、“a leetle tetched in the haid”(意为”有点神经不正常”)、“bodacious”(意为”大胆的”)和”balls o’ fire”(意为”天哪”)等著名新词。尽管如此,即使是他创造的短语,对许多无法区分真实和虚构短语的读者来说也颇具真实感。例如,1940年一位记者在介绍德贝克漫画中的著名短语列表时,称其为”山民俚语(真实的和其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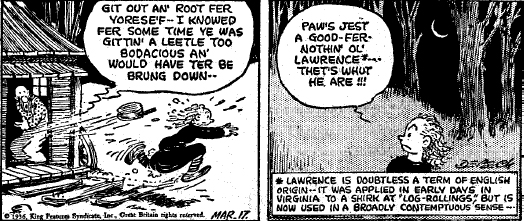
图4.13
德贝克在漫画中融入真实山区表达方式的例子。《巴尼·谷歌》,“离家的羁绊”(局部),1936年3月17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德贝克对山区社会的描绘也比他的同行更为准确和富有同情心。他的木屋、纺车和服装都基于南方山区相关文献中的照片和描述,主要目的是展示一种朴素但体面的生活方式,而非扭曲地呈现野蛮社会的贬损形象。与漫画和电影中典型的由奇形怪状的管道和加压锅炉组成的”蒸馏器”不同,德贝克描绘了更准确的酿酒设备,由橡木桶和木管连接而成。他那些图形精美的社区民俗全景图占据整个画格,反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互动的社区,妇女们给孩子洗澡、晾晒衣物、分享最新的闲话(图4.14)。与韦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韦伯笔下的人物几乎不交流——德贝克的画格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对话,他的角色似乎真正在倾听彼此,而不仅仅是在抛出笑料台词。此外,德贝克在他笔下青少年山区恋人之间、斯纳菲和巴尼之间,甚至斯纳菲和洛维齐之间萌芽的关系中传达了真挚的情感和感染力。

图4.14
德贝克描绘充满活力的山区社区的活人画(tableaux vivants)示例。《巴尼·谷歌》,“山民闲话!”1934年7月3日。© King Features。经King Features Syndicate特别许可转载。
最后,德贝克与同行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山区人民及其文化如何同时被流行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挪用和贬低。他的故事情节经常涉及电影、戏剧和文学中对山区生活的扭曲描绘。在一个这样的例子中,他通过展示衣着光鲜的观众观看一部以山区为背景的夸张情节剧,并以一种语言”猎奇”的方式采用演员们丰富多彩的语言,来说明古朴民俗对精致都市观众的吸引力。在另一集中,德贝克展示了一家好莱坞制片厂秘密拍摄斯纳菲与其死敌之间的世仇,却不给这些”演员”任何报酬。他甚至暗示了山区居民对那些记录他们所谓异国情调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外来者的不满。当一位作家拜访斯纳菲·史密斯为”山民小说”收集素材时,斯纳菲向镇上的同乡隐瞒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并警告他:“俺觉得最好别告诉他们你是那些’写字的家伙’之一……对他们来说,你会比鼹鼠还低贱——”
然而,德贝克对山民流行形象的批判以及他对山区生活描绘的真实性不应被过分夸大。作为漫画家,德贝克的首要关注点始终是娱乐而非文化教化,他在构建公众对南方山民作为卡通化人物的广泛认知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他还在将欧扎克(Ozark)和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n)的背景自由融合成一个神话般的地理位置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漫画最初设定在北卡罗来纳山区,但早期一集中的角色提到从附近的大城市”小石城”订购成衣——实际上,那里在西边600多英里之外。一个月后,赛丽·霍普金斯从胡廷霍勒逃跑,在树林里游荡三天后到达”阿肯色州水晶泉”。这种地理混乱表明,山民形象的创造者和阅读公众都愿意接受将数百英里的距离和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成一个同质化的幻想山区南方——这一过程在阿尔·卡普的作品中只会加速。
此外,尽管DeBeck多次提到媒体对山民的利用,但他从未暗示过真实山民生活中发生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变革。与Webb和Capp笔下的乡巴佬一样,DeBeck的角色基本上处于其”山谷”边界之外的更大经济体系之外。他没有承认采掘业(如煤矿开采或伐木业)的存在,也没有提及纺织厂的兴起——这些产业共同导致了数千人流离失所,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南部山区男男女女的生活。读者也无法从这部连环画中感受到1930年代席卷该地区工厂城镇的野猫罢工浪潮。尽管如此,与同时代的其他作者不同,他确实(至少在最初)呈现了一个相对可信的山区社区,在那里男女共同耕作土地、养育家庭,并在社会和经济上相互联系。
尽管(或者正因为)DeBeck对南部山区生活和社会的描绘比几乎所有其他流行形式都更加完整,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更高的读者人气。相反,他的雇主King Features Syndicate敦促他”淡化”他”如此忠实描绘的氛围”。Fred Lasswell曾协助DeBeck工作,并在1942年DeBeck去世后接替了他,他后来回忆说,“地道的山区方言”对”普通平原居民来说相当难以阅读和理解”。尽管DeBeck努力尝试远离山区背景和方言,但连环画的人气仍在持续下降。当Lasswell在1940年代初接手这部连环画时,King Features Syndicate的负责人Joe Connolly告诉他:“Billy失去了很多客户报纸,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停刊。”Connolly敦促Lasswell”最初保持相同的整体外观和风格”,然后”逐渐注入你自己的想法和角色”。Lasswell正是这样做的,几乎完全放弃了Barney Google,并增加了Snuffy家族和社区的新成员。他还放弃了地道的方言,转而遵循”保持乡土气息,带点乡村腔调”的原则来扩大读者群。他还基本放弃了长篇连载故事,转而采用每日视觉笑话和俏皮话。讽刺的是,尽管连环画越来越聚焦于Snuffy Smith和他的山区环境,Barney Google几乎消失了,但它对乡巴佬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描述却越来越少,反而变成了对美国乡村生活的一种温馨而笼统的想象。
在1930年代及之后渗透流行文化的所有乡巴佬形象漫画家中,Al Capp无疑是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鼎盛时期,《Li’l Abner》被美国近900家报纸和海外另外100家报纸转载——总发行量达6000万份,这使Capp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漫画家(1947年估计年收入为25万美元)。Capp的漫画登上了《Life》和《Time》杂志的封面;引发了全国性的Sadie Hawkins Day舞会现象;衍生出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两部电影和一个主题公园;并在普通报纸读者和知识精英中都广受欢迎。然而,尽管(或者正因为)它如此受欢迎,《Li’l Abner》却是同类主要漫画中最不聚焦于乡巴佬形象的一部。相反,Capp将他的山村Dogpatch作为一个奇幻背景,用于讲述揭露他所认为的人类贪婪和残忍的道德故事。他呈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和主题,将社会和政治讽刺与冒险故事以及对名人和时事的戏仿混合在一起。他的角色阵容同样多样,包括Yokum一家(Li’l Abner和他的父母Mammy [Pansy]和Pappy [Lucifer])、Daisy Mae Scragg(Abner数十年来的美丽追求者),以及看似无穷无尽的离奇人物,仅Dogpatch本地人就包括:巡回传教士Marryin’ Sam、极其凶恶的Scraggs家族、魁梧的Earthquake McGoon、留着浓密胡须的Hairless Joe和他的印第安搭档Lonesome Polecat,以及Moonshine McSwine和他肮脏但惊艳的女儿Moonbeam。事实上,《Li’l Abner》包含了如此丰富的角色和思想,以至于难以概括。然而,尽管Capp的故事线经常偏离主题,他的乡巴佬背景仍然是一个核心基石,既是更广泛美国社会的缩影,也是其扭曲的哈哈镜。
Capp早年生活的具体细节和《Li’l Abner》的起源很难确定,主要是因为Capp总是愿意为了讲好故事而添油加醋。尽管如此,一些事实是已知的。Capp原名Alfred Gerald Caplin,1909年9月28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在这座城市和其他东北部城市(包括布里奇波特、布鲁克林和波士顿)度过了工人阶级的童年。他后来对青年时期的重新叙述以两个核心事件为特色:十岁时在一次电车事故中失去一条腿,以及青少年时期与一位童年好友搭便车穿越南部山区的旅行。Capp和他的发行商United Features后来将后一事件视为他漫画连载的灵感来源,坚称Abner和他的家人是基于Capp曾与之共度时光的真实山民。然而,这两个男孩从波士顿到孟菲斯旅程的短暂性以及Capp有限的行动能力,都让人怀疑这种相遇的可能性。
《Li’l Abner》更可能的灵感来源是以南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山区为背景的电影、卡普童年时读过的小约翰·福克斯的小说,尤其是他大约在1933年在纽约看到的一场乡村喜剧杂耍表演。卡普的妻子后来回忆道:
我们去了哥伦布圆环的一家杂耍剧院。其中一个节目是乡巴佬表演。四五个歌手/乐手/喜剧演员在台上拉着小提琴、吹着口簧琴(Jews harps),还跳了一小段踢踏舞。他们站得很僵硬,面无表情,用南方口音单调地说话。我们觉得他们太搞笑了。那天晚上我们走回公寓的路上,对创作一部乡巴佬漫画的想法越来越兴奋。
无论这场表演是直接启发了《Li’l Abner》还是只是众多影响之一,卡普确实在他参与创作的第一部漫画——哈姆·费舍尔的《Joe Palooka》中加入了乡巴佬角色。在1933年费舍尔度假期间卡普创作的一系列情节中,帕卢卡冒险进入肯塔基山区,被人用枪逼迫与身材高大、愚笨的山民”大利未”进行一场不公平的拳击比赛。粗鲁、暴力、令人讨厌的利未和他的家人更像卡普笔下好斗的斯克拉格斯一家,而不是纯洁善良的约库姆一家,但这些情节清楚地反映了卡普对使用乡巴佬角色日益增长的兴趣。这些情节刊出后不久,卡普与费舍尔不欢而散,离开时带走了他创作乡巴佬漫画的想法。《Li’l Abner》的开局并不顺利;到1934年8月13日首次刊出时,只有八家报纸订阅了这部漫画。然而它的人气增长如此迅速,仅仅一年后就有102家报纸刊载这部漫画。
《Li’l Abner》的流行反映了报纸漫画版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一趋势与整个面向大众的娱乐产业在这些经济困难年代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相呼应。到1930年代初,美国漫画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文化现象。1933年,70%到75%的报纸读者定期阅读漫画,全国几乎每家主要报纸——共计2300家——都刊载日报或周日漫画版。两大周日漫画增刊——赫斯特旗下的《Comic Weekly》和《芝加哥论坛报》的《Metropolitan Sunday Newspaper》——覆盖了全国主要城市近一千万户家庭,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广告媒介,每页广告费在16000到17000美元之间。漫画利润丰厚,即使在1935年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漫画产业的年总收入估计仍有六七百万美元。
各辛迪加大力宣传漫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新闻》辛迪加在1935年宣称:“漫画今天正在崛起!……我们建议报社老板和出版商用审视发行量、广告和总收入的同样精明眼光来评估潜在漫画采购的收益——因为这些搞笑创作者与这些数字密切相关。”漫画数量和总发行量的稳步增长表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多么依赖幽默——尤其是那些颂扬普通人简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形式——来应对经济危机。无论是广播节目《Fibber McGee and Molly》还是《Lum and Abner》(后者以虚构的阿肯色州松岭山村为背景)、乡村音乐谷仓舞会,还是威尔·罗杰斯的专栏和舞台表演,这些对小镇居民令人安心的朴素生活方式的描绘都极受欢迎。卡普的故事情节不像这些其他作品那样是对乡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颂歌,但至少在最初,它们确实赞扬了普通人的美德,并体现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富人的敌意。
为了回应漫画读者对戏剧性连续故事日益增长的兴趣,这部漫画早期的大部分情节都巧妙地融合了冒险故事和荒诞喜剧。正如卡普后来在职业生涯中解释的那样:“如果一种观点可以被称为某种简洁的公式,那么我创作《Li’l Abner》的公式就是把喜剧角色扔进情节剧般的情境中,展示他们用头脑简单的方式解决可怕的困境。”典型的早期情节包括约库姆一家与银行劫匪、绑匪、富有的女继承人和疯狂科学家的冲突。卡普对狗窝镇社区及其周边环境的描绘同样充满幻想色彩,从未打算真实地描绘山区生活和状况。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不想把东西画得正确……我想把它们画得看起来大致像它们应该的样子。”尽管如此,他被广泛认为是南方山区的权威,尽管他本人否认,所有证据也与此相悖。评论他作品的人参与推广卡普的专家形象——即使他们同时否认这一点——暗示他在《Li’l Abner》中的描绘,就整体而言(如果不是在细节上),是准确的。因此,《纽约客》的专栏作家小E·J·卡恩在1947年强调,卡普”与偏远山区的短暂接触”是他对这个地区”唯一的第一手了解”,而”他现在被全国公认为这方面的专家”,但在下一句话中又辩称,这次短暂的旅行足以让卡普”吸收整个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
他描绘的不真实性体现在Dogpatch居民夸张的南方通用方言,以及山顶长满松树而非落叶树的景象。从地理上看,Dogpatch属于一个神话般的南方,一个山脉与沼泽相邻的地方,洞穴和岩洞绵延数英里,从阿巴拉契亚山丘出发步行两天就能到达西南沙漠。虽然Capp最初将Dogpatch设定在肯塔基州,但后来他把这个社区搬到了奥扎克山区,这一变动在漫画中从未解释,媒体也从未评论。与DeBeck相比,Capp更进一步地将相隔数千英里的各种南方景观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神话空间。
Capp对南方山区生活的描绘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忽略了南方文化的核心方面,如有组织的宗教、内战持续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后者的缺失主要是对所有报纸辛迪加避免潜在争议话题或社论评论这一要求的回应,也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但错误的大众观念,即南方山区历史上是一个没有黑人、种族敌意和奴隶制的地区。但Capp排除黑人角色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这部漫画中的山民取代了其他漫画和整个大萧条时代流行文化中的黑人角色;他们是滑稽的小丑、大城市里的乡下傻瓜、社会地位较高的白人雇主的仆人,或者像凶残的Scraggs家族那样,是威胁社会秩序的野蛮人。
Capp在《Li’l Abner》最初几年最明确地描绘了Yokum一家的文化和种族”他者性”。他很少关注山区背景,几乎所有最初的情节,以及头几年近一半的故事,都发生在Dogpatch之外,最常见的是纽约市。这些场景的主导主题是阶级和社会冲突。从第二个情节开始,Abner被他的暴发户姑妈——Bopshire公爵夫人Beatrixe(原名Bessie Hunks)——邀请到纽约,让他”享受财富和奢华的所有好处”,Capp反复对比了Abner及其家人的单纯天真和非物质主义与上流社会的势利、贪婪和自负。基于图形艺术中长期确立的传统——面相反映内在人格——Capp通过Abner的英俊外表和强健体格体现了他的道德纯洁。他阳刚的外表加上完全的天真,使Abner能够与上流社会交往,并在视觉上”冒充”为”白人”,就像在法定种族歧视时代,肤色较浅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进入全白人场所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白人身份不仅意味着”正确”的肤色,还意味着在”正确”群体中社会同化的潜力。Abner受到上流社会女性的追求(她们被山区居民所代表的原始性吸引),许多纽约上流人士甚至欣赏他古怪的方言和缺乏社交礼仪,将这些特质解读为不是无知和贫穷的标志,而是一种可爱的不做作(图4.15)。

图4.15
Li’l Abner不知不觉地讨好纽约上流人士。Al Capp,《Li’l Abner》,“We All Understand One Another”,第16条,1934年(局部)。由Capp Enterprises, Inc.和Denis Kitchen Art Agency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但所有其他来自Dogpatch的角色都过于明显地散发着他们身体、文化和社会的”他者性”,无法冒充受人尊敬的主流阶层”白人”成员。当Abner的父母穿上正式晚礼服参加Sneerworthy夫人游艇上的派对时,他们无法融入其中,反而成为Capp已经夸张的最富有阶层代表的荒谬漫画形象(图4.16)。表面上,Capp在这一情节中的主题是Yokum一家扭转了精英阶层的傲慢。但Pappy和Mammy可笑的服装和猿猴般的姿势使他们看起来比被嘲讽的角色更加滑稽,突出了他们作为白人”他者”的地位。就像其他美国插画家将他们认为威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群体——如19世纪末的爱尔兰移民、城市黑人和二战日本士兵——描绘成类人猿一样,这些形象基于所谓的关于人类进化阶段的科学理论,Capp对其角色的猿猴化借鉴了当代关于南方山民原始性的社会科学文献。

图4.16
穿着可笑的猿猴般的Yokum一家。Al Capp,《Li’l Abner》,“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局部),1936年2月5日。由Capp Enterprises, Inc.和Denis Kitchen Art Agency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正如游艇派对故事所示,这些早期情节往往带有明显的平民主义色彩,阿布纳或约库姆妈妈反复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的人免受潜在剥削者的侵害。在1935年的一个情节中,约库姆妈妈保护了一个继承了一笔财产的年轻孤女,对抗两个企图获得孩子监护权的贪婪姑妈。当法官裁定将女孩的钱存入信托基金后,这两个女人抛弃了她,约库姆妈妈得意地踢了其中一个的屁股(图4.17)。同样,在1938年,阿布纳保护瘦弱的孩子们免受一对极其残忍的夫妇的伤害,这对夫妇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秃鹫”,他们经营着一家孤儿院。在这些场景中,卡普将约库姆一家塑造成无可置疑的善良正义的被压迫者和受欺压者的捍卫者。

图4.17
约库姆妈妈,被压迫者的捍卫者,给了贪婪精英阶层的代表应得的惩罚。阿尔·卡普,《小阿布纳》,“她被压抑的欲望”(局部),1935年7月6日。图片由卡普企业公司和丹尼斯·基钦艺术经纪公司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但卡普的平民主义同情心有其局限性,他对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的长篇戏仿就是例证。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期间,卡普展示了约库姆一家经历了乔德一家绝望出走的荒诞镜像。虽然乔德一家来自俄克拉荷马平原,但两个故事都反映了那些年成千上万流离失所家庭的真实困境。狗窝镇的人们驾驶着破旧的老爷车穿越全国,追随着在波士顿所谓”橙子果园”从事流动劳动的承诺,他们在一座豪宅前停下寻求食物和住所。在他对精英阶层冷漠无情最尖锐的刻画之一中,卡普展示了一群肥胖、衣着光鲜的人——“救济饥饿山民委员会”——一边大嚼鱼子酱和龙虾,一边为同胞的命运流下鳄鱼的眼泪(图4.18)。当狗窝镇的人们试图享用丰盛的自助餐,理直气壮地说”饥饿的山民?那就是我们啊,女士!“时,他们却被这些所谓的恩人愤怒地赶走了。当狗窝镇的人们到达波士顿,意识到在白雪皑皑的新英格兰根本没有橙子果园时,市长号召市民筹集资金让他们返回家乡,并赎回被收回的房屋。故事结束时,狗窝镇的人们只是勉强持平,既没有从驱使他们离开的苦难中得到喘息,也没有像乔德一家那样获得普世兄弟情谊的觉悟。虽然卡普将他的故事呈现为对虚伪慈善的批判,但他只是将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用于喜剧目的,而不是为被压迫者建立同理心。他的最终信息是,虽然穷人需要被同情,但彻底的提升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仍然无知、落后且无法教化。

图4.18
作为平民主义者的卡普:对伪慈善的尖锐批判。阿尔·卡普,《小阿布纳》,“门外旁观!”(局部),1940年1月9日。图片由卡普企业公司和丹尼斯·基钦艺术经纪公司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然而,在一个令人困惑的变化和动荡的世界中,约库姆一家对”家”和”归属”有着清晰而持久的认知,在经历了许多冒险之后总是感激地回到狗窝镇。约库姆妈妈或许最能代表所有约库姆家族成员和黛西·梅共同拥有的对家庭和亲人坚定不移的忠诚。约库姆妈妈的动机完全是保护她的家人和社区,在狗窝镇的人中,只有她拥有一种纯粹的常识,能够看穿城里骗子的欺诈和诈骗伎俩,无论是想占阿布纳便宜的富家千金,还是企图控制狗窝镇的巧舌如簧的律师。约库姆一家的绝对忠诚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保护他们免受那些在连环画中络绎不绝出现的富有但冷酷、最终空虚的男男女女的伤害,并使他们与无数被对财富无尽渴望所驱使的普通城市人物区别开来。尽管追逐金钱是大萧条时期连环画的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但约库姆一家对获取财富毫无兴趣,当他们得到财富时通常会把它送出去。
黛西·梅和约库姆一家的公正、忠诚和非物质主义源于他们与”文明”腐蚀影响的隔绝,这些特质使这些角色及其狗窝镇(Dogpatch)的同伴成为原始但纯净自然世界的人类化身。在小阿布纳和黛西·梅身上,卡普呈现了一种堕落前的纯真无邪和身体纯洁的愿景——一对现代版的(明确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亚当和夏娃,象征着理想的美国之美(图4.19)。但狗窝镇的所有其他居民在外貌上都是怪诞的,与野生动物相差无几。他们赤脚走路,衣衫褴褛,只想着性和食物,对他们神秘领域之外的现代世界完全无知且困惑不解。卡普采纳了关于山民原始性的无数刻板印象,以狗窝镇居民所谓的肮脏、懒惰、性滥交、兽性以及社会文化落后为基础创作了无数情节。有时,他对这些标准套路的视觉和文字变奏可以相当俏皮。例如,他描绘黛西·梅因为已经十七岁还没结婚而要去老处女之家,还展示了一对代表”狗窝镇社会精英”的已婚夫妇,他们看不起阿布纳的未婚妻,因为她光着脚,而他们家里有一双鞋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即使是他对美艳动人的月光麦克斯温的描绘——她不停地挠痒痒、吐烟草汁、喜欢猪的陪伴胜过人类——也更多是荒诞而非贬低。

图4.19
黛西·梅·斯克拉格:作为美国美人原型的山地女性。阿尔·卡普,《小阿布纳》,“你说得对,伙计!”(局部),1936年2月12日。图片由卡普企业公司和丹尼斯·基钦艺术经纪公司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然而,卡普关于山区贫困和原始性的大部分幽默是贬损和刺耳的,而且越来越如此。一组反复出现的角色——阿比贾·古奇和斯克拉格三人组——提供了他对山区生活阴暗面愿景的最佳例证。虽然阿比贾在连载的头两周作为阿布纳的一个更加衣衫褴褛的对应角色出现,但到1936年10月,他变形为一个肌肉发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标本,留着长长的飘逸胡须(无疑直接受到韦伯漫画的影响),只穿一条用绳子当腰带系着的破裤子。读者后来得知阿比贾是从他父亲那里借的裤子,他父亲正在柴房里等他还回来!当麦加格尔教练(他为自己的橄榄球队招募了阿布纳和阿比贾)开车送男孩们去校园时,他心想:“也许把他们带到文明社会不是什么好主意!”卡普在接下来的场景中更明确地呈现了这些乡巴佬(hillbillies)作为现代穴居人的主题,阿比贾只穿着阿布纳的豹纹睡衣,为了取暖点燃了一把宿舍椅子(最终烧毁了整栋楼)。
如果说阿比贾·古奇代表了无可救药的无知和贫困的山民,那么罗密欧·斯克拉格和他两个魁梧的儿子莱姆和卢克则象征着无法控制的暴力和邪恶的山民。卡普后来形容他们是”不卫生、粗鲁、顽固不化、无法形容的猿类”。在贯穿连载大部分时间的持续血仇中,斯克拉格一家反复试图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杀死约库姆一家,摧毁任何挡在他们路上的人和物。作为肆无忌惮的暴力和社会混乱的永恒象征,斯克拉格一家到1930年代末和二战期间变得越来越野蛮。在1938年的一个情节中,他们穿越乡村的路径最像是一场致命的龙卷风,每当他们出现时,他们狰狞的笑脸就让文明社会充满恐惧(图4.20、4.21)。斯克拉格一家魁梧的身躯和残暴在无数来自山区的配角身上得到映射,这些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象征野蛮的兽性。卡普在描绘狗窝镇居民时自由使用猿类意象和引用,有时甚至做出逻辑跳跃,暗示这些人物不是人类(图4.22)。总的来说,这些形象强化了公众对南方山民无知和天生暴力的认知,并延续了人类学家艾伦·丘吉尔·森普尔于1901年首次提出的地区社会退化观念。

图4.20、4.21
斯克拉格一家:山民作为”顽固不化、无法形容的猿类”。阿尔·卡普,《小阿布纳》,1938年4月12日;“欢迎凶杀”,1938年4月13日。图片由卡普企业公司和丹尼斯·基钦艺术经纪公司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图4.22
被描绘成亚人类野蛮人的狗窝镇居民。阿尔·卡普,《小阿布纳》,无标题(局部),1944年10月6日。图片由卡普企业公司和丹尼斯·基钦艺术经纪公司提供 www.deniskitchen.com
卡普将小阿布纳及其家人的纯真无邪与斯克拉格家族等人的野蛮残暴进行对比,这反映了他对山民/乡巴佬二元性内在矛盾的深刻理解,甚至比德贝克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现了将朴实诚恳的现代拓荒者概念与种族、体貌和文化”他者性”观念相融合所带来的讽刺可能性。二战期间《小阿布纳》中野蛮角色的日益增多,既反映了那些年代残酷的战斗和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卡普加速转变的创作方向——从将狗窝镇描绘成一个哪怕是勉强真实的山区社区,转向一个充满性感怪诞人物和怪物的纯幻想王国。这一趋势在1946年底达到顶峰,当时卡普将小阿布纳送到”下斯洛博维亚”(他笔下的苏联版本),差点强迫他娶丑陋得难以言表的鬣狗莉娜。
尽管《小阿布纳》又延续了三十一年,但大多数爱好者认为1940年代和1950年代是该连环画的黄金时代。在这些年里,乡巴佬元素——从来就不像韦伯和德贝克的作品那样处于核心地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卡普在他的连环画中填充了各种奇幻生物,而狗窝镇居民则卷入了涉及冷战和原子试验的情节。1948年,阿布纳和他的山民同伴们参与杀死了那些无私到不可思议的施穆(Schmoos)——这些生物天性善良到愿意让自己被吃掉以给捕获者带来快乐——理由是允许这种纯粹的恩惠传播会摧毁美国的工作和消费伦理。因此,曾经可能是现代文明弊病解药的狗窝镇,越来越只是卡普眼中美国社会贪婪、腐败和残暴特征的替身。
尽管这三部漫画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失去了一些直接的文化影响力,两部连环画对山民背景和社会的关注也有所减少,但韦伯、德贝克和卡普的漫画创作对媒体中乡巴佬形象的全国性和地区性认知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也影响了公众对这些形象据称所基于的真实山区居民的看法。韦伯的乡巴佬形象尤其深入渗透到美国文化中,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例如,在战斗机和轰炸机上绘制裸体或半裸女性的做法有一个奇特的变体(许多直接基于《时尚先生》杂志的”佩蒂”和”瓦尔加”女郎折页画报),几艘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舰艇的船员采用了韦伯的角色作为徽章。通过布朗与比奇洛广告公司的赞助,韦伯的漫画还被用来推广各种产品。例如,电气自动点火公司在194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火花塞广告中使用了他的角色,甚至向军人免费邮寄了一本《山地男孩》漫画平装合集。韦伯的图像风格对好莱坞的乡巴佬形象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他改变并标志化了电影中乡巴佬的形象——此前这一形象是伐木工、佃农和自耕农的不确定混合体——以至于”《时尚先生》风格”和”韦伯式”这些术语在电影和整个流行文化中都能唤起一个即刻可辨的乡巴佬形象。
韦伯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南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山地男孩》可以说是1942年北卡罗来纳州布恩市阿巴拉契亚州立师范学院(现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学生创造的”丹尼尔·布恩·约瑟夫”角色的灵感来源。他们将这个留着长胡子、戴着高帽、叼着玉米芯烟斗的山民纳入当年的新生班级,甚至将他的形象放在年鉴封面上,作为对外界对南方山民形象的自嘲式评论。1930年代末,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高中的学生为其年鉴《乡巴佬》封面采用的乡巴佬图标更是直接基于韦伯的形象,从他的长松鼠枪到威士忌酒壶、赤脚和懒散的姿势(图4.23)。正如这些例子所清楚表明的,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后期,韦伯的形象已经成为全国和地方漫画乡巴佬的标准形象,并将在战后时代持续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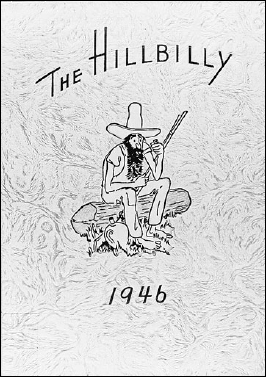
图4.23
韦伯在南方山区的影响:《乡巴佬》(以及乡巴佬形象)的进一步演变;《乡巴佬》,1946年年鉴,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李·H·爱德华兹高中。图片由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帕克纪念公共图书馆北卡罗来纳收藏馆及阿什维尔高中提供。
卡普笔下的乡巴佬形象虽然不如韦伯的影响深远(至少在二战结束前是如此),但他创造的”萨迪·霍金斯日”却成为一种全国性现象。在这一天,狗窝镇的女性有权用任何离谱的手段抓住并嫁给任何男人。从193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开始,人们穿上受漫画启发的服装,参加追逐比赛和舞会,这种做法很快传播到高中、社交俱乐部和工厂。萨迪·霍金斯节庆活动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提供了挑战当时礼仪规范和女性顺从传统的机会,但它也强化了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贫困的南方山民与激进、异常的性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一些南方山民及其自封的捍卫者的愤怒反应,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形象的持久影响。《伦弗罗山谷谷仓舞会》的约翰·莱尔无疑代表了该地区许多认为这些漫画具有贬低意味的人的心声。1951年,他在写给负责其广播节目主要赞助商(通用食品公司)宣传工作的广告主管的信中,批评了该机构为推广其节目而提供的那些温和得多的漫画,莱尔强调”人们经常表达对《时尚先生》杂志’山地男孩’和阿尔·卡普那些怪诞漫画形象的极度厌恶”。肯塔基州本地人哈丽特·阿诺在她1954年的史诗小说《雕刻师》中以稍微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漫画刻板印象的敌意。这部小说追溯了格蒂·内维尔斯一家在二战期间从肯塔基山区痛苦迁移到底特律的经历。在一个场景中,格蒂因儿子嘲笑一幅韦伯风格的漫画而打了他一巴掌——那幅漫画荒谬地描绘了一个”赤脚戴着遮阳帽”的乡巴佬老妇人赶着一头瘦骨嶙峋的骡子。“这一点都不好笑,”她厉声说道,心想这幅漫画粗鲁地讽刺了她丈夫的母亲——一位在儿子们都去打仗时被迫独自照料肯塔基农场的老人。
如果说我们只有间接的、时间较晚的证据来证明南方山民对这些乡巴佬漫画的反应,那么关于他们对这个词本身的深刻矛盾态度,则有更多证据。正如前文第三章讨论的音乐家托尼·奥尔德曼对这一标签的反应所表明的,对于南方山区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挑衅性的词”,城里人用它来贬低奥扎克山区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偏远居民。民俗学家万斯·伦道夫声称,1934年——正是乡巴佬漫画和连环画开始流行的那一年——有人因使用这个词而杀了另一个人。霍华德·奥杜姆在1936年指出,这个词被用作对中西部工业城市中南方山区移民劳工的侮辱性称呼,而阿诺的书中也充满了底特律本地人对格蒂·内维尔斯及其孩子们吐出这个词的例子,仿佛它是”一个需要迅速吐掉的肮脏东西”。1944年一篇题为《别叫我乡巴佬》的文章解释说,对于”土生土长的山民”来说,这个词”带有嘲笑的意味”,“带着一种玷污他们自尊的污名”。
然而,来自南方山区的其他人则公开接受了这个称呼。尽管万斯·伦道夫承认外人扭曲了奥扎克山民的形象,但他始终称他们为”乡巴佬”,甚至在194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乡巴佬的趣事》的轶事集。同样,安东尼·吉什在1937年为《时尚先生》杂志撰写的文章标题就是《是的,我是乡巴佬》,文中赞美了他在密苏里州奥扎克偏远地区生活方式中的独立、坚韧和男性主导地位。西弗吉尼亚州桂冠诗人罗伊·李·哈蒙坚持认为,他的《乡巴佬民谣》(1938年)中的诗句反映了阿巴拉契亚山区拓荒者的精神。他认为这个词”不带任何污名”,而是指”一个在我们挚爱的群山中出生和成长的人……在那里,坚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曾经的荒野上建立了一个现代而重要的联邦”。
当地山民的第三种反应,由露西尔·莫里斯在她1937年的文章《好老乡巴佬……》中最清晰地表达出来,是一种有些勉强的接受。她认识到,虽然这个词反映了城市人的嘲讽,但它也代表了奥扎克(以及延伸到阿巴拉契亚)独特的民间文化如何吸引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想象力,并刺激了当地旅游业——这在农业经济萧条时期是急需的发展。莫里斯敏锐地观察到,当地人对外来者居高临下态度的怨恨”在当乡巴佬变得有票房价值时就消散了”。“现在,”她继续写道,“我们把开叉的帽子往后推……抚平我们从商店买来的印花布裙子上的褶皱,娇羞地说’就叫我乡巴佬吧’”。对莫里斯来说,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反映了年轻一代奥扎克人重新发现了该地区的民间传统——他们曾经为偏远地区长辈的习俗和方言感到羞耻。“在那些被乡巴佬主义利用者拖出来的廉价粗俗背后,”莫里斯总结道,“有着古老而重要的根基。”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国大众媒体对真正山民形象的扭曲,反而让一些当地居民重新认识到了世代相传的山区农民和手工艺人技艺与习俗的价值。
对”hillbilly”(乡巴佬)一词如此广泛的地方性反应再次揭示了这个词汇和形象含义的流动性,以及不同受众和个人如何努力重新定义和重新概念化这一术语。1934年开始出现的漫画和连环画在这一持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韦布、德贝克和卡普的作品影响了比乡村音乐听众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受众群体,将山民的主流定义从真正的威胁和危险转变为无害的、虽然异常但滑稽的越轨形象。他们还巩固了这一新美国刻板印象的即时可辨识的图像形象。与此同时,他们的作品保留了这一文化建构中固有的模糊性,将落后、无知和野蛮的贬义概念与坚韧、独立以及对家庭和家园的忠诚等积极观念统一起来。通过这样做,这些漫画家以回应美国人在经历大萧条和战争时的心理需求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这一文化形式,让人们怀念地回望一个想象中更简单的时代和地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之间的这段时期,没有什么地方比电影——这一时代的主导媒介——更能清楚地展现媒体中南方山民形象的喜剧化重塑。在美国经济繁荣与崩溃之间摇摆、在国际孤立与战争之间徘徊的这些年里,山民角色几乎出现在每一种可能的电影类型中:动作惊悚片、伪纪录片、社会问题揭露片、史诗剧、音乐片、B级喜剧片、动画片,甚至政府宣传片。受到早期无声电影中山民形象以及其他媒体中乡巴佬形象新概念和流行度的强烈影响,乡巴佬的建构身份一如既往地带有模糊性,并具有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观点和条件的非凡能力。尽管早在1910年代中期,观影大众就已对无知的私酒贩子和世仇者刻板印象感到厌倦,但这些形象一直主导到1920年代。然后,随着野蛮山民形象在1920年代末逐渐失去可信度,它被乡巴佬这一新概念所取代——一个滑稽落后的乡下人。这一形象在193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与乡村音乐家和漫画家一样,乘着对普通民众的颂扬以及对地方生活和文化(尤其是南方山区)的迷恋浪潮。在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结束后——这场战争既是反对种族和民族等级制度及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也是反对纳粹德国和日本——那些陈旧的赤脚、长胡子、好斗的乡巴佬刻板印象越来越受到抨击。但这一形象只是再次被重新发明,这次以质朴但被驯化的凯特尔夫妇(Ma and Pa Kettle)的形象出现。在极受欢迎的凯特尔系列电影中,乡巴佬形象代表了战后关于以儿童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神圣性的态度,以及新的、对许多人来说令人不安的郊区化和消费主义美国社会的一面扭曲镜像。到1950年代中期,当这些电影也走完了它们的历程时,这一形象及其更广泛代表的地区逐渐淡出视野——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和再次重塑。
尽管早在1911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讽刺数百部一战前千篇一律的世仇和私酒情节剧的喜剧电影,但1920年代的绝大多数山民电影仍然围绕这些陈腐的情节展开。无知野蛮的主题从片名就可以清楚看出:《复仇的种子》(1920)、《狼法》(1922)、《仇恨之谷》(1924)和《燃烧的灵魂》(1928)——后者在《综艺》杂志中被描述为”对半开化的半野蛮民族的令人信服的描绘”。1925年剧情片《雷山》的早期剧本表明这些角色有多么野蛮。第五场介绍了”一个狂野的、半裸的男人”,他用”古老类型的手工犁”耕地,通过向灌木丛扔石头来叫孩子们吃饭。即使电影制作者超越了山区野蛮的主题,他们仍然将该地区的人民呈现为文化异类。《山疯》(1920)将”山贼和冷血警长”与在西弗吉尼亚山雾中争吵的恋人交织在一起,他们”被一种’山疯’所笼罩”;而《先知的妻子们》(1926)则聚焦于一个弗吉尼亚山民教派,该教派每年为一位据称神圣的先知选择处女伴侣。
尽管世仇和私酿威士忌在整个世纪的山区电影中仍是常见主题,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一类型已被过度开发,以至于评论家和放映商都普遍谴责这些可预测的情节和角色类型。典型的例子是一位评论汤姆·米克斯新片《世仇》的影评人,他在1919年警告影院老板:“这个片名不好卖。它陈腐老套,暗示着一个被过度使用的主题。”战后以当代山区人物和场景为特色的电影数量急剧下降,进一步证明了人们对这些标准情节剧日益增长的反感。1915年至1919年间,制片厂发行了138部此类电影,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只制作了84部,1930年至1939年间仅有37部。电影时长的增加和成本的上升可能在这一下降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类型在观众中的可信度日益降低。城市观影者显然已经对山区家族之间或执法官员与不法之徒之间的枪战情节失去了兴趣和信任(尽管这些情节后来成为西部片的核心)。然而,好莱坞坚信,对于观影大众来说,南方山区居民仍然是原始野蛮和文化愚昧的代名词,这一观念依然牢不可破。对1920年代三部不同山区电影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公众对南方山区居民的这种普遍认知,以及在接下来十年将全面出现的”乡巴佬”刻板印象的缓慢形成。
《还算不错的大卫》(1921年)仍然是有史以来最赚钱、最具影响力的山区题材电影之一。它获得了全国影院老板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一位伊利诺伊州的放映商高呼”毫无疑问,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山区生活电影”),被《电影剧》杂志读者评为1922年最佳影片,并使其年轻的男主角理查德·巴塞尔梅斯一举成名。这部剧情片改编自约瑟夫·赫格斯海默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十六岁的大卫·金尼蒙(巴塞尔梅斯饰)的成长故事。他被迫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初恋情人埃丝特,对抗三个在西弗吉尼亚州逃亡的凶残山区野蛮人。在这些暴徒中最凶残的一个打残了大卫的哥哥,并间接导致他们的父亲中风身亡后,大卫不顾母亲拼命阻拦,前去与袭击者对峙。在一场惨烈而史诗般的战斗中,大卫通过杀死野蛮的山民并救出埃丝特,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气概。
这部电影的票房成功不仅源于其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还源于人们相信,由于它避免了陈旧的情节,并在弗吉尼亚州海兰县的高地实地拍摄,它必定是对当代南方山区人民和生活状况的真实再现。巴塞尔梅斯和导演亨利·金在推广这种真实性认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邀请报纸记者加入他们,前往一篇典型新闻报道所称的”弗吉尼亚的真正荒野”,“置身于难以置信的原始环境中”。尽管金和巴塞尔梅斯都向记者强调,这”不是一个关于世仇或私酿威士忌的故事”,他们想要捕捉”弗吉尼亚山区的真实氛围”,但他们也利用世仇神话来增加作品的可信度。显然,他们相信公众认为世仇是山区文化和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必须引入这一神话才能使电影令人信服。于是,金与记者讨论了”家族世仇的起因和轰动性后果”,并声称他的摄制组在前往拍摄地点的途中曾被一群武装人员拦截,这些人正在追捕一个敌对的”家族”。《路易斯维尔先驱报》的一篇评论完美地捕捉到了这种对世仇神话的同时拒绝和接受,评论指出,这部电影虽然戏剧性很强,但揭示了”山区世仇者’以眼还眼’的信条”,并且”似乎就是故事作家们教导我们相信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山区的生活”。
虽然巴塞尔梅斯是这部电影的明星,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影评人几乎同样关注片中的主要反派卢克·哈特本——这个名字显然是为了让人联想到世仇传说中的哈特菲尔德家族——由欧内斯特·托伦斯饰演(图5.1)。哈特本在银幕山地野蛮人的长队中占据一席之地,是个粗野的巨人,开场字幕中描述他是”以摧毁所遇到的一切为乐的人”。哈特本在整部电影中完全符合这一介绍,他杀死了家里的狗,用石头砸大卫兄弟的后背然后踩踏他的头部致其残废,偷窃美国邮件,还差点强奸了埃丝特。托伦斯的表演看起来如此逼真,以至于一位影评人惊叹”它太真实了,简直让观众感到痛苦”。影评人海伍德·布朗也认同托伦斯的角色”被普遍授予本季度重量级、令人毛骨悚然的冠军”。这部电影因此巧妙地结合了山民神话身份的两面。大卫象征着农业的纯洁和正义,未被现代工业世界和一战的恐怖所腐蚀,而卢克和他的家人则代表着纯粹的邪恶,以及一种如此原始和倒退的文化和心态,以至于文明的生存需要将其消灭。在魁梧的歌利亚和矮小的大卫之间的生死搏斗中(图5.2),神话山民形象的这两面统一起来,大卫达到了击败对手并获得胜利所必需的肆意野蛮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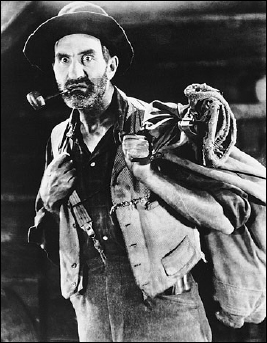
图5.1
典型的山地怪物:欧内斯特·托伦斯在《还过得去的大卫》(1922)中饰演卢克·哈特本。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图5.2
农业纯洁遇上山地野蛮:卢克·哈特本(欧内斯特·托伦斯饰)和大卫·金蒙(理查德·巴塞尔梅斯饰)在《还过得去的大卫》(1922)中的生死搏斗。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虽然《还过得去的大卫》囊括了野蛮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所有元素,但这部电影及其广告中都没有使用”hillbilly”这个词,任何影评中也没有出现。但到1924年,这个词已经足够为人熟知,被用在一部明显想借《还过得去的大卫》成功东风的电影标题中。《乡巴佬》(1924)由杰克·皮克福德(玛丽·皮克福德的弟弟)主演,是第二部在标题中使用这个标签的电影。与《还过得去的大卫》一样,英勇的年轻小伙通过杀死谋杀了他父亲的山地怪物而成长为男人。尽管明星和他的导演乔治·希尔试图通过给皮克福德的角色配一只宠物熊来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但只有标题是真正新颖的,《电影剧》的一位影评人抱怨说,这个老套的情节”已经被拍过很多次了——而且有时拍得更好”。然而,《乡巴佬》在将一个配角塑造成下巴松弛、驼背、只穿一根背带裤的无知乡巴佬方面可能也开创了新局面(图5.3)。在十多年内,这个角色将成为大多数好莱坞山区电影中的标准”类型”。由于1920年代早期的山区电影留存下来的很少,目前尚不清楚《乡巴佬》是否标志着这种角色类型的首次银幕亮相,但它确实表明这一形象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

图5.3
杰德·麦科伊(杰克·皮克福德饰)被驼背的乡巴佬”典型”嘲弄,出自《乡巴佬》(1924)。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部电影,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个词在文化上的接受度越来越广,到1920年代中期,“hillbilly”的变体开始出现在其他电影和电影评论中,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以前对南方贫穷白人的同义词。例如,《日出》(1925)的早期剧本将山区角色描述为”散居的未驯化的美国人,被称为白色垃圾(WHITE TRASH)“。然而,六个月后的最终字幕表将他们标记为”‘乡巴佬’,在南方阴郁的山丘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些影评人也采用这个词来指代角色和他们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位影评人认为,暗示山民以为法国的战争就发生在山的另一边的台词是多余的,但得出结论说它们”可能有助于让观看电影的人更牢固地了解普通乡巴佬的确切精神和教育状况”。这些引用清楚地表明,这个词作为一个标签越来越受欢迎,它在”白色垃圾”的冒犯性和”山民”的浪漫主义之间取得了平衡。
尽管”乡巴佬”(hillbilly)这一标签日益流行,南方山区居民被塑造成纯粹滑稽形象的刻板印象也随之出现,但在1920年代末的电影中,粗野无知的山民形象仍然不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影片之一是《原始之爱》(Stark Love,1927年)。尽管这部电影在当时并不成功——在美国影院短暂上映后便销声匿迹,直到1960年代才在捷克斯洛伐克电影档案馆发现了唯一留存的拷贝——但这部影片、编剧兼导演卡尔·布朗的观点,以及影评人和记者的反应,完美地反映了当时公众对山区生活堕落状态毫无质疑的普遍认知。
布朗是一位资深的好莱坞摄影师,曾因拍摄1923年讲述西部开拓的热门影片《篷车》中的史诗级风景而声名鹊起。他对自己所理解的美国边疆那种不加掩饰的性欲和近乎野蛮的状态深感着迷。传教士露西·弗曼192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关于肯塔基山区居民与世隔绝、原始生活的报道令他心驰神往,这篇报道后来以《奇异的女人们》(The Quare Women)为名出版成书。霍勒斯·凯普哈特的《我们的南方高地人》(Our Southern Highlanders)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一部内容翔实且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但对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山区的人文风情进行了高度浪漫化的冒险叙述。凯普哈特本人帮助布朗选定了拍摄地点,并经常出现在片场,为当地文化提供咨询。
鉴于布朗的先入之见和所受影响,《原始之爱》的主要主题与至少自世纪之交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南方山区的文化表现所强调的主题如出一辙,这并不令人意外。开场字幕以当时已成标准的方式介绍角色,称他们是”一群与世隔绝的原始民族,是英国拓荒者的后裔”。影片中穿插着他们粗陋生活的场景,从捶打衣物、在大壁炉上烹饪,到剥野猪皮。所有这些劳作都由女性完成,影片突出展现了男性统治的绝对性。第二张字幕卡写道:“他们的荒野法则体现在这一残酷原则中:男人是绝对的统治者——女人是劳作的奴隶。”布朗反复强调男人的懒惰和酗酒,以及女性生活的艰辛;主人公的母亲因过度劳累和频繁生育而早早离世(图5.4)。与漫画家德贝克、韦伯和卡普不同——他们的作品意在搞笑——布朗的创作意图是对前现代乡村生活进行严厉(尽管耸人听闻)的批判。与虐待性父权制主题密切相关的,是最能激发布朗想象力的观念:木屋中不受约束的肉欲。正如他在向派拉蒙制片人杰西·拉斯基推销创意之前兴奋地告诉妻子的那样:

图5.4
山区女性沦为奴隶:罗布·沃里克的母亲(阿德琳·奎恩饰)在《原始之爱》(1927年)中照看炉火。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我们对这些木屋的外观了如指掌,但对内部却一无所知……你能想象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吗……当他们在冬春季节被困在这木头牢笼里……数周甚至数月无法逃脱?你能想象当一个新生命就在年长孩子们眼前孕育时,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能看到、听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这个单间木屋的秘密正是《原始之爱》的核心所在。与《山里人》(The Hill Billy)和其他早期成长题材电影一样,一个渴望逃离山区禁锢的年轻山民小伙(本片中是罗布·沃里克,由福雷斯特·詹姆斯饰演)必须首先击败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堕落、落后和野蛮的活生生象征。但与前作不同的是,在《原始之爱》中,阻挡在男孩和他青梅竹马的恋人芭芭拉·艾伦(海伦·芒迪饰)之间的宿敌,竟是他自己的父亲。在老沃里克疲惫的妻子去世后,他”娶了”(实际上是在她父亲许可下获得了)芭芭拉·艾伦,随后试图违背她的意愿与这位新”新娘”发生关系(图5.5)。布朗关于隔绝、原始和男性权力的主题在倒数第二个场景——几近强暴的戏份中汇聚在一起:罗布攻击了他的父亲,却被更强壮的父亲扔出木屋门外,跌入汹涌的河流。芭芭拉用斧头威胁要杀死老头后,劈开了紧闩的木屋门,从湍急的河水中救出了罗布,然后带着两人漂流到安全地带。影片以罗布和芭芭拉终于挣脱山区枷锁、手牵手走向远处闪烁着希望之光的山谷小镇作为结尾。

图5.5
父权受到挑战:芭芭拉·艾伦(海伦·芒迪饰)在《原始之爱》(1927年)中怒视她的新”丈夫”詹姆斯·沃里克(赛拉斯·米拉克尔饰),这是他企图强暴她之前的一幕。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尽管这部电影采用了标准的”逃离山区”结局,布朗声称他的作品是一部独特的纪录片风格电影,超越了老套的山地乡巴佬故事情节。正如他对霍勒斯·凯普哈特所说:“我想展示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他们真正的样子。作为人,而不是漫画式的形象。”然而实际上,布朗对山区文化和社会几乎一无所知,他整个项目的设计目的不是展示他的拍摄对象的真实状态,而是展示他虔诚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他对这部电影拍摄过程的无意中令人捧腹的叙述揭示了他无知的程度。为了寻找”大烟山最黑暗角落里愚昧的人们”,他首先前往的竟然是新奥尔良!那里的记者指引他去肯塔基州的伯里亚,当地伯里亚学院的官员们可想而知对(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帮助电影剥削山区人民”毫无兴趣。然后他跌跌撞撞地从纳什维尔到诺克斯维尔再到阿什维尔,每到一处,酒店前台、门童和新闻记者都向他保证,他要找的那类人都在下一个城镇附近。最终,在阿什维尔的一家书店里,他发现了《我们的南方高地人》这本书,并最终找到了它的作者。
布朗坚定地执着于他对一种危险封闭和落后文化的先入之见,故意歪曲山区生活的现实并操纵他的演员。他选择的拍摄地点后来被他呈现为一个典型的当代山区社区,实际上是北卡罗来纳州格雷厄姆县雪鸟山脉高处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几间废弃的小屋,在桑蒂拉大坝完工后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水下。此外,他故意打乱拍摄顺序,以短小、不连贯的片段进行拍摄,以防止当地演员认识到他对他们生活描绘的冒犯性质。他后来为自己的”欺骗”辩护,解释说那些男人都是”懒惰、酗酒、一无是处的人”,而当地人”像孩子一样……绝对服从”。布朗暗示,对于这些”从未见过火车、汽车……或电话”的人,除了只告诉他们表演场景所需知道的内容,还能怎么对待他们呢?最后,尽管布朗声称他的演员几乎都是格雷厄姆县本地人,但他的四位主演实际上都是外来者。扮演罗布和芭芭拉父亲的两个男人是肯塔基人,而福雷斯特·詹姆斯和海伦·芒迪都来自诺克斯维尔,詹姆斯是当地的橄榄球运动员,芒迪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高中生。
尽管记者和评论家们意识到布朗编造了场景、操纵并歪曲了他的演员,他们仍然将这部电影呈现为对南方山区生活和人民的真实写照。一位评论家将这部电影称为”美国最原始人民实际生活和习俗的影像化呈现”。《电影新闻》走得更远。该报将这部电影与三部近期极具影响力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草原》(1925年)和《莫阿纳》(1926年)相比较,宣称《赤裸的爱》“在社会学和科学上与之前的杰出三部曲同样重要”。因此,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源自一位在全国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导演过度活跃的想象力,却被呈现为对原始土著种族具有人类学价值的研究。尽管如此,这种所谓的科学资质不足以使这部电影免于票房失败。尽管在电影行业媒体上获得了热烈好评,派拉蒙只是半心半意地推广这部电影,在短暂的全国发行后,它被撤回,胶片被熔化以回收其中的银含量。
像《赤裸的爱》和《日出》这样的电影反映了1920年代美国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面。一方面,它们聚焦于”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像他们的殖民时代祖先那样生活——反映了这个时代强烈的本土主义情绪——这些年见证了《国籍起源法》(1924年)的通过、三K党的重新崛起以及萨科和万泽蒂的处决。它们也反映了新教传教协会的要求,即将救济和教育工作重点放在愚昧的山区民众身上,而不是亚洲或非洲的”异教徒”。正如《日出》的一张字幕卡所写:“美国在中国花费数百万教他们认识白人的上帝……但政府对一些可怜的美国人——在我们自己后方山区中徘徊于黑暗中的人——做了什么。”虽然这些电影赞扬南方山民值得被提升,但它们也将他们呈现为无知、落后,在对待女性和生活习惯方面是倒退的。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数十篇关于无可救药的原始山区民众的大众媒体报道,也反映了H·L·门肯和辛克莱·刘易斯等著名作家对农村和小镇美国人的普遍谴责。与其他媒体和以往时代一样,1920年代电影中对南方山民的呈现既服务于那些想要推广非城市美国社会的人,也服务于那些想要谴责它的人。
《荒野之恋》的失败进一步表明,到1920年代末,观众对关于南方山区人民的严肃情节剧的兴趣正在急剧下降。评论家和放映商现在认为,任何带有标准山民情节线和主题暗示的影片都注定失败。随着世仇和私酿酒作为可信故事线逐渐失去合法性,标准的好莱坞动作类型转向西部背景下的牛仔与印第安人题材,这些主题越来越成为喜剧演员的专属领域。他们的电影与音乐行业的趋势相呼应,帮助逐渐将山区生活和文化重新定义为一个脱离社会经济现实的喜剧夸张场所,而非严肃的社会问题。
现存最早展现新式喜剧乡巴佬(hillbilly)形象的电影之一是巴斯特·基顿1923年的无声恶搞片《我们的待客之道》,这是对著名的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冲突的戏仿,也是对标准肯塔基世仇情节剧的讽刺。基顿饰演威利·麦凯,一个年幼时被母亲带到纽约市以逃避家族与对手坎菲尔德家族世仇的年轻人。当他得知自己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时,他确信一座宏伟的种植园庄园正等着他,尽管姑姑警告他,他还是前往蓝岭山脉去领取他的奖赏。当然,这座宏伟的庄园结果(就像德贝克的连环漫画中一样)只是一间破旧的小木屋。基顿在影片的其余部分都在躲避成为坎菲尔德家”待客之道”的受害者。
《我们的待客之道》展示了乡巴佬形象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与后来设定在当代的乡巴佬电影和形象不同,基顿的电影明确设定在19世纪初(远在实际的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冲突于1870年代开始之前),并没有暗示这种家族世仇在当代山区仍然存在。事实上,序幕中童话般的字幕卡强调了这种疏离意图:“从前,在美国某些地区,存在着代代相传的世仇。”世仇中的坎菲尔德家族被描绘成住在庄严大宅中的种植园主阶层贵族,而非贫穷狂野的山民,这表明好战乡巴佬的概念源于早期关于南方精英阶层之间决斗盛行的观念(图5.6)。最后,鉴于乡巴佬形象到1930年代末已完全具有喜剧性质,有趣的是一些评论家仍然难以在家族生死搏斗的形象中找到幽默。一位评论家写道:“我们怀疑南方世仇故事的’戏仿’是否能够始终保持幽默——因为它本身具有情节剧的特性。”

作为贵族的世仇者:威利·麦凯(巴斯特·基顿饰)在《我们的待客之道》(1923)中警惕地与对手坎菲尔德家族握手。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尽管一些评论家有所担忧,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世仇和私酿酒情节纯粹作为笑料的电影大量涌现。1927年有声电影问世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杂耍喜剧演员主演了电影——大多是二十分钟的短片而非完整长片——其中暴躁的山民纯粹作为他们闹剧冒险的陪衬出现。尽管如此,电影中的乡巴佬形象直到1930年代仍在形成中;像劳莱与哈代的《那些山丘》(1934)这样的电影尚未融入懒惰、酗酒和肮脏等预期的刻板印象。
由伯特·惠勒和罗伯特·伍尔西主演的《肯塔基玉米粒》(1934)展示了这些早期电影中乡巴佬刻板印象的持续演变。这部电影呈现了南方和西部”类型”的大杂烩,大量借鉴了早期山民情节和套路。在老套情节手法的重演中,惠勒和伍尔西的角色在得知他们监护的孩子最近继承了肯塔基州的一处庄园后来到”世仇之地”。有一个场景完全模仿了《我们的待客之道》中的一幕:围坐在餐桌旁的贵族男子们在把香槟瓶塞的爆裂声误认为是枪声时突然开枪射击。与基顿的电影一样,世仇中韦克菲尔德家族的领袖是南方种植园家族,但”家族”中的其他男子穿着各种乡村服装,从格子衬衫和软帽到牛仔帽和细绳领带。在随后的战斗中——一份报纸将其描述为”类似内战的场面”——他们的对手被更明确地呈现为刻板的山民形象(他们首次出现时聚集在小木屋外的私酿酒蒸馏器旁),但他们的服装也更像伐木工人(穿着格子衬衫和高帮靴),而非后来刻板印象中的乡巴佬。“乡巴佬”这个词在电影或剧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使用,除了提到”一个乡巴佬四重唱”乐队。因此,《肯塔基玉米粒》标志着不断演变的乡巴佬形象的又一个过渡阶段;虽然角色具有喜剧性的暴力特征,但他们还没有变得懒散和不讲卫生。
然而,到了1938年的《肯塔基月光》——下一部以蓝草州为背景的乡巴佬喜剧——那个标志性的懒惰、胡子拉碴、戴着大帽子的乡巴佬形象已经毋庸置疑地确立起来。这部电影由里兹兄弟主演——他们在1930年代中期到1943年间拍摄了十几部”B级”喜剧,是马克思兄弟同样疯狂但不那么巧妙的翻版——充分利用了这一新近形成的乡巴佬形象。剧本、宣传材料和影评都自由地使用了这个术语。剧本提到了一个”典型的懒惰乡巴佬场景”,仿佛其含义已经众所周知,几乎不需要解释。“乡巴佬”这一新的文化符号的流行,当然部分是由于商业乡村音乐的推广者和表演者采用了这个术语和形象,以及全国对南方山区作为真实民间文化所在地的日益着迷——尽管那里也存在社会退化、政治动荡和经济绝望。更直接的原因是对德贝克、卡普,尤其是保罗·韦伯的乡巴佬漫画的回应。《肯塔基月光》对韦伯作品的借鉴显而易见:一句台词描述一间破旧的小屋”看起来像是从《时尚先生》杂志逃出来的”,里兹兄弟假扮成肯塔基山城”科马”的本地人,把自己打扮成活生生的”山地男孩”(图5.7)。制片人达里尔·扎努克甚至试图聘请保罗·韦伯来设计电影的广告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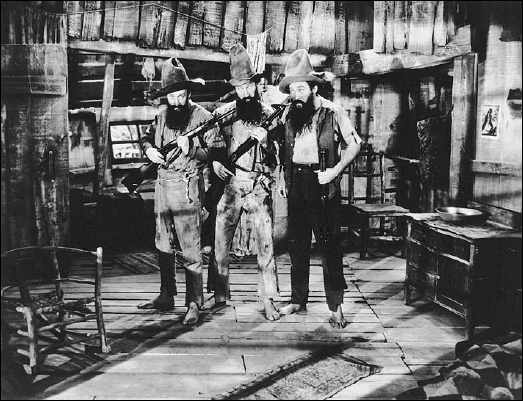
图5.7
里兹兄弟在《肯塔基月光》(1938)中扮演活生生的保罗·韦伯笔下的《山地男孩》。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编剧和演员确实做了有限的尝试来评论这一形象的建构性质。例如,剧情将里兹兄弟描绘成落魄的纽约表演者,他们前往肯塔基山区,希望被一位纽约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发现”,后者试图通过现场直播来利用乡巴佬音乐热潮赚钱。电影还包含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发生在穿着戏服的里兹兄弟和持枪警惕的哈特菲尔德家族之间。当里兹兄弟试图安抚这些山民,向他们保证”我们是乡巴佬”时,族长警惕地问道:“乡巴佬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但总体而言,这部电影强化而非削弱了山民的刻板印象。从哈特菲尔德家族和斯莱克家族之间老套的世仇,到大城市记者轻率地问其中一位兄弟的女友穿鞋是什么感觉、她是否曾是童养媳,再到”哦,我们是来自科马的斯莱克家族/请原谅我们的体味”这样的歌词,电影始终将山民呈现为荒谬堕落的形象。
对这部电影几乎一致的好评揭示了到1938年乡巴佬形象似乎已变得多么无争议,同时又显得多么新颖。这部电影未经删减就通过了美国电影协会制作法规管理局(PCA)的审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由美国革命女儿会或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等团体设立的民间审查委员会的批评,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部”欢乐而健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PCA关于潜在问题角色描绘的清单包括”黑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墨西哥人”和”其他”,但没有明确的类别涵盖南方白人、山民、山区居民或任何类似标签。尽管这部电影包含了关于山民落后和社会失礼的所有可以想象的陈词滥调,《时代》杂志称其对”乡巴佬行为”的呈现”典型地非典型”,《综艺》杂志预测这部电影将为放映商带来”哄堂大笑”和”大把银子”。诚然,与韦伯漫画和《赤裸的爱》中一些贬损性的描绘相比,里兹兄弟的恶搞相当温和。但如果一部电影呈现同样粗俗的非裔美国人或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会获得同样热情的评价吗?非裔美国人社区对《乱世佳人》中黑人角色描绘的广泛抗议表明,角色的白人身份使《肯塔基月光》被视为仅仅是对虚构人群的无害戏仿,而非对真实山民的冒犯性描绘。
尽管《肯塔基月光》表明电影和更广泛文化中对这一人群和土地进行幽默重新诠释的总体趋势,但从1930年代初到二战结束期间,一些好莱坞剧情片继续将南方山民描绘为潜在的社会问题。《烈火》(1934)由二十五岁的凯瑟琳·赫本主演,她刻意严肃地饰演”奥扎克山区那个撒谎、偷窃、唱歌、祈祷的女巫”,派拉蒙公司于1936年推出了小约翰·福克斯经典作品《孤松小径》的第三个电影版本,讲述山区与城市之间的文化鸿沟,这也是第一部彩色技术电影。即使是《约克军曹》(1941)——加里·库珀凭借饰演阿尔文·约克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将其塑造为一个贫穷但虔诚(在战时极其致命)的艰苦山区农民转变为一战英雄——也花了大量篇幅描绘山民的贫困和社会落后。
也许最能代表”山区社会问题”电影类型的是《山区正义》。这部1938年华纳兄弟发行的影片,显然是非官方地改编自伊迪丝·麦克斯韦尔案——她是弗吉尼亚州庞德镇(怀斯县)的一名年轻女教师。此案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因为当地一个全男性陪审团判定她谋杀了父亲,尽管她父亲曾在醉酒狂怒中持刀袭击她。麦克斯韦尔案连续数周占据头版头条,全国妇女党帮助支付了她的律师费,并将她塑造为性别压迫的象征。然而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真正的批判对象并非麦克斯韦尔的父亲,甚至不是判她有罪的陪审团,而是一种落后的、被泛化的”山区文化”——这种文化强制推行绝对的男性权威。
《山区正义》强化了这些关于堕落山区文化的主题:山民不健康的生活条件及其对现代医学的强烈抵制;父权社会的恐怖;以及一种古老的”山地佬正义”(影片原名)的执行——这不过是暴民统治而已。影片中最具戏剧性的场景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所谓的山区野蛮。在影片开头,杰夫·哈金斯(罗伯特·巴拉特饰)用一条巨大的牛皮鞭抽打女儿露丝(约瑟芬·哈钦森饰),因为她违抗了他让她嫁给一个令人厌恶的山区男人的命令(图5.8)。在随后的争斗中,她在自卫时意外杀死了父亲,后来被审判并被判谋杀罪成立。在影片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中,一群愤怒的镇民——他们认为露丝的惩罚(在州监狱服刑二十五年)过于宽大——头戴类似三K党的麻袋头套,试图将她处以私刑。只有一些巧妙的计谋和邻州州长(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着惊人的相似)的善意——他拒绝引渡她——才使露丝免于死在这些山区狂热分子手中。

图5.8
杰夫·哈金斯(罗伯特·巴拉特饰)高大的身影笼罩在倒地的女儿露丝(约瑟芬·哈钦森饰)身上,这是《山区正义》(1938)的一张生动的宣传剧照。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山区正义》© 1937 特纳娱乐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旗下。版权所有。
《山区正义》的宣传手册反复强调”狂热与偏执”这些主题。广告文案吸引观众去”了解’美国野蛮百万人’的真相”,去发现”二十世纪美国最后的野蛮据点……那里存在着童养媳、鞭刑法、巫术和山区恋情的神秘社区!“制片厂还为放映商提供了大厅宣传创意,比如展示儿童服装、玩偶和”其他幼稚小物件”,配上标题”《山区正义》中准新娘的嫁妆”,或者在步枪、鞭子和绞索的陈列旁边放置一块标牌,上面写着”这就是《山区正义》中山民用来执行正义的工具”。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活动,影评界对《山区正义》的反应大多是负面的。一些评论者给予了好评——有人称其为”以邪恶的技巧和真实的力量”制作的电影——大多数评论该片的妇女团体认为它是对山区社会令人不快但令人信服的描绘,称其为”生动而诚实的呈现”和”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但大多数评论者回想起过去三十年无数类似的影片,认为这是一部夸大其词的情节剧,不过是在重复山民的刻板印象。《综艺》杂志称其为”耸人听闻且缺乏说服力”的故事,“似乎包含了人类已知的所有山区陈词滥调”。另一位评论家将这部电影斥为”激动人心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废话”。“毫无疑问,”作者继续写道,“如此直白地描绘山民背后的理论是,山民很少甚至从不看电影。”虽然这种态度显然反映了全国媒体和好莱坞的主流观点,但华纳兄弟的制片厂高管实际上非常担心”山民”(特别是那些与麦克斯韦尔案有关的人)观看这部电影并可能提起诽谤诉讼,因此他们没有在弗吉尼亚州或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发行这部电影。这些预防措施可能避免了潜在的诉讼,但无法提升影片的受欢迎程度,它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只上映了几周。这样的反响表明,人们越来越排斥严肃戏剧中被反复使用的山区刻板印象,对山区作为问题地区的兴趣也再次消退。
这一时期严肃电影对山民形象塑造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政府纪录片《田纳西河谷》(1944年)——这是战争信息办公室(OWI)制作的三十多部纪录片之一,主要面向海外观众。这些影片旨在挑战轴心国的宣传攻势,用OWI主任埃尔默·戴维斯的话说,展示”美国的力量与实力”,以及美国的战争目标”将最终造福全世界”。这些影片还旨在反驳好莱坞常见的那种轻浮、暴力和不道德的社会形象。相比之下,许多OWI纪录片宣传的是一个朴实而有美德的民族形象,通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来建设一个更人道的世界。本着这种精神,《田纳西河谷》赞颂了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水电大坝建设项目和科学农业计划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它宣传的愿景与帕雷·洛伦茨颇具影响力的纪录片《河流》(1937年)以及TVA主席大卫·利连索尔1944年关于TVA”奇迹”的畅销书《民主在前进》如出一辙:一片荒芜的土地和看似被击败的人民,通过系统的社会规划和现代科学得以重生。
然而,与上述两部作品相比,《田纳西河谷》更大程度地将高地农民的落后和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而非资本利益集团或垄断性私营电力公司——描绘为社会和环境进步的敌人。这些人胡子拉碴,戴着软塌塌的帽子,在尘土中缓慢挪动。根据旁白所述,经过”多年的与世隔绝……和偏执”,他们几乎无法想象除了”贫穷、愚昧和苦役”之外的任何未来。导演亚历山大·哈米德将大多数农民最初不愿参与政府项目的态度描绘为不仅是自我毁灭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将两个邻居进行了对比:一个是”好”农民(亨利·克拉克),他勉强同意采用等高线耕作和施用磷�ite肥料等科学方法;另一个是”坏”农民(霍勒斯·希金斯),他和衣衫褴褛的家人住在破旧的棚屋里,拒绝参与这些努力。最终,当希金斯看到克拉克因采用新方法而在作物产量和生活质量上取得的显著改善后,他也被说服了。当希金斯报名参加该项目时,旁白总结道,他终于学到了”个人通过与他人合作,才能成为更重要的个人”这一教训。影片以现代集体主义结合科学规划和英雄般的工程技术所创造的光明未来场景作为结尾:一架客机飞越闪闪发光的新大坝;亨利·克拉克一家现在衣着光鲜、吃得饱足,舒适地住在白色护墙板房屋里;他的孩子们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新大坝前欢快地玩耍。
与早期的《山地正义》和《赤裸的爱》等影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影片中,只有个人能够逃离堕落的山地文化,而文化本身仍然停滞不变——《田纳西河谷》提出了通过现代技术和”自愿的”联邦干预实现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复兴的可能性。然而,早期地区主义者关于南方山民文化丰富性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影片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剧烈变革可能带来的重大个人和社会代价。相反,“乡巴佬”农民霍勒斯·希金斯仅仅代表了一个阻碍通往富裕和”进步”的反动路障,为了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利益,这个障碍需要被清除。
《山地正义》和《田纳西河谷》以阿巴拉契亚为背景,主题戏剧性强,显然是例外,恰恰证明了从1936年左右开始电影院对山民形象塑造的重心转移规律:从阿巴拉契亚转向奥扎克,从严肃的社会剧转向音乐喜剧和乡村闹剧——这一转变与反法西斯主义和新政民粹主义时期对”民间”的颂扬相呼应。尽管以南方山区为背景或以山民为题材的电影总数在1920年后的每个十年都急剧下降,但这一类型中喜剧形象的比例却稳步增长:从1920年代电影的14%,到1930年代电影的42%,再到1940年代电影的63%。几乎所有这些喜剧电影都以奥扎克为背景,这不仅反映了该地区与山民讽刺形象之间长期以来的联系,也反映了阿巴拉契亚在全国新闻报道中日益负面的形象。随着东南部山区被定义为暴力煤矿罢工、人间苦难的土地,以及更积极地被定义为大规模政府工程项目的所在地,全国电影观众越来越难以维持他们对该地区作为超越社会经济现实之地的想象。相反,电影制作人和观众更容易将奥扎克——那里缺乏类似的大规模采掘业和政府项目——定义为一个神话般的空间,居住着被夸张漫画化的男男女女。
新电影对欧扎克地区的关注,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几乎是所有杂耍舞台和广播网络乡村幽默演员的故乡,他们共同主演了这些作品。鲍勃·伯恩斯是阿肯色州范布伦的本地人,1937年至1940年间为派拉蒙主演了四部电影,他自称”阿肯色旅行者”,最出名的是他”发明”了一种叫做”巴祖卡”的音乐装置(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于外形相似的二战反坦克武器)。切斯特·劳克和诺里斯·戈夫——广播节目《卢姆和阿布纳》的明星,该节目播出了惊人的二十四年(1931-1955),并衍生出六部基于这些角色的电影——两人都在阿肯色州米纳长大,并将他们的”随手记”杂货店设定在虚构的欧扎克山城松岭镇。弗兰克、莱昂和琼·韦弗,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韦弗兄弟和艾尔维里,来自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最杰出的”乡巴佬”杂耍演员。他们将乡村幽默和音乐与朴实的道德故事相结合,在1930年至1943年间主演了十二部电影。在这个时代的主要乡村喜剧演员中,只有朱迪·卡诺瓦——“山地女金丝雀”,在1940年至1955年间主演了至少十七部电影——不是来自欧扎克地区。
这些表演者跃上大银幕,不仅是因为1930年代中后期对一切山地乡村事物的狂热,还因为”B级电影”的出现——这是由共和影业等低级别制片厂以及派拉蒙和哥伦比亚等大型电影公司制作的高度程式化的低成本电影,旨在作为双片连映的下半场。为了寻找抵消大制作成本的方法,并认识到庞大且仍在扩大的电影观众群(估计到1940年每周达7500万人,到1946年每周达1亿人——占全国人口惊人的三分之二)越来越需要整个下午或晚上的娱乐,制片厂在1930年代中期开发了双片连映,作为以最小的制作成本增加为观众提供双倍娱乐的手段。到1936年,双片连映已成为85%电影院的标配,共和影业和莫诺格拉姆等低级别制片厂几乎专门制作”B级”电影。其中大多数,包括黑帮犯罪剧和浪漫连续剧,主要针对不断扩大的城市观众。然而,共和影业和类似制片厂制作这里讨论的山地乡村音乐喜剧,主要是为了农村和小城镇市场,从193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中期,这个市场一直稳定支持这一类型。
这些电影中有许多只不过是将卡通山地人搬上银幕,就像《肯塔基月光》中那样。鲍勃·伯恩斯的作品《山地音乐》(1937)和《绕山而来》(1940),以及韦弗兄弟和艾尔维里的第一部电影《摇摆你的女士》(1937),只是保罗·韦伯风格的刻板印象集合,展示了《绕山而来》所宣传的”美国山地人属仅存的物种”。这些电影由最薄弱的情节串联,以乡巴佬喜剧和乡村化(但非正宗”乡村”)音乐为特色,记录了山地人的与世隔绝、邋遢和懒惰。在《山地音乐》中,伯恩斯扮演一个”有毛病”的山地男孩,因为工作和刮胡子而给家族蒙羞;在伯恩斯的两部电影中,故事发生地都是”单调镇”。这三部电影都充斥着破烂衣服、蓬乱胡须、赤脚和猎枪的画面(图5.9)。毫不奇怪,大多数影评人认为这些电影平淡肤浅(《综艺》杂志评价《绕山而来》是”一部温和、苍白的山地人混合物”),并嘲笑粗糙的布景和服装。然而,少数人,如《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认为这一类型是”怪异的乐趣”,提供了对真正美国风情的迷人洞察。

图5.9
猎枪、蓬乱的胡须和玉米饼幽默:鲍勃·伯恩斯在《山地音乐》(1938)中的一场猎枪婚礼上送走他的妹妹。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然而,这种真人山地人卡通的风潮是短暂的,因为这种角色塑造几乎没有情节和人物发展的空间。伯恩斯和韦弗兄弟很快放弃了彻底的山地人漫画形象,尽管他们后来的电影,如伯恩斯的《阿肯色旅行者》(1938)和《我来自密苏里》(1939),以及韦弗兄弟的《阿肯色往事》(1938)、《老密苏里》(1940)、《阿肯色法官》(1941)和《欧扎克的牧羊人》(1942),继续以欧扎克地区身份为特色。朱迪·卡诺瓦的《欧扎克的圣女贞德》(1942)也使用了这个地区标签,但除了开场简短的一幕——卡诺瓦穿着格子衬衫、牛仔裤、扎着辫子并挥舞着松鼠步枪——情节和场景(涉及卡诺瓦帮助抓获纳粹间谍网络)与山区几乎没有关系。
与之前”乡巴佬”类型电影中负面和刻板的形象形成对比,这些影片颂扬了”普通百姓”的朴素价值观、真诚和善良,剧情中那些乡下主角们战胜了代表现代美国城市弊病的象征性角色:自命不凡的大城市势利眼、剥削成性的商人和腐败的政客。如同卡尔·桑德堡的诗歌颂词《人民,是的!》(1936)、格兰维尔·希克斯的人民阵线宣言《我爱美国》(1938)、托马斯·哈特·本顿和格兰特·伍德的地方主义艺术,以及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这些故事情节反映了那些年美国文化中对普通民众的普遍赞颂。虽然远不如这些作品或弗兰克·卡普拉赞美”小人物”与既得利益集团抗争的电影三部曲那样精致或有影响力,但韦弗斯、伯恩斯和卡诺瓦的电影同样代表了民主民粹主义和国家认同的精神——在美国面临法西斯主义在海外蔓延和国内持续经济大萧条双重威胁的时期。大都市的评论家和观众继续将这些低成本的乡土喜剧和情节剧斥为过于老套,但在整个二战时期,它们吸引了稳定的农村和小镇观众。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在评论韦弗斯的《山间旋律》时所写:“大城市或大学城里的老练观众……可能会在不该笑的地方发笑”,但”在广袤的乡野以及那些人们仍被真诚地称为’乡亲’的地方,人们会喜欢这部电影。”
也许真人乡巴佬电影吸引力短暂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充分利用懒惰、邋遢、暴力的乡村蠢人这一刻板形象方面,它们根本无法与1930年代和战争年代所有主要动画工作室半定期推出的一系列乡巴佬漫画形象动画片相竞争。由弗里茨·弗雷伦和特克斯·艾弗里等著名动画师执导,这些动画片将各种视觉笑料与韦伯式的熟悉乡巴佬形象混合在一起。所有动画都包含乡村音乐元素和配乐,最重要的是家族世仇这一核心情节主题,动画师让一群山民与外貌相同的对手对抗,同时双方又都与天真的和平主义外来者对抗。
艾弗里的典型作品《曾有一场世仇》(1938)开场是一间破旧的山间小屋,半打乡巴佬在里面吵闹地打盹,只有当一个麦克风神奇地从天花板降下时,他们才中断睡眠在广播电台前表演。歌唱结束后,他们立刻又睡着了。当不可避免的世仇开始时,双方用各种荒谬的武器互相射击(包括一把有多个扳机的步枪和一门能把猪和鸡变成火腿排和煎蛋的榴弹炮)。他们相互的敌意只有对蛋头(Egghead,艾尔默·法德的前身)的蔑视才能超越,蛋头试图说服双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他的努力换来的回报是与两个家族的一场大混战。但即使在蛋头获胜并走出画面后,他还是被”剧院观众席”中一个剪影山民射杀,从而将乡巴佬呈现为不可救药的暴力分子。《曾有一场世仇》虽然是从那个时代其他卡通刻板形象中衍生出的荒诞夸张,但通过展示人类角色而非其他类似卡通中的农场动物,将这些表现与真实的山民联系起来。它还以一个故意取错名的”信不信由你”片段开场,讲述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真实冠军唤猪人(hog-caller),其形象与卡通中的乡巴佬角色几乎一模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动画师在公众心目中将幻想中的”乡巴佬”与南方山区的真实居民联系在一起。
二战前夕,这些动画短片以及鲍勃·伯恩斯和威弗斯乐队作品中出现的韦伯式乡巴佬刻板形象已广为人知。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某个真实社会群体的夸张描绘,或者更常见的是,如某妇女团体评价《山间音乐》中角色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荒谬但无害”的漫画式形象。然而到战争结束时,反对这种日益被视为冒犯性形象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随着数十万来自南阿巴拉契亚和欧扎克地区的人涌入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城市,在军工厂工作,并参军前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作战,批评者们越来越质疑这种将整个地区描绘成与社会经济现实完全脱节的流行观念,并认为这类基于民族和种族的刻板印象越来越站不住脚。这种态度转变在对战后初期最具影响力的乡巴佬形象呈现——1946年迪士尼动画音乐合集《为我谱上乐章》中的卡通音乐短剧”马丁家族与科伊家族”——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短剧呈现了两个懒惰、酗酒、生活在幸福肮脏中的乡巴佬家族之间世仇的标准故事(图5.10)。这些”鲁莽的山里小伙”(配乐歌词如此称呼他们)之间的战斗极其激烈,所有人都在枪林弹雨中丧生,只剩下每个家族各一名少年幸存。他们不可避免地结了婚,在例行的乡村舞蹈场景之后,又开始打架,“像从前一样延续世仇”,让从天上云端俯视的已故亲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图5.10 马丁家族在迪士尼《为我谱上乐章》(1946)中的”马丁家族与科伊家族”片段里,在世仇间隙醉醺醺地休息。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和迪士尼企业提供。© 迪士尼企业公司。
《为我谱上乐章》总体上没有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他们对许多选段过于甜腻和民俗化的基调表示不满。没有哪个片段比”马丁家族与科伊家族”招致更激烈的批评。詹姆斯·艾吉在《国家》杂志上称其”极其侮辱人”,《公益》杂志则认为该片段”毫无品味”。许多评论家认识到这种刻板印象的”白人他者”本质,明确从种族角度进行批评,将这部卡通与类似的非裔美国人刻板形象相比较。《时代》杂志的评论员指出,这首”乡巴佬民谣”会”冒犯那些认为此类漫画与对黑人的’闭嘴听话’式喜剧蔑视同样具有侮辱性的人”。曼尼·法伯在《新共和》杂志上将这部基于”关于乡巴佬的虚假流行态度”设计的卡通,与同一影片中同样”令人尴尬”的威利鲸鱼唱《玉米面包》的卡通相提并论,后者中一群海豚”模仿复兴布道会上的黑人”打着节拍。长期以来作为好莱坞喜剧的固定元素,在大屠杀和”双V”运动——即在海外战胜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战胜种族主义——之后,如此明目张胆的种族和民族刻板印象,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南方白人山民的刻板印象,越来越不被影评人接受,在较小程度上也不被观影公众接受。
这种滑稽的邋遢、粗鲁、荒谬危险的电影乡巴佬形象在二战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喜剧性或愚昧的山民(以及其他贫穷的南方白人)形象在百老汇舞台上出现的频率不如1920年代初和1930年代中期那么高,但非商业剧院制作继续推出喜剧乡巴佬戏剧。韦伯式的漫画形象也出现在战后初期的电影中,如《他说是谋杀》(1945年,由弗雷德·麦克默里和玛乔丽·梅恩主演)、《绕山而来》(1951年,由巴德·阿博特和卢·科斯特洛主演)、《世仇傻瓜》(1952年,由利奥·戈西和鲍厄里男孩主演),以及1959年根据百老汇热门音乐剧改编的成功电影版《小阿布纳》。这些低成本、高度程式化的电影在标准漫画形象上几乎没有新意,尽管《绕山而来》确实邀请了夜总会歌手多萝西·谢伊出演,她自称”公园大道乡巴佬女郎”。在电影中和她的舞台表演中一样,谢伊将纽约的精致与利用乡巴佬刻板印象的新奇曲目相结合,如《世仇、打架和吵闹》和《(你只会是)爸爸猎枪上的又一个刻痕(如果你不娶我的话)》(图5.11)。尽管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创新性的尝试来复兴这一类型,但这些电影似乎越来越陈旧,与当代美国人的观点格格不入。随着这种低俗的卡通乡巴佬形象在战后岁月里逐渐失去评论家和观众的青睐,电影中对这类原始人物的呈现转变为演员珀西·基尔布莱德和玛乔丽·梅恩所塑造的更柔和、更讨人喜欢的形象,他们饰演的凯特尔妈妈和凯特尔爸爸在整个195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凯特尔系列电影将邋遢、反现代的角色与古老的闹剧套路相结合,预示了乡巴佬形象在战后电视媒介中的进一步驯化。

图5.11 多萝西·谢伊,“公园大道乡巴佬女郎”,出自阿博特和科斯特洛主演的《绕山而来》(1951)宣传照。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凯特尔一家最初是1947年电影《鸡蛋与我》中的配角,该片改编自贝蒂·麦克唐纳1945年的畅销书,讲述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被迫适应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山区养鸡场新生活的故事。麦克唐纳笔下的凯特尔妈妈、凯特尔爸爸和他们的十五个孩子,或多或少是乔治·华盛顿·哈里斯1867年《萨特·洛文古德故事集》中萨特·洛文古德那衣衫褴褛、人丁兴旺家庭的直系后裔,只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美化和文明化处理。与哈里斯笔下的家族一样,麦克唐纳的凯特尔一家散发着一种邋遢懒散却生机勃勃的乡野气息,完全不顾中产阶级的社交礼仪规范。凯特尔妈妈是”一个身材臃肿的胖女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家居裙”,总是在衣服底下调整自己的身体,还宣扬着这样的座右铭:“我痒——我就挠——那又怎样!”同样,凯特尔爸爸留着”浓密飘逸的大胡子,上面沾满了面包屑”,穿着”好几层脏兮兮的内衣和毛衣”,以懒惰、邋遢和不断向邻居、叙述者及其丈夫”借”东西而著称。但麦克唐纳并没有把她的角色塑造成完全堕落或肮脏的形象,使他们与前十年真人和动画电影中的乡巴佬形象有所区别。虽然生活简朴,凯特尔一家并非穷困潦倒。他们本质上是讨人喜欢的人,对彼此和邻居都充满感情,在帮助故事中的女叙述者适应新环境中缺乏城市便利设施方面不可或缺。
电影版的凯特尔一家更加温和可爱。在梅恩和基尔布莱德的精湛演绎下(两人都长期专注于乡村角色),银幕上的凯特尔一家展现出一种质朴的魅力,尽管凯特尔妈妈用被形容为”换挡声、碎石机、咖啡研磨机”般的嗓音呼唤孩子们。虽然名义上的主角弗雷德·麦克默里和克劳黛·科尔伯特获得了好评,但评论家们把最高的赞誉留给了梅恩和基尔布莱德。大多数评论者承认,这对乡村搭档是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票房收入550万美元)的最大功臣。
认识到这对搭档的巨大潜力,环球影业的高管们在制片人伦纳德·戈德斯坦的带领下,迅速让这对夫妇主演了他们自己的大获成功的电影《凯特尔妈妈和爸爸》(1949年),随后从1950年到1957年又推出了十一部续集。尽管评论家们抨击这些电影的闹剧桥段和老套笑话,但他们也不得不勉强承认这些电影对农村和小镇观众的吸引力,甚至对据说更有品味的城市观众也有吸引力。“笑声几乎要震塌地基了”,一位评论家惊叹道,他评论的是《凯特尔妈妈和爸爸回农场》(1951年,系列第三部)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影院的观众反应。
这些电影属于中上档次的”B级片”,三周内以40万美元或更少的成本拍摄完成,完美体现了戈德斯坦的理念:制作大量廉价电影,虽然可能无法教育或启发观众,但”能在票房上赚钱”。它们确实赚钱了,仅系列前三部就获得了惊人的800万美元收入,整个系列估计赚了3500万美元。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凯特尔系列和”会说话的骡子弗朗西斯”系列一起,把环球国际影业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戈德斯坦不断重复他的口头禅”除了观众没人喜欢我的电影”,并自豪地说,影院经营者给凯特尔系列的不是奥斯卡奖,而是更有价值的”四块好时巧克力”奖。
是什么造就了”凯特尔妈妈和爸爸”现象?首先,像所有乡巴佬角色一样,凯特尔一家引发了嘲笑与同情的混合情感。一方面,观众可以嘲笑这些无知笨拙的乡下人,他们在快节奏的城市化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包括去纽约(1950年)、巴黎(1953年)和夏威夷(1955年)度假。例如,1949年原版《凯特尔妈妈和爸爸》的情节涉及凯特尔一家赢得了一座全自动”预制未来样板房”,凯特尔爸爸与新设备展开搏斗。然而,这些电影的吸引力也源于许多观众自己对日益机械化和标准化的战后美国的陌生感和不安感,以及电影对凯特尔一家面对城市骗子、势利眼和多管闲事的官僚时所展现的基本善良和诚实的正面描绘。珀西·基尔布莱德认为这些角色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卑微的流浪汉,都能感觉比凯特尔一家优越”;但伦纳德·戈德斯坦理解他电影受欢迎的双重性质:“也许人们感觉有点优越,同时也许他们认出了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他在1953年评论道。“这种认同感,无论观众是否向自己承认,与接受度同样重要。”
尽管情节通常荒诞不经,行为和态度也颇为离奇,但凯特尔一家及其众多子女身上真挚的人性光辉始终闪耀(图5.12)。凯特尔妈妈可能会挥舞猎枪驱赶试图收回她房子的地方当局(《凯特尔夫妇》,1949年),也可能会对一位傲慢的社工试图教她”卫生”重要性而怒发冲冠(《凯特尔夫妇重返农场》,1951年),但她深爱着丈夫和家人,总是向有需要的邻居伸出援手。同样,观众既能在《凯特尔夫妇》中对凯特尔爸爸不懂现代便利设施感到优越,又能欣赏他的淡泊名利和对赢得”梦想之家”而非他原本更朴素目标的常识性反应:“不需要新房子,”他慢悠悠地说,“……倒是需要个新烟袋。”

捕捉1950年代家庭价值观的精髓:凯特尔夫妇(玛乔丽·梅恩和珀西·基尔布莱德)与他们庞大的子女群,出自《凯特尔夫妇重返农场》(1950年)的宣传剧照。图片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
现代郊区”梦想之家”的情节暗示了这些电影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它们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评论,尽管是间接的。在疯狂的故事线和复古的人物塑造之下,凯特尔系列电影与战后早期的社会价值观和关注点完美契合。凯特尔夫妇与他们似乎无穷无尽的子女之间充满爱的关系,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趋势——更早结婚、生育更多孩子,以及对核心家庭的关注(而非过去的多代亲属网络)。凯特尔一家也成为数百万美国人的代言人,这些人首次面对郊区化、消费品丰富和休闲旅行这个令人困惑的新世界。毫无疑问,许多观众既对邋遢的凯特尔妈妈感到优越,又能产生认同——在《凯特尔夫妇进城》(1950年)中,她在纽约的”巴黎卢顺迪美容沙龙”做了最新潮的发型,然后回到酒店房间用木桶泡脚;或者认同《凯特尔夫妇度假记》(1953年)中的凯特尔爸爸,他试图在巴黎的街道和社交圈中找到方向。凯特尔系列电影甚至随意地暗示了原子弹和冷战焦虑。在《凯特尔夫妇重返农场》(1951年)中,凯特尔爸爸被铀辐射,而在《凯特尔夫妇度假记》中,他卷入了一个国际间谍网络。闹剧与温馨、古老的喜剧套路与当下社会关切的融合,有助于解释凯特尔一家在文化和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从大萧条和战争年代的物资短缺到战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引起的共鸣。
最后,梅恩和基尔布莱德饰演的凯特尔夫妇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如此高的人气,是因为他们坚决避免了早期的乡巴佬(hillbilly)标签、形象和人物塑造。前四集中有三集的场景设置在远离《我和蛋》中崎岖山区的大都市或郊区,即使后来电影中偶尔出现的乡村场景,也更可能是美国中部的小镇或县集市,而非与世隔绝的偏远林区。戈德斯坦和他的主演们拒绝任何传统私酿酒和家族世仇情节的暗示。凯特尔爸爸破旧的衣服和凯特尔家的大家庭是与他们声名狼藉的电影前辈们仅有的联系,而且随着系列的推进,这两者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一位评论家注意到凯特尔夫妇的幽默越来越通用化,与他们最初的人物塑造几乎没有关系。这位评论家指出,后期凯特尔电影中的大多数场景”与他们众多的子女完全无关,或者说,与任何具有凯特尔特色的东西都无关……这些是麦克·塞内特在他年轻时从当时已经过时的江湖卖艺和巡回滑稽剧时代挖掘出来的噱头、情境和套路。“事实上,唯一一部以传统乡巴佬形象为特色的电影《奥扎克的凯特尔一家》(1957年),讲述凯特尔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拜访她在奥扎克农场上游手好闲的表亲塞奇,是在系列走下坡路、珀西·基尔布莱德退出之后拍摄的。在这里,凯特尔妈妈代表社会秩序和整洁,而塞奇则象征着凯特尔一家粗犷质朴的起源。讽刺的是,回归标准的乡巴佬套路和故事线揭示了编剧和制片人已经走入的创作死胡同。该系列在一年后结束。
战后美国文化和意识中,乡巴佬形象普遍退潮,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期,凯特尔系列电影中乡巴佬角色的淡出正是这一现象的缩影。凯特尔一家的郊区化也反映了二战期间开始的南方山区身份和文化的类似商品化和驯化过程。1942年6月《House & Garden》杂志的特刊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新态度,该期专门介绍”我们的南方高地”丰富多彩的民俗和手工艺,并推广基于山区图案和形式的大规模生产的家居用品和配饰,杂志后来将这种风格称为”全新且独特的美国风格……南方高地乡村风”。战时《国家地理》的报道仍然聚焦于南方山区的贫困和简朴,尽管明确拒绝了普遍堕落的刻板印象,但战后的文章则强调住宿和旅行乐趣,对社会经济状况只是顺带提及,甚至完全不提。南方山区不再是危险的荒野,也不再是异常、贫困和敌对人群的家园,在1940年代旅行和探险杂志的页面上,它被重新概念化为一个风景如画、安全的地区,居住着友好的民间工匠,适合中产阶级度假。
随着人们以这种新眼光看待山区,乡巴佬形象在电影和整个文化领域中逐渐淡出。直到1960年代,由于贫困的阿巴拉契亚人史无前例地迁移到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城市,以及”向贫困宣战”计划的启动,乡巴佬才重新回到文化聚光灯下,主要出现在战后美国的主导媒体——电视上。
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与南方山区及其居民相关的图像和新闻报道出现的频率达到了自193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图像以各种媒体形式呈现,最突出地出现在电视上,既有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更常见的是一系列非常成功且影响深远的情景喜剧。在那个电视覆盖面极广、三大电视网几乎完全控制电波的时代,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此后也未曾再现的全国性”共同文化”,电视图像在塑造公众对美国社会和价值观的整体认知,以及对南方山区人民的特定认知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电视上对”乡巴佬”的描绘提供了我们熟悉形象的驯化版本,去除了大部分表面上的卑劣和邋遢。乡巴佬形象的这种转变部分是对战后电视严格内容限制的回应,这些限制源于(或以此为理由)该媒介及其观看空间的独特私密性。净化后的乡巴佬形象也部分反映了电视情景喜剧的程式化特性,以及需要观众每周都愿意再次收看的角色。虽然很容易将这些节目简单地视为针对不成熟的农村和小镇观众的低俗逃避现实的娱乐,但以乡巴佬角色和场景为特色的电视节目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南方山区人民和状况的关注,以及更广泛地反映了战后美国的可能性和局限性。1950年代末,对乡巴佬”入侵”中西部城市的恐惧引发了新闻报道,描述那些落后和堕落的男男女女,尽管他们拥有”优越”的种族血统,却威胁着工业腹地的和谐。1960年代初见证了阿巴拉契亚作为(据称)富裕社会中地方性”贫困口袋”的重新发现。然而,与过去一样,该地区的人民也被视为未受腐蚀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继承者,他们挑战现代都市性,指出物质主义”进步”的精神和伦理代价。这些节目也是对当时种族斗争的回应。在民权运动揭露南方白人种族主义丑陋面目的时代,这些节目描绘了田园诗般、纯白人的南方景观,颂扬南方白人朴实的善良,进而延伸到整个美国。《真正的麦科伊一家》、《安迪·格里菲斯秀》和《贝弗利山庄乡巴佬》从未明确将这种联系与全国头条新闻挂钩。尽管如此,关于贫困山民的新闻报道以及民权运动的政治和文化漩涡构成了全国电视观众观看和解读这些节目的历史背景。
电视上最早出现的乡巴佬形象,大多是对更早期杂耍表演、广播和电影中角色塑造的高度模仿。在1952年《我的英雄》中一集简单命名为”乡巴佬”的剧集里,罗伯特(鲍勃)·卡明斯饰演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卷入了一场老套的肯塔基州世仇故事,其中包括枪战场面和一位名叫露露贝尔·哈特菲尔德的多情山地女孩。杰克·本尼在1958年的一期节目中也使用了类似的陈腐刻板印象。在一个闪回场景中,他将自己虚构的阿肯色州出身描绘成乡村小提琴手”齐克·本尼和他的欧扎克乡巴佬乐队”。本尼身穿连体内衣、工装裤和草编礼帽,在表演《你是我的阳光》等商业乡村歌曲的间隙,穿插着关于童养媳和数到四就像马一样跺脚的无知乡下人的喜剧段子。
本尼的节目是1957年10月至1958年4月间至少四部使用乡巴佬角色和形象的情景喜剧和综艺节目之一。其中最有趣的是《鲍勃·卡明斯秀》,卡明斯在剧中通常扮演一位风度翩翩、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时尚摄影师。然而在”鲍勃变乡巴佬”这一集中,卡明斯和他的姐姐打扮成衣衫褴褛、缺牙的乡下人,试图给他的侄子查克(正试图讨好他势利的约会对象)上一课,让他明白社会等级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卡明斯一边傻笑着给一只小猪挤奶,一边把那位名媛吓得尖叫着逃出房子。最后,鲍勃对查克和电视观众说教道:“任何建立在阶级差异上的恋情都不会有好结果。”“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里不会有”,他姐姐附和道。因此,这个节目通过强化长期以来对山区居民贫穷、愚蠢和邋遢的刻板印象,否定了阶级分化,维护了美国人普遍持有的”无阶级”信念。有趣的是,这个节目的编剧和制片人正是保罗·亨宁,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电视乡巴佬形象的塑造,并在四年后通过《贝弗利乡巴佬》将这一形象带入了美国文化的核心。
1957年和1958年电视乡巴佬形象激增,不仅仅是因为重复使用陈腐刻板印象的便利。这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刻:全国性的新闻报道表达了长期积累的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源于南方山区居民大规模涌入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城市。二战开始后的三十年间,超过三百万南部阿巴拉契亚人外迁——这是1910年至1970年间至少一千一百万黑人和白人迁往北方和西部的更大规模南方人口流散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阿巴拉契亚人的外迁大约在世纪之交真正开始,并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持续稳定进行。尽管大萧条时期移民人数显著增加,但在1940年代初期随着工业战争生产工作的繁荣而急剧增长,并在1950年代再次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煤矿的广泛机械化和天然气作为煤炭替代品的兴起,数百万南部阿巴拉契亚人逃离煤田的大规模失业,前往辛辛那提、芝加哥、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以及俄亥俄州南部和印第安纳州的小城镇,那里经济强劲且外国移民受到限制,工作机会相当充足。
与南方黑人同胞面临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不同,大多数阿巴拉契亚移民能够找到工作并逐步改善经济状况。然而,在战后的中西部,南方白人移民被普遍视为无法同化和不受欢迎的群体。招聘启事上写着”南方人勿扰”,餐馆老板拒绝为”乡巴佬”服务,这些情况并不罕见。南部阿巴拉契亚人被贴上各种贬义标签,包括”WASPs”(白人阿巴拉契亚南方新教徒)、“SAMs”(南部阿巴拉契亚移民)、“山脊跑者”(ridgerunners)、“荆棘跳跃者”(briar-hoppers),以及最普遍的”乡巴佬”(hillbillies)。在这种语境下,“乡巴佬”无疑是一个贬义词,外来的山区居民成为各种粗俗程度不等的笑话的对象。“知道为什么布伦特·斯宾塞大桥(横跨辛辛那提的俄亥俄河)要建成双层吗?”当地有这样一个笑话。“这样所有离开俄亥俄州的乡巴佬就可以脱下鞋子,递给下面从肯塔基州去俄亥俄州的表亲们。”更刻薄的是1950年代常讲的一个笑话:现在只有四十八个州了,因为”整个肯塔基州都搬到了俄亥俄州,而俄亥俄州完蛋了。“中西部对阿巴拉契亚移民普遍反感的最明显例证,来自1951年韦恩州立大学对底特律居民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要求受访者指出”不受欢迎的人”,即”不适合留在城市里的人”。21%的受访者指出了”贫穷的南方白人”和”乡巴佬”,仅次于”罪犯”和”黑帮分子”,远高于”流浪者”、“黑人”和”外国人”。
至少从1930年代开始,南方移民”问题”就成为中西部城市日益关注的地区性议题。1950年代末,一系列在全国发行的社会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首次将这一问题推向全国舞台。这些城市贫民的白人身份是作者们的主要关注点。詹姆斯·麦克斯韦尔的《从山区下来,进入贫民窟》(1956年)以明确的种族化视角呈现其主题。文章开篇引用了一位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的话,表达了对一个未开化且危险独立的群体的恐惧。随后麦克斯韦尔告诉他那些想必震惊的读者,这个群体不是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个”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受优待的”群体。麦克斯韦尔大量依赖来自敌对执法官员的信息,引用了一位警官的话,指控这些新来者犯有各种罪行,包括”枪击、忽视儿童、强奸……以及乱伦”。尽管他强调了移民面临的困难,但麦克斯韦尔总体上将他们描绘成一个与城市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严重脱节的落后群体。
这类恐惧煽动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阿尔伯特·沃托1958年2月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乡巴佬入侵芝加哥》。“城市最棘手的融合问题与黑人无关”——文章开头这样写道——“而是涉及一小批来自南方的白人新教徒、早期美国移民——他们通常骄傲、贫穷、原始,而且动刀子很快。”接下来是对”南方’乡巴佬’“源源不断的负面甚至恶毒的描述,沃托自相矛盾地将他们描述为”冷漠却又傲慢”。与麦克斯韦尔一样依赖警方消息来源,沃托声称这些新来者”排外、骄傲、无序,不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他们有”多产的妻子和众多的孩子”,他们的”家务管理随意到近乎混乱”,而且”他们的习惯——在乱伦和法定强奸等事项上——明显与城市法律要求相悖”。他还引用了《芝加哥周日论坛报》一篇他认为残酷但准确的社论,该社论将”南方乡巴佬移民”的到来比作”蝗灾”,并描述他们拥有”最低的生活水平和道德准则(如果有的话)、最大的酒量,以及醉酒时最野蛮的行为——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醉酒”。沃托哀叹道,尽管他们本应是”’优等’美国人的原型”,但”在芝加哥街头,他们似乎是美国梦的疯狂变异”。
芝加哥市中心、底特律和其他中西部城市的许多本地白人对新来者的南方口音、对”乡巴佬酒馆”里喧闹乡村音乐和酒精的喜好、对紧密亲属网络的坚持,以及在门廊聚集和在路边修车的习惯(这些做法源于经济限制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保留)感到恼火。他们将这些社会习俗和行为视为长期建立的社区衰败的原因——而非实际上的症状。然而,沃托的一个小标题是”他们种族的耻辱?“这一事实表明,对这些移民最大的担忧不仅仅是他们的贫困或社会习俗,而是他们是贫穷的白人——在那个时代,许多中产阶级白人认为只有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应该”是穷人。长期以来将贫困、懒惰、酗酒和暴力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联系在一起的北方白人,现在发现这种种族界限受到了威胁——他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存在类似的习惯,这些人生活在(一个带有种族色彩的标签)“乡巴佬丛林”中。沃托哀叹道,南方移民”混淆了所有关于种族、宗教和文化纯洁性的观念”。他提出的唯一希望是,如果少数曾在南方城市生活过的人能够迅速同化,从而鼓励他们那些不守规矩的同胞效仿。
沃托的长篇大论引来了一些读者的愤怒回应,包括一位密歇根读者将这些移民比作他们的祖先——那些在独立战争期间在国王山和考彭斯击败英国人的先辈。对这位回应者来说,移民拒绝与政府和警察当局合作、坚持保持独特身份的做法,代表了一种值得赞扬的正当顽强独立精神。这些读者来信揭示了粗犷山民神话作为堕落乡巴佬形象对立面的持续影响力。它们也表明存在一个潜在的受众群体,愿意接受对阿巴拉契亚移民更正面的描绘。《真正的麦考伊一家》是网络电视上第一部乡村情景喜剧,也是最成功的之一,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对南方山区移民的柔化愿景。
《真正的麦考伊一家》于1957年秋季首播,讲述了一个西弗吉尼亚农场家庭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谷寻求更好生活的故事。与沃托及其同事或《愤怒的葡萄》相比,该剧呈现了一个更新颖、更乐观的南方农业移民故事——它承认了富裕时代中美国人面临的经济困难,但认为这些困难最终可以仅凭个人努力来克服。与《愤怒的葡萄》(以及后来的《贝弗利山人》)中的著名场景一样,试播集开场便是一个多代同堂的南方移民家庭,驾驶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行驶在加利福尼亚的公路上。这个家庭反映了人们对山区家庭扩展亲属网络以及山区妇女终身生育能力的观念。“魁梧的山区小伙”卢克·麦考伊(理查德·克伦纳饰)和他二十岁的妻子凯特身旁,坐着卢克七岁的弟弟小卢克、十二岁的妹妹”哈西姨妈”,以及麦考伊爷爷——“一个地道的……满脸胡茬的乡巴佬标本”(图6.1)。与乔德一家一样,一名公路巡警拦下了麦考伊一家。然而,与乔德一家遭受的蔑视和敌意不同,这里友善的警察只是想归还从他们车后掉落的备用轮胎,并祝他们”好运”。当麦考伊一家到达目的地时,他们来到的是一个从亲戚那里继承的破旧但可用的农场,而不是肮脏的流动劳工营地。

图6.1
在《真正的麦考伊一家》的宣传照中,和蔼的爷爷被他质朴的家人环绕。(从左到右,后排:凯特·麦考伊[凯瑟琳·诺兰]、阿莫斯·麦考伊爷爷[沃尔特·布伦南]、卢克·麦考伊[理查德·克伦纳];前排:小卢克[迈克尔·温克尔曼]、哈西姨妈[莉迪亚·里德]。)图片由俄克拉荷马城国家牛仔与西部遗产博物馆迪金森研究中心沃尔特·布伦南收藏提供。
与《愤怒的葡萄》更为相似的是主角们持续的经济挣扎。导演海·阿弗贝克认为,该剧的受欢迎程度源于其”能够与贫困抗争的前提”,但这场抗争麦考伊一家通常都会失败。例如,在第三季的一集中,当一位推销员向他们保证电视机现在已经便宜到”任何收入一般的家庭都买得起”时,卢克沮丧地回答:“如果我们的收入哪天能达到一般水平,我们会回来找你的。”尽管他们在那集结尾确实买了一台电视,但贯穿该剧六年播出期间的”节衣缩食”和缓慢而不稳定的经济进步主题,与1950年代末家庭情景喜剧中舒适郊区富裕生活的主流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经济困难的背景也暗示,贫困或接近贫困只是麦考伊一家”山区文化”的一部分。
脾气暴躁、守旧但可爱的爷爷由资深性格演员沃尔特·布伦南饰演,他是该剧无可争议的明星,也是反对一切现代事物的落后山民的典型代表——从”自来水”和每日洗澡,到购买新车和开设银行账户。“其实只有一条规则,”阿弗贝克这样总结剧本的特点,“那就是不管是什么,爷爷都反对。”然而,尽管他性格乖戾,爷爷也代表着强烈的职业道德、有尊严的贫困,以及多年耕作土地所积累的基本常识。当他被银行拒绝农场贷款时,爷爷质疑贷款官员过度依赖官僚方法和”科学”调查。“数字能告诉你那片土地有多肥沃吗?数字能告诉你犁地时有多轻松,刀片不会被任何石头磕到吗……你不是用心去看一个农场,”他训斥那位年轻的银行家,“你是用你的钢笔去看的!”这种对现代生活的无知与对土地和基本人性的了解相结合的特点,并非山区居民形象所独有,自乔纳森大哥时代以来就是乡村人物形象的固定元素,也是1960年代所有乡村情景喜剧的核心。
然而,除了爷爷的性格之外,角色们的山民身份通常被淡化处理,只有少数几集例外,比如《小卢克的教育》中小卢克被同学称为”愚蠢的乡巴佬(hillbilly)“,或者《全镇的话题》中他通过画一系列图画帮助隐藏爷爷的文盲身份,让爷爷在公众集会上”朗读”——客厅里的乡巴佬。麦科伊一家的穿着和行为就像典型的农场家庭(至少是好莱坞制片人想象中的样子),大多数剧情和当时其他情景喜剧一样,旨在通过幽默但具有教育意义的方式传达关于家庭、勤劳和正直重要性的道德教训。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剧本中,制片人都试图将电视剧中麦科伊一家的落后和卑微地位与当代山民区分开来。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宣传之旅中,布伦南在一间木屋前摆出持枪姿势拍照,但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在剧中的角色与他在”一个类似麦科伊的小社区”中遇到的当地居民区分开来。“爷爷是个老古董,”他向《电视指南》记者解释道,“这些麦科伊一家是思想相当现代的人。实际上没有太多真正的联系。”同样,在1961年一集名为《回到西弗吉尼亚》的剧集中,麦科伊家族回乡庆祝曾祖母的百岁生日。他们为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原以为会发现亲戚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却惊讶地发现亲戚们住在舒适的中产阶级房屋里,配有制冰冰箱、满铺的油毡地板和电视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在新建的纸箱厂的工作。
这条故事线也探讨了这种进步的局限性,以及麦科伊家亲戚们所做的浮士德式交易。在随后的剧集中,当爷爷拒绝将曾祖母出于怀旧原因想要保留的一块关键土地卖给纸箱公司后,他所有的亲戚都被解雇了。爷爷试图安慰他的亲人,向他们保证”麦科伊家的人是土地的子民”,他们都可以回去务农。然而对于爷爷的亲戚杰德和迈拉来说,一旦接触过”生活中更美好的事物”,这种回归土地是不可能的。“油毡地板会让人上瘾,”迈拉叹息道;“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吃那些电视晚餐,我发誓我会死的,”杰德补充道。编剧们将即便在当时也被视为低档的家居用品作为现代生活的象征,以及农村伦理的丧失,这提供了对进步”代价”的有限质疑。这条故事线(尽管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评论了采掘业对阿巴拉契亚地区土地和人民的剥削,反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以及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代价的担忧。然而最终,这种工业驱动的消费主义与田园伦理之间的冲突被巧妙化解:爷爷同意将土地卖给纸箱公司,而工厂老板同意将曾祖母的房子搬迁到山顶,在那里她可以俯瞰整个山谷(尽管没有提到山谷可能会被烟雾笼罩!)。该剧既提出了关于进步代价的问题,又以一种最终维护大众消费主义和工业发展至上地位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编剧欧文和诺曼·平卡斯发现,1950年代的电视网络高管最初对播出以农村为背景的情景喜剧非常谨慎,只有ABC——三大电视网中最小、最不成功的一个——愿意冒险尝试这种未经检验的产品。《真正的麦科伊一家》的巨大成功(1958年收视率排名第八,1960年排名第五,从1958年到1961年从未跌出前二十名)展示了其他农村题材节目的巨大潜力——电视网高管们很快就将这一教训铭记于心。该剧对后来的田园喜剧也产生了更具体的影响。保罗·亨宁曾为该系列编写过几集剧本,他直接借用了该剧的开场用于《贝弗利乡巴佬》,而该剧的两位主要编剧吉姆·弗里策尔和埃弗雷特·格林鲍姆(他们撰写了上述西弗吉尼亚剧集)后来为下一部大获成功的农村喜剧《安迪·格里菲斯秀》编写了许多剧集,该剧于1960年首播。
《安迪·格里菲斯秀》仍然是电视史上最成功的节目之一。在1960年至1968年播出期间,它一直保持在收视率前十名,1967年更是排名第一,自开播以来从未停播。山民只是该节目前两年的偶尔出现的角色,节目通常颂扬小镇生活的简单快乐和烦恼。但该剧始终与乡巴佬(hillbilly)形象有着至少是间接的联系。虚构的梅伯里镇以格里菲斯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艾里山为原型,该镇靠近弗吉尼亚州边界,位于蓝岭山脉边缘。格里菲斯因扮演乡村土包子而成名——他于1953年以乡巴佬单口喜剧《那是什么——橄榄球》开启职业生涯,并在1955年至1958年间在百老汇、电视和电影中成功塑造了乡下兵威尔·斯托克代尔一角(出自《没时间当中士》)。他最初的舞台形象与刻板的乡巴佬形象如此紧密交织,以至于他的第一位经纪人将他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小阿布纳(Li’l Abner)!“——这让格里菲斯颇为懊恼。
这些粗犷、略显邋遢的老年人是该剧前两季中为数不多的山区居民代表,他们作为安迪·泰勒警长(格里菲斯饰)和梅伯里镇民的乡下亲戚出现,显得朴实无华且略带敌意——而梅伯里镇民本身在大多数城市外来者眼中也被视为乡巴佬。这些山民角色象征着固执、无知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不信任,他们往往反对任何改善生活的努力。例如,在1962年的一集中,山区农民雷夫·霍利斯特拒绝接种破伤风疫苗,直到安迪运用逆向心理,唱起了他将在雷夫葬礼上表演的歌曲。更常见的是,该剧融入了标准的山民主题,如私酿酒(前四季中使用了六次)和世仇。在《世仇就是世仇》(1960年)这一集中,剧情大致基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著名世仇家族中罗珊娜·麦科伊和约翰斯·哈特菲尔德的爱情故事,两个山区农民延续着一场毫无意义的世仇,双方都已记不清起因,并禁止他们的孩子相互结婚。尽管两人都假装想要杀死对方,但每个人都害怕冒生命危险去完成这件事。在这里,老一代山民被塑造成无能的暴力乡巴佬,但他们那些刻板印象较少的孩子则代表着这类人弥合陈旧错误的”山区文化”与理想化的当代美国之间鸿沟的能力。
从1963年3月开始,该剧开始推出体现神话般山民形象不同但相关方面的常驻角色。布里斯科·达林(丹佛·派尔饰)和他的家人代表着无拘无束的音乐山民,这一形象可以追溯到坎伯兰山脊跑者乐队、山地人弦乐队,甚至阿肯色旅行者。作为过时但真实的山区文化象征,达林一家迷信、教育程度低、说话慢吞吞或沉默寡言(一个反复出现的笑点是四个达林家的儿子除了唱歌时从不说一个字),并且自给自足、怡然自得。但他们在剧中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音乐娱乐。实际上,达林家的儿子们是来自密苏里州欧扎克山区的弦乐队迪拉德乐队,他们在节目中演奏的许多歌曲都是自己创作的。

图6.2
“有时间呼吸,就有时间玩音乐”:达林一家作为《安迪·格里菲斯秀》(1963-1964)中阴郁音乐山民的典型代表。图片由TAGSRWC档案馆提供。
音乐是达林一家生活方式的核心,这一点由家族族长布里斯科反复强调。“有时间呼吸,就有时间玩音乐”,他在一集中对安迪说。虽然他们明显被塑造成滑稽的守旧派,但这并不是对韦伯式山地人的贬低描绘,而是对真正本土民间音乐的赞美。达林一家提到了许多名字可笑的歌曲,如《别用大棍子打你奶奶》,但他们实际演奏的要么是迪拉德乐队自己创作的歌曲,要么是传统的南方民谣,如《把卷心菜煮烂》和《爱与欢笑各有其时》。这家人在定期造访梅伯里时似乎总是有些不自在,甚至对镇民构成潜在威胁(布里斯科在一集中绑架了安迪的比阿姨,把她带回自己的小屋,试图说服她嫁给他)。但泰勒警长欣赏他们真实的山区举止和文化,这种感情是相互的。“你那发型可能是城里样式,”布里斯科温暖地对泰勒说,“但你的心是用碗塑造的。”
如果说达林一家代表着略显鲁莽的音乐山民,那么欧内斯特·T·巴斯则象征着疯狂的山野人,狂野到连他的山民同胞都视他为威胁。“哦,他是个祸害,”当安迪问在哪里能找到他时,布里斯科·达林的女婿解释道,“祸害会自己找上你。”由霍华德·莫里斯饰演的巴斯是个半野蛮人,走路像猿猴,尖叫起来像黑猩猩。他的标志性动作是往窗户扔石头和砖块。

图6.3
衣衫不整、脾气暴躁的欧内斯特·T·巴斯(霍华德·莫里斯饰)手持砖块策划复仇,梅伯里镇理发师弗洛伊德·劳森在一旁观望(局部)。1965年12月10日,《安迪·格里菲斯秀》。图片由威斯康星电影与戏剧研究中心提供。WCFTR-2217。
就像他之前的萨特·洛文古德一样,他是个”自然人”,不断吹嘘自己的体力,曾自豪地提到他能背着一头骡子走五英里。“我有点坏,”巴斯羞怯地承认,“但我用真正的健康来弥补。”尽管他不断试图融入社会和社会机构——不同的剧集描绘了他试图参军、在正式招待会上社交以及接受小学教育的努力——但他与文明的每一次接触都不可避免地以灾难告终,每集结尾都是泰勒警长催促他回到山里,希望他不要再回来。虽然巴斯表面上是个喜剧角色,但潜在的暴力始终隐藏在他的古怪行为之下,这个角色与《可敬的大卫》中外表凶恶的哈特本家族、《小阿布纳》中的斯克拉格家族,甚至《激流四勇士》中的山野蛮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大。
这些”山民”剧集的播出时间表明,它们并非随机选择的故事线,而是受到历史背景的塑造和反映。达林一家和欧内斯特·T·巴斯在1963年3月至1964年12月期间出现在八集节目中,但此后仅在一集额外的节目中出现,而且1966年10月之后,该剧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山民角色。这种山民形象短暂激增的部分原因无疑是《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巨大成功。但与那部剧一样,达林和巴斯的剧集也是对南部山区及其居民在全国意识中突然重新出现的回应,以及阿巴拉契亚被视为一个独特”问题地区”这一观念的反映。这些发展又是1960年代初美国重新发现贫困问题的一部分,这一令人不安的认识挑战了中产阶级普遍持有的信念——即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阿巴拉契亚首次重新进入全国视野是在1960年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总统初选期间,候选人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将该州的贫困和饥饿问题作为其竞选的主要议题。肯尼迪当选后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为西弗吉尼亚州实施紧急救济立法。他还支持建立地区发展管理局(ADA),为”萧条地区”提供发展贷款和拨款,包括某些阿巴拉契亚州的部分地区。然而,地区发展管理局的项目普遍资金不足且管理不善,肯尼迪对区域性或全国性反贫困计划的承诺也很有限。他和许多其他人当时也尚未将整个东南部山区视为”阿巴拉契亚”——一个繁荣国家中同质化的”问题地区”。这两种观念在1962年至1963年初之间随着三本有影响力的著作的出版而发生了改变。《南阿巴拉契亚地区——一项调查》(The Southern Appalachian Region—A Survey)是一部学术论文集,将阿巴拉契亚呈现为一个统一但问题重重的地区。哈里·考迪尔的《夜幕降临坎伯兰》(Night Comes to the Cumberlands,副标题为《一个萧条地区的传记》)追溯了该地区遭受经济剥削的历史,将阿巴拉契亚定义为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居住着饱受摧残的人民。最后,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是三本书中影响最大的,呼吁采取果断行动来应对四千万到五千万似乎隐形的美国贫困人口,他们”身心俱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中经历着不必要的苦难”。阿巴拉契亚和阿巴拉契亚移民(“城市山民”)是他书中的核心关注点,哈林顿将该地区呈现为美国白人贫困的集中地,相当于全国内城区的黑人贫困人口。1962年以CBS新闻纪录片《阿巴拉契亚的圣诞节》收尾,该片动人地对比了圣诞节富足的理想与偏远阿巴拉契亚山谷(hollers)中”悲惨”的贫困。
这些作品促使肯尼迪及其经济顾问将新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阿巴拉契亚的贫困问题上,最终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内宣布”向贫困无条件宣战”,成立经济机会办公室,并建立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尽管阿巴拉契亚的反贫困项目存在缺陷且管理不善,但山区居民在媒体对反贫困战争的报道中扮演了核心的象征角色,特别是在转折点的1964年,证明贫困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内城区少数族裔的问题。为了说明他当年提出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案》的必要性,约翰逊总统在四月份对肯塔基州东部进行了一次广为宣传的访问,在一间破旧小屋的门廊上与贫困的当地人短暂握手。几乎每一家主要的大众杂志和报纸都刊登了关于”山区人民困境”的文章,配以肮脏、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住在油毡纸棚屋中的面孔。
像《安迪·格里菲斯秀》(The Andy Griffith Show)和《贝弗利山人》这样以山民角色为特色的电视喜剧,反映了全国媒体对这个”白人他者”的迷恋——一个处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孤立群体。但它们也为这些令人不安的画面提供了一剂安慰剂,呈现出比新闻媒体更为乐观的形象:朴素但生活舒适的人们,正直、自信,并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样的形象减轻了人们对美国经济体系深层失败及其无力阻止看似根深蒂固的贫困的感受。它们还暗中强化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山区人民陷入了”贫困文化”,但将其从一种致残的堕落和功能失调的循环重新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个重视休闲追求胜过物质进步的民族的选择。
反贫困战争和阿巴拉契亚贫困人口当然从未在这些节目中或任何关于这些节目的新闻报道中被直接提及。我也不是要论证这些节目是有意为了反驳《阿巴拉契亚的圣诞节》之类的描绘而创作的,甚至也不是考虑到反贫困战争而制作的。一如既往,电视制作人和电视网高管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吸引尽可能广泛的观众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阿巴拉契亚被重新发现以及反贫困战争的历史背景确实使这些节目在美国公众的大部分群体中引起共鸣,因此促进了它们的流行。这些节目将贫困呈现为一种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而非经济剥削和地方政治腐败的直接结果,从而淡化了许多南方山区居民(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穷人)的困境,削弱了公众对紧急联邦干预和援助的支持情绪。
《贝弗利山人》是另一部情景喜剧,其受欢迎程度部分源于它利用了人们对当时频繁出现在新闻中的南方山区居民的恐惧和好奇。与《真正的麦科伊一家》和《安迪·格里菲斯秀》一样,《贝弗利山人》在CBS播出的八年期间(1962-1970年)赢得了广泛的观众群和高收视率。但与前辈们不同的是,《贝弗利山人》不仅仅是一部以山区人物为主角的非常成功的乡村情景喜剧。相反,这部剧成为了一场关于电视节目本质和流行文化政治可能性的全国性辩论的焦点。通过重新定义乡巴佬(hillbilly)的刻板印象,该剧还提供了一种常被忽视但有时尖锐的对战后美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批判。该节目惊人的成功重塑了电视网络,因为它成为了1960年代席卷电视荧屏的乡村情景喜剧浪潮的催化剂。
正如该剧每周重复播放的流行主题曲所讲述的,《贝弗利山人》讲述了一个奥扎克山区家庭的故事——杰德·克兰佩特(巴迪·艾布森饰)、奶奶(艾琳·瑞安饰)、艾莉·梅(唐娜·道格拉斯饰)和杰思罗(马克斯·贝尔饰)——他们在自家土地的一片沼泽地发现石油后成为百万富翁,然后搬进了贝弗利山的一座豪宅(图6.4)。该剧是保罗·亨宁的作品,他是电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制作人之一。作为《鲍勃·卡明斯秀》的编剧和制作人、《真正的麦科伊一家》和《安迪·格里菲斯秀》的客座编剧、《贝弗利山人》和《衬裙交界处》(1963-1970年,CBS)的创作者、编剧和制作人,以及《绿色田野》(1965-1971年,CBS)的执行制作人,亨宁影响了1955年至1970年间电视上几乎所有以当代乡村为背景的节目。亨宁1911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独立城,1930年代初开始职业生涯,在堪萨斯城KMBC广播电台担任歌手和杂务工,后来为广播、电影和电视撰写剧本,包括《菲伯·麦吉和莫莉》、《鲁迪·瓦利秀》、《伯恩斯和艾伦》以及《鲍勃·卡明斯秀》。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亨宁表现出对乡巴佬角色塑造的迷恋,他将这种兴趣追溯到青少年时期在密苏里州诺埃尔(位于阿肯色-俄克拉荷马边境)的一个童子军营地徒步旅行时与奥扎克山区居民的接触。“我就是爱上了那里的一切,”他后来回忆道,“那里的人们是如此善良和热情……那是一次美妙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图6.4
粗俗者中的山民:克兰佩特一家驶入贝弗利山(从左到右,下排):杰德(巴迪·艾布森饰)、杰思罗·博丁(马克斯·贝尔饰);上排:艾莉·梅(唐娜·道格拉斯饰)、杜克、奶奶(艾琳·瑞安饰)。图片由保罗·亨宁收藏提供。
亨宁也承认受到其他媒体的影响,包括”虔诚地”收听宾·克罗斯比主持的《卡夫音乐厅》中鲍勃·伯恩斯的独白,以及在堪萨斯城观看《烟草路》的演出,他认为那”非常滑稽”,但场景”太压抑了”。奇怪的是,亨宁没有提到其他明显的媒体影响,包括《愤怒的葡萄》(后来的《真正的麦科伊一家》)中超载的老爷车、《凯特尔夫妇》系列电影,尤其是阿尔·卡普的《小阿布纳》。杰思罗、艾莉·梅和奶奶显然是从阿布纳、黛西·梅和约库姆妈妈那里借鉴而来的(该剧首播时几位评论家就指出了这种联系),亨宁还直接根据卡普漫画中的情节设计了一些场景,包括杰思罗和他的双胞胎姐妹杰思琳,以及杰思罗穿着小得可笑的学生制服上小学。尽管亨宁以重要的方式重新构想了乡巴佬形象,但他的角色深深植根于过去半个世纪的形象之中。
无论早期媒体对他角色的影响如何,这部剧的实际创意是在两个地方形成的。首先,1959年,亨宁刚刚参观完亚伯拉罕·林肯在肯塔基州的故居,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时,他大声想象”如果亚伯拉罕·林肯……突然发现自己坐在我们的车里,会有什么反应。“这个想法一直留在他脑海深处,直到他读到一则新闻报道,说”奥扎克山区偏远地区”的人们”实际上……试图阻止道路建设”,亨宁推测这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靠私酿酒为生,不想让’外人’(他们这样称呼外来者)进来。“因此,对亨宁来说,就像之前的保罗·韦伯一样,山区居民不仅是落后一个世纪或更久的人群,而且他们还反对主流文化的进步观念。把这样的人带入现代化、国际化的美国中心,将提供一个关于文化对比的喜剧研究,同时也能让他”摆脱像《烟草路》那样每周都要面对的压抑的穷乡僻壤背景”。
这部剧的第二个萌芽点是1961年末在洛杉矶著名的布朗德比餐厅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议,参加者有亨宁、Filmways电视公司总裁阿尔·西蒙和董事会主席马丁·拉索霍夫。Filmways代表了正在主导网络电视制作的新型独立制作公司。西蒙多年来一直敦促亨宁为Filmways编写一部以乡村为背景的喜剧,甚至提出购买《凯特尔夫妇》(Ma and Pa Kettle)的电视版权。当他和拉索霍夫终于听到亨宁的想法时,他们立即表示支持。在参议院青少年犯罪小组委员会就电视暴力的有害社会影响举行听证会之后,西蒙认为”娱乐的时机已经成熟”,亨宁的节目”将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电视界最好的作品”。拉索霍夫当场承诺投资10万美元,甚至还没有找到赞助商。
然而,电视网的反应并不那么热情。ABC在节目首次推出时就拒绝了,虽然CBS更感兴趣,但提供的广告支持很少,并将节目安排在亨宁和西蒙认为是”电视炼狱”的周三晚上九点档,与NBC高收视率的《佩里·科莫秀》对打。为了弥补电视网有限的宣传,Filmways发起了一场宣传媒体闪电战,在八十五个城市播出,估计有三千五百万观众收看。亨宁还仔细控制主演的公众形象,以保持他们的可信度。与《真正的麦考伊一家》的演员和制片人将他们的角色塑造与真正的山区人民保持距离不同,亨宁试图将他的演员呈现为可信的山民,正如1962年6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所述:
我希望巴迪·艾布森、艾琳·瑞安、唐娜·道格拉斯和马克斯·贝尔作为他们自己不复存在。个人传记的传播和发布……以及所谓的花边新闻、宣传稿、专栏植入和他们在家中的摄影版面要尽一切可能阻止!没有报道总比错误的报道好!……而错误的报道就是损害我们乡巴佬角色电视形象的报道。
他还强调,关于他的明星巴迪·艾布森在游艇上或马克斯·贝尔在夜总会的宣传版面”不利于让人相信这些角色”,他指示演员们”将评论倾向于’节目的可信度’和’他们所扮演角色的基本真实性’。”
这场精心控制的宣传攻势的结果是从第一次播出就获得了惊人的收视率,当时估计有50%的电视观众收看。该剧在首月结束时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1962年和1963年电视季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直到最后几年才跌出前二十名。此外,该剧拥有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半小时单集,以及五十个最高收视率单集中的八集。《贝弗利乡巴佬》不仅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还在英国、荷兰和日本获得了大量追随者,成为真正的国际现象。一位英国评论员总结道:“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世界上知道《贝弗利乡巴佬》的人比知道约翰逊总统甚至教皇的人还多。”
与高收视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初的媒体反应压倒性地负面。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剧情无聊,误解笑话和老套的文字游戏令人尴尬(在早期一集中,当被问到杰思罗小时候是否去过伊顿公学时,杰德回答说:“如果我了解杰思罗的话,他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吃东西了”——这是一个”Eton”和”eatin’“的谐音双关)。”一种审美倒退,愚蠢透顶,是文化尼安德特主义的惊人展示”,一位评论家写道。《综艺》杂志称其”看着很痛苦……完全是狗窝镇和小阿布纳的翻版,却没有阿尔·卡普作品的优点。“评论家继续写道:”它从不认为观众有哪怕一点点智商……就连乡巴佬们也应该感到愤怒。”
这个节目可能是低俗文化攻势的开端,将进一步贬低美国文化——这种观点解释了许多评论家为何如此尖刻。他们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牛顿·米诺持相同看法,后者在一年前曾猛烈抨击这一媒介是”一片广袤的荒原”,充斥着”暴行、暴力、虐待狂和谋杀”,以及”关于完全不可信的家庭的公式化喜剧”。对这些评论家来说,《贝弗利山人》进一步证明了电视的破坏性空洞,是对”正统”文化的攻击——而此时肯尼迪总统的”卡米洛特”似乎正在全国掀起一场”令人振奋的文化发酵”。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总结该节目所受到的批评反应:“那种乐观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人们曾相信在肯尼迪总统、牛顿·米诺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引领下,一场大众文化觉醒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三千六百万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几位评论家将此与米诺的警告联系起来。理查德·沃伦·刘易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写道,这个节目”致力于证明……米诺的荒原实际上是一片玉米地”,而鲍勃·霍普在全国广播协会的招待会上打趣说:“牛顿·米诺的刺激把我们伟大的行业引向了《贝弗利山人》——广袤荒原中的一间茅厕。”艾琳·瑞安为自己辩护道:“我只能说……数百万人已经把那间茅厕搬进了他们的家里。”然而,就像早期贬低乡村音乐和《马和帕·凯特尔》系列电影的人一样,该节目的批评者只是将其巨大的受欢迎程度简单地解读为其低俗的证明。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该节目空前的成功。首先,特别是在最初几季,该节目制作精良,确实很有趣。埃布森和瑞安都是技艺精湛的艺人,将角色演绎得完美无缺;导演理查德·沃夫在电视和莎士比亚舞台方面都有很强的资历;而亨宁是一位精益求精的专业人士,工作日程极其繁忙。亨宁声称,该节目反响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放弃在现场观众面前拍摄的想法,因为”笑声太大了……他们的笑声盖过了台词。“即使是评论家吉尔伯特·塞尔德斯,虽然反对他所认为的该节目”对无知的鼓励”,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简单的、对某些人来说令人愤怒的事实是,《贝弗利山人》确实很有趣。”
其次,使该节目幽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亨宁有意且成功地重新定义了山民(hillbilly)的含义和形象,使其更具广泛吸引力且更加无害。最明显的是,这种对山民形象的净化是通过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并将他们从山区搬到豪华的贝弗利山庄来实现的。但亨宁也积极尝试清理和去性化他的角色,既是为了回应电视网络严格的社会道德规范(在这种媒介中,已婚夫妇直到1960年代中期仍必须被展示为分床睡觉),也是为了消除早期山民形象中所定义的肮脏和堕落的污名。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Filmways电视公司总裁阿尔·西蒙总结了该节目所实现的戏剧性概念转变。他观察到,在《贝弗利山人》之前,“’山民’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肮脏、邋遢、留着长胡子的人,住在破旧的棚屋里,后面还有茅厕。”但他声称,由于他的节目,“这个词在全美国有了新的含义。现在,它代表着迷人、可爱、美好、干净、健康的人。”
正如西蒙所说,该节目确实大幅度地——尽管不完全地——偏离了标准的山民刻板印象。观众第一次看到杰德·克兰佩特时,他冲进他那简陋的奥扎克山区小屋的门,立刻洗手。节目中从未出现过飘逸的长胡子和茅厕,也没有家族世仇或与执法人员的枪战。虽然私酿酒仍然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但山民角色的醉酒场面却没有出现。克兰佩特一家穿着牛仔裤、亚麻衬衫和格子衬衫,但除了杰德标志性的破旧软帽外,他们的服装都是干净完整的。艾莉·梅和杰思罗迷人的体格迎合了人们对山区居民天生性感的标准观念,早期剧集中充斥着关于艾莉·梅丰满身材的台词,但这两个角色始终被描绘成要么在性方面极度无能,要么天真无知。同样,潜在的威胁和暴力在所有角色身上都保持潜伏状态(体现在常见的步枪展示、杰思罗的疯狂、艾莉·梅的动物园,尤其是奶奶的急脾气),但克兰佩特一家也散发着持久的邻里温情,以及对他们认为比自己不幸的人的深切同情。最后,在一个代沟日益加深、父母权威受到挑战的时代,杰德是一位无可争议但仁慈的家长,艾莉·梅和杰思罗几乎总是立即服从长辈的命令。
亨宁还打破了高贵山民与愚蠢乡巴佬之间的标准文化分野,将两者融合到同一个家庭中。杰思罗对现代社会的完全无知与小阿布纳的形象相差无几,而杰德则像之前的麦考伊爷爷一样,象征着粗犷、独立、富有常识的山地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有着清晰的认知。这种传统乡村价值观与乡巴佬滑稽形象的混合,在1963年摄影师艾伦·格兰特为《星期六晚邮报》拍摄的封面上得到了完美呈现。封面上杰德和奶奶扮演格兰特·伍德1930年名作《美国哥特式》中那对紧闭双唇的夫妇,而傻笑的杰思罗和丰满的艾莉·梅则从两侧探出头来(图6.5)。正如格兰特所认识到的,该剧对乡巴佬的刻画从未完全抛弃早期的含义,实际上还利用了更多粗俗和堕落的刻板印象。但该剧确实拓展了”乡巴佬”(hillbilly)一词的潜在含义,使其在全国范围内不再那么具有贬义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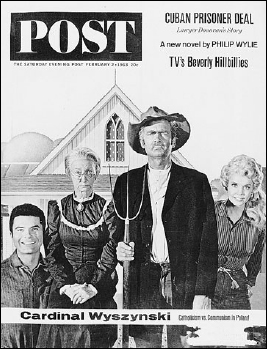
图6.5
乡村正直与乡巴佬无知的融合:克兰佩特一家作为更新版的《美国哥特式》。艾伦·格兰特,封面照片,《星期六晚邮报》,1963年2月2日。©1963 SEPS:由柯蒂斯出版公司授权,印第安纳波利斯。版权所有。www.curtispublishing.com
第三,该剧的受欢迎程度源于它像大多数流行文化一样,能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提供逃避和安全感。1960年代初期是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国外的冷战使整个国家陷入震荡。在该剧首播的那一周,报纸头条聚焦于詹姆斯·梅雷迪思试图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引发的骚乱、佐治亚州的教堂纵火案、一名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被枪杀,以及日内瓦裁军谈判持续僵局。在这样一个不确定和令人恐惧的时代,《贝弗利山人》以及情景喜剧总体上提供了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所带来的慰藉。正如导演理查德·沃夫所解释的:“你知道不会有人被杀,不会有人得脑瘤。”随着国家继续被一连串令人不安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所震撼,该节目继续为数百万人提供心灵庇护所,其中最具毁灭性的莫过于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也许这种将该剧解释为不确定氛围中的情感慰藉的说法,有助于解释1964年1月8日那集本身并不起眼的剧集所获得的惊人收视率(占所有可能电视观众的44%,实际收看观众的65%)——奶奶把一只袋鼠误认为是巨型长耳大野兔——这是电视史上任何半小时节目中最高的收视率。
然而,仅仅说《贝弗利山人》提供了”逃避”并不能说明什么。正如历史学家劳伦斯·莱文正确提醒我们的,逃避的可能性存在于所有形式的表达文化中;最重要的不是逃避这一事实本身,而是”要知道我们是从什么逃向什么”。与之前的两部作品相比,该剧在更大程度上将老套的笑话和荒诞的人物刻画与巧妙的社会反思和批评相结合。按照大多数流行文化制作人的传统,亨宁经常否认对该剧更深层意义的解读。“我们唯一的信息就是——开心”,他告诉媒体。“为什么要对它进行深入分析呢?”他在另一个场合嘲笑道。“这只是逃避,很多笑声,纯粹的娱乐……观众喜欢,就这样。”然而,演员们明白该剧的信息不仅仅是捧腹大笑。埃布森认为这是对一次性消费社会的反应,而瑞安则声称它代表了”美国最后的民间传统之一,山地人的生活和文化”。虽然两种解读都有道理,但该剧更深层的意义以及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既维护又挑战”美国梦”的方式,将对财富和休闲生活方式的颂扬与对富裕、现代性和”进步”的持续批判融为一体。
一方面,该剧沉浸于好莱坞精英的财富、地位和休闲之中,并利用了加利福尼亚在公众想象中的受欢迎程度。除了是乔德一家传奇的现代版本,克兰佩特一家的迁居也反映了二战期间和之后数百万美国人迁往”黄金之州”的情况,这一人口变迁使加利福尼亚在1960年代初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同样,他们一夜暴富的身份也夸张地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在1960年代初相对快速获得的繁荣——他们从大萧条时期的艰难困苦上升到郊区牧场式住宅。就像十年前观众对凯特尔一家的态度一样,观众既可以嘲笑也可以同情克兰佩特一家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电器和便利设施的困惑。在早期的一集中,杰德问为什么”电动绞肉机”——实际上是厨房垃圾处理器——不能正常工作,并且相信只要对着放在支架上的电话大喊就能使用它。尽管这些乡巴佬很无知,但观众在杰德和奶奶的误解中看到了自己努力适应新的商品化文化的影子。
另一方面,克兰佩特一家的价值观和行为始终在质疑这种炫耀性消费的梦想。奶奶是家庭成员中最不适应新环境的人,她认为贝弗利山庄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到处都是我见过的最懒惰、最油腻、最不友好的一群人!”亨宁有意使用讽刺手法,用历史上描述”乡巴佬”的词语来谴责势利而无所事事的贝弗利山庄精英阶层。在她的奥扎克邻居眼中,她作为厨师、管家、酿酒师、草药师和气象预报员的技能备受推崇,但在贝弗利山庄,奶奶最好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古怪的人,最坏的情况下则被视为威胁。她确实应该被这样看待,因为她是最常揭露贝弗利山庄生活方式空洞无用的角色,进而延伸到美国大部分富裕阶层社会。当杰思罗抱怨一块蜡制水果没有味道,杰德猜测也许它本来就不是用来吃的时候,奶奶怒吼道:
这就是这个倒霉地方的问题,你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养牛、养猪、养鸡……不能犁地种玉米、黑麦或苜蓿……不能生火酿点月光威士忌!你告诉我——在贝弗利山庄你能干什么?
像所有克兰佩特家的人一样,奶奶可能对所有现代事物一无所知,但她对自己和乡村传统有着清晰的认识。
像奶奶一样,但没有她的火爆脾气,杰德·克兰佩特也体现了传统的乡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建立在对家庭和亲属坚定不移的承诺、与他人交往时深厚的道德操守,以及坚如磐石的常识之上。这些特质使他能够击败或赢得每周威胁他财富的源源不断的企业骗子和小骗子。像他之前的萨特·洛文古德和斯纳菲·史密斯一样,杰德也象征着平等民主,他以体面和善良对待遇到的每一个人,不承认任何合法的阶级或地位区分。在早期的一集中,当他的银行家助理简·海瑟薇小姐(南希·库尔普饰)为自己偷偷试图把克兰佩特一家赶出城而感到羞耻时,杰德回答说:“在我看来,没有人有权利为别人感到羞耻。上帝创造了我们所有人,”他说教道,“如果我们对他来说足够好,那我们对彼此来说肯定也足够好。”
这些价值观源于他卑微的山区背景,象征着他那质朴的原木小屋家园,对杰德来说,这既是精神上的归属,也是物质上的居所。在试播集中,一家石油公司以2500万美元购买了杰德的土地后,他问他的表妹珀尔(杰思罗的母亲)他是否真的应该搬到加利福尼亚。她难以置信地回答:
杰德,你怎么能这样问?看看你周围!你离最近的邻居有八英里远!你这里到处都是臭鼬、负鼠、浣熊和山猫!你用煤油灯照明……用柴火炉子做饭,冬天夏天都是……(指着酒壶)你喝的是自酿的月光酒……(拿起肥皂)用自制的碱液肥皂洗东西……你的厕所离房子有五十英尺远!你还问该不该搬!
杰德思考了一会儿她的话,然后回答说:“是啊——我想你说得对。一个人要是离开这一切,那才是傻瓜呢!”显然,他的回答被设计成滑稽荒谬的,反映出他与现代便利设施惊人的隔绝和无知。然而,在一个社会和个人动荡日益加剧的世界里,这同样确实反映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家园归属感。尽管有了新的财富,杰德拒绝改变自己或他的生活方式。他继续穿着朴素的衣服,吃地方菜肴,开着他那辆破旧不堪的老卡车。相比之下,他那可笑的亲戚杰思罗反复试图拥抱新的加州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结果总是灾难性的。
与杰德的忠诚、诚实和正直以及奶奶的坚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兰佩特家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由贪财者、势利眼、骗子和谄媚者组成。该剧的主要反派角色,杰德的银行家米尔本·德莱斯代尔(雷蒙德·贝利饰),集这些特质于一身。他是一个如此吝啬、如此急于留住克兰佩特一家作为主要储户的人,以至于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开心,无论他必须多么羞辱和贬低自己才能做到。许多集都展示他穿着可笑的服装,或者听从艾莉·梅那群”小动物”的使唤。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哈丽特·麦克吉本饰)是一个虚荣而小气的势利眼,是一个溺爱她的贵宾犬的疑病症患者,她认为克兰佩特一家是粗俗的野蛮人,在上流社会面前让她丢尽了脸。即使是简·海瑟薇,剧中最不夸张的角色,也是优雅地向克兰佩特一家解释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但她仍然是一个常常可悲的业余爱好者,尽管老板虐待她,却无法离开工作。许多其他一次性角色试图利用克兰佩特一家的天真,骗取他们数百万的财富。因此,该节目至少在表面上将现代美国呈现为贪婪、粗俗、物质主义,最终在道德和精神上空虚的形象。
一些有洞察力的评论家认识到了这部剧集潜在信息的深层含义。作家阿诺德·哈诺理解到,尽管剧中充斥着糟糕的双关语和老套的情节,但它至少提供了对”肤浅和虚伪的嘲讽”。他还欣赏这部剧体现了对都市生活的拒绝和”回归……自然方式”的理念,他认为这本应引起那些谴责该剧的”文化崇拜者”的共鸣,因为他们”从城市蜂拥而出,寻找梭罗和卢梭”。在更具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星期六评论》上,罗伯特·刘易斯·沙永更直接地为该剧的社会意义辩护。在沙永看来,这个节目是对”我们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的挑战”,与大多数电视节目中”令人愉悦的伊甸园”形成鲜明对比。他承认该剧有”杂耍式的插科打诨”,但认为其老套并不能否定”其道德价值观的尖锐性”及其批判意义。“在电视上,具有尼尔森收视率前十名的有效社会批评绝对是罕见的,”沙永总结道。“这才是《贝弗利山人》成功的真正标准——同类节目中的首创。”
尽管沙永的评论很有洞察力,但他严重低估了这个节目的持久力。他认为该剧的道德标准如此”离经叛道”,以至于节目无法持久,因为它们要求观众”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标准并发现其空洞”。然而,他未能认识到的是,该剧社会批评的力量同时被角色不可能的无知和孩童般的天真以及荒谬的故事情节所成就和削弱。因为克兰佩特一家和他们的主要对手德莱斯代尔一家都是卡通式的漫画人物,他们与现实的距离太大,无法作为非竞争性和非物质主义的有说服力的典范(就克兰佩特一家而言),也无法作为金钱权力的合法象征。尽管该剧表面上否定了贝弗利山的生活方式,但克兰佩特一家从未离开这个享乐主义和贪婪的巢穴超过几周,他们也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重塑他们的社会环境。相反,他们仍然是异乡的陌生人,几乎没有目标感,不再耕作土地,却不愿成为周围商业社会的一部分或改变它。最终,正如哈尔·希梅尔斯坦所指出的,《贝弗利山人》的信息”相当愤世嫉俗”,“欣赏但最终贬低”与神话般的美国乡村过去相关的基本人类价值观——这种过去理论上仍存在于南方山区——同时”谴责却默认接受”贝弗利山的休闲和地位世界。
该剧受欢迎的最后一个也是不那么光彩的可能原因是它对种族关系和南方过去的处理方式。与《安迪·格里菲斯秀》(实际上几乎所有1960年代早期的情景喜剧)一样,该节目呈现了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世界,非裔美国人角色只出现在少数几集中。两个节目都对南方小镇和乡村居民进行了正面描绘,明确抵消了新闻报道中始终将现实生活中的南方人描绘成恶棍的形象。作为一个几乎是和平主义者的南方小镇警长,安迪·格里菲斯的角色拒绝佩戴枪支,并强迫他那好斗的副手把自己左轮手枪的唯一一颗子弹放在衬衫口袋里,这与种族主义暴力的南方警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如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吉姆·克拉克和伯明翰的”公牛”康纳,他们在1960年代早期的新闻媒体中被广泛描绘为南方白人对民权运动”大规模抵抗”的化身。用该剧编剧之一比尔·艾德尔森的话说,该剧宣扬”人对人的人道而非人对人的不人道”,提供了一个浪漫化的、没有社会紧张关系的温和南方过去的形象,这种平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黑人从南方景观中抹去而实现的。《贝弗利山人》远远超越了这种去种族化和平南方的描绘,不仅展示了谦逊而自豪的南方人,还展示了自称的新邦联主义者,他们向叛军旗帜敬礼,欢呼杰斐逊·戴维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虽然奶奶在对旧南方的忠诚方面最为坚定,甚至在一集中自豪地穿上邦联军服,但所有克兰佩特家族成员至少都隐含地接受了他们的邦联遗产(图6.6)。在”南方再次崛起”这一集中,奶奶把在内战电影中扮演邦联士兵的演员误认为是抵御真正联邦军队入侵的保卫者,并说服艾莉·梅、杰思罗甚至德莱斯代尔先生加入战斗。她甚至射击并俘虏了扮演格兰特将军的演员(但后来与他分享了一壶月光酒(moonshine))。当然,该剧将这些行为和信念呈现为克兰佩特一家字面主义(他们无法区分真人和假扮者)和荒谬过时世界观的进一步证据。但在晚间新闻几乎每天都报道民权活动人士被举着叛军旗帜、宣扬邦联英雄的南方白人嘲弄和骚扰的时代,该剧将新邦联主义与杰德及其亲属所倡导的其他积极传统价值观联系起来,必定受到那些主张延续种族隔离的观众的欢迎。

民权时代中的新邦联主义者:
奶奶身穿叛军制服,准备与可恨的北方佬作战,这是1967年《贝弗利山人》中的一个场景。图片由保罗·亨宁收藏提供。
该节目的粉丝中有相当大比例居住在农村、小城镇或南方地区,而且美国研究局对部分城市市场的”arbitron”收视率调查显示,该节目直到1963年春季才在大多数城市稳定进入前五名,这些事实也表明该节目在南方观众中比在北方和西部观众中更受欢迎。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对这一时期尼尔森收视率的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它高估了农村和小城镇观众的数量,而低估了城市非裔美国人观众的数量。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很少有非裔美国人观看《贝弗利山人》和其他以全白人演员阵容为特色的乡村题材节目。另一方面,艾琳·瑞安和保罗·亨宁都声称——也许是出于辩护——黑人是该节目最早、最热情的观众群体之一;亨宁后来指出,在洛杉矶机场拍摄的一个片段中,“像老朋友一样迎接我们的人是……行李搬运工和……黑人。他们是最早热情拥抱这个节目的人。”然而,无论这一评估或尼尔森收视率的准确性如何,《贝弗利山人》在广大美国民众中无可争议的受欢迎程度,都无法与它在种族斗争广泛存在的时期对历史上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宣传和辩护——尽管是不言而喻的——分割开来。
《贝弗利山人》的即时和持续成功,以及《安迪·格里菲斯秀》在较小程度上的成功,帮助重塑了电视网络尤其是CBS的面貌。它们在1960年代初期如此主导电视界,以至于1964年3月,《电视指南》连续两周将这些节目作为封面故事。亨宁的成功促使CBS向他提供了一份新节目合同,由他自行选择内容,并且史无前例地不要求先制作试播集。他的新节目《裙带关系》讲述了胡特维尔小型农业社区的故事,于1963年首播,是该季度收视率第四高的节目。两年后,亨宁合作并担任执行制片人,推出了另一部CBS乡村喜剧《绿色田野》。事实上,电视荧屏上充斥着《贝弗利山人》模式的乡村情景喜剧(但没有明确的山地人(hillbilly)角色塑造)。到1966年,CBS播出了五部非常成功的乡村题材情景喜剧——《贝弗利山人》、《裙带关系》、《绿色田野》、《安迪·格里菲斯秀》和《戈默·派尔,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者的衍生剧)——并凭借这些节目跃居电视网络的主导地位。
《贝弗利山人》现象,加上围绕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向贫困宣战”计划的大量新闻报道,催生了山地人形象的新潮流。这些形象大多与该节目本身有关;CBS发起了一场50万美元的商品推广活动,克兰佩特一家出现在家乐氏玉米片和云斯顿香烟的电视和平面广告中,甚至出现在联邦政府的公益广告中(图6.7)。这一趋势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百事公司旗下激浪汽水的初期推广活动,这是一种高糖、高咖啡因、高热量的软饮料。其名称长期以来是私酿威士忌(moonshine)的代名词,该公司选择通过采用明确的山地人广告宣传来进一步宣传产品的效力和东南部起源。1965年至1968年间,许多平面和广播广告中都有一个留着胡子、光着脚的卡通”代言人”,名叫”山地人威利”(图6.8)。广告语包括”呀呼,激浪……让你五脏六腑都舒坦”和”每瓶都有劲!“广播宣传使用了无知邋遢乡下人之间老套的喜剧对话(在一则广告中,角色”克莱姆”对一个山区女孩说:“天哪,萨拉·卢,除了俺的宠物猪,俺从没亲过任何人”)。标签上甚至还画着一个山地人朝另一个从户外厕所里出来的人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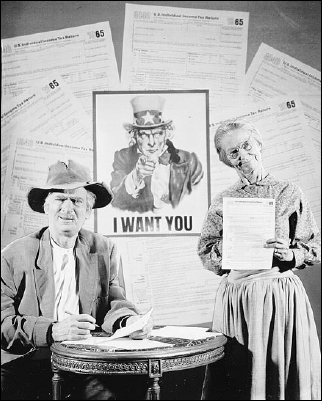
图6.7
山地人现象:埃布森和瑞安参与国税局报税宣传活动。图片由保罗·亨宁收藏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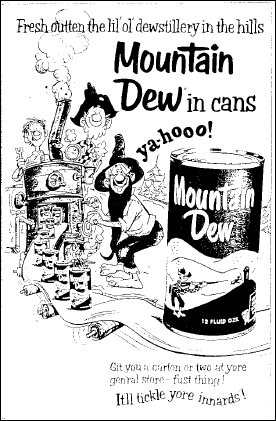
图6.8
山地人代言人:“山地人威利”和朋友们宣传激浪的效力。1966年激浪装瓶商目录。图片由百事可乐北美公司提供。© 百事可乐北美公司。
尽管激浪(Mountain Dew)广告活动一直持续到1968年,但《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文化核心地位却较为短暂。到1960年代中期,该剧的收视率已趋于平稳,最初引发的争议也逐渐消散。正如朱迪斯·克里斯特在1966年《电视指南》的评论中总结的那样:“大辩论已经结束了。”她认为,那些将该剧视为”荒原中游荡者12岁心智水平”证据的人与那些为该剧社会批评辩护的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平息,因为该剧已经陷入了可预测的喜剧套路。然而,除了节目本身的变化之外,评论家们激烈反应背后的知识分子潜台词——对文化层次应当泾渭分明的信念,以及对电视文化和教育可能性的期待——几年后似乎也不再那么紧迫了。电视应该或可以成为纯商业娱乐提供者之外的东西,这种观念并没有比牛顿·米诺在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任期持续更久(他于1963年辞职),而波普艺术的兴起、新新闻主义以及体育场规模的摇滚音乐会观众进一步打破了不同文化”品位层次”之间早已摇摇欲坠的壁垒。
正如克里斯特的评论所暗示的,《贝弗利山人》在1960年代后半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该剧逐渐远离了文化冲突的明确主题,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杰思罗荒谬的无知,或是艾莉·梅的动物们的滑稽行为,以及人们扮成动物的荒诞情节。为了让节目保持一定的新鲜感,亨宁将克兰佩特一家送到了英国、华盛顿特区、纽约,并短暂地回到了奥扎克山区——在那里,四集节目是在仿造的山民传统村落银元城拍摄的——但这些新场景都没能重现该剧最初的影响力。
除了表明亨宁在制作了150多集之后难以想出新概念之外,该剧日益离奇的故事情节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民权运动的日益激进化分裂了美国人,并激发了各种抗议运动及随后的反运动,电视开始被逃避现实的情景喜剧所主导——这一趋势因《贝弗利山人》的成功而得到鼓励。这些半小时喜剧中有许多要么以农村或小镇为背景,要么像《家有仙妻》、《怪物家族》、《亚当斯一家》甚至《太空乐梦》那样,是关于像克兰佩特一家这样的边缘群体在”正常”社会中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生活的奇异幻想。《贝弗利山人》并没有完全回避19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许多剧集都暗示了从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反战运动明显缺席)到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兴趣,再到妇女运动和环保主义等社会发展(在一集中,克兰佩特一家前往华盛顿,向总统献上他们9500万美元的财产以对抗空气污染)。这些与抗议运动相关的剧集的主旨通常是贬低这些努力,将其视为由漫画式激进分子——冒牌山民——领导的幼稚时尚,他们和克兰佩特一家本身一样困惑和荒谬。
然而,这些节目的基调并不是当时许多文化保守派和政治领导人那种直接的谴责,而是对这些挑战现状行为的愚蠢感到困惑和好笑,包括新兴的毒品文化。例如,在”罗宾汉与警长”这一集中,一群典型的嬉皮士选择追随杰思罗作为他们的新领袖,主要是因为他和他的家人似乎知道一种令人兴奋的新致幻剂,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传统”的南方小龙虾食谱。当奶奶告诉他们”我要去湖边熏一些小龙虾。但首先我需要一个小锅”时,他们的眼睛因期待而睁大。(这里利用了”smoke”和”pot”的双关语,既可以指烹饪,也可以指吸毒和大麻。)五年前,奶奶会谴责嬉皮士们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但在这里她被用来从双关语中制造幽默。因此,这一集反映了该剧已经远离了其最初的文化冲突和道德批判概念。克兰佩特一家曾经既是乡村闹剧的象征,也是美国核心美德的代表,而现在他们越来越只代表前者。
到1960年代末,“乡巴佬热潮”似乎已经走到尽头。美国对阿巴拉契亚作为”问题地区”的关注逐渐消退,反贫困战争越来越被认为是一场灾难性的资金和资源浪费,农村贫困问题再次从公众意识中淡出。意识到这一趋势,Mountain Dew在1969年放弃了其乡巴佬广告宣传活动。在电视上,大多数农村喜剧的收视率急剧下降,包括《贝弗利乡巴佬》在内,1969-1970季只有《梅伯里镇》(《安迪·格里菲斯秀》的续集)进入前十名,到第二年,没有任何农村题材节目能留在前二十五名。尽管如此,农村题材节目仍然受到数百万美国人的欢迎,CBS仍然是排名第一的电视网。然而,CBS新任总裁鲍勃·伍德意识到,该电视网在大多数大城市观众中表现不佳,而且该电视网农村题材节目的观众现在几乎完全由儿童、老年人、年长的蓝领工人以及农村和小镇居民组成——总的来说,这是对广告商最不具吸引力的观众群体。CBS还因农村节目而获得了这样的声誉,据巴迪·艾布森多年后讲述的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电视网负责人威廉·佩利的妻子在纽约一家高档餐厅被朋友们称为”乡巴佬电视网老板的妻子”。因此,在佩利的全力支持下,伍德从1970年春天开始采取行动,清除CBS节目表上所有农村题材节目。正如《绿色田野》的常驻演员帕特·巴特拉姆哀叹的那样:“他们取消了所有带树的节目——包括《灵犬莱西》。”到1971年,CBS已经”转向关注社会议题”,开始播出以具有”六十年代价值观”的年轻人为主角的节目,如《全家福》、《玛丽·泰勒·摩尔秀》,以及一年后的《陆军乐园》。虽然克兰佩特一家从荧幕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山民形象在大众媒体中的终结,但它确实标志着二十世纪电视上最后一批明确标注为”乡巴佬”(hillbilly)的角色的消失,也标志着亨宁所实现的乡巴佬/山民神话两个面向——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充满性暗示的傻瓜(或怪物)——统一的终结。
南方山区居民对电视上的乡巴佬形象有何反应?关于当时人们对这些形象的解读,现存的只是零星的轶事证据,这既是因为大多数山区居民几乎无法接触到能够传播到其直接社区之外的公共表达渠道,也是因为编辑主管们关注的是收视率和观众人口统计的汇总数据,很少认为公众对电视形象的反应——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争议的形象——值得他们花时间和精力去关注。1963年,《电视指南》确实招募了一位奥扎克山区人(被称为”真正的乡巴佬”)来评判这个节目(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看、有趣的节目”),并发表了几封后续的读者来信,其中包括一位阿肯色州读者为亨宁节目的”高级恶搞喜剧”辩护的信。但总体而言,大发行量杂志和报纸上的公众反应很少。
然而,两位著名阿巴拉契亚人发表的对立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当地反应的多样性以及这一形象所引发的持续矛盾心理。对于反露天采矿组织”拯救我们的肯塔基”的负责人詹姆斯·布兰斯科姆来说,CBS的农村喜剧《贝弗利乡巴佬》、《绿色田野》和《嘿嘿嘿》在周二晚间连续播出,在文化上相当于煤炭工业对阿巴拉契亚土地和人民的剥削,是”一个国家为贬低、侮辱和摧毁其境内少数民族所做出的最有效努力”。他继续说道,对其他少数群体的类似描绘会”立即引发公众抗议”。但对于这些冒犯性形象却没有听到任何反对声音,因为”美国人都同意:乡巴佬不美”。东田纳西州记者和广播评论员麦克·莫里斯提供了一个更为细致的解读:
作为一个地区群体,在全国大部分人眼中,我们似乎在两种形象之间交替摇摆……有时我们是一个骄傲、极度独立的民族……也许天真但很有吸引力,无论我们戴着浣熊皮帽还是杰德·克兰佩特的软帽。然后,我们又发现自己被剥去了虚假的光环,我们不再是贝弗利乡巴佬,而只是乡巴佬——贫穷、无知、懒惰、堕落的劣等公民……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摇摆以惊人的规律性发生……足以造成一种精神分裂——事实上,我认为它确实在我们身上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对我们的看法中造成了这种分裂——这也许可以解释《贝弗利乡巴佬》的流行。
正如莫里斯所意识到的,《贝弗利乡巴佬》,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情景喜剧中的山民,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正是因为这些节目捕捉到了高贵山民与滑稽低俗乡巴佬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正值真正的山民频繁出现在新闻中的时期。当到1960年代末,山区人民从公众意识中淡出,克兰佩特一家仅仅成为漫画式人物,不再是克罗克特和布恩的后裔时,他们失去了这种内在的多义性,因此也失去了大部分人气。
如果说《贝弗利山人》是”乡巴佬”(hillbilly)一词最后一次出现在主流大众媒体作品标题中,那它绝不意味着这个词汇和形象的彻底消失。事实上,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里,“乡巴佬”一直是美国文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尽管那时针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群体的类似刻板印象早已变得不可接受。韦布和卡普塑造的卡通化乡巴佬形象逐渐淡出,这一称谓和形象也遭到南部山区和中西部城市新兴政治活动人士的日益反对。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重新挪用这一标签,将其作为地区和文化认同的战斗口号。要完整讲述这个故事需要更多篇幅,但我们至少可以勾勒出乡巴佬形象在二十世纪末美国虽然影响力减弱但仍具持续意义的整体轮廓。
《贝弗利山人》停播后的第二年,即1972年,出现了战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两部山民题材作品:电视剧《沃尔顿一家》(根据厄尔·哈姆纳的半自传体作品改编,讲述他在弗吉尼亚州舒勒镇的成长经历)和电影《激流四勇士》(改编自詹姆斯·迪基1970年的畅销小说,由约翰·布尔曼执导)。《沃尔顿一家》是CBS另一部非常成功的乡村题材节目(1972-1980年),之所以能逃过电视网对所有乡村内容的大清洗,是因为它得到了CBS创始人兼董事长威廉·佩利的大力支持,佩利认为这是一档”有品位”的节目,既能吸引年轻一代,也能留住CBS传统的老年观众。这部一小时的剧集展现了高尚、勤劳的弗吉尼亚蓝岭山区居民,他们浸润在传统乡村价值观中,安全地置身于大萧条时代——那是全国山民形象最后一次引起广泛共鸣的伟大时刻。许多美国人与《沃尔顿一家》产生了深刻共鸣,渴望接受那些颂扬朴素美德的故事情节,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剧中所有矛盾”都通过理解、爱和家庭的成长得到化解”。但在公众想象中,它根本无法与《激流四勇士》中的山民形象竞争——那些智力低下、身体残疾的怪人和北乔治亚荒野中的野蛮施暴者,他们恐吓着四名来自亚特兰大的独木舟爱好者(艾德·金特里、刘易斯·梅德洛克、德鲁·巴林杰和鲍比·特里普),这四人想在水电大坝完工、整个地区被淹没之前”征服”乔治亚北部的卡胡拉瓦西河。
《激流四勇士》无疑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塑造了全国对南部山民和乡村生活的整体认知。影片中那些堕落、愚蠢、性欲旺盛的掠食者形象,给几代美国人心中植入了恐惧。正如电影学者帕特·阿诺1991年半开玩笑地指出的那样,这部电影”至今仍是许多非南方人不敢离开州际公路的最大原因”。《北乔治亚杂志》的丹尼尔·罗珀更简洁地描述了它对当地的毁灭性影响:“《激流四勇士》对北乔治亚人的影响,就像《大白鲨》对鲨鱼的影响一样。”这部电影作为文化隐喻长期存在,远超其院线放映期,在深夜脱口秀和《周六夜现场》中被反复戏仿,成为无数漫画和笑话的素材。影片中那些臭名昭著的场景——枪口下的鸡奸和一个智力低下的白化病男孩淫荡地弹奏班卓琴——成为贬低农村贫穷白人的即时可识别符号,喜剧演员只需说一句”像猪一样尖叫”(其中一名强奸犯对郊区受害者的命令)或哼几个音符的吉他-班卓琴二重奏开头,就能立即引起演播室观众的本能反应。
鉴于这种极度贬损的含义旨在唤起现代城市生活无可置疑的优越感,詹姆斯·迪基在小说中对山民和”进步”代价的更为复杂的诠释后来常常被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生存主义爱好者刘易斯·梅德洛克的话语——他因厌恶现代中产阶级生活的软弱和空虚,以及担心核毁灭后文明的退化而行动——迪基暗示”山里可能有些重要的东西”,一种将随着新大坝的到来而被抹去的生活方式。对刘易斯(和迪基)来说,山民的落后和社会隔离恰恰使他们保留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坚韧,保存了对家庭和亲族的承诺准则,而这些在追求商品化生存的浪潮中早已丧失。刘易斯向艾德讲述了他和一个朋友在狩猎途中受伤迷路、被一个私酿酒者(moonshiner)和他儿子救起的故事,他赞扬了父子相传的”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促使那个男孩找到他们并带他们脱险。尽管他们”既无知又充满迷信、流血、谋杀、私酒、钩虫病、鬼魂和早逝”,他总结道,“我钦佩这种文化造就的人,以及造就这种文化的人。”
刘易斯的故事以及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松散地取材于迪基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尤其是他与朋友阿尔·布拉塞尔顿和刘易斯·金在北乔治亚荒野的库萨瓦蒂河上划独木舟的经历,以及他们与住在河岸附近的山民的相遇。在一次河流漂流中,迪基一行人的独木舟翻了,被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卢卡斯·金特里和他的父亲艾拉救起。在确信这些外来者不是税务稽查员后,金特里一家把他们带到了他们简朴的乡村房屋,给他们提供了凉水、甘蔗和几罐私酿威士忌(moonshine)。虽然刘易斯的故事暗指了这个充满谨慎好客的真实事件,但迪基将小说的重心放在了他认为这种文化所产生的野蛮行为上,特别是鲍比·特里普遭受的残忍同性强暴。迪基将这一行为呈现为山民行为的一种模式,而非偶然事件,因为当埃德被绑在树上、即将目睹鲍比遭受侵犯时,他心想:“他们以前一定干过这种事;这不是他们临时想出来的手法。”山民的行为如此不人道,对他人身体表现出”如此漠视”,以至于埃德想要在这场磨难中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只野兽,徒手攀上陡峭的悬崖,然后追踪并杀死他认为是幸存强奸犯的那个人。
这种将山民等同于纯粹野蛮的观念在电影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该片由约翰·布尔曼执导,1971年夏天在乔治亚州拉本县实地拍摄。迪基一直希望这本书能被拍成电影,并亲自撰写了剧本,但他很快发现——用他儿子克里斯托弗的话说,那个夏天克里斯托弗在片场担任替身演员——“他对自己的书如何被拍成电影几乎没有发言权。”尽管迪基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一和剧本开头的十九个场景中,用大量篇幅批判了现代城市生活以及以进步之名对处女地的掠夺,但华纳兄弟的高管和布尔曼只对制作一部扣人心弦的冒险求生故事感兴趣,几乎删掉了迪基整个开场序列,包括刘易斯对山民价值观的有保留辩护。
布尔曼在电影简短的开场序列中加入了画外音,隐晦地质疑中产阶级生活和工业发展的好处,但在随后的所有内容中,他始终强调山民的社会退化及其与文明的彻底隔绝。例如,在小说中,性情平和、弹着吉他的德鲁·巴林杰与一个患有白化病的山区男孩班卓琴手合奏了一曲浪漫传统的《野花》(Wildwood Flower),短暂地弥合了城市与山区之间的文化鸿沟。他站得离男孩很近,有一刻他们”把乐器靠在一起,彼此靠近”,这让埃德在他们的合奏中看到了”某种罕见且不可复制的东西”。相比之下,在电影中,德鲁(由演员罗尼·考克斯饰演)和男孩(由比利·雷登饰演,一个当地十五岁的特殊教育学生,为了这个角色剃了头、涂了粉)演奏的是更喧闹、更晚近的蓝草音乐曲目《决斗班卓琴》(Dueling Banjos),而且他们被一个高高的门廊隔开。布尔曼还加入了小说中没有的场景,包括透过破旧窗帘瞥见一位当地山区妇女(由安迪·韦伯夫人饰演)怀抱着她生病的孩子(韦伯智障的孙女),她们起居室的昏暗光线加深了一种感觉:她羞于见人。克里斯托弗·迪基当时就意识到这些人是多么”极其脆弱”,以及这些场景是多么令人不快。“当然,好莱坞付钱给这些人,并尽可能温和地对待他们,”他后来写道,“但当灯光亮起、摄影机开始转动时,很难摆脱一种感觉——这里正在窃取灵魂。”
当然,强奸场景此后将永远与这部电影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影片也强化了山民彻底堕落的形象。两名未具名的强奸犯分别由西部枪战表演老手赫伯特·“牛仔”·考沃德和当地演员比尔·麦金尼饰演,后来在电影的宣传册中被夸耀地描述为”银幕历史上最卑鄙的恶棍之一”和”一个毫无可取之处的堕落角色,他在荒野中的存在似乎玷污了大自然的杰作”。这个场景在小说中已经足够露骨,但电影通过添加”像猪一样叫”的台词和受惊的鲍比(内德·比蒂饰演)发出的尖叫声,使其变得更加恶劣,将场景的含义从同性强奸转变为兽交的替代品。克里斯托弗·迪基因不得不(作为替身)跨坐在鲍比被鸡奸的那根木头上,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拍摄而感到恶心,他愤怒地打电话给父亲,警告说这个可怕的强奸场景有可能喧宾夺主。尽管詹姆斯·迪基继续坚持认为这个场景是必要的,因为他”必须把谋杀的道德重量压在郊区居民身上”,但他的儿子正确地预言道:“这正在成为电影的全部内容,成为每个人都会记住的东西。’像猪一样叫!’而不是刘易斯的生存主义,不是攀爬悬崖,不是艾德战胜自己的恐惧。一切都将围绕着肛交。”如此残忍的行为使谋杀看起来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影片明确展示了刘易斯(伯特·雷诺兹饰)用箭从背后射杀强奸犯,以及那人看到沾满鲜血的箭头从胸口穿出时震惊的表情,随后他痛苦地死去(图E.1)。詹姆斯·迪基在纽约首映式上观看这个场景时反应强烈。他以离谱的行为和醉酒的公开亮相而闻名,据说在刘易斯瞄准致命一箭的那一刻,他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杀了那个狗娘养的!“,然后在箭射中目标后喊道”太棒了”。

图E.1
唯一的好山民……:一名未具名的山民(赫伯特·“牛仔”·考沃德饰)难以置信地目瞪口呆,看着他的强奸犯同伴(比尔·麦金尼饰)被从背后射穿,在《激流四勇士》的拍摄场景中痛苦死去。《激流四勇士》© 1972华纳兄弟公司。版权所有。
拉本县以外地区对这部电影的最初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赞扬其扣人心弦的动作场面和创新的摄影技术。小说(到1973年第八次印刷时已售出180万册)和电影(第一年票房收入650万美元)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电影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纽约时报》的斯蒂芬·法伯称其为”今年发行的最令人惊叹的电影作品”)。佐治亚州的支持者热切希望这部电影能帮助宣传北佐治亚的美景并吸引旅游收入,包括州长吉米·卡特在内的数十位当地政要出席了1972年8月在亚特兰大纪念艺术中心举行的电影首映式。卡特试图说服自己这部电影会对他的家乡有益,尽管场景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这对佐治亚有好处,”他对迪基的朋友阿尔·布拉塞尔顿说,停顿了一下后补充道,“我希望如此。”
北佐治亚山区的反应则不那么确定,但令人惊讶的是,并非简单的愤怒否定。1973年接受采访的拉本县居民,无论是参演电影的还是为剧组服务的,都明显对”粗暴”和”粗俗”的场景以及拍摄智障儿童的决定感到不适。在电影拍摄期间,怨恨情绪就已经在增长。随着山民被如何刻画的消息传开,克里斯托弗·迪基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和家人住在一家廉价汽车旅馆里,比住在附近高尔夫度假村别墅里的布尔曼和主演们与当地居民演员或工作人员有更多接触。受到一个世纪以来媒体对残暴山民描绘的影响,他担心一些”真正的山民”会带着”真枪”来”给这些电影人一个教训”。弗兰克·里克曼曾担任布尔曼和剧组的当地杂务工和顾问,更重要的是,他负责在强奸场景中添加猪叫声,他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当地敌意。他后来承认,电影上映后,“我成了众矢之的。”然而,里克曼认为这部电影是一次积极的经历,许多人也同意这一点。大多数参与电影的居民表示,他们很享受与好莱坞魅力的短暂接触以及它带来的急需收入。有些人甚至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拉本县生活的真相,这些真相”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应该被揭示”。和里克曼一样,许多人也认为这部电影引起了外界对该地区的积极关注,鼓励制片厂在该地区拍摄其他电影,并帮助在查图加河上开创了蓬勃发展的漂流和划独木舟业务。
但这种关注是有代价的,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成千上万的郊区居民涌向河流寻求白水漂流的刺激,同时也留下了成堆的垃圾,给当地水上安全巡逻队带来了麻烦。许多人表现出媒体所称的”激流四勇士综合症”——对河流缺乏尊重和敬畏,就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令当地向导感到羞耻的是,有些人甚至在到达拍摄强奸场景的河段时发出猪叫声,几乎是在挑衅大自然进行报复。在某些情况下,大自然确实报复了。1972年至1975年间,有17人在这条河上溺亡(大多数人血液酒精含量过高),直到1974年这条河被正式指定为”野生与风景河流”后,新的法规才得以实施。
《激流四勇士》不仅在此后数十年间塑造了人们对山区居民的认知,还催生了一系列冒险和恐怖小说及电影,这些作品都以现代郊区居民鲁莽而不敬地闯入原始自然并遭遇血腥结局为前提。《德州电锯杀人狂》(1974)、《隔山有眼》(1977)、《鬼玩人》(1983)、《鬼玩人2》(1986)、《南瓜头》(1988),甚至独立制作的意外大片《女巫布莱尔》(1999),都或多或少直接源自《激流四勇士》。这部电影的成功还鼓励电影公司制作了数十部以私酿威士忌的南方乡村亡命徒为主角的电影,这些电影在1970年代中期的小镇和汽车影院中拥有稳定的市场,尽管这些电影(以及随后经过净化处理的电视剧《乡下人杜克》)更直接的灵感来源是罗伯特·米彻姆1958年的剧情片《雷霆路》。虽然以高性能汽车和尖叫的追车场面为特色,但这是自1904年的《私酿酒贩》以来第一部从文化内部审视私酿威士忌的电影,其核心故事是朴实但正直的卢克·杜林(米彻姆饰)和他的山区家庭努力在北方有组织犯罪势力面前保护这门被电影呈现为传统手艺的技艺。最终,杜林在公路上英勇牺牲,为保护一种注定消失的生活方式而战。
然而,随后二十年间涌现的南方好老男孩电影浪潮,既没有米彻姆作品中的经济底蕴和文化悲情,也没有《激流四勇士》对现代性的批判。相反,它们毫不含糊地颂扬男性享乐主义(几乎总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与腐败无能的”体制”斗争并获胜,以及观看车辆和建筑物被摧毁的乐趣。《月光奔跑者》(1974)、《赤脚县的炎热夏天》(1974)、《月光县快车》(1976)和《乔治亚坏路》(1977)等电影自由地混合了乡巴佬(hillbilly)、红脖子(redneck)和穷白人(cracker)的形象符号,呈现出一个奇幻的南方,那里山脉与沼泽相邻,城市和工厂无处可见。
这些电影的数量之多及其持续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南方贫穷白人形象在这些年间渗透流行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程度。南方各地乃至全国大量工人阶级男女开始接受以前明确带有贬义的称呼——包括”红脖子”、“穷白人”和”乡巴佬”——作为种族和文化自豪感的标志。这些年间大量以”红脖子”为标题的乡村音乐歌曲(如约翰尼·拉塞尔的《红脖子、白袜子和蓝带啤酒》(1973)和弗恩·牛津的《红脖子!(红脖子国歌)》(1976))既反映又鼓励了这种意识形态转变。虽然很少被如此明确地描述,但这一发展是对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妇女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的总体反弹的一部分。白人工人阶级中的数百万人(绝大多数是男性,但也包括一些女性)借用了这些运动的”身份意识”,但大多拒绝其政治议程,努力将这些术语重新概念化为”白人身份”和勤劳的正面标志。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置于与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管理者及官僚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权力的对立面,同时也与他们所认为的依赖福利且主要由少数族裔组成的底层阶级对立。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加剧了红脖子术语和形象符号的传播。卡特是来自乔治亚州南部的富有花生农场主和政治家,以政治局外人和平民代言人的身份参选,被一些华盛顿内部人士嘲笑为粗俗的南方好老男孩——这种看法因他那爱喝啤酒、喋喋不休的弟弟比利的滑稽行为而得到强化。专栏作家卡尔·罗文谴责那些”自封的知识分子和社交名流”,他们认为卡特是一个”乔治亚乡巴佬”,即将”把一群乡巴佬、玉米饼白痴和拖着长腔的蠢货强加给国家首都”。然而,卡特的总统任期也使红脖子标签在许多白人中产阶级南方人中获得了合法性,他们采用这个称呼,穿上时髦的李维斯牛仔裤和靴子,在新近流行的”乡村酒吧”(honky tonks)里喝地方啤酒,这促使社会评论家保罗·亨普希尔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红脖子时尚”。
尽管城市中产阶级中没有出现类似的”乡巴佬时尚”,但1970年代”hillbilly”(山民)一词的持续演变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呼应了”redneck”(红脖子)的变化。与”redneck”一样,“hillbilly”越来越多地被南方山区居民所接受——无论是在他们的家乡还是在中西部城市——成为种族和阶级自豪感的标志。但与”redneck”不同的是,这个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不仅代表南方白人身份和工人阶级地位,还代表对山区身份所蕴含的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的自豪。它也不像”redneck”那样专属于男性身份的象征。凯西·卡恩的《山区女性》(1977年)赞颂了工人阶级山区女性的生活,她们不仅讲述了自己的贫困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还讲述了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自尊。“我为自己是个hillbilly而自豪,”卡恩的受访者之一唐娜·雷德蒙德宣称,并补充道:“如果你不喜欢我说话的方式,那就滚回家去!”同样,老一代南方山区居民——其中大多数早已离开家乡或搬到城市中心——也在自费出版的自传中采用了这个词,书名如《叫我山民》和《天哪,我成功了!——一个奥扎克阿肯色人的山民童年》。与卡恩书中的女性相比,这些男男女女的阶级意识没有那么明确,但他们仍然使用这个意味深长的词来表达他们在南方山区农场和小镇度过的艰难但充实的童年,以及他们与一种正在快速消失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自豪联系。
然而,就在一些南方山区居民接受这个词的同时,新一代活动家和学者开始强烈谴责”hillbilly”一词及其在大众媒体中的负面含义。正如我们所见,当地人自这个标签诞生以来就一直对其感到不满并加以抵制,但1970年代中期标志着”hillbilly”的使用首次受到系统性的质疑和抨击。这些努力源于三个相互重叠但又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运动。首先,肯塔基州东部及周边地区的环保、劳工和社会福利活动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众多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参与或启发下,积极抵制采矿业、美国林务局以及公路和住宅建设商对土地和人民的进一步环境和经济剥削。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行动开始打破山区居民懒惰、没受过教育、依赖政府救济或只是被动受害者的hillbilly神话。其次,新一代阿巴拉契亚学者开创了阿巴拉契亚研究领域。他们主要出于对抗他们所认为的主流文化中严重负面刻板印象的愿望,推动了对阿巴拉契亚地区文化、社会、经济性质及其历史的学术研究。尽管他们的工作在地区层面的影响往往大于全国性话语,但削弱了南方山区及其居民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社会经济现实之外的观念。第三,中西部城市——尤其是辛辛那提——的城市阿巴拉契亚活动家在1970年代中期成立了倡导组织,以促进这些社区的社会福利,并推广阿巴拉契亚身份和文化。例如,辛辛那提城市阿巴拉契亚委员会和Appal-PAC的努力促成了1992年11月辛辛那提市议会通过了一项人权法令,明确保护阿巴拉契亚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这是全国唯一一项此类法令。尽管在所有情况下,这些阿巴拉契亚活动家和学者的主要目标是改革地方政治和社会机构,改善基层条件——无论是在肯塔基州的煤矿、弗吉尼亚州的学区,还是辛辛那提和代顿的社区中心——但他们的行动和著作也帮助在更广泛公众心目中消解了hillbilly刻板印象的合法性。
尽管如此,虽然”hillbilly”标签在商业化流行文化中出现的频率远低于过去,但hillbilly形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仍然不时出现在全国媒体和更具地方性的活动中。《正义前锋》(CBS,1979-1985年)改编自1974年的电影《私酒贩子》(该片本身主要取材于《雷霆之路》),在伯特·雷诺兹1977年的飙车电影《警察与土匪》及其众多续集大获成功后被改编成电视剧。作为1980年代初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正义前锋》借用了肯塔基州东部真实的采矿小镇哈泽德的名字作为其虚构的哈泽德县的地名,并展现了典型的hillbilly刻板印象,如衣着暴露的丰满女性、一位满脸胡茬但可爱的老私酒贩子杰西叔叔(由丹佛·派尔饰演,是他布里斯科·达林角色的升级版),甚至偶尔还有户外厕所的笑话。但该剧最大的明星(至少从观众来信数量来看)是一辆荧光橙色改装的1969年道奇Charger,名为”李将军”。然而,制作人小心翼翼地在剧本和宣传材料中避免使用日益具有争议性的”hillbilly”标签,并将故事设定在一个模糊定义的南方背景中。
20世纪80年代末,乡巴佬(hillbilly)刻板印象随着来自阿肯色州的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和总统任期而强势回归——阿肯色州长期以来在大众媒体和公众心目中与乡巴佬形象联系在一起。尽管克林顿拥有罗德学者和耶鲁法学院毕业生的身份,城市精英和媒体对他及其同僚的嘲讽程度远超当年对吉米·卡特的讽刺,将他们描绘成没有文化的乡巴佬。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乔尔·阿亨巴赫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试图幽默地表达竞选工作人员(以及大部分新闻记者)前往小石城克林顿竞选总部时的恐惧——“据他们所知,这个地方的人均牙齿数量是全美最低的”,而且”州歌应该是《决斗的班卓琴》!“对《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贝弗利山乡巴佬》(The Beverly Hillbillies)以及其他流行文化中乡巴佬形象的引用,也出现在1992年《周六夜现场》讽刺当年总统辩论的小品中。主持人山姆·唐纳森(由凯文·尼伦饰演)将克林顿(菲尔·哈特曼饰演)描述为”一个小型偏远州的州长,那里住满了醉醺醺的乡巴佬……还有穿着牛仔短裤的丰满未成年少女”,她们”在杰思罗面前嬉戏……而抽着玉米芯烟斗、扛着猎枪的老奶奶们则朝着逃跑的猪乱开枪。”
这种媒体对乡巴佬的影射延续到克林顿的总统任期,漫画家们轻而易举地用它来表现似乎无穷无尽的丑闻系列,这些丑闻玷污了他的政府(图E.2)。这些形象也强化了克林顿的公众形象——由媒体、深夜脱口秀节目和他的批评者所传播——一个对高热量食物和年轻女性有着无限动物欲望的男人。当他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证实了这些评价时,一名呼吁他辞职的街头抗议者用一块写着”奥扎克的卡里古拉”的标语牌谴责他,将长期与据称淫荡的山区居民联系在一起的山区地名与帝王式的放纵和堕落融合在一起(尽管克林顿的家乡霍普和成年后居住的小石城都远离奥扎克山区)。

图E.2
漫画家们轻松地将克林顿总统与标准的媒体乡巴佬形象联系起来。道格·马莱特,1994年3月23日。© Tribune Media Services, Inc. 版权所有。经许可转载。
尽管与克林顿相关的乡巴佬漫画和笑话在1990年代中期短暂复兴,但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商业化的乡巴佬形象似乎正在慢慢消亡。例如,1990年代中期在南阿巴拉契亚旅游密集地区的一次游览中,很少能看到仍在使用熟悉的乡巴佬标签或图像的商家——房车营地是少数例外之一。虽然各种各样的乡巴佬新奇商品(如标有”乡巴佬厕纸”的干玉米芯)、笑话书、食谱、日历、T恤和明信片仍在销售,但它们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旅游城镇边缘破旧的纪念品摊位和礼品店里找到。田纳西州鸽子谷的乡巴佬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距离多莉·帕顿的迪士尼化主题公园多莱坞(宣传册中描述为”充满质朴魅力和山区传说的氛围”)只有几个街区,距离大烟山国家公园不到一小时车程。1995年参观时,这家破旧的商店里摆满了各种恶作剧礼品和软色情材料,其大肆宣传的”正宗”私酿威士忌蒸馏器(moonshine still)不过是几十年前联邦突击搜查中留下的几个生锈的锅(图E.3)。乡巴佬形象在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奥扎克地区的旅游陷阱中比在南阿巴拉契亚地区更为普遍(也许是因为蓬勃发展的阿巴拉契亚研究学术领域没有奥扎克对应物),但即使在这里,它的存在也明显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南部山区居民谴责它具有冒犯性和贬低性,而且在一个关注”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中越来越格格不入。在这方面,1999年7月《纽约客》的一幅漫画很可能标志着漫画乡巴佬形象的最后喘息,其边缘化的景观和人物幽灵般的面孔表明这个曾经一眼就能认出的神话角色正在解体,并从全国舞台上消失(图E.4)。

图E.3
一个正在消逝的商业图标:田纳西州鸽子谷破旧的乡巴佬村纪念品商店。作者收藏。

图E.4
漫画乡巴佬的终点?哈里·布利斯,《纽约客》,1999年7月26日,第57页。©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99 Harry Bliss,来自cartoonbank.com。版权所有。
然而,这种评估并未考虑到”乡巴佬”(hillbilly)一词在文化中以各种方式——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方式——继续存在的现象,包括商业化和个人化的形式。前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越来越多的专业音乐人将自己与乡巴佬标签和形象的不同元素联系起来。尽管许多知名度较低的乡村音乐表演者从未放弃这个标签,但这一趋势真正开始于东肯塔基州的德怀特·约卡姆1987年的热门专辑《乡巴佬豪华版》(Hillbilly Deluxe)的成功。约卡姆拒绝接受”乡村”这个标签,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委婉说法”,转而接受了这个曾经被鄙视的术语,将乡村音乐重新定义为”乡巴佬大声演奏的音乐”。追随约卡姆的脚步,史蒂夫·厄尔、罗尼·米尔萨普、贾德母女组合以及马蒂·斯图尔特(他的首支单曲大胆地命名为《乡巴佬摇滚》)等跨界乡村音乐表演者,通过将自己定位为喧闹而自豪的音乐和文化遗产的”乡巴佬”继承者,获得了名声和财富。甚至英国摇滚艺术家奇想乐队和恐怖海峡乐队的马克·诺弗勒也发行了专辑或组建了融入乡巴佬标签的乐队。还有一些乐队和表演者,他们融合了从朋克到蓝草音乐的各种音乐形式,包括肯塔基猎头者乐队、哈西尔·阿德金斯和南方文化滑板乐队,他们接受的与其说是乡巴佬标签,不如说是媒体塑造的疯狂山民形象。“乡巴佬”重新崛起的另一个独特例子是纳什维尔乐队BR5-49的成功。这些表演者的乐队名称取自《嘿嘿秀》(Hee Haw)的一个经典小品,他们穿着1940年代和1950年代乡巴佬乐队的服装,演奏老式乡巴佬经典曲目以及原创歌曲,如《小拉蒙娜(乡巴佬疯了)》。这种音乐方法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表明,“乡巴佬”一词仍然蕴含着多重含义,并继续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
神殿骑士会的”乡巴佬等级大荣耀勋章”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明显商业化但更为离奇的近期挪用乡巴佬形象的例子。这个”附属等级”(神殿骑士组织内社交俱乐部和慈善机构的结合体)由肯塔基州阿什兰的埃尔哈萨神殿的吉姆·哈里斯于1969年创立,允许成员穿着刻板印象中的”乡巴佬”服装,参与山民入会仪式(包括饮用”玉米酒”(corn likker)),同时令人欣慰的是,所有会费和纪念品销售收入都将用于资助在神殿骑士医院接受治疗的烧伤和残疾儿童。1970年帝国神殿骑士大会上,成员们穿着乡巴佬服装,驾驶着装有私酿酒蒸馏器的破旧卡车游行后,阿什兰”氏族”迅速壮大。该组织很快在全国拥有了数十个分会、一个官方吉祥物和一份名为《乡巴佬新闻》(Hillbilly News)的通讯。然后,在1977年,另外两位肯塔基州的”乡巴佬”神殿骑士和煤矿工人——“阴暗”格雷迪·金尼和”脏耳朵”霍华德·斯特拉顿——在肯塔基州派克维尔(近一百年前哈特菲尔德-麦科伊冲突大部分案件审理的县城所在地)发起了乡巴佬节。他们穿着工装裤、锥形毡帽和装饰着纽扣的超大领带和外套,驾驶着荒谬破旧的老爷车游行,这个节日是一场拉伯雷式的低俗和粗鄙的狂欢。但在创始人眼中,这也是对山区身份和自豪感的庆祝,由”土生土长的乡巴佬”主办,他们是”文明的、善良的、乐于助人的邻居”。这个节日得到了当地旅游委员会和派克县商会的大力推广,商会在1995年将其宣传为”三天最好的山区音乐、舞蹈、手工艺、美食……以及著名的乡巴佬节游行”。这个利润丰厚的年度节日在2002年举办了第二十六届,在经济困难的派克县仅面临有限的反对。神殿骑士的”乡巴佬等级”附属组织也依然强大,1999年有160个”氏族”在美国和加拿大参与活动。
但是,当1982年由一位阿巴拉契亚移民领导的辛辛那提分会试图在辛辛那提举办类似游行时,他们被一些阿巴拉契亚倡导组织指责为侮辱性和令人反感的行为,会强化大众媒体传播的、被非阿巴拉契亚社区广泛接受的负面乡巴佬刻板印象。对于这些为数以万计困在破旧贫民窟、只能从事蓝领工作的阿巴拉契亚移民工作的倡导者来说,“乡巴佬”一词仍然是一个”挑衅性词汇”。正如一位当地活动人士警告《辛辛那提询问报》(Cincinnati Enquirer)记者的那样,“试着去诺伍德的通用汽车装配厂找一个阿巴拉契亚人……(使用这个词),看看会发生什么。”然而,关键因素不是这个词本身,而是说话者的”外人”身份,因为”乡巴佬”长期以来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辛辛那提、芝加哥、底特律和其他移民人口聚集的城市中心许多阿巴拉契亚血统贫穷白人可接受的、甚至是积极的包容性标签。尽管乡巴佬氏族最终举行了街头游行,但市长大卫·曼并没有像原计划那样正式批准。因此,神殿骑士们只看到了一个无害的机会来挑战中产阶级惯例、宣传神话般的山区遗产并为贫困儿童筹集资金,而辛辛那提的许多阿巴拉契亚人则将这一活动视为又一次对无知醉酒”乡巴佬”的贬低和破坏性展示,这对当地阿巴拉契亚移民社区有着现实生活中的影响。
“乡巴佬”(hillbilly)一词在网络空间中的持续影响力,或许是最清晰、最广泛的例证。2002年秋季,互联网上有超过6,330个网站在标题中包含这个词,超过192,000个网页在正文中使用了某种形式的”hillbilly”一词。这些网站中有许多推广各种各样的音乐团体,包括Hillbilly Hellcats、Hillbilly Holocaust、Hillbillies from Mars(尽管名字古怪,但这是旧金山湾区的一支对舞乐队)、Sierra Hillbillies(一群加州方块舞者,自称”美国最狂野的方块舞俱乐部”),甚至还有一支来自西班牙马拉加的乡村摇滚乐队,名叫Mike Hillman and His Latin Hillbillies。除了与音乐相关的引用和网页外,还有数十个其他网站展示各种粗俗程度不一的乡巴佬笑话,或者宣传带有这个标签的产品,从恶搞礼品(一个名为”Hillbilly Headquarters”的网站专门销售超大号和有缝隙的”Billy Bob牙齿”)到自动调平割草机。《Hillbilly Hercules 2: Lost in New York City》是一部奇特的短片,其主页包含电影中的音频片段和视频剪辑,片中这位希腊半神先被安置到西弗吉尼亚山区,然后又到了曼哈顿。在网上拍卖平台eBay上,人们可以购买各种乡巴佬纪念品,从《贝弗利山人》(Beverly Hillbillies)的歌本和漫画书,到Mountain Dew的瓶子和招牌,到印有乡巴佬小人和图案的瓷咖啡杯和啤酒杯,再到模仿Tommy Hilfiger标志、印有南方邦联旗帜和”Tommy Hillbilly”字样的T恤和汽车贴纸。互联网上甚至有几个准学术网站,专门追溯贫穷白人和乡巴佬刻板印象的发展历程。
最后,数百名个人用户设计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标签的个人主页。大多数网页设计者使用”hillbilly”来表示南方山区的居住地或出身,或者表示与好友、家人相伴、亲近自然的简单生活。但其他此类网页的范围很广,从已经停更的Hillbilly Redneck Rampage Page——一首赞美南方白人男性享乐主义的颂歌,链接到南方邦联之子、《花花公子》、百威啤酒、NASCAR和全国步枪协会——到国际信徒在线通讯的一期内容,用这个词来代表谦卑虔诚的价值,并称耶稣基督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巴佬”。“hillbilly”在互联网上如此广泛而多样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尽管大众媒体中刻板印象化的乡巴佬形象可能很快会与小黑人桑博、中国洗衣工和意大利手摇风琴师一样,成为在现代美国极不合时宜、令人无法接受的冒犯性种族和民族刻板印象,但乡巴佬形象仍然深深活在全国数百万美国人的心中。
如此多样的使用和诠释反映了这一形象非凡的生命力和持久性。“hillbilly”一词于世纪之初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此后经历了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的兴衰、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以及从广播到电影、电视再到互联网作为时代前沿媒介的转变,依然存续至今。它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其语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可塑性——这种可变性根植于其作为”白人他者”表征的核心模糊性,既颂扬又贬低美国的过去和南方山区民众的民俗传统。
这种内在的二元性使得乡巴佬的含义在整个世纪中能够持续而微妙地转变,以反映不断演变的社会关切。在世纪之交,媒体制作者对乡巴佬的使用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社会同化失败的恐惧,以及农村民俗对工业化城市社会秩序的威胁。到了1920年代,随着国家变得以大都市为主导,这些恐惧逐渐消散,乡巴佬越来越成为一个幽默角色,与笨拙的默片喜剧演员和欢乐的弦乐队音乐家联系在一起。乡巴佬形象/身份在大萧条时期达到顶峰,在从小说到电影、从连环漫画到动画片的整个文化领域蓬勃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时代,“hillbilly”既代表了对社会崩溃和退化的恐惧,也代表了对美国本土民众和民间文化的颂扬。在战后岁月里,乡巴佬的含义再次演变,被用来代表一个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民族和文化,但同时也指出了日益自动化和物质化的美国所付出的道德和社会代价。最后,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直至下一个世纪,尽管乡巴佬形象在商业流行文化中急剧衰落,但数百万美国人,尤其是南方山区内外的南方山地居民,继续排斥和接纳这个标签和身份,反映出美国人与乡巴佬之间关系一直以来的根本模糊性。
这种理解帮助我们认识到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界限的渗透性,也使我们对美国历史和文化中刻板印象与漫画形象的本质和作用有了更复杂的认识。尽管媒体产业和商业艺术家通常控制着这些形象和人物的生产,但他们并不能控制其文化意义或用途。这一结果源于生产者、推广者和受众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也源于受众内部甚至个人内部的斗争。因此,本研究表明,国家刻板印象远非仅仅是被无脑媒体消费者统一解读的无聊”大众”形象,而是在语义和概念上都很复杂。它们包含多层可能的含义,揭示的关于”主流”文化的信息,与它们表面上描绘的群体和习俗一样多。因此,仔细审视”乡巴佬”(hillbilly)形象,可以揭示美国人使用流行文化来定义个人和国家身份的无数方式,以及在快速演变的社会中帮助他们理解自身生活中的模糊性。
在我撰写这本书的多年里,我一直对媒体中乡巴佬形象的惊人持久性感到震惊,即使面对越来越多反对种族和民族刻板印象的声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针对农村和经济弱势白人的刻板印象。没有什么比CBS电视台在2002年秋季决定将《贝弗利山庄乡巴佬》(The Beverly Hillbillies)以”真人秀”节目的形式重新推出更能展示媒体对这一形象的持续拥抱,或更好地说明其呈现和接受方式如何继续演变了。这档名为《真正的贝弗利山庄乡巴佬》(The Real Beverly Hillbillies)的节目,受到MTV《奥斯本一家》(The Osbournes)惊人成功的启发——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真实生活”节目,展示前重金属歌手奥兹·奥斯本奇异但又奇怪地熟悉的核心家庭生活——该电视网试图利用那档节目的独特吸引力以及克兰佩特家族剧集持续的人气(CBS恰好拥有其版权)来获利。该电视网计划不再让演员扮演那些神奇地变得富有并搬迁到豪华贝弗利山庄的贫穷山民角色,而是从南部山区选择一个”五人或以上的多代家庭——父母、孩子和祖父母”(选角人员被派往阿肯色州、西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多山农村地区”),支付他们搬迁到南加州豪宅的所有费用,然后用影片记录他们雇佣家仆、在罗迪欧大道购物、在时尚餐厅用餐的经历。
然而,与1962年原版节目首播时不同,CBS的节目主管们意识到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一概念的适当性,因此主动尝试将节目及其意图置于正面光芒之下。因此,CBS替代节目副总裁根·梅纳德强调了该节目作为”一个精彩的鱼离开水的故事”的喜剧潜力,但他小心翼翼地强调观众将与真人演员一起笑,而不是嘲笑他们。他设想的是”一个与大多数人所知不同但仍然能产生共鸣的家庭,一个彼此深爱的家庭。“该电视网还强调,节目的主要开发者是约翰·”达布”·科内特,一位自称”阿巴拉契亚裔美国人”的人,他在弗吉尼亚州煤矿区的阿巴拉契亚镇长大,曾帮助为电影《逃狱三王》(O Brother, Where Art Thou?)制作老式乡村音乐(其原声带成为畅销专辑)。科内特敏锐地意识到山区居民对长期以来被漫画化的方式的敏感性,他坚称自己的意图不是嘲笑阿巴拉契亚人,而是嘲笑贝弗利山庄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选角得当,”他告诉媒体,“选择那些尊重自己但也能看到自己幽默之处的人,我们将取得最大的成功。我们最终会得到一部真正具有——天哪——社会评论意义的作品,也许还能启发人们,让他们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是赤脚的乡巴佬。”科内特因此试图论证,这档节目将与其前身起到同样的作用,强调好莱坞精英的荒谬奢侈和朴实山民的真挚价值观。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这档拟议中的节目还是在南部山区内外遭遇了强烈反对,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愿再容忍那些长期被接受(或至少被容忍)的刻板印象。专栏作家、学者、地方政客和政治活动人士纷纷表达他们对这样一档节目竟然被考虑的震惊。一位肯塔基州记者的文章以”请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开头,而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一位专栏作家则嘲讽地恳求道:“仁慈的上帝,饶了我们吧。”《国家评论在线》资深作家罗德·德雷尔明确聚焦于这些”乡巴佬”的种族身份,将这档节目比作现代版的”黑人滑稽剧”,其计划是”把阿巴拉契亚那些没牙的穷白人垃圾运来,让他们置身于极度奢华之中,看这些傻瓜在富人和美人面前不自觉地出丑。“其他批评者也强调,如果换成任何其他种族或民族群体,这样的电视节目创意会被立即否决,他们嘲讽地建议该电视网未来的节目可以让”一个来自布朗克斯的贫困黑人家庭”去汉普顿度假,或者让”正统派犹太大学生”转学到”亚特兰大浸信会学院”。最尖刻的是,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一位专栏作家建议做一档节目,把一位好莱坞电视高管的家人带到西弗吉尼亚州,强迫他们”像普通、理智的西弗吉尼亚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州——这里最大的私营雇主是沃尔玛,好工作稀缺得像母鸡的牙齿,企业对我们不友好,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形象问题。”
面对尖刻的批评,科内特向纳什维尔一家另类报纸的记者透露,虽然CBS可能有”不同的议程”,但他计划”欺骗电视网,让他们以为我们要做一档类似《奥斯本一家》的节目”,但实际上提供一种”真正公正的纪录片式手法”。他还承诺,“如果事情变得丑陋或恶意,我会毫不犹豫地让这艘船沉没。”但德雷尔和许多其他人认为这个前提本身就令人反感,仍然不相信他的说法。德雷尔断然拒绝科内特声称其意图是启发美国人的说法,谴责他的话是”一个骗子的狡辩之词,试图说服自己接受那笔钱,帮助把一个绝望的阿巴拉契亚家庭推向全国性的嘲笑。“《纽约新闻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同样嘲讽道:”在他(科内特)的陈词滥调之下,很难表达出对他所逃离的那种文化更多的蔑视。”
然而,证实了地区批评者最担心的事情,考德威尔和其他媒体记者也借此机会质疑该节目的动机,搬出了早期媒体对乡巴佬形象的贬损刻板印象——既是怪物又是穷困潦倒的傻瓜。例如,考德威尔认为这档节目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电视网不敢展示山区家庭的真实面貌——狂热的五旬节派信徒、反犹太主义者、暴力恐同者,只对性和毒品感兴趣。更符合早期喜剧描绘的是,《E!在线新闻》的一篇报道呼吁潜在申请者”刷刷你那颗牙”,并警告说”牲畜”不会被算作多代同堂家庭的成员。文章还质疑CBS热线接听申请者电话的效果,因为”不知道《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那帮人里有多少人有电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件事会如何发展,但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愤怒反对正在增长。虽然有些人发誓不看这档节目,或者如果播出就把电视机打烂,但其他人已经在肯塔基州派克维尔和黑泽德的CBS选角地点进行了抗议,而总部位于肯塔基州怀特斯堡的非营利农村倡导组织”农村战略中心”已经发起了一场全国性广告运动,“以羞辱该电视网延续负面农村刻板印象的行为。”作为回应,四十四名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致CBS总裁莱斯利·穆恩维斯的公开信,表达他们的”愤怒”,并要求立即停止开发”这档令人反感和恶心的节目”。《真正的贝弗利乡巴佬》的命运很可能是大众媒体乡巴佬形象的风向标。如果抗议者的所有这些压力导致CBS放弃他们的计划,这很可能标志着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形象的终结。或者,不太可能的是,也许这档节目会出乎批评者的预期,对农村美国拥抱主流现代性的代价和收益提供一个富有同情心甚至具有社会揭示性的视角,再次展示这一形象的可塑性和持续相关性。无论大众媒体形象发生什么变化,乡巴佬身份及其多重的种族、经济、性别和文化含义无疑将继续存在,正如一个多世纪以来那样,为美国人在一个快速变化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定位自己和”他者”提供一种方式。
缩写
| 缩写 | 全称 |
|---|---|
| AAT | 美国电视档案馆,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加利福尼亚州北好莱坞 |
| AG | 《安迪·格里菲斯秀》 |
AGP - Archie Green Papers,John Edwards Memorial Foundation Collection,Southern Folklife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AJ - Appalachian Journal(《阿巴拉契亚杂志》)
ASP - Arthur Satherly Papers,Country Music Foundation,Nashville,Tennessee
BH - The Beverly Hillbillies(《贝弗利山人》)
CMF - Country Music Foundation,Nashville,Tennessee
DEC - Diamond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Videocassette
EC - The Esquire Collection,Spencer Museum of Art,University of Kansas,Lawrence
FTA - Film and Television Archive,Archive Research and Study Center,Powell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FXC - Twentieth Century-Fox Film Corpora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 010),Produced Scripts,Theater Arts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GSC - George Stevens Collection,Manuscript Collection 100,Special Collection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JEMFC - John Edwards Memorial Foundation Collection,Southern Folklife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JLP - John Lair Papers,Special Collections,Hutchins Library,Berea College,Berea,Kentucky
LAD - Li’l Abner Dailies(《小阿布纳日报连载》)
LGC - Leonard Goldstein Collection,Manuscript Collection 128,Special Collection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MF - Music Folios,John Edwards Memorial Foundation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MGMC - MGM Collection,Special Collections,Cinema-Television Library,Doheny Memorial Library,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os Angeles
MPAA -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ile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MPW - Motion Picture World(《电影世界》)
MS - Movie Scripts,Special Collection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PCA -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Files,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ile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PF - Production File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PTC - Peter Tamony Collection,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Ellis Library,University of Missouri/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Columbia
RBC - Richard Barthelmess Collection,Manuscript Collection 124,Special Collections,Margaret Herrick Library,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Beverly Hills,California
RKO - RKO Collection,Produced Scripts,Collection 003,Theater Arts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RM - The Real McCoys(《真正的麦科伊一家》)
SFC - Southern Folklife Collection,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TBS -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TSS - Television Series Scripts,Theater Arts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1]. 关于术语的说明。鉴于我所讨论的标签可能具有贬义性质,同时为避免混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将使用”hillbilly”(乡巴佬)和”mountaineer”(山民)这两个标签来指代媒体对南方山区实际居民的描绘。而在指称这些人本身时,我将使用”(南方)山区人”、“(南方)山区民众”或”山地居民”等表述。唯一的例外是当我引用某位选择用我所分析的媒体标签来描述自己的个人时。
[2]. 该术语来自威廉姆森的《山地乡村:电影对山区的影响及山区对电影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南部山区的确切地理边界。简而言之,本研究所定义的”阿巴拉契亚”是美国东南部的山区,由三种主要地形组成:大阿巴拉契亚山谷、东部的蓝岭山脉,以及西部的坎伯兰高原和阿勒格尼山脉。根据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ARC)1998年提供的更广泛定义,阿巴拉契亚地区涵盖十三个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以及406个县,从密西西比州东北部延伸至纽约州西南部。“欧扎克”由阿肯色州西部和俄克拉荷马州东部的沃希托山脉、阿肯色州中西部的波士顿山脉,以及阿肯色州北部、密苏里州南部和俄克拉荷马州东北角的欧扎克高原组成。关于南部阿巴拉契亚(定义为”南部高地”)的更详细描述,参见坎贝尔《南部高地人及其家园》第10-18页。另见巴托《阿巴拉契亚的发明》第2-3页,以及万斯”该地区:新调查”,载于福特《南部阿巴拉契亚地区——调查》第1-3页。关于欧扎克,参见布莱文斯《山地居民:阿肯色州欧扎克人的历史及其形象》第11-14页。
[3]. 关于南部贫穷白人的贬义称谓介绍,参见弗林特《迪克西被遗忘的人——南方的贫穷白人》第8-9页,以及查尔斯·里根·威尔逊关于”Crackers”的词条和F·N·博尼关于”Rednecks”的词条,分别载于威尔逊和费里斯编《南方文化百科全书》第1132页和第1140-41页。关于山区居民此类称谓的列表,参见伦道夫和威尔逊《山谷深处:欧扎克民间语言集锦》第252页。帕特里克·胡贝尔对这些术语的演变提供了最佳的历史分析。参见他的”红脖子与毛帽子、胡希尔人与乡巴佬:南方白人工人阶级、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定义”以及”红脖子简史:南方白人男性身份的塑造”。关于白人阶级蔑称被挪用的近期例子,参见雷和纽维茨编《白色垃圾——美国的种族与阶级》,以及哈蒂根《种族情境:底特律白人身份的阶级困境》。
[4]. 关于美国白人身份的社会建构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中的表现,参见罗迪格《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走向废除白人身份》,萨克斯顿《白人共和国的兴衰:十九世纪美国的阶级、政治与大众文化》,伊格纳季耶夫《爱尔兰人如何成为白人》,以及雅各布森《不同颜色的白人:欧洲移民与种族的炼金术》。关于白人对非白人文化和身份的迷恋以及试图挪用和征服的深刻专著包括:洛特《爱与盗窃——黑脸滑稽剧与美国工人阶级》,皮特斯《白人论黑人——西方流行文化中的非洲和黑人形象》,弗兰肯伯格《白人女性,种族问题:白人身份的社会建构》,黑尔《制造白人身份:1890-1940年南方的种族隔离文化》,以及德洛里亚《扮演印第安人》。另见菲什金”质疑’白人身份’,复杂化’黑人身份’:重绘美国文化地图”。
[5]. 关于对大众文化的典型批评,参见伯纳德·罗森伯格”美国的大众文化”,载于罗森伯格和怀特编《大众文化:美国的流行艺术》第3-12页,麦克唐纳”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以及更近期的例子,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尤其是第61-81页。关于流行文化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参见莱文”工业社会的民俗:流行文化及其受众”,舒德森”流行文化的新认可:学术界的感性与情感”,以及利普西茨”‘这不是杂耍’:历史学家与媒体研究”和”倾听以学习,学习以倾听:流行文化、文化理论与美国研究”。
[6]. 我的研究建立在早期关于南部山区(特别是”阿巴拉契亚”)和南部山民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开创性著作包括夏皮罗《心中的阿巴拉契亚——1870-1920年美国意识中的南部山区与山民》,威廉姆斯”事实与虚构中的南部山民”,巴托《阿巴拉契亚的发明》,惠斯南特《一切本土而美好的事物——美国一个地区的文化政治》,以及威廉姆森《山地乡村》。其他有益的学术著作包括麦克尼尔编《民间与流行文化中的阿巴拉契亚形象》,贝克尔《贩卖传统:阿巴拉契亚与美国民间的建构,1930-1940》,沃尔”退化与进化:乡巴佬与牛仔作为美国野蛮人”,奥托”‘乡巴佬文化’:历史与流行文化中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居民”,以及布莱文斯《山地居民》。
[7]. 理查德·戴尔,“导言”,载于戴尔编《形象的问题——表征论文集》第4页。
[1]. 摩根《美国偶像——乔纳森兄弟与美国身份》第55-56页;同上,第23页(“愚蠢的面具”)。关于扬基人的历史,参见鲁尔克《美国幽默:民族性格研究》第一章,布莱尔《美国本土幽默》第17-62页,布莱尔和希尔《美国的幽默:从穷理查到杜恩斯伯里》第165-71、180-86页,以及布朗纳《纽约州的老式音乐制作人》第57-59页。
[2]. Morgan对乔纳森兄弟形象的含义和演变进行了细致研究。Johns的《美国风俗画:日常生活的政治》第1-2章,对”类型化”过程和杰克逊时代”扬基”(Yankee)一词的含义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3]. Byrd实际上写了三份关于这次旅程的记述:一份是他在考察期间写的日记;一份是后来所谓的”秘密历史”,是他为弗吉尼亚朋友圈私下娱乐而写的;还有一份大幅扩展的”官方”文本,旨在出版和广泛传播。虽然”官方”版《分界线历史》是在他完成测量后不久写成的,但直到1841年才出版,而”非官方”版《分界线秘史》直到1929年才付印。两个版本并排呈现在《威廉·伯德的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分界线历史》一书中。关于Byrd及其记述的一般性讨论,参见该书Adams和Boyd的导言,分别为第v-xxii页和第xxiii-xxxix页。另见Lynn《马克·吐温与西南幽默》第3-22页;McIlwaine《南方贫穷白人——从懒汉之地到烟草路》第3-15页。关于Byrd对印第安人和边疆定居者的比较,参见Slotkin《通过暴力重生——美国边疆神话,1600-1860》第215-22页。
[4]. 《分界线历史》第90-92页。有趣的是,这段文字并未出现在《秘史》版本中。显然,与他在官方版本中删除的性行为描写和关于考察队员身体特征的玩笑话不同,Byrd并不担心他预期的殖民地和欧洲精英读者会对他描述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居民的文字感到丝毫不快。Lynn甚至认为他用这些描述来替代”秘史”中对弗吉尼亚人的贬损言论。参见Lynn《马克·吐温》第14页。
[5]. Charles Woodmason,《革命前夕的卡罗来纳边远地区:查尔斯·伍德梅森的日记及其他著作,英国国教巡回传教士》,Richard J. Hooker编(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52页,引自Huber《红脖子与羊毛帽,胡希尔人与山民:南方白人工人阶级、语言与身份认同》第65-66页。
[6]. 《卡罗来纳沙丘居民》。这篇报道显然是从《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观察家报》转载的。感谢Joe Bauman与我分享这篇文章的副本。McIlwaine认为,这种出于废奴动机描绘贫穷白人困境的作品在战前北方期刊和文学中很常见。参见McIlwaine《南方贫穷白人》第32-39页。关于文学和非虚构作品中南方贫穷白人的全面综述,另见McIlwaine;Cook《从烟草路到66号公路——小说中的南方贫穷白人》第3-4页,以及Huber《红脖子与羊毛帽》。关于这一群体历史和社会地位的引人入胜但已过时的记述包括Buck《战前南方的贫穷白人》第41-54页,以及Hollander《“贫穷白人”的传统》。更当代的学术研究参见Newby《新南方的普通民众——1880-1915年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延续》,Flynt《贫穷但自豪:阿拉巴马州的贫穷白人》,Jones《被剥夺者:从内战到现在的美国底层阶级》,以及Foley《白色祸害:德克萨斯棉花文化中的墨西哥人、黑人和贫穷白人》。
[7]. Huber《红脖子与羊毛帽》第68-71、76-79页;D. R. Hundley《我们南方各州的社会关系》(纽约:1860年),第263-65页,引自Buck《贫穷白人》第43、45页。
[8]. 波士顿《每日广告报》记者引自《国会记录》,第39届国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特区:F & J Rives,1866年),第552页,引自Huber《红脖子与羊毛帽》第76页。关于十九世纪谴责”贫穷白人”并阐述其独立种族地位的各种例子,参见Huber《红脖子与羊毛帽》第75-78、88-91页及第3章各处。
[9]. 同上,第91-92页;Genovese《“宁做黑鬼也不做贫穷白人”:奴隶对南方自耕农和贫穷白人的看法》。
[10]. McIlwaine《南方贫穷白人》第48-50、57-58页;Cook《从烟草路到66号公路》第6-7页;Lynn《马克·吐温》第70-72、77-78页;Slotkin《通过暴力重生》第416-17页(文学分析);Williamson《山民之地——电影对山区做了什么,山区对电影做了什么》第34-35页。Cohen和Dillingham编《旧西南幽默》是文学摘录和有用传记概述的汇编。
[11]. Harris《萨特·洛文古德:一个”天生该死的傻瓜”讲的故事》第24页。另见Rickels《乔治·华盛顿·哈里斯》,以及Blair和Hill《美国的幽默》第213-21页。Williamson认为,洛文古德不仅应被视为山民形象的先驱,还应被视为至少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传统的一部分——那个戴着驴耳朵和鸡冠帽的傻瓜,举起镜子揭示当权者的虚荣和伪善。参见Williamson《山民之地》第21-27、33-34页。
[12]. 关于Harris的生平和政治观点,参见Rickels《乔治·华盛顿·哈里斯》第31-36页,Lynn《马克·吐温》第131-32页,以及Day《乔治·华盛顿·哈里斯的一生》;吐温的评论引自Caron和Inge《萨特·洛文古德的天生故事大王》第79页。Edmund Wilson是Harris最著名的批评者,在吐温之后近一百年,他在《爱国之血》(1962年)中认为萨特不过是”一个蹲在自己污秽中的农民”,而他的故事集是”美国文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最令人厌恶的书”。参见他的评论再版于Caron和Inge《萨特·洛文古德》第101、100页。
[1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插画家们一直将萨特描绘成典型的山民形象,要么是卡通式的乡巴佬,要么是强壮自信的山地人。我对萨特图像描绘者的分析主要借鉴了英格的文章《萨特和他的插画家们》,该文收录了上述所有插图的副本。
[14]. 《弗吉尼亚公报》(里士满),1780年11月11日,引自熊著《田纳西山区的两个世界:探索阿巴拉契亚刻板印象的起源》,第20页。
[15]. 斯洛特金,《通过暴力的再生》,第269页。关于布恩神话历史发展的精彩详细叙述,参见斯洛特金,特别是第9-10章、第12-13章。另见法拉格尔,《丹尼尔·布恩:一位美国先驱的生平与传奇》。
[16]. 参见威廉森,《乡巴佬之地》,第278-79、280页;豪克,《戴维·克罗克特电影目录》,第122-23页。克罗克特在大众记忆中是一位”山地人”,但实际上他在田纳西州中南部长大并代表该地区,远离东部的坎伯兰山脉或大烟山。关于大卫·克罗克特的生平,参见沙克福德,《戴维·克罗克特——其人与传奇》,以及威廉森,《乡巴佬之地》,第78-82页。关于克罗克特神话的文化用途,参见休伊特,《美国戏剧——1668至1957年》,第223-26页,洛法罗编,《戴维·克罗克特》,以及洛法罗和卡明斯编,《两百年后的克罗克特:关于其人与神话的新视角》。
[17]. 克罗克特的旅行见沙克福德,《戴维·克罗克特》,第212-13页,布恩的旅行见法拉格尔,《丹尼尔·布恩》,第8章。
[18]. 这些十九世纪早期游记的例子包括詹姆斯·柯克·保尔丁,《南方来信:1816年夏季旅行期间所写》(纽约:詹姆斯·伊斯特本公司,1817年),查尔斯·芬诺·霍夫曼,《西部之冬》(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835年),以及查尔斯·兰曼,《阿勒格尼山区来信》(纽约:G.P.普特南之子出版社,1849年),引自巴托,《阿巴拉契亚的发明》,第30-32页;斯特罗瑟,《南方之冬》,第16卷,第175-76页。关于斯特罗瑟及其1857年旅行的背景,参见埃比,《“门廊蜡笔”:大卫·亨特·斯特罗瑟的一生》,特别是第93-94页,以及熊著,《两个世界》,第163-73页。
[19]. 奥姆斯特德,《内陆之旅》,第275-78页。
[20]. 巴托,《阿巴拉契亚的发明》,第16-17页,以及因斯科,《奥姆斯特德在阿巴拉契亚:一位康涅狄格北方佬在1854年南方高地遭遇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21]. 斯库尔克拉夫特,《奥扎克山脉半高山地区的场景与冒险:密苏里与阿肯色》,第235页。虽然这部作品直到1850年代才出版,但斯库尔克拉夫特已于1819年和1821年发表了部分内容。参见马斯特森,《阿肯色奇谈》(波士顿:查普曼与格莱姆斯出版社,1942年),重印为《阿肯色民间传说——阿肯色旅人、戴维·克罗克特及其他传奇》,第2、306页。
[22]. 乔治·威廉·费瑟斯通豪,《穿越蓄奴州的旅行:从波托马克河畔的华盛顿到墨西哥边境》(纽约,1844年),第87-88页,引自威廉斯,《熊州形象:十九世纪的阿肯色》,第103页;弗雷德里克·格斯塔克,《远西的野外运动》(伦敦:1855年);查尔斯·芬顿·默瑟·诺兰,《魔鬼岔口的皮特·惠特斯通:致〈时代精神〉的信》,特德·R·沃利和尤金·A·诺尔特编(阿肯色州范布伦:1957年),以及托马斯·班斯·索普,《阿肯色大熊》,载于威廉·T·波特编,《阿肯色大熊及其他速写:南方与西南部人物与事件图解》(费城,1845年),第13-31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威廉斯,《熊州形象》,第103-5页。
[23]. 关于”阿肯色旅人”一词争议性用法的历史,参见马斯特森,《阿肯色民间传说》,第123-25页,以及兰开斯特,《赤脚与慢车》,第90页。关于对该州负面形象的反击,另见兰开斯特,第34-37、98-101页,戴尔,《阿肯色:神话与州》,杜,《“乘慢车穿越阿肯色”——二十世纪早期阿肯色的负面形象》,以及威廉斯,《熊州形象》,第99-111页。感谢杰里·威廉森提请我注意兰开斯特的文章。
[24]. 马斯特森记录了这个故事的十二个版本,并认为福克纳的版本是已知最早的例子,因此最可能是原始形式。参见马斯特森,《阿肯色民间传说》,第186-219页。然而,这一形象可能有更早的起源。在1833年的一篇旅行记述(1836年出版)中,作者描述了他在奥扎克山脉”优美起伏的高地乡村”遇到一间小木屋主人的经历。那位定居者”坐在门前,全身穿着皮革,正在大声拉小提琴。“与”阿肯色旅人”中的占地者不同,这个人并不肮脏暴躁,而是一位欢快强健的边疆人,非常符合戴维·克罗克特的形象,具有相当的体能:“高大健壮,他兼具豹的敏捷、狮的力量,以及印第安人沉默、迅速、隐秘的行动方式。”参见《阿肯色来信》,第25-26页。
[25]. 布朗,《阿肯色旅人:画布上的西南幽默》,第348-50、372-73页。这段对话是1859年爱德华·沃什伯恩首次出版的文本的重印,用于配合利奥波德·格罗泽利尔的”阿肯色旅人”版画。关于这个故事的起源,另见格林,《图像#67:视觉化的阿肯色旅人》,麦克尼尔,《“沿着奥扎克小径”:奥扎克在流行歌曲和民歌中的形象》,以及默瑟,《追踪”阿肯色旅人”》,第709-11页。
[26]. 马斯特森,《阿肯色民间传说》,第186页。这个1876年的版本基于小石城出版的一份战前(约1858-1860年)原版的副本。
[27]. 布朗,《阿肯色旅人》,第370页。
[28]. 1896年的版本开头是:“太阳正在平原上落下。一个戴着浣熊皮帽、腰间别着手枪和博伊刀(bowie knife)的迟归骑手,骑马来到一间拓荒者小屋前请求借宿一晚。在一间破旧棚屋的门口,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跨坐在木桶上,缓缓拉出你听到的曲调。背景中有孩子们,一个邋遢的女人站在门槛上。”见Mercer,“On the Track of ‘the Arkansas Traveller,’” 707。
[29]. 关于”新杂志”的兴起,见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The Southern Mountains and Mountaineers in the American Consciousness, 1870–1920,6–7,Schneirov,The Dream of a New Social Order—Popular Magazines in America, 1893–1914,以及Wilson,“The Rhetoric of Consumption: Mass-Market Magazines and the Demise of the Gentle Reader”;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4。
[30]. “地方色彩运动”一词是后来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创造的,他们在这些不同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统一的文学体系,虽然在艺术上有局限性,但对世纪之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多元化国家愿景的建立仍然很重要。关于地方色彩文学对阿巴拉契亚意义的详细讨论,见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xiii–xiv,3–18,以及Williams,“The Southern Mountaineer in Fact and Fiction”,117–28。关于该类型的例子,见Warfel和Orians编,American Local-Color Stories。
[31]. 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18;Harney,“A Strange Land and a Peculiar People”,45–58。
[32]. 关于质疑Murfree描写真实性的解读,见Batteau,Invention of Appalachia,39–41,Hsuing,Two Worlds,179–82,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19,以及Williams,“Southern Mountaineer”,第4章。关于相反的观点,见Durwood Dunn,“Mary Noailles Murfree: A Reappraisal”,197–204。无论她描写的真实性如何,Murfree的作品非常受欢迎,In the Tennessee Mountains在1884年至1922年间重印了二十四次。见Hsuing,Two Worlds,176,以及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19。
[33]. Allen,“Through Cumberland Gap on Horseback”,62;Harney,“Strange Land”,48,以及Semple,“The Anglo-Saxons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s: A Study in Anthropogeography”,151。
[34]. Allen,55–56。山区居民并不是Kemble刻板描绘的唯一社会群体。作为1880年至1930年代初期Collier’s、Harper’s、Leslie’s Weekly和Life等杂志的主要政治漫画家,以及Huckleberry Finn首版的插画师,Kemble最为人知的是对非裔美国人的描绘。他的一些作品集标题如Kemble’s Coons和A Pick-aninny Calendar表明,这些画作与他对山区居民的描绘一样充满了广泛(且粗俗)的刻板印象。见”Edward Winsor Kemble”,载于Horn编,The World Encyclopedia of Cartoons v. 1: 332–33;以及Holt,“A Coon Alphabet and the Comic Mask of Racial Prejudice”,307–18。
[35]. Warner,“Comments on Kentucky”,271。关于地方色彩文学中对山区女性的描绘,见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22–26;Batteau,Invention of Appalachia,49–56;Williams,“Southern Mountaineer”,153及第5章各处;以及Miller,“The Mountain Woman in Fact and Fiction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36]. Miller,Revenuers and Moonshiners—Enforcing Federal Liquor Law in the Mountain South, 1865–1900,以及Holmes,“Moonshining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Georgia, 1889–1895”,589–611。
[37]. 全国媒体聚焦于山区,尽管1874年至1895年间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报道的四十一起肯塔基州械斗中,近一半发生在东部山区县以外的地方。见Waller,“Feuding in Appalachia—Evolution of a Cultural Stereotype”,354。
[38]. Baltimore Sun社论引自Ashworth,“The Virginia Mountaineers”,188。
[39]. Waller,“Feuding”,347–76,以及Feud—Hatfields, McCoys, and Social Change in Appalachia—1860–1900;Klotter,“Feuds in Appalachia: An Overview”,290–317,以及McKinney,“Industrialization and Violence in Appalachia in the 1890’s”。Pearce,Days of Darkness: The Feuds of Eastern Kentucky,提供了一个通俗化的概述。
[40]. Crawford,An American Vendetta: A Story of Barba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9。正如Waller在Feud中详述的,双方的分歧更多是沿着经济而非血缘关系划分的——这是市场导向力量与传统导向力量之间的斗争。William Anderson(“魔鬼安斯”)Hatfield及其同伙完全融入了不断扩张的地区和国家经济,双方都在司法系统和他们所理解的法律范围内行事。此外,肯塔基州东部的各种企业家利用此案来推进他们的经济利益,将肯塔基州(McCoy家族居住地)描绘成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对抗”魔鬼安斯”Hatfield和他那些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无法无天的林中人。关于Crawford对山区居民的负面成见如何扭曲了他的叙述,见Waller,Feud,222–28。
[41]. Crawford,Vendetta,8。Hatfield的照片见MacClintock,“The Kentucky Mountains and Their Feuds”,181;Williamson,Hillbillyland,270–71。
[42]. 关于John Fox, Jr.在塑造南方山区人民形象方面的巨大影响,见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210–14;Waller,“Feuding”,362–63;Batteau,Invention of Appalachia,64–74,84–85;Titus,John Fox, Jr,以及Wilson,“The Felicitous Convergence of Mythma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John Fox Jr. and the Formation of An(Other) Almost-White American Under-class”。
[43]. Vincent,“A Retarded Frontier”,1;同上,15–16,19;Warner,“Comments on Kentucky”,270。
[44]. Lynde,“The Moonshiner of Fact”,76–78。
[45]. Davis, “The ‘Mountain Whites’ of America,” 426(“道德松弛”);Wilds, “The Mountain Whites of the South,” 921;Darlene Wilson, “Mythma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24–25(伯里亚学生对福克斯的反应)。据Darlene Wilson所述,福克斯也深受欧文·威斯特、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等极具影响力人物的喜爱,他们都认同他将山民视为最后的边疆开拓者的观点。关于二十世纪初本地山民对这一刻板印象的批评,参见Ashworth, “The Virginia Mountaineers,” 196,以及Johnson, “Life in the Kentucky Mountains. By a Mountaineer.”
[46]. 伯里亚学院院长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1899年发表的”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s”是首次将南部山区的土地和人民命名为”阿巴拉契亚美洲”的著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教育工作者、慈善工作者、社会科学家和非虚构作家巩固了阿巴拉契亚作为独特社会文化实体的概念。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包括Semple的”The Anglo-Saxons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s”、Miles的The Spirit of the Mountains、Kephart的Our Southern Highlanders—A Narrative of Adventure in the Southern Appalachians and a Study of Life among the Mountaineers,以及Campbell的The Southern Highlander and His Homeland。
[47]. Batteau,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63(“最黑暗的阿巴拉契亚”)。关于二十世纪初本土主义的概述,参见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第4–7章,以及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An Ethnic History,第5–6章。进步主义的总体概述包括Robert H. Weibe的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Rodgers的”In Search of Progressivism”,以及Paul Boyer的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第4部分。
[48]. Semple, “The Anglo-Saxons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s,” 150;Wilson,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s, 161。同样,威廉·弗罗斯特在1899年强调,虽然”上流社会”的美国家庭”已不再多产”,但山区的男女”仍在养育数量足以令族长们满意的健壮子女”。他总结道:“这样一个人口的潜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参见Frost, “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 105。
[49]. “Poor White Trash,” 579;John Fiske, Old Virginia and Her Neighbor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7),2: 319–21,引自Shapiro, Appalachia on Our Mind, 94。关于菲斯克重要性的更多内容,另见Shapiro, 92–98。
[50]. Johnston, “Romance and Tragedy of Kentucky Feuds,” 111。
[51]. Klotter, “The Black South and White Appalachia,” 62。关于”山地白人”这一标签的历史发展,参见Klotter, “Black South,” 54, 59–60,以及Shapiro, Appalachia on Our Mind, 51–54。
[52]. William Goodell Frost, “New England in Kentucky,” Advance(June 6, 1895): 1285,引自Klotter, “Black South,” 59。
[53]. Davis, “The ‘Mountain Whites’ of America,” 423。尽管戴维斯谴责”山地白人”的堕落,但与弗罗斯特一样,她赞扬他们的信仰,并以近乎末世论的口吻描述他们作为宗教堡垒的潜力:“谁知道这些人是否是上帝将从这些山中带出的后备力量,被基督拯救,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危机做准备,成为与我们一起捍卫新教的坚强队伍。”参见同上,423;Campbell, “Classification of Mountain Whites,” 2。
[54]. Samuel Wilson,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s,” 24–25。由于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06年,威尔逊很可能早在这一时期就否定了这一标签;同上,43。
[55]. Shapiro, Appalachia on Our Mind, 91。
[1]. 引自Ross, Working-Class Hollywood: Silent Film and the Shaping of Class in America, 45。
[2]. Green, “Hillbilly Music: Source and Symbol,” 204。格林指出,“hill-folk”(山地民)一词可追溯到十七世纪末,指的是反对查理二世的卡梅伦派信徒,他们先逃往苏格兰高地,后又迁至美国山区。因此,这个词带有责难和社会抵抗的含义,反映了后来”hillbilly”(乡巴佬)一词复杂的文化意涵。另见Huber, “Rednecks and Woolhats, Hoosiers and Hillbillies: Working-Class Southern Whites, Language, and the Definition of Identity,” 103,Green, “Hillbilly Music,” 204,以及Otto, “Plain Folk, Lost Frontiersmen, and Hillbillies: The Southern Mountain Folk in History and Popular Culture”;哈本的小说引自Craigie and Hulbert编,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 2: 1248。
[3]. Lovinggood, “Negro Seer: His Preparation and Mission,” 163。非裔美国人口语中使用”hillbilly”的类似例子是民谣”I Would Rather Be a Negro Than a Poor White Man”,其中有一节:“I’d druther be a Nigger, an’ plow old Beck / Dan a white Hill Billy wid his long red neck.”引自Thomas W. Talley, Negro Folk Rhymes(New York: Macmillan, 1922),42–43,引自Folder: “Hillbilly Culture and Image,” Box 3, AGP。
[4]. Blue Ridge Country(November/December 1992),51(“Camp Hillbilly”照片)。据该杂志下一期介绍,照片中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刘易斯堡的男女在西弗吉尼亚州格林布赖尔县山区露营。感谢杰里·威廉姆森与我分享这张图片。
[5]. Hawthorne, “Mountain Votes Spoil Huntington’s Revenge,” 2。
[6]. 希布勒的文本引自Masterson, Arkansas Folklore—The Arkansas Traveller, Davey Crockett, and Other Legends, 274–75;同上,275–76;关于”慢车”文学类型的概述,参见Masterson, Arkansas Folklore, 269–80,以及W. K. McNeil为Jackson的On a Slow Train through Arkansaw所写的导言,11–13。
[7]. McNeil,《慢车》导言,x-xi,3,7;Dew,“‘穿越阿肯色的慢车’——二十世纪初阿肯色的负面形象”,125-35,以及Lancaster,“赤脚与慢车”,39-41。关于非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类似建构,参见Toll,《涂黑脸——十九世纪美国的黑人滑稽剧》,Lott,《爱与盗窃——黑脸滑稽剧与美国工人阶级》,以及Hale,《制造白人身份——南方种族隔离文化,1890-1940》,尤其是151-68页。
[8]. Masterson,《阿肯色民俗》,96;Hughes,《阿肯色三年》,24-29;同上,14。人们只需回想1972年电影《激流四勇士》中臭名昭著的男性强奸场景——山民强奸犯要求受害者”像猪一样尖叫”——就能认识到这种将山地居民与猪的性关系联系起来的观念有多么强大和持久。
[9]. Hughes,《阿肯色三年》,8,73,79;同上,90-91。
[10]. 同上,76。
[11]. 同上,112-13;Masterson,《阿肯色民俗》,104。
[12]. Carr,“西北阿肯色词汇表”,416,418(原文斜体);《美国英语词典》,1248;Wentworth,《美国方言词典》,292;Cassidy编,《美国区域英语词典》第2卷,1010。
[13]. 关于世纪之交阿巴拉契亚的经济转型,参见Eller,《矿工、磨坊工与山民:阿巴拉契亚南部的现代化,1880-1930》,以及Hall等,《如同一家人:南方棉纺厂世界的形成》。关于对公司城镇和纺织厂的批评与辩护,参见Shapiro,《我们心中的阿巴拉契亚——美国意识中的南方山区与山民,1870-1920》,163-85,以及Hall等,《如同一家人》,56-60。批评和辩护棉纺厂所带来变化的当代代表性文章分别是Campbell,“从山间小屋到棉纺厂”,74-84,以及Harriman,“南方棉花产业的若干方面”,12。
[14]. Huber,“红脖子与毛帽子”,115-19(“红脖子”一词的使用)。关于世纪之交美国高度种族化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参见Kantrowitz,《本·蒂尔曼与白人至上主义的重建》,第6章及全书,Jacobsen,《不同颜色的白人身份——欧洲移民与种族的炼金术》,第2章,以及Hale,《制造白人身份》。关于”乡巴佬”(hillbilly)一词与白人至上主义重建之间的潜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注释5讨论的1900年文章中,Hawthorne明确将”乡巴佬”的投票权与佐治亚州黑人的被剥夺选举权并列对比。
[15]. Rose O’Neill是密苏里州塔尼县人,那里是奥扎克山区的中心地带,她告诉Randolph,她直到1900年以后才听到这个词,而阿肯色州芒廷霍姆的一位报人声称他直到1906年才听到这个词。参见Randolph和Wilson,《深入山谷——奥扎克民间语言集锦》,252。这个词在1897年Barrere和Leland编纂的美国俚语汇编《俚语、行话与黑话词典》中也没有出现。
[16]. 观众规模估计来自Koszarski,《一晚的娱乐:无声故事片时代1915-1928》,25-26。Koszarski指出,由于缺乏记录,1922年之前的付费入场人数无法可靠确定;Williamson,《无声电影中的南方山民:关于私酿酒、世仇及其他山区题材电影的情节概要,1904-1929》,2;《百代公报1896-1908》,229(“最广为人知……”);Williamson,《南方山民》,3-4。虽然Williamson包含了一些超出我对乡巴佬更狭义定义范围的类别(如历史人物和煤矿开采),但即使排除其中一个或多个类别,这些年间制作的山民电影数量仍然惊人。
[17]. Williamson,《南方山民》,7-8。Williamson认为他的统计数字可能偏低,因为电影行业报刊在电影概要中的描述往往含糊笼统。另见他的”南方山民电影目录”。关于这一时期无声电影的一般性介绍,参见May,《筛除过去——大众文化与电影产业的诞生》,尤其是第6章,Ross,《工人阶级的好莱坞》,11-33,Everson,《美国无声电影》,以及Koszarski,《一晚的娱乐》。
[18]. Williamson,《南方山民》,7-8。
[19]. Williamson统计了他研究的476部电影中女性犯下的11起谋杀和超过65起袭击事件。参见Williamson,《南方山民》,7;《百代公报1908-1912》,145(《山民的荣誉》);正如Williamson敏锐指出的,大多数”乡巴佬女孩无声电影……以传统的’婚姻金钱’(matrimoney,原文如此)结尾,昔日的女孩们因为接受了较弱的角色和经济依附而成为’淑女’。“参见Williamson,《乡巴佬之地——电影对山区做了什么,山区对电影做了什么》,234。
[20]. 关于观众对媒体的潜在颠覆性解读的讨论,包括Radway,《阅读言情小说——女性、父权制与通俗文学》,Jenkins,《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Fiske,《阅读大众文化》,以及Levine,“工业社会的民俗:大众文化及其受众”。关于早期无声电影颠覆性可能的两种解读,参见Hansen,《巴别塔与巴比伦:美国无声电影中的观看行为》,以及Ross,“观众的反叛:重新审视无声电影时代的观众与接受”。
[21]. 《好管家》杂志文章引自Nye,《毫不尴尬的缪斯——美国流行艺术》,373页。关于这一时期的电影审查工作,参见同上,372-74页,May,《筛选过去》,43-59页,Grieveson,“为什么1907年芝加哥的观众很重要”,79-91页,Ross,《工人阶级的好莱坞》,27-33页,以及Koszarki,《一晚的娱乐》,198-210页。
[22]. 《电影世界》46:6(1920年10月9日),引自Williamson,《南方山民》,7页。
[23]. 关于格里菲斯对非白人角色的种族主义刻画,参见Daniel Bernardi,“白人的声音:D. W. 格里菲斯的传记影片(1908-1913)”,104页;同上,111-13页。关于格里菲斯的电影,更广泛地参见Simmon,《D. W. 格里菲斯的电影》。格里菲斯为传记公司(美国活动影像和传记公司)拍摄的山民电影包括《世仇与火鸡:肯塔基山区的浪漫故事》(1908)、《山民的荣誉》(1909)、《逃亡者》(1910)、《税务官和他的女孩》(1911)、《山间之恋》(1911)和《肯塔基山区的世仇》(1912)。此外,传记公司在格里菲斯到来之前发行了多部山区电影,包括《私酿酒者》(1904)、《肯塔基世仇》(1905)和《恐怖之夜》(1908)。参见Williamson,“南方山民电影目录”,《传记公告1896-1908》,114-16、228-29、352-53、410页,以及《传记公告1908-1912》,145、337、347页。
[24]. 《希金斯家族对贾德森家族》(Lubin,1911);《特工斯尼茨》(Sterling,1914);阿巴克尔和基顿主演了《私酿酒》(派拉蒙,1918),劳埃德主演了《奥扎克浪漫曲》(百代/罗林,1918)。参见Williamson,《乡巴佬之地》,38-39、269-71页;Williamson,“南方山民电影目录”。
[25]. 关于类似种族刻板印象的多种形式,参见Toll,《涂黑脸》,Lott,《爱与盗窃》,Curtis,《猿与天使:维多利亚时代漫画中的爱尔兰人》。关于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的力量和可塑性的深思熟虑的讨论(特别是二战期间对日本人的猿类刻画),参见Dower,《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302页。
[26]. Williamson,《南方山民》,10、2页。
[27]. 关于电影业的变化,参见May,《筛选》,62-66、167-69页,Williamson,《南方山民》,9-10页,Ross,《工人阶级的好莱坞》,118-23页;《私酿酒世仇》(约1919),FTA。
[28]. S. T. Wilson,《南方山民》,188页;Deal,“‘乡巴佬’或’美国山民’……”,1、11、4页;在1920年之前撰写的关于南阿巴拉契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三部非虚构作品中,没有一部包含这个术语:坎贝尔的《南方高地人及其家园》、凯普哈特的《我们的南方高地人》或迈尔斯的《山的精神》。
[29]. 有趣的是,可以推测为什么一战前唯一使用”hillbilly”(乡巴佬)一词的电影以奥扎克地区为背景。这是否表明关于该地区的著名讽刺作品使这个术语对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山区地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更加浪漫化和神话化的南阿巴拉契亚地区来说还不行?这种幽默文学叙述与奥扎克背景之间的联系可能表明,无论与故事情节多么遥远,“hillbilly”一词及其使用始终固有一种本质上的喜剧成分。
[30]. Bradley,“与乡巴佬们交往”,95页。
[31]. 同上,103页。
[32]. 同上,100页。
[33]. 《乡巴佬》,1914年12月,第2期,1页;同上,1915年1月,第3期,19-20页。
[34]. 由于我查阅的这份出版物收藏并非完整版本,创刊号可能讨论了标题的意义,乡巴佬刻板印象可能在1939年之前就出现了;但在1935年之前并未出现。
[1]. Malone,《歌唱牛仔与音乐山民:南方文化与乡村音乐的根源》,2页,以及Malone,《别忘了你的出身:乡村音乐与南方工人阶级》,16-22页。
[2]. 乡村表演者将商业音乐产品如此无缝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以至于梅贝尔·卡特的《野花》或布拉德利·金凯德的《致命婚礼》等”民歌”的城市起源后来常常被遗忘。关于乡村音乐的前商业历史,参见Malone,《歌唱牛仔》,第1-2章,以及《乡村音乐,美国》,第1章,Wiggins,《疯狂的乔治亚小提琴手——小提琴手约翰·卡森,他的真实世界和他歌曲的世界》,第1章,Bronner,《纽约州的老式音乐制作人》,5-14页及各处,以及Wilgus,“乡巴佬音乐研究导论”,195-203页。
[3]. 广播统计数据来自Malone,《乡村音乐》,32页,以及Douglas,“广播与电视”,903-4页。关于192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参见Archdeacon,《成为美国人——一部民族史》,第5-6章,以及Dumenil,《现代气质——1920年代的美国文化与社会》,尤其是第4章。
[4]. Okeh录制的第一首布鲁斯歌曲是玛米·史密斯1920年2月的《疯狂布鲁斯》。皮尔第一次听到非裔美国人自我指称使用”种族”一词是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参见Porterfield,“维克多先生和皮尔先生”,12页;Malone,《乡村音乐》,34-35页;Crichton,“那些乡巴佬身上有金子”,24页。虽然皮尔因进行了这种音乐的首次实地录音而值得赞扬,但第一张商业录制的乡村音乐是由西南部小提琴手埃克·罗伯逊和亨利·吉利兰制作的,他们于1922年主动来到纽约,请求维克多唱机公司录制他们的歌曲。他们录制的几首歌曲销量不错,但维克多对这种”低俗”的民间音乐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参见Porterfield,“维克多先生和皮尔先生”,6-7页,Malone,《乡村音乐》,39-40页,以及Cohen,“早期先驱”,11-13页。
[5]. 关于Peer录制Carson的情况,参见Crichton的”Thar’s Gold”第24页,以及Green的”Hillbilly Music: Source and Symbol”第207-210页。一些乡村音乐学者认为Carson原本就在演出计划中,而Peer在商业乡村音乐”启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如Polk Brockman重要——后者是Okeh唱片公司亚特兰大地区的经销商,负责招募录音的音乐团体。学者们还质疑Peer的话究竟是指音乐本身还是录音质量。参见Peterson的《Creating Country Music: Fabricating Authenticity》第17-20页。尽管如此,Peer对Carson表演的反应与他对Mamie Smith首次录音的看法惊人地相似——他后来称那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唱片”,但随即补充道”它卖出了超过一百万张”。参见Crichton的”Thar’s Gold”第24页。
[6]. Peer的引言出自1959年与Lillian Borgeson的访谈,引自Peterson的《Creating》第47页。关于Peer在早期乡村音乐家录音中的作用,参见Porterfield的”Mr. Victor and Mr. Peer”第15-21页,Green的”Hillbilly Music”第206-215页,以及Wolfe的”The Legend That Peer Built—Reappraising the Bristol Sessions”第3-5页。
[7]. 文件夹:Columbia、Vocalion、Victor和Okeh唱片的目录和宣传材料,JEMFC;Pugh的”Country Music Is Here to Stay?“第34页;Pugh的研究笔记,由作者保存;Green的”Hillbilly Music”第221页。感谢Pugh先生慷慨分享他当时尚未发表的文章笔记。
[8]. 参见Columbia唱片目录,1927年9月,第9-10页,文件夹:Columbia唱片目录,1925年,JEMFC;Porterfield的”Mr. Victor and Mr. Peer”第12页(“我发明了……”)。除了DeFord Bailey——一位黑人口琴演奏家,1925年至1941年间是《Grand Ole Opry》的主要明星之一——在1965年Charley Pride打破非官方的种族壁垒之前,没有任何非裔美国表演者作为乡村音乐表演者获得全国声誉。关于Bailey在该节目中复杂经历的更完整叙述,参见Morton和Wolfe的”DeFord Bailey: They Turned Me Loose to Root Hog or Die”第13-17页。
[9]. Peterson的《Creating》第249页注8(方言表演);J. E. Mainer和他的Mountaineers乐队在1965年仍在表演他们的小品”Sambo and Liza”。参见Daniel的”The National Barn Dance on Network Radio: The 1930s”第56页,以及Malone的《Country Music》第8页。关于乡村音乐中的黑脸喜剧演员,参见Green的《Country Roots—The Origins of Country Music》第71-78页;Jordan的”Slo ‘n’ Easy Start Weakly Bull-A-Thon”第6页;Wolfe的《A Good Natured Riot: The Birth of the Grand Ole Opry》第225-230页(“Lasses & Honey”)。
[10]. Malone的《Country Music》第4-5页;Wolfe的”The White Man’s Blues, 1922–40”第38-44页。这对兄弟后来撤销了诉讼,与Victor唱片公司签约——这是一家对录制”白人布鲁斯”更感兴趣的竞争厂牌。
[11]. “Blue Bird——世界上最好的低价乡村和种族唱片”(1937年10月),PTC。Conqueror(Sears Roebuck)厂牌提供”牛仔、种族和山区乡村唱片”精选(1941年秋季),King唱片公司列出”乡村、新奇、黑人、布鲁斯”(1948年7月),Okeh唱片公司宣传”新奇舞曲、乡村舞曲、民歌和种族”音乐(1940年10月)。参见Pugh的研究笔记和Pugh的”Country Music”第38页;Crichton的”Thar’s Gold”第24页。
[12]. Daniel的《Pickin’ on Peachtree—A History of Country Music in Atlanta, Georgia》第30页(滑稽名字);Campbell的”Fiddlers and Divas: Music and Culture in New South Atlanta, 1910–1925”(嘲讽”高雅艺术”的矫饰);Daniel的《Pickin’》第99页(Skillet Lickers乐队的歌曲名);Wiggins的《Fiddlin’》第93、104页(Fiddlin’ John Carson)。
[13]. Daniel的”George Daniell’s Hill Billies: The Band That Named the Music?“第81页;Green的”Hillbilly Music”第216页;Wolfe的”The White Man’s Blues”第40页。“Hill Billie Blues”在1925年Vocalion宣传目录中被列入”喜剧”类别。参见文件夹:Vocalion-Promo, Catalogs & Info: Columbia, Victor, Vocalion, Okeh,JEMFC;“Hill Billie Blues”(Vocalion-14904);Benét的”The Mountain Whippoorwill”第635-639页。关于Benét的诗作,参见Wiggins的《Fiddlin’》第88-92页和Green的”Hillbilly Music”第220页。Wiggins认为这首诗直接取材于二十二岁的Lowe Stokes在1924年乔治亚州老式小提琴大赛上击败Fiddlin’ John Carson的故事——Benét曾在《Literary Digest》上读到过这则报道。
[14]. Benét的”The Mountain Whippoorwill”第635页。
[15]. Crichton的”Thar’s Gold”第24页(“白人山民”);Campbell的”Fiddlers and Divas”(“频频停顿”);Wiggins的《Fiddlin’》第51-52页(“普通车厢”)。
[16]. Wolfe的”The Legend”第4页。Peer后来在描述1927年他在布里斯托尔与Carter家族的录音时使用了类似的山民刻板印象:“他[A. P. Carter]穿着工装裤,那些女人们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乡下女人——穿着印花棉布衣服……她们看起来就像乡巴佬(hillbillies)。”尽管有这样的说法和当地传说称Carter一家赤着脚、从未进过城,但实际上Carter一家曾多次造访布里斯托尔,虽然穿着朴素,但肯定都穿着鞋。Wolfe的”The Legend”第4-5页。
[17]. Green的”Hillbilly Music”第212-214页;Crichton的”Thar’s Gold”第27页。
[18]. A. E. Alderman致Archie Green的信,1961年5月6日,第2页,文件夹:Tony Alderman——通信;第3盒,AGP;“’Hill Billies’占领WRC”,《Radio Digest-Illustrated》,1926年3月6日,第5页,手打副本存于第3盒,AGP;Alderman致Green,1961年5月6日,第3页。
[19]. Green的”Farewell Tony”第232页;Malone的《Singing Cowboys》第77页。
[20]. Peterson和DiMaggio,《早期Opry:其乡村形象的事实与虚构》,43页。这些学者发现,节目最初几年的大多数表演者都是中产阶级,住在纳什维尔或周边小镇;关于”乡村化”表演者的照片,见Hurst,《纳什维尔的大奥普里》,84-86页,以及Kingsbury,《大奥普里乡村音乐史》,24-29页。关于Hay在构建乡巴佬形象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见Peterson,《创造》,71-77页,以及Wolfe,《善意的骚动》,53-55页。
[21]. 《WLS家庭相册》,1933年,21页,JEMFC(“天生的山民”);Hurst,《‘谷仓舞会’时代——回忆芝加哥先驱广播节目的明星们》(转载自《芝加哥论坛报周日杂志》,1984年8月15日,11页),文件夹:WLS广播电台”全国谷仓舞会”,SFC;《WLS家庭相册》,1935年,42页,SFC;Lair,《伦弗罗山谷——过去与现在——’时间静止的山谷’中发生的事》,32页,JLP(伦弗罗山谷男孩乐队更名);Hurst,《’谷仓舞会’》,11页。
[22]. Lair演奏陶罐的照片来自照片收藏,JEMFC(P-1092);“NBC——农场与家庭——1932年8月15日——坎伯兰山脊奔跑者”,文件夹:坎伯兰山脊奔跑者——各种节目1931-2,第1箱,JLP。
[23]. John Lair,《广播中没有乡巴佬》,《WLS周刊》第1卷(1935年3月16日),7页,JLP;标题为”肯塔基女孩”的照片,《Stand By》,1936年11月21日,16页,JLP。感谢Harry Rice让我注意到这张照片。
[24]. 《Stand By》,1936年10月10日,7页,以及1936-1937年各期,JLP。感谢Harry Rice的见解以及为我提供这些漫画的例子。
[25]. Steele,《乡村音乐产业内幕》,20-21页。
[26]. Hay,《大奥普里的故事》,23、41页;“WSM大奥普里最受欢迎的歌曲”(芝加哥:M. M. Cole出版社,1942年),1页,文件夹:WSM大奥普里最受欢迎的歌曲,MF(“我们的小型非正式……”);Peterson和DiMaggio,《早期Opry》,41页(“好的……伙计们”)。关于节目命名的故事经常被复述,反映了Hay刻意的文化定位。Walter Damrosch博士主持的一档歌剧和交响乐广播节目紧接在Hay的节目之前播出,有一天晚上他在节目结束时演奏了一首模仿火车声音的古典作品,并告诉观众这是他破例一次,因为他一贯的原则是”古典音乐中没有写实主义的位置”。轮到Hay上场时,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些评论,让口琴演奏者DeFord Bailey演奏火车歌曲《泛美蓝调》,然后向观众宣布接下来的节目”将完全是写实主义”,与其说是大歌剧(grand opera),不如说更像是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见Jack Harris,《著名WSM大奥普里的真实故事》,《乡村广播》第1卷第2期(1938年10月):4页,JEMFC;Malone,《乡村音乐》,75页;Kingsbury,《大奥普里》,28-29页。
[27]. Pugh,《乡村音乐》,33、36页;Pugh,研究笔记(“最受欢迎的……演奏”);MF(“家乡与山丘……歌曲”);《乡村歌曲的流行对零售利润可能性意味着什么》,《留声机世界》,1925年12月15日,177页,以及《爱迪生圆筒唱片在农村地区销量增长》,《留声机世界》,1925年11月15日,186页,均在文件夹:“1963年5月UCLA之行后的脚注和一些未使用材料”,第4箱,AGP;Abel Green,《’乡巴佬’音乐》,1页;Daniel,《弹奏》,62页(“乡巴佬三重奏”);“1961年4月20日给Charley Bowman和Archie Green的录音带”,文件夹:Tony Alderman/Tony的采访,第3箱,AGP。Al Hopkins的乐队在看到一个名为”奥扎克乡巴佬”的竞争乐队在纽约剧院招牌上做广告后,决定寻求更名。见Green,《乡巴佬音乐》,214页。关于唱片公司公开使用”乡巴佬”一词,见Green,《乡巴佬音乐》,221-22页,以及Pugh,《乡村音乐》,33-34页。
[28]. 引用的乐队来自”著名乡巴佬的新颖原创歌曲——由著名乡巴佬广播、舞台和银幕团体演唱”(FL 0464)和”‘Pappy’ Cheshire和他的乡巴佬冠军——山歌、家乡歌、西部歌、牛仔歌”(FL 0490),MF;Oudeans Hill Boys的描述来自前一来源;“Polly Jenkins和她的犁童——山间心跳”(纽约:Bob Miller公司,1937年)(FL 0502),MF;“’红河’Dave [McEnery]歌本第1册”(Stasny音乐公司[1939年?])(FL 0529),MF。《六月的乡巴佬婚礼》最初于1941年录制,此后多次翻录,最著名的是Gene Autry的版本。见Malone,《歌唱牛仔》,91页。
[29]. Clarence A. Stout,“Hill Billy Family”载于《The Ranch Boys’ Songs of the Plains》(芝加哥:M. M. 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39)(FL 0517),“Songs of the Tennessee Ramblers Folio No. 1”(波特兰:American Music, Inc.,1940)(FL 0617);“Drifting Pioneers’ Song Folio No. 1”(波特兰:American Music, Inc.,1939)(FL 0189);“Clarke’s Comedy Song Folio”(Rialto Music Publishing Company,1935)(FL 0143);“100 WLS Barn Dance Favorites—Pioneer Songs, Southern Songs, Cowboy Songs, Fiddle Tunes, Sacred Songs, Mountain Songs, Home Songs”(芝加哥:M. M. 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35)(FL 0483):均来自MF;Daniel,“The National Barn Dance on Network Radio: The 1930s”,52;The Hoosier Hot Shots,“Them Hill-Billies Are Mountain Williams Now”,Rex 8744(78A)Cavanaugh-Sanford-Mysels。感谢Adam Wilson为我转录歌词。在我相当不科学的已出版”hillbilly(乡巴佬)“标题歌曲统计中,1940年之前有九首,1940年至1949年间新增二十五首,1949年至1960年间有三十六首。这还不包括标题中带有”hill(山)“、”mountain(山)“、”mountaineer(山民)“或相关词汇的无数其他歌曲。资料来源包括MF、《BMI General Index》、《BMI Performance Index》1941-1960,以及Huber,”Rednecks and Woolhats”,153。
[30]. Griffis,“The Beverly Hill Billies”,7。另见Griffis,“The Charlie Quirk 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Beverly Hill Billies”,173-78,以及Martin,“Zeke Manners, ‘Hillbilly’ Who Ruled Radio, Dies at 89”。
[31]. Malone,《Country Music》,93-101,以及《Singing Cowboys》,91-92,Grundy,“‘We Always Tried to Be Good People’: Respectability, Crazy Water Crystals, and Hillbilly Music on the Air, 1933-1935”,Gregory,《American Exodus—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第8章,以及Peterson,《Creating》,第3部分;Zolotow,“Hillbilly Boom”,38(Satherly引言);Malone,《Don’t Get above Your Raisin’》,23。
[32]. “Hillbilly Songs Take U.S. by Storm—Even Broadway”〔1930年代初?〕,WLS Scrapbook,5,JEMFC;Steele,“The Inside Story”,21。注意Steele描述的服装是牛仔和山民元素的混合,类似于1930年代初Beverly Hill Billies采用的风格。历史学家Gregory Waller指出,1934年福克斯音乐片《Stand Up and Cheer》中有一段华丽的歌舞表演”Broadway Goes Hillbilly”,其中合唱女郎从缎面礼服换成格子衬衫和草帽。见Waller,“Hillbilly Music and Will Rogers: Small-town Picture Shows in the 1930s”,164。
[33]. Steele,“The Inside Story”,21;Smith,“‘Hill Billy’ Folk Music—A Little-Known American Type”,154。
[34]. Abel Green,“‘Hill-Billy’ Music”,3。
[35]. 同上,22。
[36]. 见Malone,《Singing Cowboys》,82-84,Wilgus,“Bradley Kincaid”,载于Malone和McCulloh,《Stars of Country Music》,86-94(Kincaid引言),以及Wolfe,“Take Me Back to Renfro Valley”,12(Niles);Horstman,《Sing Your Heart Out, Country Boy》,119以及《Ballad of a Mountain Man—The Story of Bascom Lamar Lunsford》(Lunsford);Wolfe,“Take Me Back”,9-10(Thomas)。关于1930年代的民间音乐运动,见Whisnant,《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n American Region》,184-86及第3章各处,Wolfe,“Take Me Back”,9-12,以及Denisoff,《Great Day Coming: Folk Music and the American Left》。
[37]. 未注明日期和收件人的打字稿,署名”Art Satherly”,ASP。另见”Hill Billy Info”,《Music Business》(1946年9月),20,ASP;Malone,《Country Music》,129(“民歌”);Horstman,《Sing Your Heart Out》,171(Billy Hill);Grundy,“We Always Tried”,1604。
[38]. Daniel,“George Daniell’s Hill Billies”,58(“我们是……乡巴佬”,“长发”);Wiggins,《Fiddlin’》,xv(“Moonshine Kate” Carson引言);Lightfoot,“Belle of the Barn Dance: Reminiscing with Lulu Belle Wiseman Stamey”,9。
[39]. Bronner,《Old-Time Music Makers》,53-54,64-66。
[40]. 同上,55;Fields和Fields,《From the Bowery to Broadway—Lew Fields and the Roots of American Popular Theater》。
[41]. Bronner,《Old-Time Music Makers》,55,88。由于乐队来自纽约州工业城镇霍内尔,而该镇自1915年以来就不再叫霍内尔斯维尔了,因此自称霍内尔斯维尔乡巴佬是一个内部玩笑,类似于他们的乡巴佬舞台形象——但这也唤起了对更简单的乡村过去的回忆。见同上,85-86。关于乡村音乐中乡村家庭观念模糊性的更广泛讨论,见Malone,《Don’t Get Above Your Raisin’》,第3章。
[42]. 关于牛仔形象的发展,见Malone,《Singing Cowboys》,89-95,Peterson,《Creating》,第6章,Green,“The Singing Cowboy: An American Dream”,以及Oermann和Bufwack,“Patsy Monta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wgirl Image”。
[43]. Malone,《Country Music》,第5章,以及《Singing Cowboys》,91,99-100。
[44]. 关于新政在南部山区的努力,见Williams,《Appalachia: A History》,291-306,以及Batteau,《Invention of Appalachia》,138-43;总统致函附《The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South》(1938),重新发表于Carlton和Coclanis编,《Confronting Southern Povert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South with Related Documents》,42。Douglas B. Green,“Gene Autry”,载于Malone和McCulloh,《Stars of Country Music》,154。
[45]. Malone,《Singing Cowboys》,94;《WLS Family Album》,1930-1940,JEMFC;Wolfe,“Take Me Back”,23。
[46]. Malone,《乡村音乐》,161页。奥丹尼尔将其乐队音乐的受欢迎程度和自己的民粹主义言论转化为高级民选职位;1938年至1942年担任两届德克萨斯州州长,并于1941年(特别选举)和1942年当选美国参议员;Pugh,“乡村音乐”,33页;Betty June Glasiner的信,《Hillbilly & Western Hoedown》第1期(1953年12月):5页,JEMFC。歌迷杂志包括《Stand By》(WLS,芝加哥,1936-1938年)、《Rural Radio》(WSM,纳什维尔,1938-1939年)、《Mountain Broadcast and Prairie Recorder》(Rialto and Dixie Music,纽约,1939-1947年)以及《National Hillbilly News》(西弗吉尼亚州,1940-1952年)。Bill Malone,小册子注释,3页,《史密森尼经典乡村音乐合集》(Smithsonian P8-15640,1981年),以及与作者的对话,1996年3月3日。
[47]. “鲍勃·米勒著名的乡村心弦”(纽约:Bob Miller, Inc.,1934年)(FL 0060),MF。
[48]. 关于战争年代的乡村音乐,参见Malone,《乡村音乐》,第6章;Zolotow,“乡村音乐热潮”,Eddy,“乡村音乐天堂”,Antrim,“呼喊与欢呼歌剧”,以及Davidson,“那些乡村曲调中有金子”;Antrim,85页(“他们发现……酒”)。
[49]. Ronnie Pugh采访Ernest Tubb的转录副本,作者持有(Bond和Tubb的引语)。感谢Pugh先生分享这些材料;“罗伊·阿库夫不是乡村歌手”,《哥伦布(乔治亚州)纪事报》,1950年7月20日,ASP;Arthur Satherly未注明地址和日期的手写信(“Hill Billy Satherly”),ASP;Arthur Satherly致Thurston Mome先生[?],1969年7月13日(“垃圾”),ASP;前述未注明地址的Satherly信件(“乡村民众”)。
[50]. 从1930年代末到1960年代,音乐家、推广人、记者和观众尝试了各种替代标签,包括”西部”、“民谣”、“美国民谣”和”乡村与西部”。《公告牌》杂志的唱片评论专栏不仅反映了这种术语冲突,还反映了从将这类作品视为音乐残羹剩饭到承认其为需要独立版面的合法独立类别的更广泛转变。乡村音乐首次出现在该杂志的评论专栏中,标题为”本月乡村和外国唱片热门”(1941年12月),一周内被”西部和种族”取代。在1940年代,该专栏多次更名,从”美国民谣唱片——牛仔歌曲、乡村曲调、灵歌等”(1942年3月)到”美国民谣曲调——牛仔和乡村曲调及歌手”(1944年5月)到”民谣(乡村与西部)唱片版块——民谣人才与曲调”(1948年6月)到”最常播放的点唱机(乡村与西部)唱片”(1949年6月)。直到1962年,该榜单才采用现名,再次从”热门乡村与西部单曲”更名为”热门乡村单曲”。参见《公告牌》1940-1949年;Pugh,“乡村音乐”,35-36、38页;关于Homer和Jethro,参见Malone,《别自视过高》,181页。
[51]. 我在JEMFC查阅的使用该术语的国际歌迷出版物可能不完整的合集包括:《乡村音乐之友——乡村与牛仔音乐杂志》(日文出版,1972-1974年);《乡村音乐狂欢》(荷兰:Dutch Stickbuddy Club,1962-1963年);以及《乡村民谣唱片杂志》(英格兰埃塞克斯和肯特:乡村民谣唱片收藏家俱乐部,1954-1957年)。
[1]. 关于漫画中的南方人物和场景,参见Blackbeard,“那些乡巴佬:阿布纳、利未提库斯、斯纳菲——(惊叹!)看看阿尔·卡普释放了什么”,3、5页,Inge,“萨特、斯嘉丽及其漫画表亲:漫画中的南方”,154页,以及Inge,“漫画”,914-15页。
[2]. 另见Batteau《阿巴拉契亚的发明》127-32页和Williamson《乡巴佬之地》40-42页对韦伯作品的分析。
[3]. 韦伯的引语来自Harry Neigher的文章,《布里奇波特(康涅狄格州)先驱报》,日期不详,页码不详,EC。韦伯还为《生活》和《科利尔》杂志创作漫画,他的角色的连载漫画《山地男孩》在1930年代连载了数年,并出版了两本漫画集,《绕山而来》(1938年)和《让他们飞翔》(1942年)。参见Falk编,《美国艺术名人录》,664页,Horn编,《世界漫画百科全书》,第1卷,402-3页;第2卷,57页,Harrison H. Smith,“‘山地男孩’为艺术家赢得声誉”和”保罗·韦伯欢乐的’山地男孩’”,均来自《时代领袖、晚间新闻、记录》(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分别为1977年6月11日和1977年6月18日,页码不详,EC。感谢Stephen Goddard与我分享这些文章。
[4]. 参见Breazeale,“尽管有女性:《时尚先生》杂志与男性消费者的建构”,1、11-17页,Merrill,《Esky:时尚先生的早期岁月》,13-30页,以及Gingrich,《只有人:时尚先生的早期——个人史,1928-1958年》,102-3页。发行量统计来自Merrill,46、51页。
[5]. 《时尚先生》,1935年8月,27页;1940年5月,64页;1936年5月,60页;1936年4月,37页,1936年10月,38页,以及1938年2月,38页。
[6]. 《时尚先生》,1943年1月,52页;1937年8月,38页;1936年2月,92页。
[7]. Tindall,“蒙昧的南方:现代形象的起源”,284页。关于1920年代现代性与传统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参见Archdeacon,《成为美国人——族裔史》,第5-6章,Coben,《反抗维多利亚主义——1920年代文化变革的推动力》,以及Dumenil,《现代气质——1920年代的美国文化与社会》。关于1930年代,请参阅Pells,《激进愿景与美国梦——大萧条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思想》,以及Susman,“三十年代的文化”,150-83页。
[8]. Mencken,“The Sahara of the Bozart”,143,147;Mencken,“In Memoriam: W. J. B.”,65。关于”The Sahara of the Bozart”文化意义的详细分析,见Hobson,Serpent in Eden: H. L. Mencken and the South,尤其是11-32页。关于Mencken攻击南方山民的其他例子,见”The Hills of Zion”、“the Scopes Trial”和”Inquisition”。
[9]. Sherman和Henry,Hollow Folk,1,27(页码参考重印版);另见Batteau,Invention,96-97。Wolfe的Look Homeward Angel(1929)、Faulkner的As I Lay Dying(1930)以及Caldwell的Tobacco Road(1932)和God’s Little Acre(1933)只是Hollow Folk出版前后五年间众多以贫穷白人为主角的小说中最著名的几部。见McIlwaine,The Southern Poor-White—From Lubberland to Tobacco Road,以及Cook,From Tobacco Road to Route 66—The Southern Poor White in Fiction。
[10]. Esquire,1943年6月,55,以及1944年1月,107;Manne,“Mental Deficiency in a Closely Inbred Mountain Clan”,270,279。
[11]. Edwin Ehrhardt致编辑的信,Esquire,1939年12月,6。
[12]. 1936年至1944年间,Webb的漫画有十次出现在Stuart作品的旁边。Stuart在这些年间在该杂志发表了三十六篇作品,其职业生涯中共有七十九篇被Esquire选用。见Gingrich,Nothing but People,307。
[13]. Williamson,Hillbillyland,42。
[14]. A. L. Blinder致M. Davis,1948年4月7日,EC(“极其幸运”);Alfred Smart致Daniel Doran,1948年11月23日,EC(“已经过时了”)。感谢Stephen Goddard向我提供这些材料。关于战后Esquire的概述,见Howd,“Esquire”。
[15]. DeBeck在1922年推出Spark Plug,引发了漫画角色最早的成功大规模营销活动之一,甚至催生了Billy Rose的一首热门歌曲”Barney Google”,其令人难忘的副歌是”with your goo-goo-googly eyes”。DeBeck使许多流行语风靡全国,包括”heebie jeebies”(神经紧张)、“horse feathers”(胡说八道)和”sweet mama”(甜心妈妈),这一趋势在该连环画的后期版本中延续。关于DeBeck个人和艺术背景的最佳资料来源是Walker,Barney Google and Snuffy Smith—75 Years of an American Legend。另见Inge,“Sut Lovingood and Snuffy Smith”,69-76。
[16]. Barney Google,1934年6月14日,15;Snuffy的取代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环画的标题都从Barney Google改为Barney Google and Snuffy Smith(1938年10月24日),再改为Snuffy Smith(1942年5月11日)。目前,该连环画名为Barney Google and Snuffy Smith,尽管前一个角色几乎从不出现。(除非另有说明,本连环画文字和画作的所有引用均来自1934年6月1日至1946年2月1日期间每周六天在Capital Times(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上发表的各期。)
[17]. Inge,“Sut Lovingood”,74-75。
[18]. Barney Google,1934年6月17日,无页码;“Beyond His Knowledge!”1934年6月21日,17;“Catching Up with History!”1934年7月23日,11。
[19]. 在1940年的一次采访中,DeBeck将他的角色描述为”一个私酿酒、偷马偷鸡的文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补充说,“你就是忍不住喜欢这个小家伙。”见”Barney Google’s Birthday: He’s 21 Now but Sadly Eclipsed by the Toughie Snuffy Smith”;Barney Google,“An Unpleasant Encounter!”1934年11月28日,13。
[20]. Barney Google,1944年9月1日,8。我在1934年至1945年间只发现一个Lowizie公开反抗Snuffy的风流韵事和专制的例子(1940年4月25日,24)。
[21]. Barney Google,“Snuffy Loses Count!”1935年11月26日,17;“Under His Own Steam!”1935年12月16日,13;“Too Close for Comfort”,1938年4月12日,15;Thompson,“America’s Day-Dream”,4。
[22]. DeBeck最著名的非裔美国人角色是Sunshine,Barney Google矮小、头脑简单、永远忠诚的仆人兼骑师,他最喜欢说的话是”You sho am a smaht man, mistah Google。“见Walker,Barney Google and Snuffy Smith,86-87。关于非裔美国人刻板印象在连环画以及美国和西方流行文化中的性质和作用的更全面讨论,见Jones,”From ‘Under Cork’ to Overcoming: Black Images in the Comics”,Lott,Love and Theft—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以及Pieterse,White on Black—Images of Africa and Blacks in Western Popular Culture。
[23]. Walter Lippmann,A Preface to Morals(纽约,1929),19-20,引自Dorman,Revolt of the Provinces: The Region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 1920–1945,24。Dorman的书提供了整个运动的最佳概述。关于地方独特民间文化倡导者与统一国家文化倡导者之间竞争方式的分析,见Kammen,Mystic Chords of Memory,第13章。
[24]. Percy MacKaye,“Untamed America: A Comment on a Sojourn in the Kentucky Mountains”,Survey 51(1924年1月1日):327;引自Shapiro,Appalachia on Our Mind—The Southern Mountains and Mountaineers in the American Consciousness, 1870–1920,261。MacKaye对他基于山区民众创作的戏剧成为”精神野性自然的保护”以及”未受污染的思想遗产和未被驯服的想象力”的潜力更加诗意地赞美,见”Poetic Drama in Kentucky’s Mountains”,29。
[25]. 其他区域性联邦项目——包括建立两个国家公园(大烟山国家公园[1934年]和谢南多厄国家公园[1936年])以及蓝岭公路的建设(始于1935年)——也使该地区及其居民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关于1930年代南阿巴拉契亚与全国媒体及联邦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参见Batteau,Invention,92-94、116-26、133-43页,以及Perdue和Martin-Perdue,“Appalachian Fables and Facts: A Case Study of the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Removals”。
[26]. 1920年至1930年间发表了79篇文章,1930年至二战结束又发表了114篇。所引用的杂志文章总数包括这些年份The Reader’s Guide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中所有相关文章,涵盖56种不同出版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山区居民非虚构作品包括Sheppard的Cabins in the Laurel、Wilson的Backwoods America,以及Randolph的The Ozarks: An American Survival of Primitive Society和Ozark Mountain Folks。此外,两部广为阅读的山区民间艺术著作是Goodrich的Mountain Homespun和Eaton的Handicrafts of the Southern Highlands。四个主要节日分别是Bascom Lamar Lunsford的山地舞蹈与民俗节(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Jean Thomas的美国民歌节(肯塔基州阿什兰)、Sarah Gertrude Knott的全国民俗节(多地举办)以及Annabel Morris Buchanan的白顶民俗节(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参见Whisnant,“Finding the Wa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Mountain Dance Folk Festival and Bascom Lamar Lunsford’s Work as a Citizen”以及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n American Region第3章,以及Wolfe,“Take Me Back to Renfro Valley”,9-12页。
[27]. 关于Doris Ulmann的创作实践,参见她的长期旅行伙伴John Jacob Niles的回忆录,收录于Niles和Williams,The Appalachian Photographs of Doris Ulmann,以及Watkins,“Merchandising the Mountaineer—Photography,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Cabins in the Laurel”,235页;Watkins,217页(标注错误的照片)。
[28]. Inge,“Sut Lovingood”,75页;“Barney Google’s Birthday”,60页。
[29]. Barney Google,“A Suitor That Doesn’t Suit”,1934年6月29日,15页。
[30]. Barney Google,“A Feud That Pays”,1936年8月16日;“Maintaining a Reputation”,1938年4月27日,16页。
[31]. Barney Google,“Surprise Packages!”,1934年8月8日,13页;“Out of the Woods!”,1934年9月9日。
[32]. Scheinfeld,“A Portrait in Zowie!”,142-43页(“需要淡化处理”);Lasswell,“Billy, Barney, Snuffy & Me”,17、21页。
[33]. Inge,“Al Capp’s South: Appalachian Culture in Li’l Abner”,5页,以及McCoy,“The Art and Politics of Al Capp”,2页(作者收藏)(发行量估计);Kahn,“Ooff!! (Sob!) Eep!! (Gulp!) Zowie—I”,54页(年收入估计)。Capp进军其他媒体的尝试成败参半。虽然百老汇剧目Li’l Abner于1956年首演并大获成功,但改编的音乐电影(派拉蒙,1959年)反响平平,而同名前作(Astor Pictures,1940年)则在评论界和观众中双双遇冷。同样,1968年在阿肯色州哈里森郊外开业的主题公园Dogpatch USA到1970年代末已经举步维艰,并于1993年倒闭。参见Price和Turner,“Abner Goes Hollywood; Gets Lost in Shuffle”,Brown,“The Road to Hokum: Dogpatch, USA”,以及Russ,“Dogpatch, U.S.A.”。关于Capp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参见Steinbeck为Al Capp的The World of Li’l Abner所写的”Introduction”,6页,以及McCoy,“Art and Politics of Al Capp”,3-4页。
[34]. 关于Capp和Li’l Abner的更广泛分析,参见Berger,Li’l Abner—A Study in American Satire,以及Arnold,“Al, Abner, and Appalachia”。
[35]. 关于Capp的童年,参见Schreiner,“The Storyteller”,7-8页,以及Capp,My Well-Balanced Life on a Wooden Leg: Memoirs。关于Capp的南方之旅,参见Schreiner,“Storyteller”,8页;Inge,“Al Capp’s South”,6页。Capp为United Features 1937年新闻手册提供了一幅宣传素描(收录于LAD: 1,6页),展示了他据称与一位山区男孩的会面,而这位男孩正是Li’l Abner的原型。然而,他的兄弟Elliott Caplin称Capp后来将此解释为前期调研之旅不过是他”神话”的又一例证,并认为就像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学家一样,“Alfred成了他自己的荷马”。参见Caplin,Al Capp Remembered,61-63页。
[36]. 作为一名狂热的电影观众,年轻的Capp很可能观看了1920年至1934年间上映的数十部以南方山区为背景的电影。至于文学作品,Capp不仅阅读了Fox的小说,还阅读了旧期的Harper’s Monthly,其中一些可能包含Murfree和Fox的短篇小说以及E. W. Kemble的山民插图。参见Caplin,Al Capp Remembered,7、30-31页,以及Inge,“Al Capp’s South”,8-10页;Halberstadt,“Introduction”,4页(杂耍表演)。虽然她不记得剧团的名字,但可能是”the Weaver Brothers and Elviry”,当时最著名的”乡巴佬”杂耍演员。参见McNeil,“Special issue on the Weaver Brothers and Elviry”。
[37]. Schreiner,“Storyteller”,12页;Editor and Publisher,1935年8月17日,23页。
[38]. “The Funny Papers”,45、49页;Berchtold,“Men of Comics”,35页。稍早的一篇文章报道称,在大都市报纸读者中,68%的男性、72%的女性和99%的儿童阅读”最好的漫画”[原文斜体]。参见Tarcher,“The Serious Side of the Comic-Strip”,4页。
[39]. Editor and Publisher,1935年4月27日,1页[原文斜体];关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幽默,参见Levine,“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以及Linneman,“Will Roger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40]. Capp, “Innocents in Peril,” 5; Kahn, “Ooff!! Zowie-I,” 57 (“我不想……”); Kahn, “Ooff!! (Sob!) Eep!! (Gulp!) Zowie-II,” 48。
[41]. 辛迪加避免争议话题的政策,最好的例证是1949年King Features Syndicate出版的《著名艺术家和作家目录》中规定的”漫画准则”:“不要血腥,不要酷刑,不要恐怖,不要涉及宗教、政治和种族等争议话题。最重要的是品味问题。漫画必须干净。不要有暗示性的姿势,不要有不雅的服装。”尽管Capp反复违反了大部分规定,但他确实避开了(有组织的)宗教和种族话题。关于”漫画准则”,参见Reitberger和Fuchs,《漫画——大众媒介剖析》,146。
[42]. 参见Jacobson,《不同颜色的白人身份》,Dower,《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以及Curtis,《猿猴与天使:维多利亚时代漫画中的爱尔兰人》。
[43]. 《小阿布纳》,“有人要吗”,标注日期1935年7月5日;重印于《LAD: 1》,53;“暴动召集”,标注日期1938年7月20日;重印于《LAD: 4》,103。
[44]. 关于这一系列的解读,参见Schreiner,“1940:在路上”,14,Arnold,“解读阿布纳——Al Capp的《小阿布纳》,1940-1955”,422,以及McCoy,“Al Capp的艺术与政治”,8-13。
[45]. 《小阿布纳》,“旅程终点!”未标注日期;重印于《LAD: 6》,60;以及”狗窝镇的贵妇人”,标注日期1938年11月4日;重印于《LAD: 4》,149。
[46]. 《小阿布纳》,“大学,我们来了!”标注日期1936年10月15日;重印于《LAD: 2》,135;“阿比贾——你说得对!”标注日期1936年10月17日;重印于《LAD: 2》,136。
[47]. 重印于Schreiner,“1938:肥皂与闹剧”,6。Scraggs一家与1921年热门电影《可敬的大卫》中恐吓和平小镇的山民恶棍三人组Hatburns有着惊人的相似。年轻的Alfred Caplin很可能看过原版电影或其不太成功的1930年翻拍版;Semple,“肯塔基山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人文地理学研究”。
[48]. 关于二战期间和冷战初期《小阿布纳》的深刻分析,参见Arnold,“解读阿布纳”。
[49]. 《时尚先生》,1943年5月,123;Webb,“乡巴佬的大争斗”。比较三位艺术家对美国参与二战的不同反应很有意思。在Webb的漫画中,战争动员在他的乡巴佬周围进行,有时甚至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军队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演习;在茅房上投弹;没收他们的私酿酒作为爆炸物;但Luke和他的兄弟们始终无动于衷,懒得连转身看看驶过的坦克都不愿意。相比之下,DeBeck让Snuffy Smith在1940年10月参军,他穿军装的冒险成为连环画的中心主题。1943年Lasswell接手漫画后,让Snuffy(和Barney Google)随美军前往加勒比海、北非和南太平洋。Snuffy甚至参与了与日本士兵的(相当滑稽的)肉搏战。与两位同行不同,Capp几乎完全排除了漫画中对战争的任何提及,小阿布纳和其他狗窝镇居民都没有参军。在1942年7月4日那期给读者的公开信中,Capp解释说,他决定排除直接的战争内容是为了让狗窝镇保持”一个和平、快乐、自由的世界……在那里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聪明或愚蠢。“然而,《小阿布纳》的世界既不和平也不快乐,随着战争的进行变得越来越虐待狂、暴力和充满性暗示。关于《Snuffy Smith》与战争,参见Walker,《Barney Google和Snuffy Smith》,124,以及Lasswell,”Billy、Barney、Snuffy和我”,20。关于Capp与战争,参见Arnold,“解读阿布纳”,423-28,以及Horn,“战时《小阿布纳》:夜里不叫的狗之谜”。
[50]. 广告样本参见《时尚先生》,1942年4月,139,1942年6月,123(寄给军人的漫画书),以及1943年5月,123。《肯塔基月光》(1938)的制片人特别提到”典型的《时尚先生》式乡巴佬”作为主角的原型。参见Folder 1781.8,“与Zanuk先生关于《肯塔基月光》的会议(临时剧本,第一部分——12月4日,第二部分——12月8日)”,1937年12月8日,2,Box FX-PRS-290,FXC。
[51]. Williamson,《乡巴佬之地》,29。正如Williamson解释的,“Yoseff”作为对”yourself”的刻意变形,是”一种巧妙的镜像”,表明这些来自山区的中产阶级学生”知道在更大的权力结构中他们就是乡巴佬”。参见他的讨论,29-32。
[52]. 关于Sadie Hawkins Day的起源,参见Schreiner,“1937:Sadie的首次奔跑”。关于其受欢迎程度的例子,参见”在Sadie Hawkins Day,201所大学的女孩追男孩”,以及”小阿布纳的疯狂Capp”,60。
[53]. John Lair致Phil Bottfeld,1951年1月30日,1,Folder 5,Box 17,JLP;Arnow,《玩偶制造者》,501。
[54]. Randolph和Wilson,《深入山谷——奥扎克民间语言集锦》,252;Odum,《美国南部地区》,467;Arnow,《玩偶制造者》,147;Roberts,“别叫我乡巴佬”。
[55]. Randolph,“奥扎克选集——导言”;Randolph,《关于乡巴佬的趣事》;Gish,“是的,我是乡巴佬”,Harmon,《乡巴佬民谣》,无页码。
[56]. Morris,“好老乡巴佬……”,188-89。
[1]. 我从杰里·威廉姆森权威的《南方山民电影目录》中获益良多,非常感谢他愿意与我分享他广泛的研究档案和电影资料库。下文中我用[JW]标注来自他研究档案的资料来源。“Souls Aflame”,《Variety》,1928年7月18日,第15页[JW];“Howdy Folks剧本”,文件夹356.5,盒FX-PRS,811,FXC(《Thunder Mountain》);“‘Mountain Madness’,八月上映,展现私酒贩子”,《MPW》,1920年8月21日,1052[JW];C. S. Sewell,“‘The Wives of the Prophet’——Lee-Bradford”,《MPW》,1926年1月9日,137[JW]。
[2]. 《MPW》,1919年12月20日,1008,引自威廉姆森《Hillbillyland》,295(《The Feud》影评);各年代上映电影数量数据来自威廉姆森的电影目录,但不包括他列出的非虚构教育片以及关于煤矿开采和历史题材的影片。
[3]. 史蒂夫·法拉尔评论,奥菲姆剧院(伊利诺伊州哈里斯堡),《MPW》,1922年12月23日,768(“毫无疑问……”)[JW];《Photoplay》民意调查引自《Hillbillyland》,177-78。关于巴塞尔梅斯作为象征性”妈宝男”通过暴力获得救赎的角色分析,见威廉姆森《Hillbillyland》,177-89。
[4]. “巴塞尔梅斯深入弗吉尼亚荒野”,来源不明(标注”芝加哥”),8月28日,[1921],剪贴簿4,RBC(前三处引文);“迪克在山民与私酒之地的冒险”,《Motion Picture Post》,1921年8月,剪贴簿4,第1、3页,RBC(接下来三处引文);“发现真正的本土血统”,《巴尔的摩太阳报》,1921年9月9日,剪贴簿4,第43页,RBC(“导致……”);“无标题”,《路易斯维尔先驱报》,日期和页码不详,剪贴簿5,第73页,RBC。
[5]. “理查德·巴塞尔梅斯以《Tol’able David》首次担纲主演大获成功”,[《Movietime》?]《Review》,1922年1月7日,剪贴簿4,第87页,RBC;海伍德·布朗,“可怜的歌利亚!”《Image》,1922年2月11日,剪贴簿4,RBC。
[6]. 关于第一部以hillbilly(乡巴佬)命名的电影的讨论,见第64-65页。导演约翰·福特于1918年制作了一部最初名为《Hill Billy》的标准西部片,但该片要么从未上映,要么改了名字,可能改为《The Scarlet Drop》。见比尔·伍顿致阿奇·格林的信,1963年9月15日,文件夹:约翰·福特,盒3,AGP。
[7]. “The Hill Billy”,《Photoplay》,1924年6月,第65页,PF;杰里·威廉姆森在1926年喜剧片《Rainbow Riley》中发现了类似的”来自穷乡僻壤的瘦高个”。见《Hillbillyland》,38-39。
[8]. “Sun-Up,露露·沃尔默著,贝拉·塞克利口述,1925年2月12日”,盖章”1514——保险库副本”,第1页,文件夹:“Sun-Up/1924”,MGMC(剧情梗概);“Sun-Up/连续剧本”,日期”2月24日”,盖章”1514”,第1页,文件夹:Sun-Up/1924,MGMC;“最终字幕列表”,1925年8月5日,第2页,Sun-Up/1924,MGMC(‘Hill Billies’);“Sun-Up”,署名”Fred.”[《Variety》?],1925年8月19日,文件夹:“Sun-Up/Metro-Goldwyn/1925”,PF。
[9]. 《Stark Love》收藏于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馆。感谢杰里·威廉姆森允许我观看他收藏的这部影片副本,并与我分享他关于该片制作和反响的研究档案。关于这部影片的偶然重新发现,见布朗洛为”好莱坞在山间——《Stark Love》的拍摄”所写的引言,第171页,这是卡尔·布朗未出版手稿”派拉蒙故事”的首次发表。
[10]. 同上,171;布朗,“好莱坞在山间”,177(弗曼的影响)和184-92、206、216-17(凯普哈特的影响)。本节内容多处得益于威廉姆森在《Hillbillyland》190-207页中对该片文化政治的分析。
[11]. 《Stark Love》(1927年,派拉蒙名人拉斯基制片公司);布朗,“好莱坞在山间”,174。
[12]. 布朗,“好莱坞在山间”,189(“我想展示……漫画式形象”)(原文斜体);同上,179、182-84、187。另见威廉姆森《Hillbillyland》,198-99。
[13]. 关于拍摄地点,见布朗,“好莱坞在山间”,194-95,以及威廉姆森《Hillbillyland》,197-98、200;“山民入镜”,《纽约时报》,1926年8月29日,第VII版,第5页[JW](打乱顺序拍摄的”技巧”);“原始山民在家乡角落入镜”,《纽约时报》,1927年2月20日,第VII版,第6页[JW](山民”懒惰”;“像孩子一样”;“从未见过火车”)。
[14]. “原始山民”,6[JW](“影像化”);保罗·汤普森,无标题无日期,《Motion Picture News》,文件夹:Stark Love/Paramount/1927,PF;布朗洛,引言,171。
[15]. 《Sun-Up》剧本,日期1925年2月11日,文件夹:Sun-Up/1924/MGM,MGMC。
[16]. 《Our Hospitality》(1923年,米高梅影业/巴斯特·基顿制片公司)及该片剧情梗概见韦德和刘易斯《巴斯特·基顿电影生涯》,50-52;劳伦斯·里德,“标题”,《Motion Picture News》,1923年11月24日,第2483页,档案:Our Hospitality/Metro/1923,PF。
[17]. 早期由著名喜剧组合主演的乡巴佬题材电影包括:《The Feud》(1926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由范·比伯主演;《The Big Killing》(1928年,派拉蒙)由华莱士·比里和雷蒙德·哈顿主演;《Noisy Neighbors》(1929年,百代)由奎兰家族主演;《Them Thar Hills》(1934年,米高梅)由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迪主演。
[18]. 《伦敦纪事报》,1935年3月9日,文件夹:Kentucky Kernels——出版物和评论——4,GSC(“类似于”);估算剧本,日期1934年7月24日,第31页,文件夹:剧情梗概,Kentucky Kernels,盒RKO-S-338,RKO,以及文件夹:Kentucky Kernels,剧本1,GSC。乔治·史蒂文斯是该片导演。
[19]. 关于里兹兄弟的传记概述及影片目录,参见Parish和Leonard编辑的《The Funsters》第528-39页中的”The Ritz Brothers”;M. M. Musselman和Jack Lait, Jr.,“Kentucky Moonshine—大纲梗概”(附1937年9月25日备忘录),文件夹11A6.2.10,档案:Kentucky Moonshine,箱号FX-PRS-290(以下简称KM),FXC(“典型的懒惰”);《Kentucky Moonshine》(1938);文件夹1781.8,“Moonshine over Kentucky与Zanuk先生会议记录(关于临时剧本,第一部分—12月4日,第二部分—12月8日),1937年12月8日,第8页,KM,FXC。据我所知,Webb并未为《Kentucky Moonshine》制作海报,但他确实为《Comin’ round the Mountain》(1940,派拉蒙)制作了广告和片头字幕。
[20]. 围绕真正山民与假扮或被误认为当地人的城市表演者之间混淆的情节,至少可以追溯到《Where Broadway Meets the Mountains》(1912,American);文件夹1781.5,“Moonshine over Kentucky,1937年11月23日打字材料”,第33页,KM,FXC(“该死的”);文件夹1781.15,“Kentucky Moonshine,1938年1月24日,最终拍摄版”,第104页,KM,FXC(“童养媳”);《Kentucky Moonshine》,剧情概要,1938年4月12日,MPAA(“来自Coma的懒人”)。
[21]. 档案:Kentucky Moonshine/20世纪福克斯/1938,PCA(妇女团体的反应);“Kentucky Moonshine”,《时代》(日期不详)和”Kentucky Moonshine”,《综艺》,1938年4月30日(预映),均见于档案:Kentucky Moonshine/20世纪福克斯/1938,PCA。典型的PCA”问题性”族裔刻画检查清单见于档案:Arkansas Traveler/派拉蒙/1938,PCA。
[22]. 电影广告文案,缩微胶片:Spitfire/RKO/1934,PF;1941年,派拉蒙还制作了另一部”山地经典”《Shepherd of the Hills》的第三个版本。关于《Sergeant York》,参见Williamson,《Hillbillyland》,第207-24页。
[23]. Hatfield,“Mountain Justice: The Making of a Feminist Icon and a Cultural Scapegoat”。
[24]. “Hill Billy Justice”作为影片标题出现在PCA的Will Hayes于1936年3月11日写给Harry Warner的信中,档案:Mountain Justice/华纳/1936(以下简称MJ),PCA。
[25]. Mountain Justice新闻资料册,第4页,MJ,PF(“狂热主义”);同上,第10页(Mat 402)(“野蛮的百万人”);同上,第12页(“最后的边疆”);同上,第17页(宣传大厅展示)。
[26]. “Hutchinson Barrat Score in Grim Pic”,《好莱坞记者报》,1937年5月6日,MJ,PCA(“邪恶的技巧”);加州商业和职业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评论(“生动的”)和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评论(“赤裸裸的”),均见于MJ,PCA;《综艺》,1937年5月19日;[纽约?]《邮报》,引自”Mountain Justice”,《好莱坞记者报》,1937年6月1日,MJ,PCA;Hatfield,“Mountain Justice”,第39-40、43页。Hatfield指出,制片厂还向Edith Maxwell支付了10,500美元,以换取她对影片的秘密背书,使她不会公开批评这部电影。
[27]. Elmer Davis的声明,众议院听证会,第78届国会第二次会议,1945年国家战争机构拨款法案,1944年4月19日,转载于MacCann,《The People’s Films—A Political History of U.S. Government Motion Pictures》,第138页。关于该影片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电影局的背景信息,参见同上,第118-51页,《Documentary Film Classics—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第35、38页,以及Barsam,《Nonfiction Film—A Critical History》,第216-19页。
[28]. 《Valley of the Tennessee》(美国风景系列,第7号)(1940,战争信息办公室海外分部)。感谢David Whisnant与我分享他收藏的这部影片,以及他对该片意义的见解。我也受到了Batteau在《The Invention of Appalachia》第140-41页中对该片解读的影响。
[29]. 统计数据来自Williamson影片目录。关于1930年代对奥扎克地区的观念和媒体描绘,参见Blevins,《Hill Folks: A History of Arkansas Ozarkers and Their Image》,尤其是第6章。
[30]. 关于这些”乡巴佬”喜剧演员的概述,参见Austin,“The Real Beverly Hillbillies”。关于Bob Burns,参见Lancaster,“Bare Feet and Slow Trains”,第93-94页;关于Goff和Lauck,参见Kesterson,“A Visit with Radio Humorist Chester Lauck (Lum Edwards)”;关于Weavers,参见McNeil编,“Special Issue on the Weaver Brothers and Elviry”;关于Judy Canova,参见Parish和Leonard编辑的《The Funsters》第155-62页中的”Judy Canova”。
[31]. Miller,《B Movies》,第29-31页,以及Flynn和McCarthy,“The Economic Imperative: Why Was the B Movie Necessary?”
[32]. 《Comin’ round the Mountain》剧本,日期为1940年3月15日,档案:Comin’ round the Mountain (1940) (00314),MS(“唯一幸存的”);《综艺》,1940年8月8日,档案:Comin’ round the Mountain/派拉蒙/1940(以下简称CRTM),PCA(“温和、苍白”);“Comin’ round the Mountain”,《综艺》,1940年8月14日,CRTM,PCA(服装投诉);Crowther,“Comin’ round the Mountain”。《Swing Your Lady》还由当时尚不知名的演员Humphrey Bogart主演,他后来称这部电影是他拍过的最差的一部。
[33]. “Mountain Rhythm—时髦的玉米”,《电影先驱报》,1942年12月12日,档案:Mountain Rhythm/共和国/1942,PF。
[34]. 类似的动物主题卡通片包括《I Like Mountain Music》(1933,Max Fleischer)、《When I Yoo Hoo》(1936,华纳兄弟)、《Naughty Neighbors》(1939,华纳兄弟)和《Comin’ round the Mountain》(1940,派拉蒙/Famous)。《A Feud There Was》(1938,华纳兄弟),收录于影碟《The Golden Age of Looney Tunes》(1992,Turner Entertainment Company),第3卷。另参见Frierson,“The Image of the Hillbilly in Warner Bros. Cartoons of the Thirties”。
[35]. 联邦教会妇女理事会,《山地音乐》评论,档案:Mountain Music/Paramount/1937,PF(“荒谬”);《让音乐属于我》(迪士尼,1946);歌词来自”马丁家与科伊家”,Ted Weems和Al Cameron(1936)。感谢Jerry Williamson与我分享歌词副本并允许我观看他收藏的影片。
[36]. Agee,“Films”,517;“Fun without Mickey”,73;“Make Mine Music”,98;Farber,“Make Mine Muzak”,769。
[37]. 这类乡巴佬戏剧的例子包括Albert的《绕山而来(独幕乡巴佬喜剧)》;Braun的《世仇(独幕乡巴佬喜剧)》;以及Oswalt的《乡巴佬闹剧(热闹的独幕乡巴佬喜剧)》。音乐剧《小阿布纳》是漫画乡巴佬形象首次成功的电影改编。早期版本的《小阿布纳》(1940,Astor Pictures)在评论界和票房上都惨遭失败,以至于Capp否认与其有关。Billy DeBeck的主角曾短暂出现在1942年Monogram Pictures的两部低成本喜剧《斯纳菲·史密斯,新兵》和《乡巴佬闪电战》中,但两部影片更多涉及战时间谍情节而非山区背景,且在评论界和观众中反响都不佳。
[38]. MacDonald,《鸡蛋与我》,112-13;同上,114;同上,117。正如Jerry Williamson所指出的,MacDonald书中真正的”乡巴佬”以及她猛烈抨击的主要对象并非凯特尔一家,而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海岸印第安人矮胖、罗圈腿、皮肤黝黑、脸扁平、鼻子宽大、肮脏、疾病缠身、愚昧且狡诈,”她在一个典型例子中写道。“我见他们越多,就越觉得从他们手中夺走那片美丽的土地是多么正确的事。”见同上,210,220,以及Williamson,《乡巴佬之地》,55。
[39]. Liza Wilson和David McClure,“凯特尔大妈和大爷——好莱坞金矿”,《科利尔》1951年12月8日,剪贴簿4,第6页,LGC;Parish和Leonard,“Marjorie Main”,载于《喜剧演员》,447。
[40]. 《发行商》,1951年3月28日,剪贴簿2,LGC。
[41]. Paul Denis,“他不想要奥斯卡奖”,《每日罗盘》,1950年9月11日,剪贴簿5,LGC(“赚钱”);Wilson和McClure,“凯特尔大妈和大爷”,23(平均成本40万美元);同上(800万美元利润);Parish和Leonard,“Marjorie Main”,448(净利润3500万美元);“他会算账”,《时代》,1952年4月28日,96,剪贴簿5,LGC(“没人喜欢”);Denis(“四块好时巧克力”)。
[42]. Wilson和McClure,“凯特尔大妈和大爷”,23(“最卑微的流浪汉”);Al Hine,“百万美元的凯特尔鼓手”,《时尚先生》,1953年5月,89,LGC装订杂志(“也许人们”)。
[43]. 《电影日报》,1953年3月2日,档案:Ma and Pa Kettle on Vacation/Universal/1952,PF。
[44]. “南部高地——特刊”;“我们的南部高地今日成为新闻”;《国家地理》文章包括Simpich的”百万微笑之地”和Borah的”历史悠久的坎伯兰峡口周围的乡亲们”。战后推广欧扎克地区作为旅游胜地的代表性文章包括Strong的”友好的欧扎克”,Bradshaw夫妇的”欧扎克”,Anoe的”没有地方比得上欧扎克”,以及Eddy的”让我们去欧扎克”。关于阿巴拉契亚的当代旅游导向报道,见Lagemann的”你将绕山而来”,Holman的”大烟山——美国最受欢迎的公园”,Blassingame的”烟山假日”,以及Harshaw的”南方顶级风景带”。
[1]. “乡巴佬”,《我的英雄》(NBC,1953),FTA;“乡巴佬秀”,《杰克·本尼节目》(1958年3月20日,CBS),FTA。本尼还在1964年10月30日的节目中使用了乡巴佬小品(明显是对《贝弗利山乡巴佬》大受欢迎的回应)。
[2]. 其他”乡巴佬”剧集包括”乡巴佬神童”,《你永远发不了财》(1957年10月1日,CBS),以及”拥抱那个乡巴佬”,《爱那个吉尔》(1958年3月17日,NBC);“鲍勃变乡巴佬”,《鲍勃·卡明斯秀》(1958年1月28日,NBC)。所有节目均在FTA观看。
[3]. 关于阿巴拉契亚移民总数,见Philliber,“城市阿巴拉契亚人:不为人知、无人注意”,载于Philliber等编,《隐形少数族群:城市阿巴拉契亚人》,2,以及Jones,《被剥夺者——从内战到现在的美国底层阶级》,227;1950年代这场人口外流的规模令人震惊。这十年间,百分之十五的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白人离开了各自的州;在某些依赖煤炭的县,外迁总数几乎达到百分之四十。见Jones,《被剥夺者》,209,212。关于阿巴拉契亚移民,见Jones,第7-8章,《隐形少数族群》,以及James S. Brown和George A. Hillery, Jr.,“大迁徙,1940-1960”,载于Ford编,《南阿巴拉契亚地区——调查报告》,54-78。关于众多传记叙述充实的全面概述,见Berry,《南方移民,北方流亡者》。Gregory,“南方散居与城市被剥夺者:人口普查公共使用微观数据样本的展示”,提供了战后黑人和白人南方人迁移的近期比较。
[4]. 正如Gregory所指出的,与人们普遍认为的这些人持续面临地方性贫困的观念相反,到1970年,迁移到五大湖各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南方出生移民在平均收入和贫困线以下家庭比例方面仅略微落后于其他白人。见Gregory,“南方散居”,119-20;“日报广告要求’不要南方人’”,《密歇根纪事报》,1943年5月1日,第4页,以及George Henderson,“南方白人:一个被忽视的城市问题”,《中等教育杂志》41(1966年3月):11-14,引自Jones,《被剥夺者》,257(工作/餐厅歧视);“60年代的俄克拉荷马人”,31(标签);Clyde B. McCoy和Virginia McCoy Watkins,“阿巴拉契亚移民的刻板印象”,载于《隐形少数族群》,21-23;Dale Nouse,“调查显示底特律人对城市相当满意”,《底特律自由报》,日期不详,1952年,引自Killian,《南方白人》,98。
[5]. Maxwell, “Down from the Hills and into the Slums,” 27; 同上, 28.
[6]. Votaw, “The Hillbillies Invade Chicago,” 64–66.
[7]. 同上, 67; “‘Murder Won’t Out,’ Paper Concludes after Investigation,” Uptown News, 1957年5月21日, 引自 Guy, “The Media, the Police, and Southern White Migrant Identity in Chicago, 1955–1970,” 333; Votaw, “Hillbillies Invade Chicago,” 64. 关于芝加哥和底特律对南方移民反应的更广泛讨论,分别参见 Guy, “The Media,” 和 Hartigan, Jr., Racial Situations, 特别是26–37页。
[8]. William A. Garyls, Harper’s, 1958年4月, 10.
[9]. “Episode #1” (“Californy Here We Come!”), RM, p.1, Box TV-539, Collection 081, TSS.
[10]. “A Mutual Admiration Society”; “The Television Set” (Episode 97), RM, 1959年12月3日, p. 3, Box TV-211, TSS.
[11]. “Episode #1,” p. 24, “The New Car” (Episode 43), Box TV-539, 和 “Money in the Bank” (Episode 145), RM, TSS; “Mutual Admiration,” 7; “The Bank Loan” (Episode 55), RM, p. 34, Box TV-210, TSS.
[12]. “Little Luke’s Education” (Episode 10), RM, 描述见 Eisner 和 Krinsky, Television Comedy Series—An Episode Guide to 153 TV Sitcoms in Syndication, 695; “The Talk of the Town” (Episode 102), RM, Box TV-211, TSS; “This is the Real McCoy,” 23; “Back to West Virginny,” (Episode 147), RM, 1961年5月23日, Box TV-212, TSS.
[13]. “Back to West Virginny” (Episode 147), RM, 1961年5月23日, 和 “Fly Away Home” (Episode 148), RM, 1961年7月20日, pp. 30–32, 均为 Box TV-212, TSS. 另见 Magoc 对后一集的分析,载于 “The Machine in the Wasteland,” 27.
[14]. “This Is the Real McCoy,” 22; Brooks 和 Marsh, The Complete Directory to Prime Time Network and Cable TV Shows, 119.
[15]. Williamson, Hillbillyland: What the Movies Did to the Mountains and What the Mountains Did to the Movies, 57–61, Brooks 和 Marsh, Complete Directory, 1261–64; Graham, Framing the South: Hollywood, Television, and Race during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101.
[16]. “The County Nurse” (Episode 56, 首播于1962年3月19日), AG, TBS; “A Feud is a Feud” (Episode 8, 首播于1960年12月5日), AG, TBS.
[17]. “Mountain Wedding” (Episode 94, 首播于1963年4月29日), AG, TBS. 关于描述性山地音乐与表演性山地音乐的区别,我受益于 Smith 的未发表论文 “‘What It Was Was Real Mountain Music’: The Authentic Treatment of Music in the Andy Griffith Show,” 12, 并感谢 Jerry Williamson 与我分享这篇论文。关于 Darlings 乐队的曲目列表,参见 Harrison 和 Habeeb, Inside Mayberry, 151–52; “Briscoe Declares for Aunt Bee” (Episode 96, 首播于1963年10月28日), AG, TBS.
[18]. “Mountain Wedding”; “Ernest T. Bass Joins the Army” (Episode 99, 首播于1963年10月14日), “My Fair Ernest T. Bass” (Episode 113, 首播于1964年2月3日), “The Education of Ernest T. Bass” (Episode 133, 首播于1964年10月12日), 均为 AG, TBS.
[19]. Brauer,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War on Poverty,” 101; Batteau, The Invention of Appalachia, 150 (第一幕); 关于肯尼迪早期对阿巴拉契亚和贫困问题的关注程度,参见 Brauer, “Kennedy, Johnson,” 101–13, Batteau, Invention, 第8章, Whisnant, Modernizing the Mountaineer: People, Power, and Planning in Appalachia, 93–94; 关于这三本书的影响,参见 Batteau, 153–57, 和 Brauer, 103;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4, 186, 196.
[20]. 关于阿巴拉契亚反贫困战争的失败,参见 Whisnant, Modernizing, 第4–6章, 和 Glen, “The War on Poverty in Appalachia: A Preliminary Report.” 关于这些年媒体对阿巴拉契亚的报道,参见 Batteau, Invention, 第8–9章, 和 Bowler, “‘That Ribbon of Social Neglect’: Appalachia and the Media in 1964.”
[21]. 四位主角之间的确切家庭关系比大多数观众意识到的更为复杂。Elly May 是鳏夫 Jed Clampett 的女儿,Granny(本名 Daisy Moses)是他的岳母。Jethro Bodine 是 Jed 表妹 Pearl 的儿子,这使得 Jethro 和 Elly May 是远房表亲。但为简便起见,他们通常被称为——我也将称他们为——Clampett 一家。
[22]. Cox,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97–101, 作者与 Paul Henning 的电话采访,1997年6月3日,文字记录由作者保存;作者对 Henning 的采访。
[23]. 作者对 Henning 的采访。
[24]. Cox, Beverly Hillbillies, 3. Henning 在他与 Bob McClaster 的采访中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997年9月4日,AAT;McClaster 对 Henning 的采访,AAT。感谢 Andrew Cypiot 为我转录了这次采访。
[25]. Mark Alvey 指出,到1963年,独立电视电影制作公司负责了70%的电视节目。参见 Alvey, “The Independents: Rethinking the Television Studio System,” 146; Lewis, “The Golden Hillbillies,” 33; Cox, Beverly Hillbillies, 4.
[26]. Lewis, 34; 同上 [原文为斜体和大写]。
[27]. 同上。
[28]. 同上, 34; Brooks 和 Marsh, Complete Directory, 1262–65; Cox, Beverly Hillbillies, xvii. 这些记录可追溯到1960年尼尔森建立其现行收视率系统之时;Muggeridge, “Why Those Hillbillies Are Rampant in Britain,” 26.
[29]. “Jethro Goes to School,” BH, DEC; 引自 Hano, “The G.A.P. Love the ‘Hillbillies,’” 30; “Review,” Variety, 1962年10月3日, 35.
[30]. Newton Minow,在全国广播协会第三十九届年会上的演讲,1961年5月9日,转载于 Watson, The Expanding Vista—American Television in the Kennedy Years, 22.
[31]. Gould, “TV: ‘Beverly Hillbillys’ [原文如此],” 63.
[32]. Hano, “G.A.P.,” 30 (“legitimate”); Gould, “TV,” 63 (“heady”); Hano, “G.A.P.,” 30 (“cheerful belief”); Lewis, “Golden Hillbillies,” 30; Davidson, “Fame Arrived in a Gray Wig, Glasses and Army Boots,” 5 (Bob Hope引言); 同上, 5。
[33]. Henning接受McClaster采访, AAT; Seldes,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66, 65。
[34]. Hobson, “The Grandpappy of All Gushers,” 16。
[35]. “The Hillbillies of Beverly Hills,” (试播集), BH, DEC; Lewis, “Golden Hillbillies,” 32; Cox, Beverly Hillbillies, 18。
[36]. 标题来自《纽约时报》, 1962年10月1日, Hano, “G.A.P.,” 120; Cox, Beverly Hillbillies, 194。
[37]. Robert Escarpit,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Ernest Pick译, 第2版 (伦敦, 1971), 91, 引自Levine, “Th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Society: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Audiences,” 1375; Hano, “G.A.P.,” 120; Dern, “‘Viewers Like ’Em, and That’s That,’” 11; Hano, “G.A.P.,” 120。
[38]. 我受益于Farber在其The Age of Great Dreams: America in the 1960s中的分析, 52–54; “The Clampetts Meet Mrs. Drysdale” (第4集), BH, DEC。
[39]. 引自Barnouw, The Image Empire—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 3—from 1953), 205。
[40]. BH, 1962年10月31日播出的一集, 引自Hano, “G.A.P.,” 122。
[41]. 关于Granny与富裕现代性的文化战争, 另见Marc, Demographic Vistas—Televi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第2章, 以及Himmelstein, Television Myth and the American Mind, 146–50。
[42]. “The Clampetts Meet Mrs. Drysdale.”
[43]. Paul Henning,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试播集), 日期为1961年12月7日, Collection 081, Box TV-371, TSS。该台词在节目播出时保持不变。见”The Hillbillies of Beverly Hills,” BH, DEC。
[44]. Hano, “G.A.P.,” 123; Shayon, “Innocent Jeremiah,” 32。
[45]. Shayon, “Innocent Jeremiah,” 32; Himmelstein, Television Myth, 150。另见Marc在Demographic Vistas中的分析, xvi, 54–58, 以及Farber, Age of Great Dreams, 55。
[46]. Harrison和Habeeb, Inside Mayberry, 8 (Idelson引言)。关于Taylor警长与现实中南方警长的概念关系, 见Graham, Framing the South, 154–60。
[47]. “The South Rises Again,” BH, Episode 5000–186, Box TV-61, TSS。
[48]. 关于城市市场的arbitron样本, 见Variety中的每周联合播出数据, 1962年11月至1963年10月。关于尼尔森收视率有效性的评估, 见Mayer, About Television, 第2章。关于非裔美国观众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见Brown, Televi$ion—The Business behind the Box, 60–61。Henning的评论来自McClaster采访, AAT。
[49]. TV Guide, 1964年3月14日和21日; “The Country Slicker”; 1963年收视率前五的节目中有三个是乡村题材节目(如果算上Bonanza则是四个), Henning的节目和Andy Griffith在1965年收视率前二十一名中占据四席。CBS后来在其节目单中增加了乡村音乐综艺节目, 如Hee Haw (1969–1971)和Glen Campbell Goodtime Hour (1969–1972); 所有收视率数据来自Brooks和Marsh, Complete Directory, 1262–63。
[50]. Cox, Beverly Hillbillies, 26–27, 163–68。
[51]. 百事公司于1964年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Hartman Beverage Company收购了该品牌。Collins, “Ya-hooo! A Marketing Coup”; “Abbreviated Mountain Dew Historical Reel, 1966–1996,” 由Batton, Barton, Durstine, and Osborn (BBDO)制作, 录像带; “Kissin’ Lesson” (Spot 2), 广播广告脚本, 1966年Mountain Dew装瓶商目录。我感谢百事北美公司的Tom Bené和Jon Harris慷慨地与我分享这些资料。
[52]. Crist,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53]. 历史学家Susan Douglas敏锐地指出, 尽管这些节目的前提荒诞不经, 但许多以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女性为主角的节目也是对新兴女权运动的回应。见Douglas, Where the Girls Are, 第6章。关于1960年代电视和情景喜剧的总体趋势, 见Bryant, “Situation Comedy of the Sixties: The Evolution of a Popular Genre,” 118–39, Spigel和Curtin编, The Revolution Wasn’t Televised—Sixties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flict, 以及Baughman, The Republic of Mass Culture, 100–107。关于当时的报道, 见Moss, “The New Comedy,” 42–45, 以及Hano, “TV’s Topmost: This Is America?”
[54]. 这些情节与Irene Ryan和Buddy Ebsen的保守观点相吻合, 两人都支持Ronald Reagan 1968年的总统竞选, 并谴责”嬉皮士”是”世界上最大的随波逐流者”, 见Efron, “American Gothic—On Television and Off,” 34。
[55]. “Robin Hood and the Sheriff,” BH, TBS。
[56]. Bryant, “Situation Comedy of the Sixties,” 133, Brooks和Marsh, Complete Directory, 1264–65。
[57]. 观看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儿童如此之多, 以至于R. J. Reynolds公司响应联邦立法——该立法禁止在观众中未成年人占比至少45%的节目中播放烟草广告——于1967年撤回了赞助。见”Untitled,” 《纽约时报》, 1967年5月10日, 60。
[58]. Buddy Ebsen引言见《洛杉矶时报》, 引自”Putting the Clampett on ‘Hilbillies’“; Buttram引言来自Henning采访, AAT, 以及与Stephen Cox的对话; 关于CBS转型的概述, 见Gitlin,”The Turn toward ‘Relevance.’”
[59]. Richardson, Sr., “Junior Cobb of Three Brothers, Ark., Judges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He’s hill folks, himself)”; Dow, “Letter to the Editor.”
[60]. Branscome, “Annihilating the Hillbilly: The Appalachians’ Struggle with America’s Institutions,” 120–21。Mack Morriss引言引自Day, “Pride and Poverty: An Impressionistic View of the Family in the Cumberlands of Appalachia,” 376。
[1]. Gitlin, “The Turn toward ‘Relevance,’” 218–19; Roiphe, “Ma and Pa and John-Boy in Mythic America: The Waltons,” 132。
[2]. Arnow,《The Hills Meet Hollywood—The Now and Then Guide to Selected Feature Films about Appalachia》,8–9;Hart,《James Dickey: The World as a Lie》,513。
[3]. Dickey,《Deliverance》,40;同上,48–49。
[4]. Dickey,《Summer of Deliverance》,98–99。另见Hart,《James Dickey》,250–51。
[5]. Dickey,《Deliverance》,111;同上,112。
[6]. 在该书出版前五个月,Dickey就与华纳兄弟签订了编剧合同。见Hart,《James Dickey》,442。Dickey,《Summer》,163。尽管James Dickey想在电影制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霸道的态度和不断的干预让Boorman和主演们非常恼火,以至于他被相当不客气地赶出了片场。后来他被允许出演当地警长的小角色。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自我吹嘘者,Dickey后来多次虚假声称电影中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他负责的,从表演、导演到音乐创作。见Hart,《James Dickey》,第25、27章,以及Dickey,《Summer》,167–68。
[7]. Dickey,《Summer》,165。关于这部电影作为对城市人和现代性破坏潜力的评论的深思熟虑的讨论,见Williamson,《Hillbillyland》,155–67。
[8]. Dickey,《Deliverance》,60。
[9]. Dickey,《Summer》,170,以及Graham,《Tale a Mixed Blessing for Rabun County》,M4(Redden)。Boorman一直打算后期配音,让Cox和Redden假装演奏乐器,但Redden完全无法模仿指法动作,制片人不得不设计一件特殊的衬衫,让另一个男孩偷偷把手臂穿过袖子来”弹奏”和弦。因此,突出山民愚蠢的决定导致需要隐藏另一个男孩,也排除了小说中并排演奏的场景。见Taylor、Thomas和Brunson,《‘He Shouted Loud, “Hosanna, DELIVERANCE Will Come,”’》,无页码;同上(Webb和孙女);Dickey,《Summer》,170。
[10]. 新闻资料册,《Deliverance》(华纳兄弟,1972),PF;Dickey,《Summer》,180;Hart,《James Dickey》,508。关于Dickey毁灭性的酗酒和离谱的公开行为,见Hart,《James Dickey》,以及Dickey,《Summer》。
[11]. Hart,《James Dickey》,455,512(销售统计);新闻资料册,《Deliverance》(Farber引文);Hart,《James Dickey》,508–11。
[12]. Taylor、Thomas和Brunson,《‘He Shouted Loud,’》,无页码;Dickey,《Summer》,180;Hart,《James Dickey》,514。
[13]. Hart,《James Dickey》,514;Taylor、Thomas和Brunson,《‘He Shouted Loud,’》,无页码。
[14]. Chattooga河上的漂流者数量在1972年(当时有7600人顺流而下)到1973年间增加了两倍,到1989年达到68000人。见Graham,《Tale a Mixed Blessing》,M4。关于”《Deliverance》综合症”,见Taylor、Thomas和Brunson,《‘He Shouted Loud,’》,无页码,以及Williamson,《Hillbillyland》,162–63,290。
[15]. Williamson,《Hillbillyland》,124–31。
[16]. 同上,131–41。
[17]. Huber,《A Short History of Redneck: The Fashioning of a Southern White Masculine Identity》,158–60。
[18]. Carl Rowan,《Hillbilly Jokes Are an Insult》,《San Francisco Examiner》,1976年11月19日,第36页,PTC;Huber,《Short History》,158–59。
[19]. Kahn,《Hillbilly Women》,180;Russell,《Call Me Hillbilly—A True Humorous Account of the Simple Life in the Smokies before the Tourists Came》,以及Lawson,《By Gum, I Made It!—An Ozark Arkie’s Hillbilly Boyhood》。其他例子包括Silcox,《A Hillbilly Marine》,以及Heath,《Hillbilly Homestead》。
[20]. Fisher,《The Grass Roots Speak Back》,203–14,以及Fisher编,《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Traditions of Resistance and Change》;Obermiller,《Paving the Way—Urban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age of Appalachians》,251–66。
[21]. Brooks和Marsh,《The Complete Directory to Prime Time Network and Cable TV Shows》,1267–69,Sackett,《Prime Time Hits—Television’s Most Popular Network Programs》,264–65。
[22]. Joel Achenbach,《Little Rock, Where Spin Meets Homespun》,《Washington Post》,1992年10月2日,C1–2,引自《The Hillbillies at the New Center of Civilization》,《AJ》20(1993年春):259;转载于Cox,《The Beverly Hillbillies》,143(《Saturday Night Live》小品)。
[23]. J. Emilio Flores摄影,《New York Times》,1998年9月15日,A23。
[24]. 感谢Paul Boyer让我注意到这幅漫画。
[25]. 《Dwight Yoakam Says He Hasn’t Changed, Country Music Has》,Scripps-Howard新闻社,1993年12月9日,CMF;Pam Lambert和Todd Gold,《Dwight Attitude》,《People Magazine》,1993年4月26日,48;以及Jim Lewis,《Marty Stuart Earns Respect as a ‘Hillbilly,’》,《Chicago Sun-Times》,1990年12月3日,CMF。另见Williamson,《Hillbillyland》,8。The Kinks乐队于1971年发行了《Muswell Hillbillies》(RCA),而Knopfler于1990年组建了Notting Hillbillies乐队;BR5-49,《BR5-49》(Arista,1996)。BR5-49这个名字来源于Junior Samples在《Hee Haw》节目中固定小品里他的二手车行的电话号码。
[26]. Harris, History—Grand & Glorious Order of the Hillbilly Degree, “Here’s How It Is in Pikeville,” letter from Howard “Dirty Ear” Stratton to “Hillbilly Bob” (n.d., c. 1983), Williamson, Hillbillyland, 10–12. 我要感谢Jerry Williamson与我分享这些文件;派克县商会出版的宣传卡片,约1995年4月;Hillbilly Days网站 (http://www.hillbillydays.com);“History: Grand & Glorious Order of the Hillbilly Degree,” 网站管理员注释 (http://www.trowel.com/hillbilly99/history.htm) (1999年”氏族”统计数据)。另见Brown, Ghost Dancing on the Cracker Circuit: The Culture of Festivals in the American South, 第3章。有趣的是,派克维尔的节日并非南部山区首次举办此类庆祝乡巴佬(hillbilly)身份和形象的活动。北卡罗来纳州海兰兹的居民——阿什维尔郊外一个时尚社区——在1951年至至少1957年间每年八月举办”海兰兹乡巴佬日”。与派克维尔节日类似,参与者打扮成乡巴佬,参加选美比赛,以及更传统的活动如劈柴、方块舞和民谣演唱。参见Asheville Citizen-Times这些年份的文章。
[27]. “Hillbilly Convention Drawing Criticism,” Cincinnati Enquirer, 1982年10月12日, C1–2, 转载为”Fed Up in Cincinnati,” 载于AJ 10 (1983年春), 225。另见Williamson, Hillbillyland, 13–14。关于”hillbilly”作为包容性标签的使用,参见Hartigan, Jr., “Name Calling: Objectifying ‘Poor Whites’ and ‘White Trash’ in Detroit,” 载于Wray and Newitz编, White Trash—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41–56, 以及Hartigan, Racial Situations: Class Predicaments of Whiteness in Detroit, 第2章。
[28]. http://www.rockabillyhall.com/HillHellcats.html (Hillbilly Hellcats); http://www.squank.net/albums/hh/hhalbm01.htm (Hillbilly Holocaust); http://www.instantharmony.com/HfM/ (Hillbillies from Mars); http://sierrahillbillies.homestead.com/files/Hillbillies_Main.htm (Sierra Hillbillies); www.angelfire.com/hi/MikeLatinHillbillies/ (Mike Hillman and Latin Hillbillies); www.hbhq.com/ (Hillbilly Headquarters); http://home.dti.net/pwilhelm/hh2/ (Hillbilly Hercules); http://www.ebay.com/ (E-bay链接); http://xroads.virginia.edu/~MA97/price/open.htm (“White Tras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Scapegoat”)。所有网站访问于2002年12月4日。
[1]. de Moraes, “Gold in Them Thar ‘Hillbillies’?”
[2]. “Beverly Hillbillies to Become Reality Show”; de Moraes, “Gold in Them Thar.”
[3]. Kinney, “Reality Show Will Perpetuate Hillbilly Stereotype”; Rogers, “Shootin’ for Some Crude”; Dreher, “Minstrel Show”; Pitts, Jr., “Reintarnation! Second ‘Beverly Hillbillies’ as Reality TV Not Funny”; Peyton, “First Beverly Hillbillies Bad Enough: ‘Montani semper Stereotype’ Strikes W. Va. Once Again.”
[4]. Garrigan, “Bubba Goes to Hollywood”; Dreher, “Minstrel Show,” Caldwell, “Hill of Beans—Reality Is Optional.”
[5]. Caldwell, “Hill of Beans—Reality Is Optional”; “Must Hee-Haw TV.”
[6]. Kinney, “Reality Show Will Perpetuate Hillbilly Stereotype”; Rogers, “Shootin’ for Some Crude”; Abramson, “New ‘Hillbillies’ Sure to Take Swipe at South”; 国会议员Hal Rogers(及四十三位同事)致Leslie Moonves的信函,2003年3月12日,农村战略中心网站 <http://www.ruralstrategies.org/campaign/cong.ltr.html>。
档案来源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玛格丽特·赫里克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
传记档案
一般主题档案
电影剧本
制作档案
特别收藏
理查德·巴塞尔梅斯收藏
伦纳德·戈德斯坦收藏
乔治·史蒂文斯收藏
美国电影协会
制作法规管理局案例档案
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加利福尼亚州北好莱坞
美国电视档案馆
安迪·格里菲斯访谈
保罗·亨宁访谈
谢尔顿·伦纳德访谈
亚伦·鲁本访谈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威廉·L·尤里阿巴拉契亚收藏,北卡罗来纳州布恩
垂直档案
山区人民
刻板印象
伯里亚学院,哈钦斯图书馆,肯塔基州伯里亚
特别收藏
约翰·莱尔文献
乡村音乐基金会,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乡村音乐期刊和歌迷杂志收藏
亚瑟·萨瑟利文献
传记文件夹
东田纳西州立大学,阿巴拉契亚档案馆,谢罗德图书馆,田纳西州约翰逊城
托马斯·G·伯顿-安布罗斯·N·曼宁收藏
小查尔斯·R·冈特收藏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戏剧艺术图书馆/特别收藏,大学研究图书馆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收藏
已制作剧本:Kentucky Moonshine; Thunder Mountain
雷电华电影公司收藏
已制作剧本
华纳兄弟收藏
查尔斯·艾萨克斯收藏
电视剧剧本
安迪·格里菲斯秀
贝弗利山人
真正的麦科伊一家
沃尔顿一家
特别收藏部,大学研究图书馆
理查德·威尔逊文献
电影电视档案馆,档案研究与学习中心,鲍威尔图书馆
堪萨斯大学,斯宾塞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州劳伦斯
《时尚先生》收藏
肯塔基大学图书馆,大学档案馆,列克星敦
特藏与档案部
肯塔基明信片收藏
约翰·雅各布·奈尔斯收藏
阿巴拉契亚收藏
密苏里大学/密苏里州历史学会,哥伦比亚
西部历史手稿收藏,埃利斯图书馆
彼得·塔莫尼收藏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南方民俗收藏,威尔逊图书馆
约翰·爱德华兹纪念基金会收藏
音乐活页乐谱
WLS家庭相册,1930-1957
阿奇·格林文献
照片收藏
音乐目录
人物传记文件夹
期刊收藏
南加州大学,洛杉矶
电影电视图书馆,多亨尼纪念图书馆
特藏
二十世纪福克斯收藏
米高梅收藏
新闻资料册
真人电影
《阿肯色法官》:共和国电影公司,1941年。
《棉花地里的小屋》:第一国家电影公司,1932年。
《童养媳》:雷蒙德·弗里德根,1952年。
《翻山越岭》:环球电影公司,1951年。
《激流四勇士》:华纳兄弟,1972年。
《鸡蛋与我》:环球电影公司,1947年。
《肯塔基山丘》:华纳兄弟,1927年。
《在老密苏里》:共和国电影公司,1940年。
《奥扎克的圣女贞德》:共和国电影公司,1942年。
《肯塔基世仇》:比沃格拉夫公司,1905年。
《肯塔基玉米粒》:雷电华电影公司,1934年。
《肯塔基月光》: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1938年。
《凯特尔一家在奥扎克》:环球国际电影公司,1955年。
《小阿布纳》:三合制片公司/派拉蒙,1959年。
《凯特尔夫妇》:环球国际电影公司,1949年。
《凯特尔夫妇进城》:环球国际电影公司,1949年。
《凯特尔夫妇回农场》:环球国际电影公司,1951年。
《为我奏乐》:华特迪士尼工作室,1946年。
《私酿酒世仇》:1919年。
《私酿酒贩》:比沃格拉夫公司,1904年。
《山地正义》:华纳兄弟,1937年。
《山地音乐》:派拉蒙电影公司,1937年。
《他说是谋杀!》:派拉蒙电影公司,1944年。
《我们的待客之道》:大都会公司,1923年。
《税务官和他的女孩》:比沃格拉夫公司,1911年。
《原始之爱》:派拉蒙名人拉斯基制片公司,1927年。
《摇摆你的女士》:华纳兄弟,1937年。
《雷霆之路》:DRM制片公司,1958年。
《烟草路》:二十世纪福克斯,1941年。
《可敬的大卫》:灵感电影公司,1921年。
《孤松小径》:派拉蒙电影公司,1936年。
《田纳西河谷》:美国风景系列,第7号,战时新闻局海外分部,1940年。
《冬日人家》:尼尔森娱乐公司,1989年。
动画短片
《翻山越岭》:派拉蒙,1949年。
《曾有一场世仇》:华纳兄弟,1938年。
《乡巴佬兔子》:华纳兄弟,1950年。
《当我呼唤时》:华纳兄弟,1936年。
音乐短片
“乡巴佬大歌剧”:米诺科制片公司,1941年。
“乡巴佬监狱”:声画发行公司,1942年。
“乡巴佬之恋”:斯基博-教育福克斯,1935年。
“萨迪·霍金斯日”:声画发行公司,1942年。
系列剧
《安迪·格里菲斯秀》:丹尼·托马斯制片公司,1960-1968年。1960-1968年各集:通过特纳广播系统联播观看。
《贝弗利乡巴佬》:菲尔姆韦斯制片公司,1962-1971年。1962-1964年各集:钻石娱乐公司录像带;1965-1970年:通过特纳广播系统联播观看。
单集节目与广告
《激浪历史精选集,1966-1996》。BBDO广告公司。录像带。
《贝弗利乡巴佬》(试播集):1962年9月26日首播;FTA。
《鲍勃·卡明斯秀》。“鲍勃变乡巴佬”;(1958年1月28日),FTA。
《黑猩猩》。“争吵与打斗”;宾·克罗斯比娱乐公司,1959年;FTA。
《杰克·本尼节目》。“乡巴佬秀”;1958年3月20日,CBS;FTA。
______。“乡巴佬小品”;1964年10月30日,NBC;FTA。
《爱那个吉尔》。“拥抱那个乡巴佬”;1958年3月17日,NBC;FTA。
《麦克黑尔海军》。“PT 73号的乡巴佬”;1963年6月6日,ABC;FTA。
《门基乐队》。“乡巴佬蜜月:双管猎枪婚礼”;1967年10月23日;FTA。
《我的英雄》。“乡巴佬”;1953年,NBC,FTA。
《你永远发不了财》。“乡巴佬神童”:1957年10月1日,CBS;FTA。
贝尔,鲍比,《底特律城》。RCA Victor LSP 2776。1963年。
胡希尔热门乐队。“那些乡巴佬现在是山地威廉姆斯了。”Rex 8744 (78A) 卡瓦诺-桑福德-迈塞尔斯(国会图书馆,录音收藏)。
梅肯,戴夫大叔。“乡巴佬布鲁斯。”Vocalion-14904。1925年。
谢伊,多萝西。《多萝西·谢伊演唱》。Columbia CL 6003。1947年。
《史密森尼经典乡村音乐收藏》。Smithsonian P8-15640。1981年。
约卡姆,德怀特。《乡巴佬豪华版》。华纳兄弟唱片。1987年。
《阿巴拉契亚杂志》,1972-1999年。
《公告牌》,1940-1954年。
《(麦迪逊)首府时报》,1934-1950年。
《编辑与出版商》,1934-1945年。
《时尚先生》,1934-1960年。
《乡巴佬》(阿什维尔高中)文学杂志;年鉴,1914-1948年。
《小阿布纳日报》。厨房水槽出版社。第1-26卷(阿尔·卡普1934-1960年的每日连环漫画)。
《电视指南》,1955-1975年。
《综艺》,1960-1965年。
《WLS家庭相册》(《全国谷仓舞会》粉丝杂志),1930-1957年。
保罗·亨宁。作者电话采访,1997年6月3日。文字记录由作者保存。
艾布拉姆森,鲁迪。“新’乡巴佬’必将嘲讽南方。”《图森公民报》,2002年12月9日(http://www.tucsoncitizen.com/opinion/12_9_02tv.html)
亚当斯,E. C. L。“卡罗来纳荒野。”《斯克里布纳杂志》,1931年6月,611-17页。
艾吉,詹姆斯。“电影。”《国家》,1946年4月27日,516-17页。
“Aid for Mountain Childr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Weekly Magazine, September 29, 1937, 12.
Albert, Ned. Comin’ round the Mountain (A Hillbilly Comedy in One Act). New York: Samuel French, 1938.
Allen, James Lane. “Mountain Passes of the Cumberlands.” Harper’s, September 1890, 561–76.
______. “Through Cumberland Gap on Horseback.”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une 1886, 561–76.
Alpert, Hollis. “The Golden Kettles.” Saturday Review, March 28, 1953, 29–30.
“—And High Time! After 7 Years on the Air,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Pay Their First Visit to the Ozarks.” TV Guide, August 23, 1969, 10–13.
Anoe, Pearl. “There’s No Place like the OZARKS.” Americas, May 1955, 10–15.
Antrim, Doron K. “Whoop-and-Holler Opera.” Collier’s, January 26, 1946, 18, 85.
“Appalachia: Myth and Reality: A Panel Discussion.” James Dickey Newsletter 2, no. 1 (Fall) (1985): 11–16.
Armory, Cleveland. “Green Acres [Review].” TV Guide, November 27, 1965, 19.______. “The Waltons [Review].” TV Guide, November 18, 1972, 49.
Armstrong, Anne W.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s.” Yale Review, n.s., 24, no. 3 (1935): 539–54.
Arnow, Harriette. The Dollmaker. 1954. Reprint,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0.
______. “The Gray Woman of Appalachia.” The Nation, December 28, 1970, 684–87.
Ashworth, John H. “The Virginia Mountaineer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2 (July 1913): 193–211.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187–203.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AuCoin, Bill. Redneck. Matteson, IL: Greatlakes Living Press, 1977.
“Backwoods Sparkin’.”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1937, 127–28.
Barker, Catharine S. Yesterday Today. Caldwell, ID: Caxton Printers, 1941.
“Barney Google’s Birthday: He’s 21 Now but Sadly Eclipsed by the Toughie Snuffy Smith.” Newsweek, October 14, 1940, 59–60.
Barrere, Albert, and Charles Leland. A Dictionary of Slang, Jargon and Cant.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97.
Barry, Phillips. “Miscellaneous Notes.” American Speech, August 2, 1927, 473.
Barton, Bruce. “Exercise Your Spirit—Don’t Wrap It Up in Your Business and Let It Grow Flabby. Have a Pet Enthusiasm; It Will Keep You Young and Make You Happy.” Good Housekeeping, September 1925, 23, 128–40.
Becker, Edwin J. “Made in the Land of Do Without.” American Mercury, May 1954, 141–43.
Benét, Stephen Vincent. “The Mountain Whippoorwhill—How Hill-Billy Jim Won the Great Fiddlers’ Prize.” Century Magazine, March 25, 1925, 635–39.
Berchtold, William E. “Men of Comics.” New Outlook, April 1935, 34–40.
Bergren, Ellen H. “Pioneering Days in Appalachia.”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June 1939, 302–9.
“The Beverly . . . What?” TV Guide, January 18, 1964, 12–13.
“Beverly Hillbillies.” Variety, October 3, 1962, 35.
“‘Beverly Hillbillies’ to Become Reality Show.” Reuters. CNN.com, August 28, 2002 (http://www.cnn.com/2002/SHOWBIZ/TV/08/28/television.hillbillies.reut/index.html)
Biggs, Wallace R. “A Man Is Hanged.” American Mercury, January 1940, 37–41.
Biograph Bulletins, 1908–1912.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3.
Biograph Bulletins, 1896–1908. Los Angeles: Locare Research Group, 1971.
Blassingame, Wyatt. “Smoky Mountain Holiday.” American Magazine, April 1956, 98–101.
Boleman-Herring, Elizabeth. “James Dickey: An Interview.” James Dickey Newsletter 12, no. 2 (1996): 13–18.
Borah, Leo A. “Home Folk around Historic Cumberland Gap.”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November 1943, 741–68.
Botkin, B. A., ed. A 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 Stories, Ballads, 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New York: Crown, 1944.
Braden, William, and Morton Kondracke. “What City Is Doing for Hill Folk.” Chicago Sun Times, February 10, 1964, 4+.
Bradley, William A. “Hobnobbing with Hillbillies.” Harper’s Monthly Magazine, December 1915, 91–103.
Bradshaw, Henry, and Vera Bradshaw. “The Ozarks.”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May 1952, 70–71, 238–44.
Branscome, James G. “Annihilating the Hillbilly: The Appalachian’s Struggle with America’s Institutions.” In The Failure and the Hope—Essays of Southern Churchmen, ed. Will D. Campbell and James Y. Holloway, 120–39.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1972.
Braun, Wilbur. Feudin’ (A Hillbilly Comedy in One Act). New York: Samuel French, 1948.
Brearkey, H. C. “Are Southerners Really Lazy?” American Scholar 18 (1949): 68–75.
Breckinridge, Mary. “The Corn-Bread Line.” Survey, August 15, 1930, 422–23.
______. “Maternity in the Mountains.” North American Review, December 1930, 765–68.
______. “Is Birth Control the Answer?” Harper’s Magazine, July 1931, 157–63.
Breitigam, Gerald B. “Lifting Up the Mountains—Bringing a Knowledge of America to Pure-Blooded Americans.” Ladies’ Home Journal, July 1920, 45, 152.
Broun, Heywood. “Wham! and Pow!” New Republic, May 17, 1939, 44.
Brown, John Mason. “The Case against the Comics.”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March 20, 1948, 31–32.
Brown, William P. “A Peculiar People.” Overland Monthly, November 1888, 505–8.
Buck, P. H. “The Poor Whites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1 (1926): 41–54.
“Bull Market in Corn.” Time Magazine, October 4, 1943, 33–34.
Burman, Ben Lucien. “That Good Old Mountain Justice.” Collier’s Magazine, July 25, 1953, 46–49.
Burt, Struthers. “The Wood Choppers of Nass.” Scribner’s Magazine, June 1936, 351–54.
Cable, Raymond M. “Fishbone College.” American Mercury, May 1933, 117.
Caldwell, Christopher. “Hill of Beans—Reality Is Optional.” New York Press 15, no. 36 (2002) (http://www.nypress.com/print.cfm?content_id=6971)
Caldwell, Mary F. “Change Comes to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eer.” Current History 31 (1930): 961–67.
“A Call to Combat Race Suicide.” Literary Digest, November 22, 1924, 36.
“Camp Hillbilly”(照片)。Blue Ridge Country, November/December 1992.
Campbell, John C. “From Mountain Cabin to Cotton Mill.” Child Labor Bulletin, May 1913, 74–84.
______. The Southern Highlander and His Homel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21.
Campbell, Reverend Robert F. Classification of Mountain Whites. N.p.: Hampton Institute Press, 1901.
Canterbury, Edith. “Background Years.” Mountain Life and Work 30 (1954): 11–12.
Caplin, Elliot. Al Capp Remembered.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94.
Capp, Al. “The Case for the Comics.”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March 20, 1948, 31–32.
______. “There Is a Real Schmoo.” New Republic, March 21, 1949, 14–15.
______. “It’s Hideously True!! The Creator of Li’l Abner Tells Why His Hero Is (Sob!) Wed.” Life, March 31, 1952, 100–108.
______. “Innocents in Peril.” In Al Capp, The World of Li’l Abner. N.p.: Capp Enterprises, 1953.
______. My Well-Balanced Life on a Wooden Leg: Memoirs. Santa Barbara: John Daniel and Company, 1991.
“Capp’s Cuts.” Time, April 11, 1969, 67–68.
“The Carolina Sand-Hillers.” (Boston) Odd Fellow, September 15, 1847, 193.
Carr, Joseph W. “A List of Words from Northwest Arkansas.” Dialect Notes 2 (1900–1904): 416–420.
Cash, W. J. “Genesis of the Southern Cracker.” American Mercury, May 1935, 105–8.
“Casting Agents in Search of ‘The Real Beverly Hillbillies.’” Associate Press. Concord Monitor Online, September 20, 2002 (http://www.cmonitor.com/stories/a&e2002/hillbillysearch_07y14y54_2002.shtml)
Caudill, Harry M. Night Comes to the Cumberlands—A Biography of a Depressed Are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
______. “The Mountaineers in the Affluent Society.” National Parks & Conservation Magazine, July 1971, 17–20.
“The Causes of Feuds and Moonshining.” Literary Digest, April 22, 1922, 35–36.
Chapman, Maristan. “The Mountain Man—An Unbiased View of Our Southern Highlanders.” Century Magazine, February 1929, 505–11.
______. “American Speech—As Practised in the Southern Highlands.” Century Magazine, March 1929, 617–23.
Churchill, Allen. “Tin Pan Alley’s Git-tar Blu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5, 1951, section 6, reprinted in A History and Encyclopedia of Country, Western, and Gospel Music, ed. Linnell Gentry, n.p. St.Clair Shores, MI: Scholarly Press, 1972.
Cleghorn, Reese. “Appalachia—Poverty, Beauty and Povert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25, 1965, 12–13, 124–27.
Coleman, McAlister, and Stephen Raushenbush. Red Neck. New York: Harrison Smith & Robert Haas, 1936.
Combs, Josiah H. The Kentucky Highlanders from a Native Mountaineer Viewpoint. Lexington: J. L. Richardson, 1913.
“Comics—1894–1934.” Editor and Publisher, November 17, 1934, 26.
Cooper, James Fenimore.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Narrative of 1757. 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19??.
“The Corn Is Green.” Newsweek, December 3, 1962, 70.
“The Corn Is Still Green.” Time Magazine, August 8, 1969, 59.
“Country Music Snaps Its Regional Bounds.” Business Week, March 19, 1966, 96–98, 103.
“The Country Slicker.” Newsweek, December 6, 1965, 97.
Craddock, Charles Egbert (Mary Noailles Murfree). “The Star in the Valley.” Atlantic Monthly, November 1878, 532–43.
______. In the Tennessee Mountai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2.
Craigie, Sir William A., and James Hulbert, eds.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Cralle, Walter O. “Social Change and Isolation in the Ozark Mountain Region of Missour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1 (1936): 435–46.
Crawford, T. C. An American Vendetta: A Story of Barba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elford, Clarke, and Company, 1889.
Crichton, Kyle. “Thar’s Gold in Them Hillbillies.” Collier’s National Weekly, April 30, 1938, 24, 27.
______. “Hillbilly Judy.” Collier’s, May 16, 1942, 17+.
Crist, Judith.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TV Guide, August 27, 1966, 1.
Crowther, Bosley. “Comin’ round the Mountai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40, 27:3.
Daley, Mary Dowling. “The Not So Beverly Hillbillies.” Commonweal, March 13, 1970, 4–5.
Davenport, Walter. “Just a-settin’.” Collier’s National Weekly, July 30, 1927, 8–9, 28.
______. “Up an-gittin’.” Collier’s National Weekly, September 10, 1927, 19, 42–43.
Davidson, Bill. “Thar’s Gold in Them Thar Hillbilly Tunes.” Collier’s Magazine, July 28, 1951, 34–35, 42–45.
Davidson, Muriel. “Fame Arrived in a Gray Wig, Glasses and Army Boots.” TV Guide, September 7, 1963, 4–7.
Davidson, Theodore F. “The Carolina Mountaineer—The Highest Type of American Character.” First Annual Transactions of the Pen and Plate Club of Asheville, N.C., May 11, 1905, 1–11.
Davis, D. H. “Changing Role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s and the Passing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eers.” Journal of Geography 24 (February 1925): 41–52.
Davis, Mrs. S. M. “The ‘Mountain Whites’ of America.”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June 1895, 422–26.
Davis, Rebecca Harding. “By-Paths in the Mountains.”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61 (1880): 167–85, 353–69, 532–47.
Dawber, Rev. M. A. “The ‘Forgotten Man’ of the Mountain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April 1934, 177–79.
Dawley, Thomas R. “Our Southern Mountaineers: Removal the Remedy for the Evils that Isolation and Poverty Have Brought.” World’s Work, March 1910, 12704–714.
Deal, J. A. “The Hillbilly” or “American Mountaineer.” Asheville, NC: Inland Press, c. 1915.
de Moraes, Lisa. “Gold in Them Thar ‘Hillbillie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9, 2002, A1.
“A Defense of the Mountaineer.” Literary Digest, April 20, 1912, 800–801.
Dern, Marian. “Viewers Like ’Em, and That’s That.” TV Guide, March 14, 1964, 10–13.
Dickey, Christopher. Summer of Deliveran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Dickey, James. Delivera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Dingman, Helen H. “New Trails in Southern Highland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September 1933, 437–41.
“Dogpatch in Semi-Nude.” Newsweek, December 21, 1959, 92–93.
“Dogpatch Is Ready for Freddie—After 43 years, Al Capp Decides to Hang Up His Pen.” Time Magazine, October 17, 1977, 78.
Douglas, Paul. “Strip-mined Landscape and Impoverished Souls.” Christian Century, June 8, 1966, 753–54.
Dow, Jack. “Letter to the Editor.” TV Guide, April 19, 1969, A-1.
“The Dream of a Shirt-Tail Boy Comes True.” Outlook and Independent, July 28, 1920, 557–58.
Dreher, Rod. “Minstrel Show.” National Review Online, August 30, 2002
Eaton, Allen H. Handicrafts of the Southern Highla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37.
Eddy, Don. “Hillbilly Heaven.” American Magazine, March 1952, 28–29, 119–23.
______. “Let’s Go to the Ozarks.” American Magazine, March 1954, 38–41, 92–97.
“The Editor’s Forum: Hillbilly Music.” Mountain Life and Work 35, no. 2 (1959): 34–42.
Efron, Edith. “American Gothic—On television and off.” TV Guide, April 20, 1968, 32–34.
“Eliminate the Racial Slur!” Christian Century, June 10, 1964, 757–58.
Elliot, Lawrence. “Andy Griffith: Yokel Boy Makes Good.” Coronet, October 1957, 105–10.
Ellison, Jerome. “The Plight of the Hill People.”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4, 1960, 43+.
Ernst, Harry W., and Charles H. Drake. “‘Poor, Proud and Primitive’ . . .—The Lost Appalachians.” The Nation, May 30, 1959, 490–93.
Estabrook, Arthur H. “Is There a Mountain Problem?” Mountain Life and Work, July 1928, 5–13, 35–36.
______. “The Population of the Ozarks.” Mountain Life and Work, April 1929, 2–3, 25–28.
Everts, Mrs. C. S. “Modern Methods Invading the Mountain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May 1917, 365–67.
Farber, Manny. “Make Mine Muzak.” New Republic, May 27, 1946, 769.
Fetterman, John. “The People of Cumberland Gap.”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November 1971, 591–621.
“Forgotten Men: The Poor Whit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7, 1967, 76.
“Fortune Survey: VI: The Comic Strips.” Fortune, April 1937, 190–91.
“The Founding of the Hindman Settlement School.” Outlook and Independent, July 28, 1920, 558.
Fox, John, Jr. “A Mountain Europa.” Century Magazine, September–October 1892, 760–75, 846–58.
______.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 Scribner’s Magazine, April–May 1901, 387–99, 556–70.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121–44.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______. “On Horseback to Kingdom Come.” Scribner’s Magazine, August 1910, 175–86.
______. “On 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 Scribner’s Magazine, October 1910, 417–29.
French, Laurence. “When I Get Good and Ready.” Appalachian Journal 16, no. 1 (1988): 62–70.
Frome, Michael. “Threats to Southern Appalachia.” National Parks & Conservation Magazine, July 1971, 6–9.
Frost, William Goodell. “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s.”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899, 311–19.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92–106.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______.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s: Our Kindred of the Boone and Lincoln Type.” American Monthly Review of Reviews, March 1900, 308–11.
______. “God’s Plan for the Southern Mountains.” Biblical Review, 1921, 405–25.
“Fun without Mickey.” Commonweal, May 3, 1946, 72–73.
“FUNNIES: Colored Comic Strips in the Best Health at 40.” Newsweek, December 1, 1934, 26–28.
“Funny Paper Advts.” Fortune, April 1933, 98–99.
“The Funny Papers.” Fortune, April 1933, 44–49+.
“Funny Strips: Cartoon-Drawing Is Big Business; Effects on Children Debated.” Literary Digest, December 12, 1936, 18–19.
Garrigan, Liz Murray. “Bubba Goes to Hollywood.” Nashville Scene, September 5–11, 2002
Garyls, William A. “Letter to the Editor.” Harper’s, April 1958, 10.
Gavit, John Palmer. “Bootstrapping among the Pioneers.” Survey, July 1, 1932, 304–6.
Gingrich, Arnold. Nothing but People: The Early Days at Esquire—A Personal History, 1928–1958. New York: Crown, 1971.
Gish, Anthony. “Yes, I’m a Hillbilly.” Esquire, April 1937, 95, 128, 130.
Gitlin, Todd. “JOIN: Coal-Operatin’ in Uptown.” Christian Century, June 8, 1966, 754–58.
Gitlin, Todd, and Nancy Hollander. Uptown—Poor Whites in Chicag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Goat’s Nest Neighbors: They Swap Food and Houn’s for Photos.” Newsweek, September 21, 1942, 47.
“The Gold Guitars.” Newsweek, April 4, 1966, 96–97.
Goodrich, Frances Louise. Mountain Homespun(山地手织布). 1931. Reprint,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9.
Goodwin, Fritz. “Right at Home with the Clampetts.” TV Guide, November 10, 1962, 15–16, 18–19.
Gould, Jack. “TV: ‘Beverly Hillbillys [sic].’”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 1962, 63.
“Grandpap’s A-Makin’.”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38, 551–52.
Grattan, C. Hartley. “Trouble in the Hills.” Scribner’s Magazine, November 1935, 290–94.
Green, Abel. “‘Hill-Billy’ Music.” Variety, December 29, 1926, 1.
Greene, Laurence. “I Found a Hide-Out.”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2, 1951, 36–37+.
Haddix, Cecille, ed. Who Speaks for Appalachia?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5.
Halberstadt, Catherine Capp. “Introduction.”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1 (1934–1936), 3–4.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8.
Hall, Mordaunt. “Primitive Mountaineers.” New York Times Film Review, February 28, 1927, 22:3.
______. “Where Man Is Vile—‘Stark Love’ a Realistic Reproduction of Life of Mountaineers.”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27, Sect. VII, p. 7.
Ham, Tom. “Close-Up of a Hillbilly Family.” American Mercury, June 1941, 659–65.
Haney, William H. The Mountain People of Kentucky: By a Kentucky Mountain Man. Cincinnati: Robert Clarke, 1906.
Hano, Arnold. “The G.A.P. Love the ‘Hillbilli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17, 1963, 30, 120, 122–23.
______. “TV’s Topmost—This Is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26, 1965, 10–11+.
“The Happy Pappies of Handshoe Holler.” Time Magazine, November 5, 1965, 38–39.
Harlow, Alvin F. “People of the Hills.”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2, 1935, 12–13+.
Harman, A. F. “Culture in the Sout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Weekly, June 30, 1937, 1–2.
Harmon, Lee. Hillbilly Ballads. Beckley, WV: Beckley Newspaper Corporation, 1938.
Harmon, Ronald Lynd. “American Rustic: The Ozarks.” Travel, August 1977, 42–45.
Harney, Will Wallace. “A Strange Land and a Peculiar People.” Lippincott’s Magazine (October 1873): 429–38.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ed., 45–58.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Harriman, Mrs. J. Borden. “Some Phases of the Southern Cotton Industry.” Harper’s Weekly, July 11, 1911, 12.
Harrington, Michael.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Harris, Corra. “Behind the Times.”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15, 1928, 37+.
Harris, George Washington. Sut Lovingood: Yarns Spun by a “Nat’ral Born Durn’d Fool.” New York: Dick & Fitzgerald, 1867. Reprint edited by M. Thomas Inge. New Have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1966.
Harris, Imperial Jim. History—Grand & Glorious Order of the Hillbilly Degree. Milford, OH: Hillbilly Press, 1982.
Harris, Jay S., ed. TV Guide—The First 25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Harshaw, Lou. “South’s Top Scenic Strip.” Travel, August 1956, 18–21.
Haselden, Kyle. “Mountain Movements.” Christian Century, May 10, 1961, 582–83.
“Haute Couture—Hillbilly Style.” TV Guide, March 9, 1963, 6–8.
Hawthorne, Julian. “Mountain Votes Spoil Huntington’s Revenge.” The Journal, April 23, 1900, 2.
Hay, George D. A Story of the Grand Ole Opry. Nashville: N.p., 1953.
Haynes, Henry “Homer,” and Kenneth “Jethro” Burns. “From Moonshine to Martinis.”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15–16 (1993–1994).
Heath, Evelyn. Hillbilly Homestead.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65.
“Hillbilly Bus.” American Magazine, March 1956, 54–55.
“Hillbilly TV Show Hits the Big Time.” Business Week, March 10, 1956, 30–31.
Hine, Al. “Million Dollar Kettle Drummer.” Esquire, May 1953, 88–89, 132.
Hobson, Dick. “The Grandpappy of All Gushers.” TV Guide, April 24, 1971, 16–20.
Hogue, Wayman. “Ozark People.” Scribner’s Magazine, April 1931, 509–20.
Hollander, A. N. J. “The Tradition of ‘Poor Whites.’” In Culture in the South, ed. William T. Couch, 403–3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5.
Holman, Ross L. “The Great Smokies—America’s Most Popular Park.” Travel, October 1948, 18–21, 33.
Holmes, S. J. “Will Birth Control Lead to Extinction?” Scientific Monthly, March 1932, 247–51.
Hughes, Marion. Three Years in Arkansaw. Chicago: M. A. Donohue & Company, 1905.
Hutchins, William J. “Introduction.” Mountain Life and Work, April 1925, 1.
Jackson, Thomas W. On a Slow Train through Arkansaw. 1903. Reprint. Ed. W. K. McNeil.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5.
Janofsky, Michael. “Pessimism Retains Grip on Region Shaped by War on Povert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1998, A-1, A-13.
Johnson, Samuel. “Life in the Kentucky Mountains. By a Mountaineer.” Independent 65 (July 1908): 72–78.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175–85.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Johnston, Josiah Stoddard. “Romance and Tragedy of Kentucky Feuds.” Cosmopolitan 27, (September 1899): 551–58.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107–19.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Jones, Howard Mumford. “The Southern Legend.” Scribner’s Magazine, May 1929, 538–42.
Jones, Ora L. Peculiarities of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eers. Detroit: Harlo Press, 1967.
Jordan, Dick. “Slo ‘n’ Easy Start Weakly Bull-A-Thon.” Rural Radio, March 1939, 6.
Kahn, E. J., Jr. “Ooff!! (Sob!) Eep!! (Gulp!) Zowie—I.” New Yorker, November 29, 1947, 46–50+.
______. “Ooff!! (Sob!) Eep!! (Gulp!) Zowie—II.” New Yorker, December 9, 1947, 48–59.
Kahn, Kathy. Hillbilly Women. New York: Doubleday Press, 1973.
Kennedy, Paul. “Minstrels of the Kentucky Hills.” Travel, June 1942, 14–15, 39.
“The Kentucky Mountaineers.” Science, April 6, 1928, 12.
Kephart, Horace. Our Southern Highlanders—A Narrative of Adventure in the Southern Appalachians and a Study of Life among the Mountaineers. 1913. Reprint,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6.
Kernodle, Wayne. “Last of the Rugged Individualists.” Harper’s Magazine, January 1960, 46–51.
King, Nelson. “Hillbilly Music Leaves the Hills.” Good Housekeeping, June 1954, 18.
“King of Corn.” Newsweek, July 14, 1969, 94.
Kinney, Courtney. “Reality Show Will Perpetuate Hillbilly Stereotype.”(真人秀将延续乡巴佬刻板印象)Kentucky Post, August 31, 2002 (http://www.kypost.com/2002/aug/31/kinney083102.html)
Kirkland, Winifred. “Mountain Mothers.”(山区母亲)Ladies’ Home Journal, December 1920, 26–27, 193.
Krout, Maurice H. “Culture and Culture Change.”(文化与文化变迁)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8 (September 1932): 253–63.
Lagemann, John Kord. “You’ll Be Comin’ round the Mountain.”(你将绕山而来)Collier’s Magazine, May 15, 1948, 84–89.
Lane, Rose Wilder. Hill Billy(乡巴佬).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6.
Lasswell, Fred. “Billy, Barney, Snuffy & Me.”(比利、巴尼、斯纳菲和我)Cartoonist PROfiles, June 1994, 10–21.
Lawson, Marvin. By Gum, I Made It!—An Ozark Arkie’s Hillbilly Boyhood(天哪,我成功了!——一个奥扎克阿肯色人的乡村童年). Branson, MO: Ozarks Mountaineer, 1977.
Leamy, Hugh. “Now Come All You Good People.”(善良的人们,请过来)Collier’s Magazine, November 2, 1929, 20, 58–59.
Lee, Alfred. Race Riot(种族骚乱).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3.
“Leena the Unseena.”(看不见的莉娜)Newsweek, July 1, 1946, 58.
Lessing, Bruno. “Humor-Laughter-‘Comics.’”(幽默-笑声-“漫画”)Circulation, April 1925, 12–13, 40–41.
“Letters from Arkansas.”(来自阿肯色的信)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 n.s., 1 (1836): 25–26.
“Leviticus vs. Yokums.”(利未记对约库姆一家)Newsweek, November 29, 1948, 58.
Lewis, Richard Warren. “The Golden Hillbillies.”(金色乡巴佬)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2 1963, 30–35.
“A Light in the Mountains.”(山中之光)Time Magazine, October 16, 1950, 74–75.
“Li’l Abner’s Mad Capp.”(小阿布纳的疯狂卡普)Newsweek, November 24, 1947, 60–61.
“Li’l Abner—Broadway and Dogpatch.”(小阿布纳——百老汇与狗窝镇)Life, January 14, 1957, 74–83.
Lilienthal, David E. The Journals of David Lilienthal: The TVA Years 1939–1945(大卫·利连索尔日记: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岁月1939–194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______. TVA—Democracy on the March(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前进中的民主).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4.
Lovinggood, R. S. “Negro Seer: His Preparation and Mission.”(黑人先知:他的准备与使命)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Review 24, no. 2 (1907): 156–72. 引自 The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Ohio, 1850–1920(俄亥俄州非裔美国人经历,1850–1920). 网站 (http://dbs.ohiohistory.org/africanam/)
Lowrie, Sarah D. “The Comic Strips.”(连环漫画)Forum, April 1928, 527–36.
“Luring the Poor Out of the Hills.”(引诱穷人走出山区)Business Week, July 1, 1967, 74–78.
Lynde, Francis. “The Moonshiner of Fact.”(真实的私酒贩子)Lippincott’s Magazine 57 (January 1896): 66–76. 重印于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民间与流行文化中的阿巴拉契亚形象), ed. W. K. McNeil, 75–88.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MacClintock, S. S. “The Kentucky Mountains and Their Feuds.”(肯塔基山区及其世仇)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 (1901): 1–28, 171–87.
MacDonald, Betty. The Egg and I(鸡蛋与我).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45.
MacKaye, Marion Morse. “God, Humanity, and the Mountains.”(上帝、人类与山脉)Survey Graphic, August 1946, 288–93, 302.
MacKaye, Percy. “Poetic Drama in Kentucky’s Mountains.”(肯塔基山区的诗剧)Literary Digest, January 26, 1924, 29–31.
______. This Fine Pretty World: A Comedy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s(这美好的世界:肯塔基山区喜剧).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Make Mine Music.”(给我音乐)Time, May 6, 1946, 98, 101.
Maloney, John. “Time Stood Still in the Smokies.”(时间在大烟山静止)Saturday Evening Post, April 27, 1946, 16–17+.
Maloney, Russell. “Li’l Abner’s Capp: His Cartoon Characters Are America’s Favorite Hillbillies.”(小阿布纳的卡普:他的卡通人物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乡巴佬)Life, June 24, 1946, 58–62+.
Manne, Jack. “Mental Deficiency in a Closely Inbred Mountain Clan.”(近亲繁殖山区家族中的智力缺陷)Mental Hygiene, April 1936, 269–79.
Marey, Stuart. “Pioneer of 1941.”(1941年的先驱)American Magazine, March 1941, 104.
Markham, R. H. “As Old as the Mountains.”(与山同龄)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Weekly Magazine, March 1, 1941, 12.
Martin, Roscoe. TVA—The First Twenty Years—A Staff Report(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最初二十年——工作人员报告). University, AL, and Knoxville, TN: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56.
Masters, Victor I. “The Mountaineer of the South.”(南方山民)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November 1919, 845–49.
Maxwell, James A. “Down from the Hills and into the Slums.”(从山区下来进入贫民窟)The Reporter, December 13, 1956, 27–29.
McAdoo, Julia. “Where the Poor Are Rich.”(穷人富有的地方)American Mercury, September 1955, 86–89.
McCord, David Frederick. “The Social Rise of the Comics.”(漫画的社会崛起)American Mercury, July 1935, 360–64.
McVey, Frank L. “Is There a Mountain Problem?”(山区问题存在吗?)Mountain Life and Work, July 1935, 1–4.
Meek, Frederick M. “Sweet Land of Andy Gump.”(安迪·甘普的甜蜜土地)Christian Century, May 8, 1935, 605–7.
Mell, Mildred. “The Southern Poor White—Myth, Symbol, and Reality of a Nation.”(南方贫穷白人——一个国家的神话、象征与现实)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January 23, 1943, 13–15.
Mencken, H. L. “The Sahara of the Bozart.”(艺术的撒哈拉)载于 Pejudices: Second Series(偏见:第二辑), 136–54.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20.
______. “The Hills of Zion.”(锡安山)载于 Prejudices: Fifth Series(偏见:第五辑), 75–86.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______. “In Memoriam: W. J. B.”(悼念:W. J. B.)载于 Prejudices: Fifth Series(偏见:第五辑), 64–74.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______. “Inquisition.”(审讯)载于 The Days of H. L. Mencken: Heathen Days(H. L. 门肯的日子:异教徒时代), 214–3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7.
______. “The Scopes Trial.”(斯科普斯审判)载于 The Impossible H. L. Mencken(不可能的H. L. 门肯), ed. Marion Elizabeth Rodgers, 560–611. New York: Doubleday, 1991.
Mercer, H. C. “On the Track of the Arkansas Traveler.”(追踪阿肯色旅行者)Century Magazine, March 1896, 707–12.
Miles, Emma Beth. The Spirit of the Mountains(山之精神). 1905. 重印,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5.
“Modernizing Elizabethans of To-day.”(当代伊丽莎白时代人的现代化)Literary Digest, February 15, 1936, 17.
Morgan, Arthur E. The Making of the TVA(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创建).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74.
Morris, Lucille. “Good Ol’ Hillbilly . . .”(好老乡巴佬……)University Review—A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4, no. 2 (1937): 188–90.
Moss, Sylvia. “The New Comedy.”(新喜剧)Television Quarterly 4 (1965): 42–45.
“Mountain Dew Bottler Catalog.”(激浪装瓶商目录)Pepsi-Cola, 1966.
“The Mountain Whites.”(山区白人)Outlook and Independent, May 17, 1922, 92, 94.
“Mountaineers in Picture.”(图片中的山民)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1926, Sect. VII, p. 5.
Muggeridge, Malcolm. “Why Those Hillbillies Are Rampant in Britain.”(为什么那些乡巴佬在英国如此流行)TV Guide, March 6, 1965, 22–26.
“Must Hee-Haw TV.” E! Online News, August 29, 2002 (http://entertainment.msn.com/news/eonline/082902_hee.asp)
“A Mutual Admiration Society.” TV Guide, January 23, 1960, 6–7.
“My Neighbors and Myself—By a Country Doctor.” Ladies’ Home Journal, February 1928, 6–7, 58, 60, 62.
Newman, Thomas. “The Folk of Bloody Mountain.” Esquire, January 1938, 68–69, 139.
Newton, Dwight. “High Flying Hillbillie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November 18, 1965, 33.
Niles, John Jacob. “Hill Billies.” Scribner’s Magazine, November 1927, 601–5.
______. “In Defense of the Backwoods.” Scribner’s Magazine, June 1928, 738–45.
______. “My Precarious Life in the Public Domain.”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1948, 129–31.
Niles, John Jacob, and Jonathan Williams. The Appalachian Photographs of Doris Ulmann. Highlands, NC: Jargon Society, 1971.
Nixon, Herman Clarence. Forty Acres and Steel Mul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8.
O’Connell, Mary Rebecca. “One Hundred Percent American.” Catholic World, May 1930, 153–56.
Odum, Howard W. Southern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6.
“The Okies—A National Problem.” Business Week, February 10, 1940, 16–17.
“Okies of the ’60s.” Time Magazine, April 20, 1962, 31.
Olmsted, Frederick Law. A Journey in the Back Country. New York: Mason Brothers, 1863.
“On Sadie Hawkins Day, Girls Chase Boys in 201 Colleges.” Life, December 11, 1939, 32–33.
“On the Cob.” Time Magazine, November 30, 1962, 76.
Oswalt, Lovat. Hillbilly High Jinks (A Rousing Hillbilly Comedy in One Act). Boston: Walter H. Baker, 1952.
“Our Southern Highlands Makes News To-day.” House and Garden, November 1942, 48–51.
“A People Who ‘Hanker Fer Larnin.’” Literary Digest, February 10, 1923, 34–35.
“Personal and Otherwise—the Embarrassing Truth about Davy Crockett, the Alamo, Yoknapatawpha County, and Other Dear Myths.” Harper’s Magazine, July 1955, 16–18.
Peyton, Dave. “First Beverly Hillbillies Bad Enough. ‘Montani Semper Stereotype’ Strikes W.Va. Once Again.” Charleston Daily Mail, September 2, 2002, 4A.
Photiadis, John D., and Harry K. Schwarzweller, eds. Change in Rural Appalachia—Implications for Action Program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Pistol Packin’ Mama.” Life, October 11, 1943, reprinted in A History and Encyclopedia of Country, Western, and Gospel Music, ed. Linnell Gentry, n.p. St. Clair Shores, MI: Scholarly Press, 1972.
Pitts, Leonard, Jr. “Reintarnation! Second ‘Beverly Hillbillies’ as Reality TV Not Funny.” Charleston Gazette, September 6, 2002, 4A.
Plumb, Charlie. “Inside the Funny Page.” Esquire, April 1942, 57, 110–11.
“Poetic Drama in Kentucky’s Mountains.” Literary Digest, January 26, 1924, 29–30.
Politzer, Heinz. “From Little Nemo to Li’l Abner—Comic Strips as Present-Day American Folklore.” Commentary, October 1949, 346–54.
Poole, Ernest. “The Nurse on Horseback—Has Brought New Life and Hope to the Kentucky Mountaineers.” Good Housekeeping, June 1932, 38–37+.
“Poor White Trash.” Cornhill Magazine, April 1882, 579–84.
Portis, Charles. “That New Sound from Nashville.”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12, 1966, 30–38.
Portor, Laura Spencer. “In Search of Local Color.” Harper’s Magazine, August–September 1922, 281–94, 451–66.
Powell, Levi W. Who Are These Mountain People? An Intimate Historical Account of Southern Appalachia.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66.
Pridemore, Francis. “What Prohibition Has Done for the Mountaineers.” Outlook and Independent, July 20, 1927, 884–85.
“Primitive Mountaineers Filmed in Native Nook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27, Sect. VII, p. 6.
“Putting the Clampett on ‘Hillbillies.’” Appalachian Journal 21, no. 1 (1993): 22.
Quinn, Arthur Hobson. “New Notes and Old in the Drama: 1923–1924.” Scribner’s Magazine 76 (1924): 79–87.
R., of Tennessee. “A Week in 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31 (August 1860): 117–31.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23–44.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Raine, James Watt. The Land of Saddle-Bags: A Study of the Mountain People of Appalachia. New York: Council of Women for Home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24.
Ralph, Julian. “Our Appalachian Americans.” Harper’s Magazine, June 1903, 32–41.
Randolph, Vance. “The Ozark Dialect in Fiction.” American Speech, March 1927, 283–89.
______. The Ozarks: An American Survival of Primitive Society.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31.
______. Ozark Mountain Folk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32.
______. “Ozark Anthology—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Review—A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4, no. 2 (1937): 101–4.
______. Funny Stories about Hillbillies. Girard, KS: Haldeman-Julius Publications, 1944.
______. Ozark Supersti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7.
A Reminiscent History of the Ozarks Region. 1894. Reprint, Easley, SC: Southern Historical Press, 1978.
Reynolds, Horace. “I Hear America Singing.” American Mercury, October 1944, 463–67.
Richardson, Don, Sr. “Junior Cobb of Three Brothers, Ark., Judges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He’s hill folks, himself).” TV Guide, July 16, 1963, 8–9.
Richardson, Eudora Ramsay. “Contented Though American.” Forum and Century 89, no. 5 (1933): 263–67.
Roberts, A. W. “Don’t Call Me Hillbill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Weekly Magazine, March 18, 1944, 4.
Roberts, Bruce, and Nancy Roberts. Where Time Stood Still: A Portrait of Appalachia.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Rodell, Fred. “Everybody Reads the Comics.” Esquire, March 1945, 50–51+.
Rogers, Dennis. “Shootin’ for Some Crude.” Newsobserver.com, September 4, 2002
Roiphe, Anne. “The Waltons—Ma and Pa and John-Boy in Mythic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18, 1973, 40–41+.
Ross, Malcolm. Machine Age in the Hills.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______. “My Neighbors Hold to Mountain Ways.”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June 1958, 856–80.
Russell, Gladys Trentham. Call Me Hillbilly—A True Humorous Account of the Simple Life in the Smokies before the Tourists Came. Rev. ed. Alcoa, TN: Russ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Sadie Hawkins at Yale.” Time, November 11, 1940, 51.
Sauer, Carl O.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Ozark Highland.” Scientific Monthly, September 1920, 215–27.
Scheinfeld, Amram. “A Portrait in Zowie!” Esquire, November 1935, 78+.
Scherman, Robert. “Hillbilly Phenomen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Weekly Magazine, March 13, 1948, 10.
“The Schmoo’s Return.” New Yorker, October 26, 1963, 39–40.
Schoolcraft, Henry. Scen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Semi-Alpine Region of the Ozark Mountains of Missouri and Arkansa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Grambo, and Company, 1863.
Schuyler, George. “Our White Folks.” American Mercury, December 1927, 385–92.
Seitz, Don C. “Mountain Folks—Some Glimpses of the One Hundred Per Cent Americans in the Blue Ridge Country.” Outlook and Independent, September 29, 1926, 146–47.
Seldes, Gilbert. The Seven Lively Ar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4.
______.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TV Guide, December 15, 1962. Reprinted in TV Guide—The First 25 Years, ed. Jay S. Harris, 65–66.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Semple, Ellen Churchill. “The Anglo-Saxons of the Kentucky Mountains: A Study in Anthropogeography.” Geographical Journal 17 (June 1901).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145–74.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Shanley, John. “TV: Simplicity Rescues One of Four Weekly Comedi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1962, 63.
Shaub, Earl L. “Tennessee’s Vanishing Mountaineer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Weekly Magazine, February 20, 1943, 8–9.
Shayon, Robert Lewis. “Innocent Jeremiah.” Saturday Review, January 5, 1963, 32.
Sheppard, Muriel Earley. Cabins in the Laure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5.
Sherman, Mandel, and Thomas R. Henry. Hollow Folk. 1933. Reprint, Berryville, VA: Virginia Book Company, 1973.
Sherwood, Herbert Francis. “Our New Racial Drama: Southern Mountaineers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North American Review, October 1922, 489–96.
Silcox, Segil Glenn. A Hillbilly Marine. N.p., 1977.
Simon, Charlie May. “Retreat to the Land—An Experience in Poverty.” Scribner’s Magazine, May 1933, 309–12.
Simpich, Frederick. “Land of a Million Smiles.”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May 1943, 589–623.
Smith, Arthur. “‘Hill Billy’ Folk Music—A Little-Known American Type.” The Etude, March 1933, 154, 208.
Smith, Beverly, Jr. “The Change in the Mountains.”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28, 1964, 60–62.
Somerndike, J. M.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March 1928, 198–203.
“Southern Highlands—Special Issue.” House and Garden, June 1942, 1–51.
“The Southern Highlands: A Short History.” National Parks & Conservation Magazine, July 1971, 5.
Spaulding, Arthur W. The Men of the Mountains. Nashville: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5.
“Special Hillbilly Issue.” Western Folklore, July 1971.
“Sprightly Comics Really Middle-Aged.” Editor and Publisher, July 21, 1934, 306–7.
“Stark Love.” Variety, March 2, 1927.
“‘Stark Love’—Interesting and Absorbing Drama of Primitive Life of Mountaineers, Acted by a Native Cast.” Moving Picture World, March 19, 1927, 214.
Starr, Fred. Of These Hills and Us. Boston: Christopher Publishing House, 1958.
Staunton, Helen M. “Editors, Specialists Discuss the Comics.” Editor and Publisher, November 22, 1947, 40.
Steele, Harry.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Hillbilly Business.” Radio Guide (1936): 20–21, 42. Reprinted in JEMF Quarterly 10, pt. 2 (Summer 1974): 51–54.
Steinbeck, John. “Introduction.” In Al Capp, The World of Li’l Abner. N.p.: Capp Enterprises, 1953.
Stepmann, Charles A. “What Is Wrong with TV—and with U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9, 1964, 13+.
Strong, Phil. “The Friendly Ozarks.” Holiday, August 1951, 90–97+.
Strother, David Hunter. “A Winter in the South.”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15 (1857): 433–51; 594–606; 721–40; 16 (1858): 167–83; 721–36.
“The Subject Is Television.” TV Guide, July 20, 1963, 15–27.
Swift, W. H. “The Campaign in North Carolina. The Mountain Whites—By One of Them.” Child Labor Bulletin, May 1913, 96–104.
“Tain’t Funny.” Time, September 29, 1947, 79.
Tannenbaum, Frank. Darker Phases of the South.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1969.
Tarcher, J. D. “The Serious Side of the Comic-Strip.” Printer’s Ink, April 28, 1932, 3–6.
Taylor, Barbara, Mary Thomas, and Laurie Branson. “‘He Shouted Loud, “Hosanna, DELIVERANCE Will Come”.’” Foxfire 7, no. 4 (Winter 1973): Special Insert, n.p.
“There Are No 100% Americans.” Collier’s Magazine, July 26, 1941, 58.
These Are Our Lives (as Told by the People and Written by Members of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of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in North Carolina, Tennessee, and Georg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
“They Love Mountain Music.” Time Magazine, May 7, 1956, 60.
“They’re Still Single.” TV Guide, February 27, 1965, 22–24.
“This Is the Real McCoy.” TV Guide, August 2, 1958, 20–23.
Thomas, Jean. “The Changing Mountain Folk.” American Mercury, July 1945, 43–49.
Thompson, Lovell. “America’s Day-Dream.”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November 13, 1937, 3–4, 16.
______. “How Serious Are the Comics.”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42, 127–29.
Thompson, Samuel H. The Highlanders of the South. New York: Eaton & Mains, 1910.
Thornborough, Laura. “Americans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got.” Travel, April 1928, 25–28, 42.
“Thousands Expected Here for ‘Hillbilly Days.’” Pike County News, March 31, 1977, 1:1, 1:3.
Tommasini, Anthony. “Those Backwater Folks, Happily Dispensable.”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98, A-13.
Trotter, Margaret. “Appalachia Speaking.” Mountain Life and Work, October 1937, 25–27.
Tunley, Roul. “The Strange Case of West Virginia.”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6, 1960, 19–21, 64–66.
Ulmann, Doris (photographer). “The Mountaineers of Kentucky—A Series of Portrait Studies.” Scribner’s Magazine, June 1928, 675–81.
Vaughn, Marshall Everett. “Purpose of This Magazine.” Mountain Life and Work, April 1925, 2–3.
Verde, Tom. “98 Moonshiners Add Drugs and Guns to the Recip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98, A-12.
Vincent, George E. “A Retarded Fronti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 no. 1 (1898): 1–20.
Vlamos, James Frank. “The Sad Case of the Funnies.” American Mercury, April 1941, 411–16.
Votaw, Albert N. “The Hillbillies Invade Chicago.” Harper’s Magazine, February 1958, 64–67.
Wallace, Henry A. “Racial Theories and the Genetic Basis for Democracy.” Science, February 17, 1939, 140–43.
Warner, Charles Dudley. “On Horseback.” Atlantic Monthly, July–October 1885, 88–100, 194–207, 388–98.
______. “Comments on Kentucky.”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January 1889, 255–71.
Watkins, Floyd C. Yesterday in the Hills.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
Watterson, Henry. Oddities in Southern Life and Charact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0.
Webb, Paul. “Hillbillies in the Bigtime Feud.” Esquire, December 1943, 10.
Weller, Jack E. Yesterday’s People—Life in Contemporary Appalachi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65.
Wenrick, Lewis A. “Teaching the Mountaineers of Tennesse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October 1922, 811–12.
Wentworth, Harold. American Dialect Dictiona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44.
“When Whites Migrate from the South.”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14, 1963, 70–73.
Whitney, Dwight. “It’s about the Atavistic Urge.” TV Guide, January 8, 1966, 16–19.
______. “The Simple Virtues Are Back in Style.” TV Guide, April 28, 1973, 24–28.
Wiggam, Albert Edward. “The Rising Tide of Degeneracy—What Everybody Ought to Know about Eugenics.” World’s Work, November 1926, 25–33.
Wightman, Reverend Robert S. “The Southern Mountain Problem—A Study of the Efforts to Solve a Great Unfinished Task.”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February 1922, 120–26.
Wilds, Reverend J. T. “The Mountain Whites of the South.”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December 1895, 921–23.
William Byrd’s Histories of the Dividing Line betwixt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7.
Williamson, Gladys Parker. “Living Memorials to Abraham Lincoln—Teaching Independence, Industry and Christian Service at Cumberland Gap.”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April 1923, 279–82.
Wilson, Charles Morrow. “Moonshiners(私酿酒者).” Outlook and Independent, December 19, 1928, 1350–52, 1381.
______. “Backwoods Morality.” Outlook and Independent, January 9, 1929, 65–67, 80.
______. “Backhill Culture.” The Nation, July 17, 1929, 63–65.
______. “Elizabethan America.”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29, 238–44. Reprinted in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ed. W. K. McNeil, 205–14.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______. Backwoods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4.
Wilson, Liza, and David McClure. “Ma and Pa Kettle—Hollywood Goldmine.” Collier’s, December 8, 1951, 22+.
Wilson, Samuel Tyndale.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s. New York: Literature Department—Presbyterian Home Missions, 1914.
Wobus, Paul A. “Experiences among Ozark Mountaineer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June 1939, 282–85.
Woodward, C. Vann. “Hillbilly Realism.” Southern Review 4 (1938/1939): 676–81.
“Yokum Gold.” Newsweek, July 21, 1947, 54.
Zolotow, Maurice. “Hillbilly Boom.”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12, 1944, 22–23+.
Alvey, Mark. “The Independents: Rethinking the Television Studio System.” In The Revolution Wasn’t Televised—Sixties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flict, ed. Lynn Spigel and Michael Curtin, 139–58.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Amossy, Ruth. “Commonplace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ubStance 62/63 (1990): 145–56.
Archdeacon, Thomas J. Becoming American—An Ethn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Arnold, Edwin T. “Al, Abner, and Appalachia.” Appalachian Journal 17, no. 3 (1990): 262–75.
______. “Abner Unpinned—Al Capp’s Li’l Abner, 1940–1955.” Appalachian Journal 24, no. 4 (1997): 420–36.
Arnow, Pat. “The Hills Meet Hollywood—The Now and Then Guide to Selected Feature Films about Appalachia.” Now and Then 8, no. 3 (1991): 8–12.
Asbell, Bernard. “The Vanishing Hillbilly(乡巴佬).”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23, 1961, 92–95.
Askins, Donald. “John Fox, Jr.: A Re-Appraisal; or, With Friends Like That, Who Needs Enemies.” Mountain Review, Winter 1975, 15–16.
Austin, Wade. “The Real Beverly Hillbillies.” Southern Quarterly 19, no. 3–4 (1981): 83–94.
Averill, Patricia. “Folk and Popular Elements in Modern Country Music.”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5, no. 2 (1975): 43–54.
Balio, Tino 编. 电视时代的好莱坞. 波士顿: Unwin Hyman, 1990.
Banes, Ruth A. “Doris Ulmann和她的山地民众.” 美国文化杂志 8 (1985年春): 29–42.
Barnouw, Erik. 影像帝国——美国广播史(第3卷——1953年起).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
______. 纪录片——非虚构电影史.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Baron, Robert 和 Nicholas R. Spitzer 编. 公共民俗. 华盛顿特区: 史密森学会出版社, 1992.
Barsam, Richard Meran. 非虚构电影——批评史. 纽约: E. P. Dutton, 1973.
Bartlett, Richard. “丹尼尔·布恩.” 载于 美国历史读者指南, Eric Foner 和 John Garraty 编, 122–23. 波士顿: Houghton Mifflin, 1991.
Batteau, Allen. “阿巴拉契亚与文化概念:共同误解理论.” 阿巴拉契亚杂志 7, 第1–2期 (1979–1980年秋冬): 9–31.
______ 编. 阿巴拉契亚与美国——自治与区域依赖. 列克星敦: 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3.
______. 阿巴拉契亚的发明. 图森: 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 1990.
Baughman, James L. 大众文化共和国——1941年以来美国的新闻、电影制作与广播. 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Baughman, Ronald. 理解詹姆斯·迪基. 哥伦比亚: 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85.
Becker, Jane S. 贩卖传统:阿巴拉契亚与美国民俗的建构,1930–1940. 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8.
Belcher, Anndrena. “相对陌生——《近亲》片场记.” 此时彼刻——阿巴拉契亚杂志, 1991年秋, 22, 25–26.
Belton, John. 美国电影/美国文化. 纽约: McGraw-Hill, 1994.
Berger, Arthur Asa. 小阿布纳——美国讽刺研究. 纽约: Twayne, 1970.
Bernardi, Daniel 编. 白人性的诞生——种族与美国电影的兴起. 新布伦瑞克: 罗格斯大学出版社, 1996.
______. “白人性之声:D. W. 格里菲斯的传记影片(1908–1913).” 载于 白人性的诞生:种族与美国电影的兴起, Daniel Bernardi 编, 103–28. 新布伦瑞克: 罗格斯大学出版社, 1996.
Bertrand, Michael T. 种族、摇滚与猫王. 厄巴纳: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2000.
Billings, Dwight B., Gurney Norman 和 Katherine Ledford 编. 直面阿巴拉契亚刻板印象——来自美国一个地区的反驳. 列克星敦: 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99.
Billings, Dwight B., Mary Beth Pudup 和 Altina L. Waller. “对例外论的例外——阿巴拉契亚历史研究的兴起与转变.” 载于 阿巴拉契亚的形成——十九世纪的南部山区, Dwight B. Billings, Mary Beth Pudup 和 Altina L. Waller 编, 1–24. 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5.
Biskind, Peter. 眼见为实——好莱坞如何教我们停止担忧并爱上五十年代. 纽约: Pantheon Books, 1983.
Blackbeard, Bill. “那些山里人:阿布纳、利未提库斯、斯纳菲——(喘气!)看看阿尔·卡普释放了什么.” 载于 小阿布纳日报:第3卷(1937), 3–7. 普林斯顿, 威斯康星: Kitchen Sink Press, 1988.
Blair, Walter. 美国本土幽默(1800–1900). 纽约: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7.
______. 美国幽默论文集——布莱尔穿越时代. 麦迪逊: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93.
Blair, Walter 和 Hamlin Hill. 美国的幽默——从穷理查到杜恩斯伯里.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8.
Blevins, Brooks. 山地民众:阿肯色奥扎克人及其形象史. 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2002.
Bloom, Alan. 美国精神的封闭. 纽约: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Bogart, Leo. 电视时代. 纽约: Frederick Ungar, 1972.
Boskin, Joseph 和 Joseph Dorinson. “族裔幽默:颠覆与生存.” 美国季刊 37, 第1期 (1985): 81–97.
Bowler, Betty Miller. “‘那条社会忽视的丝带’:1964年的阿巴拉契亚与媒体.” 阿巴拉契亚杂志 12, 第3期 (1985): 239–47.
Boyer, Paul. 城市大众与美国的道德秩序,1820–1920.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8.
Bradley, Donald S., Jacqueline Boles 和 Christopher Jones. “从情妇到妓女:男性杂志中40年的卡通幽默.” 质性社会学 (1979年9月): 42–62.
Brauer, Carl M. “肯尼迪、约翰逊与反贫困战争.” 美国历史杂志 69 (1982年6月): 98–119.
Breazeale, Kenon. “尽管有女性:《时尚先生》杂志与男性消费者的建构.” 符号 20, 第1期 (1994): 1–22.
Brodbeck, Arthur J. 和 David M. White. “如何聪明地阅读小阿布纳.” 载于 大众文化——美国的流行艺术, Bernard Rosenberg 和 David M. White 编, 218–23. 格伦科, 伊利诺伊: Free Press, 1957.
Bronner, Simon J. 纽约州的老式音乐制作人. 锡拉丘兹: 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1987.
Brooks, Tim 和 Earle Marsh. 黄金时段网络与有线电视节目完全指南——1946至今. 第6版. 纽约: McGraw-Hill, 1982.
Brown, Charles T. 美国音乐——美国乡村与西部传统. 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新泽西: Prentice Hall, 1986.
Brown, James S.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阿巴拉契亚注脚.” 阿巴拉契亚杂志 6, 第1期 (1978): 29–32.
Brown, Karl. “山中好莱坞——《赤裸的爱》的拍摄.” 阿巴拉契亚杂志 18, 第2期 (1991): 170–220.
Brown, Lester. 电视——屏幕背后的生意. 纽约: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Brown, Rodger. “通往骗局之路:美国狗窝镇.” 南方变迁 (1994).
______. 饼干巡回赛上的鬼舞:美国南方的节日文化. 杰克逊: 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 1997.
Brown, Sarah. “The Arkansas Traveller: Southwest Humor on Canva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46, no. 4 (1987): 348–75.
Brownlow, Kevin. The War, the West, and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______. Introduction to “Hollywood in the Hills—The Making of Stark Love.” Appalachian Journal 18, no. 2 (1991): 171–73.
Brundage, W. Fitzhugh. “Racial Violence, Lynchings,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Mountain South.” In Appalachians and Race: The Mountain South from Slavery to Segregation, ed. John Inscoe, 302–1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Bryant, John. “Situation Comedy of the Sixties: The Evolution of a Popular Genre.” Studies in American Humor n.s., 7 (1989): 118–39.
Cantwell, Robert. When We Were Good: The Folk Reviv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arawan, Guy, and Candie Carawan. Voices from the Mountai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5.
Carlton, David L., and Peter A. Coclanis. Confronting Southern Povert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South with Related Documents. The Bedford Serie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6.
Caron, James E., and M. Thomas Inge, eds. Sut Lovingood’s Nat’ral Born Yarnspinner: Essays on George Washington Harri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6.
Carr, Patrick, ed.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ountry Music.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Cassidy, Frederic G.,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Regional English. Vol. 2.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1.
Castleman, Harry, and Walter J. Podrazik. Watching TV—Four Decades of American Tele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2.
Chappell, Fred. “The Ninety-Ninth Foxfire Book.” Appalachian Journal 11, no. 3 (1984): 260–67.
Chase, Allan. “Eugenics vs. Poor White Trash—The Great Pellagra Cover-Up.” Psychology Today, February 1975, 83–86.
Ching, Barbara. Wrong’s What I Do Best: Hard Country Music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labough, Casey Howard. Elements: The Novels of James Dickey.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Cobb, James C. “From Muskogee to Luckenbach: Country Music and the ‘Southernization’ of America.”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6, no. 3 (1982): 81–91.
Coben, Stanley. Rebellion against Victorianism—The Impetus for Cultural Change in 1920s America.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ohen, Henning, and William B. Dillingham. Humor of the Old Southwes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4.
Cohen, Norman. “The Skillet Lickers: A Study of a Hillbilly String Band and Its Repertoi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8, no. 309 (1965): 229–44.
______. “Early Pioneers.” In Stars of Country Music—Uncle Dave Macon to Johnny Rodriguez, ed. Bill C. Malone and Judith McCulloh, 11–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Coles, Robert. Migrants, Sharecroppers, Mountaine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______. The South Goes North.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Collins, Glenn. “Ya-hooo! A Marketing Coup—At 50, Mountain Dew Manages to Tickle Innards of Young Me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30, 1995, C1+.
Coltman, Robert. “Sweethearts of the Hills: Women in Early Country Music.” JEMF Quarterly 14, no. 52 (1978): 161–80.
Cook, Sylvia Jenkins. From Tobacco Road to Route 66: The Southern Poor White in Fic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6.
Cooper, B. Lee. Popular Music Perspectives: Ideas, Themes, and Patterns in Contemporary Lyrics.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91.
Cox, John Harrington, ed. Folk-Songs of the South. Hatboro, PA: Folklore Associates, 1963.
Cox, Stephen.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Culture Wars—David Hackett Fischer’s Albion’s Seed.” Appalachian Journal 19, no. 2 (1992): 161–200.
Cumming, William P., ed. The Discoveries of John Lederer.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58.
Cunningham, Rodger. “Eat Grits and Die; or, Cracker, Your Breed Ain’t Hermeneutical.” Appalachian Journal 17, no. 2 (1990): 176–82.
______. “Scotch-Irish and Others.” Appalachian Journal 18, no. 1 (1990): 84–90.
______. “Signs of Civilization: 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 as Colonial Narrative.” Journal of the Appalachian Studies Association 2 (1990): 21–46.
Curtis, L. Perry, Jr. Apes and Angels: The Irishman in Victorian Caricatur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7.
Cusic, Don. “Comedy and Humor in Country Music.”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16, no. 2 (1993): 45–50.
Dale, E. E. “Arkansas: The Myth and the State.”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12, no. 1 (1953): 8–29.
Daniel, Pete.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Southern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______. Lost Revolutions: The South in the 1950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or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2000.
Daniel, Wayne W. “George Daniell’s Hill Billies: The Band That Named the Music?” JEMF Quarterly 19, no. 73 (1983): 81–84.
______. “The National Barn Dance on Network Radio: The 1930s.”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9, no. 3 (1983): 47–62.
______. Pickin’ on Peachtree—A History of Country Music in Atlanta, Georgi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Davis, Lloyd. “When Country Wasn’t Cool.” Southern Quarterly 22, no. 3 (1984): 158–72.
Day, Donald. “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Harris,”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6 (1947): 3–38. Reprinted in Sut Lovingood’s Nat’ral Born Yarnspinner: Essays on George Washington Harris, ed. James E. Caron and M. Thomas Inge, 33–68.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6.
Day, Ronnie. “Pride and Poverty: An Impressionistic View of the Family in the Cumberlands of Appalachia.” 载于 Appalachia Inside Out—Culture and Custom,Robert J. Higgs、Ambrose N. Manning 和 Jim Wayne Miller 编,370–76。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95年。
DeLoria, Philip J. Playing India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Denisoff, Serge. Great Day Coming: Folk Music and the American Left。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1年。
Dew, Lee A. “On a Slow Train through Arkansaw—The Negative Image of Arkansa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35, no. 2 (1980): 125–35。
Documentary Film Classics—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华盛顿特区:国家视听中心,1980年。
Dorman, Robert L. Revolt of the Provinces: The Region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
Dorson, Richard M. American Folklore and the Historia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
Douglas, Susan J. “Radio and Television.” 载于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Eric Foner 和 John A. Garraty 编,903–6。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91年。
______. Where the Girls Are: Growing Up Female with the Mass Media。纽约:三河出版社,1994年。
Dower, John W.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万神殿图书,1986年。
Drake, Richard B. A History of Appalachia。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1年。
Dumenil, Lynn. The Modern Temper—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1920s。纽约:希尔与王出版社,1995年。
Dunn, Durwood. “Mary Noailles Murfree: A Reappraisal.” Appalachian Journal 6, no. 3 (1979): 197–204。
Dyer, Richard. The Matter of Images—Essays on Representations。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3年。
Eby, Cecil D., Jr. “Porte Crayon”: The Life of David Hunter Strother。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0年。
Eisner, Joel 和 David Krinsky. Television Comedy Series—An Episode Guide to 153 TV Sitcoms in Syndication。杰斐逊,北卡罗来纳州:麦克法兰出版公司,1984年。
Eller, Ronald D. Miners, Millhands and Mountaineer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ppalachian South, 1880–1930。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1年。
Ely, Melvin Patrick. The Adventures of Amos ‘n’ Andy—A Social History of an American Phenomenon。纽约:自由出版社,1991年。
Everson, William K. American Silent Film,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il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
Falk, Paul Hastings 编. Who Was Who in American Art。纽约:Sound View 出版社,1985年。
Faragher, John Mack. Daniel Boone: The Life and Legend of an American Pioneer。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92年。
Farber, David. The Age of Great Dreams—America in the 1960s。纽约:希尔与王出版社,1994年。
Fields, Armond 和 L. Marc Fields. From the Bowery to Broadway: Lew Fields and the Roots of American Popular Theate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Fisher, Stephen L. 编. 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Traditions of Resistance and Change。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
Fisher, Stephen S. “The Grass Roots Speak Back.” 载于 Confronting Appalachian Stereotypes—Back Talk from an American Region,Dwight B. Billings、Gurney Norman 和 Katherine Ledford 编,203–14。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99年。
Fishkin, Shelley Fisher. “Interrogating ‘Whiteness,’ Complicating ‘Blackness’: Remapping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Quarterly 47 (September 1995): 428–66。
Fiske, John. Reading the Popular。波士顿:Unwin Hyman 出版社,1989年。
Flynn, Charles 和 Todd McCarthy. “The Economic Imperative: Why Was the B Movie Necessary?” 载于 King of the Bs—Working within the Hollywood System,Todd McCarthy 和 Charles Flynn 编,13–43。纽约:E. P. 达顿出版社,1975年。
Flynt, J. Wayne. Dixie’s Forgotten People—The South’s Poor Whites。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
______. Poor but Proud—Alabama’s Poor Whites。塔斯卡卢萨: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9年。
Foley, Neil. The White Scourge: Mexicans, Blacks, and Poor Whites in Texas Cotton Cultur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
Ford, Thomas R. 编. The Southern Appalachian Region—A Survey。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62年。
Frankenberg, Ruth.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
Frierson, Michael. “The Image of the Hillbilly in Warner Bros. Cartoons of the Thirties.” 载于 Reading the Rabbit: Exploration in Warner Bros. Animation,Kevin S. Sandler 编,86–100。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
Genovese, Eugene D. “‘Rather Be a Nigger Than a Poor White Man’: Slave Perceptions of Southern Yeomen and Poor Whites.” 载于 Toward a New View of America—Essays in Honor of Arthur C. Cole,Hans L. Trefousse 编,79–95。纽约:伯特·富兰克林出版社,1977年。
Gitlin, Todd. “The Turn toward ‘Relevance.’” 载于 Inside Prime Time,203–20。纽约:万神殿图书,1983年。
Glen, John M. “The War on Poverty in Appalachia—A Preliminary Report.” Register of the Kentucky Historical Society 87 (Winter 1989): 40–57。
Glenn, Max E. 编. Appalachia in Transition。圣路易斯:伯大尼出版社,1970年。
Goad, Jim. The Redneck Manifesto。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7年。
Goldstein, Kalman. “Al Capp and Walt Kelly: Pioneer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atire in the Comics.”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5, no. 4 (1992): 81–95。
Gorn, Elliot J. “‘Gouge and Bite, Pull Hair and Scratch’: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Fighting in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0, no. 1 (1985): 18–43。
Goulart, Ron. The Adventurous Decade。纽约:阿灵顿之家出版社,1975年。
Graham, Allison. Framing the South: Hollywood, Television, and Race during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
Graham, Hugh D., and Ted R. Gurr, eds.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9.
Graham, S. Keith. “Tale a Mixed Blessing for Rabun County.”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March 18, 1990, M1+.
Green, Archie. “Hillbilly Music: Source and Symbol.”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8, no. 309 (1965): 204–28.
______. “Commercial Music Graphics: Sixteen.” JEMF Quarterly 7, no. 21 (1971): 23–26.
______. “Portraits of Appalachian Musicians.” JEMF Quarterly 15, no. 54 (1979): 99–106.
______. “Farewell Tony.” JEMF Quarterly 19, no. 72 (1983): 231–40.
______. “Graphics #67: The Visual Arkansas Traveler.” JEMF Quarterly 21, no. 75/76 (1985): 31–46.
Green, Douglas B. Country Roots—The Origins of Country Music.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6.
______. “The Singing Cowboy: An American Dream.”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7, no. 2 (1978): 4–61.
Gregory, James N. American Exodus—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______. “The Southern Diaspora and the Urban Dispossessed: Demonstrating the Census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June 1995): 111–34.
Grieveson, Lee. “Why the Audience Mattered in Chicago in 1907.” In American Movie Audiences: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the Early Sound Era, ed. Melvyn Stokes and Richard Maltby, 79–91.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9.
Griffis, Ken. “The Charlie Quirk 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Beverly Hill Billies.” JEMF Quarterly 8, no. 28 (1972): 173–78.
______. “The Beverly Hill Billies.” JEMF Quarterly 16, no. 57 (1980): 3–17.
Grundy, Pamela. “‘We Always Tried to Be Good People’: Respectability, Crazy Water Crystals, and Hillbilly Music on the Air 1933–1935.”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 (March 1995): 1591–1620.
Guy, Roger. “The Media, the Police, and Southern White Migrant Identity in Chicago, 1955–1970.”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6, no. 3 (2000): 329–49.
Hackney, Sheldon. “The South as a Counterculture.” American Scholar 42, no. 2 (1973): 283–93.
Hahn, Steven. The Roots of Southern Populism—Yeoman Farm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rgia Upcountry, 1850–18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Hahn, Steven, and Jonathan Prude, eds.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Hale, Grace Elizabeth. Making Whiteness: The Culture of Segregation in the South, 1890–1940. New York: Vintage, 1998.
Hall, Jacquelyn Dowd, et al.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Hammack, David C., and Stanton Wheeler. Social Science in the Making—Essays on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07–197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Hansen, Miriam. Babel and Babylon—Spectatorship in American Silent Fil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Hardy, Charles. “A Brief History of Ethnicity in the Comics.” In Ethnic Images in the Comics, ed. Charles Hardy and Gail F. Stern, 7–10. Philadelphia: The Balch Institute for Ethnic Studies, 1986.
Harrison, Dan, and Bill Habeeb. Inside Mayber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Hart, Henry. James Dickey: The World as a Lie. New York: Picador USA, 2000.
Hartigan, John, Jr. “Name Calling: Objectifying ‘Poor Whites’ and ‘White Trash’ in Detroit.” In White Trash—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ed. Matt Wray and Annalee Newitz, 41–56.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______. Racial Situations: Class Predicaments of Whiteness in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rvey, Robert. The Art of the Funnies: An Aesthetic History.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4.
Harvey, R. C., Milton Caniff, and Al Capp. “Nightowls in the Bullpen.”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2 (1936), 7–11.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8.
Hatfield, Sharon. “Mountain Justice: The Making of a Feminist Icon and a Cultural Scapegoat.” Appalachian Journal 23, no. 1 (1995): 26–47.
Hauck, Richard Boyd. “A Davy Crockett Filmography.” In Davy Crockett: The Man, the Legend, the Legacy, ed. Michael A. Lofaro, 122–23.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5.
Herrin, Dean. “Poor, Proud, and Primitive—Images of Appalachian Domestic Interiors.” I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Furniture, ed. Gerald W. R. Ward, 93–111. New York: W. W. Norton. Published for the Henry Francis DuPont Winterthur Museum, Winterthur, DE, 1988.
Hewitt, Barnard. Theatre USA—1668 to 1957.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Higgs, Robert J., and Ambrose N. Manning, eds. Voices from the Hills—Selected Readings of Southern Appalachia.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5.
Higham, John. Strangers in the Land—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Himmelstein, Hal. Television Myth and the American Mind.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Hobson, Fred C., Jr. Serpent in Eden: H. L. Mencken and the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4.
Holmes, William F. “Moonshining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Georgia, 1889–1895.”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7 (December 1990): 589–611.
Holt, Elvin. “A Coon Alphabet and the Comic Mask of Racial Prejudice.” Studies in American Humor, n.s., 5 (1986–1987): 307–18.
Horn, Maurice. “Li’l Abner in Wartime: The Mystery of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in the Night.”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8 (1942), 5–9.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90.
Horn, Maurice, ed. The World Encyclopedia of Cartoons. Vol. 1–2. New York: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0.
Horstman, Dorothy. Sing Your Heart Out, Country Boy.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6.
Howd, Dean. “Esquire.” 载于 American Mass-Market Magazines,Alan Nourie 和 Barbara Nourie 编,108–15。纽约:Greenwood Press,1990。
Hsiung, David C. Two Worlds in the Tennessee Mountains: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Appalachian Stereotypes。列克星敦: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7。
Huber, Patrick. “A Short History of Redneck: The Fashioning of a Southern White Masculine Identity.” Southern Cultures 1, no. 2 (1995): 144–66。
Hunt, Lynn 编。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Hurst, Jack. Nashville’s Grand Ole Opry。纽约:Harry N. Abrams,1975。
______. “‘Barn Dance’ Days—Remembering the Stars of a Pioneering Chicago Radio Show.” Chicago Tribune Sunday Magazine,1984年8月15日,11。
Hutson, Cecil Kirk. “Cotton Pickin’, Hillbillies and Rednecks: An Analysis of Black Oak Arkansas and the Perpetual Stereotyping of the Rural South.”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17, no. 4 (1993): 47–62。
Ignatiev, Noel.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纽约:Routledge,1995。
Inge, M. Thomas. “Sut and His Illustrators.” 载于 The Lovingood Papers: 1965,Ben Harris McClary 编,26–35。诺克斯维尔: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for the Sut Society),1965。
______. “Comic Strips.” 载于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Culture,Charles Reagan Wilson 和 William Ferris 编,914–15。教堂山: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
______. “Sut Lovingood and Snuffy Smith.” 载于 Inge, Comics as Culture,69–77。杰克逊: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1990。
______. “Sut, Scarlet, and Their Comic Cousins: The South in the Comics Strip.”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19, no. 2 (1996): 153–66。
______. “Al Capp’s South: Appalachian Culture in Li’l Abner.” 载于 Li’l Abner Dailies: Volume 26 (1960),5–26。北安普顿,马萨诸塞州:Kitchen Sink Press,1997。
Inscoe, John. “Race and Rac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ern Appalachia—Myths, Realities, and Ambiguities.” 载于 Appalachia in the Making—The Mountain Sou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Dwight B. Billings, Mary Beth Pudup 和 Altina L. Waller 编,103–31。教堂山: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______. “Olmsted in Appalachia: A Connecticut Yankee Encounters Slavery and Racism in the Southern Highlands, 1854.” 载于 Appalachians and Race: The Mountain South from Slavery to Segregation,John Inscoe 编,154–64。列克星敦: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1。
______ 编。Appalachians and Race: The Mountain South from Slavery to Segregation。列克星敦: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1。
Isserman, Andrew M. “Appalachia Then and Now: Update of ‘The Realities of Deprivation’ Reported to the President in 1964.” Journal of Appalachian Studies 3 (1997): 43–61。
Jacobson, Matthew Frye.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Jenkins, Henry. 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纽约:Routledge,1992。
Jenkins, Henry 和 Kristine Brunovska Karnick. “Introduction: Golden Eras and Blind Spots—Genre, History and Comedy.” 载于 Classical Hollywood Comedy,Henry Jenkins 和 Kristine Brunovska Karnick 编,1–13。纽约:Routledge,1995。
Johns, Elizabeth. American Genre Painting: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纽黑文: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Johnson, Don. “Balanc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in Deliverance.” James Dickey Newsletter 2, no. 2 (1986年春): 17–22。
Johnson, Victoria E. “Citizen Welk: Bubbles, Blue Hair, and Middle America.” 载于 The Revolution Wasn’t Televised—Sixties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flict,Lynn Spigel 和 Michael Curtin 编,265–85。纽约:Routledge,1997。
Jones, Jacqueline. The Dispossessed—America’s Underclasse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纽约:Basic Books,1992。
Jones, Jesse Aquillah. “Say It Ain’t True, Davy! The Real David Crockett vs. the Backwoodsman in Us All.” Appalachian Journal 15, no. 1 (1987): 45–51。
Jones, Loyal. “A Complete Mountaineer.” Appalachian Journal 13, no. 3 (1986): 288–96。
Jones, Steven Loring. “From ‘Under Cork’ to Overcoming: Black Images in the Comics.” 载于 Ethnic Images in the Comics,Charles Hardy 和 Gail F. Stern 编,21–30。费城:The Balch Institute for Ethnic Studies,1986。
Kahn, Ed. “Hillbilly Music: Source and Resourc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8, no. 309 (1965): 257–66。
Kammen, Michael. Mystic Chords of Memory。纽约:Vintage,1991。
Kantrowitz, Stephen. Ben Tillm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hite Supremacy。教堂山: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S.v. “Kemble, Edward Wilson.” 载于 The World Encyclopedia of Cartoons,Maurice Horn 编,332–33。纽约:Gale Research Company,1980。
Kesterson, David B. “A Visit with Radio Humorist Chester Lauck (Lum Edwards).” Studies in American Humor 3, no. 3 (1997): 142–48。
Killian, Lewis. White Southerners。阿默斯特: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5。
Kingsbury, Paul. The Grand Ole Opry History of Country Music。纽约:Villard Books,1995。
Kingsbury, Paul 和 Alan Axelrod 编。Country—The Music and the Musicians。纽约:Abbeville Press,1988。
Klotter, James C. “Feuds in Appalachia: An Overview.” Filson Club History Quarterly 56, no. 3 (1982): 290–317。
______. “The Black South and White Appalachia.” 载于 Blacks in Appalachia,William H. Turner 和 Edward J. Cabbell 编,51–67。列克星敦: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
Koszarski, Richard. An Evening’s Entertainment: The Age of the Silent Feature Picture, 1915–1928。第3卷,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nema。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0。
Lancaster, Bob. “Bare Feet and Slow Trains.” Arkansas Times,1987年6月,34–41, 88–101。
______. The Jungles of Arkansa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Wonder State。费耶特维尔: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89。
Langrall, Peggy. “The Evolution of Country Music.” Charlotte (NC) Observer, October 16, 1985, E-1, E-6.
Levine, Lawrence. “Th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Society: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Audienc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1992): 1369–1429.
______.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Levine, The Unpredictable Past—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 206–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Lewis, George H., ed. All That Glitters: Country Music in America.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93.
______. “The Maine That Never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Popular Myth in Reg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16, no. 2 (1993): 91–99.
Lightfoot, William E. “Belle of the Barn Dance: Reminiscing with Lulu Belle Wiseman Stamey.”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11, no. 1 (1987): 2–15.
Linneman, William R. “Will Roger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Studies in American Humor 3, no. 2–3 (1984): 173–86.
Lipsitz, George. “‘This Ain’t No Sideshow’: Historians and Media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5, no. 2 (1988): 147–61.
______. “Listening to Learn and Learning to Listen: Popular Culture, Cultural Theory, and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42, no. 4 (1990): 615–36.
Lisenby, Foy. “A Survey of Arkansas’s Image Problem.”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30, no. 1 (1971): 60–71.
Lofaro, Michael, ed. Davy Crockett—The Man, the Legend, the Legac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5.
Lofaro, Michael A., and Joe Cummings, eds. Crockett at Two Hundr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Man and the Myth.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9.
Lornell, Kip. “Early Country Music and the Mass Media in Roanoke, Virginia.” American Music 5, no. 4 (1987): 403–16.
Lott, Eric. Love and Theft—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Lynn, Kenneth S. Mark Twain and Southwestern Humo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9.
MacCann, Richard Dyer. The People’s Films—A Political History of U.S. Government Motion Pictures.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3.
MacDonald, Dwight. “Masscult and Midcult.” In Against the Grain, 3–7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MacDonald, J. Fred. One Nation under Televisio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etwork TV.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Magoc, Chris J. “The Machine in the Wasteland.”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19, no. 1 (1991): 25–34.
Malone, Bill C. Country Music USA: A Fifty-Year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r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1968.
______. Southern Music American Music.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9.
______. Singing Cowboys and Musical Mountaineers—Southern Culture and the Roots of Country Music.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
______. Don’t Get above Your Raisin’: Country Music and the Southern Working Cla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Malone, Bill C., and Judith McCulloh. Stars of Country Music: Uncle Dave Macon to Johnny Rodriguez.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Marc, David. Demographic Vistas—Televi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Rev. e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Marcus, Greil. “Review of Elvis by Albert Goodman.” In The Country Reader: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ed. Paul Kingsbury, 298–305. Nashville: Country Music Foundation Press, 1997.
Marschall, Richard. “Al Capp (1909–1980).” In Marschall, America’s Great Comic-Strip Artists, 237–253.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1989.
Martin, Douglas. “Zeke Manners: ‘Hillbilly’ Who Ruled Radio, Dies at 89.”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2000, 46.
Mason, Bobbie Ann. “Recycling Kentucky.” New Yorker, November 1, 1993, 50–56+.
Mason, Michael, ed. The Country Music Book.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Mast, Gerald. The Comic Mind—Comedy and the Mov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Masterson, James R. Arkansas Folklore—The Arkansas Traveller, Davey Crockett, and Other Legends. 1942. Reprint, Little Rock: Rose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all Tales of Arkansaw.
May, Lary. Screening Out the Past—The Birth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McCraw, Thomas K. Morgan vs. Lilienthal: The Feud within the TVA.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70.
McGee, Marsha G. “Prime Time Dixie: Television’s View of a ‘Simple’ South.”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6, no. 3 (1983): 100–109.
McIlwaine, Shields. The Southern Poor-White: From Lubberland to Tobacco Roa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39.
McKinney, Gordon B. “Industrialization and Violence in Appalachia in the 1890s.” In An Appalachian Symposium: Essays in Honor of Cratis D. Williams, ed. J. W. Williamson, 131–44. Boone, NC: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McNeil, W. K. “Appalachi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ppalachian Journal 5, no. 1 (1977): 55–64.
______. “‘By the Ozark Trail’: The Image of the Ozarks in Popular and Folk Songs.” JEMF Quarterly (Spring/Summer 1985): 20–30.
______, ed. Appalachian Images in Folk and Popular Culture.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______. “Special Issue on the Weaver Brothers and Elviry.” Old Time Country, Winter 1998.
McWhiney, Grady. Cracker Culture—Celtic Ways in the Old South.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
Merrill, Hugh. Esky: The Early Years at Esquir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rtz, Paul E. New Deal Policy and Southern Rural Povert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Miller, Don. B Movi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7.
Miller, Danny. “The Mountain Woman—In Fact and Fiction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ppalachian Heritage 6 (Summer 1978): 48–73; (Fall 1978): 66–72; 7 (Winter 1979): 16–21.
Miller, Wilbur R. Revenuers and Moonshiners—Enforcing Federal Liquor Laws in the Mountain South, 1865–190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Mintz, Lawrence E. “Situation Comedy.” In TV Genres—A Handbook and Reference Guide, ed. Brian G. Rose, 107–29.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5.
______. “Humor and Ethnic Stereotypes in Vaudeville and Burlesque.” MELUS 21 (1996): 19–28.
Mitchell, Catherine C., and C. Joan Schnyder. “Public Relations for Appalachia: Berea’s Mountain Life and Work.” Journalism Quarterly 66, no. 4 (1989): 974–978, 1049.
Mordden, Ethan. The American Theat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Morgan, Winifred. An American Icon—Brother Jonathan and American Identity.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8.
Morton, David C., and Charles K. Wolfe. “DeFord Bailey: They Turned Me Loose to Root Hog or Die.”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14, no. 2 (1992): 13–17.
Munzer, Martha E. Valley of Vision—The TVA Year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9.
Nesbitt, Eddie. “A History of the Mountain Broadcast and Prairie Recorder.” JEMF Quarterly 18, no. 65/66 (1982): 23–30.
Newby, I. A. Plain Folk in the New South—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Persistence, 1880–191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Newcomb, Horace. TV: The Most Popular Art.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4.
______. “Appalachia on Television: Region as Symbol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ppalachian Journal 7, nos. 1–2 (1979–1980): 155–64.
Nye, Russell. The Unembarrassed Muse—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ork: Dial Press, 1970.
Obermiller, Philip J. “Paving the Way—Urban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age of Appalachians.” In Confronting Appalachian Stereotypes—Back Talk from an American Region, ed. Dwight B. Billings, Gurney Norman, and Katherine Ledford, 251–6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9.
O’Connor, John E., ed.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Television—Interpreting the Video Past.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83.
Oermann, Robert K., and Mary A. Bufwack. “Patsy Monta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wgirl Image.”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8, no. 3 (1981): 18–32.
Otto, John S. “‘Hillbilly Culture’: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 Folk in History and Popular Culture.” Southern Quarterly 24, no. 3 (1986): 25–34.
______. “Plain Folk, Lost Frontiersmen, and Hillbillies: The Southern Mountain Folk in History and Popular Culture.” Southern Studies 26, no. 1 (1987): 5–17.
Otto, John S., and Augustus M. Burns. “Black and White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outh: Race and Hillbilly Music.” Phylon—The Atlanta University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 35, no. 4 (1974): 407–17.
Owsley, Frank Lawrence. Plain Folk of the Old South.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aredes, Americo, and Morton Leeds.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Stripping and Reintegration—The Rural Migrant in the City.” In The Urban Experience and Folk Tradition, ed. Ellen J. Stebert, 165–76.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r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1971.
Parish, James Robert, and William T. Leonard, eds. The Funsters.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9.
Patterson, Timothy A. “Hillbilly Music among the Flatlanders: Early Midwestern Radio Barn Dances.”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6, no. 1 (1975): 12–18.
Pearce, John Ed. Days of Darkness: The Feuds of Eastern Kentuck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4.
Peck, Elisabeth S. Berea’s First 125 Years, 1855–1980.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Pells, Richard. 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Culture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Depress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erdue Jr., Charles L., and Nancy J. Martin-Perdue. “Appalachian Fables and Facts: A Case Study of the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Removals.” Appalachian Journal 7, nos. 1–2 (1979–1980): 84–104.
Peterson, Richard. Creating Country Mus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eterson, Richard A., and Paul DiMaggio. “The Early Opry: Its Hillbilly Image in Fact and Fancy.”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4 (Summer 1973): 39–51.
______. “From Region to Class, the Changing Locus of Country Music: A Test of the Massification Hypothesis.” Social Forces 53, no. 3 (1975): 497–506.
Peterson, Richard A., and Marcus V. Gowan. “What’s in a Country Music Band Name.”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2, no. 4 (1971): 1–9.
Philliber, William W., Clyde B. McCoy, and Harry C. Dillingham, eds. The Invisible Minority—Urban Appalachian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1.
Pieterse, Jan Nederveen. White on Black—Images of Africa and Blacks in Western Popular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later, Ormonde. “The Lovingood Patriarchy.” Appalachian Journal 2 (Spring 1973): 82–93.
Porterfield, Nolan. “Mr. Victor and Mr. Peer.”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7, no. 3 (1978): 3–21.
Precourt, Walter. “The Image of Appalachian Poverty.” In Appalachia and America—Autonomy and Regional Dependence, ed. Allen Batteau, 86–110.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rice, Michael H., and George E. Turner. “Abner Goes Hollywood; Gets Lost in Shuffle.”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6 (1940), 5–13.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9.
Pugh, Ronnie. “Country Music Is Here to Stay?”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19, no. 1 (1997): 32–38.
Quinn, Arthur Hobson. A History of America Dram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23.
Radway, Janice. Reading the Romance—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Randolph, Vance, and George Wilson. Down in the Holler: A Gallery of Ozark Folk Speech.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3.
Reed, John Shelton. Southern Folk, Plain & Fancy—Native White Social Type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Reed, John Shelton, and Daniel Joseph Singal, eds. Regionalism and the South—Selected Papers of Rupert V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Reitberger, Rheinhold, and Wolfgang Fuchs. Comics—Anatomy of a Mass Medium. London: Studio Vista, 1972.
Rickels, Milton. George Washington Harris. New York: Twayne, 1965.
Riddell, Frank S. Appalachia: Its People, Heritage, and Problems. Dubuque: Kendall Hunt, 1974.
Rodgers, Daniel. “In Search of Progressiv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0, no. 4 (1982): 113–32.
Roediger, David 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1991.
______. Towards the Abolition of Whiteness. New York: Verso, 1994.
Rogers, Jimmie. The Country Music Message: Revisited.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89.
Rosaldo, Renat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Rosenberg, Bernard,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Ross, Stephen J. Working-Class Hollywood: Silent Film and the Shaping of Class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______. “The Revolt of the Audience: Reconsidering Audiences and Reception during the Silent Era.” In American Movie Audiences: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the Early Sound Era, ed. Melvyn Stokes and Richard Maltby, 92–111.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9.
Rourke, Constance. American Humor: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1.
Rouse, Sarah, and Katharine Loughney, eds. Three Decades of Television—A Catalog of Television Programs Acquir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9–1979.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9.
Russ, John. “Dogpatch, U.S.A.” (http://www.aristotle.net/~russjohn/attractions/dogpatch.html)
Sackett, Susan. Prime Time Hits—Television’s Most Popular Network Programs. New York: Billboard Books, 1993.
Sagarin, Edward. “The Deviant in the Comic Strip: The Case History of Barney Googl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5, no. 1 (1971): 178–93.
Salstrom, Paul. Appalachia’s Path to Dependency: Rethinking a Region’s Economic History, 1730–1940.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4.
Saxton, Alexand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Class Politics and Mas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Verso, 1991.
Schneirov, Matthew. The Dream of a New Social Order—Popular Magazines in America, 1893–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hreiner, Dave. “The Storyteller.”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1 (1934–1935), 7–12.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8.
______. “1937: Sadie’s First Run.”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3 (1937), 8–9.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8.
______. “1938: Soap and Slapstick.”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4 (1938), 6.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8.
______. “1940: On The Road.” In Li’l Abner Dailies: Vol. 6 (1940), 14–15.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1989.
Schudson, Michael. “The New Valid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Sense and Sentimentality in Academi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 no. 1 (1987): 51–68.
Schuster, Laura, and Sharyn McCrumb. “Appalachian Film List.” Appalachian Journal 11, no. 4 (1984): 329–83.
Seeger, Charles. “The Folkness of the Non-Folk vs. the Non-Folkness of the Folk.” In Folklore and Society—Essays in Honor of Benjamin A. Botkin, 1–9. Hatboro, PA: Folklore Associates, 1966.
Seiter, Ellen. “Stereotypes and the Media: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 (Spring 1986): 14–26.
Selznick, Philip.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Shackelford, Laurel, and Bill Weinberg, eds. Our Appalachi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Shackford, James Atkins. Davy Crockett—The Man and the Lege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Shapiro, Henry D. Appalachia on Our Mind—The Southern Mountains and Mountaineers in the American Consciousness, 1870–192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
______. “John F. Day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Appalachia from the American Consciousness.” Appalachian Journal 10, no. 2 (1983): 157–64.
Silber, Nina. “‘What Does America Need So Much as Americans?’: Race and Northern Reconciliation with Southern Appalachia, 1870–1900.” In Appalachians and Race: The Mountain South from Slavery to Segregation, ed. John Inscoe, 245–58.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Simmon, Scott. The Films of D. W. Griff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lotkin, Richard.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3.
Smyth, Willie. “A Preliminary Index of Country Music Artists and Songs in Commercial Motion Pictures (1928–1953).” JEMF Quarterly 19–20, nos. 70–73 (1983–1984): 88–18, 103–11, 188–96, 241–47.
Solomon, Eric. “Eustace Tilley Sees the Thirties through a Glass Monocle, Lightly: New Yorker Cartoonists and the Depression Years.” Studies in American Humor 3, no. 2–3 (1984): 201–19.
“Special Hillbilly Issu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8, no. 309 (1965).
Speer, Jean Haskell. “‘Hillbilly Sold Here’: Appalachian Folk Culture and Parkway in Tourism.” In Parkway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Proceeding of the Second Biennial Linear Parks Conference, 212–20. Boone, NC: Appalachian Consortium Press, 1987.
______. The Appalachian Photographs of Earl Palmer.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0.
______. “From Stereotype to Regional Hype: Strategies for Changing Media Portrayals of Appalachia.” Journal of Appalachian Studies Association 5 (1993): 12–19. Spigel, Lynn. Make Room for TV—Television and the Family Ideal in Postwar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pigel, Lynn, and Michael Curtin. “Introduction.” In The Revolution Wasn’t Televised—Sixties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flict, ed. Lynn Spigel and Michael Curtin, 1–18.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Spigel, Lynn, and Michael Curtin, eds. The Revolution Wasn’t Televised—Sixties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Staiger, Janet. Interpreting Films—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the American Cinem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earns, Peter N., and Mark Knapp. “Men and Romantic Love: Pinpointing a 20th Century Chan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6 (Summer 1993): 769–95.
Stott, William.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Summers, Harrison B., ed. A Thirty-Year History of Programs Carried on National Radio Net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6–1956.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971.
Susman, Warren. “The Culture of the Thirties.” In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150–83.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Terrill, Tom E., and Jerrold Hirsch, eds. Such as Us—Southern Voices of the Thir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
Tindall, George B. “The Benighted South: Origins of a Modern Imag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40 (Spring 1964): 281–94.
Titus, Warren. John Fox, Jr. New York: Twayne, 1971.
Toll, Robert. Blacking Up—The Minstrel Sho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______. The Entertainment Machine—American Show Busines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oplin, Robert Brent, ed. Hollywood as Mirror—Changing Views of “Outsiders” and “Enemies” in American Movi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3.
Tosches, Nick. Country—The Biggest Music in America.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7.
Trachtenberg, Alan. Reading American Photographs: Images as History—Mathew Brady to Walker Ev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Tribe, Ivan M. “The Hillbilly versus the City: Urban Images in Country Music.” JEMF Quarterly 10, no. 34 (1974): 41–54.
Usai, Paolo Cherchi, ed. The Griffith Project. Vol. 5 (Films produced in 1911). New York: BFI Publishing, 2001.
Verschuure, Eric Peter. “Stumble, Bumble, Mumble: TV’s Image of the South.”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6, no. 3 (1982): 92–96.
Walker, Brian. Barney Google and Snuffy Smith—75 Years of an American Legend. Wilton, CT: Comicana Books and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1994.
Walle, Alf H. “Devolution and Evolution: Hillbillies and Cowboys as American Savages.” Kentucky Folklore Record 32, no. 1 (1986): 58–68.
Waller, Altina L. Feud—Hatfields, McCoys, and Social Change in Appalachia, 1860–190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______. “The Hatfield-McCoy Feud.” In True Stories from the American Past, ed. William Graebner, 35–54.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______. “Feuding in Appalachia—Evolution of a Cultural Stereotype.” In Appalachia in the Making—The Mountain Sou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Dwight B. Billings, Mary Beth Pudup, and Altina L. Waller, 34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Waller, Gregory. “Hillbilly Music and Will Rogers: Small-town Picture Shows in the 1930s.” In American Movie Audiences, ed. Malvyn Stokes and Richard Maltby, 164–79.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9.
Walls, David S., and John B. Stephenson, eds. Appalachia in the Sixties—Decade of Reawakening.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2.
Ward, William S. A Literary History of Kentuck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Warfel, Harry R., and G. Harrison Orians, eds. American Local-Color Stori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41.
Warren-Findley, Janelle. “Musicians and Mountaineers: The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s Music Program in Appalachia, 1935–37.” Appalachian Journal 7, nos. 1–2 (1979–1980): 105–23.
Watkins, Charles Alan. “Merchandising the Mountaineer—Photography,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Cabins in the Laurel.” Appalachian Journal 12, no. 3 (1985): 215–38.
Watson, Mary Ann. The Expanding Vista—American Television in the Kennedy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ead, George, and George Lewis. The Film Career of Buster Keaton. Boston: G. K. Hall, 1977.
Weibe, Robert H.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Whisnant, David E. “Finding the Wa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Mountain Dance and Folk Festival and Bascom Lamar Lunsford’s Work as a Citizen.” Appalachian Journal 7, nos. 1–2 (1979–1980): 135–54.
______. Modernizing the Mountaineer: People, Power, and Planning in Appalachia. Boone, NC: Appalachian Consortium Press, 1980.
______. 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n American Reg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White, David Manning, and Robert H. Abel. The Funnies—An American Idio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Wiggins, Gene. Fiddlin’ Georgia Crazy—Fiddlin’ John Carson, His Real World, and the World of His Song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Wilgus, D. 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llbilly Music.”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8, no. 309 (1965): 195–203.
______. “The Hillbilly Movement.” In Our Living Trad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Folklore, ed. Tristram Potter Coffin, 263–71.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______. “Country-Western Music and the Urban Hillbilly.” In The Urban Experience and Folk Tradition, ed. Ellen J. Stebert, 137–5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r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1970.
Williams, C. Fred. “The Bear State Image: Arkans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35, no. 2 (1980): 99–111.
Williams, Cratis.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 in Fact and Fiction.” Edited by Martha H. Pipes. Appalachian Journal 3, nos. 1–4 (Fall 1975–Summer 1976): 8–61; 100–162; 186–261; 334–92.
Williams, John Alexander. Appalachia: A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Williams, Martin. “The Hidden World of ‘Li’l Abner.’” Comics Journal 147 (1991): 74–76.
Williamson, J. W., ed. An Appalachian Symposium: Essays in Honor of Cratis D. Williams. Boone, NC: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liamson, J. W. Southern Mountaineers in Silent Films: Plot Synopses of Movies about Moonshining, Feuding, and Other Mountain Topics, 1904–1929.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1994.
______. Hillbillyland—What the Movies Did to the Mountains and What the Mountains Did to the Mov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______. “Southern Mountaineers Filmography (1904–1995).” W. L. Eury Appalachian Collection, Belk Library,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library.appstate.edu/appcoll/filmography.html)
Wilson, Charles Reagan, and William Ferris, eds.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Wilson, Christopher. “The Rhetoric of Consumption: Mass-Market Magazines and the Demise of the Gentle Reader.” In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 ed. Richard Wightman Fox and T. J. Jackson Lears, 41–6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Wilson, Darlene. “The Felicitous Convergence of Mythma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John Fox, Jr.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Other) Almost-White American Underclass.” Journal of Appalachian Studies 1 (1995): 5–44.
Wolfe, Charles K. “Nashville and Country Music, 1926–1930: Notes on Early Nashville Media and Its Response to Old-Time Music.”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4, no. 1 (1973): 2–16.
______. “Clayton McMichen: Reluctant Hillbilly.” Bluegrass Unlimited (May 1979): 56–61.
______. “Take Me Back to Renfro Valley.”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9, no. 3 (1983): 9–27.
______. “The White Man’s Blues, 1922–1940.”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15, no. 3 (1993): 38–44.
______. “The Legend That Peer Built: Reappraising the Bristol Sessions.” In The Country Reader: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Journal of Country Music, ed. Paul Kingsbury, 3–18. Nashville: Country Music Foundation Press, 1997.
______. A Good-Natured Riot: The Birth of the Grand Ole Opry. Nashville: Country Music Foundation and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99.
Woll, Allen L., and Randall M. Miller. Ethnic and Racial Images in Ame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Historical Essays and Bibliography. New York: Garland, 1987.
Wood, Gerald C. “The Pasto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Film before World War II.” Markham Review 12 (Spring 1983): 52–60.
Woodward, C. Vann. The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
______.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Wray, Matt, and Annalee Newitz, eds. White Trash—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Campbell, Gavin J. “Fiddlers and Divas: Music and Culture in New South Atlanta, 1910–192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o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South, Charlottesville, VA, April 1995.
Hsiung, David C. “Iso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Upper East Tennessee, 1780–1860: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ppalachian Characterization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1.
Huber, Patrick J. “Rednecks and Woolhats, Hoosiers and Hillbillies: Working-Class Southern Whites, Language, and the Definition of Identity.”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Columbia, 1992.
Maxwell, Angela. “The South Beheld: The Influence of James Agee on James Dickey.”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2.
McCoy, John.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Al Capp.” Boston University, 1998.
McKinney, Edgar D. “Images, Realiti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ssouri Ozarks, 1920–196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Columbia, 1990.
Perkins, Melody Joy. “Hillbilly Music and Its Components: A Survey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Hillbilly Music Collect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91.
Pugh, Ronnie. “Personal Research for ‘Country Music Is Here to Stay?’” Copy in author’s possession.
Smith, Kermit Stephen. “What It Was Was Real Mountain Music: The Authentic Treatment of Music in the Andy Griffith Show.”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1993.
Stoneback, Harry Robert. “The Hillfolk Tradition and Images of the Hillfolk in American Fiction since 1926.” Ph.D. diss., Vanderbilt University, 1970.
Williams, Cratis D. “The Southern Mountaineer in Fact and Fiction.”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61.
Ballad of a Mountain Man—The Story of Bascom Lamar Lunsford: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1990.
Stranger with a Camera: Appalshop, Inc., 2000.
Strangers and Kin: Appalshop, Inc., 1983.
粗体页码指图片
《阿肯色法官》,162
《阿肯色旅人》,162
《糟糕的乔治亚路》,211
《比利——山地人》,57,64
《一个国家的诞生》,114
《女巫布莱尔》,211
《翻山越岭》(1940),161
《翻山越岭》(1951),166
《手提箱的内容》,62
《篷车》,147
《幼崽》,38
《激流四勇士》。见主索引
《在阿肯色》,162
《蛋与我》,167,170
《鬼玩人》,210
《鬼玩人2》,210
《费迪的家族世仇》,62
《世仇》,142
《世仇傻瓜》,166
《曾经的世仇》,163-64
《禁忌山谷》,60
《乱世佳人》,156
《大奥普里》,101
《愤怒的葡萄》,178-79,188
《草原》,151
《她的原始人》,62
《山地人》(音乐短片),79
《山地人》,145-46,146,149
《山地大力士2》,219
《隔山有眼》,210
《赤脚县的炎夏》,211
《我来自密苏里》,162
《在老密苏里》,162
《大白鲨》,206
《奥扎克的圣女贞德》,162
《肯塔基人》,63
《肯塔基玉米》,152-54
《肯塔基月光》,154-56,155,161
《奥扎克的凯特尔一家》,170
《他们种族的最后一人》,58
《小阿布纳》,166,188,250注33
《凯特尔夫妇》,167,168,169
《凯特尔夫妇回农场》,168,169,170
《凯特尔夫妇进城》,170
《凯特尔夫妇度假》,170
《让我的音乐》,164
“马丁家与科伊家”,164,165
《欺骗小姐》,62
《莫阿纳》,151
《私酒飞车党》,211,213
《私酒县快车》,211
《私酒世仇》,64
《私酒贩子》,58,211
《山地正义》,156-58,157,159,160
《山地疯狂》,142
《山地音乐》,161,162,164
《山地节奏》,163
《山民的荣誉》,59
《他说是谋杀》,166
《北方的纳努克》,151
《没时间当中士》,181
《逃狱三王》,224
《我们的好客》,152,153
《南瓜头》,210
《税务员和他的女孩》,62
《大河》,159
《复仇的种子》,142
《乡下佬约克》,156
《山丘牧羊人》,254注22
《奥扎克牧羊人》,162
《横冲直撞斗飞车》,213
《燃烧的灵魂》,142
《烈火》,156
《赤裸的爱》,147-51,148,149,155,159
《日出》,146-47,151
《摇摆你的女士》,161
《德州电锯杀人狂》,210
《那些山丘》,152
《雷霆山》,142
《雷霆之路》,211,213
《可敬的大卫》,3,143,144,145,184
《孤松小径》,156
《仇恨山谷》,142
《田纳西山谷》,158-59,160
《先知的妻子们》,142
《狼法》,142
《伯恩斯与艾伦》,188
《菲伯·麦基与莫莉》,127,188
《弗莱施曼时间》,90
《大奥普里》,75,80,84,85,89,99,101
《卡夫音乐厅》,188
《拉姆与阿布纳》,127,160
《魔毯时间》,89-90
《全国谷仓舞会》,75,80,81,87,89,91,92,95,96
《伦弗罗山谷谷仓舞会》,81,138
《鲁迪·瓦利秀》,188
“煮卷心菜”,182
“百老汇变乡巴佬”,244注32
“查塔努加布鲁斯”,75
“乔治亚的玉米酒蒸馏器”,76
“疯狂布鲁斯”,241注4
“决斗班卓琴”,208,214
“致命婚礼”,240注2
“争斗、打架和吵闹”,166
“老新英格兰的收获时节”,99
“他是个山地高乔人(带伦巴节拍)”,87
“犹豫布鲁斯”,76
“山地布鲁斯”,76
“山地家庭”,86
“山地热”,101
“山地天堂”,101
“山地摇滚”,217
“六月的山地婚礼”,86
“牧场是我家”,96
“爱尔兰洗衣妇”,92
“约翰酿好酒”,76
“基卡普欢乐汁”,76
“小山地甜心”,86
“小拉蒙娜(山地疯狂)”,217
“山露”,91
“我的山地玫瑰”,87
“别用大棍子打你奶奶”,182
“小路边的老木屋”,74
“在迪克西蜂线上”,73
“泛美布鲁斯”,243注26
“红河谷”,88
“乡巴佬!”,211
“乡巴佬、白袜子和蓝带啤酒”,211
“快跑黑鬼快跑”,74
“水手号笛舞”,92
“自从尤塞尔学会约德尔(他是个犹太山民)”,87
“沉睡的里奥格兰德”,99
“缅因州的雪顶山”,99
“士兵的欢乐”,92
“纺纱房布鲁斯”,73
“草莓骝马”,88
“那些山地人现在是山地威廉姆斯了”,87
“有欢笑有爱的时光”,182
“山中有个山地天堂”,86
“稻草中的火鸡”,92
“沃巴什炮弹”,73
“等火车”,73
“织布房布鲁斯”,73
“当鼠尾草开花时”,88
“野花”,208,240注2
“老97号的残骸”,73
“你是我的阳光”,174
“(你只是)父亲猎枪上的又一个刻痕”,166
“对我来说你还是个山地人”,87
《亚当斯一家》,201
《全家福》,203
《安迪·格里菲斯秀》。见主索引
《贝弗利山人》。见主索引
《鲍勃·卡明斯秀》,174,187,188
“阿巴拉契亚的圣诞节”,185,186
《哈乍德公爵》,211,213-14
《格伦·坎贝尔欢乐时光》,213注49
《戈默·派尔,美国海军陆战队》,199
《乡下人进城》,187,199,203
《嘻哈》,203,217
《太空乔妮》,201
《灵犬莱西》,203
《陆军乐医院》,203
《玛丽·泰勒·摩尔秀》,203
《梅伯里镇》,202
《怪物家族》,201
《我的英雄》,174
《奥斯本一家》,223,225
《佩里·科莫秀》,189
《裙带交界处》,187,199
《真正的贝弗利山人》,11,223-26及反对意见,224-26
《真正的麦考伊一家》。见主索引
《周六夜现场》,206,214
《沃尔顿一家》,205-6
Abbott, Bud,[166]
ABC-TV(美国广播公司),[181],[189]
Achenbach, Joel,[214]
Acuff, Roy,[75],[101]
Adkins, Hasil,[217]
非裔美国人,[13],[156]
对乡村音乐的影响,[71],[72]
对”hillbilly(乡巴佬)“一词的使用,[48],[237n. 3]
对南方贫穷白人的看法,[13],[16],[17],[25]
Agee, James,[164]–[65]
阿拉巴马州,[47],[49],[50],[55]
阿拉莫,[22]
Alderman, Tony,[77],[78],[79],[80],[81]
Allen, James Lane,[30],[31]
艾伦兄弟乐队,[75],[242n. 10]
美国民歌节,[91],[249n. 26]
《美国哥特式》(绘画),[192]
《安迪·格里菲斯秀》,[10],[174],[181]–[84],[183],[184],[186],[187],[197],[199],[202]
山地居民角色,[181]–[82],[184]
与反贫困战争相关的”山民”剧集,[184]
对小镇、全白人南方的正面描绘,[197]
收视率,[181]
小镇角色,[182]
另见 [Bass, Ernest T.];[Darling, Briscoe];[达林一家];[Taylor, Sheriff Andy]
动画片。见 [动画片]
阿巴拉契亚,[8],[9],[10],[13],[22],[41],[42],[54],[120],[199],[201],[202],[203],[214],[224]
被定义为一个独特的地区,[33],[35],[47]
被定义为一个问题地区,[96],[160],[174],[184]–[85],[186]
相关事件,[35],[160],[184]–[85]
被设想为浪漫化过去的遗存,[82],[91]
地理定义,[229n. 2]
以此为背景的文学和非印刷媒体,[19],[60],[112],[125],[137],[151],[160],[186]
媒体对地区形象的建构,[30],[236n. 46]
弗吉尼亚州阿巴拉契亚,[224]
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185]
阿巴拉契亚州立师范学院,[137]
阿巴拉契亚研究的创立,[213]
Appal-PAC,[213]
Arbitron收视率,[198]
Arbuckle, Fatty,[62]
地区发展管理局,[185]
阿肯色州,[9],[13],[21],[22],[28],[47],[203],[214]
与比尔·克林顿,[214]
喜剧演员,[160]–[61]
文学描绘,[25]–[27],[29],[50]–[52],[54]–[55]
与之相关的媒体作品,[123],[174],[223]
阿肯色旅行者,[26]–[28],[27],[28],[182]
不断变化的版本,[27]–[28],[234n. 28]
Bob Burns的绰号,[160]
可能的起源,[233n. 24]
Arnow, Harriete,[138]
Arnow, Pat,[206]
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64],[67],[69],[91],[137],[150]
肯塔基州阿什兰,[91],[218]
亚特兰大,[73],[76],[78],[209]
观众
对山民电影兴趣下降,[63],[142],[143],[151]–[52],[167]
电影中乡巴佬形象日益不被接受,[165]
大众媒体的本质,[221]
山民电影的观众,[163],[168]
读者对乡巴佬形象的反应,[177]
对南方贫穷白人的看法,[112]
另见 乡村音乐
Autry, Gene,[89],[95]
Averback, Hy,[179]
Avery, Tex,[163]
Babcock, Bernice,[51]
《美国边远地区》[Wilson],[121]
Baer, Max,[187],[189],[192],[198]
Bailey, DeFord,[241n. 8],[243n. 26]
Bailey, Raymond,[195]
Ballinger, Drew,[206],[208]
巴尔的摩,[99]
《巴尼·谷歌与斯纳菲·史密斯》,[9],[103],[113],[114],[248n. 15],[248n. 16]
Barrat, Robert,[156],[157]
Barthelmess, Richard,[143],[144],[145]
Bass, Ernest T.,[183]–[84]
Bate, Humphrey博士,[75],[80]
Batteau, Allen,[42]
Bauersfeld, Marjorie “Mirandy”,[88]
Beardsley, Aubrey,[67]
Beason, George,[51]
Beatty, Ned,[208]
“国际信徒”,[220]
Benét, Stephen Vincent,[76]–[77]
“蒙昧的南方”,[109],[118]
Benny, Jack,[174],[257n. 1]
Benton, Thomas Hart,[163]
伯里亚学院,[41],[43],[150]
柏林墙,[193]
Bernstein, Leonard,[190]
贝弗利山乡巴佬乐队,[3],[87],[88],[89],[95]
《贝弗利山庄的乡巴佬》,[10],[174],[175],[178],[181],[184],[186]–[87],[187],[188]–[99],[192],[198],[200],[201],[202],[205]
与非裔美国人,[198]–[99]
观众,[198],[261n. 57]
停播,[202]–[3]
对”美国梦”的挑战与维护,[193]–[97]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187],[194],[196]
以及关于电视质量的争论,[186],[190]
文化中心地位的下降,[201]–[2]
电视半小时节目最高收视率,[193]
以及”乡巴佬”热潮,[199]–[201]
幽默,[190],[191]
缺乏持久的社会批判,[196]–[97],[202]
周边商品,[219]
与新邦联主义,[197]–[99]
试播集,[187],[189],[195]
计划以《真正的贝弗利山庄乡巴佬》重拍,[223]
受欢迎程度,[189]–[90]
媒体反应,[190],[191],[196]
推广的产品,[199]
以及节目宣传,[189]
为观众提供的心理逃避,[193]
收视率,[189]–[90]:Arbitron,[198]
以及对”乡巴佬”的重新定义,[191],[192]
以及暗示的社会运动,[201]–[2]
以及南方山区居民的反应,[203]–[4]
配角,[195]
另见 [Bodine, Jethro];[Clampett, Elly May];[Clampett, Jed];[Drysdale, Margaret];[Drysdale, Milton];[奶奶(Daisy Moses)];[Hathaway, Jane];[Henning, Paul]
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庄,[194],[197],[223]
百代电影公司(美国活动影像与百代公司),[58],[61],[63],[239n. 23]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197]
Blaeholder, Henry “Hank Skillet”,[88]
Blevins, Ruby。见 [Montana, Patsy]。
Bliss, Harry,[217]
蓝鸟唱片,[74],[75],[86]
蓝天男孩,[91]–[92]
Bodine, Jethro,[187],[188],[190],[191],[192],[194],[197],[198],[201]
Bogart, Humphrey,[255n. 32]
Bollick, Bill,[91]。另见 [蓝天男孩]
Bollick, Earl,[91]。另见 [蓝天男孩]
Bond, Johnny,[99]
Boone, Daniel,[21]–[22],[116]
北卡罗来纳州布恩,[137]
Boorman, John, 205, 207-8, 210
Bowery Boys, The, 166
BR 5-49, 101, 217, 263n. 25
Bradley, William Aspenwall, 65-67
Branscome, James, 203-4
Braselton, Al, 207, 209
Brennan, Walter, 178, 179-80
Bristol, Tennessee, 74, 158, 242n. 16
Britt, Elton, 88
百老汇与乡巴佬形象, 254n. 20
Brockman, Polk, 241n. 5
Bronner, Simon, 94
Brooks, Garth, 101
Brooks and Dunn, 101
Brother Jonathan, 14-15, 179
Broun, Heywood, 144
Brown, George. 参见 Hill, Billy
Brown, Karl, 147-51
歪曲事实, 150
对南方山区的无知, 150
Brown and Bigelow, 136
Brown Derby Restaurant, 189
Buchanan, Annabel Morris, 249n. 26
Buck, Charles Neville, 58
Bumppo, Natty, 21
Burnett, Frances Hodgson, 30
Burns, Bob, 160, 161, 162, 163, 164, 188
Burns, Kenneth. 参见 Homer and Jethro
Buttram, Pat, 203
Byrd II, William, 15-16, 25
《秘史》的不同版本, 230n. 3
Caldwell, Christopher, 225
Caldwell, Erskine, 20, 110, 112, 119
加利福尼亚州, 3, 178
Call Me Hillbilly(叫我乡巴佬)[Russell], 212
Campbell, John C., 236n. 46, 240n. 28
Campbell, Robert (牧师), 44
Canova, Judy, 161, 162, 163
Caplin, Alfred Gerald. 参见 Al Capp
Caplin, Elliot, 250n. 35
Capp, Al, 3, 9, 76, 103, 104, 113, 114, 118, 121, 123, 124-26, 127-28, 129-32, 130-31, 132, 133, 134-36, 148, 190
生平背景, 125
对其作品的评论, 127, 133, 251n. 49
收入, 124
影响力, 137-38, 154, 188
民粹主义的局限性, 130-31
角色的起源, 125-26, 250nn. 35, 36
成功, 124-25, 250n. 33
Capra, Frank, 163
Carr, Joseph W., 55
Carson, Fiddlin’ John, 73-74, 76, 77, 78, 101, 242n. 13
Carson, Rosa Lee, 76, 92
Carter, Billy, 212
Carter, Jimmy (James Earl), 209
被嘲笑为乡巴佬, 212
Carter, Maybelle, 240n. 2
Carter Family, 74, 89, 242n. 16
动画片, 163, 255n. 34
印刷漫画, 103-4 (另见 Mountain Boys, The)
Caudill, Harry, 185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85, 186, 187, 189, 199, 202, 205
被视为”乡巴佬电视网”, 203
转向城市题材节目, 203
与《真正的贝弗利乡巴佬》, 223, 224, 225
农村战略中心, 225
Chattooga River, 乔治亚州, 210, 262n. 14
Cheshire, “Pappy” 和他的 Hill Bill Champions 乐队, 86
芝加哥, 80, 82, 84, 113, 116, 126, 175, 176, 177, 219
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新闻联合报业, 126
童工(议题), 56
Chilton, Andrew Guy, 51
辛辛那提, 俄亥俄州, 175, 176, 213, 218-19
民权运动, 174, 193, 197-98, 201, 211
Clampett, Elly May, 187, 188, 191, 192, 196, 197, 198, 201
Clampett, Jed, 187, 190, 191, 192, 194, 198, 200
Clampetts 一家, 194, 195, 196, 201, 202, 203, 204
家庭关系, 259n. 21
Clark, 警长 Jim, 197
Classification of Mountain Whites(山区白人分类)[Campbell], 44
Clifford Gross’s Texas Cowboys, 97. 另见 Gross, Clifford.
Clinton, Bill (William Jefferson), 11, 214, 215
Clod Hoppers, The, 80
与乡巴佬形象, 124
与罢工, 120
与露天采矿, 203
Colbert, Claudette, 167
冷战与乡巴佬形象, 135-36, 170
Colorado Hillbillies, 97
Colvin Hollow, 弗吉尼亚州, 110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161
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75, 79, 89, 101
非裔美国人角色, 118, 119, 128, 248n. 22
回避争议, 128, 251n. 41
大萧条时期的流行, 126-27, 250n. 38
Connolly, Joe, 124
Connor, 警长 “Bull,” 197
消费文化与乡巴佬形象, 169-70
Cooper, Gary, 156
Cooper, James Fenimore, 21, 118
Cornett, John “Dub,” 224-25
Costello, Lou, 166
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和作用, 73, 75, 241n. 8
替代性标签, 98, 246n. 50
观众的接受度, 79, 89, 91
与黑脸表演(blackface), 74-75, 241n. 9
喜剧传统, 76
与拓荒者传统的联系, 82
音乐人的服装和外表, 77, 79, 80, 81, 84, 87-88, 90, 92, 95, 97
评论家的嘲讽, 84, 89, 90, 91, 99
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影响, 72-73, 89
扩张, 84, 99
民间音乐人对其的蔑视, 91
与大萧条, 89
与”乡巴佬”(hillbilly). 参见 “Hillbilly”
乐器, 79, 82, 99
音乐起源, 72
媒体报道, 75, 76, 78, 84, 86, 87-88, 89
从乡巴佬形象转向牛仔形象, 88, 89, 95-96, 97
歌曲主题, 89
与”白人性”, 74, 76, 82
与大萧条, 92
与乡土化, 78, 79, 80-84
另见 乡村音乐
Coward, Herbert “Cowboy,” 208, 209
Cox, Ronny, 208
“Cracker”(乡巴佬), 17, 43, 211
Craddock, Charles Egbert. 参见 Murfree, Mary Noailles
Crawford, T. C., 36
Crazy Blue Ridge Hillbillies, 92
Crazy Water Crystals, 91
Crenna, Richard, 178
Crichton, Kyle, 75
Crist, Judith, 201
Crockett, David (Davy), 21-22, 23, 232n. 16, 115, 116
Crosby, Bing, 188
Cross, Hugh, 83
Crowther, Bosley, 161
文化”品位层级”的打破, 190, 201
1920年代的文化冲突, 73, 109
文化:民间、大众、流行之间的界限, 221
Cumberland Gap, 肯塔基州, 21
Cumberland Ridge Runners, 82, 182
Cumberland Vendetta, A(坎伯兰仇杀)[Fox, Jr.], 39
Cummings, Bob, 174, 175
Currier and Ives, 26
Daisy Mae Scragg, [125], [131], [132], [133], [135], [188]
Daley, “Blind Billy,” [91]
Damrosch, Walter博士, [243n. 26]
Daniell, George, [92]
Darling, Briscoe, [182]
Darlings乐队, [182]–[83], [184]
美国共和国女儿会, [155]
Davenport, Homer, [49], [50]
Davis, Elmer, [158]
Davis, Jefferson, [197]
Davis, Jimmie, [76]
Davis, Karl, [81], [82], [83]
Davis, S. M.夫人, [43], [236n. 53]
Davis, Rebecca Harding, [30], [31]
《大卫·克罗克特;或确信你是对的,然后勇往直前》[Mayo], [22]
俄亥俄州代顿, [213]
田纳西州代顿, [110]
DeBeck, Billy, [9], [103], [104], [114]–[17], [115], [116], [118], [119], [121]–[24], [135], [148], [152], [154], [251n. 49]
漫画的读者反响, [124]
生平背景, [113]–[14], [248n. 15], [248n. 22]
对作品的评论, [248n. 19]
影响力, [136], [139], [154]
乡巴佬角色的起源, [114]
对乡巴佬刻板印象的戏仿, [122]–[23]
对山区社区的描绘, [122]–[23], [124]
对非裔美国人的描绘, [118]–[19]
方言的使用, [114], [121]–[122], [124]
Decca唱片公司, [74], [86], [95], [97], [98], [99]
Dees, Ashley “Jad,” [88]
《激流四勇士》(小说)[Dickey], [205], [206]–[7]
模糊性, [206]
与电影的对比, [207], [208]–[9]
销量, [209]
作者经历的运用, [207]
《激流四勇士》(电影), [3], [10], [184], [205], [206], [207]–[10], [215], [237n. 8]
白化病班卓琴手场景, [206], [208], [262n. 9]
观众反应, [209]:在佐治亚州, [209]
票房收入, [209]
与小说的对比, [207], [208]–[9]
“激流综合症”, [210], [262n. 14]
对其他电影的影响, [210]–[11]
与南方山区居民的关系, [208]
鸡奸场景, [206], [208]–[9]
“像猪一样尖叫”, [208], [210]
《民主在前进》[Lilienthal], [159]
大萧条, [4]
对普通民众的颂扬, [160], [163]
与乡巴佬形象, [9], [10], [72], [103]–[4], [112], [206]
幽默在此期间的重要性, [126]–[27]
后来以此为背景的节目, [206]
此期间的人口迁移, [175]
底特律, [99], [138], [175], [176], [177], [219]
Dickey, Christopher, [207], [208], [209], [210]
Dickey, James, [205], [206], [208]
参与电影《激流四勇士》的制作, [261n. 6]
对电影的反应, [209]
Dillards乐队。参见Darlings乐队
迪士尼工作室, [164]
Dogpatch USA主题公园, [250n. 33]
《造偶者》[Arnow], [138]
多莉坞主题公园, [215]
Doolin, Luke, [211]
双V运动, [165]
Douglas, Donna, [187], [189], [192], [198]
《在阿肯色》[Hibler], [50]
Dreher, Rod, [224], [225]
Drysdale, Margaret, [196]
Drysdale, Milton, [195]–[96], [197]
Dyer, Richard, [9]
Earle, Steve, [217]
Eaton, Allen H., [249n. 26]
Ebsen, Buddy, [187], [189], [191], [192], [193], [198], [200], [203], [261n. 54]
对《贝弗利山人》的评论, [193]
《蛋与我》[MacDonald], [167], [170]
另见电影条目
Electric Auto-Lite公司, [136]
El Hasa Shrine神庙, [218]
《时尚先生》杂志, [9], [103], [109], [112], [113], [136], [138], [139], [154]
漫画, [106]
创刊, [105]
男性主导的描绘, [106]
销量, [105]
主题, [105], [107]
Ezra K. Hillbilly, [84]
Farber, Manny, [165]
Farber, Stephen, [209]
Faulkner, Sandford上校, [26]
Faulkner, William, [20], [110]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190], [201]
Featherstonhaugh, George, [25]
Ferguson, Patrick(英国少校), [21]
世仇, [35], [36]
电影中的描绘, [58], [62], [142], [143]–[144], [151], [152]–[153], [154], [163]–[64]
Martin-Tolliver世仇, [35]
通俗文学中的描绘, [37], [40], [65]
涉及世仇的电视剧情, [182], [197]
另见Hatfield-McCoy世仇
Fields (Lew)和Weber (Joe), [93]
电影产业,相关公司, [58]。另见Biograph、Republic Pictures、Monogram Studios、迪士尼工作室、派拉蒙工作室、华纳兄弟工作室、环球国际影业
“B级片”的引入, [161]
乡巴佬刻板印象的延续, [143]
迁至好莱坞, [63]
电影, [57]–[58], [59]
观众规模:1922年, [57];1930年代, [161]
与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关注点, [60]
故事片的发展, [63]
其他媒体对乡巴佬形象的影响, [136], [154], [160]
另见山民电影
Filmways电视公司, [189], [191]
Filson, John, [21]
Fisher, Ham, [126]
Fiske, John, [42]
Foley, Clyde “Red,” [81], [83]
民俗节, [120], [249n. 26]
民谣音乐, [82], [91]
Fox Jr., John, [39], [41], [56], [58], [156], [235n. 45]
对乡巴佬形象的影响, [125], [250n. 36]
Foxworthy, Jeff, [6]
会说话的骡子弗朗西斯, [168]
Freleng, Fritz, [163]
Fritzell, Jim, [181]
田纳西州蛙山, [19]
Frost, William Goodell, [43], [65], [236nn]. [46], [48]
Fruit Jar Drinkers乐队, [80]
Furman, Lucy, [147]
弗吉尼亚州加拉克斯, [74]
“李将军号”, [214]
Gentry, Ed, [206], [207], [208], [209]
Gentry, Lucas和Ira, [207]
George Daniell’s Hillbillies乐队, [76]
佐治亚州, [18], [34], [40], [47], [48], [55], [76], [192], [193]
与《激流四勇士》, [206], [207], [209]
与吉米·卡特, [211]
佐治亚州老式小提琴大赛, [76]
Gerstaecker, Frederick, [25]
Giles, Lem, [88]
Gilliland, Henry, [241n. 4]
Gingrich, Arnold, [105], [113]
“金色西部女孩”, [95], [96]
Gish, Anthony, [139]
Goff, Norris, [160]。另见Lum and Abner
Goldstein, Leonard, [167], [168], [170]
Gooch, Abijah, [133]
Good, Millie和Dolly。参见”金色西部女孩”
Goodrich, Frances Louise, [249n. 26]
Google, Barney, [113], [114], [116], [117], [119], [122], [124], [251n. 49]
Gorcey, Leo, [166]
Graham County, North Carolina(北卡罗来纳州格雷厄姆县), [150]
Granny (Daisy Moses), [187], [188], [192], [194], [197], [198], [200], [202]
Grant, Allan, [192]
《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斯坦贝克], [130]–[31], [163]。另见 [乔德一家]
Green, Abel, [90]
Green, Archie, [48], [75]
Green, Douglass, [96]
Greenbaum, Everett, [181]
Greenbrier County, West Virginia(西弗吉尼亚州格林布赖尔县), [237n. 4]
Griffith, Andy, [181], [183]
喜剧表演”那是什么——足球”, [181]
与Li’l Abner的比较, [181]
Griffith, D.W. (David Wark), [58], [59], [61]–[62], [114]
Gross, Clifford, [96]–[97]
Gully Jumpers乐队, [80]
Hammid, Alexander, [159]
Hamner, Jr., Earl, [205]
Handy, W. C., [76]
Hano, Arnold, [196]
Harben, William Nathan, [48]
Harlan County, Kentucky(肯塔基州哈兰县), [120]
Harmon, Roy Lee, [139]
Harney, William Wallace, [30]
Harrington, Michael, [185]
Harris, George Washington, [19], [31], [107], [114], [167]
Harris, Jim, [218]
Hatburn, Luke, [144]
Hatburn家族, [3], [184], [251n. 47]
Hatfield, Johnse, [182]
Hatfield, William Anderson “Devil Anse”(“魔鬼安斯”), [36], [37]–[38], [155]
媒体对其形象的塑造, [37]–[38]
Hatfield-McCoy世仇, [36]–[38], [152], [235n. 40]。
另见 [Hatfield, William Anderson “Devil Anse”]; [McCoy, Randolph “Old Ranel”]
Hathaway, Jane, [195], [196]
Hatton Gap, Arkansas(阿肯色州哈顿峡口), [52]
Hawthorne, Julian, [49]
Hay, George Dewey, [80], [81], [86], [99]
关于”hillbilly”(乡巴佬)一词的评论, [84]–[85]
《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的命名, [243n. 26]
以及乡村表演者的乡土化, [80]
Haynes, Henry。见 [Homer and Jethro]
Hazard, Kentucky(肯塔基州黑泽德), [213], [225]
Hemphill, Paul, [212]
Henning, Paul, [175], [181], [187]–[89], [191], [192], [194], [198], [201], [203]
生平背景, [187]–[88]
对《贝弗利山人》的评论, [193]
努力将角色呈现为真正的山民, [189]
对hillbilly角色的迷恋, [188]
《贝弗利山人》创意的起源, [188]–[89]
Henry, Thomas, [110]
Hepburn, Katherine, [156]
Hergesheimer, Joseph, [143]
Hibler, Charles S., [50]–[51]
Hicks, Granville, [163]
Highland County, Virginia(弗吉尼亚州高地县), [143]
“高地人”, [44]–[45]
Highlands, North Carolina(北卡罗来纳州高地镇), [263n. 26]
Hildreth, Richard, [18]
Hill, Billy, [91]
Hill, George, [146]
Hill Billies乐队, [74], [77], [78], [80], [81], [93], [101], [182]
命名, [78]–[79]
Hillbillies from Mars(来自火星的乡巴佬), [219]
“乡巴佬入侵芝加哥” [Votaw], [176]–[77]
二十世纪早期媒体中的缺失, [57], [64], [69], [238n. 15], [240n. 28]
在乡村音乐中:听众对该词的使用, [79], [98];使用该词的乐队名称, [74], [76], [86], [87]–[89], [243n. 27];表演者对该词的反应, [79], [91]–[92], [99], [101];表演者对该词的使用, [78]–[79], [90], [92], [93], [94]–[95], [98];使用该词的乡村音乐新闻报道, [76], [78], [84], [86], [90], [99];制作人对该词的使用, [79], [82], [84], [87]–[88], [91], [101], [242n. 16];歌曲标题中含有该词, [76], [86], [87], [244n. 29](另见 [“Hillbilly音乐”])
被定义为贬义词, [48], [79], [138], [175], [176]
定义, [49], [51], [55], [191]–[92]
与”redneck”(红脖子)的区别, [6]
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 [49]
早期在电影中的使用, [145], [146]–[47], [153]–[54], [156], [253n. 6]
早期在印刷媒体中的使用, [48], [50]–[51], [55], [57], [64], [176]
该词的地方性使用, [93], [212]
反对使用该词, [69], [91]–[92], [138], [205], [212]–[13], [218]–[19]
该词的起源, [48], [56], [237n. 2]
南方山区人对该词的使用, [48]–[49], [79], [138]–[39], [203]–[4], [219]–[20]
各种拼写方式, [57]
本书中的使用方式, [228n. 1]
《乡巴佬》(The Hillbilly)(文学杂志/年鉴), [67]–[68], [137], [240n. 34]
乡巴佬节日庆典
北卡罗来纳州高地镇, [263n. 26]
肯塔基州派克维尔, [11], [218]–[19]
《豪华乡巴佬》(Hillbilly Deluxe) [Yoakam专辑], [216]
“乡巴佬总部” [网站], [219]
Hillbilly Hellcats(乡巴佬地狱猫乐队), [219]
Hillbilly Holocaust(乡巴佬大屠杀乐队), [219]
模糊性, [3], [6], [48], [49], [64], [77], [94], [118], [134]–[35], [139]–[40], [151], [193], [204], [218]
相关联想:世仇(见 世仇);小提琴音乐, [26], [54], [76], [99], [126], [161], [163], [164], [182];木屋, [26], [27], [51], [52], [68], [82], [103], [104], [120], [148]–[49], [152], [153], [154], [162], [163], [180], [185], [195];长内衣, [107], [108], [167], [174];私酿酒(见 [私酿酒]);神话般的风景, [5], [22], [107], [121], [123], [127], [211];户外厕所, [107], [190], [191], [200], [201], [214];猪, [52], [54], [133], [199], [206], [238n. 8];烟草, [15], [33], [53], [55], [99], [100], [133], [137]
喜剧表现形式, [15]–[16], [32], [54], [62], [76]–[77], [133], [154], [192], [240n. 29]
作为对消费主义社会的批判, [4], [6], [41]–[42], [82], [119]–[20], [163], [180], [193]–[94], [206]
性别关系方面:性别角色的颠倒, [15], [25], [138];父权制, [6], [115]–[16], [117], [147]–[48], [156], [192];女性(见 [乡巴佬女性])
一般特征, [3]–[4], [5], [6]–[7], [19], [39], [103]–[104], [105], [112], [114], [139]–[40], [214]
历史:衰落, [10], [213], [215]–[16];驯化, [170], [173], [191];1930年代对”民间”的颂扬, [141], [162]–[63];起源, [13]–[14];从威胁到喜剧配角的转变, [62]–[63], [64], [141], [151]–[52], [154]
地方性使用, [48]–[49], [67]–[68], [92]–[94], [137], [139], [218]–[19]
作为应对现代性的手段,[48],[94],[169]–[70],[194]
身体特征,[18],[19],[20],[31],[51],[66]:赤脚,[16],[20],[28],[39],[53],[54],[61],[68],[78],[82],[84],[85],[99],[100],[103],[104],[108],[109],[111],[133],[135],[137],[142],[154],[161],[165],[242n. 16];胡须,[18],[23],[27],[37],[39],[49],[50],[51],[61],[62],[68],[84],[92],[93],[99],[100],[103],[104],[133],[137],[154],[161],[191],[199];服装,[218](另见乡村音乐);精神和身体畸形,[110],[111],[134],[175],[208];类猿特征,[110],[129],[130],[134],[135],[183]
与”扮演傻瓜”,[14],[19],[27],[232n. 11]
各方反应:普通观众,[203],[206];媒体评论家,[158],[165];南方山区居民,[138]–[39],[203]–[4],[209]–[10],[212]–[13],[224],[225]
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刻板印象,[138],[165],[203]–[4],[213],[218]–[19],[224]–[25]
作为象征:落后,[7],[17],[107],[156],[194],[207];常识思维,[132],[169],[192],[194]–[95];平等民主,[19],[116],[118],[195];家庭和亲属,[82],[132],[168]–[69],[178],[194],[206],[207];肮脏,[86]–[87],[107],[110],[111],[116]–[18],[133],[154],[167],[176];无知,[7],[25],[90],[96],[181];独立和个人主义,[6],[7],[82],[118];与世隔绝,[82],[91],[107],[132],[147],[149],[159],[161],[195],[206];土地和自然,[6],[94],[101],[114],[132],[179],[195];懒惰,[15],[16],[25],[66],[82],[84],[115],[148],[154],[161];道德纯洁,[128],[132],[194]–[95];反对进步,[36],[67],[156],[159],[179],[181]–[82],[188];拓荒精神,[6],[13],[22],[42],[43],[60],[65],[66],[82],[112],[139],[147];普通民众,[6],[82],[85],[94],[116],[163],[195];贫困,[16],[17],[25],[49],[51],[54],[77],[90],[107],[179],[186];坚韧,[112],[113];野蛮,[133],[134],[142],[183],[206],[207];暴力,[7],[21],[65],[115],[118],[119],[133]–[34],[134],[144]–[45],[149],[157]–[58],[183]–[84],[191]–[92],[210]
与性相关:性与强奸,[148]–[49],[206],[207],[208]–[9];性变态,[7],[52],[110]–[11],[120],[138],[154],[157]–[58],[175],[176],[177],[225],[214];性吸引力,[118],[128],[191];与白人身份(见[白人身份];[“白人他者”])
“乡巴佬音乐”(Hillbilly music),[71],[72],[73]–[74],[76],[84],[86],[91],[103]
标签的模糊性,[71]–[72]
与”种族音乐”的关联,[74],[75]–[76]
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90]
二十世纪末音乐家重新接受该术语,[11],[101],[216]–[18]
1940至1950年代寻找替代标签,[95],[101]
乡巴佬音乐,歌迷杂志,[97]
“乡巴佬红脖子狂暴页面”[网站],[220]
来自皮肯斯县的乡巴佬三人组,[86]
乡巴佬村,[215],[216]
《乡巴佬女人》[卡恩著],[212]
乡巴佬女性,[32],[33],[38],[53],[55],[84],[85],[117],[133],[167]–[70],[178],[194],[212],[248n. 20]
作为美人,[132],[133],[166],[191],[192],[214]
作为苦工,[15],[53],[54],[107],[108],[109],[115]–[16],[138],[147]–[48]
作为多产者,[19],[26],[27],[42],[107],[109],[167],[169],[176],[236n. 48]
作为暴力天性者,[59],[130],[192],[197]
另见[山民电影];乡巴佬形象;[山民形象]
山地民众。见[南方山区居民]
山区人民。见[南方山区居民]
弗吉尼亚州希尔斯维尔,[35]–[36],[65]–[66]
希梅尔斯坦,哈尔,[197]
“与乡巴佬交往”[布拉德利著],[65]–[67]
霍奇(约克郡人的典型形象),[14]
《空谷居民》[谢尔曼和亨利著],[110],[111]
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63],[64]
好莱坞乡巴佬乐队,[86]
霍默与杰斯罗(亨利·海恩斯和肯尼斯·伯恩斯),[101]
胡珀,约翰逊·J.,[18]
胡西尔热门乐队,[87]
霍普,鲍勃,[190]
霍普金斯,阿尔,[77],[78],[80],[81],[86],[92],[93]
霍普金斯,约翰,[77],[78],[80],[81]
阿肯色州霍雷肖,[52]
纽约州霍内尔,[245n. 41]
霍内尔斯维尔乡巴佬乐队,[92],[93],[94],[95]
霍华德,贾斯汀·O.,[20]
休斯,玛丽昂,[52]–[55],[57]
亨德利,D. R.,[16]–[17]
亨廷顿,科利斯,[49],[50]
哈钦森,约瑟芬,[156],[157]
艾德尔森,比尔,[197]
密苏里州独立城,[188]
印第安纳州,[175]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176]
互联网,[219]–[20]
《在田纳西山区》[默弗里著],[30]
美国国税局,[200]
杰克逊,安德鲁,[22]
杰克逊,“莫莉阿姨”,[120]
杰克逊,托马斯,[51],[52]
詹姆斯,福雷斯特,[149],[150]
乔德一家,[131],[178],[179],[194]
《乔·帕卢卡》,[126]
约翰逊,林登·B.,[185],[190]
约翰斯顿,乔赛亚·斯托达德,[43]
《穿越边远地区之旅》[奥姆斯特德著],[24]
贾德母女组合,[217]
卡恩,小E. J.,[127]
卡恩,凯西,[212]
堪萨斯州,[55]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50],[188]
基顿,巴斯特,[62],[152],[153]
家乐氏公司,[199]
肯布尔,爱德华·温瑟,[31]–[32],[32],[33],[39],[234n. 34],[250n. 36]
肯尼迪,约翰·F.,[185],[190],[193]
肯塔基州,[21],[22],[42],[44],[55],[61],[82],[96],[114],[147],[185],[188],[213],[223],[257n. 3]
文学描写,[30],[33],[40],[127],[138]
大众媒体描写,[35],[36],[60],[62],[153],[154],[156],[174]
肯塔基猎头乐队,[217]
肯塔基乡巴佬乐队,[97]
肯塔基漫游者乐队,[96]
凯普哈特,霍勒斯,[236n. 46],[240n. 28]
与《原始之爱》的关联,[147],[150]
凯特尔夫妇,[142],[167],[168]–[70],[189],[194]
在书籍《蛋与我》中,[167]
基尔布赖德,珀西,[167],[168],[169],[170]
Kincaid, Bradley, [91], [240n. 2]
King, Henry, [143]
King, Lewis, [207]
King Features Syndicate, [124], [251n. 41]
国王山战役,南卡罗来纳州, [21], [177]
Kinks乐队, [217]
Kinney, “Shady” Grady, [218]
KMBC(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188]
KMPC(洛杉矶), [87]
Knopfler, Mark, [217]
Knott, Sarah Gertrude, [249n. 26]
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州, [42], [150]
Kouf家族, [93]
三K党, [151], [157]
Kulp, Nancy, [195]
南方山区居民的称谓, [44]–[45], [175]–[76], [225]。另见[“高地人”]; [“乡巴佬”]; [“山区白人”]; “山民”; [“沙丘居民”]
南方贫穷白人的称谓, [5], [43]。另见[“穷白人”]; [“(贫穷)白人垃圾”]; [“红脖子”]
Lair, John, [81]–[84], [83], [85], [138]
为音乐家创造明确的山区形象, [81]–[82]
与”乡巴佬”一词, [82], [84], [85]–[86]
Lasky, Jesse, [148]
Lasswell, Fred, [124]
Lauck, Chester, [160]
劳雷尔(斯坦)和哈迪(奥利弗), [152]
Ledford, Lily May, [81], [84], [85]
Levine, Lawrence, [193]
莱温斯基,莫妮卡, [214]
Lewis, Jerry Lee, [101]
Lewis, Richard Warren, [190]
Lewis, Sinclair, [151]
刘易斯堡,西弗吉尼亚州, [237n. 4]
Light Crust Doughboys乐队, [97]
《小阿布纳》, [3], [9], [76], [103], [113], [124], [125], [129]–[32], [134]–[35], [184], [190], [251n. 49]
与野蛮主题, [133]–[36]
角色, [125], [128], [130], [131], [132], [133], [134]–[36], [188]
与阶级冲突主题, [127], [128], [130]–[31]
情节, [127]
与民粹主义, [130]
另见 [Capp, Al]; [Gooch, Abijah]; [Scragg, Daisy Mae]; [Scraggs一家, Yokum, Li’l Abner]; [Yokum, Mammy]
Lilienthal, David, [159]
林肯,亚伯拉罕, [188]
李普曼,沃尔特, [119]
小石城,阿肯色州, [123], [214]
《王国来的小牧羊人》 [Fox, Jr.], [39]
Lloyd, Harold, [62]
地方色彩运动, [29]–[30], [234n. 30]
Lodge, Henry Cabot, [235n. 45]
伦敦唱片公司, [100]
孤独牛仔, [95]
Longstreet, Augustus B., [18], [31]
Lorentz, Pare, [159]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 [87], [99], [189], [198]
路易斯安那州, [30], [55]
Lovingood, R. S. 牧师, [48]
Lovingood, Sut, [19]–[21], [20], [115], [167], [183]
与其他乡巴佬角色的比较, [195]
Lowizie Smith。见 [Smith, Lowizie]
Lunsford, Bascom Lamar, [91], [249n. 26]
Lynde, Francis, [40]–[41]
《凯特尔夫妇》系列电影(总论), [10], [142], [167], [168]–[69], [188], [190]
吸引力, [168]–[70]
观众群体, [168]
对社会问题的评论, [169]–[70]
商业成功, [168]
MacDonald, Betty, [167]
MacGibbon, Harriet, [196]
Mack, Gus, [88]
MacKaye, Percy, [120], [249n. 24]
MacMurray, Fred, [166], [167]
Macon, Uncle Dave, [75], [76]
Madison, Pete, [93]
内战后”新”杂志, [29]
旅游杂志。见 [旅游杂志]
Main, Marjorie, [166], [167], [169], [170]
Malone, Bill, [72], [96], [98]
Mammy Yokum。见 [Yokum, Mammy]
Mann, David, [219]
Manne, Jack, [111]
Mannes, Leo, [87]
Marlette, Doug, [215]
马克思兄弟, [154]
Maxwell, Edith, [156], [255n. 26]
Maxwell, James, [176]
Maynard, Ghen, [224]
Mayo, Frank, [22]
McChesney, Fay, [93]
McCoy, Grampa Amos, [178], [179], [180], [192]
McCoy, Randolph “老兰尼尔”, [36]
McCoy, Roseanna, [182]
McEnery, Dave “红河戴夫”, [95]
McKinney, Bill, [208], [209]
McMichen, Clayton, [97]
Medlock, Lewis, [206], [207], [208], [209]
梅纳,阿肯色州, [160]
门肯,H. L.(亨利·路易斯), [110], [119], [151]
Mercer, H. C., [28]
水星唱片公司, [100]
梅雷迪斯,詹姆斯, [193]
Meunich, Jean(Linda Parker,“遮阳帽女孩”), [82], [83]
Meyer和Mike。见 [Fields (Lew)和Weber (Joe)]
南方山区居民的迁徙, [164], [175], [257n. 3]
相关担忧, [10], [138], [174], [175], [176]–[77]
相关笑话, [176]
相关通俗文学, [138], [185]
Mike Hillman和他的拉丁乡巴佬乐队, [219]
Miles, Emma Beth, [236n. 46], [240n. 28]
Miles, Lyle, [93]
Miller, Homer “Slim”, [81], [82], [83]
Milsap, Ronnie, [217]
明戈县,西弗吉尼亚州, [38]
Minow, Newton, [190], [201]
Miracle, Silas, [149]
Mirandy。见 [Bauersfield, Marjorie]
传教士对南方贫穷白人的反应, [13], [41], [43]–[44], [151]
密西西比州, [56]
密苏里州, [21], [22], [25], [47], [50], [55], [90]
以该州为背景的电影, [162]
奥扎克山区, [139], [182], [215]
Mitchum, Robert, [211]
Mix, Tom, [142]
Monogram制片厂, [161]
Montana, Patsy(Ruby Blevins), [96]
“真实的私酿者” [Lynde], [40]–[41]
在漫画和卡通中, [103], [107], [115], [122], [125]
在乡村音乐中, [76], [84], [91], [99]
历史, [34]
在山民电影中, [58], [59], [62], [142], [143], [151], [152], [153], [154], [164], [165], [207], [211]
在其他文化形式中, [199], [215], [218]
在通俗文学中, [39], [40], [55], [64], [112], [207]
在电视中, [182], [188], [194], [195], [197], [199], [200], [214]
Moonves, Leslie, [225]
Morris, Howard, [183], [184]
Morris, Lucille, [139]
Morriss, Mack, [204]
《电影世界》, [63]
Moses, Daisy。见 [奶奶]
山地男孩乐队, [9], [103], [104], [105], [107]–[13], [108], [109], [111], [113], [136], [137], [138]
角色作为人类韧性的象征, [112]
与其他《时尚先生》漫画的比较, [106]
角色的道德堕落, [110]–[11]
孤立主题, [106], [107]
另见 [Webb, Paul]
山城,田纳西州, [77]
山地舞蹈与民俗节, [91], [249n. 26]
激浪汽水(Mountain Dew), [199], [200], [201], [202], [260n. 51]
周边商品, [219]
另见 [乡巴佬威利]
词源, [44]–[45]
本书中的用法, [228n. 1]
山地人电影,57-58,61,62-63,141
观众反应。参见观众
制作数量的变化,63,142-43
角色服装,61-62,153,161
刻板印象乡巴佬的首次出现,146
无声电影数量,57,238注16
受欢迎程度,59
喜剧比例上升,160
被视为无争议性,154-55,156
从阿巴拉契亚到欧扎克地区背景的转变,160
主题,58,61,142-43,156,162-63(另见乡巴佬形象)
作为边疆拓荒者,21-22,31
对山地人刻板印象的挑战,37,40,41,51,64,65-66
与世仇(参见世仇)
与地理隔离,30,43,66
媒体对南方山区居民的歪曲,65-66,120-21,150
与忧郁症,30,33
与私酿酒。参见私酿酒
乡巴佬刻板印象之前的描绘,21,23,24-25,61,152,153
与进步改革者,41-42,43,56
与新教,41,42,43-44,236注53
与苏格兰血统,35,44
与社会退化,42,110-11
与工业化的支持者/反对者,56
作为威胁,34,36,38-39,40,142,143
另见乡巴佬形象
阿肯色州山地之家,238注15
“山地夜鹰”[贝内特],76-77
“山地白人”,43-44,45
北卡罗来纳州艾里山,181
肯塔基州弗农山,81
海伦·芒迪,149,150
弗兰克·默多克,22
玛丽·诺艾尔·默弗里,30,58,114,250注36
小说的受欢迎程度,234注32
汤姆·默里,87
纳什维尔,80,101,150
托马斯·纳斯特,63
全国广播协会,190
国家审查委员会与电影审查,60
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155
国籍起源法,151
全国妇女党,156
本土主义,151
NBC(全国广播公司),189
格蒂·内维尔斯,138
新政计划,96,120,160,249注25。另见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新英格兰,9,13,14,30,42
新奥尔良,150
纽约,5,28,92
纽约市,14
《夜幕降临坎伯兰》[考迪尔],185
约翰·雅各布·奈尔斯,91
密苏里州诺埃尔,188
凯瑟琳·诺兰,178
查尔斯·芬顿·诺兰,25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15
北卡罗来纳州,15,64,67,78,90,121,223
文学作品中的引用,23,25,40,44,147
媒体背景设定,114,123
俄亥俄州诺伍德,219
威尔伯·李·“老爹”·奥丹尼尔与乡巴佬男孩乐队,97,245注46
霍华德·奥杜姆,138
经济机会办公室,185
战争信息办公室,158
俄亥俄州,44,175,176
沃尔特·奥基夫,89
奥克唱片公司,73,74,78,86,95,101
俄克拉荷马州,131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24-25
《慢车穿越阿肯色》[杰克逊],51,52
罗斯·奥尼尔,238注15
奥兹·奥斯本,223
《另一个美国》[哈灵顿],185
奥特的伐木工乐队,92,94,95
奥迪恩斯乡巴佬男孩乐队,86
“我们当代的祖先”[弗罗斯特],43
《我们的南方高地人》[凯普哈特],147,150,240注28
弗恩·牛津,211
欧扎克乡巴佬乐队,243注27
欧扎克地区,5,22,55,60,62,65,88,120,121,127,139,156,174,176,187,191
喜剧联想,240注29
地理定义,229注2
幽默作家,160
威廉·佩利,203,205
派拉蒙电影公司,148,151,156,161
琳达·帕克。参见让·穆尼希
多莉·帕顿,215
詹姆斯·柯克·保尔丁,22
塞浦里安·保莱特,87,88
PCA(制片法典管理局),155
拉尔夫·西尔维斯特·皮尔,73,74,75,241注4
对乡村音乐家的态度,74
与小提琴手约翰·卡森,73-74,241注5
与乡巴佬乐队,74,78-79,81
表演者的乡土化,78,79,242注16
宾夕法尼亚州,34
百事公司,199
卡尔·帕金斯,101
杰克·皮克福德,145,146
玛丽·皮克福德,58,145
田纳西州鸽子锻造镇,215
肯塔基州派克维尔,11,225
欧文和诺曼·平卡斯,180
派尼克斯止咳糖浆,84,85
乡巴佬戏剧,166,256注37
J·H·波尔赫穆斯牧师,41
“(穷)白人垃圾”,90,110,147,224
波普艺术,201
人民阵线,163
民粹党,56
“克雷永港”。参见大卫·亨特·斯特罗瑟
威廉·T·波特,19
弗吉尼亚州庞德,156
贫困被描绘为”山区文化”的一部分,179。另见乡巴佬形象
草原漫步者乐队,96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01
查理·普莱德,241注8
进步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56,60
《大烟山的先知》[默弗里],30
丹佛·派尔,182,214
《奇怪的女人》[弗曼],147
阿德琳·奎因,148
佐治亚州拉本县,207,210
与非裔美国人的比较,43,49,51,53,60,118,119,165,176,177,197,198,224
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比较,15,16,17,25,35-36,60,119,233注24,256注38
与墨西哥人和拉丁裔的比较,17,60,176
与其他非白人的比较,60,155
与种族和民族刻板印象的联系,63,130,220
另见非裔美国人;白人性;“白人他者”
“种族”唱片,73,241注4
广播电台和销售的增长,73
铁路
对乡村音乐歌曲的影响,73,243注26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224
牧场男孩乐队,86
万斯·伦道夫,57,138,139,249注26
马丁·拉萨霍夫,189
《真正的麦考伊一家》,10,174,177,178,178-81,186,187,188,189
characters(角色),[178],[179],[180]:与真正的山区居民区分开来,[180]
与《愤怒的葡萄》比较,[178]–[179]
收视率,[181]
另见 [McCoy, Grampa (Amos)];“Aunt” Hassie;McCoy, Kate;Little Luke;McCoy, Luke
唱片公司,早期”乡村音乐”厂牌,[74],[75],[86]
Rector, John,[77],[81],[81]
Redden, Billy,[208],[262n. 9]
Redmond, Donna,[212]
“Redneck”(乡巴佬),[6],[56],[211],[212]
在乡村音乐标题中,[211]
Reed, Lydia,[178]
地方主义,[119]–[21],[159]
Renfro Valley Boys乐队,[82]
Republic Pictures,[101]
Reynolds, Burt,[209],[213]
Rice, Glen,[87]–[88]
Rickman, Frank,[210]
Riopelli, Edwin,[93]
Ritz Brothers乐队,[154],[155]
Robertson, Eck,[95],[241n. 4]
Robinson, Carson J.,[95]
Rodgers, Jimmie,[74],[75],[89],[95]
Rogers议员Hal,[264n. 6]
Rogers, Will,[127]
Roosevelt, Franklin,[96],[157]
Roosevelt, Theodore,[235n. 45]
Roper, Daniel,[206]
Rowan, Carl,[212]
乡村题材电视节目,[173],[186],[187],[199]
观众,[202],[261n. 57]
停播,[203]
主导1960年代电视,[199],[260n. 49]
收视率下降,[202]
抵消贫困形象,[185]
反映社会关切,[173]–[74]
与电视行业,[181],[205]–[6]
Russell, Johnny,[211]
Ryan, Irene,[187],[189],[191],[192],[198],[200]
评论,[190],[193],[261n. 54]
Sacco和Vanzetti,[151]
Sadie Hawkins Day(萨迪·霍金斯日),[125],[137]–[38]。另见 [Capp, Al]
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1904年),[51]
Sandburg, Carl,[163]
“Sand-hillers”(沙丘居民),[16]
Satherly, Arthur “Uncle Art”,[89],[91],[101]
《星期六晚邮报》,[192]
Save Our Kentucky,[203]
Schoolcraft, Henry Rowe,[25]
Schuyler, Virginia,[205]
斯科普斯”猴子”审判,[110]
Scraggs一家,[3],[126],[133],[134],[184]
《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分界线秘史》[Byrd],[15],[16],[25],[32],[230n. 3],[231n. 4]
Seldes, Gilbert,[191]
塞尔玛,阿拉巴马州,[197]
Semple, Ellen Church,[31],[42],[134],[236n. 46]
参议院青少年犯罪小组委员会,[189]
Setters, Jilson。见 [Daley, “Blind Billy”]
Shay, Dorothy,[166]
Shayon, Robert Lewis,[196]
Sheppard, Muriel Earley,[249n. 26]
Sherman, Mandell,[110]
Shinn, Everett,[106]
Shriner的”Hillbilly Degree”,[218]
Sierra Hillbillies,[219]
Silver Dollar City,密苏里州,[201]
Simms, William Gilmore,[18]
Simon, Al,[189],[191]
Skillet Lickers乐队,[76],[97],[101]
“慢车”,[50],[51]
Smart, Alfred,[112]
Smart, David,[112],[113]
Smith, Arthur,[90]
Smith, Lowizie,[115],[116],[117],[122],[248n. 20]
Smith, Mamie,[241n. 4]
Smith, Snuffy,[3],[9],[101],[114],[115],[116],[117],[118],[119],[122],[123],[124],[248n. 19],[251n. 49]
与其他hillbilly(乡巴佬)角色比较,[195]
Sniffle, Ransy,[18]
Snuffy Smith。见 [Barney Google and Snuffy Smith]。
Solan, Joseph,[93]
南卡罗来纳州,[16],[21]
《南阿巴拉契亚地区——调查报告》[Ford编],[185]
Southern Culture on the Skids乐队,[217]
南部山区居民,
社会运动,[212]–[13],[218]–[19]
与工业转型,[56],[65]–[66]
与向中西部和西部的迁移(见 [Migration])
作为本书使用的术语,[228n. 1]
另见 [Hillbilly image];[Mountaineer Image]
西南幽默作家,[18]
《时代精神》,[19],[26]
Sprague, Carl T.,[95]
斯普林菲尔德,密苏里州,[160]
Stand-By,[84]
Stand Up and Cheer,[244n. 32]
Steele, Harry,[84],[86],[90]
Steinbeck, John,[130],[163]
Stokes, Lowe,[242n. 13]
Stoneman, Ernest “Pop”,[79]
Stowe, Harriet Beecher,[18]
“一片奇异的土地和一群奇特的人”[Harney],[30]
Stratton, Howard “Dirty Ear”,[218]
Strother, David Hunter,[22]–[24]
Stuart, Jesse,[112],[247n. 12]
Stuart, Marty,[101],[217]
Stuart, Uncle Am,[77]
Suggs, Simon,[18]
《Sut Lovingood:一个”天生蠢货”讲的故事》[Harris],[19],[20],[107],[114],[167]
Tanner, Gid,[76]
Taylor, Hartford “Harty” Connecticut,[81],[82],[83]
Taylor警长Andy,[181],[182],[183],[197]
尼尔森收视率的准确性,[198]
关于文化功能的争论,[173],[189],[190],[201],[259n. 25]
逃避现实的情景喜剧,[201],[260n. 53]
hillbilly(乡巴佬)形象,[174]–[75],[257n. 2]
关于南部山区的新闻节目,[173],[185]
“巨大荒原”批评,[190]
另见 [Andy Griffith Show, The];[Beverly Hillbillies, The];Bob Cummings Show;The Dukes of Hazzard, The;[Real McCoys, The];[Rural-based television programs]
田纳西州,[19],[21],[22],[25],[44],[64],[66],[82],[90],[93],[121],[147],[204],[223]
文学参考,[23],[30],[40]
在大众媒体中,[158]
德克萨斯州,[22]
纺织厂,罢工,[124]
“那些乡巴佬身上有金子”[Crichton],[75]–[76]
Thomas, Jean,[91],[249n. 26]
Thompson, Lovell,[118]
Thorpe, Archie,[93]
Thorpe, Thomas Bangs,[25]
《阿肯色三年》[Hughes],[52]–[55],[57]
Tindall, George,[109]
Tin Pan Alley(锡盘巷),[72],[84],[90]
《烟草路》[Caldwell],[188]
Torrence, Ernest,[144],[145]
Tourneur, Maurice,[38],[63]
《孤松小径》[Fox, Jr.],[39]
旅游杂志,[171],[256n. 44]
Trippe, Bobby,[206],[207]
Tubb, Ernest,[99],[100],[101]
TVA(田纳西河谷管理局),[96],[120],[158],[159]
Twain, Mark,[19]
Ullmann, Davis,[120]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125]
Universal-International Pictures,[167],[168]
Universal Studios。见 [Universal-International Pictures]
密西西比大学,[193]
城市阿巴拉契亚委员会,[213]
瓦利,鲁迪,[90]
范布伦,阿肯色州,[160]
瓦达曼,詹姆斯,[56]
胜利唱片公司,[74],[241n. 4],[242n. 10]
越南战争,[201]
文森特,乔治,[40]
弗吉尼亚州,[15],[21],[25],[35],[44],[65]–[66],[78],[114],[158],[213],[223]
文学参考,[23],[31],[40],[42],[110],[111]
以该地为背景的流行媒体,[38],[142],[206]
沃托,阿尔伯特,[176]–[77],[178]
沃勒,阿尔蒂娜,[36],[235n. 40]
华纳,查尔斯·达德利,[30],[33],[40]
华纳兄弟制片厂,[156],[158],[207]
反贫困战争与乡巴佬形象,[8],[171],[185]–[86],[199],[202]
沃什伯恩,爱德华,[26]
华盛顿州,[5]
奥林匹克山脉,[167]
韦弗兄弟埃尔维里(弗兰克、莱昂和琼·韦弗),[160],[161],[162],[163],[164],[250n. 36]
韦布夫人,安迪,[208]
韦布,保罗,[9],[103],[104],[106],[107],[108],[109],[111],[113],[114],[118],[119],[121],[136],[188],[251n. 49]
生平背景,[105],[247n. 3]
影响,[133],[136],[137],[138],[139],[148],[154],[155],[161]
乡巴佬角色的起源,[105]
与《时尚先生》杂志的关系,[112]–[13]
《山地男孩》吸引力的衰退,[112]–[13]
威德,坦布尔,[96]
西弗吉尼亚州,[23],[25],[48]–[49],[139],[181],[223],[224]
事件,[36],[96],[185],[257n. 3]
文学参考,[31]
以该地为背景的流行媒体,[142],[143],[178],[180],[219]
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总统初选(1960年),[184]–[85]
惠勒,伯特,[152],[153]
1794年”威士忌叛乱”,[34]
白人性,[7],[8],[13],[17],[42]
与山民和乡巴佬形象的关系,[59]–[60],[118],[132],[185],[197]–[98]
“白人他者”
定义,[4],[5]
与山民和乡巴佬形象的关系,[17],[35]–[36],[44],[61],[76],[128],[129],[165]
“白人垃圾”。参见[“(贫穷)白人垃圾”]
沃尔夫,理查德,[191],[193]
怀尔兹牧师,J. T.,[41]
威廉姆斯,汉克,[75]
威廉姆森,J.W.(杰里·韦恩),[38],[57],[112],[256n. 38]
威利乡巴佬,[199],[200],[201]
威尔逊,查尔斯·莫罗,[121],[249n. 26]
威尔逊,埃德蒙,[232n. 12]
威尔逊牧师,塞缪尔,[42],[44]
温克尔曼,迈克尔,[178]
云斯顿香烟,[199]
“南方的冬天”[斯特罗瑟],[22]–[24]
怀斯曼,露露·贝尔,[92]
威斯特,欧文,[235n. 45]
WLS(芝加哥),[80]
沃尔夫,查尔斯,[78]
沃尔夫,托马斯,[110]
伍德,鲍勃,[202],[203]
伍德,格兰特,[163],[192]
伍德赫尔,弗洛伊德,[93]
伍德赫尔老式大师乐队,[92]
伍德梅森,查尔斯,[16]
伍尔西,罗伯特,[152],[15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乡巴佬形象,[145],[147],[15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乡巴佬形象,[107],[112],[116],[133],[135],[136],[138],[141]–[42],[158],[164],[165],[171],[251n. 49]
WRC(华盛顿特区),[79]
WSB(亚特兰大),[73],[76]
WSM(纳什维尔),[80],[85]
扬基”类型”,[13],[14],[19]
约卡姆,德怀特,[101],[216]–[17]
约库姆,小阿布纳,[125],[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88],[192],[251n. 49]
约库姆,老妈,[125],[129],[130],[131],[132],[188]
约克,阿尔文,[156]
约瑟夫,丹尼尔·布恩,[137],[252n. 51]
扎努克,达里尔,[154]